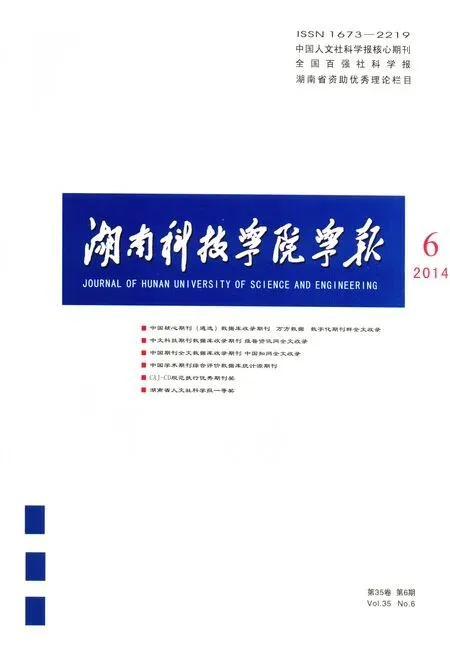“知变化之道者”的三种视角——由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的易学观点切入
[台湾]王汝华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通识教育中心,台湾 台南 71082)
一 前 言
《易经》一书译为“The Book of Changes”,正点出《易经》是一本索探宇宙人生变化,注重观变、习变、应变的书;而《周易》的“易”字也揭示其内里所蕴含的简易、变易、不易等三层义涵;至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则透过:“《易》以道化”点出《易》言天地阴阳变化的特质;又《周易》经传更透过49个“变”字呈现出丰富的变化之道,其中仅《系辞传》即有33个,如强调在“变动不居”中“唯变所适”的法则;透过“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强调变动神化的效能;并称扬“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此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亦不外乎变;天地絪缊、万物化醇,更不脱变化一环。再者《周易》又通过43个“生”字,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乃至乾坤之“大生”、“广生”等,来呈现天地宇宙的变动日新、终始反复及开物成务,而凡此亦莫不脱变化一途。由此看来,《易经》确乎是一本窥探天地之机、深究生化之理、强调创进精神、展现变化妙道的著作。
至于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与马一浮(1883-1967)则被并誉为“现代儒家三圣”①如: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上),载《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第9页。除“现代儒家三圣”外,另又有“儒家三圣”、“新儒家的三圣”、“新儒家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三圣”、“现代儒家三圣”等称号。,就梁言,有“行动的儒者”及“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等封誉②景海峰、徐业明:《梁漱溟评传》,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贺麟:《梁漱溟与东西文化文化问题》,见梁培宽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就熊言,徐复观赞其“熊先生的生命,即是中国文化活生生地长城”③徐复观:《悼念熊十力先生》,《徐复观文录选粹》,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340页。。196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称扬其为“儒学、佛学和西方哲学三方面的调和中,最具独创性的综合者”;就马言,贺麟誉之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曾昭旭赞其为“传统之儒之最后典型”④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台北:台湾时代书局,1974年版,第12页;曾昭旭:《六十年来之理学》绪言,见程发轫主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四册,第561页。。三人订交半世纪,在当代儒学的开展上互有切磋与激荡,也各有开展与发挥,此外三人的学术资源丰沛且多元,此中对于《易经》各有领受与阐扬,并援之为建立其新儒学理论的重要奥援,而三者对《易经》内蕴所揭变化之道,亦各有体悟与辟拓,本文即由此视角切入,一索三者如何在《易经》言“变”的活水源头上,开展出专属于个人风格及见识的论述要点。
二 梁漱溟的观“变”要义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形而上学,就其问题及方法而言,均迥异于西方或印度,而其内涵则主要体现于《易经》一书①梁漱溟:《东西文化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8页:“此刻我们来讲中国这一套形而上学的大意。中国这一套东西,大约都具于《周易》。”,并由之而成为一切大小高低学术的根本思想。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实际内容则“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绝非静体的”②《东西文化哲学》,第145页。,由于注重变化上抽象的道理,因此鲜少过问具体的问题,也鲜少采纳静的或呆板的观念。例如阴阳乾坤仅表示意味而不是实物,“就是具体的东西如‘潜龙’‘牝马’之类,到他手里也都成了抽象的意味。”③同前注,第146页。变动的、抽象的、主观的,正是中国形上学的主要特色,基立于此,梁遂开展出以下具个人特色的思想内涵:
(一)调和及生生的宇宙观
如上所言,梁认为宇宙万物的本质乃在于“变化”,舍此不断变化的历程外,别无所谓的本体,而其更在《易经》重视变易、强调变化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其调和的宇宙观,梁曰:“《易经》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可以说这所有许多的不同,无论如何不同,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论的中心意思,就是‘调和’”、“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④同前注,第148页。。梁漱溟认为,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宇宙观,呈现出对宇宙变化流行的深刻洞见,生命之流不断生发,毫无止息停歇之际,而在宇宙动态的变化流行中,或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凡所变化结果终归于调和,因此不断变动、调和、折衷,遂成为唯一的迁变法则,梁漱溟也由此衍申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相关见地。⑤同前注,第70页。此外梁漱溟更举《易》卦以言,认为64卦的每一卦均表示某种程度的不调和,并以此来象征宇宙的不调和,如《乾》初九:“潜龙,勿用”,当阳伏藏在下时即以“潜龙”示之,在此意味或处境下当谨守“勿用”的原则,如此即可达臻调和之境。另一例举王船山讲《乾卦》时,有《坤卦》隐于其后以佐辅其调和观,⑥《东西文化哲学》,第151页:“还有我彷佛记得王船山讲这《乾卦》说,有一定全《坤卦》隐于其后,颇为别家所不及,就算是善于讲调和的。”梁所称指的船山观点,即是乾坤并建以及十二位阴阳向背、半隐半现之说。其次,梁漱溟透过变化流转的历程观,进而提揭其宇宙间无歇息的生生之道。他强调以一“生”字即可代表儒家的道理,又说:“孔子……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⑦《东西文化哲学》,第152页。并举《系辞下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系辞上传》“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等,以颂赞宇宙间确乎满溢着盎然生意。他并再三突出“生”字的观念,强调“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⑧同前注,第152-153页。。点出宇宙的生命本性即是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究实说来,其生生之说仍不脱其变化的历程观。至于其纳归于孔家的思想要义,强调宇宙的本体是生命,其思想资源除来自《易经》生生观、《论语》及《中庸》、宋儒“天理流行”、“万物生化”以及泰州学派的乐生主义外,也嫁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柏视生命为世界的唯一实体,生命在时间中永远向前变化,此即是所谓“绵延”,不仅生命是一种变化,宇宙间的一切均是一种绵延,梁漱溟衔接通合了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与绵延概念,借此来阐说中国哲学的变易特点,并由此通会、创造出其生命本体论。
(二)直觉的认识方法
如上所申,梁漱溟认为宇宙的本体并非固定的静体,生命本性是无歇息的向上奋进,对于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本体,梁提出其形上学的认识方法论——直觉,认为唯有透过直观方式始能掌握此种浑融的流动的形上概念,因此梁漱溟言:“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辨,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绝对。直觉所得自不能不用语音文字表出来,然一纳入理智的形式即全不对,所以讲形而上学要用流动的观念,不要用明晰固定的概念。”⑨同前注,第101页。又曰:“我们要用这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是用什么作用呢?这就是直觉。我们要认识这种抽象的意味或倾向,完全要用直觉去体会玩味,才能得到所谓‘阴’‘阳’‘乾’‘坤’”。⑩同前注,第146页。梁所谓直觉的认识方法是一种遇事随感而应、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认识形式,即是一种求对求善的本能,即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天理,即是一种自然流行的法则,更是孔子的仁、《易经》的生、《中庸》的率性、阳明与心斋的良知、也是聂双江的“归寂以通天下之感”、宋儒的无欲……此外梁并活化《系辞上传》的“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义,强调“寂——像是顶平静而默默生息的样子”、“感——最敏锐而易感且很强”,①《东西文化哲学》,第161页。以此转说此敏锐直觉——亦即是仁的特性。梁眼中的直觉与理智的私心打量、计较利弊得失、费心计算安排等彼此对反,他屡屡强调唯有沿循着直觉之路,才能走出对的路,才能真正认识生命本体,才能使理智自然退伏。
大抵说来,梁漱溟的直觉是一广泛融摄、取源中西,乃至不断迁变的观念,它既是形上学的方法,也是获取知识的三种工具——现量、比量、非量(即直觉)之一,并是心理方面的作用之一,亦具道德实践的功能,乃至为一种生活态度。在1921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它是与理智对立的求善本能,也是人的生命主宰、价值之源,一种认识宇宙生命本体的顿悟方法,自1949年出版《中国文化要义》起,直觉则改以“理性”称之,将人类心理由前期的“本能”、“理智”二分法,改为“本能”、“理智”、“理性”三分法,将原归属于“本能”的人类无私情感改纳入“理性”之中,及至1986年出版《人心与人生》,更强化理性观(即原直觉)的圆熟发展,并扣紧吾心与宇宙本体来加以发挥。不管如何,梁漱溟透过直觉为主轴来理解儒家思想,并倾力发挥,此等改造使其赢得“中国思想界近一二十年来,第一个倡直觉说最有力的人”的称号。②贺麟:《宋儒的思想方法》,《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1991年版,第四章,第87页。
(三)不认定等人生态度
以发皇新孔学为毕生职志的梁漱溟,在标举《周易》的形而上学调和精神,及直觉的认识方法的基础上,也进而提出其新孔学的人生态度。在《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强调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孔家的形而上学——《周易》,并阐扬“生生”之理,以及孔家的不认定、无表示、刚、一任直觉、仁、性善、不计较利害、生活之乐等人生态度。其后在1923-1924年出版的《孔家思想史》中提出“仁”、“乐”、“讷言敏行”、“看自己”、“看当下”、“反宗教”、“毋意、必、固、我”、“非功利”、“非刑罚”、“礼乐”、“孝悌”、“不迁怒 不贰过”、“天命”等十三种孔子人生态度。再后透过《中国文化要义》的出版,强调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以道德代宗教”的特色。例如就“不认定”一项而言,梁举《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等,说明此种不计算、一任直觉的生活态度;至于“不计较利害的生活”,亦即是在直觉作主下的作仁生活,呈现出油然而发的盎然生趣,与算账的生活迥别;至于“刚”的态度即是无私欲、自觉的主动性,也切合于《乾·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的刚健精神。大抵而言,其所提出的人生态度,系上承直觉的认识方法,亦绾合于其所提出的调和与生生的宇宙观,而凡此均统摄于其强调变化的形上学中,并多有资用且改造于《周易》者。
三 熊十力的言“变”要点
熊十力时称《易经》为《变经》,至于其掌握《易经》以言变者,所在遍是,姑由以下三面向略窥其要:
(一)由其学术著作的显出看
熊十力毕生著作多本诸《易》、系乎《易》、归宗于《易》,如经学系列诸作:《读经示要》探历代易家,阐其尊生、彰有、健动、率性四大易学要旨,并说解各卦大义;《原儒》提撮《大易》要义,原为《大易广传》的缩减代本,其中《原外王》强调倡科学理论,莫盛于《易》,《原内圣》探天人不二、心物不二,并及孔子人生论、宇宙论,发《大易》奥蕴,《序文》赞:“《易》大传以知物、备物、成物、化裁变通乎万物,为大道所由济。”③熊十力:《原儒序》,《原儒》,台北:明文书局,1988年版,第2页。《乾坤衍·辨伪》独详于《易》,《广义》则衍扩《乾》《坤》二《彖》,书前自序语及称名之故:“余学《易》而识乾坤,用功在于衍也,故以名吾书”④熊十力:《自序》,《乾坤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2页。,则轴系于《易》,昭然可见。至于体用系列作品也时阐易理,如《新唯识论》言翕辟、乾坤、心物,不脱《易》变之理,而马一浮更于文言本序文中赞其“深于知化,长于语变”;⑤马浮:《序》,《新唯识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体用论》中明指其学宗主于《易》;《明心篇》阐述实体具复杂性、体用不二、心物未可分割,自谓此三原理均取源于《易》,则其资用及发阐于《易》者,实所在皆是。再者其著作中亦遍在对《易》变动及生生之理的显扬,如屡引《乾·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生化的威势,如此迅疾而毫无所滞,天德刚健,人亦当如此;诠解《乾》九四:“或跃在渊”时强调生命进程并非恒常而绝对,发展时必有上下进退的曲折进程,但总体以观,仍上进不已;引《坤·彖》:“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强调坤亦有健德;引《无妄·彖》:“动而健”明本体的流行;引《系辞上传》“日新之谓盛德”强调人体天行之健,而富创造力,故能日新不守其故,并屡成大业;又时引《随》、《鼎》、《革》三卦,以明随时革故取新之义;援《大有卦》彰显实有之义;引《观卦》观生,呈生生不竭义。此外对于《易》言天道“刚健中正”、“变动不居”、“生生”的健德,推之于人事的“开物成务”、“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等均有发挥。
(二)由其学术体系的要蕴观
熊十力学术体大用宏,若专就其体用不二哲学言:首先,强调中学归极见体、吾学贵在见体的熊十力,在其对本体的诸多名义中,以“恒转”、“能变”等词,道出本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能生且无始无终、变动不已的万物根源;以“乾元”一词来强调生生不息的真体。在《新唯识论》中并提出本体六义,其中“本体是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法尔清净本然”,以及“若说本体是不变易的,便已涵着变易了,若说本体是变易的,便已涵着不变易了”①《转变章》,《新唯识论》,第313、314页。及至《体用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9页更而言本体四义,仍强调“本体显为无穷无尽的大用,应说是变易的。然大用流行毕竟不曾改用其本体固有生生、健动,乃至种种德性,应说是不变易的。”两点,已赅见本体具空寂、真常、刚健、无滞碍、能生化,且系变动不居的特性。若就其言“功用”观:熊十力强调本体空寂而刚健,因而恒是生生不已、化化不停,即依实体的变动不居、现作万行,而名之为功用或作用。至于“用”一词,也称名为“势用”、“变动”、“胜能”、“生生化化流行不息之机”、“气”等,均重在指陈大用流行剎剎势速、其势能无有穷竭。就用而言,并非单纯势能,用不孤起,必有二面,或翕辟、或乾坤、或心物、或精神物质,若专就“翕辟成变”言:翕辟代表宇宙生成变化的二大势用,翕是一种积极收凝的摄聚势用,具成形及下坠的趋势,在翕势兴起的同时,别有一种使本体恒如其性,不为物化、向上、伸张、猛进、刚健不物化的动势兴起,此即是辟。二者一体二面,彼此相须、同时存在,辟施翕受、辟主翕从,对立而融和、相反而相成,宇宙的运动发展即在此翕辟的相互作用下展开。若就“乾坤互含”言,乾为乾元流行的主力,具有刚健、生生、照明、升进、恒畅诸性,坤为乾元流行的翕敛,具柔顺、迷闇、闭塞、下坠诸性,乾以健统坤、坤以顺承乾,乾坤彼此相须、彼此互反以成变,终臻保合太和之境。至于其全副心神所开展而出的“体用不二”说,除托寄于孔子名义下外,并屡言一己来自《大易》的触悟与影响,②《广义》,《乾坤衍》,第343页:“孔子作《周易》,创明体用不二之论。”《明变》,《体用论》,第59页:“余之宇宙论,主体用不二,盖由不敢茍同于佛法,乃返而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积渐启悟,遂归宗乎《大易》也。”又指出“易”之“不易”,指宇宙基本原理本是不易;“易”之“变易”,指宇宙为刚健不息,时时变易,而宇宙的终极真实即是新新不已的大化流行,一切现象均是此终极真实的具现;他如《系辞传》的“显诸仁,藏诸用”以及“神无方而易无体”等,均已发体用不二之蕴。③参《佛法下》,《体用论》,第216、217、220、238页。而其体用不二内涵则强调即用显体、于用识体;摄体归用、体用可分而不可分;即用即体、即体即用;证体知用;即工夫即本体;作用见性等。此外更由宇宙论中体用不二的关系,衍为治化论的道器不二;人生论的天人不二;乃至理欲不二、理气不二、动静不二、成己成物不二、知行不二等,架构成一套理论严谨、内容完整的不二系统观。
(三)由其学术资源的运用言
以“六经注我”自成一家之学的熊十力,在其卓绝的哲学慧识背后,仍有其广征博采的学术资源,除根基于孔子、阳明、船山等儒学外,并融摄佛学、取舍老庄、参稽诸子、取益时贤、兼取西学。以其资源广浩,姑择其间一二以窥其要:首先,就其对船山资源的汲摄言:熊十力非仅深入其间,提出“尊生”、“健动”、“明有”、“率性”四大纲领综赅船山思想要义,④参《读经示要》卷二,第481、482页。并汲援为一己的思想核轴,熊曰:“吾平生之学,穷探大乘,而通之于《易》。尊生而不可溺寂,彰有而不可耽空,健动而不可颓废,率性而无事绝欲。此《新唯识论》所以有作,而实根柢《大易》以出也。(…王船山《易外传》,颇得此旨。然其言散见,学者或不知综其纲要。)”⑤《读经示要》,卷三,第605页。专就此四大纲领中的“尊生”言,由《系辞上传》的“生生之谓易”,到船山于归隐地题名“观生居”,阐扬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到熊十力深玩生生之理,由体及用,强调乾坤相资的生化势能;强调翕辟变动为一永不止息的生化过程;强调心性以生生刚健之德斡运于物,终能趋向保合太和,完成大生广生的德业;又强调宇宙只是一团生机,天的好生之德落于人即是仁,因此其素重求仁之学,如何呈露仁体,流行无间,不使私欲起而违碍,即是熊再三强调的要点。沿循儒家《易经》及船山的传统,致力于生生哲学的表彰,强调尊生而不可溺寂,一方面彰显宇宙为一生机洋溢、鸢飞鱼跃的世界,一方面也强调了人参赞天地的责任。另就四大纲领的“健动”言:“生”的创化作用,须在“变”、“动”的过程中始能完成,因此由《易》的“唯变所适”,到船山强调宇宙的本体“太虚”、“太极”,其动是不息不滞的,又提出健动不息的世界实有论,至熊十力强调本体是一能生且无始无终变动不已的万物根源,而熊言天道,则喜借《无妄·彖》的“动而健”来说明本体的流行,由于变动不居、于穆不已,因此才能生生而不穷竭、不留滞。要之,船山确乎是熊十力生命中的千古同参,熊十力依循《大易》及船山的轨迹,由形上到形下,由宇宙论至人生论,着力于其生生及健动等哲学要道的表彰。其次,以其对佛学思想的改造言:熊十力曾历经长时期的探佛研佛历程,由其34岁时所辑的《心书》中,见其对佛初有涉猎,然多依傍他家;及至1920起赴南京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问习佛法,为恪守师说期;1926年后《唯识学概论》第二种版本印出后,开启其改造佛学、摄佛入儒期;1945《读经示要》出,专主于儒,亦可称为出佛成熟期。在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用论》等作品中,重心多置于空有二宗,其以“破相显性”概括空宗哲学要点,认为空宗对性体寂静领会甚深,然观空同时又流于耽空、归寂同时又流于滞寂,不悟生生之盛、化化之妙,因此其屡强调空宗与己的差别,主在于“真儒即是诸法实性”和“真如显现为一切法”的不同。对于有宗他基本上接受唯识宗“万法唯识”的理论,然对于有宗的“唯识非境”,熊则强调境非离心而独在,亦即“离心无境”,熊主张要透过本心去究极真实,探究本体的活动,终以回归自家本心为首要。要之,熊十力屡屡诟病空有二宗之谈体遗用,不悟盛化之神而拘泥寂灭,有求体废用、耽空滞寂之病,因乃改造而提出在现实中识本体、本体即呈现于现实界中的体用不二论。就人生问题言,佛家各派强调超脱生死苦海、悟入涅盘寂静,熊则强调天道的“健”与“仁”,及人生的自强不懈;就知识论言,熊认为佛家过任冥思、失之空幻,主张重哲学而不废科学、言智而不偏弃知识、论性智而不舍量智、重德性之知而不忽闻见之知。
四 马一浮的申“变”要旨
六艺之教是马一浮的为学纲领,其认同《诗》、《书》、《礼》、《乐》、《易》、《春秋》中温柔敦厚、疏通知远、恭俭庄敬、广博易良、絜静精微、属辞比事等古来教义,并认肯六艺对道德与智识的全幅提升,强调此为孔子之教,亦是二千余年的学术渊本,而在六艺中又特为突显《易》的地位,因言:“《易》为六艺之原,亦为六艺之归”①《序说》,《观象卮言》,《复性书院讲录》第六卷,《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册,第422页。,以下亦由三个面向观察其如何在易学基础上申变言变:
(一)由其诠解《周易》经传的内涵观
马一浮诠释《周易》经传,无专门著作,《马一浮集》中偶见散篇涉易学课题者,如《易教上》、《易教下》、《太极图说赘言》等,仅《复性书院讲录》第六卷中的《观象卮言》专论易学课题,最能具现其观点。至于其阐《易》方式则多灵活穿插于各文中,常融铸全《易》,兼摄佛老,旁及宋明诸儒,并浑融六艺要义以见指撝。虽然其论《易》文字有限,但相关的诠解、推扩及体悟,却又时时散见于全集,如《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续编》、《濠上杂著》、《蠲戏斋杂著》、《序跋书启》、《书札》内均时见提点,且诠说或推阐范围几乎涵括全经各卦,并时分论或援引《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杂卦传》等以佐其说。至于其说《易》的方式亦称多端,或简释卦名要义;或直接说解卦爻辞文义、段义、句义、词义、字义;或各爻逐次申说;或多卦、两卦或多词、双词并列比观;或申言易的体例;或援历代易学家之说来加以辅成;或引经籍襄助说解;或持佛家禅意以增广易义;或例举生活经验与自然现象来辅助说明;或以史事证之,或持以个人经验,或采用譬喻、或以人事说明等,堪称灵活多变。若专就其释解《周易》经传要句言,语涉“变”意者尤多,例举之,如其通过《系辞传》:“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以及“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等,而申言趋吉避凶之道,强调知进退变化的重要,以及“易简”为吉、险阻为凶之理。次如对《艮卦》“止”义的厘析与推扩,由“寂灭义”说“息妄”,由“不迁义”义说“显真”,强调动静不失其时。②详参《说止》,《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集》第一册,第85-89页。又如其诠《系辞上传》:“生生之谓易”,强调“生”即变化之义,“变化故非常,无穷故非断”③《太极图说赘言》,《濠上杂著》初集,《马一浮集》第一册,第718页。,而所谓变即是化之渐,而化即是变之成,透过乾道变化,因能各正性命,又强调《易》之言生,非幻而是实理,此与佛氏的缘生有别,佛是缘生,生则有灭,无其自体之性。另如针对《系辞上传》“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强调“一阖一辟,即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也。然阴阳又有动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不是往而不返,静不是息而有间”,④同前注,第716页。在此动静无端、大化不停下,完成宇宙间大生广生之业。再如其通过《系辞上传》第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强调要能知进退、知变化、知失得,因为《易》分别藉“吉凶悔吝”与“变化刚柔”,以象人事的“失得忧虞”及天地阴阳的“昼夜进退”。天地间的刚柔变化无一息间歇;人世间的吉凶悔吝,也彼此相贯无一刻息停,悔则自凶而转趋吉,吝则自吉而转趋凶;至于进退与昼夜亦变动不居、循环反复。无论天道或人事,均以“变”为常道。他如释《系辞上·传》“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强调此系强调应通过六爻刚柔的变化,定出行事的适应准则,而马一浮则在此基础上更着力申说人心即是变的根源,心变则境变:“‘观变’云者,不必定指卦变。人心一动,变即从此始矣。有变而之吉,有变而之凶,其象亦见于卦。……然吉凶之道,皆由自致。”①《序说》,《观象卮言》,《马一浮集》第一册,第423页。卦象爻象虽示吉凶,而吉凶则肇源于心的变动,象为自心之影的反射,因此观象即是观心,马一浮并由此强调应由察心、定心、正心进入,才是应变良策。凡上随举,可见其诠解《周易》经传,多有紧扣变化之道而发者,另马一浮更在《易教上》援《易》文近十处,以见《易》法象天地,反映出自然与人生界变动、屡迁的不二本质,而《易教下》对于如何在迁流中见不迁、变易中见不易亦多所发挥。②参《复性书院讲录》第二卷,《马一浮集》第一册,第182-190页。
(二)由其论述常变的要义言
1939年9月15日,马一浮于其所主持的复性书院举行开讲礼,立“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为学规,并印发《复性书院开讲日示诸生》文,该文起首即发其对常变之道的领会,文曰:“天下之道,常变而已。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易·恒》之《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雷风动荡是变也,‘立不易方’是恒也。事殊曰变,理一曰常。处变之时,不失其常道,斯乃酬酢万变而无为,动静以时而常定。故曰:吉凶之道,‘贞胜者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不患不能御变,患不能知常”、“随时变易以从道,斯知变矣;夭寿不贰以俟命,斯知常矣”③同前注,第一卷,第103、104、105页。。以上系强调《易》本长于变,然而要在通过变以显常,“常”为本、“变”为迹;力愿在于己者是常、事物之从缘者是变;应变固然重要,知常尤为要务。例如其时正值逢夷狄侵凌的蹇难之际而设置书院,此为变,然而书院仍持守义理经术的讲授,此为常;也因此其引《恒·大象》的“君子以立不易方”,强调物之变固然无穷,而吾人之心当恒一以立,藉此与学子共勉互励,期其持敬秉诚以进德修业,务求尽己之性,如此方能合吻于常道。要之,世间事物固然酬酢万变,妙用无方,然为学处世仍应有所树立,穷理尽性、明伦察物,恒而能变、变中有恒,应坚持正确的恒久之道,卓然不可移易。观上重点,可见其确善于守常知变,将常变之道融通并运用于教育、生活、学术、德性之中。
(三)由其推扩三易的内涵言
三易之义可源溯《系辞下·传》,郑玄抉发之并定名“易简”、“变易”、“ 不易”。善于观变察变的马一浮,除对三易之理有透澈慧悟外,对《易》以变易为名、以不易为理、以简易为用,并有多元且深入的推衍,期藉兹彰显《大易》的精神。④详参陆宝千:《马一浮之易学——儒学新体系之基础》,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1995年6月,第11-16页;另李永亮:《略论马一浮视野中的三易之义》,载《周易研究》2012年第1期,第9-14页则专就马一浮如何持三易之义说解心性论与功夫论发挥。以下姑举例以观其如何灵活运用及说阐三易之理:如其在《泰和宜山会语·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文中强调理是不易、事是变易,于事中见理即是变易;同书《理气》文中强调理是不易、气是变易,而全气是理、全理是气、理气不二、气中见理、以理率气即是简易;同书《知能》文中强调性为不易、修为变易,而性修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则是简易之教;又如《复性书院讲录·易教下》文,将《易》教融摄于佛氏圆顿教义的体、相、用三大,强调不易是体大、变易为相大、简易则相当于用大;同文又及佛之“不生不灭”为不易、“生灭”为变义、“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为简易;同书《释三才》文就《孝经》:“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强调“经”为不易、“义”为变易、“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为简易;同文再申天地人三才关系,引《孝经》“父子之道天‘性’也”,明天道之不易,“君臣之‘义’也”,明地道之有变易,而知父子之道即是君臣之义、知天性即是人道,则又属归变易;同文又以理法界为不易、理事无碍法界为变易、事法界为简易,合言之则为事事无碍法界,并以之诠释三才关系。同书《约旨 卦始 本象》文强调理为不易、象为变易,见此则简易之用可得;又《尔雅台答问续编·示张德钧》文强调性为不易、情为变易、心统性情则是简易。……另马于《蠲戏斋杂著》中收有《三易略义》一文,通纳《易》、《中庸》、《太极图说》、《通书》等典籍,并兼摄易佛,唯仅提示要目,如言涅盘德为不易、解脱德为变易、般若德为简易;法身为不易、应身为变易、报身为简易;位为不易、气为变易、德为简易;“天命之谓性”为不易、“修道之谓教”为变易、“率性之谓道”为简易;“无极而太极”为不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为变易、“阴阳一太极,太极本无极”为简易。……要之,其灵活融通的全面开展了三易的丰富内涵,乃至持三易之理释解生生之义、诠释君子之道、以变易不易说继善与成性、以易简说“贞一”及“险”“阻”、将三易通会礼乐、以三易说《中庸》之“高明”、“博厚”、融入《孝经》解说、持之以说解《太极图》、持之以说解佛学之心物及缘生、会说华严的三观等,其心性论与功夫论,援三易以持说者,可谓俯拾皆是。
五 结 语
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同样身为当代新儒家的开疆健将,三者均以发皇中学为鹄的;均融摄佛学、西学及儒学;并同时标举新时代孔学;亦均重宋明诸子。梁漱溟拓荒于文化哲学,以世界三期说闻名;熊十力着力于体用哲学,致力于传统儒学的理论改造;马一浮以儒家六艺论为旨归,以道德实践为核轴。一践履笃实、一规模宏大、一义理精纯,且对于易学均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及开展,而对于《易》为言变之书的本质,尤有不同面向的体悟与发挥,三者均能将《易》的言变精神带入其学术体系中,进行有机的结合,由宇宙论、认识论、心性论到人生论,多呈现一体交融的特色。分言之,梁漱溟援《易》变内涵,而落实于其调和及生生的宇宙观、直觉的方法论及不认定、刚等人生态度的阐扬。熊十力学术归宗于《易》,并掌握其变化之道,由体及用,由乾元本体至翕辟成变、乾坤互含,乃至体用不二、心物不二,无不圆融立说,而其更援船山尊生、彰有、健动、率性四纲,立为一己学说之本,既消化亦批判空有二宗,在在见其对此课题的深刻彰显。至于马一浮的易学发阐,则如矫健游龙,灵活布立于其各著作中,而微收束于其《观象巵言》一书,透过其释解《易》经传要句,得窥其观变的格局;由其论常变要义,得见其知常守变的视野;由其推扩三易之理,得见其由心性论到功夫论之一端,融儒佛乃至各家为一体之梗概。三者相较,梁为行动儒者,著作中对《易》理发抒有限,多见诸《东西文化哲学》;熊归本于《易》,开展与跳跃最多;马浑融于《易》,融铸与冶炼最深。然三者对于《易》言变化之道,确各有体悟与发挥,此中梁居立先锋,为理论基石及发展方向跨出关键性的步伐;熊灵活运用、嘎然独造出体用不二等学术体系,并传承后学,影响匪浅;马则兼容并蓄、融会通贯、圆熟开展其常变思想,并成为传统色彩趋浓的现代醇儒。倘泯除彼此界限与分别,则得观作为现代儒学鼎足而立的三大重镇,梁熊马三人的学术体系中,均具现援《易》说变之迹,后二者尤丰,成为饶具特色、殊值玩索的一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