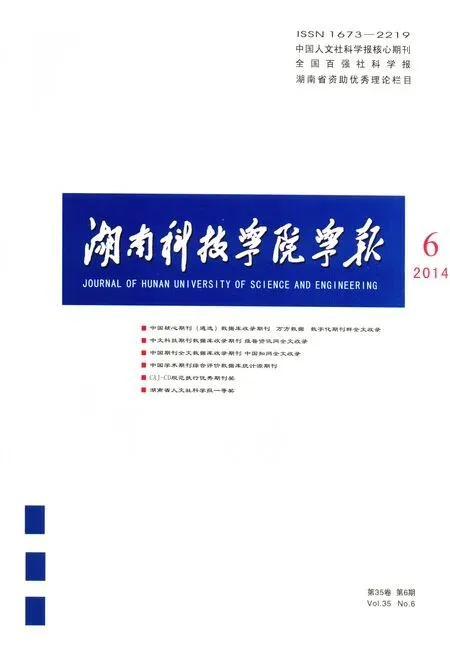临川“二陈”生平著述考辨
周 婷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临川“二陈”生平著述考辨
周 婷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宋代家族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大家族研究,但一些小作家、小家族却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如“临川二陈”,陈郁、陈世崇父子,鲜有问津。该文将对其生平、著述、交游、文学观念等进行论述,其中对陈世崇入元改号为名,补余嘉锡《辩证》考证、补录与其交游诗人。
陈郁;陈世崇;交游;诗论;《藏一话腴》;《随隐漫录》
一 陈氏父子生平考
陈郁,《宋史》无传,字仲文,号藏一,今江西临川人,“理宗朝,充辑熙殿应制。景定间,充东宫讲堂掌书兼撰述”[1]卷六十八。据《崇仁县志》“人物传” [2]第七篇·第一章 人物传载 载:“陈郁(1184-1275),字仲文,号藏一,巴山镇人。以文学优异受理宗知遇,命他记天竺华严阁。特旨以布衣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兼撰述。德佑元年(1275)卒,年92岁。”巴山镇,据《县志》载,即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巴山镇。《四库全书总目》[3]卷一百二十一·子部·三十一云:“宋陈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隐漫录》中。”通检《随隐漫录》中有关其记载,“藏一”之号,卷之二云:“先君号藏一,盖取坡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陈氏父子均为布衣,后以诗闻达于朝廷,《漫录》云:“先君会天下诗盟于通都,随隐才十二三,诸先生以孺子学诗可教而教以诗”,“庚申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犀韶部头,陈盻儿捧牙板歌‘寻寻觅觅’句,上曰:‘愁闷之词,非所宜听。’顾太子曰:‘可令陈藏一,撰一即景快活《声声慢》。’”“庚申八月”即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陈郁时76岁,诗文已然风靡于宫阁。藏一乃布衣,未经科举,后因诗入仕途,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八·子部九有《临川陈氏族谱》,其谓“谱前载有元至大二年旴江周端礼所撰《故宫讲陈公随隐先生行状》”,云:“父藏一,故宋随龙忠翊郎、辑熙殿应制、东宫讲堂说书兼两宫撰述备咨问”、 “甲子十月绍陵践祚,父子俱预附依淳熙十年等第,推恩补承信郎,仍赐随龙系御。咸淳初后受玉册,御笔除皇城司检法。丙寅赋乐府长短句,往往含讥讽之意,由是权奸嫉之。”盖指因《雪词》讥贾似道,故妒之。“令中书缴其稠叠。公遂奉亲归故里。于是藏一公住临川,不复作出山想。”因而陈郁因诗祸而避世不出,其子补阙。“癸酉,公再赴部申述前恩,转承信郎,补阁门寄班。至明年秋,遂别都门。又明年藏一公捐世。”癸酉年,即宋度宗朝,公元1273年,陈郁卒当在1275年。
陈世崇,《宋诗纪事》[1]卷七十六云:“陈世崇,字伯仁,崇仁人。原注云一作“临川”。据《行状》,实则家住抚州崇仁县。世崇随父入宫禁,“仍充东宫讲堂说书,兼两宫撰述。后仕皇城司检法。贾似道忌之,遂归于乡。入元著《随隐漫录》,多述宋季事。景定癸亥明禋庆成,储皇亚献,藏一公袖公十诗贺太子,除东宫讲堂掌书,兼椒殿掌笺,借紫赐带,年已十八矣。”又卷之三载:“景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东宫掌书,吟社贺诗数十仅记五首。”“景定癸亥”即景定四年,1263年,当知世崇入宫在此年,“景定癸亥”即宋理宗景定四年,即公元1263年,可知世崇生于1245年。《行状》[4]卷十八·子部九又云:“及所著《漫录》,乃效藏一公取旧号为名,与之游者皆曰‘随隐先生’。 至大元年十二月卒,年四十六。”世崇于 “至大元年”卒,即元武宗1308年。对于世崇之名号,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6]史部`政书类`卷三十二·官僚三载:“宋陈郁,字仲文,号藏一,宋季官尚书。其子晦,入元著《随隠漫录》,云‘先君号藏一,盖取坡诗“唯有王城最堪隠,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凡遇诏词皆称藏一。’初以为晦避父名,故改书号,非诏本文也。后阅刘埙《水云村藁》有题‘度皇在东宫时,御札云“令旨付藏一,所有陈世崇(字伯仁)诗文稿都好,……”四月五日辰初札付陈藏一。’据此则东宫已称其号,意诏词亦尔也。”然《四库全书总目》[3]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谓:“《随隠漫录》五卷,旧本题宋临川陈随隐撰,盖后人以书中自称随隐而称。陈郁为先君,知为临川陈姓,故题此名,实则随隠非名也。”又云:“藏一为郁字,则其子当即世崇证,以书中所记与此批一一吻合知随隐即世崇号也。”余嘉锡先生《辩证》驳《四库》“随隐”非世崇入元后名一说。但余先生谓“沈嘉辙《南宋杂事诗》、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卷首引用书目,于《随隐漫录》下均题作陈晦,未详其故,疑别有所据也”,盖以之周氏之说为故。
二 父子著述、交游
藏一诗词及著述,今存《全宋诗》中诗近一百首,《全宋词》录词四首,《四库全书》收《藏一话腴》4卷。其诗集早已散佚,今可见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九十《陈藏一后集序》云:“陈藏一抚人也,以诗文遭际先皇帝获事……携诗文过余,谓‘前集已得西山阙二大老为序,此后集也幸续序之’。”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八·子部云:“藏一《话腴》、《内编》二卷、《外编》二卷,旧抄本。……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法度,而风月梦怪、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四库全书总目》[3]卷一百二十一·子部·三十一谓:“《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是书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记南北宋杂事闲及诗话,亦或自抒议论。”
世崇诗文今存极少,于《全宋诗》收录9首。黄震曾为其诗集作序,《黄氏日钞》卷九十《陈藏一后集序》云:“陈藏一以诗文际遇先皇帝事阙,今宠烨然及归老故乡依然一布衣。余尝阙其人之贤过相如远矣。藏一有子克绍阙隠,亦以诗来求余为序。”[5]子部·儒家类708册所著《随隐漫录》,《行状》谓“十二卷”,据嵇璜《续文献通考》、《续通志》、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等皆云“陳世崇《随隐漫录》五卷”。《四库全书总目》[3]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云:“《随隠漫录》五卷,其书多记同时人诗话而于南宋故事,言之尤详……颇有史传所未及者,他所记诗话杂事亦多可采”、“尤非他说部所及也”,肯定了其价值。
陈氏父子均为布衣,其交游多见于世崇《随隐漫录》中,《漫录》卷之三曾云“先君会天下诗盟于通都”, 又云“景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东宫掌书,吟社贺诗数十仅记五首”,可知当时以陈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唱和文人与一定规模的诗社,由其闻达之后,很自然得便成为了诗社的中心。《漫录》录其唱和诗人十二人,陈世崇随父入东宫,钱舜选、吕三余、柳桂孙、刘彦朝、吴石翁、俞氏(号菊窗)、杜汝能,皆作诗歌“贺陈随隐以布衣除东宫掌书”,其诗大都表现出江湖游士文人对于一朝闻达天子脚的钦羡。待其受忌归隐,“丙寅来归江西名胜又赠诗词”,有周济川(号埜舟)、张彝(号溪居)、黄力叙(号梅堂)作《赠陈随隐归江西》。黄鹏飞(字桂隐)“送余游庐山云天下庐山第一奇”作诗《送陈随隐游庐山》。《漫录》卷三载:“壬申秋,留西湖半载,吴松壑大友饯行。”宋度宗咸淳五年己巳,即公元1296年,世崇归杭,留居半载,诗社友人饯行唱和,吴大有饯行之作《饯陈随隐归临川》:“我昔见君方成童,长吉才华惊炬公。人间科第不屑就,直使声名闻九重。乃翁引上凝华殿,子虚不待他人荐……今日重来发长吁,忍看清平破草庐。尽拈书籍向人卖,归买田园供荷锄。乃翁八十齿发落,倚门待儿斜日薄……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穷达一场春梦。”
从诗中可以看出吴大有与陈氏父子感情甚笃,交往时间甚长,对于父子的遭际和落魄的生活境况——“尽拈书籍向人卖,归买田园供荷锄”,更是惺惺相惜。陈郁诗歌中不乏唱和,《忆钱春塘》“识面论心已半生,买山无计得同盟。行藏为是关天理,会聚因难遂客怀,月户评春花影澹,风廊逃暑竹声清。安舲何日来城角,细举前吟为再赓”、《赠勉周济川》“坐窗长记别时愁,欲讯平安尚未由。客袂重来惊日久,义怀高甚薄云浮。论心句好能令喜,到骨贫深不足忧。更向吟边策勋业,江湖近日欠清流”、《送诗友归西湖》等文人之间的诗歌唱和。又据民国陈思《白石道人年谱》[7]史部·传记类37册:“陈藏一曰:‘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而自高远居苕溪上,与白石洞天为邻。’潘德久字曰‘白石道人’,梦窗词《三部乐·赋姜石帚渔隐》,晚年又号石帚……。’”姜夔《白石道人詩集》卷上录其号来源,“余居苕溪上,与白石洞天为邻,潘德久字予曰‘白石道人’。”又于卷下载白石与潘德久同作《明妃》诗,故可知潘德久与姜夔间有来往,文英谓姜夔晚号“石帚”亦有可考处。姜石帚即姜夔,藏一与石帚当时有来往,且尝作诗《姜石帚贻书寄诗谢》,其谓“酬恩别有男儿事,它日逢君仔细论”。“男儿事”,见于唐李颀诗句“男儿事长征,生作幽燕客” 可知二人不仅有诗歌往来,同为布衣的二人,在当时的国家境况之下,亦发出了一介匹夫之担当。藏一与吴文英亦有诗词往来,《漫录》卷之二谓陈郁藏一之号取苏东坡之句,盖吴文英“为度夷则商犯无射宫腔,制此赠之”。
三 诗歌理论及其创作
江西诗风在南宋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其余风不减,但很多大家诸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姜夔、严羽等都曾受其影响,出入江西诗风,地处江西的陈氏父子当然也不免,善化用典故,且有晚唐体之余味。父子二人诗歌理论主要见于其诗话《藏一话腴》、《随隐漫录》,因世崇仅存诗9首,故以藏一诗论之。
(一)常以字句论诗,注重锻字炼句
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痩”之句天下称之。余爱赵彦若《剪彩花》诗云“花随红意发,叶就绿情新”,“绿情红意”似尤胜于李云。(《藏一话腴》甲集卷下)
唐人诗工于下生字:“‘走月逆行云’、‘芙蓉抱香死’、‘笠卸 晩峰阴’、‘山雨慢琴弦’、松凉夏健人’、‘绿竹助秋声’、‘岁月换红颜’、‘石磴扫春云’、‘画角赴边愁’、‘远帆 开浦烟’、‘ 踈雨滴梧桐’,字字稳帖不觉”。(《随隐漫录》卷之一)
藏一之诗,《漫录》卷之一曾记“西山真先生点先君集中警句如‘辟戸夜通月’、‘掬泉朝饮星’……‘莫看王侯面,失脚恐为名利人’,千古留芳惟好句一时得……跋曰:‘学充而意广,气大而体不偏。用力于先圣之书。’漫塘刘先生曰:‘观其文词赡旨,远为诗深于运思,使人嘉叹不足。’紫巗潘先生曰:‘出入于江西晚唐之间,而不堕于刻与率者也。’”今品其诗,大致如此,如《苦吟》:“水驿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闭门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闭门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自是想到了无己的“闭门觅句”,文思之艰辛,一句“分付梅花自主张”,却由搔首苦思一下子见到户外的月光照在点点梅花,“分付”二字算是琢磨锻炼,各自流光熠熠,诗人心中也是各自忖度、自有主张,顿时豁然开朗。又如《上林归鸦》:“夕阳鸦背斂残红,万点飞归傍帝宫”之“敛”字、《赵园看白牡丹》:“雨艳寒轻清入骨”、“几欲宝酥煎洛蕊”之“雨艳”、“寒轻”、“煎”等等,均可看出其对字句的锤炼,不失晚唐体遗风。
(二)注重诗歌的含蓄委婉,讲求韵味
李文山群玉《吟鹧鸪》诗,世惟以“屈曲崎岖”、“钩 辀格磔”一联称,不知文山用工正在第五第六句,云:“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但咏其鸣之时与地,鹧鸪明矣。其《失鹤》诗亦然,“清海蓬壶远,秋风碧落深”,隐然失鹤之意,所谓吟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是也。 (《藏一话腴》甲集卷上)
陈郁论诗,讲求诗歌含蓄婉转,追求韵味之旨。“所谓吟诗必此诗”“此”即“隐然”之意。其诗歌也大致如此,《东园书所见》:“娉婷游女步东园,曲径相逢一少年。不肯比肩花下过,含羞却立海棠边。”将少女的娇羞描写地很具韵味,时二人擦肩,少女定垂目低头,藏笑海棠之间,此中滋味,别是一番,且诗歌别致精巧,细节生动婉转。又《石湖归隐》:“人与西风结约来,芙蓉花气扑吟杯。曲塘好处都行遍,带得一身秋色回。”尤其最后一句“带得一身秋色回”,将诗歌的余味细细焖了出来,纵然处处观赏都不够,仿佛能将秋色带回仔细回味,秋的美景一转再转,更是无穷。
(三)强调巧妙化典、用事切题
太白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江南李后主曰“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略加融点已觉精彩,至寇莱公则谓“愁情不断如春水”,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
诗中用全书句固有此格须是十分着题方佳,如坡诗云:‘君特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盖就题引用极是切当。近有赋《多景楼》者曰:‘逝者如斯未 甞甞,后之视昔亦犹今’,于多景乎何干……。(《藏一话腴》甲集卷上)
藏一公诗歌还算平白晓畅,但用典举事之处都贴切,《赋薛侯》云:“齿坚食肉何曾老,骑马身轻飞一鸟”,反用辛弃疾“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之典,化用杜甫《送蔡都尉》一诗中的“身轻一鸟过”之句,对薛侯的赞叹,十分形象贴切。《琵琶亭》:“二叹浔阳送客翁,忍将吾道等秋蓬。茕然商妇千呼至,贵其监州一笑同。力学本为明德计,能文只是立言工。琶琵亭下悉情远,付与长江写不穷。”诗前两联则是直接用白居易《琵琶行》之事,诗人即景生情,咏怀畅叙。又《藏一话腴·乙集卷上》谓:“永乐城陷独王湛曲真,夜缒以出,真持木为兵且走,且敌前陷大泽中,顾其旁有马而白,暂腾上驰去,五鼔达米脂城,因以得脫,真名其马为‘天赐白’,蔡天启得其事於西人邀余同赋。”藏一诗云:
君不见书生镌羌勒兵入,羌来薄城束缚急。……睚椎杂宝涂箭创,心折骨惊如昨日。……。样舟不渡谢亭长,有何面目归江东。将军偶生名已弱,铁花暗涩龙文锷。
谢亭,即谢公亭,《李诗选注》卷十二云:“谢公亭,谢眺范云同游处。谢公离别处,风景每生愁。……此李白之咏谢公亭也,言谢公之亭者,乃谢眺与范云离别之处也”。后来谢亭便成为送别的典型代表,又直接用项羽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之典,全诗将仓皇出逃的惊恐、壮志未酬的不甘、英雄末路的悲壮凝练地表现了出来。
(四)注重诗歌创作中形神的把握和艺术手法
写照非画科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者也……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 必写其心……形虽似何益,故曰‘写心惟难。夫善论写心者,当观其人,必胸次广识鉴高,讨论博。……唐摩诘,诗人也,前辈谓其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其与苔矶同。一志趣欤。故曰:“写照非画科比,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者,良有以也。”(《藏一话腴》乙集卷下)
藏一公强调“形神”之间的关系,“写照”之所以不同于“画图”,乃是通过字句描述出来的事物,很难与原貌相符,也无法区别于相同的其他事物,更难得其神韵。唯有得其神韵,方可区别于它事物,这需要诗人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和感悟能力,如同王摩诘之诗,画图感极强,乃是抓住了事物的线条、声音、空间距离等各种因素,从而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世崇亦推崇诗歌动静结合、融情与景、情景交融、言不尽意之创作技巧,方可得《诗经》之余风。
临川二陈虽不是大家,今考之父子二人生平、交游、诗歌创作,及诗歌理论,亦有可取之处,且诗话也保存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展现了南宋末年的诗坛一角也有一定的功用。
[1]厉鹗.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江西崇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崇仁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上海:中华书局,1980.
[5]纪昀,等.四库全书[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上海书店编辑部.丛书集成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1994.
[8]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I206
A
1673-2219(2014)06-0061-03
2014-03-01
周婷(1988-),女,四川乐山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