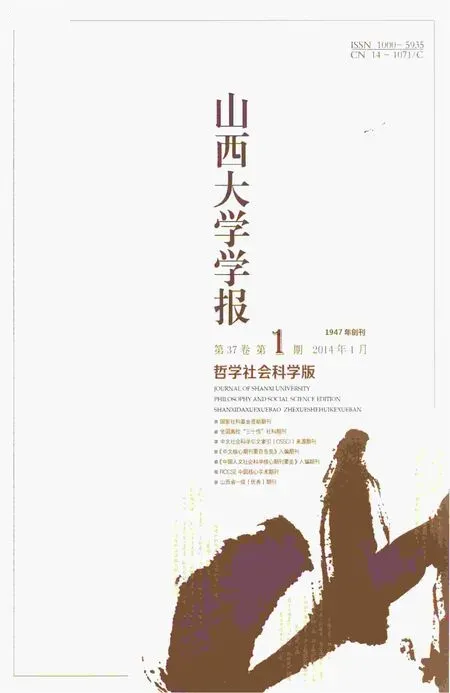海外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写作①
[德]顾 彬
(1.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2.波恩大学,德国波恩 53113)
我们现在的文学世界很奇怪:好像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文学。诗歌在边缘化,话剧不存在,散文也不存在;短篇小说卖不出去,中篇小说市场不好。无论是美国、德国、中国,都是这样。
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些好的小说,但有的到底是长篇还是中篇小说仍然值得争论。另外一些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对我个人而言不是“高度”的白酒,恐怕有点像“黄酒”——我不喝低度的黄酒,对我的阅读刺激不大。
今天的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所以会更加注重扩大文化影响力,这也是很自然和应该的事。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状况,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复杂和艰难的。我的学生刘江凯在波恩大学留学期间,经常和我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他的许多观点与我并不一致,但这样的交流更有意思。他在博士论文《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请我写了序)中提出了一些有意思也可以说是大胆的观点,值得思考:比如他认为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仍然属于中国文学,所以应该把“海外接受”纳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论是现代或者当代)的写作视野里。他认为这种海外视角将会从材料、方法、写作理论模式、结论等方面对现有文学史写作产生影响,也可能出现原来不曾注意的新问题,等等。[1]那么海外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写作状况如何呢?也许我下面的讨论会和刘江凯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形成一种对话。
一 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的翻译差别
我在北京有机会跟国内国外的作家、诗人讨论一些诗歌和翻译的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美国诗人,他老在中国找美国或者说英语国家的当代文学。他告诉我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位美国诗人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美国、英国当代文学,也不感兴趣。那些在世作者的作品没有人看,很少被介绍或者翻译。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敢确定。因为你们更热爱美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不了解我们德国,或者德语国家的当代文学是正常的。
那么中国当代文学或者说诗歌在德国如何呢?王家新是北京一个很好的诗人,人民大学的教授,他老帮我了解中国当代诗歌,也帮我在德语国家出版中国当代诗人的诗选。我在奥地利出了他的诗集,除了这个诗集以外,我还翻译了不少他的诗。好像在首都师范大学讨论中国当代诗歌翻译的问题时,他突然说了几句让我觉得很奇怪的话,他说:他1992年到伦敦以后,对所有的译者非常失望,到现在还是这样。而我翻译出版了他的书,还有不少诗,那他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来得及具体了解。但我估计他谈的不是我或者德语国家,可能是美国、英国或英语国家。如果从美国来看他是对的,因为美国翻译的基本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我非常重视的翻译家葛浩文,我欣赏他的翻译,他对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做了很多贡献。但美国不重视诗人,也不重视中国诗人,中国诗人在美国或英语国家没有什么地位。即使在英语国家会有什么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诗人的诗集的话,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翻译差得很。但这不应该怪译者,因为你们自己都不看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可是中国当代诗人在德国却很有地位,也有读者,在德语国家可以很快卖光他们的诗集。
在翻译工作上我们会发现美国和德国有很大的区别。美国重视翻译中国的当代小说,比较认可莫言、余华、苏童等,老请他们去美国大学做报告。虽然这类小说家在德国也会有译本,但我们基本上不由大学,也不一定是文学中心请他们。另外美国的读者不一定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基本上是喜欢看故事的人,所以他们觉得莫言他们写的都是通俗文学之类的作品,可能看完以后把书扔掉。而在德语国家最红的是你们的诗人,他们是由大学、文学中心邀请在那里开朗诵会,会来好多人欣赏或者跟他们交流,他们出版的书也会卖得很好。诗人们来德国能赚不少钱,稿费比较高,还会有书评,德国或德语国家最重要的杂志、报纸都会发表他们诗集的书评。
一般的来说德国比美国更重视翻译,我们和美国或英语国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几乎全部能有德文译作出版。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在德语国家至少会有一本译作,也可能会有好几本,这和我们的出版社也有关系。德语国家有不少小的成功的出版社,他们不仅仅考虑赚钱,且有一种使命感,如果完成好一个任务会觉得体现了作为人的价值。所以如果有人爱好可能卖不出去的中国当代诗歌,他们也会努力出它们的诗集。另外我们的翻译家们同时也都是诗人,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德语国家中国诗人这么成功的原因。很可惜我们原来一共4个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希望我的翻译还可以。其他的人他们现在翻译小说,因为可以赚钱,也包括廖亦武在内。他在德国非常红,书卖得特别好,他发财了,跟你们所谓的那些美女作家棉棉、虹影等一样,一本书最少会卖几万册。
美国喜欢出中国当代小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而德语国家除了出中国当代小说,还会出中国当代散文、话剧、诗歌。现在我们要面对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德语国家的作家老在翻译你们,无论当代中国有什么重要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话剧家,他们在德语国家都有翻译,可能是5本书,也可能是10本书。比如我自己翻译了北岛5本书、杨炼5本书、梁秉君2本书等等。但是德语国家很好的还在世的一流诗人,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几乎看不到。可是人家还会问我:你翻译这个了吗?你翻译那个了吗?好像我翻译了100本书还不够!但是,每个人都会有私人的限制,我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学好外语来帮助中国当代作家或者自己成为能用外语写作的作家。另外,学习外语可以帮助你们打开视野,直接阅读并准确地理解原意,不用通过翻译去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状况,这样更有利于提高文化交流的质量。
不少中国人习惯透过美国人来看我们德国,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我经常听到“你们西方人”这样的话,如果我对中国、日本、韩国不加区分地说“你们东方人”,你们大概也会非常不高兴。德国每年出的书可能70%是译本。德国人不光看德国人写的书,更看外国人写的书。美国人每年出的书5%是译本,英国可能是2%的译本,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他们对外国包括德国在内没有了解的兴趣。美国人75%不用护照,不去国外,德国人基本都用护照出国。所以统一地说“西方人”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美国人,和美国根本不一样,这两种文化的区别跟日本与中国一样。你们的文化跟日本的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请你们别从美国来看我们欧洲或德国,我们也不从日本来看你们。这同样也是中国学者研究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二 德国与美国的中国文学史及当代文学研究
那么海外怎么写中国文学史?以下当然仅限于我自己的体会。德国汉学家非常喜欢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宗教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这类“史”。不知道为什么德国这么小的国家会有最少11本或者12本中国文学史。好像我们自己不写什么哲学、文学这类的历史就缺少太多东西。我们已经有近100年写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了,我们比中国早5年或者10年写了中国文学史。
如果不谈中国、韩国、日本,甚至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从什么时候起欧洲开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呢?我应该承认欧洲最好的国家是当时的捷克。捷克布拉格学派的普实克(Prusek Jaroslav,1906-1980)教授,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但很早,而且水平真的很高。美国到了70年代末,感觉到普实克是个了不起的汉学家,出版了他的很多书和文章。普实克的德文也很好,在四五十年代就出版了延安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其包括了当时非常红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这本书约800页,很有价值。我自己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老用他的研究成果,如果我的文学史还可以的话,应该感谢他。他对茅盾、郁达夫、鲁迅等等的研究是了不起的,我从中受到不少启发。比如他解释了为什么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野史、小说会代替诗歌,他的认识太棒了!他说:一个传统的社会主张“闲暇”、“修心”、“放松”。写诗的时候,人在“深思”(meditation)。但是一个搞革命、搞改革、搞民主的社会时代需要人心“涌动”,如果人心涌动的话就不再写诗而写小说。小说里头的主人公是在“动”的,他在不断地行动、说话、做事等等。[2]普实克的学派有非常重要的学生,包括高利克(Marián Gálik,1933 -)在内。他有两个长处我没办法比:第一,他搞的是比较文学。他有一部书专门谈中国现代文学如何依赖欧洲文学史,也翻译成了中文。所以他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后来不太重视的作家比如茅盾等还是重要的。我200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学者让我别看茅盾他们的小说了,说《子夜》没有什么意思,已经过时了。高利克会反对这种意见:茅盾读过北欧的神话,如果我们不从北欧的神话看《子夜》的话,可能会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们如果要了解中国当时的那个现代性,并且同时了解欧洲当时不断体现的现代性,就懂得茅盾的作品仍然有很高的价值。[3]第二,高利克是天主教的教徒,我是新教徒。他知道《圣经》写什么,所以他可以告诉你们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哪个中国作家受到《圣经》的哪些影响等等。他分析得非常清楚,能查到所有的痕迹,包括王蒙在内。[4]所以要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关系,就要看他的书和文章。
到现在大约一共有10个德国人(好像没有什么奥地利、瑞士人)写了中国文学史。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不一定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专著,而是一本800多页的中国文学普及本①这本800多页的简明文学史读本的作者和书名,经和顾彬教授本人联系,确认为:1990年施寒微(H.Schmidt-Glintzer)的《中国文学史》(实际大约686页,德语为:Helwig Schmidt-Glintzer:Geschichi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Munich:scherz,1990.)。这本书是80年代末写的,出了两版。一般来说德国汉学家都是从德国的哲学、历史、文学领域来的,所以思想太复杂,人们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但是这个很有才能的汉学家能把我们研究的结果简化后出普及本,比如说中国文学普及本。这类书恐怕其他欧洲国家、美国都没有。在这个方面美国、英语国家可以向德国学习。另外我得公开承认我的不少书写得太复杂,特别是我的《中国古典诗歌史》(2013年在中国出版)。如果这本书受到你们的批判的话,我都会承认你们是对的。
美国五六十年代有许多来自中国内地、台湾的汉学教授,出了许多非常好的、一流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很可惜的是其中基本上不包括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这可能也和当时的冷战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大约比我们德国早20年已经开始研究中国内地的当代文学。我非常重视加州的一个汉学家名叫Cyril Birch(中文名白之,1925-)。他好像在60年代初请美国汉学家(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延安时期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他们当时做的报告到现在还有价值。除了白之外,荷兰有一个搞比较文学的学者叫佛克马(Douwe Fokkema),曾用英文写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政治的关系,写得非常客观和冷静。[5]这本书因为他对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见解了不起,到现在也还有价值。德国海德堡大学的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Wagner,1941-),对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和文学感兴趣,他在80年代初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与政治》一书也了不起。他是左派,是我们德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所以当时没有办法在德国,而去了美国作教授。他用英文写中国1949年以后的话剧、1949年以后的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等,出了两本一流的书,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在这个方面能和他比。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原来是革命家,是我们那个时代革命的领导,因此他知道革命是什么,革命的毛病是什么等等。所以看了他的书就能了解和理解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学和政治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离奇的关系。
虽然我老批评美国,但我不是反美的。就“汉学”研究来说,美国汉学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其他国家没办法比。第二大概是日本,第三可能是你们中国或者德国。这个可以争论,但并不重要。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原来德国比美国进步得多,现在不再是了。原因之一可能和我们德国之前没有统一有关。当时的西德首都——波恩是非常小的城市,大约30万的人口。民主德国,1961年后作为苏联的追随者不再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因为太怕中国,取消了他们当时很好的汉学。西德在1972年开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西德也有自己的革命,好多文人、作家、知识分子、教授是左派,所以从1972年开始的中德合作非常理想。美国从70年代末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好像1982年后学生才能相互交流学习,所以到了90年代后美国很快超过了我们。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内地的学者不断地去美国,代替了原来的台湾学者成为美国重要的教授和汉学家,从而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实力。而在德国或德语国家,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是非常少的,更缺少从中国来的学者加入。另外,1989年前后中国和德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美国却无所谓,可以继续很好地做他们的研究。虽然我对美国汉学的研究有不同看法,但我承认他们的贡献。
三 我的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
20世纪60年代末,德语国家除了一两个地方外(包括奥地利、瑞士在内)没办法学现代汉语,只能够学古代汉语。那么是谁在德国教并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呢?是当时的民主德国。他们不仅早已开始研究现代汉语,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从1949年开始,他们的学生来中国留学回国后,拼命地翻译介绍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包括赵树理、周立波、艾芜等等。那时他们培养了许多很好的译者。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我前面已讲:1961年以后民主德国怕革命,但西德不怕革命,我们开始跟着你们一样搞革命,跟你们一样否定古代:不需要什么精英的中文,精英的德文,需要的是老百姓的中文和德文。这是为什么西德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这么差,汉学家的德文这么差的一个原因。但民主德国跟中国、西德不一样,很好地保留了古典德语的精华,所以现在德国最好的作家都是从原来的民主德国来的,也包括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在内,西德的汉学家们到了90年代后开始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1961年后民主德国的领导不允许他们的国家介绍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但是他们仍然研究中国现代汉语、普通话,还有一些不错的成果。西德人1973年开始可以来华学习,我是1974年来的,当时在中国学了不少,老师非常好地给我们介绍了鲁迅。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翻译介绍鲁迅,一共出了大约9本专著。
1977年,因为当时西德很需要招老师教现代汉语,我有机会去了柏林自由大学,它当时是红色的革命大学。很多人劝我别去,说去了就没有机会回来找到工作。他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我是在柏林自由大学考取教授资格的,所以没办法作为招收对象。但我是保守的,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反动派,平常人一个,波恩大学不从政治来看我,所以1985年他们接受了我。我1978年到了柏林自由大学以后,那里马上开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会,来了很多国家的人,专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革命的柏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不少出版社想出一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因为他们想了解当代中国的革命状况等,这也是当时德国大学生的要求。所以当时德国越来越多的大学要求应该有人教现代汉语,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当时柏林有一个比较左但不太绝对的出版社要求合作出版茅盾、巴金、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他们出非常漂亮的书,卖得很快。所以从1977年前后我慢慢从研究古代文学、古代哲学转到研究现代、当代文学上来。到了1995年我决定应该回到古代去,因为我的心还在那里。我在德国已经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孟子各一本书,直到现在还在研究孟子。
我在波恩培养了不少年轻的翻译家、译者、学者,他们现在都是40多岁,中国当代小说都翻译得不错。有好多原因使他们不想翻译诗歌、散文,所以我决定自己翻译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基本上每天都翻译。我每天翻译当代作品也和我的写作有密切关系,因为通过翻译我可以提高自己的德文水平。到了2000年,我才公开地说我是翻译家、作家。2000年以前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好像基本上都是一种社会学角度,和其他汉学家们一样,觉得通过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多了解中国社会,当时研究工作的目的不一定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在政治、社会学,文学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王蒙,从女作家张洁、张抗抗了解到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之类等等,从理论上可以这样那样的分析,其实并不重视作家本人。我为什么2000年后慢慢开始公开地批判中国当代小说?因为我开始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不再仅从社会角度来看文学,而是从文学本身、从语言来看。我觉得应该用这样的标准看待中国作家和当代小说。
德国汉学家的问题不在于中文,也不在于我们能看多少,我们的问题在德文。德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基本上没有哪个德国人可以说“我擅长德文”。所以我写的书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如果给一个德文水平比我高的人看,他肯定能给我找出来好多错误。作家、出版社非常宽容地说德文没办法掌握,希望我们的错误少一些就好了。所以如果中国当代作家批评我们德文太差,导致他们在德语国家作品翻译不成功,我得承认这是合理的。我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中文不好也是从这个意义讲的,因为好的中文应该也是很难的,需要反复推敲,就像中国古代文学里的语言一样。我不知道如果用古代文学的中文标准看当代作家的语言,作家们还会觉得他们的中文水平高吗?我自己是通过学习外语、翻译来不断提高我的德文水平,但是好像中国当代作家不喜欢这么做,他们更想通过喝酒、玩、聊天来找到创作灵感。
一个人写什么样的文学史应该由他自己决定。我希望看到有个人思想的“不同”的文学史,而不是看了一本后就不用再看其他100本差不多相似的文学史了。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材料,并且有很好的思想理论,但不一定什么都要写,像一部文学辞典。比如说我非常重视的澳大利亚的汉学家杜博妮,20世纪90年代末她与雷金庆合著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6]从我来看它不是很好的中国文学史,而更像一部文学家、文学作品的辞典,因为它没有什么贯穿始终的“红”线,她的文学史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而且缺少鲜明的理论与批评等等。
我们的中国文学史一共10卷,是从1988年开始计划的,但基本上是1999年才慢慢开始出版。美国呢?虽然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1988年开始写,不谈日本、韩国、中国的话,差不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史,至少是最厚的。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出了10卷,他们才出来两本。我们是5个人写了10卷,美国是6个人写了两本。为什么才写两本呢?因为美国的出版界和德国的不一样。美国的出版社考虑的是赚钱,如果要卖两本的话基本上没问题;如果要卖10本就可能很有问题。但是德国出版社不一定这么看,他们看得非常远。如果有中国文学史一共10卷的话,这个国家在20、30……100年后还能够卖。所以过了10、20年后,所有的投资会回来的。美国已经出的两本中国文学史是不错的,但是非常保守,没有什么“红”线,就是给人家报道有谁、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书,有什么内容等等。他们整理了好多资料,和德国学者更注重形而上的思想有所区别,这当然也是不同的学术风格。
我老是说好的书应该有几个“故事”,有多种声音和表达。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不仅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思想史,并且我在其中谈了很多关于欧洲的问题。我是从法国革命开始,谈革命的问题,通过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我也思考了欧洲从法国革命以后的所有革命问题。[7]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出版社没有问我却删掉了20%内容的原因。但这才是我的理论,是我文学史中重要的“思想”内容。是他们觉得我的理论太可怕?但我的理论都是从左派来的,中国本可以不怕,可为什么又删掉呢?遭受删除思想理论的并不止我一个人,比如还有林语堂英文著作中关于“梁山”的思考、谈王安石的意见等。我曾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过一个所谓“keynote speech(主题演讲)”的重要发言,但是我失败了。一个星期后有人告诉我,“你的文章我们不发表,我们不敢。”我说了什么呢?我只不过说了林语堂的第二个、第三个故事。中国读者可能没有发现,原来我想翻译成中文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也被删掉了好多地方,可能是译者也可能是出版社不了解林语堂原来在写什么。所以,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批评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什么逻辑①参见:陈晓明《“对中国的执迷”:放逐与皈依——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编辑注。,他是对的。为什么?因为陈晓明也不懂德语,如果他懂德语的话就可以看原文,如果他看原文的话就会发现原文并没有什么逻辑的问题。而中文版删掉了20%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当然会有逻辑问题了。
[1]刘江凯.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李欧梵.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李燕乔,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3]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M].陈圣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4]高利克.影响、翻译和类似——《圣经》在中国研究选集[M].英文版.圣·奥古斯丁:华裔学志研究所,2004.
[5]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M].程光炜,编;季 进,聂友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杜博妮,雷金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M].英文版.纽约,1997.
[7]顾 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范 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