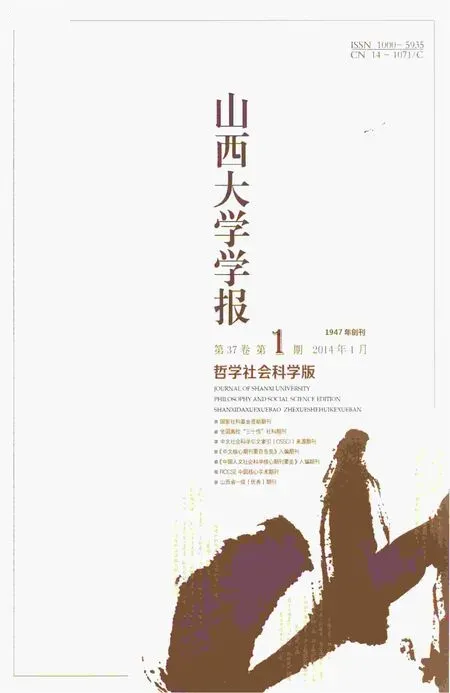莫言小说荷文翻译随想①——从《蛙》谈起
[荷]马苏菲(著),吴锦华(译),2
(1.莱顿大学,荷兰 莱顿2311;2.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浙江金华321004)
一 “《蛙》是我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大约10年前,我向一个荷兰出版社提议翻译莫言的《檀香刑》。那时这个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四本莫言的作品,但都依赖于英译本,根据英文翻译为荷兰文。我提议最好能够按照中文的原本,直接翻译为荷兰文。因为翻译不是简单地在不同语言间找对应词。一位译者得好好地考虑每个所要选的词,如果你基于中介语言(如英文)进行翻译,那么你实际是在对第一译者(如英译者)的语言决定进行翻译。而且,翻译一本书需要对两门语言、两国文学传统以及作品的写作背景有通透的理解。当需要依赖于英译本(或其他非中文译本)进行翻译,一个译者大概完全不懂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或文学,或只是略知一二。
这个出版社最后还是放弃了翻译莫言作品的计划,个中原因大概与销量不高有关。2010年我试着联系另外一个出版社。据我所知,这个出版社关注莫言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时《蛙》的中文版刚出版不久,我就已经开始着手翻译它。就在我将译稿交给出版社后的第10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蛙》实际上是我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以前曾翻译过一些短篇小说,目前正在与另两位同行一起翻译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我的精力更多集中在诗歌的翻译上,这是我大学时的主要兴趣所在。我自1995年始便开始翻译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现代诗歌。而后转向1950年后的台湾诗歌,并以此为研究对象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之后我绞尽脑汁开始翻译中国古典山水诗,已在去年出版了翻译作品集《山水》。翻译现代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从未尝试过的新事物。
二 “翻译小说并不比翻译诗歌来得容易”
由于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所有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一种改头换面;词与词之间的一一对应和转换是不存在的。不管是游走于哪种语言,译者总是在两个世界间搭建桥梁,拉近时空的距离,试着用译入语中的谚语、概念、词语和文学规范来传达译出语中的谚语、概念、词语和文学规范。除了凸显特色性,译者需强调普遍性和一般性,传递足够的熟悉度,否则读者会因太陌生而感到不适,不愿意继续阅读,去琢磨文意。译者跟读者的关系很微妙,过度的陌生化会把读者吓跑,然而译者又必须用陌生化的效果激起读者的探索欲望,这会给他们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逻辑上说,若两种文化因时间或空间或时空的差距而像两片隔离的岛屿,那么它们离得越远,翻译这两种文化的难度越大。
当我翻译小说时,我发现,不见得像很多人想的那样,翻译小说比翻译诗歌来得容易。这完全取决于你翻译怎样的文本。这段散文化文字里,作者是不是玩了些语言游戏?这诗歌是不是写得相当直白?译者总是想把文本的所有特点琢磨透彻,这些特点是从声音、节奏、风格、氛围、情绪等无形的因素中浮现出来。这些无形的因素,在不同的语言里是有所区别的。一个译者是对文本琢磨得最为通透的其中一人,他/她首先需要抓住本质的元素,随后将之转移到新的语言中。从这个意义来说,翻译一篇好的小说和翻译一首好的诗歌本质上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当翻译莫言的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如《蛙》)时,译者需要对几百页的文字有宏观把握,而诗歌的力量则来自于它的简约和紧凑。我认为,翻译有着固定格式的诗歌(如古代诗)时最有难度。因为要在翻译里呈现有固定格式的文本时,译者会觉得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对其他文类来说,翻译古典诗留给译者的可发挥空间比较小。另外,文言文诗歌中语言非常紧凑,而荷兰文则相对散文化些。产生于几世纪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留给当代荷兰读者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差距感,还有时间上的遥远感。
三 “我喜欢翻译那些敢于实验创新、能够让读者耳目一新的文本,如莫言的小说”
我总是能够顺利地翻译我自主选择的、个人很喜欢的文本。我喜欢那些敢于实验创新、能够让读者耳目一新的作者,那些既有幽默感又善用夸张修辞手法,而且能带来强烈视觉效果的作者,如小说家莫言,诗人夏宇和商禽等。
当古典诗歌以绘画般的静止画面感染读者时,现代诗歌以电影般的充满动感的画面触动读者。夏宇的语言突出显示了现代诗的特点。夏宇的诗《给时间以时间》[1]5-6里有这么一个场景:有人受了枪伤,鲜血像牙膏一样往外涌。这让我既震惊又饶有兴趣,因为她竟把枪击这样大的事情和早上刷牙这样的平常事做类比。这样的场景在脑海里活灵活现。她将有强烈反差效果的意象并置而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画面,这更凸显了她散文化的语言特点。从句法的角度看,诗中的大部分句子合乎规则,但情况因作者的分行带来的模糊性而变得复杂。例如《写给别人》[2]90-91这首诗,她的句子锁链般一环紧扣另一环,很难去判断哪是前一句的结束,哪是后一句的开始,因此,后一行经常给前一行带来不同的色彩,往往会改变前一行所说的意思。将这样的语言游戏“移花接木”,用新的语言进行呈现,这有时成为相当难的事情。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我往往可以用荷兰语设计出可以与原文相匹配的文字游戏。
商禽的散文诗,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中文现代诗的散文化风格。商禽的诗歌很人性,也富有同情心,但丝毫没有伤感的味道。因为他在诗中经常惊人地将悲和喜杂糅在一起。他用较长且拗口的句子制造障碍,延长阅读的过程。以《长颈鹿》[2]为例,几个句子便描绘出一幅有想象力的画面,给予读者精神的盛宴。
除欣赏夏宇和商禽之外,我也欣赏莫言书中的幽默感和古怪感。在《檀香刑》开篇,有一个场景是,媚娘梦到她的父亲被砍头了。接着笔锋一转,场面开始变得滑稽:被砍下的头(连同脑后的辫子)落地时还活蹦乱跳,还会出于自卫的考虑跟紧随其后的野狗搏斗。这样离奇的描写,为整本书奠定了基调。翻译这样的作品时,总会有不少的乐趣,因为你为了确保读者能明白书中的幽默,往往需要对某些出人意料的细节进行强调。
莫言的语言和夏宇、商禽的语言都很不同。两位诗人试图将中文推向极致,带来模糊性,或是延长阅读过程。而莫言首先是口头传统文化中的说书人——在他的所有小说里,技巧和结构都非常多样化。他的语言偏口语化,有叠词、夸张和讽刺,并经常将四字成语嵌入小说中,引述有名的古典文学文本。他的长处在于讲述的方式,动用了全方位的感官,叙述时极其详细且别具巴洛克风格。在莫言的写作里,仿佛可以闻到、吃到、听到、看到和感受到书中所写的东西。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对人物深层次心理的挖掘这方面,如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人物内心进行详细刻画的那样,莫言是欠缺的。莫言任由读者根据人物特性和故事情节去自行揣摩人物的内心。
四 “我是如何翻译小说《蛙》的”
莫言的这些写作特点,我希望在《蛙》的荷兰文翻译中有所体现。然而,为了确保荷兰译文的地道性,我依然需要对莫言的写作风格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荷兰文比中文更少地使用叠词。实际上,语法上说,中文已经自然而然地包含了不少的叠词,荷文则要求能避则避。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将叠词的使用减少到一个荷兰读者能够接受的程度,这样同时还能保留原文的口语化、重复化的特点。
类似的考虑和选择处处可见,译者需要时时品味原文“独具匠心”之处,并琢磨在译文中如何再现原文中的效果。要想翻译莫言原文中常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字成语以及类似的语言,译者可以采用相应的荷兰等同物(也许有时也不仅仅限于荷兰),或者提供字面上的翻译,或者可以将原文的成语进行“易容手术”,让人“忘记”它原本是个成语。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荷兰语比中文更少地使用成语。除了成语的翻译这点外,译者还需要注意“夸张”和“讽刺”特点的翻译。夸张和讽刺是否成立,这视乎文化的定义。因此将中文中的夸张和讽刺翻译成荷兰文时,往往需要多花些笔墨进行适当的强调或解释,否则荷兰读者很难感受到里面的幽默。
姓名的翻译有时也会成为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叙述者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朋友的信。蝌蚪是这样开始讲述他的姑姑的故事的: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3]
要想翻译这段文字没有很大的问题,但这段究竟要怎么翻译,会对后面的翻译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叙述者特别为这些看似荒谬的名字做了解释,那么我必须翻译这些名字。可是,这在中荷文学翻译中是比较少见的。几十年前,译者们会偶尔去翻译人名,毕竟名字是有含义的。但这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笑果”,有时还会激怒读者(因为荷兰人没有这个名字风俗)。在《蛙》里,命名方式与身体部分相联系这点让人发笑,就像叙述者(笔名蝌蚪,学名万足,乳名小跑)解释的那样。
叙述者的妻子,是文中为数不多的名字与身体无关的人。她的名字叫仁美,正义且美丽的意思。我在翻译时只是写下她名字的拼音,并没有把意思翻译为荷兰文。但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她的姓氏时并不奏效,还因此带来了一个相当好笑的问题——因为她姓王,王字的拼音写法和荷兰语中的“脸颊”单词的写法一模一样,这样她的姓就和身体相关了!出于这样的考虑,在荷兰文译本中,她的姓氏被去掉了……
五 “莫言的小说创作具有普世价值,我将继续翻译他的更多作品”
《蛙》的主人公是个妇科医生,在山东高密乡工作。这位女主人公,在文中被称为“姑姑”,是一个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医生。她的主要工作原是帮助孕妇接生,而后她必须面对新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一个忠诚的中共党员,姑姑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并想尽办法将之落到实处。她越来越频繁地要对已经有一个孩子的男人实施节育手术,对怀了第二胎的妇女实施堕胎手术。在从医早期,姑姑曾被作为英雄,因为她拯救了好几个在传统接生婆和传统接生方法下濒临死亡边缘的母亲和婴儿。但是,(因为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缘故,)她最终被视为村里的恶魔。虽然几经磨难,姑姑还是给大家留下了不屈不挠的、有正义感的印象。她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一个没有自己孩子的女人,一个掌握着许多婴儿命运的人,一个在晚年有着巨大罪恶感的人。
莫言的许多作品都以20世纪的中国为背景,展现这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体现了自己对社会民生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莫言是位热心政治的作家。他显然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蛙》也不是一部政治性的作品。通过描绘妇科医生人生的跌宕起伏,通过讲述她的亲人和村民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了解大饥荒中饥饿的孩童吃木炭的悲戚,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残忍。但国家历史始终作为一个背景,真正产生意义的,是这些作品如何描绘人物及他们的行为。他们不是扁平的纸板小人,而是好坏并存、面对人生两难抉择的人。
对一些主要人物来说,一件事或一个行为原来是会决定他们的余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试图通过小说《蛙》,去探讨“每个人都需为他自己的生活及行为负责”这样的话题。这和萨特如出一辙。书中的叙述者,以蝌蚪为笔名,在开篇就表达了他对萨特戏剧如《苍蝇》和《脏手》的欣赏之情,并流露出了想仿效着给姑姑写个戏剧的欲望。给姑姑写的戏剧,成了书中的结尾部分。
莫言的小说主要是提出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答案。姑姑当时能拒绝执行当局下达的任务吗?当妻子遭到强制堕胎时,为什么蝌蚪不去反抗?为什么他会认为事业比孩儿更重要?为什么他的妻子要冒着生命危险违法怀孕?总的来说,小说《蛙》以负罪感和责任感为主题。这两个主题足以超越中国的语境。
这就是一年半来翻译《蛙》时我的一些随想。这本书仿佛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出版后,我每天都看报纸,希望能得到一些肯定的评价。而外界的反应冷热兼有:佛兰芒语区(比利时北部)的大部分报纸反响很是热烈,而荷兰的报纸则较为中立,没有特别追捧,也没有强烈批评。至于读者,大部分似乎都挺欣赏这本小说,销量相当不错。上述莫言小说的特点,加上莫言的诺贝尔奖荣誉,定会吸引荷兰公众接着去阅读更多莫言的作品。即使不是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由我来翻译,至少我已开始着手莫言的另一部巨著《檀香刑》的翻译工作,预计两年内即可与读者见面。
[1]夏 宇.夏宇诗集:Salsa[M].中国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
[2]商 禽.梦或者黎明及其他[M].中国台北:书林出版社,1988:33.
[3]莫 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