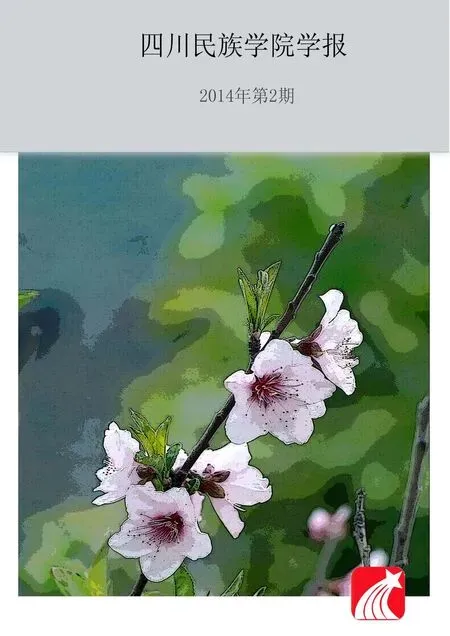丹巴古碉相关问题探究
陈学义 陈卓玲
青藏高原的碉楼主要密集地存在于以下两个大的区域:一是处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二是处于青藏高原南部地区。横断山脉地区的碉楼主要分布于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冕宁、盐源等县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的江达县等地。青藏高原南部的碉楼主要分布于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山南和日喀则地区[1]。位于横断山脉藏彝走廊地区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相汇处的丹巴,历史上及现今都以碉楼分布最密集、数量最多而被誉为“千碉之国”。丹巴不仅仅是因为碉楼众多引起人们关注,更主要的是丹巴与大渡河上游碉楼的起源密切相关。石硕先生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青藏高原碉楼分布所对应的若干因素探讨》一文中论述青藏高原碉楼主要分布在“依山”和“近川谷”的自然环境中,与石砌房屋分布区域呈现对应关系,得出“‘依山’和‘近川谷’当是古代碉楼修建地区的一个基本的自然环境条件。”“石砌建筑技术的传统则是产生碉楼这一独特建筑形式的文化与技术前提[2]。”石硕先生在这里实际上阐述了碉楼产生所必需的基础与条件。丹巴地处青藏高原高山峡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路罕额依遗址揭露出的石砌房屋所展现的高超的石砌技术,具备了碉楼产生的必需的自然基础与技术条件,丹巴地区极有可能孕育出碉楼这一独特的建筑,成为大渡河上游碉楼发源地之一。2004年杨嘉铭先生推断丹巴“中路一带极有可能就是四川西部藏羌地区高碉文化的发祥地[3]”。杨先生是提出川西高原藏羌地区碉楼发源于丹巴的第一人。
笔者1990年曾数次到中路罕额依遗址发掘现场考察,考察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先生对遗址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笔者试图依据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及实地考察材料对大渡河上游碉楼产生的原因、发源地、年代作初步的探讨。
一、丹巴碉楼最初的原始形态及产生的年代
青藏高原碉楼产生的年代久远,史籍中有关碉楼产生的年代无记载,碉楼究竟产生于何时,确有探讨的必要。藏彝走廊地区碉楼最早的记载见于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书中记述东汉时岷江上游的冉駹夷时记载:“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即碉,证明东汉时岷江上游已有碉存在,距今2000年。这是史籍中记载的有关碉的较早年代。石硕先生指出:“碉见于记载的年代并不能等于其产生的年代。根据史籍的记载,冉駹夷存在于岷江上游地区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秦代或更早……碉即‘邛笼’产生的年代很可能要早于东汉。”[1]徐学书先生根据文献记载,结合现代羌族《羌戈大战》的历史传说,结合嘉绒人的古老传说,相互印证,得出系西汉中期岷江上游的冉駹夷人为抵御南下的羌人而修筑[4]。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原始形态的碉楼建筑出现的年代早于两汉时期,石硕先生关于碉楼产生的年代很可能要早于东汉的推测无疑是正确的。
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所公布的材料,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12层。发掘者通过对典型陶器的分析、对比,将遗址分为三期。地层的第10、11、12层为第一期;地层的第6、7、8、9层为第二期;地层的2、3、4、5层为第三期。第三期共测定了7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其中除1个数据的年代明显偏早以外,其它6个数据均以第三期较早的地层和遗迹单位所出标本测定,年代大致为距今3800-3200年。第三期最晚的地层单位中出土有与岷江上游石棺墓晚期中的双大耳罐相同的器物,双大耳罐相同的器物出现的年代约在西汉武帝前后。因此,第三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800-2000年之间。中路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有关地层堆积的描述中提到:“第6层……此层下压有F2叠压并打破第6层。”说明F2建于第6层。至于发掘简报中提到的第三期较早的地层,显然就是指第5层。F2位于第三期较早的地层,又是第三期较早的遗迹单位,而第三期所测定的年代是从典型房屋F2、F7、F5、F6中采集的碳素标本测出的,所以F2、F7的年代亦应在距今3800-3200年之间[6]。另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在《丹巴县中路遗址1989-1990年度发掘情况简介》中介绍:“遗址中已知的年代是第2号房子填土中木碳经碳十四断代测出的,其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前期……”①此简介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执笔。碳十四测定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第2号房屋F2的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从考古年代学来判断,这可能就是中路罕额依石砌碉楼最初的原始形态的大致年代。
碉楼是多层楼层的高大石砌建筑,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F4只是碉楼最初的原始形态,与完整的碉楼相比相去甚远。在此基础上还需增加楼层,增加高度,完善防御设施。这之中需解决许多石砌建筑的技术难题,其过程是长期缓慢的。尽管如此,距今2800年左右,大渡河上游极有可能出现完整的碉楼,大约在距今2500年前后,以丹巴为源向东、向北、向西扩展。其依据为青藏高原“现有的碉楼除极个别在底层开设碉门外,大多都在2-4层设置碉门,碉门距地表往往高达5-10米。”这与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F4的结构相似,证明与中路罕额依遗址最初原始的碉楼形态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向北、向东扩展的路线是沿大、小金川河谷。大金川河畔的丹巴县聂呷乡甲居三队班玛柯家的家碉甲居卡碉,高三十余米,有十三层。第一层至第八层,每层系用石片阶梯上下;小金县沃日乡小官寨碉上部亦用片石阶梯上下。这与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的片石阶梯砌筑方式相同,为碉楼沿大、小金川向北、向东扩展提供了线索。
二、丹巴中路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葬、碉楼之间的内在关系
碉楼是青藏高原古老、独特的文化遗存,石棺葬是新石器时代后出现于青藏高原地区一种普遍的考古墓葬遗存,两者的分布区域重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相汇处的丹巴县中路碉楼密布的台地上,不仅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石棺葬,还发现了有大量石砌房屋基址的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碉楼、石棺葬、古遗址三者重合一地。在青藏高原碉楼与石棺葬分布区重合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碉楼、石棺葬、古遗址三者重合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从青藏高原目前来看是非常罕见的,暗示了三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石棺葬集中分布于青藏高原南部的林芝、山南、日喀则等地区;东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横断山脉地区石棺葬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地区;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流域地区;雅砻江上游及其支流鲜水河地区;川、滇相毗邻的金沙江中下游地区[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位于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相汇处的丹巴县境内的中路乡、梭坡乡、半扇门乡腊月山村、巴底乡、聂呷乡、东谷乡、水子乡、岳扎乡纳顶村、章谷镇白呷依等乡、村,相继发现石棺墓。
长期以来,中路一带民间流传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在遥远的古代,中路的罕额依、克格依、几卡依村从东至西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人口众多,地下埋葬大量的石棺墓,数量达到上万座。多年来这一传说未引起任何人的重视。1987年夏,甘孜州文物普查队在中路乡罕额依村发现分布范围大、埋葬方式特殊的石棺墓群。翌年秋,四川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派员复查,在罕额依村发现了古代文化遗址。1989年至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中路罕额依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主体部分在罕额依村刹拉科寺所在的台地上,遗址中及其外围有大量石棺墓分布,遍及中路乡的罕额依、克格依、呷仁依、折龙等村寨。罕额依遗址不远处的断层上裸露出地面的石棺墓达50余座。石棺墓排列整齐,呈长方形,长1.7-2米,宽0.5-0.7米,高0.5-0.6米。也有近似正方形的,大约长2.5米,宽2.3米左右。中路石棺墓结构有两种类型,其一为无底石棺,中路石棺墓也以无底石棺墓为大宗;其二为完整石棺,坑底和四壁衬铺打制较规则的石板,上面再盖上石板封闭,或坑底、上方及前后壁用石板,侧壁用片石砌筑。
中路石棺墓没有正式发掘,1989年至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在中路罕额依遗址发掘期间,征集到一些石棺墓中出土的随葬陶器。1996年丹巴县文化馆在中路折龙征集到18件石棺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①资料由丹巴县文化馆提供。。器型有饰羊头的平底双耳罐、四足菱口双耳罐、饰羊头三足双耳罐、四足双耳罐、单耳罐、四足罐、单耳杯、方口圈足单耳杯,高圈足单耳杯、饰乳钉纹单耳杯、四足提梁羊首壶、豆、圈足器。另有磨制石斧、铜手镯等。
中路石棺墓出土的陶器饰堆塑羊头平底双耳罐、四足菱口双耳罐、饰羊头的三足双耳罐、四足双耳罐、四足提梁羊首壶等陶器的造型特征、装饰风格见于青衣江上游宝兴老场类型墓葬中[6]。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最晚的地层第2层的石砌房屋F1中出土了一件饰漩涡纹的双大耳罐,其造型与装饰风格均与岷江上游石棺墓晚期的双大耳罐相同。一件出土于F6的双大耳罐与岷江上游石棺墓晚期的同类器也有相似之处[9]。饰漩涡纹菱口双耳罐在青衣江上游宝兴老场墓地中与带足双耳罐、饰羊头的双耳罐同出。说明中路罕额依遗址采集的陶器与中路石棺墓出土陶器的造型特征、装饰风格相同相似。
中路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器的纹饰有细绳纹、弦纹、戳印纹等[6]。而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遗存的陶器有粗绳纹、戳印纹、刻画纹、乳钉纹,附加堆纹等[5]。两者出土陶器的纹饰基本相似。
中路石棺墓出土的陶器有夹砂、泥质红褐陶或红陶、泥质磨光黑皮陶、泥质灰陶[6]。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陶色以灰陶为主,红褐次之,有少量褐陶及橙黄陶,磨光陶的数量较第二期有所减少[5],说明两者陶系基本相同。
中路石棺墓中出土陶器中夹有大量的云母片[6],而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陶器陶片中均夹有大量云母片[5]。很显然两者的陶器均系用当地含有云母片的泥土制作而成。从碉楼的发展演变脉络来看,最早产生的碉楼的造型应为四角碉,四角碉是碉楼建筑的基本型,在四角碉的基础上发展出特殊的五角碉、六角碉、八角碉及十二角碉等其他形体类型的碉型。四角碉产生的年代肯定早于其他类型的碉楼,在探讨碉楼起源问题方面也应以四角碉为突破口。距今5000年前的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房屋基址,全都是石墙房屋,其后中路一带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石砌碉楼。此种现象表明古遗址与碉楼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披露,遗址发掘中共开探方4个,4个探方中仅有第1号探方T1发掘至底,另3个探方因发现完整的石砌建筑而做保护性回填。遗址中揭露出的房屋F2、F4、F7等正是发掘简报中提到的完整的石砌建筑。F2、F4两座房屋呈全封闭式,四面墙未设门道,都是双层墙体,石墙基本上都是用片石砌成。F2墙体高度为2.5米,是残存的石墙中最高的墙体。F2更为奇特的是,在西墙内墙上部砌有4级倾斜向上的石阶梯。阶梯用单块片石构成,一端砌入墙体,大部分露在墙外,墙的下部则未砌筑阶梯,推测墙下部可能使用独木梯上下。F2、F4室内外有部分掉落的石块,分析残墙高度并不是石墙的原始高度,且墙体厚度达50厘米左右,石墙砌筑水平相当高,承重大,极有可能承受二层荷载。笔者据此推测F2、F4是两层平顶的房屋。F2、F4的门设在第二层,从屋外地表架设独木梯至第二层,然后从第二层的楼梯口沿片石阶梯及架设于下部的独木梯上下。中路罕额依遗址地层第二层,有大量红烧土块,土块中掺有草 (麦)杆。罗二虎先生认为这些红烧土块是垮塌的土墙[6]。笔者推测罕额依遗址中两层平顶房屋的第二层外墙可能是夯筑的土墙,这与昌都卡若遗址中两层平顶石墙房屋的第二层未用石砌墙类似。
丹巴境内古代遗存的四角碉除极个别在底层开设碉门外,大多在2-4层设置碉门,大部分碉楼底层呈封闭式,为实心砌体,碉门距离地表的高度为2-6米以上。从碉墙外地表架设独木梯至碉门的楼层后,再沿独木梯下至第一层或上至上边的楼层。中路乡克格依村康波碉,呷仁依村然卡卡碉的结构皆如此,这与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F4的结构、布局相似。
中路乡罕额依村与克格依村相邻,克格依村然卡波家的家碉然卡碉高30余米,楼层十二层,碉门建于第三层。从第三层起至第八层,每层都有一列倾斜向上的片石阶梯,每块片石的一端砌入墙体,伸出墙外的部分长约40厘米,宽约30厘米。这与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内墙上部的片石阶梯惊人地相似。
四角碉的建筑平面通常呈正方形、矩形两种几何形状。丹巴境内的四角碉建筑平面多呈正方形,呈矩形的四角碉数量不多。另有相当一部分四角碉建筑平面边长非常接近,近似于正方形。如中路乡克格依村康波碉边长宽5.4米,长6米;中路乡呷仁依村然卡卡碉边长宽5.1米,长5.56米;巴旺乡光都村巴旺沟口碉边长宽6.4米,长6.8米。中路乡罕额依遗址揭露出的房屋F4边长宽为2.75米,长为3.06米,建筑平面的几何形状近似正方形。而F2、F7的建筑几何平面形状呈长方形。说明建碉的人群在建造四角碉的过程中,沿袭了中路罕额依先民掌握的砌筑接近正方形及长方形房屋建筑平面边长的比例。
丹巴境内的古碉楼的建筑材料多选用片 (块)石。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丹巴用片石砌筑的古碉楼只是轻微受损,这一现象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对其建筑特点进行认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古碉楼历经几百年甚至大地震不倒的原因有三方面:即与碉楼的折角有关;与碉楼建筑材料片石有关;与碉楼的建筑工艺有关。指出修建碉楼的片石为当地所独有,具有一定的韧性。碉楼建好以后,经历风雨,片石越挤压越结实,这是一般土墙或砖墙所不能比拟的。[7]同时石碉砌筑时用来粘接石料的土是当地的一种富含硝的粘土,蕴含着独特的化学成分,粘合性极强。1990年,笔者在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先生介绍说:“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石砌房屋基本上都是石片砌成,中间用麦杆加泥做粘接”。说明丹巴境内古代遗留下来的碉楼的建筑材料与中路罕额依遗址揭露出的房屋的建筑材料如出一辙。
丹巴古碉楼在砌筑中,使用了片石砌墙技术,整座碉楼几乎都是用片石叠砌而成。建成的碉楼墙角端直,墙面平整,达到“如笔削然”的程度,可谓世界石砌建筑的精妙之作。碉楼片石砌墙技术正是源自于中路罕额依。据中路罕额依古遗址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口稠密的土著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自己的农业文明,用石块砌筑房屋居住。对石砌建筑的材料“石”的石性有所了解。罕额依人在砌筑房屋的石墙时,已经掌握了较高的片石砌墙技术,能根据砌墙的需要来选择石料。由于片石至少有3个以上平整面,形状比较规则,石块有两个面平行,砌筑时易摆放。罕额依人砌筑F2、F4、F7的石墙时,把大面平放,选择具有平整面的石面作外露表面,石块之间空隙填充夹有草杆的粘土泥浆并用碎石嵌实,粘土加草杆的泥浆粘性相当强。砌出的石墙整体性、稳定性相当强。
专家对中路折龙石棺墓出土的陶器进行初步鉴定,其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组成的丹巴县中路乡古遗址发掘考古队的专家鉴定。。其中饰堆塑羊头平底双耳罐、四足菱口双耳罐、饰羊头的三足双耳罐、四足双耳罐、四足提梁羊首壶等一组陶器的造型特征、装饰风格见于青衣江上游地区的老场类型墓葬中。老场类型墓葬的年代大体为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中路石棺墓出土陶器的年代与老场类型墓葬的年代较为接近,其下限为两汉时期[6]。
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的年代为距今3800-2000年,遗址第三期最晚的地层中出土有漩涡纹菱口双耳罐,这种双耳罐在宝兴老场墓葬中与带足双耳罐,饰羊头双耳罐也同出。证明中路石棺墓葬的年代与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的年代基本相近。前已谈及中路罕额依遗址中出土的碉楼最初原始形态的建筑F2产生的年代距今3500年前后,完整的碉楼产生的年代大致距今2800年前后。碉楼、石棺葬两者存在的年代相近。从中路碉楼产生的年代及中路石棺墓存在的年代看,建造石砌碉楼、石棺墓葬的人群为同一人群。正如杨嘉铭先生指出石碉文化与石棺葬文化的“创造者是同一主人。所不同的是一个作为隐蔽文化而被深埋在地下,一个作为表露文化而残留于地面。”[3]
童恩正先生在《试论我国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对石质坟墓产生的原因作了精辟地阐述,“古代某些民族之所以兴建石棺葬,大石墓——石棚这一形式的墓葬,其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对于石质建筑有所熟悉,有所应用,最后才能产生宗教信仰上的观念。根据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习惯,为死者修建的幽宅,往往模仿生前的住宅,所以石质坟墓的出现,亦与其地的实用建筑有关。”[8]新石器时代晚期,罕额依先民长期在此繁衍生息,砌筑石质房屋居住,人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对石质建筑的主要材料“石”的特性有所熟悉,尤其是对石形的分辨应用及处理大、小石块、粘土的关系有所熟悉,掌握了精湛的砌石技术,砌筑了大量石质房屋居住。在此基础上根据事死如事生旳习惯,模仿死者生前的住宅,修建石质坟墓,让死者在另一世界生活。既然石棺墓的出现与实用建筑有关,碉楼的产生也与其地的实用建筑有关,为了防止部落、族群之间纷争引发的战争,在石砌房屋的基础上修建了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
中路石棺墓与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陶器的造型特征、装饰风格、纹饰、陶系及制作材料等文化因素存在相似之处。中路古代遗存的四角碉又与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的石砌房屋F2、F4的结构、布局方面相似。如碉门设置的位置,一层以下部分呈全封闭式,楼层之间使用片石阶梯和独木梯上下;建筑平面沿袭了F2、F4的建筑平面的几何形状;使用了相同的建筑材料;沿袭发展了罕额依先民的砌石技术等。中路乡克格依村与罕额依遗址近在咫尺,位于克格依村古代遗留的四角碉然卡碉、康波碉的结构、布局与罕额依古遗址中出土的房屋F2、F4存在相似之处。可见四角碉在建筑过程中沿袭了F2、F4的基本结构与风格,四角碉是在F2、F4基础上发展起来的。F2、F4与其后的四角碉相比,尽管形状简单,结构还不完美,但它是四角碉的萌芽,是四角最早的原始形态。从以上分析比较中不难看出,中路古代遗存的四角碉与石棺葬,二者和中路罕额依遗址关系密切,存在若干相似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的确难以用偶然的巧合来解释。充分说明中路石砌碉楼、石棺墓葬与古遗址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石砌房屋在前,是石砌碉楼的母体,在石砌房屋的基础上产生碉楼、石棺墓。中路罕额依遗址的石砌建筑房屋,与其后出现的碉楼、石棺墓三者之间清晰地展现出石砌建筑发展的演变脉络。中路罕额依先民生居碉楼、碉房,死葬石棺,这是中路古代行石棺葬人群的生活状态。杨嘉铭先生对碉楼与石砌房屋的渊源关系作了阐述:“在古代,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流域地区实行石棺葬的先民,是高碉的建造者。高碉与石室之间有着源与流的关系;即是说,高碉是在石室的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特殊防御功能的建筑,石室在先而高碉在后。”[3]
三、古代先民最初修建碉楼的原因
青藏高原碉楼这一独特的文化遗存,最初修建的目的是什么?由于史籍中有关早期碉楼的记载极少,探讨此问题难度相当大。尽管如此,笔者从史籍记载、民间传说、考古材料几方面结合进行分析研究,试图对古代先民最初修建碉楼的原因进行探讨。关于古代人修建碉楼的目的,史籍并非没有一点记载,《北史》《隋书》两书均记载了古人最初修建碉楼的目的。《隋书·附国传》记载隋时位于川西高原的附国时云:“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一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屠。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9]《隋书》是唐代魏征、令狐德棻等撰,书中关于碉的记载是继《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之后,汉文史籍中有关川西高原地区碉楼较早、最为详细的记载。这段文字不仅仅是对碉楼的功能作了说明,同时对古代人群最初修建碉楼的原因作了诠释。
附国的中心区域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炉霍、甘孜和新龙县一带。嘉良夷地处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地区,位于附国东部,紧靠附国。嘉良夷与附国一样,不是单一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而是由众多种姓不同的大、小部落组成的联盟。风俗习惯同于附国,民风强悍,俗好复仇。部落、族群之间有交融,也有纷争,甚至由冲突引发的战争时有发生。这一段文字中的“以避其患”的“避”是“防止、躲避”之意,“患”即“灾祸”。附国、嘉良夷的人群躲避、防止什么灾祸?显然就是由于“俗好复仇”的部落、族群之间的冲突引发的战争。“故垒石为巢”的“故”字乃“缘故、原因”之意。为了防止部落、族群之间的纷争引发的战争这一原因,所以“垒石”修建了“巢”,即用石头砌筑了碉。魏征、令狐德棻在这段文字中,用“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以避其患。”13个字概括了碉楼的主要功能,同时阐释了附国、嘉良夷人最初建造具有防御功能的“巢”的根本原因。
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相汇处的丹巴,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今都是横断山脉地区碉楼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碉楼的形状类型和功能最齐全的地区。碉楼文化十分发达,保存了不少有关碉楼的传说,其中有的传说与碉楼的起源相关。
传说一:很早以前,中路一带常有野人出没。野人身强力壮,经常袭击村寨,抢夺粮食、牲畜,寨子里时有村民被野人虏走吃掉。村民整天人心惶惶,上山劳作时,为防避野人,用树枝编成手箍,戴在手腕部。如被野人抓获,野人必抓住村民手腕,然后抬头目视太阳。野人的习惯为猎获猎物后不立即吃掉,而要待到夕阳西下方食用。村民趁野人聚精会神等太阳下山的机会,趁其不备,将手从树箍中抽出脱身,然后逃离险境。村民居住的房屋门建在地面,对野人没有一点防卫作用。村民在首领的带领下,用石块修砌较高坚固的房屋,底层不设门,门安在石墙高处,窗户建得十分狭小。这种房屋能有效地防避野人的侵袭,从而保证了村民的安全。
传说二:千百年来,丹巴藏族凡生男孩,即备石、泥和木料,开始修砌碉楼,在碉旁埋一毛铁。孩子长一岁,建一层碉,同时取出毛铁锤炼一次。孩子长到18岁,碉修至18层,而毛铁已打制成钢刀,长辈把钢刀赠与男孩,表示男孩已成年,已能成家立业。倘若男孩成年时,家中尚未建起碉,就娶不到妻、成不了家、立不了业。
古老的传说往往具有史料价值,找到历史的痕迹。林向先生在《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一文中,对羌族民间传说《羌戈大战》进行了较全面的历史学分析,内容涉及到岷江上游羌族的来源,氐羌族关系及石棺葬的族属等问题,揭示出羌族是战国秦汉以后从甘肃一带迁徙到达岷江上游的。戈基人是氐族,先于羌族居于岷江上游,与后到的羌族发生冲突,战败后迁徒的这段历史。[10]中路有关碉楼的民间传说,向人们透露出古代人们最初为什么修建碉楼的信息。传说中提到的野人也许就是外来的人群,或古代丹巴一带的众多部落或族群中的人。第一则传说透露出古代人群修建碉楼是为了抵御野人的侵袭。第二则传说则把修碉与家庭、家族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只有修起了碉楼,家庭的安全才有可靠地保障,男孩子才能成家立业,姑娘才会嫁给他。同样告诉人们最初建碉的目的。碉楼是古代先民为自身安全需要,修筑的具有防卫功能的独特建筑。
“生子必建碉”应该就是附国、嘉良夷人“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以避其患。”建碉初衷的延续,这种为维护自身安全而修建碉楼的传统,千百年来早已相沿成习。1938年,庄学本先生考察了中路碉楼,有碉楼的人户占全村总户数十分之七,几乎达到户户有碉的程度,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史籍记载与民间传说、习俗证实碉楼的起源与防御有关,有关考古材料向我们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线索。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公布的材料,罕额依遗址地层堆积有12层,分为三期,出土17座石砌房屋基址。简报中记载遗址中“发现完整的石砌建筑”,F2、F4、F7正是简报中提到的完整的石砌建筑中的三座房屋。分析F2、F4和F7三座房屋的用途及建筑特点,可以大致了解3000年前罕额依先民最初修建碉楼这种独特建筑的目的。
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的房屋基址中,F4的位置靠北,右后侧是F7,左后侧为F2。F7朝向为坐南朝北,北墙近东墙角的地表处设有一道门,放置一块封门石,进门有三级石砌阶梯通往室内。F2和F4的石墙呈全封闭式,未设任何门道。F2的石墙高度为2.5米,西墙内墙上部有四级倾斜向上的石片阶梯,推测下部采用独木梯上下,①笔者1990年在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时,根据古遗址现状实录。F2、F4极有可能是二层平顶石墙房屋。
从房屋F2、F4的结构可以看出是一种独特的石砌建筑,在3000年以前,罕额依的先民为什么要建造这两座异于当时人们居住的建筑呢?这与丹巴的地理位置、环境及古代先民的安全需要有关。丹巴位于横断山脉地区,地处古代民族迁徙的藏彝走廊地区。考古材料、民族志材料证实这一带是古代人群不断迁徙流动的场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披露,中路乡罕额依遗址中房屋叠压打破关系复杂,12层地层堆积层中除第1层、第2层、第4层外,其余每层均存在叠压打破关系。说明罕额依遗址中的大量房屋是重复使用的,迁徙的人群在此地建起了房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又迁往异地,另外的人群又来到罕额依生活。人群迁移走后有的房屋可能由于地质变化被掩埋于地下,后到的人群在原址上建起房屋。丹巴世居民族有藏、汉、羌、回等民族,语言复杂多样,仅藏语就有嘉绒语、藏语康方言、安多语、尔龚语等语支,各语支小区域内又有差异,形成典型的“一条沟一口话”。应该说这就是《隋书·附国传》所记载的附国、嘉良夷人“言语少殊,不相统一”的真实写照。古遗址的发掘和语言的多样性均证实,古代这一带是人群不断迁移、流动的场所,部落、族群众多。部落、族群之间有交融,也有纷争,由纷争引发的战争时有发生。羌族民间诗史《羌戈大战》再现了古代岷江上游发生的部落、族群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史诗记载了古代甘青地区南下的羌族到达岷江上游,与早于羌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戈基人发生冲突,羌族在天神的启示下,用白石作武器战胜了戈基人,战败的戈基人迁往常年落雪,更加高寒的地方居住[10]。
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7的用途非常明显,是罕额依先民的民居。F7这类房屋成为他们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袭的安身之所。而对于手持长矛、弓箭、石刀、石斧的人群,这类房屋形同无设防之地,入侵者极有可能轻易地推开封门石,破门而入。在粮食、牲畜被掠夺,亲人被掳走、杀害的惨痛事实面前,罕额依先民极需建造一种既能居住,更能提供安全的建筑。于是罕额依先民利用其高超的砌石技术,把F2、F4的石墙砌至2.5米以上的高度,底层不设门道,形成全封闭式,门开在2.5米以上的第二层,室外架设独木梯上下。石硕、杨嘉铭、邹立波先生等所著《青藏高原碉楼研究》一书记载了青藏高原碉楼的功能,云:“青藏高原上的许多碉楼都有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现有的碉楼除极个别在底层开设碉门外,大都在2-4层设置碉门,碉门距地表往往高达5-10米以上。碉楼的中上部各层,则于不同方向的墙面上错位开设通风、瞭望、射击孔。”[1]由此可知,碉楼体现其防御功能的部分主要有两大部分,其一为碉门的设置,底层的封闭式结构;其二为开设的通风、瞭望、射击孔。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F4已初步具有碉楼的防御功能的第一部分,即碉门高开,底层为封闭石墙。从F2、F4的结构、形态来看,这类建筑在其后的部落、族群之间的冲突中,起到了保护人群的作用。罕额依先民进一步意识到,门道高开,底层为封闭式的石墙结构的建筑能有效地保护人群的安全,这类建筑的高度与防御功能的强弱密切相关,建筑愈高,防御功能愈强。经过漫长的岁月,具有多层楼层的石碉建筑在罕额依人手中建成。人们为了更好的进行防卫,在碉楼中上部分设置了通风瞭望的窗口及杀伤敌人的射击孔,这样完整的碉楼得以产生。这种碉门高开,一层以下墙体为封闭石墙砌体的结构成为青藏高原碉楼建筑的最基本的结构。
四、源远流长的石砌技术传统
丹巴位于嘉绒藏区的核心地区,是嘉绒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嘉绒藏族就以善于砌石著称于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就有东汉时岷江上游的冉駹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的记载。所记的是2000年前岷江上游的冉駹夷人依靠高超的砌石技术,冬季到成都平原谋生的习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长寿先生到嘉绒地区进行数月的社会调查,写出《嘉绒民族社会史》一书。书中马先生提出“汉之冉駹即隋唐之嘉良,亦即近代的嘉绒”。列出了嘉绒民族的历史源流与演变序列,并描述了嘉绒人每年冬天到成都平原做佣工,承担凿深井、砌井壁的特殊工作的情形。在马先生的笔下展现了嘉绒人“斫制契石、碾转调度。故所砌壁,坚固整齐,如笔削然”[11]的精湛砌石绝技。
任乃强先生盛赞丹巴的嘉绒藏族工匠的砌石技艺,称其为“叠石奇技”。在所著的《西康图经·民俗篇》中描述嘉绒工匠砌成的高数丈、厚数尺的番寨子的碉墙,皆用乱石砌成,已达到“不引绳墨,能使圆如规,直如矢,垂直地表,不稍倾畸。”[12]的地步。
嘉绒人的石砌技术传统由来已久,考古发现证实,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川西高原的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石砌房屋,产生了石砌房屋建筑技术。中路乡罕额依遗址的12层地层中除第1层耕土层外,几乎每层都揭露出石砌房屋,数量达17座。[5]房屋均为长方形或近方的“回”字形石、木结构,以石块为主要建筑材料。墙体有单层和双层。[6]从石墙房屋的整体面貌看,罕额依人已经掌握了片石砌墙技术,墙体砌筑过程中,注意墙体平面的平整度和内外、上下左右石块之间错缝叠压关系,石块之间的空隙处用小石块填充,①笔者1990年在中路罕额依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时所见到的房屋基址石墙砌筑的基本情况。用拌有草杆的泥浆作石墙砌筑的粘接剂和敷内墙壁。其间还发现多处含料礓石的黄土硬面,结构紧密,推测应为经过处理的房屋居住面。[13]保存下来的房屋多不甚高,一般在0.7-1.5米左右,仅第2号房屋F2高约2.5米。[13]石墙墙面平整,墙角端直,与现代砌筑的石墙大同小异。②同上。笔者推测,罕额依遗址中最早的房屋可能是石墙与木柱承重的单层平顶房屋,第二期的房屋可能已经出现两层平顶房屋。③笔者1990年在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时,在较早的地层观察到柱洞。另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在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执笔所写的《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村古代遗址调查、发掘工作情况汇报》中记载罕额依遗址的房屋“以石块为主要建筑材料,木头立柱和搭楼板”,据此笔者推测罕额依遗址中第一期的房屋为石墙与木柱承重的单层平顶房屋。在第二期、第三期的房屋内外有不少的石块,推测残存的石墙高度不是原始高度。双层石墙厚度达50厘米左右,砌筑技术精湛,石墙能承受较大荷载,笔者推测出现二层平顶房屋。
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罕额依遗址第一期的年代大致距今5000-4500年之间;第二期的年代大致距今4500-4100年之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距今3800-2000年之间。[5]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对地层堆积的描述,“第11层……此层下见F17,其叠压并打破第12层及生土”。说明房屋F17建于第12层,第12层又是中路罕额依遗址最早的地层。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一期的年代是从房屋F15、F17中采集的碳素标本测定的,[5]即是说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渡河上游已经出现了石砌房屋,丹巴中路罕额依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成熟、精湛的砌石建筑技术。
在建造石砌房屋时,“越是高大的石砌房屋建筑,越要求有十分精湛、成熟的石砌建筑技术。而精湛、成熟的石砌建筑技术,又是建造高耸的石砌碉楼所必需的前提”。[2]罕额依先民掌握的高超砌石绝技,是碉楼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式产生、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3000年以来,丹巴人在碉楼砌筑中大展身手,无数高大的碉楼在丹巴的山头、河谷两岸、村寨、关隘间耸立。丹巴成为大渡河上游碉楼的发源地之一,成为青藏高原碉楼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至今丹巴境内古代遗留下来的碉楼遗存仍有562座,为迄今整个青藏高原乃至全国碉楼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其根本原因正是有赖于丹巴罕额依先民形成和延续下来的源远流长的砌石技术传统。
[1]石硕、杨嘉铭、邹立波等.青藏高原碉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p24、p26、p34、p143、p235、p236、p238、p54
[2]石硕.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青藏高原碉楼分布所对应的若干因素探讨[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p387、p392、p393
[3]杨嘉铭、杨艺.千碉之国——丹巴[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p81、p79、p73
[4]徐学书.川西北的石碉建筑[J].康藏研究通讯,2001年第3期,p8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p60、p61、p68、p74、p76、p75、p68、p74
[6]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p182、p183、p177
[7]何永斌、邹吉辉、李生军、蒋秀碧.民族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p216
[8]童恩正.试论我国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A].王仁湘主编.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C].北京: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p201
[9]魏征、令狐德棻等.隋书·附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p1858
[10]林向.巴蜀考古论集《羌戈大战的历史分析——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族属》[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马长寿.嘉绒民族社会史[A].民族学研究集刊[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第4辑
[12]任乃强.西康图径·民俗篇 [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p253、p254
[13]丹巴县志编篡委员会.丹巴县志 [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p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