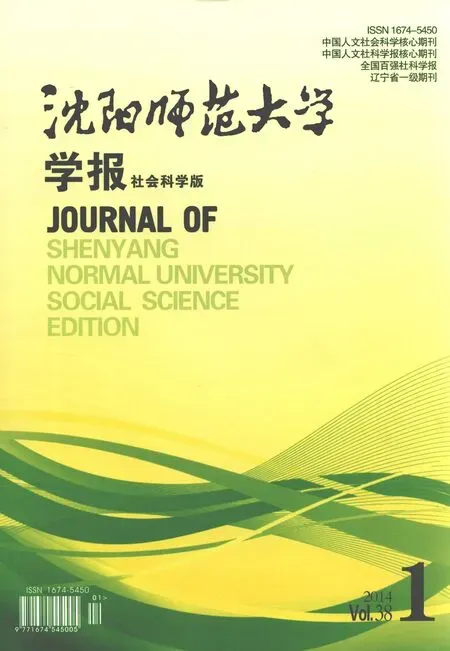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抗争精神溯源(1931—1945)
——以满族、朝鲜族作家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范庆超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32)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抗争精神溯源(1931—1945)
——以满族、朝鲜族作家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范庆超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32)
在1931—1945年间的中华抗战文学格局中,东北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异常突出的抗争精神。满族、朝鲜族、蒙古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作家纷纷以笔为刀枪,协力奏响了中华反帝抗战的最强音。其中,满族作家和朝鲜族作家在抗争精神的表达上表现出“集群”性的优势和更大规模的反抗声浪。这既受到反帝抗战普遍性时代风潮的感召,还源于满族、朝鲜族作家基于特殊历史境遇而生的故土情结、祖先意识、仇日情绪、自尊和耻感等民族心理。捋清这抗争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将有助于认识抗战时期东北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和民族特质。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满族作家;朝鲜族作家;抗争精神;溯源
在1931—1945年间的中华抗战文学格局中,东北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突出的抗争精神。面对东北故土的沦陷和日帝残酷高压的民族政策,东北的满族作家(端木蕻良、李辉英、舒群、马加、关沫南、金剑啸、田贲等),朝鲜族作家(尹东柱、李旭、金昌杰、申采浩等),蒙古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嘎莫拉、克兴额等),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等)等少数民族作家纷纷以笔为刀枪,控诉日帝的侵略罪行,并艺术复现了东北少数民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在东北少数民族作家这一创作群体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和遭逢,东北的满族作家和朝鲜族作家得以异军突起,发出了更大规模、更具典型性的反帝呼声。因此,本文试以抗战时期东北满族作家和朝鲜族作家的创作为中心,展示东北少数民族文学所表现出的雄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并考察这种抗争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
抗战时期的东北满族作家从活动区域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流亡关内的作家,包括端木蕻良、李辉英、舒群、马加等。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其歌哭呐喊自由放纵,反抗性十足自不必说。另一部分留守关内的满族作家包括关沫南、金剑啸、田贲等人,虽然身处沦陷区的暗夜,却依然表现出顽强的反抗精神。由于其反抗环境异常恶劣,所以这批东北满族作家“殉道般”的坚持尤为难能可贵。他们的不屈抗争,更充分证明了东北满族作家确是一个极富反抗精神的创作群体。沦陷区满族诗人金剑啸表现出的罕见的斗争勇气,“他在《大北新报画刊》上揭露哈尔滨警察厅的警备车在街上如入无人之境狂驱,压死7岁无辜小孩的兽行,斥责日伪当局查封进步刊物,实行文化专制统治的嘴脸。……他甚至在画刊上报道东北抗日联军和中国工农红军斗争的消息。”[1]长篇革命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更是以充满血气的文字,对金剑啸的反抗精神做了最有力的诠释:
是山崩,
是海啸,
抑是狂风骤雨的来到?
人与马的混嘶,
死亡在每个人头上飞绕……
诗的每一处都跳动着抗争的音符,“象进军的号角,似鏖战的鼓声,起着号召、鼓舞人民,揭露、打击日寇的作用”[3]。金剑啸凭借着这样的战斗诗篇,实现了他“山河破碎难提笔,画嘛,写嘛,就要画反抗,画斗争,写反抗,写斗争”[4]的诺言。更用其鲜血和生命,为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做了一个最有力的注脚。另一位满族诗人田贲,与金剑啸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诗风。在东北沦陷区的高压统治下,田贲组织具有强烈反日倾向的L.S(鲁迅)文学研究社(这个社团活动时间之长,是当时的文坛所罕见的[5])、发行抗日文学刊物《行行》、领导抗日文艺团体“星火同人”、发表大量反帝爱国诗歌……1944年被日本殖民者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46年牺牲于沈阳。田贲的诗歌澎湃着战斗激情,“特别是他在狱中和出狱后的诗作,带有明显的革命烈士诗抄的特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战斗性,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诗作”[6]。田贲极富反抗性的激情诗风酷似金剑啸,东北现代文坛素有“南田北金”之说。这两位满族的优秀儿女,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岁月里,共同发出了反帝抗战的铿然之声。
与东北满族作家的抗争怒吼相呼应,东北朝鲜族作家亦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反抗精神。年轻诗人尹东柱因大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族民众的深重压迫而惨遭杀害。“南朝鲜有的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把尹东柱称作宁死不屈的反抗诗人,认为他的诗作填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覆亡前的黑暗时期朝鲜文学史的空白,将他及其文学成就写进了朝鲜文学史”[7]62。还有学者从更深层面评价了尹东柱诗歌的反抗性:“尹东柱的诗作不是单纯的反抗诗,应当正确地把握它,把它看作从总体上揭示根源性的问题的反抗诗。”[7]62这也侧面说明了尹东柱反抗诗的彻底性和深刻性。其《序诗》《故乡的故居》《悲哀的族属》等诗作在展示民族苦难、歌颂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始终在寻找反日压迫的源动力。另一位朝鲜族诗人李旭同样充满斗争的豪情与血性。他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道:“生活,是劳动也是斗争。劳动创造生活,斗争改造世界。”[8]侧面反映出了诗人的“斗士品格”。有论者曾这样评价:“在李旭的诗作之中,最灿烂的一个部分是解放前写的那些诗。”[9]解放前的李旭诗歌之所以博得较高评价,正是因为它们所体现出的鲜明抗争性。
二
东北少数民族作家何以表现出异常强烈的反抗精神?原因大概主要跟以下两因素有关。第一,从对东北大地的情感来看,东北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满族作家对东北故土怀有深沉的挚爱。在历史上,满、蒙、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一直是东北大地的世居民族。他们长期生息繁衍于东北大地,自然对这方水土怀有深厚感情。特别是作为古肃慎人后裔的满族,已在东北大地生存几近两千多年。对这片黑土地的热爱已牢固深植于满族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而且,东北不仅是满族的发祥地,还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这种双重意义更是极大加深了满族人对东北故地的热爱。而这种热爱也必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渗入到抗战时期东北满族作家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
李辉英曾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一文中说道:“个人身为东北人,对于东北的沦陷,不能熟视无睹。别人可以不要东北,东北人可不能袖手。……做为生养在东北大地上的一份子,我不能放弃任何可以打击敌人的具体行动。”[10]这充分体现出李辉英强烈的故土意识。著名旅美画家、李辉英的东北老乡侯北人先生曾在《念李辉英兄》一文中,描述了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场景:“当我乘船离开海岛的那天夜里,他在码头上默默的交给我一包东西,说是留为纪念,待后来我打开时,我才知道那是一包土,一包土,一包黑色的土。在舱房中的暗淡灯光下,我面对着这礼物,我几乎流下泪来。”[11]可见李辉英对黑土地的挚爱是何等强烈!在李辉英那里,故乡是写不完、说不尽的,那是他永远的家园。
《小白山》关注故乡的历史。以一种温情笔调遥想满族的圣山。《江南公园》镜头转向故乡的杨林、花坞和渡口。《北山与庙会》里的钟声、晚风和浓雾泛起的是淡淡乡愁。《新年忆旧》《正月里》如数家珍般的民风描述中回荡着久违的乡情。《驴皮影》《水院子》那生气盎然地述说中渗透着作者对满族民俗文化的骄矜和自豪。特别是在《江南公园》中,李辉英用大幅笔墨描绘了家乡的“小威虎”。何为“小威虎”?在满语中,“威虎”(weihu)意为独木船。这种带有鲜明满族文化印记的故乡追忆,充分反映出李辉英对满族故土的深深眷恋。
端木蕻良对东北的黑土地同样充满了深沉挚爱。他曾在一篇创作自述中说:“在人类的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住了她。……在沉睡的梦里,甚至在离开了土地的海洋漂泊的途中,我仍然能闻到土地的气息和泥土的芬芳。”[12]很显然,端木将生养他的东北大地比作了母亲。有时端木又以“长白山的儿子”[13]370自诩,显出对满族故地的深情。纵然家乡的人事曾带给端木伤痛的回忆,但其对故土的本真热爱却依然不减:“说故乡带给我痛苦,那是由于人事,倘然单单专指风景,那也是美的”[14],“抬起含泪的眼我向上望着,想起了故乡的蔚蓝的可爱的天!……一个人对于故乡,‘这是不由心中选择的,只能爱的’”[13]372。这是端木作为一个满族作家对东北故地的真情告白。
马加对东北故乡同样怀有深挚的情感。他曾深情地说:“我终于回到故乡来了,但我的故乡却已沦为殖民地。这多令人痛苦。但人们的良心并没有泯灭,故乡的人民是会起而反抗的。我的命运是和故乡人民连在一起的。”[15]在《我们的祖先》这篇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里,马加更是异常鲜明地表达了对满族祖先、对白山黑水的挚爱与缅怀。
正是因为对生养自己的东北故园、对光荣的“祖先的故乡”的强烈热爱,才使得东北满族作家们在面对日帝侵略时,产生了“家园被占、族根被毁”的巨大失落感。正如马加所描述:“我们的祖先用血汗创造的产业已经丢失了,变成别人的财产了。……绝没有想到他们亲手开垦的土地后来会被敌人占去。……现在损失的不仅是我们祖先的产业,也是我们祖先的灵魂,在那个草原上再没有人唱着我们祖先时代的歌曲了,故乡的一切气象都显得消沉、破落与衰败”[16]74,75,77。这种强烈的失落感,必然促使抗战时期的东北满族作家们发出“反抗侵略、夺回家园”的黄钟大吕之音。
第二,东北少数民族作家对日帝怀有异常强烈的仇恨,这种仇恨必然燃烧其抗争怒火。就东北朝鲜族作家来看,其先辈大都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迁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先辈的“外来民族”意识、对朝鲜的国家认同感势必会影响到这些朝鲜族作家。另外,当时中国东北混乱动荡,这样的分裂形势也很难使其建立统一的“家国意识”。有学者曾谈到:“我国的朝鲜族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以定居于我国之日起就明确地划清了国家界限,清政府和东北军阀政府当年虽然曾在一个时期要求他们归化,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却曾把他们视为外国人。”[17]而且,中国朝鲜族作家和朝鲜人民拥有一脉相承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民族文化传统,这都使他们普遍看重朝鲜“故土”。故土被日帝所强占,故土人民饱受压迫和屈辱:“被日本帝国主义歧视为‘先盖’,过着连乞丐都不如的生活”[18]。而不甘当“亡国奴”、饱经背井离乡之苦、艰难跋涉至中国的朝鲜同胞们依然没有摆脱日帝的残酷蹂躏。据《朝鲜族简史》记载:日本侵略者在延边地区建立“集团部落”,实施“连坐法”,“动辄以‘抗日嫌疑’罪名,恣意对爱国人士和群众进行屠杀”[19]90。还制定了“自耕农创定法”,“把朝鲜族农民从封建地主的隶属关系转变为日本殖民者的隶属关系,从而肆意盘剥朝鲜族农民”[19]90,“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居住地区掠夺土地更加惊人……在日伪法西斯统治与疯狂掠夺下,朝鲜族居住地区与东北各地一样变成了人间地狱,人民过着牛马般的凄惨生活”[19]138。在陌生的大地上,移民同胞们遭受着如此深重的苦难,而故土的人民也依然在痛苦和屈辱中挣扎。这种“双重被压迫意识”极大加深了朝鲜族作家对日帝的憎恨。
再来看东北满族作家。他们的故乡、国土、“龙兴之地”被日帝蹂躏践踏,广大族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更让满族作家羞愤的是:日帝以他们的族名——“满洲”为旗号,麻痹满族民众,制造了“伪满洲国”这样无耻的历史骗局。满族本就是十分讲求自尊的民族,“好面子”是他们的民族习惯,所谓“注重名与耻”[20]。日帝制造“伪满洲国”的历史骗局必然会伤害满族作家的民族自尊心,令其倍感羞愤和耻辱。马加在很多作品中都或隐或显地流露出这种“羞愤”和“耻辱”。看《同路人》中的记述:
我看着那坐在汽车上的日本人,心灵中反映出一种羞愤的情绪;我用手指弹着衣裳,仍然走我的路。
营口,我还是第一次来。它从前是怎样我不知道,不过这一次给我的印象却是恐怖的,同时夹杂着一种令人酸痛的气氛,五色旗,标语,宣传图片,那一切都只能引起我的厌恶。任何一个中国人,一个有感情的中国人,都不会从那无聊的标语中引出啥快感来。似乎在这一条街上已经找不出多少中国的痕迹来,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太灰暗了!太消沉了![15]11
而《潜伏的火焰》则在嘲谑和困惑中突出耻辱感;
《我们的祖先》中的“耻感”更加直接而强烈:
对着那坟墓却是敌人的炮垒,他们的战旗骄傲的飘荡着,飞舞着,似乎在夸耀着夺取殖民地的胜利。这对于我们的祖先是怎样一种侮辱呢?那种侮辱也正是对着我们自己……每当我想到这里总有一种卑污的感觉……[16]79
这种“耻感”极大地加深了东北满族作家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流露出强烈的反抗精神。
总之,以满族作家和朝鲜族作家创作为主体的抗战时期的东北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抗争精神、奏响了中华抗战文学的最强音。这既缘于“反抗外侮,保卫家国”的普遍性的时代风潮感召,也与满、朝鲜这两个民族自身特殊的历史境遇、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1]申殿和,黄万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220-221.
[2]金剑啸.兴安岭的风雪.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诗歌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626-627.
[3]杨乃坤.东北文坛上的一颗灿星——东北革命文艺的拓荒者金剑啸[J].党史纵横,1993(6).
[4]李春燕.东北文学史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67.
[5]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7.
[6]陆地,关纪新.当代满族作家论[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87.
[7]任润德.略谈尹东柱诗歌的反抗性[J].延边大学学报,1992(2).
[8]戈勤,子金.李旭论诗歌创作[J].延边大学学报,1993(2).
[9]全国权,雨田.李旭民族史诗的历史地位[J].延边大学学报,1998(2).
[10]李辉英.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112.
[11]侯北人.念李辉英兄.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96.
[12]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端木蕻良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77.
[13]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端木蕻良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70.
[14]端木蕻良.有人问起我的家.端木蕻良代表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75.
[15]马加.同路人.马加文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20.
[16]马加.我们的祖先.马加文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73-75.
[17]郑判龙.浅议我国朝鲜族文化的性质[J].延边大学学报,1992(4).
[18]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4).
[19]朝鲜族简史[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90.
[20]鲍明.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295.
[21]马加.潜伏的火焰.马加文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33-34.
【责任编辑 詹 丽】
I206.6
A
1674-5450(2014)01-0025-03
2013-09-21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288)
范庆超,男,辽宁清原人,长春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