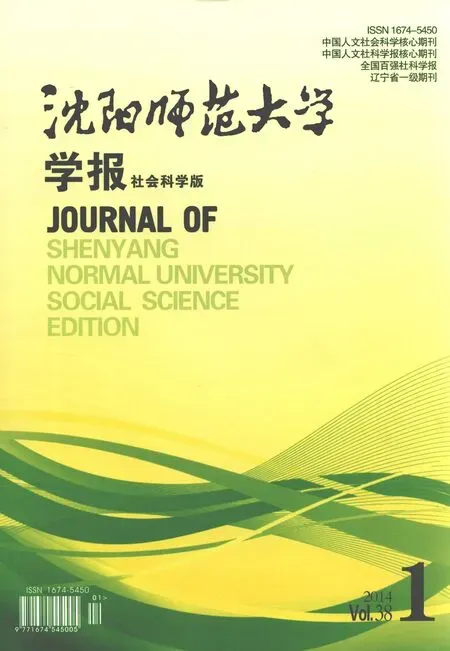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新视角
轩小杨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的新视角
轩小杨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近三十年,西方文艺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涌进国内学界,冲激进而占据很多学者的思维及话语。如今浪潮渐渐退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并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学科内涵以及话语范式,音乐美学就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从其哲学性质、人类学事实、艺术学前提这三重属性看,音乐美学与人的生存实践、生活样态、生存境界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因此,人的生存实践就成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不可忽视的新视角。
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生存实践
第九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2011年)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主话语及话语范式。各方学者围绕现代性进程、多元化语境、跨学科策略等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生态环境,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各抒己见,针对时下学科建设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与相关实践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使与会者对中国音乐美学的未来发展充满希冀,同时勃发使命感。时隔年余,思绪渐趋沉实,深感音乐美学的学科性质乃至音乐美学的中国化建设的问题尚需澄汰。毕竟,这是学科建设的根本问题。本人赞同韩钟恩先生提出的“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人类学事实与艺术学前提”[1]等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角度谈些意见。
一、从人的生存实践追问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
哲学究其根本属性乃在于对人的生存实践的反思、追问与回答。所谓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就是用哲学的思维与视角来研究音乐,回答音乐是什么?人与音乐存在怎样的关系?音乐具有怎样的价值和功能?这些价值和功能的存在形态及其判断标准是什么等等关于音乐艺术的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是音乐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更是对音乐之于人的存在的本质追问。
首先,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意味着音乐美学的理论根基应建立在人的生存实践上。无论是研究“音乐(的)美学”,还是研究“音乐美(的)学”[1],思维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都应落实在人的生存这一基本问题上面。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音乐美学的学术研究才会始终具有明确的方向与目标,即如何有效地提升音乐在人的生存实践中的意义与价值;也才会有缤纷的话题及话语的涌出,即如何多角度多维度地思考并构建音乐与人的合理性关系。尽管两百多年前,德国诗人、音乐家舒巴特的著作《论音乐美学的思想》出版,音乐美学才以学科的面貌出现,但音乐美学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光芒璀璨。众所周知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已经围绕音乐的本质、音乐的社会功用、音乐的审美标准等核心问题给予深具时代色彩与文化因缘的反思、追问与回答。不论是儒家的倡行礼乐,还是道家的推崇自然,抑或墨家的“非乐”,这些主张共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点,即所谓的“实践理性”[2]。
其次,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意味着以对音乐的哲学追问来观照现实的音乐实践。理论的生成源于实践,生成的理论也要能作用于实践。当我们聆听西方所谓后现代音乐时,对于其中的反形式、反美的美学倾向以及随意拼贴、什么都行的音乐概念泛化,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信仰危机所导致的审美逆反心理、现代科技广泛制造的虚拟空间所促生的对无机世界的审美探求、现代工业环境下艺术品的批量生产所带来的普遍的审美饱和等复杂因素,造成了人的审美活动的异化、音乐的异化;另一方面,音乐的美作为人的本质需要,美的音乐的基本元素何以倾覆,追根究底,是关于音乐是什么、音乐与人的合理性关系是怎样的这些基本认识被遮蔽,才使得在追求新异的旗号下制造出令人难以卒听甚至无以为听的“音乐”产品。这是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音乐本质与人的生存实质背离的必然的结果。
最后,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最终意味着音乐美学的学科构建,是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上,以理论追索引领艺术实践。音乐美学的发展不仅是理论家的事业,同时是音乐家的事业,无论音乐家还是理论家都应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综合素养。音乐家的艺术实践不仅是在外部世界的召唤下发生的,更应是在内心世界对音乐哲学的深刻追问中发生的。纵观历史上的伟大音乐家,无不是以深邃的艺术思想撼人心魄,同时以生动的音乐作品扣人心弦。
总之,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首先在于对音乐是什么、音乐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坚守这样的终极关怀,音乐才有意义,音乐的学术才有意义;这样的哲学追问更是学科构建的前提与基础,所谓学科话语缺失、话语范式零乱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二、从“田野工作”语境探讨音乐美学的人类学事实
作为音乐美学的姊妹学科,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性质一般被定义为:“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或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由于其内涵不断扩展,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又将学科主流倾向定义为:在地方性、区域性、或全球性的背景中,研究音乐的社会和文化方面。”[3]250显然,音乐美学与其有很大的交叉叠合处。韩钟恩先生曾引述赵宋光先生在《历史引发的美学思索》中提出的音乐学东西方研究的三个区别及需要注意的五对范畴,以及在《为在北京举行的2009音乐美学专题笔会拟订的讨论题纲》的相关内容,其结论是,“毫无疑问,这里提出的三个区别和五对范畴完全不限于美学论域,至少,有向哲学与文化人类学扩充的趋向”;“很显然,此讨论题纲已然越出传统音乐美学论域,不乏有诸多跨学科意义的艺术学前提与人类学事实。”[1]文本信息尤为显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音乐美学交叉叠合。如此,便涉及到对“田野工作”的再认识。
这里引据王耀华主编的《音乐学概论》对“田野工作”的描述:田野工作是指观察处在原地的人……早期曾研究口头传统的民族民间形式、异族农民社会的音乐、异国或原始民族的音乐、东方古典音乐体系,这些现在仍旧是流行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题日益丰富,既有内地遥远的少数族群,也有现代化、西方化的城市音乐生活、流行音乐和音乐工业。田野可以是地理区域或语言区域;一个族群;一个村庄、城镇、郊区或都市;沙漠或丛林;热带雨林或北极冻原。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档案馆和图书馆也是田野[3]251。
音乐美学的人类学事实决定了其对田野工作的依赖。但是,现如今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音乐美学的田野工作开展得不充分,甚至存在很大误区,留下很多盲区。比如,对少数族群的音乐研究大都交给了音乐人类学,对流行音乐、音乐工业的研究更多扔给了音乐社会学,至于当下城市音乐生活也似乎游离在研究者的视线之外,与如火如荼的“回馈”“反哺”等等艺术实践难相匹配的是理论研究的清冷。殊不知,现代都市音乐生活众相纷纭,亟待做出理论高度的澄清与梳理。比如,层出不穷的“超男”“快女”,排山倒海的大众粉丝,艳若昙花的劲歌慢曲,以及华山论剑般的歌手才艺大PK。凡此总总,营造出一个全民性的审美假象。之所以说“假象”,是因为,人们迷恋的,与其说是音乐,莫若说是传播媒介打造出的歌手的风光抑或风光的歌手;与其说媒体在推出歌手的同时,也在传播音乐,莫若说媒体借助音乐的审美之外的实用功能来实现收视率的攀升。当代媒体的强势使得音乐的广告宣传、移情宣泄等实用价值被强化更被漫衍,以至湮没了单纯的音乐审美功能,并在大众中引发广泛误读。再如,KTV练歌厅成了人们业余时间蜗居的主要场所;广告音乐的审美趣味、艺术品质及其价值追求不期然地影响到广大的人群;乡土文化、民间音乐在城市化进程与学院派演绎中悄然发生着改变……这些纷繁复杂的音乐现象,理应引起音乐美学研究者的深度关切,成为音乐美学研究的课题。如果研究者通识本学科的人类学事实,就不会有“议题危机”的出现,更不会有田野工作的闲置。从根本上说,音乐美学言说的对象就包括人类学所面对的此时、此地、此人(群)的真实的存在,这些构成音乐美学不竭的话语;音乐美学的话语范式就生成于与此相贯通契合的语言逻辑,成为立足于生活实在、构架于逻辑推演、成就于终极关怀的话语现实。
三、从人的生存境界确认音乐美学的艺术学前提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于所谓的“实践理性”,即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既如此,人的生存境界以超拔于生存实践的心灵体悟,成为中国文人的理想追求及中国文化的显明特点。
《乐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理论文献,其中不乏这样的表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4]此论不仅表达了对以“声”“音”“乐”为指称的不同艺术层次的认知,更指认了由“知声”“知音”而“知乐”所代表的不同审美层次,进而指示出对“众庶”与“君子”不同人格境界的评断与取向。显然,《乐记》的思想立足于人,力图在众相纷扰的现实中拨云见日,引领众人走向更高的生存境界。若剥离历史的外衣视其思想的内核,其智慧及努力堪可称道,实则指明了为今人所困惑的音乐美学本该坚守的一个研究方向,亦即探讨音乐之于人生的指引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因于文人的自觉还是始于为政的理性,在社会生活中,音乐怡情悦性以至移风易俗的“教”与“化”的功能均受到重视并引以实践。先贤孔子每日“弦歌不衰”,以乐成性,实现其“从心所欲不愈矩”[5]12的人生境界,而成就人世丰碑;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智识其影响又何止千年。
在如今多元开放的中国,音乐产品层出不穷,大众品赏也是随心所欲,应和了一般艺术理论所谓艺术生产与艺术鉴赏的双重“主体性”,亦即《乐记》所云“众庶知音”“君子知乐”。然而,面对时下艺术生产中泛滥的怪异、低俗之“音”与单薄、势弱之“乐”,以及艺术消费潮流中的“审丑”趋向,音乐理论工作者却未能及时有效地发出像古圣先贤“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5]164“恶郑声之乱雅乐”[5]187般的感慨与疾呼,而彰显文人的智慧与担当。当然,必须澄清的是,“放郑声”的主张自有其历史局限,其狭隘与保守早已为世人所洞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引导作用以及对后世文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反观现今,在纷繁复杂的音乐现象面前,当代音乐理论工作者却失语了,音乐美学的这一方价值与意义被自我悬置。
进入21世纪,古老的中华文明走向复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神舟”飞船相继升天,伦敦奥运会奖牌总数世界第二,世界富豪排行榜中有不断增加的中国人的身影……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百姓的生活水平正在节节攀升。与此同时,一连串的事件却极不和谐地充斥眼前与耳畔:小悦悦事件、彭宇案件、地沟油、染色馒头、致癌牛奶等现象频频发生,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所面临的人心疏离、情感扭曲、诚信缺失、道德错位、文化贬值、金钱至上的社会问题,并开始意识到,这些在记忆中本来属于“西方自由国度”的现象,而今已悄无声息地就在自己的身边,甚至在心灵深处落脚了。肩负社会先进文化的引领者之重责的文人,对此是否有所反思?又该有怎样的作为?如果说,我们曾经一如众多国人,面对改革大潮席卷而至的西方各种哲学思潮、文艺流派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长期闭锁的心灵被撞击,过去不曾质疑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被撼动,于是沉陷其中,“与狼共舞”,那么,狂欢过后,我们是否还能拾回一丝冷静,复苏一度休眠的心灵触觉?
音乐,作为艺术家族中的一员,不论对其作怎样的“感性的抽象”[1]的新表述,抑或“艺术的先验性”[1]的再思考,其“感人至深,化人最速”的基本特性,尤其需要人们对其如何发挥“兴、观、群、怨”[5]185等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给予高度重视。当然,经历了历史的淬炼,人们早已明了,乐教不是政治的代言,音乐的选择本该从属于个人的价值取向,但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理论先导的力量,以文人对文化的自省、自觉与自信,引领大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提升审美品格,从而提升其生存境界呢?所以,对于韩钟恩先生提出的“艺术家是不是人类奢侈品的最后生产者?艺术学家又是不是人类奢侈品的最后消费者?”[1]的设问,我的回答,或许应该说,我的理想答案是否定的。
由此可见,音乐美学的学科建构,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无论是音乐美学哲学性质的追问,还是人类学事实、艺术学前提的探讨,都应立足于人的生存实践,在人与音乐的关系、音乐对于人的价值与功能的实现等基本问题上展开持久而深入的研究。理顺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广阔无比、蕴藏深厚的学术世界。
[1]韩钟恩.音乐美学的哲学性质、人类学事实与艺术学前提以及音乐本质力量的先在性——由2011第九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议题引发的三个讨论与进一步问题[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1(9):5-12.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88.
[3]王耀华.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276.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J601
A
1674-5450(2014)01-0159-03
2013-11-25
轩小杨,女,辽宁彰武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文艺学博士。
【责任编辑 赵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