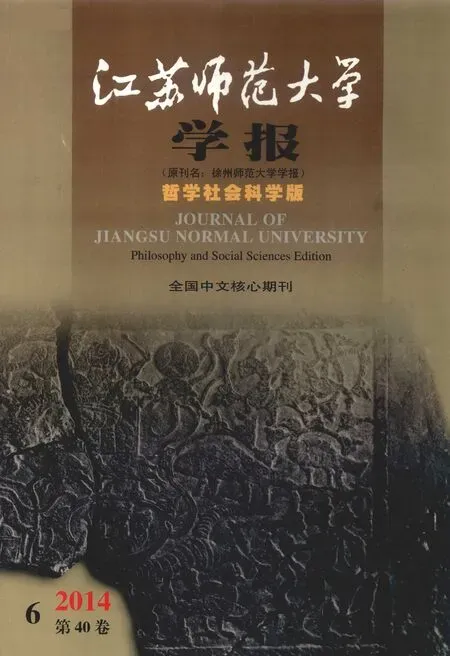敦煌写本曲子辞抄写年代三考
张长彬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敦煌写本曲子辞抄写年代三考
张长彬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2)
敦煌曲子辞;抄写年代;《云谣集》;斯2607;伯3128
抄有《云谣集》的斯1441、伯2838以及保存了大量曲子辞的2607、伯3128是最重要的三种敦煌曲子辞文献,这三种曲子辞文献的抄写年代问题尚未最终解决。通过伯2838斋文中的“令公”一词结合斯1441中的相关信息,可以推知《云谣集》抄写于928年至935年间或稍晚。通过对斯2607两面文书正背面关系的考查,再结合该卷点检历中相关僧人的生平,可确定斯2607之曲子辞抄写于十世纪中叶左右。通过伯3128中三首《望江南》与伯4889定千诗相互关系的考查,可得知伯3128之曲子辞的抄写年代上限为944年。
据统计,敦煌遗书中保存着53个敦煌曲子辞写本。这些写本一般不具有直接而明确的时间标志,学界对其抄写年代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作品的抄写年代,是讨论其他问题的前提,故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研究。《云谣集》写本(斯1441、伯2838)及保存了大量曲子辞的斯2607、伯3128写本是最重要的三种敦煌曲子辞文献:《云谣集》共存辞30首(斯1441抄18首,伯2838抄14首,其中两首二本互见),斯2607存辞29首,伯3128存辞15首。本文拟对此三种曲子辞写本文献的抄写年代予以重新考证。
一、《云谣集》抄写年代
《云谣集》写本的抄写年代历来分歧不大。1950年,王重民考云:“原卷(伯2838)一面写中和四年破除历,一面写金山天子时代所用之杂斋文式。此《云谣集》即接书于杂斋文式之后。笔迹虽不同,其书写年代,不应距金山天子太远。金山天子与朱梁一代相终始,故可视为梁唐间写本。”[1]这一结论现已成为学界较通行的观点。汤涒的观点与王重民稍有不同,认为《云谣集》“最迟当抄在公元910-914年之间”,而所持的根本证据也是所谓金山国时代的斋文[2]。
事实上,伯2838与《云谣集》同抄于一面的斋文中,除“我金山圣文神武天子”(该本背面第五文)一句带有金山国时期的信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名词——“令公”。“令公”是仅见于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节度使封号,使用时代晚于金山国。该词屡次出现在伯2838背面的第五、六、七三文之中,而幸运的是这三篇斋文还有另一种抄本伯3765。经对比可发现,凡伯2838作“令公”者,伯3765作“金山白帝”或“金山天子”。由此可知伯2838的这三篇斋文乃抄自金山国时期的写本,抄写时则以当时习惯替换了金山国时期的用语,或许由于抄写中的疏忽,所以还保留了“我金山圣文神武天子”字样,与“令公”并存。据荣新江考证,敦煌历史上享有“令公”称号的节度使有曹议金(928-935)、曹元忠(956-960)、曹延恭(975)、曹延禄(984-1002)四人[3]。因为斋文中毕竟还残存着金山国的信息,故可断定其抄写年代距金山国不远,其中的“令公”当是指曹议金,这些斋文应抄写于928-935年间,时属后唐。这样一来,位于斋文之后的伯2838本《云谣集》也应抄写于这一段时间或稍晚。
斯1441本《云谣集》的抄写时间应与伯2838同时。对比两本《云谣集》的笔迹可发现:伯2838本之《凤归云》2首与斯1441本18首辞的笔迹相同,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潘重规曾指出这一点:“余曾细观巴黎伯二八三八卷凤归云二首笔迹与伦敦斯一四四一卷云谣集相同,盖一人所书。”[4]另外,《云谣集》篇题中所标明的首数是30首,而两个抄本去其重复抄写的2首《凤归云》恰好与之相符,这些情况都说明:斯1441、伯2838应为同一群人于同一时地按顺序抄成。
两本中的其他一些信息也可以佐证这一结论。斯1441背面右端先后抄有两件《二月八日文》,分别位于背面的第一位和第三位,第一件《二月八日文》内有“河西节度使尚书”字样,第二件《二月八日文》内并见“仆射”、“大唐”字样。由于两文笔迹不同,它们应是在各自应用之后不久分别抄入的,所以透露了真实的时代变迁信息。由于两文位置相距很近,所以抄写的时间跨度应该不大,在这段时间中,“尚书”、“仆射”这两个节度使称号应是相继出现的。经查归义军时期节度使先称“尚书”继称“仆射”的时代有三段,分别为张议潮(848-858称尚书,858-861称仆射)、张淮深(872-890称尚书,887-890又称仆射)、曹议金(914-920称尚书,920-924称仆射)在位期间[5],这两件《二月八日文》的抄写时间应在这三个时代中的一段,而《云谣集》的抄写则在这一段时间之后。上文我们曾说到伯2838的斋文抄写于归义军节度使称“令公”时期,而敦煌历史上称令公的有曹议金、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四人。现在将两种时间信息进行复合比对,符合所有条件的年代就只有曹议金时期了。
综上所述,斯1441、伯2838之《云谣集》曲子辞的抄写年代应在928-935年间或稍后。
二、斯2607曲子辞抄写年代
斯2607长卷一面抄曲子辞,另一面抄“金光明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要考察斯2607所载曲子辞的抄写年代,需先辨明以上两种文书的正背面关系。现今的各种目录、文献集成以及相关著述均把点检历一面当作背面,未见有异议者。本文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点检历一面实为正面。理由如下:
首先,以同类文书对比来看,曲子辞集一般多抄于卷子背面,而什物历皆写于正面。
宽泛地说,除斯2607以外,敦煌遗书中具有曲子辞集形态的长卷还有如下几号:
1.斯1441,《云谣集》杂曲子18首,抄于《励忠节抄》卷背。
2.伯2838,《云谣集》杂曲子14首,抄于两件寺院破历会算牒卷背。
3.伯3128,曲子辞15首,抄于《大佛名忏悔文》卷背。
4.斯6537,歌辞集,20首,内有部分曲子辞,抄于《金刚映序》卷背。
5.伯3271,内容同斯6537歌辞集,13首,抄于《论语集解》卷背。
6.津艺134,曲子辞13首,抄于《维摩诘所说经》卷背。
7.伯2809,曲子辞11首,分两处抄,两处字迹不同。第一处8首,抄于《道安法师念佛赞文》之后,自正面抄起,转至背面;第二处3首,抄于背面。
从以上各本来看,敦煌遗书中的曲子辞集一般都是抄于各种文书的卷背。与斯2607情况尤其相似的是伯2838,其《云谣集》杂曲子亦抄于会计文书之背。唯一例外的是伯2809,但该卷乃是表演伎艺底本的合抄本,全卷文书为同一层面上的事物,不分主次;且其卷幅较窄,从形式到性质均与上述写卷不同。这些材料说明敦煌遗书中现存曲子辞集凡与不同性质文书抄于一长卷者,均位于卷背。
下面再来看寺院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的抄写情况。《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收录了寺院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共16件,除斯2607以外,还有伯2706、伯2613、伯5031(16)、斯5899、伯3495、斯1774、伯2917、斯4199、伯3598、伯4004+斯4706+伯3067+伯4908、斯4215、伯3161、斯6217、斯1776、斯1624诸号[6]。其中前12号之点检历均为单面独立文书,另一面无文字或有少量非主题杂写。斯6217号之交割常住什物历与分付常住什物历及破历合抄,形式稍显特殊,其背面也是仅有少量杂写。斯1776点检历亦抄于正面,其背抄有《历代法宝记》。唯斯1624之点检历《英藏敦煌文献》以背面文书收录,并将另一面著录作“杂抄”。其他目录与文献集成亦将此号点检历定为背面。查看原卷可知,该号之点检历仅余中间一段,前后均因卷子断裂而佚失,而另外一面除了有《英藏敦煌文献》所提到两件文书以外,还有两个草书大字。从内容上来看,斯1624被《英藏敦煌文献》著录为正面者诚如其所拟之名称那样,实为“杂抄”;从形式上来看,该面文字未有佚失,显然为原卷已断裂后抄入。综合这些因素可知,斯1624什物点检历一面也应为正面,诸目录及文献集成皆误。
以上现象说明,寺院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乃是严肃的会计文书,它总是抄写于卷子正面;而曲子辞集却总是以旧卷的背面来抄写。此外,斯2607点检历的自身形态也能说明它是一件严肃的文书,其抄写时间必早于另一面的曲子辞集。这件点检历的书法虽然相对于另一面的曲子辞较差、较潦草,但它留有两字余的天头且无地脚,行款与同类正规会计文书相当。另外,文中有修改的痕迹,说明它是实用文书而不是抄件。它还有朱批,说明它是经过上级人员审批过的,通常情况下它的审批者是都僧统。这些特征都说明它是一件严肃的办公文书,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抄于旧纸之上。从物理特征上来看,点检历一面墨迹脱落远较曲子辞严重,这第一说明点检历的年代更加久远,第二说明在此卷的生命周期以内,人们是长期把曲子辞当作内面而把点检历当作外面来保存的。后一点暗示着该卷的保存者更加珍惜曲子辞一面的内容,若曲子辞一面为先抄,也就没有理由再拿去抄写别的文书。
根据以上证据可以确定,抄有点检历的一面为卷子的正面,曲子辞集一面为背面。因而,点检历的制作时间便是曲子辞抄写时间的上限。
以下进入点检历制作时间的考查。该件点检历中出现了若干僧名,其中道政、法真二人生活年代可考。道政,妙智《英藏敦煌遗书人物小考》一文有所考证。该文证明此人乃是生活于10世纪初的金光明寺僧人,还据此将斯2607点检历定名作“金光明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7]。
法真,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对其有小考[8],后来郑先生又将其小传写入《敦煌学大辞典》,其文曰:“五代沙州僧人。俗姓马。初住龙兴寺。早年曾至伊州游学。后唐同光四年(926)出任金光明寺寺主。”[9]郑先生根据撰写于乾宁三年(896)的《唐沙州龙兴寺上座马德胜和尚宕泉创修功德记》(斯2113)内有“弟僧龙兴寺临坛大德法真”知法真姓马,是龙兴寺僧。又根据斯6417《同光四年(926)金光明寺徒众庆寂神咸状》知法真于同光四年任金光明寺寺主。郑先生认为这两件文书中的法真是同一人,并据此断定该法真先住龙兴寺后入金光明寺。本文认为,这两件文书的法真乃是两人。作出这一判断的证据有二:
第一,二法真的出身和文化程度不同。斯2113关于法真的描述语句为:“龙兴寺临坛大德法真,威仪冰操,不若纤尘;戒护鹅珠,澄清转洁。”对于其父的描写为:“敦煌县耆寿,讳太平,字时清。孝悌承家,闲居得志。履谦恭于乡闾,慕直道于前贤。风响许由,不移名利。”对其伯的描写为:“前三窟教授,法号法坚,可为缁林硕德,顿悟若空,弃舍嚣尘。”其兄时为龙兴寺上座,此文对他的描写为:“精闲六礼,明达藏经;谈演多机,伟貌清肃……”由此可见,此法真应出身于当地大族。而斯6417之请法真为寺主的状文对于法真的描写则是:“自己生于卑劣,终日敬重尊人。每亦修身护行,不曾随从恶人。虽然少会文字,礼法不下于庶人。”都僧统海晏对此法真的评价亦不甚佳,其批复曰:“尚自凡僧,寺徒来请,众意难为,便宜了事。”两文对比可知,同光四年(926)方任寺主的“凡僧”法真绝不会是30年前(乾宁三年)就已被称为“临坛大德”之法真。
第二,二法真的年龄不合。龙兴寺法真乾宁三年(896)已称“大德”,其年岁当时应已不低。有两条证据:第一,其兄德胜大中五年(851)已出任龙兴寺寺主[10],乾宁三年必已高龄,法真与其岁数相差应不会太大。第二,在据考写于895至902年间的斯2614《沙州诸寺僧尼名簿》[11]中,法真名列龙兴寺僧第三位,仅次于翟僧正和威净,而高于法律、判官等僧官。古代有敬重老人的传统,法真作为一名无官衔的僧人排位如此靠前,应与其年高有关。这样一个年高位重的“大德”法真不可能在30年后又任金光明寺寺主。寺主虽说通常为三纲之一,但该职在当时的敦煌地位应不高,因为当时的敦煌一所寺院不止一名寺主。斯2607点检历中就出现了石、阴两位寺主,更有甚者伯4004等号所载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中竟然出现了保惠、明戒、明信、定昌、善清、教珎、法浄、法兴、戒惠、明藏、员会、保藏、法清、法林等14位寺主,这说明当时寺主的地位何其普通也!
由此可知,龙兴寺法真与金光明寺法真乃不同时期的两位僧人,龙兴寺法真在9世纪末年事已高,不可能于30年后出任金光明寺寺主,斯2607点检历中的法真应为金光明寺法真。金光明寺法真于同光四年(926)方任寺主,而在这件点检历中他还是以普通僧人的名义出现的,故该点检历的书写时间当在同光四年(926)之前,这一时间也就是其背面曲子辞集抄写的时间上限。寺院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是重要的会计文书,应当有一段时间的保密期限。按照其功能,它至少应在相关部门(应为都司)保存至下任寺院管理者到任为止。曲子辞集的抄写需等到点检历解密之后,其时代应在10世纪中叶左右。
三、伯3128曲子辞抄写年代
伯3128卷并无直接的抄写时间信息。因该卷部分曲子辞多涉历史事件,前贤便以之附会史实,轮番考证了其中大部分作品的创作年代,并以作品的创作时代来为写本断代。这类考证主要见于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半塘《敦煌曲初探》与《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敦煌曲》、苏莹辉《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12]、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等著述。笔者曾列表对比过各家考证之结论,发现几乎每一首作品的创作时间都分歧很大,有的结论竟相差一二百年[13]。这一现象说明,作品年代的考证不可仅依据作品内容的片断来进行推测。
与之相反,当我们获知了作品的创作背景之后,它的创作时间就有了被科学认识的可能。如今,我们恰好发现了一条材料可以表明本卷所载《望江南》之“龙沙塞”、“敦煌县”、“边塞苦”三辞的创作背景,由此可以推导出它们的创作年代。
这条可证明以上观点的材料是写于伯4889的一首诗,作者为定千,其诗云:
况说龙沙最边陲,关河阻隔远明时。蕃戎把隘当路坐,何日申奏圣人知。今遇司空来宣问,枯林滋润再生枝。四面六蕃多围绕,伏恐寻常失朝仪。若不远仗天威力,只怕河湟陷戎夷。请须司空奏论事,封册加官莫改移。比至来秋新恩降,山林草木总光辉。塞上艰辛无说处,一心目断望龙墀。
该诗还有序文,以下根据需要选择引用。为便于对比,兹以原卷之顺序再录伯3128三首《望江南》词如下(录文对原抄讹误处已作校改):
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隍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
龙沙塞。远路隔烟波。每恨诸蕃生留滞。只缘把截寇雠多。抱屈争那何。新恩照。圣泽遍天涯。大朝宣差中外使。今因绝塞暂经过。路次合通和。
边塞苦。圣上合闻声。背蕃归汉经数岁。常闻大国作长城。金榜有嘉名。太傅化。永保更延龄。每抱沉机扶社禝。一人有庆万家荣。早愿拜龙旌。
上引两种作品有许多语句相同或相近,李正宇认为定千诗乃袭《望江南》“敦煌郡”篇之辞而作[14],徐俊则认为《望江南》“敦煌郡”词乃隐括定千诗而成[15]。我们认为徐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下文有证。
事实上,《望江南》隐括定千诗的语句不仅见于“敦煌郡”一篇,还见于“龙沙塞”、“边塞苦”二篇。“龙沙塞”篇之上片之“龙沙塞。远路隔烟波。每恨诸藩生留滞。只缘把截寇雠多。抱屈争那何”,基本上可以对应于上诗之“况说龙沙最边陲,关河阻隔远明时。蕃戎把隘当路坐,何日申奏圣人知”等句。该词之下片“新恩照,圣泽遍天涯。大朝宣差中外使,今因绝塞暂经过。路次合通和”诸语虽未见于上诗,但却是对诗序中“今则我□当今皇帝,临轩西顾;照绝塞之黎民;远遣使臣,宣皇猷于边上”的隐括和补充。任半塘先生曾敏锐地发觉该词上、下片内容不甚衔接[16],原因即在于该词乃分别隐括诗之正文和诗序而成。词人为何在下片中生硬地加入了诗序中的内容?原因在于诗之正文中的多数语句已被隐括入词,余下的诗句不足以再隐括出下片,无奈之下,词人就加入了诗序中的内容,导致了上下片的主题分离。这个现象就证明了我们上面的观点,即词乃隐括诗而成,并非诗袭词而作。另外,“边塞苦”篇开端二句在定千诗中也有对应之语,该词起首二句为“边塞苦,圣上合闻声”,与诗中的“塞上艰辛无说处”、“须请司空奏论事”两句意义相合。该词后面的语句与诗无关,乃词人自创,这是因为前诗至此已无可隐括之句,所以词人只好补入了其他内容。从“龙沙塞”一词已知该词人的谋篇能力确实不高,这一弱点在此词中再次显现。此词的起句既为“边塞苦,圣上合闻声”,接下来应当是铺叙塞上艰辛的内容才符合主题。但原词接下来的语句却是“背蕃归汉经数岁,常闻大国作长城。金榜有嘉名。太傅化,永保更延龄。每抱沉机扶社禝,一人有庆万家荣。早愿拜龙旌”,与“边塞苦”之主题统统无关。这一现象可以说明该词的前二句与后数句之间的写作情形发生了变化,它们要么是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写作,要么是隐括了不同的作品,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无法抹去其前二句隐括了定千诗的事实。
如此以来,定千诗与3首《望江南》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信息互补互证的关系。从定千诗可以确知该诗写作于中原皇朝使节来访之当时,来使具有“司空”头衔;从3首《望江南》可知,这次使节来访并非是对敦煌的专访,而只是从敦煌这一绝塞“暂经过”,是其使团的“路次”(路途之中)事件,这一顺便访问的目的是“合通和”(商谈往来和好之事),而和谈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敦煌一方“愿拜龙旌”。将这些信息与敦煌史实相比较,恰好与后晋册封于阗使张匡业的到访相符。张匡业西来的任务是册封于阗国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来回途中两次经过敦煌,时间分别是天福四年(939)8月和天福七年(942)11月,第二次到访时敦煌曾遣使随其同赴晋廷[17]。这些事实都与诗、词内容相符,唯具有司空头衔的访敦煌使节在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中都无记录。《新五代史》卷七十四云张匡业原为供奉官,假鸿胪卿出使。历史上鸿胪卿的级别浮动于三、四品之间,但此次出使是为了册封国王,而且当时司空只是荣誉官衔,所以张匡邺当时拥有司空头衔也不无可能。
以上事实证明,伯3128三首《望江南》的创作时间上限当为张匡业第一次到访的天福四年(939)8月。由于《望江南》曲词中又有“太傅化”之句,939年之后敦煌第一次出现太傅称号的时间是944年[18],因而该卷的抄写时间下限当为944年。
[1]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6年修订版,第99页。
[2]汤涒:《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3]括号内的年代为该节度使称“令公”的时间。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
[4]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石门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39页。
[5][17][18]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129、21-23、130页。
[6]唐耦耕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9-48页。
[7]妙智:《英藏敦煌遗书人物小考》,《法源》,2004年号总第22期。
[8][10]参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315、314页。
[9]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11]该名簿中有“康僧统”字样,乃贤照,于895-902年间在都僧统位(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292页),故此名簿当写于此数年之间。
[12]苏莹辉:《论敦煌本〈望江南〉杂曲四首之写作时代》,原发表于新加坡《新社学报》1973年第5期;又载其《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115-128页。
[13]参张长彬:《敦煌曲子辞写本整理与研究》,扬州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打印本,第80-81页。
[14]李正宇:《敦煌遗书宋人诗辑校》,《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15]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38-839页。
[16]任二北:《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58页。
Three Textual Researches on Copying Time of Dunhaung Quzici
ZHANG Chang-bin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Dunhuang Quzici;copying time;Yunyaoji;Stein.2067;Pel.chin.3128
There are thre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of Dunhuang Quzici——Stein.1441 and Pel.chin.2838,the manuscripts of Yunyaoji and Stein.2607 and Pel.chin.3128,whose copying time was still unknown.By the evidence of the word——“Ling-gong”an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evidences to infer that Yunyaoji was copied between the years 928 and 935 or later.By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tein.2067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monk’s life from the document inside Stein.2067,we conclude that the copying time of Stein.2067 is at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ary.By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pieces Wanjiangnan in Pel.chin.3128 and Dingqian’s poem in Pel.chin.4889,we could know that the copying time of Stein.2067 is after the year 944.
I276.6
A
2095-5170(2014)06-0018-05
[责任编辑:邵迎武]
2014-09-21
张长彬,男,安徽萧县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