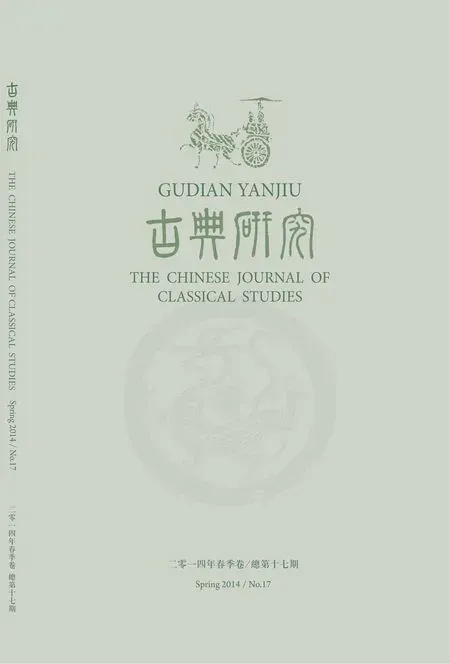皮科致巴爾巴羅信中的雙重面具
徐衛翔
(同濟大學哲學系)
皮科致巴爾巴羅信中的雙重面具
徐衛翔
(同濟大學哲學系)
修辭學與哲學之爭,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傳統主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古典修辭學的復興,爲這古老的問題增添了新內容。1485年,哲學家皮科與人文主義者巴爾巴羅之間的通信,突出反映了這一時期哲學與修辭學的衝突。巴爾巴羅抨擊經院哲學家的文體,皮科在回信中假托某個經院哲學家之口,以雄辯的語言,爲經院哲學家們的智慧以及他們的文體做了辯護。學術界通常認爲,這位“經院哲學家”的話反映了皮科本人的立場和態度。近些年來,另有學者從修辭學的角度,認爲皮科的“經院哲學家”只是一副面具,他對經院哲學的辯護是一種悖謬式讚揚,其真實立場與巴爾巴羅等人文主義者並無區別。本文認爲,皮科的信有雙重的面具:他以“經院哲學家”面具所表達的,是他真實的思想;而他以第一人稱所說的話,是另一副面具,用以掩飾其想法,減輕其衝擊。因而,這些修辭學研究者的看法是片面的,雖然他們的研究方法很有借鑒意義。而傳統上對皮科書信的評價大體上是可靠的,只是有些簡單化。
Author:Xu W eixiang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E-mail:xuweixiang@yahoo.com一
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古典修辭學在十四和十五世紀的復興。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昆體良等古代作者的修辭學、雄辯術或者演說術的著作,被重新發現,且譯爲(或再譯爲)拉丁文,一種被人文主義者們古典化、精緻化了的拉丁文,而後則被譯爲各種歐洲民族語言。通過這種“傳播與接受”(diffusion and reception),西歐的文學、文化以及教育得以改變,其影響流布於今。
修辭學作爲一門關於言說的學問,與哲學、科學一樣,也是希臘理智(以及實踐)文化的特質之一。而從其實踐性的一面來看,它對後世西方文化的影響,甚至可能比前兩者更大。修辭學與哲學的關係,自古希臘以來,在整個西方思想史上便錯綜複雜,甚至夾纏不清。從原則和理念上說,兩者的區分還是比較清楚的:哲學探索真理,尋求確定性、必然性的知識,而修辭學往往關注意見,滿足于或然性、莫須性(probability)的東西;哲學從事教導,教導人去發現永恆的事物,而修辭學關心的是勸導、說服;哲學可能會與政治事務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修辭學則一頭紮到俗世之中,悠游於法庭論辯、政治商議、節慶典禮;哲學對少數人說話,期待的是他們的理智以及求真的意願,而修辭學則跟大眾打交道,玩弄的是他們的情感、信念以至軟弱;哲學一般只會說老實話,從外表看沒有絲毫的神奇之處,而修辭學則神通廣大,能隨意改變事物的形像,左右人們的內心,無怪乎教會早期的一些護教士,對哲學恨之入骨,用起修辭學來倒可能手段嫺熟。然而,兩者實際的關係遠不是這麼分明。任何一部古代修辭學文選,可能都要收入柏拉圖的《申辯》。修辭家的功夫,哲學家有時也要用一用,甚至比他們用得還好。後世的許多哲學家,說不定其實是修辭家,並且這一點可能連自己都不知道。
修辭學的復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時人對哲學的看法。十四、十五世紀,既有經院哲學的餘緒,又有人文主義的肇興。所謂帕多瓦(Padova)與佛羅倫薩(Firenze)之對立的說法,雖然在二十世紀廣受批評,從大線條上來看,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但畢竟,人文主義思想,尤其是修辭學的興起,使人們的哲學視野不再限於經院哲學、(老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有些人文主義者甚至認爲自己比(傳統)哲學家哲學做得更好。
1485年,就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鼎盛時期,在當時大哲學家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和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翻譯家、威尼斯主教及元老院成員巴爾巴羅之間,發生了一場重要的通信。他們之間的通信,用巴爾巴羅的話說,是關於哲學家的言說方式(de genere dicendi philosophorum),在當時是文人圈子的一樁大事,也構成了哲學與修辭學之爭新的一頁。
在十五世紀意大利的思想家中,皮科常被稱作是“文藝復興的象徵”。作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最有獨創性、也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被視作文藝復興哲學的代表當之無愧。但是,這一稱號的豐富含義,需要建立在對其思想全面深入的研究之上。如果僅僅因爲他寫了《論人的尊嚴》,便認爲他作爲人文主義的代表,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張揚人性,貶抑神性,主張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云云,則可能與事實相去甚遠,不得要領。
儘管皮科只活了短短31年,但天賦、家世、以及勤奮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使他少年時便躋身於當時意大利乃至整個西歐一流思想家之列。他的思想活動,幾乎涉及當時學界的每一個方面,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其他人。人文主義、修辭學、柏拉圖主義、亞里士多德主義、經院哲學(盛期經院哲學及晚期經院哲學)、希臘與羅馬時期的文學、希伯來語言與思想傳統、阿拉伯哲學、秘傳智慧、甚至自然科學,在所有這些領域中,均留下了他探索的足跡,但每一個領域,甚至全部這些領域,似乎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思想。即以《論人的尊嚴》而言,便根本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著作。
巴爾巴羅(Ermolao Barbaro,1454-1493)出身於威尼斯望族,一家數代人,連同他自己,都在學術、政治、教會、外交等多方面起過重要的作用。他先後在維羅納、羅馬、帕多瓦等地求學,因其詩作被腓特烈三世授以桂冠,二十多歲時便出任帕多瓦大學的哲學教授。他還擔任過威尼斯共和國駐米蘭和教廷的大使。1491年,因其才華出眾,教宗英諾森八世(Innocent VIII)提名他擔任阿奎萊亞宗主教(Patriarch of Aquileia),以大使身份接受國外的任命,此舉違反了威尼斯共和國的有關法律。他遂被故鄉撤職、流放,並罰沒財產。巴爾巴羅的學術貢獻主要在於翻譯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政治學》、尤其是《修辭學》,以及忒彌斯蒂烏斯(Themistius)的亞里士多德著作注疏。
他們的通信可簡述如下:1485年四月,巴爾巴羅寫信給皮科,在信中他斥責經院哲學家爲粗野、遲鈍、缺乏文化,是蠻族(rude,dull,uncultured,barbarians),他不認爲他們能夠不朽。皮科回復了一封雄辯的長信,爲經院學者辯護,說他們是哲學家,也是不朽者。而且他提出,哲學高於修辭學,兩門學科互不相容。
在學術史上,這場爭論中無論是皮科還是巴爾巴羅的形像和立場似乎並不成問題。二十世紀的大思想史家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在他四十年代著名的論文中,討論了皮科所理解的哲學,以及他對人文主義者們工作的態度,
“從哲學上說,也就是說,在最普遍的意義上就對真理的追求而言,而不是從語文學上來說,皮科試圖探尋本質上的和真正的‘人性'(humanitas)。是哲學,而不是有關言說或者語法的學科,對於他才是真正的知識之核心。”
他還逐字逐句地引用了皮科信中的話:Vivere sine lingua possumus forte,non commode,sed sine corde nullomodo possumus.Non esthumanus qui sit insolens politioris literaturae.Non est homo,qui sit expers philosophiae[沒有舌頭我們也能生活,雖說不太方便;沒有心則不能活。不懂優雅文學的人,沒有文化。缺乏哲學的人,根本就不是人](同上,頁326)。同樣是在四十年代,另一位深刻影響了後世幾代人的文藝復興研究者克里斯特勒(Paul Oscar Kristeller)則說,“在與巴爾巴羅的一場有趣的通信中,皮科站出來爲中世紀哲學家們辯護,強調哲學內容遠比文學形式重要這一點”。至於皮科(以及當時另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斐奇諾)對經院哲學的態度,“我們現在知道,毫無疑問,斐奇諾在佛羅倫薩大學就讀時接受了這方面的訓練,而皮科則在帕多瓦巴黎的大學研修經院哲學,這一點更是沒有疑問。這一訓練在他們的思想和寫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同前)。在他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思想的連續性,是一個恒久的主題。
我們再來看一看意大利著名的文藝復興研究者加林(Eugenio Ga-rin)。在他的《意大利哲學史》(History of Italian Philosophy),他詳細敍述皮科的學習、研究經歷,以及他所交往的圈子。有關皮科與巴爾巴羅的關係,加林不僅介紹了這場通信,還交代了其前傳和結局。他用了好幾頁來討論皮科的信,大段地引用了皮科的話。皮科以雄辯的方式來嘲笑雄辯術和人文主義者(語法學家):
巴爾巴羅啊,我們作爲著名的人生活過,我們還將活在未來,不是在語法學家的學堂裏,小孩子才在那裏上學,而是在哲學家的學園智慧者的集會上,在這樣的地方,諸如安德羅馬克的母親、尼俄柏的兒子是誰之類瑣碎的問題,是不會討論的。所討論的是屬人屬神之事的原則。在深思中、在探尋中、在厘清這些事情中,我們是如此的銳利、機敏、富有洞見,有時顯得太激動太一絲不苟,如果說人們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居然會太一絲不苟太好奇的話。如果有誰要在這些事情上指責我們遲鈍麻木,不管他是誰,我們都要請他亮個相。他就會明白,蠻族舌頭上沒有墨丘里(雄辯之神),心裏卻有;蠻族也許並不雄辯,卻不乏智慧。(同上,頁300-301)
我們援引這些大學者,是爲了說明傳統上對皮科及其思想的評價。可是,皮科的信中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其哲學內容和文學形式之間的衝突。因爲,如果皮科要讚揚經院哲學,反對修辭學,認爲修辭學會損害對智慧的追求,那我們就有理由期待皮科自己在他反對修辭學的信中,使用一種很不雄辯的,適合托馬斯、司各脫等經院哲學家的語言。可恰恰相反,他的信充滿了修辭技巧、典故、以及直接間接對古典修辭學的徵引。
其次,也許更重要的是,皮科信中的主要部分,也是往往被人所引用說明他對哲學與修辭學關係問題之態度的部分,其實不是以皮科的第一人稱來表達的。相反,這些話出自一個虛擬的經院哲學家,皮科把他從墳墓中喚起,讓他來回擊人文主義者的批評。在書信的結尾,皮科又說,他並不完全同意這些意見。他讓這位經院哲學家來表達這些意見,不過就像柏拉圖在《王制》中讓格勞孔爲不正義辯護,以此刺激蘇格拉底爲正義辯護。這樣,我們就看到兩種態度相互之間是衝突的。於是,問題就出現了:這兩種意見到底哪種是皮科真正的想法?傳統上把這經院哲學家的意見等同于皮科自己的思想。如果不作審查就加以接受,難道沒有風險嗎?
二
近幾十年來,對皮科與巴爾巴羅的通信,尤其是對皮科書信的性質和意圖,出現了另一種解釋。這一進路主要出自修辭學研究界的學者們。他們會認爲,這一爭論就算是爭論,也是人文主義者同仁們之間的友好討論,且不乏幽默,是有意爲之的無害的玩笑。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來曾任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校長的女學者格雷(Hanna Holborn Gray),在承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潮之複雜性和多樣性的前提下,認爲我們依然可以在這一大傳統中找到某些持久的特徵,某些爲各派人士所共有的前提和態度。對修辭學的關注,在她看來,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將人文主義者們聯繫起來的紐帶——不管他們在觀點和時間上相距多遠——乃是對雄辯術及其用途的觀念。通過它,他們分享了一種共同的理智方法,以及對此方法之價值寬泛的贊同。古典修辭學——或者說在文藝復興時期所解釋並採納的古典修辭學,爲這兩方面都提供了主要的資源”。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立場,格雷把這一著名爭論的雙方——再加上七十多年後爲巴爾巴羅辯護的梅蘭希頓(Philip Melanchthon)——都歸在人文主義者這一大陣營中。她注意到皮科採取了經院哲學家所不具備的雄辯文體,充滿了古典修辭學的技巧和用典,其用意則是模仿古代的論辯傳統,利用修辭學來支撐一邊的論點。說到底,論戰的各方並沒有實質的分歧,只是側重點不同。
這一解釋進路充分注意到皮科書信的文學形式,尤其是其修辭技巧以及與古典文化的關係。屬於這一解釋進路的學者,近來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或許是帕尼扎(Letizia Panizza)。
帕尼扎反對傳統對皮科書信的解讀。她認爲,皮科、巴爾巴羅、以及其他人諸如波利齊亞諾(Poliziano),都是人文主義者,也都是哲學家——就她所理解而言。分歧不在皮科與巴爾巴羅之間,而是在他們與經院哲學家之間。在她的論文中,討論到巴爾巴羅致皮科的信時,她徑直將皮科稱爲“那位更年輕的人文主義者”(l'umanista piùgiovane)(同上,頁73)。她強調古典修辭學復興對皮科與巴爾巴羅通信的影響:
“……在兩封主要的書信(即皮科的信和巴爾巴羅的第三封信)中,是declamationes[申論]的一個範例,無論是皮科還是巴爾巴羅都戴著虛構角色的面具;借此兩位作者都繞開了‘教導'(didascalie)的話語,以此說明在何種意義上它們可以被解釋爲某種一本正經的玩笑(serio ludere)。對於這兩位作者,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在十五世紀末的傳播(以及對作爲適合哲學散文之文體的明晰表達的強調),給了他們一種工具,借此,傳統上哲學對被理解爲純粹修飾的雄辯術的貶低,便得到了克服”。(同上,頁70)
帕尼扎將信的開頭和結尾——皮科以第一人稱(in prima persona)說話——稱爲“教導”(didascalia),也就是說,在這一部分,皮科所說的話完全是他本人的想法。而信中段更長的部分則是某種精緻的修辭學實踐“申論”(declamatio),皮科此時戴上了一個經院哲學家的面具(maschera),去讚頌粗糙的拉丁文以及其同儕的文風,將人文主義者的雄辯貶爲浮誇的文字,有害於對真理的探尋。照帕尼扎的說法,皮科這樣做,其目的是要開一個朋友間的玩笑,是爲了逗巴爾巴羅開心(同上,頁75)。
在古典修辭學的傳統中,申論是修辭學訓練和實踐的重要一環。在修辭學的訓練中,
申論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辯論的形式,也不同於系列各派哲學中辯證法的運用:參與者並沒有被區分爲對立的雙方,也沒有哪一方獲勝。每一個演說都被指派或者選定一個立場,有時幾個演說者都只陳述一個立場。
也就是說,在申論中,立場其實並不重要,關鍵是修辭技巧和演說能力的展現。而在申論中,經常可以用的手法是“面具代言法”(proswpopoi…a/fictio personarum),即演說者以他人——往往是古人或者是虛構人物——之口來說話,讓他去代作者說出作者未必全然同意的話,或者是從另一個(或者更多的)視角來審視所討論的問題,以此獲得更大的表達自由。面具代言法的神奇之處,照昆體良的說法,甚至可以上天入地,讓諸神和死人都出來說話。皮科在這信中所做的,就是虛構出一個早已死去的經院哲學家,以他的口吻來說出對經院哲學以及修辭學的看法。
帕尼扎注意到,這位經院哲學家的說辭,不但語言非常雄辯華麗,而且有許多古典學問的典故,實際上是經院哲學家們不可能知曉的。帕尼扎的結論是,皮科運用這一修辭技巧,是一種形褒實貶,一種悖謬式讚揚(encomio paradossale)。也就是說,表面上皮科是在讚揚經院哲學家們,實際上,皮科和巴爾巴羅一樣,是在嘲笑他們。
把皮科信中的主體部分,那位經院哲學家的說辭理解爲一種對經院哲學及其粗礪文體的悖謬式讚揚之後,帕尼扎把書信的開頭和結尾看成了完全反映皮科本人思想的話語,即她所謂“教導”。皮科對巴爾巴羅說:“如果我認爲經院哲學家們忽視雄辯術是正確的,那我就不會幾乎全盤拋棄對他們的研究;我也就不會在前不久開始研讀希臘文學,以及你那怎麼誇獎也不爲過的‘忒彌斯蒂烏斯'(亞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臘注疏者,其著作由巴爾巴羅譯爲拉丁文,巴氏甚爲珍視其譯本)”。她把這稱爲“悔其前言”(palinodia),這意味著皮科最後的態度與那經院哲學家完全相反。
三
這樣一來,對皮科書信的這一主要部分,我們就面臨兩種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釋。一種是哲學史界傳統的看法:皮科爲經院哲學的智慧辯護,反對脫離內容的空洞形式和浮誇的文體。另一種是修辭學觀點:皮科與當時的人文主義者沒有根本的分歧,他們都屬於一個多世紀的意大利人文主義大潮流,信中經院哲學家的說辭是皮科與人文主義者圈內好友之間的遊戲筆墨。
後一種理解,儘管在當代學術史上不是很悠久,也不占主流和優勢地位,但有若干方面我們必須注意。首先是它的學術支撐。這一派的學者,如帕尼扎,仔細梳理了文藝復興時期所復興的古典修辭學的傳統,從那經院哲學家的措辭中辨識了許多修辭學的典故,從亞里士多德到西塞羅和昆體良,從蓋利烏斯(Aulus Gellius)的《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到路吉阿諾斯的雋語,更少不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和《會飲》,其考據細緻入微,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這些細膩的論證所支持的論點:這些東西根本就不是一個在文藝復興運動到來之前早已死去的經院哲學家所知曉的。
這一派觀點的另一個來源或許是這一論戰的一方當事人,那就是巴爾巴羅本人。最初將皮科的經院哲學家說辭解讀爲一本正經的玩笑和悖謬式讚揚的人就是巴爾巴羅。接到皮科的信後,在他精心寫就的回信中(很可能沒有寄出,見前面的相關註釋),他說:
在我看來這是一樁節慶般逗樂的事:你這最完善、最有人文教養、最好的拉丁文作者,卻爲蠻族辯護而反對巴爾巴羅(barbaros contra Barbarum defendis),就像是敵人去幫助敵人、盟友去反對盟友、你自己反對自己(ut hostis pro hoste,socius contra socium,ipse contra te ipsum)……你以辯護爲偽裝,卻給了你所辯護者致命一擊(sub specie defesionis exitialiter iugulas quos defendis)。
何以巴爾巴羅這麼說?因爲,
要不是靠雄辯之士,雄辯術的敵人便不能維護他們的主張,就像是奴隸、女人和野獸。
要想把握皮科的真實意圖,需要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更細緻的探究,傳統思想史、哲學史的視角與方法,以及修辭學研究的進路都不能輕易加以否定,也未必可以草率地接受某一方。正如在一項對皮科有關修辭學與哲學關係之思想的研究中,克芮(Jill Kraye,倫敦瓦堡學院著名的文藝復興思想史家)說,
這封信充滿了悖謬和歧義。所以,如果我們要想理解皮科對修辭學與哲學之關係的真實立場,我們就不能孤立地閱讀它。這份複雜的文獻需要結合他的其他著述與活動,方能得到解讀。
聽其言觀其行也許是更爲審慎合理的方式。
巴爾巴羅對經院哲學家們的攻擊,有一點是說他們的語言粗糙缺乏修辭,也就是說,不夠古典、不夠羅馬。在皮科的信中,那經院哲學家則說,如果語言是約定俗成的,那就不能說一種標準是錯誤的,另一種才是正確的。如果經院哲學家們沒有以羅馬人的方式來寫作,那沒關係,你可以稱它們是法國式的、英國式的、西班牙式的,或者是人們俗稱巴黎式的。如果名(因而就是語言)的正確性是基於事物的本性,那麼,是否正確的評判者將不會是只玩弄詞語的修辭家,而是沉思與探索萬物之本性的哲學家。
就在他們通信的一年後,皮科籌畫在羅馬舉辦一場大辯論。這場辯論沒有辦成,因爲在他爲辯論所準備的《900個論題》(900 Theses)中,有些被教宗所指派的委員會判定爲異端或者正統性可疑。在論題的序言中,皮科自己寫道,
米蘭朵拉的喬萬尼·皮科,孔柯迪亞的伯爵。在陳述這些意見時,並沒有仿效羅馬人語言的輝煌,而是巴黎最著名辯手們的
言說風格,因爲這是我們這一時代幾乎所有哲學家們所使用的。
顯然,有關語言、哲學文體,這位經院哲學家與皮科本人持同樣的意見。
在信的開頭,皮科以自己的面目說話——帕尼扎說這一部分是“教導”——皮科說,他浪費了許多青春韶華去讀托馬斯、司各脫、阿爾伯特以及阿威羅伊,似乎悔不當初。但在他著名的《論人的尊嚴》(On the Dignity of Man)——同樣是爲這場辯論而作——中,他認爲每一派哲學都有與眾不同之處。他高度讚揚經院哲學,稱之爲“我們自己的”(nostris):
在司各脫那兒,有生動與明晰,在托馬斯那兒,有穩健與均衡,在吉爾(Aegidius/Giles)那兒,有精練和準確,在方濟各那兒,有銳利與深刻,在老阿爾伯特那兒,有古樸、寬闊與宏大,在亨利那兒,在我看來,則始終有崇高與可敬。
在信的結尾,皮科熱情洋溢地寫給巴爾巴羅,說他拋棄了經院哲學,轉而研讀希臘文學,尤其是巴爾巴羅的譯本。但我們知道,就在寫完信的一個月後,1485年的七月,皮科就離開了佛羅倫薩,前往巴黎,繼續研究經院哲學,還很可能是在爲來年的《900論題》所準備。
皮科信中所擬構的經院哲學家,無疑是一個面具,是一種修辭手段,皮科借此可獲得更寬闊的空間,更大的自由,來處理諸多複雜的問題。因爲,他可以說出他想表達但不太好自己說的東西。帕尼扎的論文體現了對古典修辭學廣闊的視野、對精細的語言與修辭手法的熟練把握,以及對皮科和其他人文本的細膩分析。但是,她對經院哲學家這一面具的最終評價,不太能夠令人滿意。
帕尼扎論證的根據,乃是皮科以自己的面目說話的段落——所謂“教導”——反映了他的真實態度。但如今,經過諸如克芮等人的努力,我們可以在皮科生平傳記、思想史、甚至皮科哲學的內在體系等方面加以否證。
在我們看來,帕尼扎的修辭學研究方法固然可貴,但可惜她(也許以及她的同行)沒有將這一精微的分析梳理貫徹到底。問題就出在書信開頭和結尾皮科以第一人稱所說的話。第一人稱就一定是“教導”嗎?誠然,didascalia[教導]是哲學的方式,後世的哲學家們往往更喜歡採取直抒胸臆的方式,但歷來也有把自己隱藏起來的。由此,我們完全可以對該部分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把修辭學的研究也運用到皮科書信的開頭和結尾。在我們看來,這一部分非但不是反映皮科思想的透明部分,不是所謂的“教導”。相反,這第一人稱是另一個面具,是由皮科創造的一個更爲精緻的修辭工具,它和那經院哲學家的面具一道,來表達他對修辭學與哲學關係關係的態度,同時還能掩飾他自己,或者說避免某些東西。戴上這一面具,皮科也許是想要挽回他與巴爾巴羅的友誼。但他的真正立場,則是在哲學這一邊。
也許,現在我們有望對皮科的這封信以及他對有關修辭學與哲學之關係問題的立場與態度,獲得較爲全面和準確的理解:皮科以融貫古今各種智慧——古希臘哲學、聖經啟示、各種近東思想、中世紀經院哲學等——爲己任,他反對人文主義者重語言形式、輕思想內容的傾向。因而在與巴爾巴羅的通信中要爲經院哲學辯護。他以“經院哲學家”這一層面具,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又以自己的第一人稱爲第二層面具,對真實的想法加以掩飾。如此說來,傳統上(如凱西爾、克里斯特勒、加林等人)對此的評價大體上是可靠的,雖然有些簡單化。而修辭學界的另一種評價,雖然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有獨到之處,但總體上是片面的。進一步說,修辭學的作用是服務於哲學,而不是取代哲學,或者把自己當成另一種哲學(甚至自認爲是真正的哲學)。
皮科在書信的結尾說,他不同意那經院哲學家的話,他拋棄了他們的哲學轉而研究希臘文學。他自己的其他著述以及他後來的活動表明,這些話不是謊言,就是純粹的客套話。進而他又說:
我要坦誠地說(dicam libere),某些語法學家(grammatistae)讓我倒胃口,他們知道了兩個詞的來歷就四處賣弄,炫耀自己,好像哲學家們就一錢不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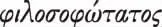
看來巴爾巴羅完全明白了皮科通過這一雙重面具所傳遞的資訊。這一點可以從巴爾巴羅對皮科書信的反應中看出。收到皮科的信後,巴爾巴羅先是草擬了一封短簡,他用玩笑的口吻,說他內心苦澀。但之後,他並沒有寄出這短簡,而是又寫了一封非常長的信。在這第三封精雕細琢的信中,他又顯得興高采烈,把皮科的信解讀爲是對雄辯術之敵(即經院哲學家們)的致命一擊,然而是以他們的朋友爲偽裝。現在我們當然知道了,這並不是皮科真實意圖。於是,我們不由得要想,這是不是另一個面具,只不過這一回是巴爾巴羅戴的,而且不免有些強作歡笑?
不管怎麼說,照加林的說法,這場通信嚴重傷害了這兩位朋友之間的友誼。
參考文獻[References]
Breen,Quirinus.“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on the Conflict of Philosophy and Rhetoric.”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3.3(Jun.,1952):384-391.
---.“Melancthon's Reply to G.Pico della Mirandol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3.3(Jun.1952):413-426.
Cassirer,Ernst.“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Ideas.”(Part I)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2(Apr.,1942):123-144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Ideas.”(Part II)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3(Jun.,1942):319-346.
Cassirer,Ernst,et al.,eds.The Renaissance Philosophy of M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Dorez,Léon,et Louis Thuasne.Pic de la Mirandole en France[1485-1488].Paris:Ernest Leroux Editeur,1897.
Farmer,Stephen Alan.Syncretism of the West:Pico's 900 Theses[1486]–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and Philosophical Systems,with Text,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Tempe: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and Studies,1998.
Garin,Eugenio.History of Italian Philosophy.Trans.Giorgio Pinton.Amsterdam:Editions Rodopi B.V.,2008.
Garin,Eugenio,a cura di.Prosatori latini del quattrocento.Milano:Riccardo Ricciardi Editore,1976.
Gray,Hanna Holborn.“Renaissance Humanism:The Pursuit of Eloquenc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4.4(Oct.-Dec.,1963):498.
Hankins,James.Religion and the Modernity of Renaissance Humanism.Interpretations of Renaissance Humanism.Ed.Angelo Mazzocco.Leiden:Koninklijke Brill NV,2006.
Kennedy,George Alexander.ANew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Kraye,Jill.Pico on the Relationship of Rhetoric and Philosophy.Pico della Mirandola:New Essays.Ed.M.V.Dougher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Kristeller,Paul Oskar.“The Philosophy of Man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Italica 24.2(Jun.,1947):99.
Mack,Peter.A History of Renaissance Rhetoric 1380-1620.Oxford-Warburg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anizza,Letizia.“Pico della Mirandola e il DeGenere Dicendi Philosophorum del 1485:L'encomio paradossale dei‘barbari'e la loro parodia.”I Tatti Studies:Essays in the Renaissance Vol.8(1999):69-103.
Pico della Mirandola,Giovanni.On the Dignity of Man.Trans.C.G.Wallis.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1965.
皮科,《論人的尊嚴》,顧超一、樊虹谷譯,吳功青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Pico della Mirandola,Giovanni.On the Dignity of Man.Trans.Gu Chaoyi and Fan Honggu.Rev.Wu Gongqi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0.]
Quintilian.Institutio Oratoria.Vol.III.Trans.H.E.Butl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1/1976.
Vickers,Brian.Rhetoric and Poetic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s.Charles Schmitt 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The Double M ask in Giovanni Pico's Letter to Ermolao Barbaro
The conflict between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is a traditional theme in the history ofwestern thought,towhich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rhetoric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dds a new dimension.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philosopher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the humanist Ermolao Barbaro in 1485 highlighted this conflict in that period.Itwas Barbaro who initiated the correspondence by launching an attack on the scholas-tics and their style as rude,dull,uncultured and barbarians in his letter to Pico,denying their immortality as authors,in reply to which,Picomade a defense for the wisdom and style of the scholastics with eloquence,through the words of a certain scholastics,holding that the scholastics,who might not be eloquent,were sapient in the final analysis with vigor in their heart rather than in their tongue.Furthermore,Pico criticized the humanists(grammatistae)that they just stared at the superficial form of language,omitting the inner philosophical content which was far more important.He believed that rhetoric was conflicting to and therefore below the things about God,Men,and Nature,which were the subjectmatters of philosophers.It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scholars such as Ernst Cassirer,Paul Oskar Kristeller,and Eugenio Garin,that the words of the“scholastic”give vent to the standpoint and attitude of Pico himself.Recently,some scholars look at it from the angle of rhetoric and take Pico's“scholastic”as simply a mask,a rhetoric device,maintaining that his defense of the scholasticism is actually a paradoxical encomium,i.e.a criticizing in the disguise of praise,and the true position of Pico is the same as that of his fellow humanists.This kind of evaluation,however,is not compatiblewith Pico's otherwritings and activities.In his On the Dignity ofMan and elsewhere,Pico highly applauds scholastic philosophy,and even imitates its style.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re is a double-mask in Pico's letter:what he expresses in themask of the“scholastic”reflects his true thought,and what he says in prima persona is the othermask(persona),ofwhich the aim is to conceal his true intentions and to make them seem less striking.Consequently,the opinion of those scholars is one-sided,though not without inspiration.And the traditional evaluation of Pico's letter is largely reliable,yet somewhat oversimplified.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Ermolao Barbaro;Renaissance;rhetoric;philosophy;mask
關鍵詞:
皮科 巴爾巴羅 文藝復興 修辭學 哲學 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