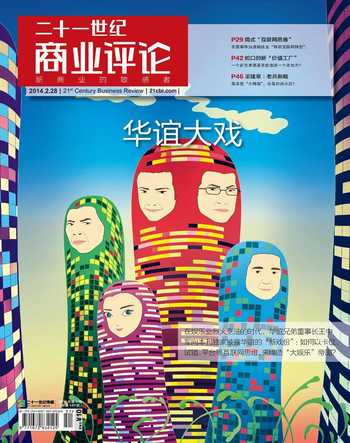聊斋里的“财富托管人”
刘黎平
在中国传统财富观念里,强调道德对财富的决定作用,在这个系统里,道德是父,财富是子。不存在父亲向儿子传授经营技巧的问题,只有道德延续的终端产生财富的奇迹。
《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宫梦弼》似乎也是走的这条路线,父亲积德,儿子在此基础上获取财富。然而,小说出于文艺的要求,让故事曲折化,道德与财富并不直接相关,这种结构反而接近财富产生的真相。
小說里的父亲柳芳华是一位慷慨的富豪,“座上常百人;急人之急,千金不靳;宾友假贷常不还”,父辈对财富的态度就是有出无入,柳芳华可以大方地借贷出去,却连本金都难得收回,遑论利息。家里还养着大量的食客。
父亲柳芳华是钱财的消散者,却是道德的积累者,然而,对他人慷慨的施舍,并没有换来他人在道德方面和财富方面的良好回报。柳芳华在千金散尽后,贫穷得不能下葬。
柳芳华的儿子柳和因为无法生存而去昔日曾经受过其恩惠的人家里请求支援,结果几乎是零:“凡二十余日不能致一文。惟优人李四旧受恩恤,闻其事,义赠一金。”其实这也是一个真理:既然是不计回报的施舍财富, 那么就要将这个原则坚持到底,哪怕施舍方真的需要回报。
蒲松龄的这个故事似乎在证明积德与积财之间的曲折关系,然而却证明了一个事实:父辈的积德与子辈的物质幸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小说往往比道德家的神话要来得真实。
要实现道德神话的终端效应:财富,必须通过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宫梦弼。
宫梦弼是个神秘的人物,他与柳家的父辈柳芳华是情义之交,每年总要和柳芳华聚会一两次,两人除了畅谈和饮酒,宫梦弼从来不向柳芳华索取半分银两,他们的交往和财富无关。

然而,柳家财富的复兴,却和这个人物紧密相关。
宫梦弼是柳家的常客,因此和柳芳华的儿子也很熟悉。当柳芳华去世无法下葬时,宫梦弼及时地出现了,他出资金使柳芳华得以体面下葬。但当柳和眼巴巴地期望宫叔叔改变柳家的处境时,他却冷冷地说出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子不知作苦之难。无论无金;即授汝千金可立尽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贫?”然后,宫梦弼神秘地一去不返。
这个家庭陷入绝望和贫穷,在经受了重重打击和羞辱后,终于等来了转机:巨额财富忽然出现。而这些财富来源于往年宫梦弼刻意扔在院子里角落里的很多瓦砾,它们全部变成了黄金!
对于这个财富神话,蒲松龄交待了他的写作意图:“慷慨好客之报也。”然而,这个财富神话的客观意义并没有局限在蒲松龄的主观意图里。宫梦弼的出现使这个故事有了新的生命力。
在客观的故事环境里和情节里,父辈的积德并没有换来儿辈的富裕,相反,是因为有宫梦弼这么一个类似于财富托管人的尽心策划,才使儿辈在财富上翻身。那些扔在地上变成黄金的瓦砾,不妨理解为一种低成本的理财产品和基金,在若干年后大幅增值了,由瓦砾增值为黄金。
子辈的重新富裕并非来自于父辈的积德,而是来自于合格的财富托管人,来自于暴然增值的低门槛理财产品。蒲松龄可能连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塑造的瓦砾变黄金这个神话,其实不自觉地推翻了中国传统式的道德变财富的荒诞情结,却揭示了一条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财富规律:父辈遗留的财富管理机构和良好的增值产品,才是子辈财富翻身的契机。
道德的归道德,财富的归财富,父辈丰厚的道德财富未必能兑换出子辈的物质财富。蒲松龄在这个方面出奇地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