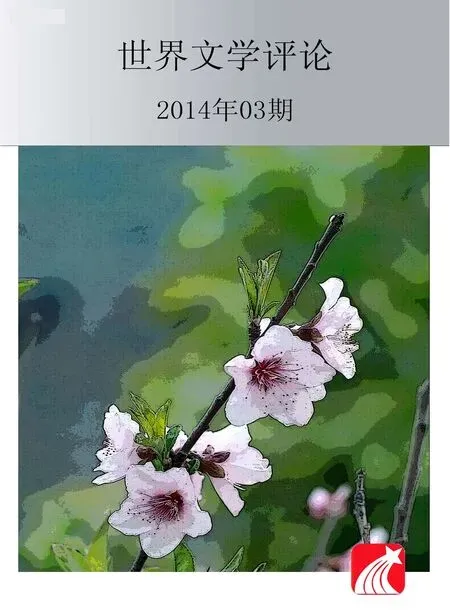论女性主义对《简·爱》的解读*
孙学棋 李向欣
论女性主义对《简·爱》的解读
孙学棋 李向欣
《简·爱》自从出版至今一直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使得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别开生面。女性主义批评认为,《简·爱》浓缩了女性的声音从湮没无闻到大胆发声的过程,但是采取了“双声话语”的隐秘策略。除了简·爱的大胆宣言,小说中次要的女性人物疯女人伯莎也受到女性批评的重视,甚至被重新改写。她们都体现了女性所受的压抑和反抗,因而她们构成了互补的关系。通过对《简·爱》的女性主义阅读脉络进行梳理,从各个角度反映出《简·爱》这部不朽作品的永恒魅力和文本生产能力。女性主义通过对《简·爱》的解读同时也丰富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呼应了各个时期的女权主义运动。
《简·爱》 女性主义 女性叙事
Authors: Sun Xueqi,
is from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Li Xiangxin,
is from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简·爱》:从争议走向经典
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160年前发表至今,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这充分地说明了它的文本异质性和丰富性,因而被誉为“最具生产能力的文本”。(卡普兰 99)
《简·爱》是一篇出自女作家之手,以女性为小说主人公,讲述女性生活经历和追求的女性文学文本。小说描写了19世纪中叶一个出身贫寒、相貌平常的家庭女教师简·爱的生活经历。她自幼失去双亲,先是寄养在舅母家,后来寄读于教会学校。后来,她到桑菲尔德庄园做了一名家庭教师,并与庄园主罗切斯特产生了爱情。罗切斯特的前妻放火烧掉了庄园,罗切斯特失去了财产,落下了残疾。简·爱则在此前意外获得一笔丰厚遗产,但她没有抛弃罗切斯特,毅然嫁给了他。
《简·爱》刚一问世就遇到了评论界迥然不同的反应,毁誉反差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评论家以极大的热情对之给予积极的肯定,认为《简·爱》思想深刻健康、人物真实感人、创作手法独特新颖。有的评论家指出作者写作技巧不够成熟、情节设置不尽合理、感情描写夸张等缺陷。也有少数人对之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将《简·爱》及其作者斥为“粗野”、“叛逆”、“反基督教”、“异教徒”、“道德上的雅各宾主义”、“宪章运动分子”等。这部分人虽然不多,但是代表了当时一些权威的看法,也得到了持有“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人群的认同。这部分人从《简·爱》的解读中察觉到该文本对传统父权社会及宗教顽固势力的颠覆性,因此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诋毁。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简·爱》确实切入了当时涉及女性的敏感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对《简·爱》及其作者恶意进行诋毁的言论逐渐销声匿迹,理性、客观地评价《简·爱》开始成为主流的声音。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逐渐崛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对许多经典文学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简·爱》的解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玛丽·伊格尔顿的划分,从1840年出现男性笔名开始,到1880年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去世时为止,这个时期的女性文学为“女人气(feminine)阶段”。伊格尔顿认为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品“是模仿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使其艺术标准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 。(伊格尔顿20)从1880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妇女争取到选举权的女权运动是“女权主义者(Feminist)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进入了“女性(female)文学阶段”,即一个新的自我意识阶段。女性从对男权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自我发现、自我认同,取得主体身份的阶段。事实上,不仅是女性的写作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对《简·爱》的女性主义解读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发展过程。本文即以这三个阶段为线索,来探讨女性主义批评家如何解读《简·爱》,以及《简·爱》又怎样促进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
二、女人气 (feminine) 阶段:发出女性的声音
结构主义文本观认为,文本具有开放性及异质性。文本的异质性使读者必须放弃对文本终极理解的探索。在文本面前,作者、评论家和读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女性主义批评指出,任何文本阅读都不是中性的,也不会是完全客观的,读者的阅读行为总要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点。显然,阅读主体的不同性别角色、文化背景和审美经验势必导致不同的阅读效果。女性阅读正是强调了其性别视角,要求其作为女人去阅读。因此,对女性文学文本的解读要紧密联系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
《简·爱》发表的时候,英国正处在维多利亚时代,正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倡导平权自由。但广大妇女,包括资产阶级的妇女,仍处于无权地位。在这样的父权社会中,道德和法律的预设使妇女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庸,在家庭中相夫教子。女性即使走向社会也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延伸行业,如充当护士、秘书、售货员和家庭教师之类的角色。她们社会地位地下,经济收入微薄,处于社会的边缘。
在这个时期,小说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学形式,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小说家。文学文本开始有了平民阶层的读者,但这些文学文本主要是面向男性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写作是以书信体方式,在女性之间的私人范围内互相倾吐“闺情”及两性情感,根本不入“大雅之堂”。当然更谈不上关于女性(of woman),由女性生产(by woman)、为女性申诉(for woman)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由于当时对女性写作仍有许多禁忌,尤其是对女性自传体小说经常有人说三道四,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女性作者大多被迫匿名写作。她们渴望得到女读者的认同,又畏惧男读者的敌意;期盼自我表现又怯于自我表现。为此,女性作者不得不隐姓埋名。
而小说《简·爱》则开风气之先。简·爱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对争取权利的强烈诉求。它颠覆了父权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模式,第一次明确地将女性的声音传递给每一个读者,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性文学文本。
《简·爱》这部小说尽管以中性笔名发表,但小说作者的女性身份很明显,作者的叙事权威与女性身份地位之间并不相称。这马上引起了评论家对文本作者真实身份的诘问,同时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对此,夏洛蒂·勃朗特承认,她之所以“将自己的真名隐去,而选取这种模棱两可的名字,乃由于一方面不愿公开自己的女性身分,同时出于谨慎的顾虑,也不愿采用那些一望而知即是男性的名字……我们有一种笼统的印象,就是:人们看待女作家往往怀有偏见;批评家有时拿性别当作惩罚的武器,有时又以此作为吹捧的因由——而吹捧当然不是真实的赞扬。” (勃朗特 17) 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和父权社会下女性作者尴尬的处境,夏洛蒂·勃朗特多次力争,希望不要再拿自己女性作者的身份说事。
三、女权主义者(feminist)阶段:观点的转变
20世纪20年代,英国女作家、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对简·爱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生活体验以及夏洛蒂·勃朗特的创作主旨做了精炼的概括。她指出,夏洛蒂·勃朗特将“全部力量——这种力量由于浓缩变得格外强大——全部投入了这样一句话:‘我爱’,‘我恨’,‘我痛苦’”(伍尔夫 293)。“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的口才、辉煌的辞令和激情宣称‘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体验虽然比我们的更加紧张强烈,却是与我们自己的体验处于同一水平上。”(伍尔夫 295)伍尔夫之所以这样概括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小说《简·爱》所表达的生活体验,正是由于伍尔夫有着与夏洛蒂“处于同一水平上”的相似遭遇。从伍尔夫对《简·爱》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与夏洛蒂在心灵深处的共鸣。
英国评论家戴维·塞西尔高度评价了夏洛蒂·勃朗特,说她是“第一个把小说当作披露个人心怀的工具的作家,她是我们的第一位主观主义的小说家,是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以及所有其他个人意识史家的鼻祖”(塞西尔 302—303)。“《简·爱》震惊了公众,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女主人公是个其貌不扬的女家庭教师;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那么直言不讳地表露自己爱情的狂热。”(塞西尔 319)《简·爱》将当时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家庭教师当作主人公,赋予她聪明睿智、率直善良的品格。按当时英国小说的常规,小说主人公理所当然地应当是男性,他们应有合体的仪态、理想的体形、俊秀的容颜、高雅的举止,应是极富教养的、落落大方的绅士。但是《简·爱》中出现的两个男人却不是这样:罗切斯特专横跋扈、粗暴任性、相貌平平,最后终成了残疾人;圣约翰·里弗斯作为一个牧师只想殉道、不懂生活。这样的男性形象在熠熠生辉的女主人公面前都失去了神采,这无疑使处于社会中心位置的男人大失颜面。更何况在妇女从事写作尚遭质疑的年代,作者居然敢在小说里诉说自己的身世、追求平等爱情、女性权利和价值。
四、女性(f e m a l e)文学阶段:对《简·爱》的深入研究及其文本增殖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公开的女性叙述声音对于女性作者而言,已经司空见惯。形形色色的表现女性生活的文学作品都推到了读者的面前,与100年前的夏洛蒂·勃朗特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时,女性文学批评家从女性读者的特殊视角,深入挖掘文本中的独立女性意识。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女性主义批评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和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中对于《简·爱》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并把对《简·爱》的解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指出,那些不甘心认同父权制,不愿将其内在化的女性作者在创作时不得不采用另一种“双声话语” 的隐秘策略。“双声话语”使女性文本表面含义模糊,因而能见容于主流社会;但文本中掩盖着不易解读、难以被父权社会接受的深一层含义,后者可以看成一种“失声”的故事。细心的女性读者的“揭秘性”阅读就在于将“失声”的故事重新解读出来。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作时恰恰采取了这一策略。《简·爱》表面上是写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其结局是平凡的女家庭教师嫁给了“富翁”——不外乎是灰姑娘的爱情故事俗套。但这仅是“双声话语”中“发声”表达的那部分故事,细读起来还有一段“失声”的故事。简·爱不屈地与命运抗争,她既不想成为罗切斯特的情妇,也不想成为里弗斯的殉道者,她拒绝成为男性的附庸。只有当她与罗切斯特在经济上的对比有利于己,而且她比罗切斯特还占有道德上的优势时,她才“嫁给了他”,而不是罗切斯特“娶了她”。从这个角度来讲,故事结尾别具一格,不落窠臼。夏洛蒂·勃朗特使用“双声话语”写作策略,巧妙地否定了男性中心主义,弘扬了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双声话语”实际上是拒绝统治传统的流行模式,同时也表现了19世纪中期女性作者在强大的男权压制下的无奈和抗争。
吉尔伯特和古芭还认为《简·爱》的人生经历就是从形成双重人格意识到人格分裂,最后自己努力治愈分裂创伤的过程。《简·爱》在童年时因反抗表兄的欺侮而被舅母关进了“红房子”。简·爱在“红房子”中的经历与感受透射出简·爱的双重人格意识。也就是说,在她的深层意识中,除了一个愤怒、仇恨的简·爱外,还有一个疯狂的简·爱。对囚禁的愤怒和恐惧最终导致了简·爱自我形象的陌生化直至人格的分裂。直到罗切斯特丧失财产、其前妻伯莎纵火身亡,简·爱才得以平等地与罗切斯特站在一起时,她的精神创伤终于愈合。吉尔伯特和古芭强调了简·爱身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压抑以及由此产生的愤怒、疯狂和自我解放。
另外,她们还指出,简·爱是感情理性的伯莎,而伯莎是愤怒疯狂的简·爱,她们正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如此看来,疯女人伯莎绝不是为了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而设的道具和陪衬。在对她寥寥的形象刻画中,储存着丰富、复杂的信息。伯莎的反抗、愤怒和疯狂正是简·爱时而凸显、更多隐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另一面。伯莎一次次的逃离、一次次的纵火,直到最后烧掉桑菲尔德庄园,这暗示着简·爱反抗男权的强烈欲望。伯莎的所作所为正是简·爱无意识中要做的事,也是一种“失声”的表达 。
美国批评家苏珊·S·兰瑟则选择《简·爱》的叙事方式作为切入点,指出女性叙事权威对世俗发起了挑战。曾有人指出:“整个说来,简·爱自传是一部突出的反基督教作品。从头到尾,它对富人的舒适生活和穷人的贫困发出了喋喋不休的抱怨声,就每个人来说,这是对上帝安排的抱怨——书中有一种高傲的、无休止的坚持人的权利的断言,不论在神谕或天意中我们都找不到这样做的依据。” (里格比 140)但是,这样直白不讳的叙事在兰瑟的眼中却是《简·爱》这部小说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它“方方面面最显眼的独特性,莫过于它的叙事形式了”(兰瑟 202)。
《简·爱》作为女性自传体小说,它从女性个人角度出发的自我权威化和总体化叙述声音震撼着每一个读者。作者冲破了当时对女性叙事权威的种种羁绊,创造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女性叙事主体。小说中,“简·爱一概不理睬别人对她的看法,而喜欢根据她自己的感觉、情感和经验,即根据某种根本的浪漫主义权威来享受一种“‘崭新的说话方式’。”(兰瑟 209)当简·爱还是一个寄居在舅母家的孩子时,她就敢对舅母的无端指责说不。后来在寄宿学校简·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坦普尔小姐,从而澄清了布罗克赫斯特的指控。这让童年的简·爱懂得了开口说话的重要性,她不屈地拒绝沉默,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另外,简·爱在婚姻问题上保持着自己独立的声音,破除了婚姻最终导致女主人公失语的故事俗套。
《简·爱》已被公认为女性自传体小说的滥觞。在夏洛蒂·勃朗特身后的几十年间,欧美的其他女性作家相继塑造了一群敢于直言的女性叙述者。她们为女性的独立而呐喊,其激进程度比起简·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文本的写作契合了女权主义者(Feminist)阶段的文学创作的主旨。苏珊·S·兰瑟特别关注了“叙事声音”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关注文本所表达的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从而为对《简·爱》进行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提供了一个好范本。
苏珊·S·兰瑟特别指出,《简·爱》还制造出了比女主人公的声音更加刚烈、更加独特的声音,那就是“疯女人”伯莎·梅森——一个西印度群岛女人发出的声音。伯莎的声音代表了一群女性的心声,她们拒绝采用“女人的语言”、拒绝女人的地位,或者说拒绝整个女性象征系统。对于父权社会而言,简·爱的声音尽管率直无忌,但并无太大的敌意;而伯莎发出的“野性十足、尖刻凄厉”的咆哮则完全站在处于“他者”的位置上。她不像简·爱那样仅仅是替女性发出声音和进行辩护,而是为父权社会中被压抑的所有边缘女性(包括有色人种女性)发出的抗议声音。她的声音又构成了对单一的白人女性叙事声音的挑战。
女性主义批评家还结合精神分析学说,对女性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她们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始终是被压抑的,父权制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压抑并隐匿这种压抑而得以维系。这种状况在文学中得以反映,《简·爱》即体现了这一典型。一般说来,女性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要么屈从于父权制,并将其内化为自我需求,如文学作品中常出现的“天使”形象;要么抗争、反叛,乃至疯狂、偏激地反抗父权制,如文学作品中的“妖妇”形象,《简·爱》中的伯莎可归于此类;要么试图寻求一种平衡和协调,其代价是导致了女性人格的分裂,简·爱则属于这一类女性。显然,夏洛蒂·勃朗特着力正面刻画的简·爱和着墨不多的伯莎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女性:在父权制度下,她们的心理和人格遭到扭曲和分裂,但她们仍不屈不挠地从不同角度向父权制度发出挑战。
英籍多米尼加女作家简·里斯(Jean Rhys,1894-1979)始终为《简·爱》中的伯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忿忿不平。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彻底错误地诠释了伯莎·梅森这个克里奥尔女人以及整个西印度群岛。“凭什么她(夏洛蒂·勃朗特)认为克里奥尔女人就是疯子这一类的人?把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塑造成这样一个可怕的疯女人多么的可耻。我立刻就想到我应该按事情本来的面貌写一个小说。”(O'Connor 144)简·里斯认为《简·爱》将伯莎野兽化、妖魔化,歪曲了殖民地非白人女性的形象。《简·爱》中的伯莎话语不多,没有倾诉的机会,简·里斯要为她夺回话语权,使她从文本的边缘走向文本的中心。为此,简·里斯于1966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颠覆性地改写了疯女人伯莎·梅森的故事,成为《简·爱》的互文本。如果说,《简·爱》间接描写了伯莎从疯狂到毁灭的过程的话,那么《藻海无边》则从正面描写了她如何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到被构建成疯女人的过程。《藻海无边》无情地控诉了殖民地宗主国男性对殖民地女性的迫害,指出伯莎的命运是买卖婚姻和英国殖民者的罪恶造成的。简·里斯的小说站在阶级、种族的视角下,写出殖民地女性的不幸遭遇,契合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新潮流,也为《简·爱》的文本阐释扩展了新的视角。
简·里斯的改写体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女权主义运动的统一立场开始发生改变,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主体受到了冲击。这是由于在白人妇女/黑人妇女、中产阶级职业妇女/劳动阶级妇女、发达国家妇女/不发达国家妇女、异性恋妇女/同性恋妇女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不同的权利诉求。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认为,不同种族、阶级和文化背景的女性有着不同的经验。事实上,女性的经验是多元的、复杂的,因此根据白人中产阶级和异性恋妇女的经验建构出来的所谓“女性经验”往往忽视、否认或者是歪曲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其他女性的经验。
五、结 语
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女性主义对《简·爱》的典型解读。无论从怎样的角度和观点出发,《简·爱》这部小说本身及其评论,无不显示了它强大的艺术魅力、思想的深度和超前性,使得其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观点的照射下都放出光芒,给读者以震撼和思考。
注解【Notes】
*本文系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西方文学精神生态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B63)阶段性成果。
[英]科拉·卡普兰:《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阶级、和性征》,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英]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英]夏洛蒂·勃朗特:《埃利斯·贝尔与阿克顿·贝尔生平纪略》,载杨静远选编:《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简·爱〉和〈呼啸山庄〉》,载杨静远选编:《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英]戴维·塞西尔:《夏洛蒂·勃朗特》,载杨静远选编:《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英]伊丽莎白·里格比:《〈名利场〉、〈简·爱〉和女家庭教师联合会》,载杨静远选编:《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美]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O'Connor, Teresa F.Jean Rhys: The West Indian Novels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Jane Eyre
has drawn attention from both readers and critics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e feminism literary theory broke a new ground in its interpretation. The feminist critics believed thatJane Eyre
was the miniature of the process from women's silence to voicing, using the secret strategy of "double voice". Apart from Jane Eyre's outspoken declaration, the madwoman Bertha was also scrutinized and even rewritten by the feminists. Both of them re fl ect the repression and the revolt of women, and therefore they form a complementary character relation. In this paper, the feminist reading ofJane Eyre
has been combed and analyzed, which from varied perspectives shows the everlasting charm and textual productivity ofJane Eyre
. The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Jane Eyre
in return enriched feminism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choed feminism movement of different phases.Jane Eyre
Feminism Female Narration孙学棋,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李向欣,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作品【Works Cited】
Title:
On Feminism's Interpretation ofJane Ey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