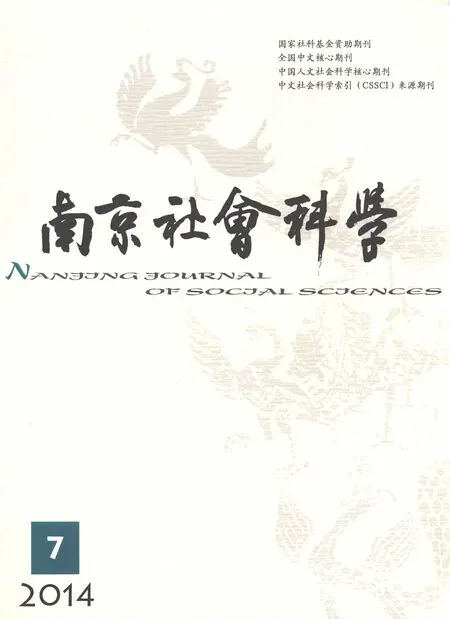通向“Being”的知觉是如何发生的?*
——海德格尔《泰阿泰德》(184B-186E)一节的解读
孙冠臣
通向“Being”的知觉是如何发生的?*
——海德格尔《泰阿泰德》(184B-186E)一节的解读
孙冠臣
柏拉图《泰阿泰德》的主旨是要探讨“知识是什么?”。在对话中,泰阿泰德给出的第一个定义是“知识是知觉”。通过细致入微地解读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的对话,海德格尔分析了知觉的通道并不是感觉器官,而是灵魂,揭示出知觉中“多出来的存在”。他认为知识作为对真理的占有,追问“知识是什么”实质上就是追问知识的可能性问题,这一问题只能到存在本身发生的领域中寻找,灵魂的本质规定是力求存在,既是“存在”、“非存在”、“同一”、“差异”、“和”等的聚集地,也是存在本身发生的场地。海德格尔由此主张,知识与真理的关系、灵魂与存在的关系、存在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是同一个问题,进而将知识、存在真理与逻各斯(语言)统一起来。但由于这种解释走的是存在学的解释学之路,与现代知识论的逻辑主义之路完全不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双方之间相互不理解,对话与交流异常困难。
知觉;知识;灵魂;存在;海德格尔
一、问题的提出
在此,我们将谨慎地选取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泰阿泰德》解读中的一节“知觉是知识”这一定义的最后反驳环节(184B-186E)①来构建我们的问题:从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的对话中,海德格尔意图推论出什么?其对《泰阿泰德》的解读是否还属于坊间所认可的知识论问题?他所开启的问题是否能够得到知识论专家的认可?
海德格尔曾经主张,要比希腊人还“希腊的”理解柏拉图,何谓“希腊的”?如何才能通达哲学的这种希腊性?众所周知,探讨哲学问题,或者追问什么是哲学,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柏拉图,毕竟,哲学在柏拉图那里才成其为哲学。但是海德格尔一方面主张回到希腊这一哲学源头去理解哲学是什么,另一方面却又将柏拉图看作是西方哲学柏拉图主义的肇事者大加批判。在此双重语境中,海德格尔对《泰阿泰德》的解释兴趣显然不同于传统知识论的解释立场,他的解释重点并不关乎“知识是什么”的传统“三元”定义,而只关乎确定知识与真理、非真理,知识与存在的关系。
众所周知,柏拉图区分了知识与意见,知识是关于“是”或“存在”的;意见是关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事物的。知识犹如人的灵魂清醒状态,而意见犹如人在睡梦中。在梦中,我们不能区分真实与虚幻、形式与摹本,一个有知识的灵魂能够区分形式与其分有物,因此,求知就是从梦中醒来。把求知理解为从梦中醒来的过程,把知识看做是灵魂的清醒状态,这种思路与笛卡尔以来的知识论思路不同:近代以来的知识论主要目的在于追求确定性,以对抗怀疑论的质疑,知要从怀疑中解放出来,因此近代以来的知识论是一种纯理论的探索,尤其是经“语言转向”之后,完全演变成对语言、对命题或真值条件的分析与论证。而柏拉图把求真、求知的过程看做是追求对“至善”、“形式”、存在者整体的理解,以期获取解释、说明的力量,获得对本原、原因的认知,不再困惑,求个明白,以对抗浑浑噩噩的混沌状态,所以苏格拉底才说,未经审视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海德格尔的出现是对近代知识论的反抗,他重申了第一哲学的永恒主题是存在问题,拯救性地恢复了希腊哲学的传统,他经常用林中空地来比喻存在真理作为澄明,求真就是求无蔽、求理解。因此,在海德格尔所确立的解释视域中,柏拉图追问的“知识”并不等同于近代以来的科学知识体系意义上的知识,它指向我们日常用语中的“我知道……”、“他精通制鞋”、“他懂得兵法”等中的知道、精通、懂得等含义,与“科学本身是什么”没有多少牵涉。海德格尔认为,认识/知道在希腊人那里首先是“对在场之物本身的当前居有,在其在场状态中占有它,即使当它可能是不在场的时候。”“这样,知识(对……的精通)就达到了对存在者揭示出来(无蔽)的占有,即达到了对真理的拥有或占有。”②海德格尔将知识定义为对真理的拥有或占有,而真理在其上述知识的定义中则是某物的自明和自身呈现,也就是说知识在海德格尔的解释中已经被“希腊的”解释为对在场的看与在场呈现本身的融合。通过这种所谓回到源头的先行确认,关于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就不再是回答知识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知识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亦即真理如何发生的问题,海德格尔指出,此问题在一种本源的意义上就是对人本质的追问。《泰阿泰德》的引导性问题:“知识是什么?”在海德格尔这里就变成了这样的问题:人本身在其基本行为中,需要或应该如何使自己精通于诸事物,如果他想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就应该或必须如何使自己处于这种关系之中。
跳出知识的三元定义,“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被归入人本身在其基本行为中的关系中,亦即纳入到此在之生存论结构的分析中,此在之先行理解、之寻视操劳结构中,从而与近代知识论以及现代知识论所追问的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区分开来:一边是科学知识本质条件的逻辑设定,一边是解释学的存在学建构。海德格尔的解读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来看,显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知识是什么”的知识定义或解释,他提供的毋宁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表达,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增加我们的知识。但从解释学的立场上来看,人类知识的根源就扎根于生活世界中,海德格尔以及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都不会为我们提交一份科学实验报告,而只能作为人类灵魂中的一份文件给予签署。
接下来我们按照海德格尔的解读思路,还原他的解释过程,通过分析“知觉的通道”、“在知觉中多出来的东西”,揭示其解读柏拉图《泰阿泰德》的意图,并通过分析“存在与真理”指出海德格尔“解释学的知识论”完全不同于现代知识论的逻辑建构,在知识论的研究版图中,不应无视与排斥,而应展开有效的对话并寻找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二、知觉的通道
什么是知识?泰阿泰德的第一个回答“知识是知觉”很容易将知识等同于“意见”,实际上苏格拉底也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反问泰阿泰德的,并且动用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这样强有力的论证。考虑到柏拉图在《理想国》第5卷中,已将知识与意见区分开来,显然在这里也不能将知识等同于意见。
近代心理学把知觉理解为知觉过程、人的知觉活动,从这一立场出发,普罗泰戈拉的命题和苏格拉底的反驳就是成立的。但是,海德格尔把知觉定义为某物的被知觉状态,不从人这一认识主体出发,而是从物的被知觉状态亦即物被摆置出来、被呈现出来的状态出发谈论知觉。“某物的自身显现、在场、逗留、即某物的敞开状态,任何一种无蔽的形式,就存在于知觉中。哪里有知觉,哪里就有直接的、从本身出来的如颜色、彩色的、发生的东西等诸如此类无蔽,所以,在这里就有真理;就有知识。”③如此解释知觉,“知识就是知觉”这一定义成立。海德格尔认为,知识、对某事物的精通、对真理的拥有,就是被知觉状态。被知觉状态是某物的自身显现,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主体的主导地位也被弱化。而且,通常心理学意义上感觉器官在这里也仅是知觉的通道而已。
——人们是借助什么看见了白的或黑的东西,又是借助什么听见了高的或低的声音,那么,我相信你会说:用眼睛或耳朵,是吗?
——是的(184:b8)
眼睛在看,耳朵在听,更精确地说,知觉活动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意味着感觉器官只是知觉活动发生的通道,本身并不是知觉活动中知觉着的东西。
——眼睛是那种进行着看的活动的东西,还是说,是那种看所通过它而发生的东西,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呢?(184:c5)
眼睛、耳朵作为感官在今天的心理学中是功能性的器官,而在海德格尔的柏拉图这里则被规定为知觉活动的通道,而不是进行知觉的东西。是什么在“通过”它而“看”呢?“看”本身就具有统摄功能,正如康德所言,感觉意义上的杂多必须归于统一,才能够形成知识,柏拉图不是从感觉器官出发寻找知识的根源,而是从灵魂那里寻找知识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评论说,“灵魂作为可觉察事物的统一并与之保持着开放关系。”④虽然看蓝天白云,听小鸟啾啾,但我们不是在眼睛中看到颜色,不是在耳朵中听到声音,也不是在大脑的某个神经区域,在任何东西“之内”都觉察不到颜色和声音,而是在“之外”,我们是在书皮上看到颜色,听到某人关门的声音,我们闻到食堂散发的气味,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现成事物,它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空间,所有这些被知觉到的东西在这个领域中汇聚。海德格尔解释说,柏拉图把这一知觉到的东西可能的可觉察性领域称呼为“灵魂”。灵魂就是这样一个包围着我们的可觉察性领域,灵魂首先借助于这样一个可觉察性领域本身,呈献出这个领域中的东西,这个彻底包围着我们的领域,属于我们本身,而且还是一个同一的东西,柏拉图称为某种其本身就在我们自身中的东西。笛卡尔首次把这个同一的东西规定为那个思想着的我——主体。海德格尔说:“我们之所以知觉到颜色、声音和气味,不是因为看、听、嗅,而是相反,是因为我们的本已在本质上就是关系性的,就是事先呈献或呈献一般可觉察性领域,并处于这个领域之中的东西,因此,我们才可以在一个或同一个领域内,将自己分散为这样一些觉察着的器官,而且首先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能作为同一个存在者,时而从事于某种看或听,时而与某种气味发生关联。”
根据海德格尔的解读,“灵魂首先必然是:关系性的东西,在自身中接纳与某物的关系的东西,由此首先使这种接纳某种觉察的东西,此外使那种发生知觉所通过的通道成为可能并得以存在。”
——我们身上藏有许多感觉器官,就像在特洛伊木马中藏身的勇士,一切事物会在某个单一性质中会聚和集中,这个性质被人们称作灵魂或其他什么东西。我们通过那些作为工具的器官,用灵魂感觉一切感觉的对象(184:d4)。
灵魂就是那种“基于它,首先形成作为工具的所通过的东西,通过这些所通过的东西,我们知觉所有那些一般可知觉的事物。”(这是海德格尔对184:d4的翻译)⑤所以,只有在已经延伸了的、与某物关系的基础上,从躯体性的东西划分为器官性的东西才得以可能,只有这样,一个躯体(Körper)才变成身体(Leib)。身体,相对于一种躯体的东西而言,它只有沉浸于灵魂中才得以存在,而不是相反,某个躯体被灌入了一个灵魂,才能成为身体。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知觉在感官的感觉意义上,必然以另外的东西为依据,这种东西使某物自行呈现并使被觉察得以可能。灵魂是知觉着的东西,因此当泰阿泰德想要说,在具有感觉(刺激)和“经历”的意义上,知识就是知觉的时候,他的话也并不代表任何“感觉主义”。这与批评普罗泰戈拉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相呼应,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的对话想要表明的是,这些(感觉)理论有它们自己明确的适用范围,可知觉或可感觉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它们是真理,但是,可感世界不是整个世界,因此这些理论也不是真正的真理。实际上,柏拉图意欲寻求的是他的形式的世界,亦即真实的世界。感性世界与形式世界的区分在这里再次成为讨论知识问题的背景。
2.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普罗泰戈拉与赫拉克利特观点的反驳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知觉,实际上,知觉对象是流动的也是他的主张之一。反驳普罗泰戈拉的观点是要区分出:
(1)主张“知觉对象是变动不居的”与主张“任何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是不一样的;
(2)纯粹的感觉意识与在此感觉意识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3.仅从纯粹感觉意识而言,人的感觉不比动物灵敏,也不比神的感觉迟钝,但人的判断力显然比动物优越,而据说神的判断力更是远远凌驾于人的判断力之上。但柏拉图自己的知觉理论要告诉我们的正是人的知觉在什么意义上超越于动物,而落后于神,因此,决定性的东西始于“我们借助或通过什么来进行知觉”这个问题,眼睛、耳朵,它们是什么?借助于这个问题,视线转向了知觉与展现、外观之间关系的基础,即转向了其关系的所在地,在同一个东西中的共同归属性、“一”及其统一性、“联合”、汇集、在场、无蔽、揭蔽。海德格尔通过考察说明:这种关系不是由身体的感官组成或存在于身体的感官中;这种关系就是可视性、可听性、可觉察性,就是灵魂本身。
三、在知觉中“多出来的东西”
1.“和”
灵魂作为可觉察领域,作为知觉得以发生的可能性,确保了知觉的统一性,知觉活动又通过各种不同的通道(感觉器官)得以实现。在知觉活动中,各种通道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眼睛只能看,不能听;耳朵只能听,不能看。我们不能听颜色,也不能与声音一道同时听它;不能看声音,也不能与颜色一道同时看。但我们在知觉活动中有时在获得某种颜色的同时,听到了某种声音,颜色和声音被同时获得。对此,苏格拉底问道:
——所以,如果你在两者或超出两者(颜色和声音)的范围内,同时觉察到了某些被知觉对象,更准确地说:从一种到另外一种通彻地思考⑥它们,那么,你难道可以不通过某种感觉器官,也不通过其他与两者相关的感官,就能知觉到超出两种觉察对象之外的东西。
——当然不会。(185:a4)
毫无疑问,我们知觉到另外的东西:“和”。而两种参与活动的器官,眼睛和耳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觉察到这个“和”。我们既然不可能看到或者听到或者闻到这个“和”,那么当我们同时知觉到颜色和声音,即觉察到与两者相关的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此时所觉察的究竟是什么。
柏拉图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再次向我们表明,颜色和声音的被知觉状态,存在于一个或同一个被知觉状态中,也就是说,同时存在于一个或同一个可觉察性领域中,而同一个可觉察性领域,正是知觉着的灵魂。在知觉中多出来的“和”揭示着灵魂的统摄(统一)功能。
2.“多出来的存在”
我们看到了蓝天白云同时听到了云雀歌唱,颜色和声音同时向我们展示,我们觉察到了两者,我们究竟觉察到了与两者相关的什么东西呢?我们此时能觉察到什么呢?仅仅是颜色和声音吗?
——与声音和颜色相关:你难道没有首先从对两者的通察中,觉察到它们两者都存在吗?
——当然(185:a8)
我们觉察颜色和声音,蓝色与歌唱,“首先”两者都是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更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也被觉察了的情况下,这个“首先”才“先行发生”。颜色是一种存在者,声音是另外一种,每一个都既是不同的(与另外一种存在者不同),又是相同的(与自身则是同一个存在者)存在着的东西。我们在注目(看)两者的时候,能够看出或感受到两者的不同与相同。只有在一个和另外一个存在者被知觉到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计数。一个和另一个就是二,但在这里“多出来的东西”,显然并不是相加得出来的,一个和另一个首先必须被给予存在性,然后,我们才可能计数。⑦
海德格尔解释说:“借助于所有这些(存在着的东西、一个和另一个存在、两者、同一个、两个、一个、不同的存在、相同存在),我们觉察到了那些附加在颜色和声音上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获得了一种在可知觉和被知觉之物的范围内无法回避的、从可觉察的东西中多出来的存在。”⑧柏拉图意在强调,在对于某种看到和听到的东西的知觉活动中,我们觉察到了比颜色和声音更多的东西;当然,这种显示出来的“更多”,存在着的特性意义上的颜色和声音,如此自明地直接被觉察,以至于我们根本不会首先注意到。当我们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白云,听者云雀啾啾,乐于其中时,并没有特别注意,或根本不会去考察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别无所思时,才会觉察到这么多的存在者,一个又一个,以及每一个本身。
3.感觉器官不是觉察所有被知觉物共同的东西时的通道
既然每一个感觉器官都是一个独特的通道,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耳朵只能听到声音,那么,颜色“和”声音“同时”呈现给我们的共同的东西,即“和”、“同时”揭示着的“多出来的存在”的感觉通道在哪里呢?苏格拉底提出了这一决定性的问题:
——你是通过什么来觉察与此(颜色和声音)相关的、所有这些(前面提到的多出来的存在)呢?要想获得或遇到与之相关的、它们所共同的东西(被知觉的事物由此而保持一致)本身,既不可能通过所听到的,也不可能通过所见到的东西。(185:b7)
我们不可能通过哪个感觉器官来觉察“存在着的”或“不同的存在着的”,但毋庸置疑,这类东西在觉察中呈现给我们,我们能够去“觉察”“存在着”、“另一个”、“同一个”、“不同的”、“相同存在”。
——无论如何都指示着某种通道的能力,不仅使得所有你通常可知觉的东西,而且使得颜色和声音所共同的东西对你显现,由此,你提及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我们现在所要追问的正是这个东西。
——你认为哪个感觉器官可以达及所有这些东西(即超出颜色和声音而可知觉的共同的东西),我们里面的知觉器官通过什么来知觉每一种(被知觉到的东西)?
——你指的是存在和非存在,相同和不同,同一存在,被计数的存在。我们在个别情况下还觉察到偶数和奇数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那么,通过躯体的哪个器官,灵魂在通道中觉察我们(对所显示出来的多出来的存在)的知觉活动。
——这些(多出来的存在)和那些(颜色、声音、气味)一样,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其特有的通道,我觉得灵魂本身就是那样的东西,即它在通道中通过其自身来接受所有这些共同的东西。(185:c4-d8)
对于存在、非存在、相同、差异等诸如此类的觉察来说,与对颜色、声音、气味等的觉察一样,并没有其特有的通道,甚至根本没有躯体、身体性的器官;而是灵魂本身,通过其自身而贯通于对那些(存在)的觉察活动中,并因此自发地将显现出来的普遍性带进视野。可见,“灵魂是自身呈现某种可觉察性领域的东西,所有可觉察的东西都汇聚其中,并在那里保持统一和同一性。”⑨灵魂不是躯体的某一种器官或能力,它就作为通道而起作用,它本身就是通道,通过这一通道,呈现着可觉察事物之统一的领域,而且它就贯通于这个它所呈现着的领域中。
接下来,苏格拉底总结了泰阿泰德的回答(185:e6):
——在对某物的知觉中,灵魂之眼感受到双重的东西:一种是自在的并通过自身的东西,另一种则是自发地在通道中通过身体
性官能的东西。
海德格尔解释说:“在知觉活动中有两种觉察,一种是前面所说的多出来的存在、非存在等,灵魂通过自身而觉察它们,另一种同样由灵魂觉察,但是在通道中通过身体或身体性的官能。”⑩在柏拉图这里有一个肉体向身体的所谓“进化”,灵魂进驻肉体以后,肉体进化成了能感知的身体;自笛卡尔以来,这种进化被取消,肉体总是肉体,精神性的我晋升为主体。这一主体作为认识着的“自我”就被功能化了,尤其在康德那里,不仅是承担着综合功能的统觉,而且还是认识可能性的逻辑上的极点。先验哲学作为自我设定的学说虽然解决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但灵魂作为知觉同一性、差异性、普遍性的通道所呈现出来的领域就被忽略了,被关注的仅仅是统一性、普遍性。尤其是当主体与客体二分成为探讨认识可能性的出发点以后,除了认识对象、客体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多出来的存在”了。
4.如何安置这个“多出来的存在”呢?——对存在而言,知觉活动是非关系、非概念的觉察活动。
苏格拉底首先给出了存在的简单特性:我们觉察某物的时候,存在总是在此,是无法摆脱的东西。“存在超出一切可觉察事物的领域而发挥着全面的功能。我们所想象、觉察、思考、规定的东西,都已经被标画为存在着的。”(11)
——你把存在安置在两者(即知觉和被知觉事物的关系环节)的什么地方呢?它通常可总是伴随着一切东西。
——对此我认为,存在属于那种灵魂通过其自身、为了其自身而奋力趋向的东西。(186:a2)
海德格尔说:“存在是灵魂所力求趋向的场所——不仅仅是偶然的,而且也不是随便的一个什么目标,而是灵魂自发地,依照其本质并唯一地为自身所趋向的场所。”(12)灵魂就是这种趋向存在的努力,“灵魂”这个词就是为说明力求存在的词。力求存在同时形成知觉与被知觉事物的关系。可见,海德格尔对《泰阿泰德》解读的意图就在于揭示出灵魂与存在的关系,亦即此在与存在的关系。通过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灵魂概念的解释,即力求存在,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哲学思想中的关键术语“此在”的含义,此在与存在相互归属,此在是根据它与存在的关系来定义的。“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它在其存在中有所理解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13)
灵魂与存在的关系还规定了“多出来的存在”并不是感觉的附加物,而是“灵魂本身给我们突出地展现出来的”(186:b2-10)。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对话中提到的对硬和软的东西的知觉,与对颜色和声音的知觉一样,我们只能通过被触及、被看到、被闻到东西来觉察某物的硬、颜色、气味,但我们触摸一个硬东西,但不可能触及到硬本身(硬性),颜色性也同样无法感受到,而只能感觉到颜色(个别色彩的东西)。尽管如此,为了知觉硬的东西和有色彩的东西,我们只有先行明确地领会到了硬性和颜色性所意味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无论如何都在此存在着,并因此要求一种让它们在此被拥有的行为。
海德格尔指出,就考察的顺序而言,当我们考察被觉察的颜色和声音时,多出来的东西才会显现,存在、差异存在等等才会给予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多出来的东西”是感觉的附属物。但就知觉的可能性而言,“多出来的存在”不是“多余的”,不是感觉的附属物,而毋宁是先行被给予的东西,只是其本身并没有被认识、把握、追问。就其没有被特意地看到而言,海德格尔认为,“它是在奋力追求着的察看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是先行保持在眼中的东西,必然已经被领会了的东西,由此通常被我们觉察为某种存在者的可感的东西——无非就是形成呈现可能的可觉察性领域的那种东西。”(14)需要指出的是,其“先行”特征,后来被康德规定为先天。
而海德格尔并不满意康德的努力,他认为,这里揭示的先行被给予的东西、先行领会、先行把握,是一种非关系、非概念的觉察活动。“存在”(das Sein)这个词是语法上的动名词,相对于动词“是”(sein),这个词最熟悉的形式就是起谓词功能的是(ist)。“天是蓝的。”、“门是关着的。”每个人都理解这个“是”,我们立刻就知道“是”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使用“是”或宽泛的“是”的时候,完全理解它们的意思,它们隐藏在我们的语言所有口头或日常的表达中。我们领会了“是”这个词,我们熟悉其含义,但我们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明我们借助于它所“真正”意味着的东西。当我们劈头盖脸地被问及:这个“是”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们领会了它,但我们并没有把握它,我们对于“是”没有概念,我们领会具体的“是”或一般的“是”,却没有概念——非概念地领会它。
与此相应,直接地、沉浸着被所知觉之物带走的知觉活动,不仅是非概念的,而且是非关系的存在领会。我们躺在草坪上,沉浸于蓝天白云中,沉浸于所自行给予的东西中,跟随着小鸟的歌声,听任自己似乎被这种存在者所带走,以至于它包围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没有特意关注某个东西。每当我们特意关注某个东西时,这种沉浸状态、与歌随行的状态就消失了,也就意味着我们从直接的知觉活动中退出来,与存在者相对而立,存在者将作为认识对象、审美对象而呈现给我们。存在者在直接的知觉活动中,是非关系性地被觉察,亦即不是作为主-客关系中的认识对象被把握。
海德格尔认为,知觉活动的本质在于对存在者的一种非关系、非概念的觉察活动,而对于知觉活动中“多出来的存在”而言,它是在直接的沉浸活动中自行呈现出来的,不但不能通过关系、概念来把握,甚至都不具有可觉察性。在他看来,正是存在的不可觉察性造就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亦即存在的命运是存在之离弃、遗忘状态。每当对存在有所界定、有所把握的时候,存在总是从人类概念化思维的指间溜走。实际上灵魂与存在及其各种样态的关系首先就是在柏拉图的“相”、理念中被概念化,然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彻底带入到与理性的本质性关联中,带进了思维和判断的形式中,后来在中世纪和康德那里,先验的真、善、美作为对存在的本质性阐释就被确定下来了。
四、存在与真理
知觉是否构成,或能否构成知识之本质,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中被确定为与存在真理的关系,如果说知识就是对真理的占有,按照海氏的思路就是对存在者之无蔽的占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知识就处于与存在者的关系中。但知觉能够给予我们这种关系吗?尽管从知觉中,我们赢得了“多出来的存在”,但是知觉从感觉印象的角度而言,完全不同于存在本身,因为如果不是存在先行给予我们,我们是无法感知存在者的。显然,知觉不是被用于获得无蔽,当然也就不是被用来获得存在的。因此,也就不能说知觉是知识,“知觉是与知识不同的某种东西。”
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对知觉的全盘否定,更不表明知觉在知识中根本就没有地位和作用,相反却可能表明,知觉虽然、甚至必然属于知识,但并不是从自身出发,也不是首要地构成知识的东西。在柏拉图这里,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追问。但是,毋庸置疑,“知识是知觉”这一定义还是给我们指明了关键的一步,海德格尔指出:“知识是什么,知识的本质及其内在可能性,必须从一开始就要在力求存在本身发生的领域中去寻找;或者简单地说:知识之本质及其真理的可能性问题,就是一个存在之本质的问题。”(15)苏格拉底作为精神助产士,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泰阿泰德的定义,而是引导泰阿泰德逐步意识到,应该到什么领域去寻找知识的本质。知识之本质只可能居于灵魂本身所熟悉的存在者的范围内——简而言之:在灵魂奋力追求存在者(力求存在)的领域内,在占有存在者之无蔽的领域内。
通过解读泰阿泰德的第一个知识定义——“知识是知觉”,海德格尔指明了知识是什么这一问题应该到哪个领域去追问,这个领域就是存在领域,通过追问灵魂的内在规定性即力求存在本身,才能赢得回答知识是什么的方向。在这一力求存在的方向上,判断有真有假,信念有真有假,虽然知识只能为真,真是知识的本质特性,但是假、非真亦是知识的本质规定。与传统知识论者关注柏拉图《泰阿泰德》所提供的知识三元定义不同,海德格尔通过解读《泰阿泰德》,不但指出了追问知识是什么的领域和方向,而且还通过分析泰阿泰德所提供的第二个定义,揭示出真理与非真理的一体两面之本质性的渊源关系。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阐释柏拉图的《泰阿泰德》,其主要意图就在于揭示非真理的本质问题。
海德格尔通过解读《泰阿泰德》指出,知识与真、存在、逻各斯密切相关,必须从存在、无蔽(真理)的领域中寻找知识是什么的答案。这一结论,在传统知识论以及现代知识论者看来,是无意义的。无论是传统知识论的三元定义,还是现代知识论的确证理论,都支持知识与真理的本质关系,也承认知识与语言(逻各斯)的关系,但都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不可理解,甚至其真理概念即无蔽也是不可理解的。一方是存在学的解释学,它侧重于探究知识的发生及其发生的可能性;一方是科学逻辑主义,它侧重于建构知识、真理的逻辑条件及推演其逻辑值。两方相互不理解的焦点在“真”这一概念上,在海德格尔这里,“真”是动态地发生,亦即敞开、呈现、揭示的态势;而站在逻辑主义的立场上,“真”只是一个确定的值,一个静态的结果或实现。因此,海德格尔要为知识确定一个发生的领域,而现代知识论者则要为知识设置条件。海德格尔为知识提供了最本源的内容,现代知识论者为知识建构了最严格的形式,完全可以相互补充,但只是由于解释学的话语系统与逻辑主义的话语系统不能很好的兼容,因此造成的局面是知识论学术共同体普遍排斥和无视海德格尔对“知识”的思考。
实际上,回过头来看现代知识论的三个主题:真理、信念、确证,依然属于海德格尔所指明的知识领域。这个领域被柏拉图界定为灵魂问题,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存在问题。在这个领域中,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灵魂问题是一个问题。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现代知识论的讨论路向已经完全转向逻辑条件的自我设定,并沉溺于数学的精确性之美,再也不能容纳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对灵魂与存在的追问、对存在与真理的追问了,海德格尔说,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已经再也不会像柏拉图那样思考了。
注:
①本文所引柏拉图《泰阿泰德》,载《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714页,行文中统一在小括号中标出国际通行的斯特方码,不再一一标注。通过与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讲疏》中对所引段落的重新翻译和解读相对照,以彰显海德格尔的独特视角。
②③④⑤⑧⑨⑩(11)(12)(14)(15)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讲疏》,赵卫国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 156、160、166、172、181、191、195、198、199、225—226、224 页。
⑥海德格尔认为,施莱尔马赫按照习惯将希腊词 διαυοει~υ翻译为思维,而没有注意到 δια 通彻地(durch),υοει~υ觉察(vernehmen),这种流行翻译就沿着思维和理性的道路解释柏拉图关于知识的理论,一直到康德,这条道路就成为西方哲学的可能性之根据。
⑦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想要借此来说明,我们每次现实地知觉两种东西的活动中,不一定必然要特意地用眼睛把握所显示的东西,但也许任何时候都能够去把握。此时在进一步可觉察和被觉察对象上所显示出来的东西,也不是随意或无选择性地被选取或计数的,而是显示出了某种关系。只有当它们还以不同或相同的方式,可计数和被计数的方式等存在着的时候,两者才首先被觉察为存在着的。
(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62页。
〔责任编辑:金 宁〕
Perception:on the Way to“Being”:O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Theaetetus
Sun Guanchen
The key question in Plato’s dialogue Theaetetus is“what is knowledge?”In the dialogue,Theaetetus states his first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as:“Knowledge is perception”.Through intensively reading of the dialogue about the first definition of knowledge,Heidegger raises a question,what is knowledge?i.e.the nat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we must look for it in the area where the Being itself happening.That is to say,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 of possibility of truth are the problem of the nature of Being.From this point,we will argue that the passage of perception is not individual sense organ,but soul,and the essence of soul is pursuing the Being,the area of the possibility of perception is the area of the Being happening,is soul itself.So,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truth,soul and Being,Being and truth is the same problem in Plato’s Theaetetus.Because Heidegger’s ontological hermeneutical interpretation is absolutely different to modern epistemological logical interpretation,both side cannot understand each other,and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perception;knowledge;soul;being;heidegger
B516.54
A
1001-8263(2014)07-0035-08
孙冠臣,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 兰州730000
*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寂静的知识——埃克哈特与海德格尔”(14LZUJBWZY0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