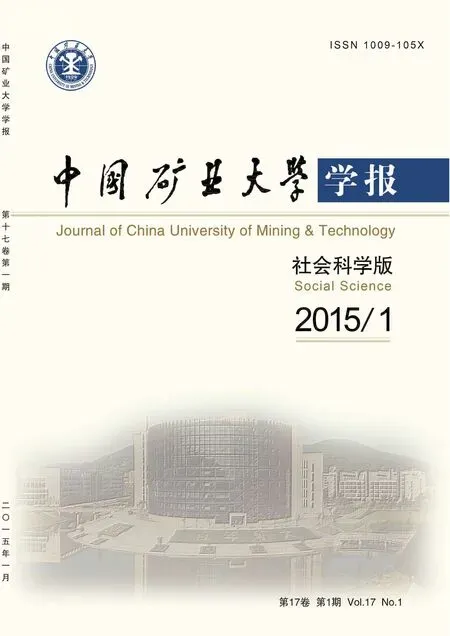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任 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任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100732)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议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承诺,国际舆论并非全是赞誉,“中国威胁论”始终未曾退出国际舆论场,只不过版本和形式不断翻新而已。目前,“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中国责任论”成为中国面临的主导性舆论环境。对这种舆论导向我们要有清醒认识,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定位,要处理好承担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的辩证关系,要处理好承担国际责任与协调西方大国的关系。
关键词:和平发展;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关于中国的种种议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主要存在“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四种论调。总体来说,“中国崩溃论”和“中国机遇论”处于国际舆论的边缘地位,没有占据国际舆论的中心。而“中国威胁论”却始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版本和形式不断翻新,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变种“中国责任论”的兴起晚于“中国威胁论”,却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结构性位置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国在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不俗”表现,颇受国际社会青睐,加之“中国责任论”相比“中国威胁论”而言要隐蔽、温和许多,所以“中国责任论”成为当下中国面对的主导性国际舆论环境。
一、“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原因和发展演变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论调。一般认为,“中国威胁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1]:第一阶段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的“黄祸论”;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立场,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在东南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极端仇视中国的红色政权,大肆渲染“红色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曾提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并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通过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日本、美国等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1990年8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首次提出“中国威胁”的说法。从村井友秀提出“中国威胁”至今20多年的时间,“中国威胁论”已经掀起了四次大范围的波澜。
第一波发生在1992~1993年间,由于苏联解体,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中国一时成为受西方发达国家关注的头号社会主义大国。这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主要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明冲突问题上做文章。时任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最先发难,他于1992年9月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办的刊物《政策研究》秋季号上发表了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的文章。他提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挑战”的论点,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美国学者哈克特甚至将中国描述为“苏联之后的一个新的邪恶帝国”。
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芒罗在这次辩论中依然发挥了主力作用。1997年,他和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出版,该书声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的方式行事”;“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作者预言,21世纪,“中美对抗将是世界最主要的两大势力的对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2]
第三波发生在1998~1999年间“李文和案件”爆发后,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出笼,由此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华声浪。这一波“中国威胁论”中,美国国内政治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第四波发生在2000年之后,延续至今。2000年之后的“中国威胁论”总体而言并未出现20世纪90年代那样集中爆发的浪潮,但是却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其一是“中国威胁论”的版本不断翻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就属于“中国威胁论”的“变种”;其二,“中国威胁论”涉及的领域和议题日益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议题从军事威胁、科技威胁、经济威胁、能源威胁到网络威胁、环境威胁、食品安全威胁、人口威胁等,几乎没有空白点,呈现全面性、深刻性特征;其三,这一波“中国威胁论”,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起着重要作用,即认定“后起的大国必挑战现有的霸权”。美国等发达国家正是在这种理论思维的支配下,炮制了种种关于中国威胁的版本和议题。
“中国军事威胁论”一直是“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议题之一。自2000年起,美国仿照冷战时期发布的年度苏联军力报告,每年都撰写和发布一本《中国军力年度报告》,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攻击中国军力的透明度。显而易见,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假想敌”。科技威胁、经济威胁、能源威胁等几种“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调,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者几种论调联袂登场,共同为中国的舆论环境制造压力。至于网络威胁、环境威胁、食品安全威胁、人口威胁等议题,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影响更为全面广泛。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产生,有一定的原因可寻:
第一是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事实。中国的发展速度着实让国际社会吃了一惊,也引发了美国的忧惧之心。2010年2月初,美国两大新闻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共同进行了一项题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1%的美国人认为21世纪左右世界经济的是中国人,43%的美国人表示21世纪的国际事务将由中国人主导,比认为这两个领域仍由美国人支配的比例分别高出1个和5个百分点。根据这一调查结果,有学者认为,这实际反映了美国人近年来在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过程时日趋明显的焦躁心理[3]。此外,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也让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切身感受到来自强大中国的“威胁”。
第二是大国崛起的经验推论。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国家,往往根据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得出国强必霸的结论。面对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西方一些国家难免会起猜忌,因为以他们的国际战略理论和经验来看,强国崛起难免会挑战既有的国际秩序,为确立本国霸权扫清障碍。
第三是美国等国家的国内政治原因。每当国内政治上有所需要,美国就会拿中国说事,可以说,炒作“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一贯的伎俩。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大选之年散布的一些舆论,“中国威胁论”是经常性的话题。只不过中国威胁论的具体内容时有改变而已。2012年是美国大选之年,世界金融危机尚未触底,美国经济仍萎靡不振,奥巴马和罗姆尼为赢得选票竞相攻击中国,中国经济威胁论甚嚣尘上。同时,“中国威胁论”也是美国建立和加强盟友关系的借口之一。近几年,美国通过叫嚣中国威胁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得以加强,也与中国周边国家如越南、缅甸等国家建立了密切关系。不管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还是出于结交和提升国家盟友关系的国际政治需要,设置关于中国的各种话题,包括“中国威胁论”,总是能够达到吸引选民注意、转移国内矛盾、提高政客政治知名度的良好效果。因此,炒作包括“中国威胁论”在内的各种中国话题,拿中国说事是美国等国家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段之一。
第四是文化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当今世界,争夺和占领文化与意识形态阵地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试图牢牢控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实际上,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美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导力确实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且不说其他指标,单是从“文化软实力”、“文化巧实力”等一系列引领文化意识形态潮流的新名词发源于美国而言,就可窥见美国文化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一斑。应该说,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充满自信的,这种自信包括对本国发展模式的自信。自建国起,美国只把纳粹德国和苏联所谓的“极权”国家视为本国发展模式的真正挑战,除此之外并未觉得有其他发展模式能够真正对美国的发展和霸权构成强大的外在威胁。但是“中国模式”却让美国有了危机感。尤其是中国在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扮演的“救星”角色,中国以大量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支持美国经济,这反而加重了美国对中国发展强大的威胁感。在美国看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和美国模式的衰落,连带的效应便是美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及美国掌控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的能力。所以,为了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重新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占领优势地位,炮制和炒作中国威胁论,歪曲、诋毁中国形象是美国必然采取的斗争手段。
第五是冷战思维阴魂未散。尽管1991年的苏联解体标志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抗的冷战局面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却并未立刻消失。美国并不认为遏制中国却又不诉诸武力的冷战思维已经过时。美国依然习惯于用冷战思维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和应对中国问题。冷战思维的存在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始终难以互相信任,猜忌心理的存在使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试探性因素,难以达成共识。现在虽然已经在讲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讲谋求两国的利益汇合点,但是由于冷战思维的影响,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如何谋求利益汇合点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威胁论”之所以一直没有退出国际舆论的舞台,并且版本不断翻新,一定程度上也受冷战思维的影响。
二、“中国责任论”的出场及其潜台词
从时间上考察,“中国责任论”的兴起要晚于“中国威胁论”,更确切地说,“中国责任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为什么得出如此论断呢?我们不妨对“中国责任论”的出场和流行做一番简单回顾和总结,看看“中国责任论”背后到底隐藏着何种潜台词,中国在“责任”面前应该何去何从。
“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实力的显著提升,尤其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强大密切相关。国际舆论在“中国威胁论”的主论调下,实际上也潜藏着国际社会对强大起来的中国的责任期待。早在1994年10月,时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的佩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冷战结束后,美中两国面临的挑战是确保亚太地区未来几代人享有充分的稳定与繁荣,“在这一方面,美中两国负有共同的特殊的责任”。1995年10月,佩里又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大国。我们确信接触是最佳战略,可确保在中国实力增强之时,它是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做的。”2001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凯利向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证词时说,我们要看中国怎样对我们做出回应,我们鼓励中国做出能够反映其社会地位和国际社会责任的选择。可见,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有责任期待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华战略的方向不明确,以及之后的小布什政府对华采取的遏制性预防战略,所以“中国责任论”常被“中国威胁论”压倒,从而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4]。
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随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被明确写入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变化,表明美国已经能够务实面对并接纳中国崛起的现实,愿意同中国共同经营双方都能从中获益的国际体系。用佐利克先生的话说,“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的提出,实质是对中国发展成就的一种承认。但是,这种接纳和承认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中国要“负责任”[5]。以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为标志,相对温和、理性、务实的“中国责任论”开始取代激进、非理性、情绪化的“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对华的主流态度。在美国的影响下,国际社会也开始使用“中国责任论”的提法。一时,“中国责任论”代替“中国威胁论”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主要舆论环境。
2008年,始于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让“中国责任论”再度升温。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展深受影响,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新兴经济体难以独善其身,而中国经济却能“一枝独秀”。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积极为缓解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献计献策,为稳定全球经济、恢复世界经济秩序贡献了本国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责任论”成为国际社会广为流行的主导舆论。在伦敦金融峰会上,中国甚至被西方媒体描述为“拯救世界的骑士”,美国智库提出“世界经济问题的解决基本上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两国集团(G2)”*中美两国集团“G2”的构想最早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在2008年夏季的《外交》杂志上提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2007年创造出“Chimerica”一词,以此表明中美两国战略地位的趋近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弗格森认为,“世界经济一直是由我们将其称为‘中美国(Chimerica)’的独特的地域经济体系所主导,即在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与其未来对手中国的经济联姻基础下,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形成了世界经济秩序”[6],其含义是中国被美国“同化”后与美国合作或“共同治理”世界[7]。不管是西方国家吹捧中国为“拯救世界的骑士”,还是鼓噪的G2、“Chimerica”,其实都是想通过强调中国的重要性来让中国为金融危机承担责任。“中国责任论”不过是西方国家试图让中国为金融危机买单的舆论工具之一。
“中国责任论”的流行,当然不仅仅局限在金融经济领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期待和要求也不会仅囿于这一领域。于是我们还可以把视野从金融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可以发现“中国责任论”具有多种形式,不仅涉及经济金融领域的贸易顺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涉及军事领域的军费开支问题、气候环境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资源能源领域的消费量问题等等,可谓领域广泛、形式多样。具体到美国对中国的责任期待,美国希望中国在经济上更大程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最好能够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以改变中美贸易逆差关系,并希望中国更多地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经济危机分担责任;军事上增加透明度,控制军费开支的增长;外交上帮助解决朝鲜、伊朗、苏丹达尔富尔等地区安全问题和热点问题;气候环境问题上,与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国际义务,等等。
从积极意义上看,相比较于激进的、情绪化的“中国威胁论”而言,“中国责任论”要温和得多,理性得多,而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期待和要求首先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发展崛起,英国前副首相赫赛尔廷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变化具有三“大”特征,即变化范围之大、变化速度之快和变化观念之深,中国对西方世界正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并无二致,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中国责任论”以合作的姿态和更具隐蔽性、迷惑性的形式,要求中国为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些责任和作用已经超越了中国的能力和责任范围。如果我们把敌意昭然的“中国威胁论”看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棒杀”,那么,温和隐蔽的“中国责任论”则可以看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捧杀”。在形式多样的“中国责任论”的舆论攻势面前,中国需要保持清醒认识,既不可在责任面前逞强显能,也不能逃避应尽责任,把握好应该承担和能够承担的责任的“度”和“量”。
三、责任面前,中国何去何从?
目前,中国正处在“责任论”的舆论包围中。对中国而言,积极参与、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关键问题是,中国要对国际社会承担多少责任、在哪些领域承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定要正确定位、清醒认识,否则一旦承担超过国家实力和能力范围的责任,不但无益于提升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反而将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
第一,要清醒认识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定位。从根本上讲,一国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能够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基于此,确定中国能够在哪些领域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首先要清醒认识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定位。对于中国的实力,中国国家领导人一直有清醒认识,这种清醒认识体现在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正确定位上。温家宝总理曾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8]
中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位,决定了在国际上中国还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大国、强国。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这绝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简单站队,而是由中国的国情、国力客观决定的现实。
看看我国的GDP总量,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GDP总量不断翻番,但是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更不用说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有可观的GDP总量,但只要按人均计算,甚至还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排在世界八九十名的位置。还有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都与世界大国有一定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全球政治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在世界国家综合国力排名中只位居第6名,排在美、日、法、英、德之后。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提供的世界主要国家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中国的指数是40,而位居第一的瑞典高达120,美国达115,与中国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为42、俄罗斯为65。这一组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数字说明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名号还有一定距离,国际社会所谓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提法其实是为中国设置的一个甜蜜陷阱,无非是为了忽悠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管国际社会如何定位中国,棒杀也好,捧杀也罢,中国人自己一定要有清醒认识,这是认定中国国际责任的大前提。
第二,要处理好承担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的辩证关系。一个国家能够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大前提是本国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中国古语说得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连自身修养都不达标、自己后院的家庭内务都料理不清楚的人如何能够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同理,一个本国贫弱不堪、动荡不安的国家如何能够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承担责任?可见,发展好本国的经济,处理好本国的事情,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好本国的经济,处理好国家内部事务,尽好本国的国内责任本身就是国际责任的一部分,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不管是从国际责任与国内责任的辩证关系上,还是从国内责任原本就是国际责任的一部分而言,承担好国内责任是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根本。
具体讲,中国如果能够在保持本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文化多元共存、生态环保可持续等方面有所成绩,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显而易见,中国若能发展好本国经济,解决本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民生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作为世界发展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为全球贸易增长、为全球扶贫减贫和提高生命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保持中国社会内部的和谐稳定将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推进。一个国家内部衰败不堪、战乱频仍,不仅无助于世界和平稳定,反而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已有的战争萌芽,导致战争规模扩大。中国近代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时的中国,由于国力衰微备受列强的侵略欺凌,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不仅无力维护世界和平,反而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和战争的中心区。国内尚且动荡不安,更遑论承担国际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若能处理好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并存共荣,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或许能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正在沿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向前发展,中国将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9]。这种新型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力求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力求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本身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贡献。
第三,要处理好承担国际责任与协调西方大国的关系。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的,绝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际责任”。西方国家一再强调中国作为“利益攸关者”的角色定位,其实质是希望中国承担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运行的成本,让中国替西方国家“分忧”。这不仅要求中国认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认同西方国家建构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而且暗含着中国必须完全融入其中,成为它们中的一分子。中国当然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设置的责任权限承担所谓的“国际责任”,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要做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绝不是跟在西方国家后边亦步亦趋,为它们分担责任。
但是,中国也无意以西方国家的对抗者和挑战者承担国际责任。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本意绝不在于与西方国家为敌,这与中国追求共建和谐世界、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初衷相违背。中国要让西方国家明白,在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面前,中国义不容辞,但是中国承担的责任与西方国家的责任并不完全相同,中国能够承担的国际责任必须是中国能力范围内的,并且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比如说在气候环境问题上,中国一直努力承担责任,承诺在未来的发展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必须是中国能力范围内的、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责任,超出中国能力范围、遏制中国发展的责任中国一定会说“不”。在国际责任问题上,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同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这不妨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的双重关系。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西方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全球性难题,必须互相合作、同舟共济,共同承担责任才能解决难题、化解危机,这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是“合作”关系;但同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共同的“国际责任”面前,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博弈,存在竞争关系。
总之,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必须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整体战略框架下,精心筹划,从被动更多转向积极主动,努力成为‘中国议程’设置的主导者,国际性议程的重要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在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的同时,更主动地以中国的话语声音去影响世界。”[10]同时要协调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既要勇于承担本国的国际责任,也要善于承担国际责任,既不简单按照西方国家的责任摊派承担违背本国发展利益、超越本国能力范围的责任,也不与西方国家为敌,让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误解。
参考文献:
[1]金灿荣.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与应对[J].绿叶,2009(9):64.
[2][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美)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M].隋丽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6,8,17.
[3]林泉忠.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主宰世界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17(14).
[4]金灿荣.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变化与应对[J].绿叶,2009(9):65.
[5]袁鹏.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N].东方早报,2005-12-22(A15).
[6][英]尼尔·弗格森,[德]莫里兹·舒拉里克.“中美国”的终结[J].金融评论,2012(1):13.
[7]张宇燕.G20是世界与中国的转折点[N].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4-16(2).
[8]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2007-2-27(2).
[9]刘建飞.“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J].现代国际关系,2007(4):26.
[10]陈正良,高辉,薛秀霞.国际话语权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93.
Dominan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Faced by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From "China Threat Theory" to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REN Jie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for international media because of the upgrad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with over thirty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Not all international media praise China’s commitments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 threat theory" with its constantly renewed versions has always been ther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t present,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which is the new version of "China threat theory" has become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We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this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strength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We should dialectical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domestic responsibi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western powers.
Key Words:peacefu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China threat theory; China responsibility theory
中图分类号:D641;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1-00013-06
作者简介:任洁(1977-),女,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2013)。
收稿日期:2014 - 08 -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