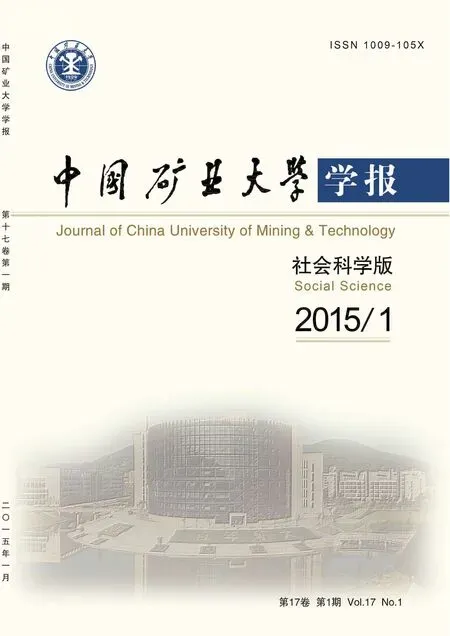探寻中国文化编码:叶舒宪的神话研究述论
王 倩
(1.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探寻中国文化编码:叶舒宪的神话研究述论
王倩1,2
(1.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叶舒宪的神话学创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神话原型理论的阐释与重构,并且出于重构本土文化大传统的需要,将神话原型的范畴从文学扩展到文化层面;第二,借用新史学“神话历史”概念,强调神话在历史进程中的塑造性作用,继而倡导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神话中国”概念;第三,为探寻中华文明发生机制的动力起源,创造性提出“玉石神话”(玉教)概念,以此建构自史前时期到当下的“玉石文化共同体”。上述三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为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反映了叶舒宪的大神话理念,即将神话从文学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文化基因与文化编码的本相。
关键词:叶舒宪;神话原型;原型编码,神话历史;玉石神话
目前,神话学在中国现有的学科机制内并不是一门学科,而在西方学术界,神话学却是引领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潮流的显学,它是唯一能够打通文史哲各个学科的一门综合性学问。自19世纪诞生以来,神话学就一直扮演了学术前沿阵地的角色,该领域的一些学者对欧美学术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诸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布劳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等等。在联接西方神话学与中国神话学方面,叶舒宪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作用,他对神话学的贡献与开创性工作,值得该领域的学人瞩目。
一、 从神话原型到原型编码
叶舒宪迄今出版了40余部论著,其中关于神话原型研究的有13部①具体论著信息如下: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译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叶舒宪:《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叶舒宪:《神话意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叶舒宪:《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叶舒宪:《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叶舒宪等主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从20世纪80年代编译的《神话-原型批评》一书,到近期主编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论文集来看,其学术生涯始于神话原型,学术创新亦源自神话原型。
叶舒宪对神话原型的兴趣源自剑桥人类学派的奠基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George Frazer)。叶舒宪童年时曾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法语班就读,此后在西安第四十一中学读书,“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对象’,中学毕业时分配到一家兵工厂当学徒。7年后赶上恢复高考,以24岁的年龄走进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课堂。”[1]15大学毕业后留校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叶舒宪,因个人求知与工作需要,大量涉猎了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书籍,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神学等。叶舒宪说,“为了弄明白《圣经》洪水神话的性质,我在北图借到了弗雷泽的大著《旧约中的民间故事》,这位人类学家俯视全球的学术气魄和详赡的资料收集功夫,给我了很大的震动。这也就是促动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醉心于译介原型批评的潜在因素。当我看到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称赞弗雷泽的《金枝》为伟大的文学批评著作时,一种打通人类学与文学研究的意愿就开始萌发了。一部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竟然被文学理论家视为本学科的珍宝,这是否可以提示人们,学科的藩篱是人为的,而事物的存在本来是不分学科和专业的。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人类学。如今回想起来,她也许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能使人心胸开阔、眼界开阔的一门学科了。文学理论家弗莱之所以能够创立他的原型批评体系,显然同人类学的强烈影响密不可分。由于同样出身于文学专业,我对神话学、人类学的兴趣使我自然地选择了弗莱的理论取向,从翻译、介绍到尝试应用原型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等)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现象。”[2]自序1-2从以上表述可见,叶舒宪对神话原型的兴趣始于个人学术爱好,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剑桥人类学派看待问题的整体性视角,以及神话原型具有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深深吸引了他。基于对神话原型批评的认同,叶舒宪开始系统介绍神话原型批评。他早期系统介绍神话原型批评的著作如《神话-原型批评》、《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这两部著作重点在于阐释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这两部著作可谓应运而生,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是中国学界引入西方理论与方法的高潮时期,加之中国大陆文艺学界出现本体论转向。
叶舒宪对于以弗雷泽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派极为推崇,但他早期关于神话原型的译介中并未重点阐释与介绍剑桥学派,而是将其与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派、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学派置于同等地位,将三者视为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渊源。叶舒宪仅用简短的一句话表明了自己对文化人类学的认知:“可以说,来自上述三方面的跨学科动力,及其在文艺学中的重新组合,奠定了原型批评坚实的理论基石。其中以人类学的影响渗透最早,也最为重要,因而也有人把原型批评理论称为‘文学的人类学’。”[3]43
作为一种外来理论,神话原型批评是在总结西方学现象与规律基础上提出的,其适用度尚待进一步检验。方克强早就指出,因弗莱等倡导者自身学养的限制,神话原型批评忽略了东方文学,具有跨文化研究的不彻底性,中国学者在运用神话原型时应特别谨慎,尤其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神话概念与批评对象的选择;第二,原型概念与批评方法的运用;第三,人类集体意识、集体潜意识概念与批评目标的达成[4]79。关于这一点,叶舒宪其实非常明白,只不过他对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兴趣并不在于单纯译介,而是另有目的。“从叶氏原型批评的实践来看,他并非单是倡导原型在中国文学中的应用,也不只是拿中国文学文本来检验原型理论,其首要主旨是利用原型批评来探寻中国文学的发生机制,进而重构中国文学的生成语境。”[5]30
这里要指出一种现象,即叶氏关于神话原型的应用多半与中国的女神有关。早在1987年,叶舒宪主持的课题《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欲主题》,获得国家教育部首届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该书后来完成后定为《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于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后来的一些论著或译著,诸如《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活着的女神》,不少与女神相关。那么,这究竟是神话原型理论所致,还是另有缘由?关于这一点,叶舒宪在《激情》这部叙述自我体验与学术成长的书中详细讲到了其中的缘由。概而言之,大致有两种原因促使他走上了探索爱与美相关的学术探讨,一是大学期间同学的不幸遭遇激起的感慨,二是个人心中的一些情感郁结。他的大学同学张久平因在大学谈恋爱而被学校开除,以及另外一位校友康正果毕业论文因探讨晚唐诗人韩偓诗歌而被学校以宣扬色情思想为名被取消答辩资格。叶舒宪对此极为痛心,并坦率表明自己的心态:“我自己在大学时代之所以对以上两桩发生在身边的事件感触颇深,这可能同12岁那年被外国语学校革除学籍的少年心灵创伤有关,容易引发同病相怜的反应。”[1]27同学的不幸际遇给了叶舒宪一种世间无情无爱的感慨,而他自身因为本科毕业论文险些被学校极左思潮终结学术道路的经历,使他对学术之外的机制产生另一种发自内心的反叛心理。除此之外,他大学毕业后个人情感上的一些不如意经历,也促使青年时代的叶舒宪在不自觉间将爱情主题列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叶舒宪并不讳言,“在相遇与寻求的双重希望中进一步体尝爱情的真谛,并在不知不觉地走上研究爱情乃至性爱的学术旅程。……为了从根源上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爱情观念,和古代文学中性爱主题的表达方式,我进入了比较神话的领地,试图从文学的母胎——神话中去寻觅爱欲女神的足迹。”[1]32由爱神至女神,由此出现了《千面女神》、《活着的女神》这类与神话图像学相关的著述。对于神话的痴迷以及对神话原型的研究,使叶舒宪发现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现象中的一些难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些难题无法用神话原型的理论来解决,必须从思维模式或发生机制入手进行探讨。
利用神话原型重构中国本土文学发生机制,这样的尝试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叶舒宪关于原型的理解依然局限在文学范畴,并未突破弗莱的界定。在研究范式上,叶舒宪一方面采用弗莱的整体文学思路,另一方面采用了弗雷泽的比较研究模式,将研究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以此获得阔大的比较效果。叶舒宪极为认同弗雷泽的比较研究模式,他甚至在学术回顾中这样写道:“备课阅读中让我受惠最多的不是文学研究家,而是人类学家弗雷泽。他的巨著《〈旧约〉中的民间传说》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知识全球化的打通式境界。回过头来再看那些就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而评头品足的文学批评,会显得单调乏味。眼界被局限在民族国家这种近代以来‘想象的共同体’之内的学人,难以练就一种俯视环宇的学术气魄,也就不易打开知识创新的局面。这种意识或许在暗中驱动我逐渐脱离东方文学、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教学,热衷加入比较文学领域。”[6]6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弗雷泽的比较视野开阔,但同时存在将同一现象罗列堆积的不足,国外一些学者对此颇有微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E.E.埃文斯-普理查德(E.E.Evans-Pritchard)将这种比较称为“剪刀加浆糊”的方法,他颇为严厉地指出:“这里压根儿就没有比较,有的只是将那些似乎有些共同性的事项拼凑在一起。对此,我们确实可以说,它使得作家们能够做初步的分类,而在此种分类中,大量的观察能够被置于数量有限的标题之下,由此导入一些秩序;就此而言,它曾有过价值。但是,与其说它是比较研究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描述,差不多就是心理学家过去所说的‘猎奇法’(anecdotal method)。大量偶然的事例被拼凑在一起,以阐释某种一般性的观念,并支持作者论述那种观念的论文。从来不曾有过以未被选择的事例来检验其理论的尝试。当从一个任意的猜测推导出另一个任意的猜测(被称作假说)时,连最起码的谨慎也被忽略了,归纳法(求同法、求异法和共变法)的最简单的准则也被忽视了。”[7]12(按: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中谈及闻一多神话考辨“强作解人”这一方法上的危险,同时谈到叶舒宪的神话考论每每流于牵强附会之弊端。)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叶舒宪当然明白弗雷泽比较方法的不足,但他并非是简单套用,而是欲借助神话原型的理论与弗雷泽的比较模式,研究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学现象,继而解决中国文学与文化发生机制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叶舒宪神话原型的研究从阐释转向了重构,直至创造性地提出原型编码的学说。
叶舒宪从这种以文学意象和象征形式出现的原型内涵的启发中提出了原型图像学这个术语。所谓原型图像学,实为一种跨学科的图像阐释理论,叶舒宪对其阐释特征做出概括:“比较图像学的方法特征有二,即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指的是不同文化的图像之比较,希望能够达到异中求同的‘打通’效果;或者从同中见异,更加明确地把握不同文化的艺术形象特色。纵向指的是某一个原型图像与其后代的各种变形图像之间关联的认识。”[8]5国外神话学与图像学领域并不存在“原型图像学”或“比较图像学”这样的概念或术语,叶舒宪之所以创造性使用这样的术语,实乃希望借助二者打通原型与图像之间的隔阂,并在理论上加以提升。因缺乏足够的理论建构体系,比较图像或原型图像学方法在叶舒宪的图像研究中并未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真正富有方法论意义的图像理论建设是“原型编码”概念的提出。
“原型编码”也称“N级编码理论”,是叶舒宪近期提出的原型概念,其内容指向了文本、图像、口传等几种表述方式。叶舒宪这样界定原型编码的概念:“将文物和图像构成的大传统文化文本编码算作一级编码;将文字小传统的萌生算作二级编码的出现;用文字书写成文本的早期经典,则被确认为三级编码;经典时代以后的所有写作,无非都是再编码,多不胜数,统称N级编码。”[9]3此处的概念出现了“大、小传统”,尚需略加解释。“大、小传统”这一概念并非是叶氏首创,其名称最初源自美国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一直致力于分析非西方世界原住民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他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小传统的概念。雷氏眼中的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10]71。叶舒宪改造了大小传统的概念与内涵,赋予它们以特定的意义:“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11]9就像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一样,叶氏的大小传统也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它是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现状而提出的,有轻文字而重非文字资料的倾向。关于这一点,叶舒宪有明确的表述:“我们再造大传统小传统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书本主义知识观、历史观的束缚,面对实际的新材料、新知识,有效地重建新的中国文化观。”[12]4换言之,叶氏对雷氏大小传统的改造服务于重构中国文化观这一现实诉求,即希望借助于文字之外的图像、实物、符号、仪式、口传叙事等非文字资料重构中国文化大传统,以此还原被文字叙事遮蔽、扭曲乃至颠覆的历史与文化本相。
原型编码这种主张是针对什么而提出的呢?它与神话原型究竟有何关系?概括地说,原型编码是针对中国长时段前文字时代的大传统与短时段的文字小传统而言的,要解决的是人类如何记忆文化原型的过程问题。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强调,人类记忆文化的过程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按照某种编码规律进行的。史前无文字书写时代的人类的神话与信仰是后世文字时代所有文化编码的源头,即一至N级编码的文化原型。明显看出,叶氏的原型编码强调神话信仰时代的叙事对后世文化表述的编码作用,这是叶氏对原型内涵的扩展与改造,与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原型概念有着根本不同。“从理论渊源来看,原型有两种类型:荣格的心理学原型与弗莱的文学原型。尽管二者同时被称为原型,但它们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别。荣格从心理学视角观照文学,强调原型的非理性因素,其理论模式侧重于描述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及心理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荣格的原型其实等同于原始意象。另外,荣格的原型批评主要探讨文学创造过程中心理意识的历史,更多带有一种将文学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意图。就原型的内涵而言,弗莱的原型批评是一种文学研究模式,原型因而属于文学范畴,它是一种文学的功能性单位,用来揭示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弗莱的意向并非强调原型的独立性与创造性,而是偏向于考察原型的传统性与历史性,其原型批评的最终旨趣是探索文学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规律,从文学自身去描述文学之本质。该批评模式带有鲜明的整体文学史意识。”[5]33可以说,叶氏的原型编码已经脱离了荣格与弗莱的范畴而进入文化层面,指向了人类文化表述与记忆的编码问题。
叶氏的原型编码仅仅具有时间上的指向,对于空间并无具体所指。一个突出的特征,原型编码下文化涵盖的空间范围极为宽泛,且不说其他国家,姑且以中国为例,它指向现代中国版图上的所有地域,东西南北中各有所指。但这里同时存在的问题是,同一时间限度下的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差异,譬如,广汉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迥异于同一时期的中原文化,出土文物展现的各种特征已充分表明这一点。因此,如何利用各级编码阐释中国版图内不同区域的文化在同一时段内的互动关系,继而重构该时期的文化传统,这一问题成为当前原型编码学说建构的关键。从理论层面而言,该论题的难度极大,论及内容极为复杂,涉及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神话学等相关学科。因此,原型编码迄今尚不能称之为理论,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学说或假说,因为其理论深度与逻辑框架皆有待于不断完善,其普遍性与适用性尚需在实践中不断验证。
至此,我们要发问:叶舒宪为何要提出原型编码这种主张?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因为它涉及原型编码的生成语境。笔者以为,催生原型编码主张的缘由有三:第一,文学人类学学科理论建构的需要;第二,神话原型自身的不足;第三,神话自身作为文化基因的特征。这里重点阐释第一种缘由。作为一种跨学科的阐释模式,文学人类学的生成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上半叶,但直到20世纪末叶,它才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确切地说,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模式始于20世纪上半叶,凝聚了茅盾、闻一多、郑振铎、鲁迅等早期先行者的努力,他们以西方人类学视角阐释中国本土文学及文学现象的研究,开启了中国文学人类学跨学科阐释模式的先河*因缺乏人类学的田野实地考察,所以他们的阐释模式某种程度上是借用人类学的视野观照中国神话,但各有侧重。茅盾主要利用人类学的神话仪式学派相关观点解读中国古代神话;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运用了人类学学者芮逸夫收集的苗族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以及人类学关于图腾的相关理论来解读伏羲;郑振铎的《汤祷篇》直接运用弗雷泽替罪羊理论改写了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商汤祈雨故事,将商汤塑造为一位代民受过的替罪羊形象。通过一系列的文学解读工作,这些早期的学者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文学人类学跨学科的阐释模式,它不同于后期学科意义上的文学人类学,本质上为解读中国本土文学及其现象的一种路径。。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面临学科理论建构的艰巨任务,关于这一点,叶舒宪有明确的表述:“现在大家面临新学科建构的任务,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起码有以下几点基本诉求:一要有学理依据,能够有效解释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二要有独树一帜的开拓性,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三要有可传播性,便于学习、推广和应用。不希望搞成玄虚的自娱自乐或纸上谈兵。出于传播的考虑,要尽量避免将中、西方的东西彼此生硬地翻译,选择采用简明的、便于表现和记忆的术语。”[9]2在此背景下,叶舒宪建设性地提出了“四重证据法”*所谓“四重证据”,指的是如下四个方面的研究资料:一,传世文献及传统文字训诂,谓之第一重证据;二,传世文献中所没有的新出土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及竹简帛书等书写文献,谓之第二重证据;三,汉语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之外的、具有人类学特色的材料,包括民间口传叙事、仪式、礼俗,民俗学、民族学提供的跨文化资料,谓之第三重证据;四,考古出土的和传世的实物及其图像,谓之第四重证据。表面看来,“四重证据法”似乎有一种工具论的色彩,从命名上可以看出这一意味,但实际上,“四重证据法”不单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古史重构路径,而是人类学重构本土文学的框架的基本路径,其背后是“文学共同体”这一宏观文学理念。与“大小传统”之概念,试图以此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理论框架。当然,这就涉及第二重缘由,即与神话原型理论的缺陷有关。荣格等人倡导的神话原型理论限于文学范畴,且不涉及神话图像,在实践中有许多现象无法解释,叶舒宪改造之后的原型编码主张则能够解释弗莱神话原型无法解释的文化传承问题。最后,原型编码的提出与神话自身作为文化基因的特性有关。国外神话学因自身为跨学科研究范式,对于神话的界定并未限于文学范畴,神话的文化属性已成为所有神话研究者解读神话的前提。但在中国,神话尚属于文学范畴,文学本位主义的研究依然在学界盛行,这也是叶舒宪最后要破除文学范畴神话理念的原因所在。
一旦意识到神话具有的塑造文化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功能,叶舒宪的原型编码学说便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大传统注定发生不可分割的关联。原型编码便不仅仅是针对重构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它面对的将是重构中国历史叙事与发生机制的问题,由此出现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神话历史”。
二、 “神话历史”与“神话中国”
从2009年开始,叶舒宪的神话研究中频繁出现了“神话历史” ( mythistory)这个词语,与之同时还有“神话中国”这个名词。那么,在叶舒宪的学术名词中,究竟什么是“神话历史”,什么是“神话中国”呢?叶舒宪使用这些学术术语的意图何在?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神话历史”一词做简短梳理。
就“神话历史”一词的来源而言,叶舒宪并不是这个术语的首次使用者,他只不过是这个术语的借用者。确切地说,“神话历史”这个词语源自新史学,是新史学反思历史属性的产物。“神话历史”一词首次出现于1985年,美国学者威廉·H·麦克尼尔( William H·McNeill)是这个术语的首创者。在1985年的美国历史协会第100 届年会上,作为会长的威廉·H·麦克尼尔发表了题为《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演说*参见McNeill,H.William. “Mythistory or Truth,Myth,History, and Historia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1986) : 1-10.该文后被收入麦克尼尔论文集《神话历史及其他论文》一书(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 3 -22.) 。中文译文曾刊载于《史学理论》杂志1987 年第1 期,后被《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 年第8 期全文转载,最后被收入《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一书。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王建华等译: 《现代史学的挑战: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75 -488。。当年威廉·H·麦克尼尔使用“神话历史”一词时,其意图在于反思历史的虚构性,“神话历史”指的是神话般虚构的历史。“在使用神话历史这一术语时,麦克尼尔强调: 历史叙述只不过是历史事件的阐释,历史的根本属性是神话性——虚构,作为科学的历史并不存在,只有作为阐释学或诗学的历史。在麦克尼尔的神话历史范畴内,神话并非是历史的代名词,而是虚构的同义词,它与真实相去甚远。麦克尼尔的立足点是史学的诗学性质或虚构性,他本人并未对神话与历史生成的先后顺序做任何甄别。”[13]202时至1990年,新史学理论的另外一名倡导者唐纳德·R·凯利(Donald R.Kelley)再次对“神话历史”做了阐释*参见Kelley,R Donald.“Mythistory in the Ages of Ranke.”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e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Eds.Iggers,G.G,and J.M.Powell.Syracuse &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0: 3 -20.。唐纳德·R·凯利眼中的“神话历史”指的是具有诗性性质的历史,即强调历史的叙事性。与此同时,纳德·R·凯利又强调神话叙事的真实性。“历史起源于神话并且逐渐摆脱了这种神话特性,直到马基雅维利和奎恰尔迪尼时代,它获得彻底觉悟为止——或者可能是伏尔泰和吉本时代,或者可能是蒙森和兰克时代,或者可能是这个世纪‘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等等。”[14]本质上说,新史学研究者眼中的“神话历史”概念与新史学关于历史属性的再界定密切相关,它要破除的是历史作为科学这样一种宏大历史观,强调历史是诗学或阐释学的本质属性。对于神话,麦克尼尔与凯利并未做过多阐释,他们至多承认神话在叙述历史层面具有真实性的一面。
进入21 世纪之后,新史学对于“神话历史”有了新的理解。身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对“神话历史”做了更为深入的阐释。马里的“神话历史”概念则以承认神话作为历史性叙述为前提,探寻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在他看来,神话在历史之前产生,并且是作为历史的“史前史”而存在。马里坚持认为,神话被证明是根本的起源性叙述,因此,神话是第一位的,历史是第二位的。他断言,“一则神话无论多么富有传奇意味,它并不表示编造或纯粹的虚构,因为它通常包括共同体历史中所含有或涉及的关键问题,诸如共同体共同的祖先和边界的传奇。这些问题需要并能催生关于历史的神话,因为它们不仅适于形而上学的神秘事物,诸如共同体的最初起源和命运,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真实的叙述是共同体成员所信赖并经历的事实,即便( 或者正好因为) 它们是神话的而非逻辑的或历史演绎的。”[15]4不难看出,马里的“神话历史”概念强调神话的凝聚力即神话整合社会文化情感的功能。就像威廉·H·麦克尼尔与唐纳德·R·凯利,马里的“神话历史”概念是其反思历史的概念性工具,其基本意图在于通过神话探寻历史的元初面貌,继而重构历史及史学观念。
熟知西方知识界动态的叶舒宪,极为敏锐地觉察到了“神话历史”一词的整合性作用,他将其应用在神话学领域,用来彰显神话的塑造性功能。颇有意味的是,叶舒宪使用“神话历史”这个概念时,淡化了它原来所指的历史诗学性质,而强调神话在历史进程中具有的整合文化作用。他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按照《神话历史》一书著者马里教授的判断,这个词在古代的对应称呼应是‘历史的神话’(historical myth)。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则是把经书神话、圣人神话、皇权神话等看做是‘天人互动’范式支配下构成的历史神话(叙事)。‘历史的神话’或 ‘神话历史’概念的再提出,可以驱散 ‘历史科学’说造成的假象,消解历史与神话的截然对立,将神话从狭小的文学本位的学科概念局限中释放出来,使它发挥文化编码和神圣叙事的方法论作用,成为探索中华文明本源的一把观念钥匙。华夏文化几千年传统并未像古希腊传统那样,让神话被哲学和科学代表的理性主义所取代。神话作为一种信仰和思维,从史前的口传时代穿越漫长的文字历史,早已作为文化根基和编码规则。”[16]8上述话语明确地表明了叶舒宪本人的意图:他使用“神话历史”这个概念并非是强调历史的诗性特征,而是强调神话具有的文化编码和神圣叙事功用,以此来揭示并重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因此,他在“神话历史”的思维方式基础上提出了“神话中国”这个概念,以此表明神话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塑造性作用。关于为何使用神话历史与神话中国这两个语词,叶舒宪本人有非常明确的表述:“研究神话历史,不等于研究神话,而是要研究文化文本及其编码程序。出于这个目的,才会有研究对象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的根本性转换。”[17]11
那么,究竟什么是神话中国呢?叶舒宪对此有所界定:“所谓‘神话中国’,指的是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式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五千年文化传统,它并未像荷马所代表的古希腊神话叙事传统那样,因为遭遇到‘轴心时代’的所谓‘哲学的突破’,而被逻各斯所代表的哲学和科学的理性传统所取代、所压抑。惟其如此,神话思维在中国决不只是文学家们的专利。从屈原到曹雪芹的本土文学家群体固然都是再造神话感知与神话叙事的行家里手,不过,由老子、孔子开启的儒道思想传统同样离不开神话思维的支配。道家理想中的神仙们和儒家推崇备至的圣人和圣王,无不是最具有本土特色的‘神话中国’之体现。”[18]35不难看出,“神话中国”并非是地理学范畴,而是文化范畴,它指向了中国久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这样说,叶氏的“神话中国”绝非是为了反思中国的历史属性而创造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西方新史学的研究者有着本质性不同。根据叶舒宪本人的论述,我们能够判断,“神话中国”是叶舒宪为了重构中国文化传统而建构的一个术语,其工具便是前文探讨的原型编码理论。从叶舒宪2009年以来的神话研究看,与其说他的“神话中国”是重构中国的文化大传统,倒不如说是为了验证“神话历史”这个概念。因为叶舒宪所有的神话研究都围绕神话般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进行的。他的研究表明,中国八千年的文化传统具体说来是以玉器崇拜为源头的文化传统,都是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模式进行编码的。这就表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神话为基因而进行编码延续下去的,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神话文化传统,只不过这种传统一般人难以觉察,需要借助于神话编码理论加以层层解读。
较之于西方新史学的“神话历史”概念,叶氏的“神话中国”明显缺乏理论支撑与逻辑论证,并且中国史学界对这个术语似乎不是特别感兴趣,相关的探讨少之又少。在笔者看来,“神话中国”这个术语所指是中国几千年来具有神话性质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已经偏离了这个术语的能指,因为“神话中国”的语义核心是中国,而叶氏的界定是文化传统,这就在称谓上给人一种错觉。另外,“神话中国”中的“中国”实际上也不恰当。叶氏拿“神话中国”来重构中国五千年甚至八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在五千年或八千年之前,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否将其所处的地域称为“中国”还是个问题。
在“神话中国”这个概念中,神话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叶舒宪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中国学界应当突破狭隘的将神话当做文学范畴的做法,还原神话应有的文化基因面貌。他明确表示,中国当下的学科体制将神话划归到文学的做法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神话概念远大于文学。“研究实践表明,神话作为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一种概念工具,它具有贯通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从这种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因而,不光是学习文学要从神话开始;要进入历史,首先面对的就是神话历史;要进入哲学史,首先就要熟悉神话哲学和神话思维。”[18]34实际上,这种强调对于叶舒宪而言非常无奈,它是叶舒宪出于神话在中国学界的错误定位而发出的呼喊。因为国际神话学界早就将神话学作为一门科学,自19世纪诞生以来,神话学与文学、历史、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一样,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然,西方的神话在概念与范畴上均是独立的,除却神话学之外,它并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但在中国,因现代学术语词中并未出现“神话”一词,现有的“神话”概念“是20世纪初期梁启超、蒋观云等人引入现代汉语中的。在此之前,中国学术话语中没有这个词,当然也没有神话学这门学问。最初热衷于介绍和研究神话的学者以文学家为主体,如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谢六逸等,所以至今我国的神话学教学仍然只限于在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课程范围里进行。”[19]1这种还原神话地位的呼声大概源自两个方面,其一,国外神话学日新月异的研究与对神话文化范畴的定位;其二,国内学界对国外神话学的隔膜以及学科机制将神话视为虚构文学叙事的做法。与第二个原因密切相关的是神话的文学范畴,这一点是叶舒宪极为不满的。叶氏这种将神话从文学中解放出来的做法实际上与他倡导跨学科的神话研究方式有关,因为将神话视为虚构之物的文学本位主义的研究方式极为严重了阻碍了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毕竟,国外神话学的研究是多方位多学科交叉进行的,出现了众多的理论流派与方法*20世纪国外神话学理论与方法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阐释可参见王倩:《20世纪希腊神话研究史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中国神话研究的单一模式需要有人打破,并将中国神话学与国际神话学对接起来。
从研究路径上看,叶舒宪“神话中国”的概念主要是依靠玉石神话的研究进行的,叶舒宪对此有极为严肃的总结:“探索中华大传统的关键,是弄清从多元到一体的转变奥秘。玉石神话观的传播就恰好起到奠定文化认同基石的作用。”[6]8这并不奇怪,因为叶舒宪的学术生涯源自神话原型,他对原型的理解早已超越了文学范畴而进入图像原型世界,玉石具有的特殊性质与功用使得叶舒宪敏锐地意识到玉石神话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塑造性作用。
三、 玉石神话
叶舒宪关于玉文化的研究始于2005年,最初的契机来自对考古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的关注,如他在2006年第4期《文艺研究》发表的《猪龙与熊龙》、2006年第5期《文学评论》发表的《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跨文化解读为例》等论文。因“第四重证据”理论建构需要,他开始将玉器、青铜器、彩陶等作为第四重证据的资料纳入研究视野。但此时他对于玉器的关注仅限于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物证,并未关注玉器自身的形制、质地与相关情况。直到2009年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启动,因探讨文明发生机制的需要,他才正式将玉器列为重点研究对象。2012年该项课题结项,通过一系列的玉器图像研究,叶舒宪意识到玉器对于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性,在2012年课题结项之后,继续投身于玉器研究,并提出了“玉石神话”和“玉帛之路”等概念。叶舒宪为此总结道:“2012年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得出结论:伴随华夏文明产生的神话想象有其深远的史前根脉,远远不是汉字出现的年代所能局限。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石神话及由此形成的玉教信仰。从神话学视野看东亚地区的玉器起源,可以发现每一种主要的玉器形式(如玉玦、玉璜) 的发生,背后都有一种相应的神话观念在驱动。”[20]
只不过,叶舒宪关于玉石神话的定义过于简单,他采用了一种描述的方式来界定玉石神话:“在大自然提供给人类的物质材料中,石头曾经是人类祖先时代接触最多也最为熟悉的一种。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际,石头中的某些特殊种类获得先民的青睐。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成为所谓神石或圣石,玉石神话由此应运而生。从黑曜石和绿松石,再到青金石、金和铜等金属矿石,所有这些特殊的石头都曾经被神话思维赋予类比天神的联想和宗教意义。”[21]29从上述界定中,我们无法获知玉石神话的起源、发展,以及时间与地域分布,更无法获知其具体所指,即玉石神话是中国特有的还是史前时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神话信仰?从叶舒宪一系列的研究中似乎可以看出,玉石神话普遍存在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以及中国早期的神权政治时代,只不过随着那些早期文明的消亡,玉石神话信仰也随之消亡,而在中国一直延续到封建帝国时期,甚至延展到了近代和当代中国社会。
为何史前人类将石头作为崇拜的神圣之物?叶舒宪并未做深入阐释,这里做个简短的补充。从比较神话学的国际视野来看,史前时期即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的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石头信仰,只要看看世界各地出土的石头建筑、石制物品、乃至于石头洞穴就可以明白。即便是到了王权时期,世界各地依然继承了巨石文化的传统,留下了诸如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帕特农神庙、金字塔,以及卢克索神庙(Luxor Temple)、卡尔纳克神庙(Temple of Karnak)之类的遗迹。史前时期文化传统中的石头不同于现代化学意义上作为硅铝酸盐、硅磷酸盐、硅硼酸盐等化合物的石头。一种普遍的认知乃是,石头因为其自身的质地与存在方式较为恒久而得到了关注。按照宗教学者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说法就是,石头具有特殊的外形与性质,“它的伟力、它的静止、它的体积、以及它奇特的外形与人类绝无共性;它们同时表明存在着某种外形炫目的、可怕的、富有吸引力的以及颇具威胁的事物。它以其崇高、坚硬、外形状和色彩,使人类直面某种与他所属的世俗世界判然有别的实在和力量。”[22]206总之,正因为石头的这种属性,它成为了持久、永恒、不朽,乃至于神圣的象征符号。世界各地的石头崇拜与玉石神话建立在石头的特殊的性质之上,后起的玉石神话也与石头质地有关。
叶舒宪为何要使用“玉石神话”这个概念?难道仅仅是出于个人喜好?实际上,玉石神话是一种策略,是叶舒宪重构中国文明之根与文明发生动力机制的工具。他明确表示:“探究中国文化大传统,需要立足于世界文明的全局视野,找出华夏特有的要素。判断文明的起源,国际学界通用的有三要素指标:文字、城市、青铜器。在这三要素之外,华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要素:玉的信仰和玉器生产。也就是说,世界主要古文明的起源均有三要素的推动之功。而探讨华夏文明发生历程,还必须加上更为深远的一种动力,那就是史前的玉文化。在文字、城市、青铜器三者都没有出现于东亚的情况下,玉文化却率先出现于北方地区,并且随后在辽河流域、黄淮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的范围里长期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中原地区以外的几大玉文化圈,最后汇聚成华夏玉礼器传统,同后起的青铜器一起,衍生出文明史上以金声玉振为奇观的伟大体系。”[11]11不难看出,叶舒宪的玉石神话研究强调神话图像在建构宗教意识形态与王权机制方面的建构性作用,它对文明起源研究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长久以来,文明探源的研究者习惯了从文字、城邦、金属冶炼技术等方面探讨文明起源,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图像尤其是神话图像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发挥的建构性作用。原籍希腊的美国学者南诺·马瑞纳托斯(Nanno Marinatos)在近期一部著作即《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中,借助于对米诺时代地中海金戒指与神话图像的研究,还原出一个具有共同女神信仰的“地中海文化共同体”*Nanno Marinatos.Minoan Kingship and the Solar Goddess: A Near Eastern Koine[M].Urbana, Chicago, and Springfie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10.中文译本由王倩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从比较神话学的视野来看,叶舒宪关于玉石神话的研究可以与南诺·马瑞纳托斯相互对照,揭示出世界范围内的石头崇拜神话是如何在不同地区与国家分化,最后演变为玉教神话与黄金神话这两种类型的。
关于玉石神话对中国文明发生机制的塑造性作用,叶舒宪有自己的理解,他反复强调:“玉石神话观对于理解当时的宗教意识形态及神权政治体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屈指可数的几种主要玉石,一方面装点着各大文明五花八门的圣物和宝物,另一方面则充当着绘制天国或神仙世界图景的美学符号。”[23]5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玉石神话信仰源自史前时期的石头崇拜信仰,后来的宗教与神权政治出于建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选择了天青石、绿松石、和田玉与各种美石,将其作为通神的媒介以及权力、社会身份乃至于地位的象征物。但在古代中国,玉器的佩戴者仅仅限于宗教人士与有社会地位的,一般的人是没有权力佩戴美玉的。只要去看看中国各个朝代的墓葬就会明白,凡是有玉器出土的墓葬,其主人的地位都比较高,平民的墓葬中不会出现美玉。平民没有资格用宝玉,但是可以用低贱的材料模仿玉器,如玻璃璧、陶璧的大量生产和使用,这也是原型和置换变形的关系。最近考古报告陕西发现西周的石玦作坊,大量生产玉器的替代普及品,给谁用呢?王公贵族们才不稀罕石头,可见是平民。由此可见,玉石神话信仰实际上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起到塑造性作用。
事实上,发端于旧石器时代的石头信仰是玉石神话信仰的前身与源头,对于中国而言,早期的神权政治出于建构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的需要,才开始将玉石作为王权与神权的象征物,进而建构了一系列的玉石神话,诸如玉斧、玉璋、玉璧、玉琮、玉钺、玉圭等。关于这一点,中国的仪礼制度有明确的规定,略懂古代礼仪文化的人都有印象。但在民间,史前的石头信仰并未消失,它依然以口传神话、实物神话、仪式神话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众多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与仪式表演是这方面的明证。不用说自史前沿袭到当下的民间石制墓穴,只要看看毛泽东的乳名“石三伢子”就会知道,这种石头信仰在中国社会是多么根深蒂固。因此,叶舒宪的“玉石神话”仅仅阐释了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起源问题,其适用性有多大,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四、 余论
由叶舒宪上述三个方面的建树而言,他要解决的是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联问题,即神话如何进入历史这一话题。“神话原型编码”、“神话中国”、“玉石神话”、“玉帛之路”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表明叶舒宪对神话如何进入历史的思考是多方位的,其证据也是多层面的,图像文本、仪式、口传资料均是其重构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依据。总的来看,叶舒宪偏重于从实物与图像这两个方面探讨神话与历史的关联问题,书写文本在其使用的证据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
从国际神话学关于神话与历史关联的探讨来看,神话进入历史有三种路径:“对于王权象征符号而言,神话通过图像叙述进入王权意识形态;就族谱叙述而言,神话以神话思维的方式编造族谱时间链而将王室族谱神话化;就城邦创建而言,神话借助于英雄流浪神话和神谕神话为土地制度提供叙述框架。”[13]206这就意味着神话进入历史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它对历史的建构性功能也是多层面的。就神话的内涵而言,多数学者达成的共识就是,作为历史源头的神话,它并非是一种虚构的叙述,更不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故事,而是一种以多种方式存在的文化基因,它能够被文化不加验证地接受并转换为巨大的叙述性力量,继而发挥整合文化编码的功效。多数研究者在面对神话这一古老而具有多面性的存在形式时,承认其作为口传时代的元历史这样一种事实。概而言之,作为元历史的神话是历史发生的叙述性动力机制。因探讨范围主要限于神权与史前宗教意识形态,叶舒宪使用的证据多半为图像与实物,但他给出的神话图像通过编码方式进入历史的答案并不具有全面性,需要后人在理论与实践上加以补充。
叶舒宪上述三个方面的创建促使他反思神话在中国学科机制内的定位,他充分意识到中国学科机制将神话置于文学范畴的狭隘性,极力倡导一种大神话理念,即将神话视为文化基因与编码的文化神话概念:“从整合性视野看, 神话是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当代比较神话学整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前提是:必须把神话概念从现代性的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就在于:将归类为民间文学一种体裁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基因的神话。”[24]7这种呼声是叶舒宪对中国学科机制的反思,也是对封闭自守的学科本位主义的批评,其意图在于倡导一种跨学科乃至于破学科的学术研究范式,从而更为有效地重构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叶舒宪.激情[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
[2]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3]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4]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内容与前景[J].上海文学,1992(1):78-80.
[5]王倩.阐释与重构:原型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发展[J].文艺理论研究,2010(5):29-35.
[6]叶舒宪.我的“石头”记[J].民族艺术,2012(3):5-9.
[7][英]E.E.埃文斯-普理查德.原始宗教理论[M].孙尚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叶舒宪.千面女神[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4.
[9]叶舒宪.文化文本的构成:从“表述”到“编码”[M]//叶舒宪.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
[10]Redfield ,Robert.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M].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71.
[11]叶舒宪.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J].社会科学家,2011(11):8-14.
[12]叶舒宪.文化大传统研究及其意义[J].百色学院学报,2012(4):1-8.
[13]王倩.论文明起源研究的神话历史模式[J].文艺理论研究,2013(1):202-208.
[14]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M].陈恒,宋立宏,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15]Mali,Joseph.Mythistory:The Making of a Modern Historiograph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4.
[16]叶舒宪,廖明君.新世纪神话观的变革与神话研究新趋势:中国神话学会前沿对话[J].百色学院学报,2013(6):1-8.
[17]叶舒宪.N级编码与“神话历史”[M]//叶舒宪.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
[18]叶舒宪.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J].百色学院学报,2009(1):33-37.
[19]叶舒宪.神话作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8-12,跨学科版.
[20]叶舒宪.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的形成[N].光明日报,2013-07-25,理论版.
[21]叶舒宪.玉石神话信仰与文明起源[J].政大中文学报,2013(15).
[22][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M].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3]叶舒宪,唐启翠.玉石神话信仰:文明探源新视野——叶舒宪先生访谈录[J].社会科学家,2011(11):3-7.
[24]叶舒宪.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8.
Discove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Coding:
On Ye Shuxian’s Mythological Research
WANG Qian1,2
(1.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2. College of Art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China)
Abstract:The creation of Ye Shuxian’s mythology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his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and his expansion of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from literature into culture out of the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local culture; second, he emphasized the shaping function of the myths in the course of the human history by borrowing the concept of "myth history" of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n advocating the concept of "mythical China"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features; thir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ynamic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is creatively putting forward the concept of "jade myths" to establish "the jade cultural community" from pre-historical period to today. How myths enter into history is the core of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which reflect Ye Shuxian’s concept of great myth, namely, liberating myth from literature and restoring its nature as cultural gene and cultural code.
Key Words:Ye Shuxian; archetype of myth; archetypal code; mythistory; jade myths
中图分类号:I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1-0045-10
作者简介:王倩(1974-)女,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东南大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4 - 09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