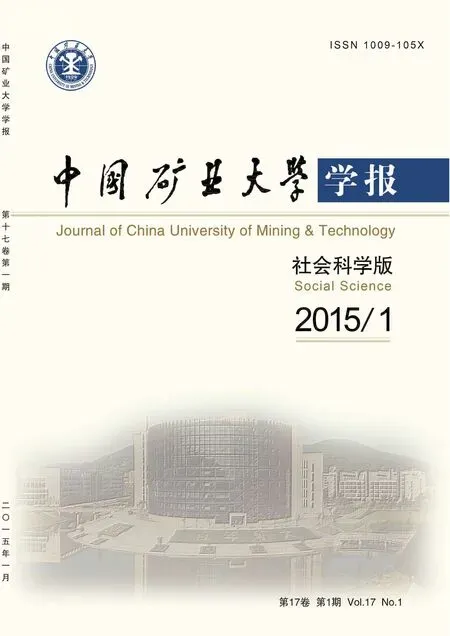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矿业开发
邹放鸣
(中国矿业大学 党委办公室,江苏 徐州 221116)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矿业开发
邹放鸣
(中国矿业大学 党委办公室,江苏 徐州221116)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包含着丰富的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记述及关于积极开发矿产资源以强国富民的经济技术观点的阐述,其文化与思想基础主要体现为“天地观”和“经济观”。在汉代,作为重要矿产资源的煤炭已开始进入生活和生产领域,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铁矿等自然富源开发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关注,记载了古代人们对于矿产资源成矿规律的重要认识,且与现代大地构造控矿理论暗合;还记述了汉代煤炭生产的情景,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记录。司马迁对于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关注独具慧眼,对于发展“农工商虞”各业的见解十分精辟。研究和探索我国古代煤炭矿业发展的历史,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古代中国;矿业开发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不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专列《货殖列传》一篇,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矿产资源开发状况做了详尽的描述和记载,还在相关篇目中阐发了对于发展“农工商虞”各业的精辟见解。《史记》及司马迁的成就超迈前人,惠及后世,显然仅从“史家”的角度对其给予评价似并不全面。《史记》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实际上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社会和经济技术的思想,研究和探索我国古代煤炭矿业发展的历史,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记述及关于积极开发矿产资源以强国富民的经济技术观点的阐述十分可贵,其文化与思想基础有二:
其一,天地观。这是司马迁《史记》的思想文化基础。天地观实际上就是世界观。人类认识世界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首先就要面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或自然界。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开篇的《太史公自序》中就指出:“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尊序,各成法度” 。在《天官书》中,司马迁认为,“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仰则观象于天,附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人类要尊重和顺应客观规律,不可违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评论阴阳家学说时指出:“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尽管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前科学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但司马迁“法天则地”的思想也有着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要取法天地,就要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煤炭作为自然资源,其开发利用也应当遵循这一思想。“法天则地”就是中国整个煤炭开发利用的过程包括经济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反映。
其二,经济观。司马迁之后的汉代史学家班固曾经在其《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的《史记》:“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其实,班固所指之弊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之精华。《史记·货殖列传》及《史记·平准书》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殖货列传》中,司马迁将当时的中国分为“四大经济区域”,他写道:“夫山西饶材,竹、榖 、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 、桂、金、锡、连、丹砂 、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载?人各任其能、竭其力 ,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进一步指出:“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这里的“徼山海之业”,按照《管子》的说法,就是从山与海的事业中求取财富。所谓“山业”,主要是铜、金、铁、铅、锡等矿业——当然也包括煤业,只不过煤炭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崭露头角虽为时久远,但是其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十分重要。所谓“海业”,则是渔业、盐业等。
煤炭的开发利用在汉代有了一定的发展,已经初步应用于生产与生活当中。煤炭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在古代手工业体系中,煤炭业属于大矿业的范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对矿产资源开发问题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注。
在司马迁看来,从满足社会需要和国家富强的角度,也就是要积极开发 “中国人民所喜好”的物产和自然资源,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劝其业、乐其事,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司马迁还转引《周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辟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农工商虞四业实际上互有交叉,其中的“虞”又分为“山虞”和“泽虞”,主要就是矿产资源及生物资源开发。对于开发山西、山东、江南、漠北各地的矿产资源,他主张“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并提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使各大经济部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的这些思想仍然很精彩、很有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相关篇目中关于矿产资源的记载,实际上还透露出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对于相关矿产资源成矿规律的重要认识和把握。其中关于“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的表述,揭示了铜矿、铁矿等矿藏的成矿规律。这应该是根据古代矿业开发的经验而进行的概括,它前承《管子·地数》的描述,虽然含有猜测的成分,但却与现代地学理论相符合。在我国现代地学理论的大地构造学派中,就有学者认为,中国东西向大地构造与南北向大地构造,或者北东向大地构造与北西向大地构造相叠加,形成了所谓“棋盘格”构造系,而这种棋盘格的网状交汇处即有利于成矿——这就是现代地学理论中的“大地构造控矿理论。这种理论是现代成矿理论的重要学说之一。中国古代关于铜铁矿“棋置”的思想与现代构造控矿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的智慧[1]。
关于中国古代农工商虞等各业的发展情况的记述,《史记·货殖列传》为“令后世得以观择”,列出了从春秋战国到汉代的若干富豪,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财富榜”。《史记》所列最早的富豪,一是范蠡,越王勾践的主要谋臣,灭吴之后,弃政从商,“乘扁舟浮游于江湖,变名易姓,经商聚财,从事货物交易,“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再一是子贡,“学于仲尼”,即孔子的学生,“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从事商业贸易,在孔子的“七十子之徒”中,子贡“最为饶益”,由于他的资助并跟随其前后,才使得孔子之名能够“布扬于天下”。其后从事商品贸易的有魏国的白圭,曾为魏惠王的相国,后来弃政从商,经商策略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从事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买卖。但更多的富豪具有产业基础:战国时期的猗顿,起于盐业;郭纵以冶铁成业,二人皆“与王者埒富”。在秦始皇时代,还有乌氏倮,从事畜牧业,马牛多得不能细数,“畜至用谷量马牛”,即只能以一条条山谷为计量牛马数目的单位,秦始皇因此为他“封君”,“以时与列臣相请”。又有巴蜀的“穷乡寡妇”清,世代开采丹穴,其财富传了几代,秦始皇以她“能守其业”,“以为贞妇而客之”,并为其筑“女怀清台”,使其名显天下。
至汉代,实行“弛山泽之禁”的政策, 致富者以冶铁或冶铸为最多,被列入富豪榜的有蜀之卓氏、山东迁虏程郑、祖先为梁人的孔氏、鲁人曹邴氏四家。尤其是在秦破赵之后自告奋勇由赵迁往蜀地临邛的卓氏家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按司马迁的描述,卓氏家族应该拥有汉代最大的冶铁手工业工场,受雇者上千人,蔚为大观,其影响及于云南和四川两地。程郑也居蜀地临邛,且以冶铸为业,司马迁称其“富埒卓氏”。孔氏自秦伐魏之后迁往南阳,亦事“鼓铸”,“家致富数千金”。而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还有齐国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起富数千万;桥姚则从事边疆垦荒致富,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
在长安周边,有田啬、田兰、栗氏、杜氏等家资“巨万”的关中富商大贾,有靠种田而“以盖一州”的秦阳。尤为值得提及的是,司马迁不仅列出了当时靠商贸、运输、货郎担(行贾)、养殖、卖油、卖浆、卖羊肚、磨刀、做马医等致富者,而且还列出了靠囤积居奇、放高利贷、行贿、赌博(博戏)、盗墓(掘冢)而积累财富达至“千金”、“千万”、“鼎食”、“连骑”、“击钟”的一批富豪。这显示出司马迁对“商人”所持的宽容态度,并评价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皆诚壹之所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无商不奸”的偏见判然有别。
《史记》所列举的汉代富豪,反映了汉代经济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状况,从中可见其农工商虞各业之盛,以作为重要手工业部门的新兴官营或私营冶铁业执其牛耳。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置官铁的郡县有49处。而在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的西汉冶铸遗址已有60多处,这些遗址中的很多地区,汉代朝廷从未设置过铁官,证明这些冶铁工场有许多属于私人经营的。到了东汉,这种冶铸遗址则发现了100多处,而且规模一般都很大[2]。如在河南巩县生铁沟,发现矿源附近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同时出土的还有泥质陶范,这说明当时是将冶铁和铸造结合进行的。遗址中还发现有一整套冶铸生产设备,包括选料、配料、入炉、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而在这里发现的冶铁炉就有炼炉、排炉、和锻炉等20余座[3]。相关遗址考古已经证实,汉代冶铸业和其他手工业所用燃料,除薪材木炭之外,已经有了煤炭,只是尚不普遍。如前所述的生铁沟遗址就是一座当时的大型冶铸工场。其所用燃料,“煤和木炭都有发现,煤分原煤和煤饼两种。在炼炉7的南边还发现有烧过的煤渣一堆,同时在炼渣中常觅有木柴痕迹”。“生铁沟所在的河南巩县蕴藏着优质的铁矿和丰富的煤炭是煤铁资源丰富的矿区。汉代用煤、木炭和木柴进行冶炼, 已为这里的出土遗物所证实”[4]。
就司马迁对于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的关注而言,可谓独具慧眼,在中国古代史家中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很了不起的。国学家钱穆认为中国在传统上的两大特点就是“集权”、“抑商”。因而对工商业的轻视,在中国古代可谓根深蒂固,而对工商业族群,除《史记》之外,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以工商业繁盛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而史书上所记的妓女名字却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陕西商帮所控制的财富总和相当于当时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而在536卷《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却仅有1人[5]前言!对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的轻视甚至蔑视,在一个长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中国许多人一直认为“无商不奸”。而西方学者哈耶克在其《致命的自负》一书中也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这种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然而哈耶克所述的情况,在西方,只是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即使是在当代,却仍然相当顽固地存在着。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的重大分野。
司马迁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关注和重视还体现在《史记》的末篇《太史公自序》中。如“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关于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则有“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如《平准书》所载,“从建元以来……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以致“钱益轻薄而物贵”。所以对矿产资源的开发,要顺应自然规律,取之以时,合理开发,并注意开源节用;与金属货币密切相关的矿产如铜矿、金矿、银矿等不能允许私采、私冶、私铸。既要“本末俱利”,又要防止“争于机利”。这些都是《史记》中体现的关于矿产资源开发以及矿政管理的重要思想。司马迁提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包括煤矿在内的中国矿业发展史上从古至今贯穿始终。
纵观司马迁关于汉代矿冶业的记载,显然引发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汉代已经开始了用煤作为冶铁燃料,在《货殖列传》中,以冶铁为业而富甲一方的“四大家族”所在地——临邛、南阳、鲁地,除南阳地区历史上无煤炭开采的纪录,但在距今一亿年左右的三叠系上统地质时期的有含煤构造之外,临邛即今四川邛崃,早在先秦时代成书的《山海经》中就有发现煤炭(石涅)的记载,《山海经》中所指的“石涅”当为三叠系上统地质时期形成的煤炭,大多为无烟煤;含煤地层为须家河组、大荞地组、宝鼎组、白果湾组、冬瓜岭组等。《史记》所载鲁地,即今山东省,煤炭资源分布广,储量大,煤质优良,煤种多样,以气煤、肥煤为主,兼有焦煤、瘦煤、贫煤、无烟煤、褐煤和天然焦,含煤地层为石炭二叠系、下侏罗统、下第三系 、第四系全新统——那么,冶铁“四大家族”所办的颇具规模的冶铸工场是否有用煤作冶铸燃料的情况呢?在《货殖列传》中无记载。但这只说明,由于汉代冶铁使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是作为植物燃料的薪柴,用煤作冶铸燃料的情况还较少。在这里,司马迁集中关注的是在汉代蓬勃发展而且作为新兴产业的冶铁业,这些手工业工场即使以煤为冶铸燃料,作为一个细节显然未能进入太史公的视野。但是,也不能排除这些冶铸工场以煤作燃料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手工业工场在那个时代是领先的,而且冶铸“四大家族”的这些冶铸工场的处所大多是在已经发现煤炭或富含煤炭资源的区域。这应该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由古代矿冶遗址的考古发掘来加以证实或证否。
虽然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关于汉代手工业矿产资源开发的叙述中未提及以煤为冶铸燃料,但在记述名人大事的《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述了汉景帝刘启的内弟窦广国遭遇煤矿坍塌事故的经历:“窦皇后……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实际上,窦广国“入山作炭”就是进山采煤。因《史记》中未指明此“炭”是石炭还是木炭,致学者们持论各异。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认为“入山作炭”的炭是指石炭即煤;赵承泽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史记》之岸字,皆是炭字之讹文”,窦广国入山作炭就是进山采煤[6]。祁守华、吴晓煜等专家学者经考证亦持此论[7]。而且,河南宜阳地区确实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不少地区埋藏较浅。本文认为,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不仅揭示了汉代前期宜阳地区就有煤炭开采,煤窑规模不小,而且也是关于煤矿坍塌事故的最早记载。显而易见,《史记》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关于汉代煤炭生产情景的历史记录。
《史记·货殖列传》和《史记·平准书》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他对于“山泽之利”即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视。唐代学者司马贞注《史记索隐》中转引孔安国注《尚书》云:“殖,生也。生资货财利”。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要广生财货之利,促进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就离不开矿产资源的开发。司马迁高度赞许“徼山海之业”的管仲之谋,实际上表明了他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积极主动态度,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这既根本不同于班固所谓“崇势利”,“羞贫贱”,也和当时及其后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对“山泽之利”在“弛”与“禁”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而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论及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时也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管锥篇·史记会注考证》)总而言之,对于《史记》,学界的公认是:“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特别是其对“徼山海之业”思想的发挥和对“中国人民所喜好”的物产和自然资源开发的倡导,更是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霍有光.司马迁的地学思想 [M]//中国古代科技史钩沉.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80.
[2]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39.
[3]巩县生铁沟[M].文物出版社,1962.
[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巩县生铁沟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J].文物,1959(5):15-16.
[5]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M].中信出版社,2012:X.
[6]赵承泽.关于西汉的用煤问题[N].光明日报,1957-02-04.
[7]编写组.中国古代煤矿开发史[M].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21-24.
中图分类号:F4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1-0081-04
作者简介:邹放鸣(1957-),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4 - 11 -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