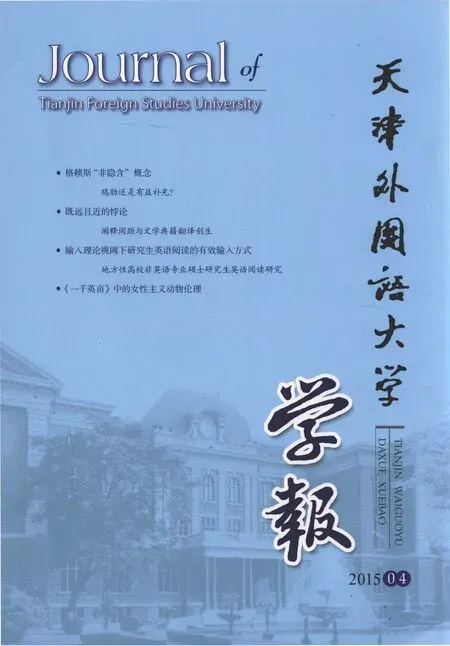《一千英亩》中的女性主义动物伦理
刘 彬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665)
一、引言
1991年,简•斯迈利(Jane Smiley)的小说《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此书被誉为一部道德小说、责任小说(Nakadate,1999:23),是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ibid.:159)。在论及此书的创作动因时,斯迈利(Smiley,1999:171)说:“关心农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各种农业问题和环境问题交织在一起。我关心的首要生态问题是我们饮用的地下水是否遭受硝酸盐的污染?如果我怀孕,是否能足月生产?第二个生态问题是这些年来我们家周围的那些蜜蜂有多少死于农药?”这番话表明女性身体、环境和动物共同架构了斯迈利的生态观。这种整体性生态观源于斯托 (John H. Store)的《生命之网》一书。斯迈利上八年级时便读了此书,书中宣扬的土地、动物、植物、人等共同编织的生命之网的生态整体观极大影响了她日后的思想和创作,成为《一千英亩》中的首要原则(Nakadate,1999:4)。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一千英亩》进行了“绿色阅读”。O’dair(2005)认为,小说充分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理念,即父权制代言人拉里强奸女儿和强奸大地象征性地彼此联系。Hicks(2013)认为,小说是典型的生态世界主义叙事(eco-cosmopolitanism),其中的生态关怀超越人类世界,凸显了生命和无生命物种之间的密切关联、相互影响和能量交换。国内学者也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揭示了父权制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程静,2008;张瑛,2005;左金梅,2004)。
而在这场“绿色阅读”中动物并不在场。动物的缺失既偏离了斯迈利一贯尊崇的生命之网的整体观,也不符合将颠覆一切压迫视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整体观。本文试图纠正动物缺失的研究现状,将动物视为社会文化符码,解码动物所隐含的性别意义,并解析小说中体现的女性主义动物伦理思想。小说中被物化的动物与被动物化的女人都沦落为父权制社会压迫、利用的对象,体现了性别主义和物种主义 (speciesism)①之间盘根错节的勾连,证实了女性主义动物伦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小说还提出了女人的动物性、宠物饲养、语言、素食、集约型动物农场等与动物伦理相关的问题,并以主人公吉妮与杰斯的言行为实例,诠释并宣扬强调情感、提倡素食、警惕语言中的性别主义与物种主义等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动物伦理观。这些伦理思想既为动物保护带来启示,也引发了系列困惑。
二、物种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勾连
历史考证和哲学思辨都显示物种主义背后总是闪现着性别主义鬼魅般的阴影,反之亦然,两者属于共谋关系(刘彬,2015:88)。小说《一千英亩》中描述的物种主义体现在两种对待动物的态度上。
第一,对动物占有性的热爱。吉妮的丈夫泰伊和吉妮儿时的邻居卡尔一家是这种态度的代表。泰伊的父亲是养猪农场主,泰伊自小便梦想子承父业,建造一个现代化工业养猪基地。他眼中的猪是“那些粉红色的可爱的小家伙”,因为它们“会带给你滚滚财源”(斯迈利,1999:23)。显然泰伊热爱的不是猪本身,而是猪驱动的经济利益。猪被物化为工具和财产,它的价值体现在是否促成他人利益的实现。这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否定了动物的天赋价值,即不是由他人或组织授予的,也不是由于做了某事而获得的价值,剥夺了动物最基本的伦理权利,即不被当作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的权利。
与泰伊相似但更加隐蔽的是卡尔一家。卡尔家养了各种动物,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些动物身上,训练鹦鹉说话,教狗玩杂耍。他家的牧羊犬能在鼻子上顶一支火柴盒,并抛向空中,再用嘴接住,猎狐犬能够向后翻跟头,三只狗能够在主人的命令下步调一致地做出各种动作。卡尔热爱宠物不假,但宠物是以财产形式存在,还是为了让人类利用。卡尔训练宠物的目的是消遣娱乐,背后隐含着对动物施加的肉体以及文化性的暴力。首先,在训练动物时势必要采取暴力,还要迫使它们日复一日地重复操练,这显然有悖于动物伦理;其次,“言说的动物以及动物表演中的动物常常代表着对作为动物他者的践踏,对动物自然本性的践踏,因为尊重动物就是要尊重它们的他者性或他者身份”(卡勒,2012:49-63)。让鹦鹉说话是对动物进行拟人化处理,是对动物进行“强制性收编与变形。这样剥夺动物的身份不仅可笑,也违背伦理道德。这好比在文化征服过程中,用一种文化收编另一种文化,然后彻底抹煞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迫使被收编文化偏离原有常规而丧失其完整性。”(Schiesari,2012:10-11)对动物而言,这种收编无疑就是压迫。
第二,漠视动物生命。拉里是一个狂热的肉食者,一日三餐都要吃肉。一方面,肉在父权制社会演变为一种具有男性气质的食物,食肉成为衡量个体和社会男性气质的标准(Adams,2000:36)。肉在饮食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和男人对女性统治的加强相辅相成(Collard,1989:36),由此形成了“肉的性别政治”(Adams,2000:22)。另一方面,对大部分现代人而言,尤其是都市和近郊的人,“与动物接触的最直接、最频繁的方式在餐桌上,即吃肉。这个简单的事实既体现了人类对其他动物的态度,也暗示了我们每个人能为改变这种态度做些什么。”(Singer,1990:95)拉里对肉的嗜好与占有既彰显了父亲与国王②的身份,又表明了他对动物生命的漠视。拉里对生命的漠视还体现在他采取的农耕方式中。为了使土地增产,他用飞机大面积喷洒杀虫剂来杀死玉米害虫,结果导致农场附近的各种动物都消失了。
以拉里为代表的男性社会一味追求农业高产,大量使用有毒化学物质,最终渗透到地下,污染了井水。大女儿吉妮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她五次流产并最终不孕。二女儿罗丝在34岁时罹患上乳腺癌而英年早逝。拉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投毒者。斯迈利在回忆拉里的罪行时指出了他给女人和自然带来的灾难,强调在父权制社会“女人和自然互相表征,互相印证”(Nakadate,1999:163)的关系。简言之,拉里们伤害动物的同时也伤害了女性身体。
在拉里使用的语言中也交织着他的物种主义和性别主义偏见。在他眼里所有女人都是丫头(girl),即没有思想和观点的人。他把小女儿卡罗琳称呼为 “我的小鸟”、“我的鹪鹩”。经常将女儿和母猪、母牛相提并论,认为女儿再养就卖不出去了,年龄大了恐不能生育。对秉持物种主义的人而言,雌性动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繁殖能力,一旦丧失此种能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将物种主义的价值衡量标准强加给女人。事实上,父权制社会建构了一套让女人屈从的话语系统,表征之一便是女人的价值在于她的生育能力。生育是女人地位的保障,也是赢得男人欢心和爱的条件(Collard,1989:106-107)。早在 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Woolf,1981:112)便警告女性:“一旦孩子不再被需要时,女性也将不再被需要。”语言伤害在拉里酗酒后偷偷开车导致车祸的那晚达到高潮。一向温顺的吉妮回击了拉里,激怒了他,他破口大骂:“你真称得上头母狗!”“你这个不下崽的婊子……你真算不上个女人,就是头母狗,对,一头被榨干的浪狗。”(斯迈利,1999:196)而另一位父权制大家长哈罗德之后也曾大骂吉妮母狗。
“母狗”一词同时贬低了女人和狗,充分体现了物种主义和性别主义的交融。“女人被视为动物,是父权制权力施展的主要手段之一。”(Adams,1995:12)而“将任何人类群体等同于动物都成为剥削那个群体的合法依据”(Gaard,1993:204)。在物种主义思想中,雌性动物位于最底层,人类往往通过控制雌性动物的生育功能实施压迫。雌性动物如鸡、母牛、母狗、母猪等具有一切男性厌恶和恐惧的消极含义,一旦将这些动物的形象投射到女性身上,其中的负面意义也转移到了女性身上,同时社会对雌性动物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应用到女性身上。被称为母狗的女人不仅可憎可恨,而且她们的经验世界完全被抹去,只剩下具有繁殖能力的身体。
吉妮被辱骂为母狗隐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女人一旦被降格为母狗,自然被驱逐出人类的道德共同体,沦为任人蹂躏的对象。正如有着清醒认识的二女儿罗丝所言,对父亲而言,性侵和殴打她们姐妹在性质上毫无二致,和杀死农场上的动物也毫无二致,因为“我们是他的。他对我们就像对池塘、屋子、猪或庄稼,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斯迈利,1999:207)其次,一旦将母狗和人类痛恨的婊子联系在一起,此消极负面形象投射到母狗身上。既然“每一个物种的负面形象都将那个物种锁定在被剥削的境地”(Adams,1995:17),母狗遭受剥削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再次,母狗的功能是生育小狗,一旦此功能耗尽便毫无利用价值。不能生育的吉妮于父权制社会而言是“被榨干”了使用价值的等待被遗弃的工具,男性自然可以对她为所欲为。最后,吉妮是婊子,而婊子是专门魅惑男人的女人,拉里对她的性骚扰就变成诱惑使然,便可成功规避自己的罪责。由此可见,“母狗”一词所包含的人类经验体系既折射也加强了人与动物、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对立,充分证明了物种主义与性别主义的狼狈为奸。
三、女性主义动物伦理
拉里们的物种主义态度和性别主义思想都源自男人优越于女人与动物这一传统积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种主义与性别主义的这种同源性愈发明晰,越来越多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开始建立女人和动物在历史、哲学和现实中的联系。克拉德(Collard,1989)指出,父权制是一种疾病,向自然和动物施暴是这种疾病最凶险的病症,这种暴力和对女性的压迫密切交织。一方面,对女人的压迫效仿了动物被奴役的模式,剥削女人的劳动和生育能力便是其中一例(Fisher,1979:190-194);另一方面,男人通过虐待动物来控制女性,男性施暴者的权力和女性受害者对动物的关怀成正比关系,女性受害者越关怀动物,施暴者的权力就越大(Adams,1995:11)。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人类与动物的二元等级体系可被简化为男人凌驾于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及女性化的动物之上(ibid.:80)。因此,女性主义如果只为女性争取自由,而不同时为那些像女性一样饱受父权制残酷压迫的生命争取自由,这“既不公平也不正义”(Benney,1983:151)。作为体现整体性价值观的生态女性主义,既然声称将一切压迫形式划归到自己的理论范畴并将之政治化,反对二元对立,强调所有生命过程的相互联系,倡导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缔结的互惠互助的伦理关系,就不能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同时却人为建构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
小说中的动物已被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这种伦理关怀首先体现为吉妮对动物一种本能性的认同与同情。吉妮从小就特别喜欢和动物在一起时的那种相依为伴的感觉,动物于她意味着“一切温柔、有趣、快乐的事物”(斯迈利,1999:144)。而动物不仅成为吉妮生活中的乐趣,也让她对动物的痛苦感同身受。听说一只小羊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她泪流满面。而感同身受又促进了吉妮与动物的认同。焦虑时她感觉“身上潜伏着另一种兽性,就像一匹被圈在狭小马厩里的马”(同上:216),气愤时会意识到“自己天性中的狗”(同上:266)在狂吠,在品尝到性的快乐时想象“身体好像是母猪隆起的身体,弧线一端是长着猪鼻子的猪头,另一端是又短又粗的尾巴”。她感觉到了自己“天性中仍然和母猪一样的那部分”(同上:173),这让她置身于一个极少经历的梦幻中。
相对于吉妮出自女人天性的动物意识,杰斯的动物意识更具伦理自觉性及理论深度。杰斯是“正面人物形象,代表正确的自然伦理观”(都岚岚,2011:45)。这种正确性首先体现在他对传统农耕方式带来的环境破坏表示极大担忧,他力图摈弃化学物质,以自然耕作法替代传统方法,利用作物自身来增加土壤的肥力,使用农作物轮作、免耕法、生态休闲法等促使农业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为农场带来了生态意识。
杰斯的正确性还体现在其素食者身份。“对肉的看法,对这个地方生产肉的方式,以及肉对人身体的作用的看法都改变了。我的意思是,我以为鲍勃过得不错。我把它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它又与众不同。它有名字。你知不知道那种新型的杂种鸡肥得很快,腿都支持不住自己的身体?我的意思是,既然它们都呆在笼子里,它们并不需要用腿支撑身体。我想,既然它们的腿不好使,它们也不会想走出笼子去。可这一切让我恶心。我不想吃肉。我不想干这一行。”(斯迈利,1999:137)杰斯的这段话包含了动物伦理中两个主要问题:食肉和集约型动物农场。食肉是压迫动物的最主要形式,但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采取了一种“不在场的所指体系”,刻意抹煞肉与动物的关联,人们食肉时并不会联想到这是在食用动物的身体。动物的不在场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第一,字面上,食肉时动物确实消失了,因为它们已死了;第二,定义上,吃动物时人们改变了谈论它们的方式,如不会提及动物幼仔,而只说veal或 lamb;第三,隐喻上,动物成为描写人类经验的暗喻,如被强奸和殴打的女性常说自己就像一块肉,意为一个被暴力剥夺了感觉的东西。此时肉的意义不再指向自身,而是指向女性被侵犯时的感觉。动物原初的、实际的体验就变为不在场了。杰斯的讲述恢复了动物的在场,既还原了食肉的真相,也揭示了动物遭到的残酷剥削。为了满足人类食肉的欲望,肉鸡必须忍受终身囚禁。如果动物拥有被尊重的权利这一点是正确的,对那些肉鸡日复一日的大量侵害,对它们基本自由的剥夺和对生命的摧毁就构成“重大的恶,这个恶如此巨大,像天文学中的光年一样,以致让人无法想象”(雷根、科亨,2005:157)。动物的悲惨境遇触动了杰斯,他开始“倾听心灵的声音”,最终拒绝再食肉。
吉妮与杰斯对动物充满了同情,“同情,只有同情才能让一个主体暂时地分享他人的存在”(Coetzee,1999:34)。这种诉诸于情感而不是理智的动物伦理颇具女性主义动物伦理色彩。他们的言行突出了女性主义动物伦理,第一,食肉是最为严重的压迫动物的形式;第二,警惕将女性动物化的语言现象,因为其中大多包含着对动物的偏见和对女性的诋毁,“解放语言是解放动物的重要一步”(Adams,2000:76);第三,关怀被忽视的农场动物,揭露集约型动物农场中动物悲惨的生活状况,因为女人与农场动物之间的类比将更有利于揭示女人的命运(Adams,1995:196)。杰斯怜悯动物,但他对女人的态度却呈现出悖论。一方面,他与农场里那些贬抑女性身体的男性不同,他欣赏吉妮姐妹俩,不仅帮助吉妮认清了周围女性罹患乳腺癌以及自己五次流产的真相,还促进了吉妮的自我觉醒;另一方面,他像拉里一样具有破坏性,破坏了两姐妹的婚姻,导致罗丝的丈夫彼得自杀,离间了两姐妹的关系。他集保护者与破坏者于一身,这反映了动物解放运动的复杂性。
四、结语
《一千英亩》中无论是物种主义还是女性被动物化,都根源于西方思想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这种思想拒斥差异,并将一切差异定性为他者,转而成为压迫剥削各种他者的合法依据,显示出物种主义、性别主义等各种主义之间在逻辑上的同源性,再次证实了女性主义动物伦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些推断与论证无疑带来很多启迪:第一,基于逻辑思维的一致性,各种压迫编织成一张层层叠叠纵横交错的大网,消除任何压迫任重而道远,意味着动物解放运动应该与其他各种围绕人的解放运动同时展开,动物解放运动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Singer,1990:iii);第二,“食肉的习惯决定着我们对动物的态度”(ibid.:v),饲养动物的集约化农场和屠宰动物的屠宰厂每天都在上演着虐待和杀害动物的虐心场面,放弃食肉接受素食是每一个立志动物福利的人应该改变的生活习惯;第三,很多有毒物质首先危害的便是女性,可以通过记录环境污染对女性和动物生活的影响来建立三者的联系;第四,善待自然,其中包括动物,动物伦理观不是为了逆转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而是在以关怀为核心的基础上为动物谋取福利。
在动物伦理建构中,鼓励女人与动物认同以达到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直到20世纪,女人的动物性仍然成为将其排除在公民权利之外的充分理由,鼓励认同是否会加固女性的模式化形象,使女性主义在过去若干年取得的进步功亏一篑?假如让动物在生前无忧无虑地生活,然后以无痛苦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这是不是动物伦理?通过素食来谋取动物福利是否意味着动物权利运动者将一种“个人的饮食习惯强制性的变成公共禁忌”(Coetzee,1999:67)?倡导素食是不是一种不论个体和民族差异的普适主义?如果禁止动物农场,那一部分人的生计将如何解决?动物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该如何解决?作为一项激进的思想与实践运动,动物伦理不得不与传统的思维观念正面交锋,势必会产生诸多困惑。正是不断产生的困惑及不断解决困惑的勇气与智慧推动着动物伦理的纵深发展,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悄然改变着人与动物的关系。
注释:
① 物种主义对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泛指对非人类物种的歧视和偏见,最先由动物保护人士Richard D.Ryder提出。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推进了此概念的广泛运用。
②《一千英亩》是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的改写。斯迈利在回忆自己的创作动机时也承认了这一点。她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创作一个现代版的《李尔王》,采用大女儿吉妮的视角进行叙述(Nakadate,1999:12-13)。
[1] Adams, C. & J. Donovan. 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C].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Adams, C.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M].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3] Benney, N. All of One Flesh: The Rights of Animals[A]. In L. Caldecott & S. Leland (eds.) Reclaim the Earth[C].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3.
[4] Coetzee, J. The Lives of Animals[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Collard, A. Rape of the Wild: Man’s Violence against Animals and the Earth[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Gaard, G.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M].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7] Fisher, E. Woman’s Creation: Sexual Evolution and the Shaping of Society[M].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9.
[8] Hicks, S.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 and Archival, Reimaginations of Eco-cosmopolitanism[J].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2013, (2): 1-20.
[9] Nakadate, N. Understanding Jane Smiley[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10] O’dair, S. Horror or Realism? Filming ‘Toxic Discourse’ in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J]. Textual Practice, 2005, (2): 263-282.
[11] Schiesari, J. Polymorphous Domesticities: Pets, Bodies, and Desire in Four Modern Writers[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2.
[12] Singer, P. Animal Liberation: 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13] Smiley, J. Shakespeare in Iceland in Marianne Novel[A].In M. Novy (ed.) Transforming Shakespeare—Contemporary Women’s Re-visions in 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C]. New York Palgrave, 1999.
[14] Woolf, V. A Room of One’s Own[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1.
[15] 程静.《一千英亩》:父权制农业文化下的生态意识和土地伦理观[J].郑州大学学报, 2008, (3): 134-137.
[16] 都岚岚.《一千英亩》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当代外语研究, 2011, (10): 44-49.
[17] 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J].生安峰译.外国文学评论, 2012, (4): 49-63.
[18] 简·斯迈利.一千英亩[M].张冲,张瑛,朱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9] 刘彬.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动物伦理及其困惑[J].外国文学, 2015, (1): 144-152.
[20] 汤姆·雷根,卡尔·科亨.动物权利论争[M].杨通进,江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21] 张瑛.土地 女性 绿色阅读——小说《一千英亩》生态批评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 2005, (3): 72-77.
[22] 左金梅.《千亩农庄》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J].外国文学评论, 2004, (3): 9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