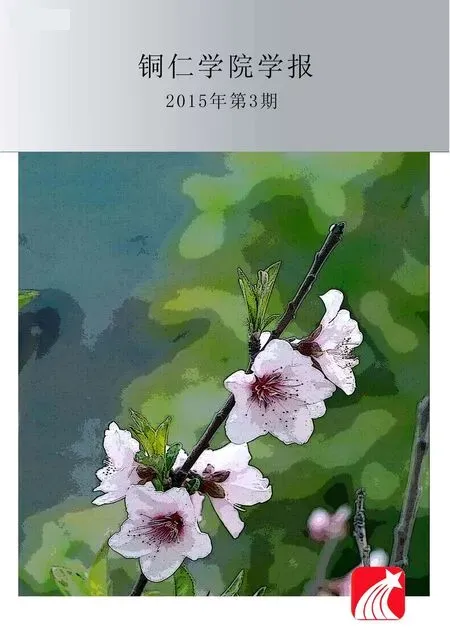民族融合刍议
——以铜仁市为例
刘新华
( 铜仁市档案局,贵州 铜仁 554300 )
民族融合刍议
——以铜仁市为例
刘新华
( 铜仁市档案局,贵州 铜仁 554300 )
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完成了不同民族的语言、服饰和习俗乃至血统的融合。这种水乳交融的民族融合是时代的进步,是各民族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传播的结果。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任何人都不能逆转的。我们只能加强对它的认识,才能相应地不断完善我们的民族政策,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民族; 融合; 铜仁市
现代人做民族文化研究,往往注重于各个民族的差异性,注重于研究不同民族的独特性,这应该是做民族文化研究的主流,当然无可厚非。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同一性,同样不应忽略。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同一性的内涵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是时代的进步,是各民族团结交融的结果,因此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而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造成各民族文化同一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于民族融合。远在新石器时期,铜仁各族人民的祖先就在黔东这片青山绿水之间生息繁衍。东汉时,对分布在今湘西及黔、渝、鄂三省市交界地区沅水上游的若干少数民族,总称为“五溪蛮”。从《辞海》称五溪蛮“与今天的土家、苗、瑶、侗和仡佬等民族有渊源关系”[1]39来看,在东汉这短短两百来年的时间中,铜仁一带的湘黔边境的土家、苗、瑶、侗和仡佬等民族的先民,就已经以“五溪蛮”的称谓记入史册了。五溪蛮在黔东这片热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渔樵耕牧,历经数千年的寒来暑往,逐渐细分成了侗族、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等不同的民族,并同时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铜仁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志书,明代万历年间编撰的《铜仁府志·风俗》中,对这种现象就有所记载:“郡属各司,汉夷杂居,有土、仡、苗、仲,种类不一,习俗各殊”[2]67。然而,随着汉人的大量移入,处于“汉夷杂居”的铜仁的各民族的融合,在本地土著民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本地土著民族与汉族的相互融合,也随之开始了。
一、民族的融合,首当其冲的是语言的融合
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在汉人移入前,生活在黔东的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明嘉靖《思南府志·风俗》就描述了“蛮夷杂居,语言各异。居郡东南者,若印江、若朗溪,号曰‘南客’,有客语,多艰鴃不可晓。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婺川、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皆同。惟在官应役者,为汉语”[3]8;明万历《铜仁府志·风俗·节序附》中,也描述了“土人即洞人[即土著民,俗名“南客”(应为侗族和土家族)]……语艰鴃不可晓”[2]68和“苗人语音鴃舌”[2]69,说明了那时铜仁的侗族、土家族和苗族都是在使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的。
由于明代在黔东改土归流,从而导致了建立铜仁、思南、石阡、乌罗等八府并同时设置了贵州省以总管八府,汉人开始大量移入。而来此地做官的又多为汉人,汉语自然成了官方语言。黔东的各少数民族要同官府交涉,要同汉人交际,就必需学习汉语、使用汉语,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今人交接之间,言语俱类中州”[3]8,“土人即洞人……渐被日久,语言食饮,不异华人”[2]68,“宋元以来,土彝杂处。自明开设,语言服习,大类中州”[4]60,“城市贸易,苗妇居多。其与汉民居相近者,言语皆与汉民同”[5]118的局面。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它植根于社会交际的土壤中。当少数民族的语言在与汉人的交际中无法与汉人交流沟通时,少数民族的语言逐渐被汉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在黔东,除了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族“自相毗连至数十寨不等者,所居多幽阻险隘之地,崇山广谷,自为风气。前明设府以来,其窎远者,均为数土司所不能辖。又其地北接酉、秀,东连辰、永,松桃所领,实介川、楚之交。设城最后,饮食、衣服、居室有与汉民迥别者”[5]116,能把本民族的语言继续使用从而保存至今外,其余的侗族、土家族和仡佬族,他们的本民族语言,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即使是在像松桃苗族自治县这样古代其“所居多幽阻险隘之地”的苗族群居的地方,现在由于交通的便利,也同外界有了广泛的接触,并且随着大量的年轻人外出,跻身于汉人群居的地区,日积月累地使用汉族语言文字思维和交际,语言文字的汉化已是在所难免,留守在故土的老人,很难再把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传承下去了。现在的侗族、苗族和土家族群居的地区,虽然有的地方在使用双语教学,力图把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薪火相传下去,但是一种语言一旦不再作为交际工具来使用,那它就失去了它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也就不能再用作人们用以积累、传承人类的文明、交流沟通的第一个信息工具,消失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是基于语言的社会性的本质所决定,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民族的融合,居于其次的是服饰的融合
服饰是最直观的,是以第一印象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的。居住在铜仁的少数民族,各自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这些服饰,一部分承袭下来,传承至今,而绝大部分则逐渐汉化,趋于消亡。
清道光《松桃厅志·苗蛮》对苗族的服饰,记载得比较详细:“苗人服饰,五姓皆同,青布裹头,衣尚青,短仅蔽膝。男著裤,女著裙,裙多至数匝,百褶褊韆,甚风。不举盛饰时用斑丝,常服惟青布。近则少壮妇女多用浅蓝,亦名‘月蓝’。绾髻以簪,博可七八分,富者以银丝作假髻,两旁副以银笏,形仿雁翎,觺觺然冠于首。平常堕耳之环,大几及肩。项束银圈,多至七八支。贫者以铜为胎,外镀以银,稚女亦然。女未嫁者,青布蒙首,以发为辫,绾于帕外。男女皆跣足。近颇仿汉制,间用鞋。其男之黠者,装束全与汉民同。惟女不弓足而已。被用花斑,甚短。女亦娴纺织,所织斑布,精致古雅,坚韧耐用。”[5]117这在清光绪《铜仁府志·苗蛮》中也有相同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铜仁府的苗族服饰,与松桃厅的苗族服饰基本相同。生活在黔东的侗族、土家族和仡佬族的服饰,古籍中记载甚少,比如仡佬族,明万历《铜仁府志·风俗·节序附》中,仅仅只记载了“仡佬本地夷……男子刀耕火种,妇人勤绩纺,陶珠为餙”[2]68。生活在黔东的少数民族,其中的土家族、侗族和仡佬族的服饰,有一部分一直传承到20世纪作80年代,而大部分,则在明代就已经汉化了。明万历《铜仁府志·风俗》记载:“郡居辰、沅上游,舟楫往来,商贾互集,故其风俗、言语、服饰,大抵相同。”[2]67
造成少数民族服饰的汉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地域上“郡居辰、沅上游,舟楫往来,商贾互集”的原因,但诸多因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避免民族歧视。乾嘉年间,石柳邓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嘉庆元年,平定苗匪,男皆雉发,衣帽悉仿汉人”[6]30,“近城女苗闲学汉装”[6]30。清道光《松桃厅志·苗蛮》也记载:“其男之黠者,装束全与汉民同。”[5]117这里的“黠”,既有“狡黠”的意思,也不排除“黠慧”的意思。经历了一场血腥的镇压后,“衣帽悉仿汉人”,从而在直观上去避免民族歧视,自然是聪明之举。另外,官府的强制限制,也对少数民族的服饰变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清道光《思南府志·风俗》中的“十年前,胥隶华靡,相耀服饰,轶于士夫。府县严申束,此风稍戢”[3]109,就是官府强制限制的结果。
当然,汉人的衣着也有它优秀的一面,比如穿鞋,是值得效仿的,所以早在明代,铜仁的一些苗族就已经是“男子不蓬不跣,巾履衣服,无异中华”[2]69了。松桃地处偏远的苗族,在清代也一改“男女皆跣足”[5]117的习惯,“近颇仿汉制,间用鞋”[5]117了。《铜仁市粮食志》中用了一张解放初期川硐区上交公粮的老照片,照片中的几十个苗族男女,全都是身着银饰,但十几年后,川硐区的苗族银饰装束,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黔东的很多少数民族,衣着基本上已经完全汉化了。
少数民族服饰的汉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那么多的空闲时间去绣制那些五色斑斓的民族服饰了。现代机器化的流水作业,加工出的成衣,既经济又时髦,绣制那些五色斑斓的民族服饰,相对来说已经是高成本的奢侈品了。因此民族服饰的融合,也是势在必行。
三、民族融合,较为普遍的是习俗的融合
生活在黔东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这种在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和习惯等,在古籍中都曾有明晰的记载,如明万历《贵州通志·铜仁府·风俗》中就记载了铜仁府“郡属各司,夷汉杂居,有土人、仡佬、苗人,种类不同,习俗各尚”[7]779,明万历《贵州通志·石阡府·风俗》中也记载了石阡府“土著夷民,其俗各异”[7]。
但是,由于自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朝廷在铜仁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外来汉族人员大量流入,各民族的习俗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期相互融化磨合,逐渐被汉化。清光绪《铜仁府志·风俗》记载:“铜仁地处偏隅,夙称朴厚。自改土以来,流寓是邦者,多吴、楚、闽、蜀人,各从其方之俗,相杂成俗,久之遂忘其自来”[6]26,“苗僚种类不一,习俗各异,声教渐敷,为之丕变”[6]26;清乾隆《玉屏县志·风俗》也记载了“宋元以来,土彝杂处。自明开设,语言服习,大类中州”[4]60。
造成黔东少数民族习俗融合,“迨今渐被华风,洒然变易”[7]乃至“涵濡日久,渐拟中州”[7]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的强制性的移风易俗,二是各少数民族的自觉变易。
《礼记·乐记》记载:“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所以古代社会都把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作为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职责。龚自珍就曾在《对策》强调过:“守令久乎其任,皆有移风易俗之权。”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章程》中也曾特别规定:“切实讲求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这种由官方强制变易的,依靠的是法律法规,变易的也大多是一些陋习。清光绪《铜仁府志·风俗》就曾记载苗族“近年颇知畏法,恶俗渐更。”[6]30应该知道的是,中国古代历来都提倡仁政,主张“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所望于化民者”[6]26。不可否认,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就是执政者长期坚持教化百姓的结果。教化百姓是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吏的主要职责之一,“牧民者因地以施其政教。其准乎礼而得中者,亟与振兴;其沿乎习而近陋者,默与转移,是有道焉。”[5]110所以,黔东各少数民族习俗的变易,占其主要的,是在与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自觉地完成的。
古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恶之心,人皆有之;悚惕惊惧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心态,促使人们爱美恶丑,趋吉避凶,黔东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从而促使了各民族习俗的水乳交融。比如说对于毛虫,大家都是厌恶的,于是在汉族四月初八佛的生日举行浴佛活动时,黔东的少数民族便有了“四月佛日,嫁毛虫”[5]115的活动。四月初八日,家家户户都用红纸写上“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到深山外,永世不归家”等字句,贴在堂屋左侧中柱上面,用以驱除虫害,祈求四季平安。这种习俗,黔东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流行,因此黔东少数民族的很多习俗,“久之遂忘其自来”,已经分不清它的由来最先是源自哪个民族的了。再如八月十五中秋节时,黔东的少数民族流行偷瓜送与不育人家。“八月十五,夜摘瓜送艰嗣者,燕饮以为娱乐”[6]27,“八月中秋夜访 ,艰于子嗣之家,亲友摘瓜送之,以兆举子”[5]115。这种寄予了亲友美好祝愿的习俗,在黔东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间同样非常流行。值得一提是铜仁端午节的龙舟竞渡。端午节本是汉族纪念屈原的节日,由于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而铜仁端午节的锦江龙舟竞渡,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且由于端午节“楚俗相传为竞渡之戏,郡为楚地,故此风极盛”[6]29。清光绪《铜仁府志·风俗》记载:“五月五日为龙舟戏,集双江渡,斗胜争先。胜者以红锦奖之。倾城围观,士女衣轻罗,摇折叠扇,弄扁舟,缓荡烟波,钗光鬓影,与水色山光相映,亦盛会也。五显庙、川主庙一带,观者众,肩以下皆隐,惟见万头攒动而已。”[6]29龙舟竞渡的时间是五月初五,这时春耕春种的大忙季节已过,田间的劳作不那么紧张了,人们不仅在时间上有了闲暇,心理上也需要放松一下,而且这时的时令已处于半夏,气候也渐渐暖和起来,河水的温度也适宜于水上运动,龙舟竞渡在“天时”上便成了铜仁各少数民族的最佳选择。这是其一。其二是锦江河网密度为贵州之冠,不仅水质好,深浅和宽窄以及“水平无激浪”的河面都适宜于龙舟活动。既有集中比赛河面,也有各村寨就近练习的河面,在“地利”上亦有了铜仁特有的优势。其三是“人和”。龙舟竞渡不仅有很大的竞技性,而且在观看上具有全民参与的娱乐性,铜仁自古以来,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府,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对锦江龙舟竞渡都是很支持的。每只龙舟都代表了一个地方,为了本地的荣誉,除了凑份子外,该地的富足人家大多是乐于解囊相助的,铜仁的龙舟竞渡,在人和上有着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优势。由此,每逢端午节,铜仁城万人空巷,四野八乡的各族人民纷至沓来,从明代留下的诗文不难看出中,那时的锦江龙舟竞渡,就已经是各族人民非常喜爱的习俗,并且已经形成了“画船齐逐万人看”的规模了。趋吉避凶,祈求神佛、祖宗保佑,祈求平安吉祥的例子很多,比如清明节“扫墓,设墓祭”[2]68,比如端午节“门插艾虎,人佩五色寿丝,饮蒲酒,杂以雄黄,褁角黍相馈遗,採药苗、治药饵”[2]68,又如中元节“祭祖先及姻戚”[2]68,再如重阳节“饮茱萸酒,作饧食,登高会饮,赏菊华”[2]68,再如腊月二十四祭灶,祈求灶王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等等,不胜枚举。
民族习俗上的融合还有一种形式是随大流。例如松桃苗族“向以十一月为年节,祭也从同。近圴用正月,与汉民无异”[5]118。如果不是入乡随俗随大流的话,松桃苗族过年时间上的变易,其原因尚有待考证。
四、民族的融合,最根本的是血统的融合
血统的融合,是民族的融合中最根本的融合,它是在不同民族的语言、服饰和习俗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不同民族的语言、服饰和习俗的水乳交融。提到不同民族血统的融合,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往往是昭君出塞,是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其实这种皇家的和亲,范围是相当小的。生活在黔东的少数民族,长期“汉夷杂居”,各民族之间大量地相互通婚,从而促进了各民族相互之间的血统融合。
以沈从文的祖先为例,臧励和等编纂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姓氏考略》中就曾记载:“《姓谱》沈姓出吴兴,本周文王子聃季,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舆沈亭,以国为氏。”[8]由此可见,沈姓原是周文王的后代,封地于沈,以国为姓,自然是典型的汉族了。但自从沈从文的入黔始祖沈思远在明代到铜仁做官后“宦留黔、楚”,几百年后,“族大枝繁”,发展到了数千人,但长期生活在“汉夷杂居”之地,因与苗族通婚,如今在铜仁市碧江区的滑石乡的谷坳、杨柳坪、小田、、举屯、梗竹林、乱岩塘和万山区谢桥办事处的沈家(野鸭塘)等沈姓后裔居住的村寨,其民族成份大部分都是填的苗族。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也经常提到他的很多苗族表亲。这种苗族表亲,实际上就是苗汉通婚形成的。比如说姑姑嫁给了苗族就有了苗族的姑表亲,舅舅娶了苗族,就有了苗族的舅表亲,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姑舅老表。此处还有姨表亲等,盘根错节,各民族的血统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沈姓后裔是否变为苗族,没有文献记载,只是在民族识别时,才正式明确了其苗族的民族成份。而与铜仁相邻的湖南省麻阳县的滕姓变为苗族,则在其《麻阳县志·人口·姓氏》中有了明确的记载:“滕姓……元至元十年,洪水浸溢,再迁居高村坪,与苗人通婚。……至今滕姓苗裔子孙传28代”[9]137。
在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具体的单个人的民族血统是很复杂的。比如笔者的一个朋友,母亲是汉族,父亲在民族识别时由汉族改成了侗族,岳母是汉族,岳父在民族识别时也由汉族改成了土家族。在笔者朋友的子女身上,既流淌着汉族的血液,也流淌着侗族、土家族的血液,甚至也许还流淌着仡佬族、苗族的血液。而在子女的民族成份的确定上,作父母的为了得到高考时的民族加分或其他民族政策的优惠,大多数都是弃汉族血统而选择了少数民族。这种状况,导致了汉族人口大量减少,少数民族人口激增的后果。有人担心,如果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若干年后,中国的汉族甚至会成为少数民族。
五、结语
民族的融合是时代的进步,是各民族互相接近,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传播,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任何人都不能逆转的。我们只能加强对它的认识,才能相应地不断完善我们的民族政策,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1] 夏征农,主编.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2] 刘新华.铜仁府志注[M].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民族出版社,2014.
[3] 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点校本)[M].贵阳:贵州省华泰印刷厂印装,2002.
[4] (清)赵沁,主修.田榕,撰修.钟德善,等,注释.(清乾隆)玉屏县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
[5] (清)萧撰修,龙云清,点校.清道光·松桃厅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6] (清)喻勋,等,撰.(光绪)铜仁府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7] (明)王来贤,许一德,纂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整理.(明万历)贵州通志[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内部发行.
[8] 臧励和,等,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M].上海:上海书店,1980.
[9] 湖南省麻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麻阳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My Humble Opinion on National Fusion:Taking Tongren as An Example
LIU Xinhua
( Bureau of Archives,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
In the long time communication, various ethnic groups keep close contact and interact in many aspects of their lives, and eventually complete the fusion of languages, costumes, customs and even blood. Such harmonious national fusion is a progr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mutual attraction,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The result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customary relationship among ethnic groups has its great vitality and nobody can reverse it. We should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it and make our national policies better and better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reat unity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China.
nationality, fusion, Tongren
G127
A
1673-9639 (2015) 03-0039-05
(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谢国先)
2015-03-05
刘新华(1952-),男,侗族,湖北武汉人,曾任《铜仁市志》副主编,《黔东作家》副主编,铜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铜仁地域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