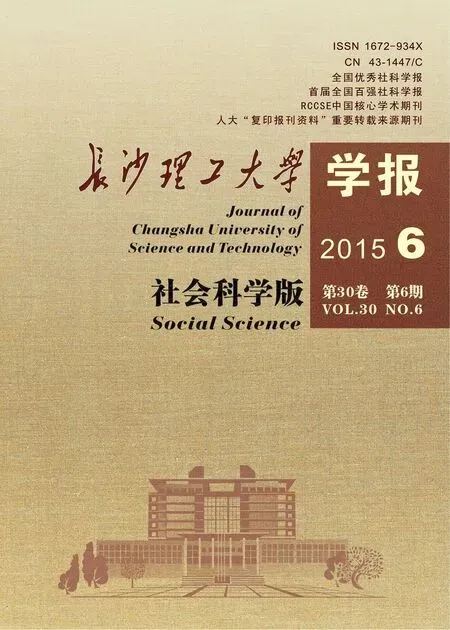文学史书写视域下的朦胧诗经——以洪子诚四本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许永宁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
文学史书写视域下的朦胧诗经——以洪子诚四本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许永宁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
文学史作为朦胧诗研究重要场域,在其书写过程中对朦胧诗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朦胧诗文学史书写的缺席到文学谱系的建立,历史轮廓的勾勒和细节史实的阐述以及各种思潮文化影响下的流动,朦胧诗与文学史互为因果,共同参与和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
朦胧诗;经典化;文学史的书写;洪子诚
朦胧诗传播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就是大学校园。而考察朦胧诗的经典化过程,不得不谈到的就是作为权威的文学史的书写在校园传播中的功用。在校园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文学史作为学院派的理论产物,对朦胧诗的经典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积极而肯定的态度。学院派的学者们也曾积极参与到这场争论中,进而把对这场争论的认识深入到一种学术机制,并将其经典化。
然而文学的经典化历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史参与其中进行构建,同时对文学史而言也产生了一种流变,从对一种现象外围的感知进入到内部的观察,从对它的感性评价上升到理性回归,这都是有意义的环节。从最早的1985年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教研室编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76.10—1982.9)》开始,到最新修订版2007年由洪子诚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学史在对朦胧诗的关注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研究文学史对朦胧诗的书写这一动态变化,从细处观察这种流变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一睹朦胧诗经典化的流变历程。因此在这里选取洪子诚史著作为分析对象,即《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和《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年)、《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2005年),以文学史和诗歌史两个分类来取样进行分析。
一、从轮廓的勾勒到谱系的建立
洪子诚从1985年着手开始编纂《中国当代新诗史》到2007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其间历经二十余载可谓呕心沥血。这二十年也正是中国自“文革”结束以来剧烈变化的二十年,一系列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风起云涌,文学也跟着复杂多变起来。
1978年创刊的《今天》将一个诗歌群体从地下推出地表,跟随着的是轰轰烈烈的诗歌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诗歌批评,这一凸显的诗歌现象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几次大的朦胧诗争论中,稍显落寞的是文学史的书写,有关这一时期的书写在争论中大多处于一个空白期。这个空白期使得对于朦胧诗的认知和评论在一定意义上活跃了思想,各种争议和批评的声音纷至沓来,抗辩和声援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史的书写,一个原因在于距离太近,看不清朦胧诗的全貌,不便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厘清其全貌,另一方面从当代文学史一开始书写就伴随的“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的讨论让朦胧诗在文学史上的出现犹豫缓慢。当然在洪子诚199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之前,关于朦胧诗争论和研究的专著也有,如1987年10月出版的田志伟的《朦胧诗纵横谈》和1988年7月出版的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这可以看作是洪子诚文学史著作出现的一个过渡,或者说是对其文学史出现的一次理论上的尝试。毕竟在时间稍近的叙述中,很难以一个完整全面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和角度对一次文学运动或文学现象进行细致和独到的把握,更不用说以一人之力完成文学史的理论建设。不可否认个人在修史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一以贯之的史学观念以及精准独到的史学理论的实践,但是个体的能力毕竟有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变动使得文学史的书写显得难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社会时时影响着理论的变化和生成。
对于朦胧诗的文学史书写亦不例外。洪子诚最早的关于朦胧诗现象论述的著作是于1985-1987年完稿,1988年4月后记于北京,1991年冬略改,1993年5月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这本是成书较早、距朦胧诗争论最近的诗歌史专著,可以说代表了198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文学史著者对朦胧诗的认知和观点。在对朦胧诗整体的感知中,初版借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一词来概括1980年代“青年诗人”的创作;同时又将“青年诗人”按照“一开始表现出来的互异的发展趋向”和“他们与中国当代诗歌‘传统’的联系方式上”进行划分;将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为主体的“青年诗人”以“革命”和“叛逆”的标准廓清出来。在章节的分配上,以“崛起的诗群”命名,分为上下两章:上章主要陈述的是作为“青年诗人”的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等的诗歌创作;下章则主要论述作为另一种“青年诗人”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的创作。相较于2005年《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修订版,这一论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作为“青年诗人”的这一概念逐渐淡出,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等一批“青年诗人”也淡出诗歌史视野,代之而起的则是对以朦胧诗人为主体的“青年诗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同时也对朦胧诗的诗歌谱系进行了梳理,除重点关注在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活动和对诗人食指的发掘以外,对围绕在《今天》周围的诗人或游离于朦胧诗的诗人多多都进行了重点的关照。
在1993年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从一种看似对1980年代诗歌现象的整合来看,对于朦胧诗的论述试图通过对于传统的继承中寻求理解和突围,将其作为“文革”中反对“四人帮”的产物,以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和时代命运相结合的方式,解读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个“新诗潮”的共同趋向。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作中,研究朦胧诗对于新诗的贡献不在于个体在诗歌艺术上对新诗做出的努力,而是作为整体与反抗“文革”时期文艺观念捆绑在一起,虽然在论述中,对顾城、舒婷等诗人的表述力图显现出个体的诗艺,但是却多被强大的主流话语所掩盖。同时在梳理朦胧诗的发展流变中也显得含混不清,一方面是资料搜集整理的缺憾,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方面所表现出的忽视。这种忽视在2005年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有所补缺。2005版《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对诗歌的整体概貌,诗歌的理论建树和诗歌的谱系都有所涉猎。尤其在诗歌的谱系建立上,肯定了食指等地下诗歌的地位,为朦胧诗的发展找到其合理性的源头,同时将“白洋淀诗群”作为朦胧诗从地下浮出地表的历史沉淀,为其做了大量的铺垫。这样完整体系性的建设,清楚的了解了朦胧诗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整个流变过程。虽然一再强调历史的叙述并非线性的表达,但是对新诗阅读者的大学生了解整个诗歌发展的潮流和脉络无疑具有很好的普及作用。于朦胧诗而言,谱系化体系的建立,将朦胧诗从一开始的争论到最终的接受这个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推动其向经典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细节化历史叙述的深入
细节存在于文学形象和文学事件的描述上,也存在于文学史或历史的叙述上,大量丰富而具体的历史细节,使得在面对历史或文学时更加可感可知。我们一再强调的“回到现场”和“还原历史”虽说只是一种向往,但是这种无限止的接近与触摸,弥补了一丝遗憾,增添了在认知和判断时一种客观公正的理性。
朦胧诗出现伊始,首先面临的就是对其概念的廓清。洪子诚在1993年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以“一批青年诗人的崛起和一个新诗潮的出现”并论,在这里他采用“青年诗人”和“新诗潮”这个概念,将青年诗人作为新诗潮的主要群体,这里不仅包含着以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为代表的“干预”现实的青年诗人,也包含着“叛逆”的朦胧诗人。在其详细的论述中将继承“政治抒情诗”传统的“干预”现实的青年诗人和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新潮前卫的朦胧诗人区分开来。这样一来,作为“新诗潮”的“新”就完全沦落在一个含混的概念里,何为“新”成了初识新诗潮的一个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新诗潮”作为一整章节论述,而这一次的论述中,摒弃了之前对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等青年诗人的讨论,重点放在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换句话说,朦胧诗代表了整个新诗潮,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发展中的“新”概念的变化,通过比较可以得出,“新诗潮”的“新”不仅体现了时代对于文学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文学发展的方向,一种有别于旧文学所带来的革新的力量和求变的精神,使得历史的叙述朝着一种更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在随后有关于80年代诗歌的论述中,2007年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继续沿用了这一概念。新诗潮的代表不仅为朦胧诗,其后也增添“第三代诗”,整体上反映了诗歌观念的流变。
在对整体方面的论述进行修订之外,对作为朦胧诗内部的诗歌现象也进行了修正。在朦胧诗代表人物的指认方面,1993年初版本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北岛直接被过滤掉,在综述中一笔带过。到1999年初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岛开始进入朦胧诗代表诗人的序列,并将其排在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之后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再到2005年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这一排序发生了变化,北岛居于朦胧诗代表诗人首位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顾城也排在舒婷前面进行了阐述,这也延续到后来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同时,由于对朦胧诗的考古使得一些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走出地下,在对朦胧诗的诗歌地图的绘制中,食指、黄翔、芒克、多多也加入进来,一起作为朦胧诗代表诗人。
细察北岛诗歌排位的问题,大致与1993年《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同时的文学史著作,大抵都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整体表述时一笔带过,详细讨论时集体忽略。北岛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尴尬存在,尤其是在政治气候的变幻莫测时期,这样的变动更显得文学史在叙述方面的谨慎和小心。不提或者是少说成了回避问题的最好办法,这也是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的一个尴尬存在。
同样在细节的叙述中,作为民刊的《今天》在文学史的表述上也成了一种尴尬。考察现代文学的历史,大多的文学流派都围绕这一个或几个刊物存在,刊物成了文学发声的前线阵地,如《现代》与“现代派”,《新月》与“新月派”等。《今天》无疑在朦胧诗的出现和新诗潮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然而作为民办刊物被取缔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和叙述中的政治话语问题,在1993年《中国当代新诗史》和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只是将其作为朦胧诗存在的一个载体进行简单的略写。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期刊改制以及文学史研究对于刊物的重视,《今天》作为朦胧诗重要的载体和理论发生地,越来越得到重视。在2005年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和2007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作为讨论朦胧诗的重点章节,开篇专门辟出一节来书写《今天》对于朦胧诗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一重要的变化不仅得益于文学研究视域的开阔和变动,更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注意力转向经济为中心的物质追求,文学日益边缘化。当然宽松的文化环境对于异质文化的一种包容,即使这一异质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之上生成与发展的,也使得文学史在历史细节深处叙述显得更加的丰富和客观。
三、文学史“重写”视域下的经典建构
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的专栏,是“对过去把政治作为唯一标准研究文学史的结果的怀疑”[1],而这一怀疑的结果则是拉开了“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大幕。
主要部分完成于1988年,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似乎没有赶上这个重写的浪潮,虽然早在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已经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史视野,但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显得并不是那么的积极。由于理论的提出需要经过多方的讨论和论证,构建理论的框架和确认文学史实的细节等方面有待加强,稍显迟缓的文学史在这一问题上的展现则约略有十年之久的间隔。而这个间隔时间依然沿用了重写思潮开始之前的文学史史学观念和叙述方法,洪子诚在1993年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的表现亦是如此。
具体到朦胧诗,随着对朦胧诗资料的挖掘和完善,对于朦胧诗整体的面貌有了较为清晰的辨识,一反过去以“新诗潮”或“崛起的诗群”的概念来评述1980年代的诗歌现象,在1999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于朦胧诗逐渐有了谱系上的认识,同时也将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现象进行了廓清,这样历史在经过了十年的发展之后,由厚变薄的历史书写逐步得到实现。与此同时,由于距离朦胧诗发生发展的时间较短,1993年版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在作家作品的历史表述上显出的“当代性”,即文本的叙述多有文学批评的性质,其优势就是除了一定的历史眼光的梳理之外,当事人的见证和参与提供了现场感,批评家所作的倾向性的批评展现出的鲜活性。这也就牵扯到当代文学史在写作中如何处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回忆等复杂资源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带来的对于文学史中“文学性”的讨论。所以在2005年《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修订版中,洪子诚除了将带有专著性质的教材进一步教材化之外,在内容方面力图表现出史的叙述。而这带有史的努力方向的表现,在朦胧诗经典的建构中,首先谱系化的构建了朦胧诗发生发展的脉络,将朦胧诗的发生延续到“前史”时代,在“前史”时代的叙述中增加了对朦胧诗具有影响力的食指和哺育朦胧诗产生环境的“白洋淀湿地”。其次在对于朦胧诗的建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各种文化语境和研究发生的变化,着力点重在《今天》以及围绕着《今天》所做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论述上,这一论述增添了进入文学场域的历史现场感,将一鳞半爪的叙述丰富到具有代入感的语境中,可以说看出了文学史在吸收和接纳最新文学研究成果的努力。最后,在对主要诗人和诗歌的论述中,除了将北岛放在朦胧诗具有代表性诗人首位,增添了其对朦胧诗所做的贡献和努力之外,更加注重文学理论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功用。可以说北岛从朦胧诗边缘地带到中心地位的位移,不仅是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和文学观念的深入,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史写作重要参考标准的政治逐渐将文学从其战车上松绑了下来,文学不再以政治标准为唯一标准,文学史也就避免了政治文学史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我们重点是在文学观念的变动上,过去“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过于强调朦胧诗人在过去的“上山下乡”经历带来的诗歌创作上的同一性,而忽视了诗歌艺术个性化的特质。
他们作为“流派”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们的艺术创造和探索,在精神实质和主导意向上存在着共同点。这表现为:在个人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揭示这一代青年心灵历程的诗的主题;对于窒息着新的审美追求的传统艺术规范的反叛姿态;对于诗人的工作、诗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信念;……当然,这一“流派”在它取得最大影响、并被诗界接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解体、分化,成为“历史”[2](P414)。从这一历史的理论分析中,一方面可以看出作为朦胧诗群体出现不是因为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是在以“朦胧诗”的诗歌艺术聚集在“反叛”的姿态这一面大旗之下;另一方面,这种对于诗歌的理解流于传统的历史事实和背景的结合,忽视了在艺术个性方面个人的表现力和着重点。这种叙述在重写思潮的影响之下不再是简单的归纳和罗列,在2005年再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以一种开放性的方式从“诗歌精神”“时代意义”“诗学贡献”等多方面加以解读。
不可否认,在重写思潮影响下的朦胧诗经典的建构在文学史的书写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地重塑和再造确立了其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但我们也看到,文学史在重写思潮影响下的经典建构的有限性。换句话说,历经多次文学思潮变换的文学史,在历史的叙述上一再的发生变动,这一变动不仅因时而异,甚至会因观念而异,这样文学的经典的就具有了一种流动性,在这一点上,朦胧诗的经典建构也就有了时间的限度,甚至是历史的局限。虽然朦胧诗在后世文学史的书写中会历经怎样的变化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会被遗忘。
杜威说过:“历史无法逃避其本身的进程。因此,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随着新的当前的出现,过去就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3]因此文学史也就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又符合经典的开放性这一特点。这就是时代洪流影响下的文学史观念的作用,由于不能拉开距离,进行一种“历史性”的观察并辅以客观冷静的判断,文学史的表述在某一时期也就出现了相同的现象。这种“距离”在洪子诚1993年这本《中国当代新诗史》和同时期的其他文学史著作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在对朦胧诗代表诗人的处理上大致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由金汉、冯云清、李新宇主编,华东地区高师院校协编,于1992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也没有北岛的身影,舒婷单列一节,顾城和梁小斌列一节,江河和杨炼列一节。在1997年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北岛和舒婷作为朦胧诗的第一个浪潮而被单列一节进行论述。大致同时在1999年洪子诚初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北岛也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专节的叙述之列。
当然文学史的叙述除了时代洪流的影响之外,由于著作者的个人的文学史观念、艺术审美观念的不同,同时期的文学史对朦胧诗的论述也呈现出千差万别的风景。洪子诚著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编写体例上主要采取对“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现象”的重点关注,以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为主体的分类方式,“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查”以增加“靠近历史的可能性”。而同年由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重点以文学作品解读的方式介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具体到对朦胧诗的评论问题上,洪子诚著作以朦胧诗现象的发生为出发点,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朦胧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并同时对代表诗人进行了重点阐释,其语言平实,力求客观、冷静。而陈思和著作则以“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大标题,以西方现代主义为主要判断标准,将朦胧诗运动缩略为其中一个部分,并且以朦胧诗代表诗人舒婷的两首诗《致橡树》和《双桅船》为介绍对象,以点代面的评述了这种诗歌现象,其语言稍显感性。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表述,体现了著者不同的文学史观念和对历史真实的个体感知,正如洪子诚先生在面对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所谈到的:“我们还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目的不仅为‘当代人’立一块碑碣,还希望给后来者提供一份同代人的一种认识的参照。”[2](P549)无疑两本交相辉映的文学史著作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种默契,共同展示了当代人对当下文学的一种个体的理解和把握。
洪子诚在1993年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后记中不无遗憾的谈到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困境:“生活是瞪着明天走去,而写史却是朝着后面张望。虽然必须是站在‘今天’张望,但‘今天’却是一块漂浮的土地,永远都在移动。”[2](P550)我们既不能认同某一本文学史或某个文学史家更具有权威,也不能认为其对当下文学的阐释更具权威性,并保证其千百年后依然正确。然而他们在某一时间段所做的文学史的努力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这也构成了文学史的一种独特风景,毕竟文学史所反映的是对当下文学生态的一种或多种解读。从对朦胧诗代表诗人的确认,到对其诗歌谱系的梳理,再到其长时间内稳定性的积极评价,文学史的权力在参与文学经典的流变与朦胧诗的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1]陈思和,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J].上海文论,1989(6):4.
[2]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美]约翰·杜威.逻辑探究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Misty Poetr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Writing on Literature History: Discussing on the Four Works of Hong Zicheng about Literature History
XU Yong-ning
(Center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3,China)
Literature history,one of the vital fields for the research of misty poetry,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canonization du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 misty poetry.Misty poetry and literature history act mutually as cause and effect,and jointly participate in as well as fulfill the construction of canon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literature from the absence of the writing on literature history in misty poetry,the description on history profile and elaboration of detailed historic events,and the flowing under influence from all kinds of cultural thoughts.
misty poetry;canonization;the writing on literature history;Hong Zicheng
I207.25
A
1672-934X(2015)06-0085-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6.014
2015-10-16
许永宁(1987—),男,陕西旬邑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