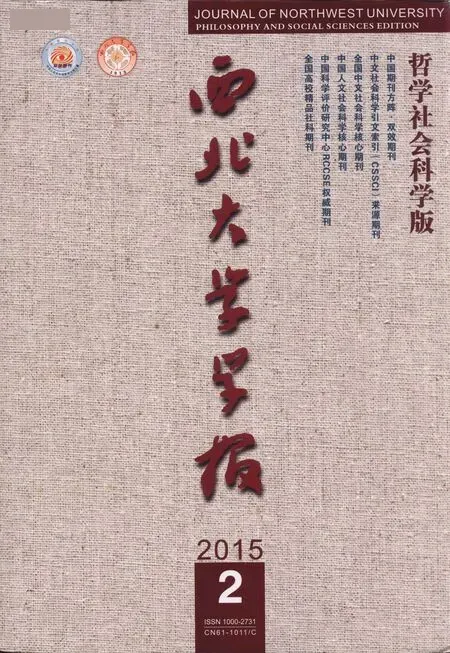模拟投票1824年在美国出现的制度前提与历史语境
张 健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尽管有学者声称“现代民意调查的知识谱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战争、商业、政治和人道主义都是其发展的诱因”[1],大多数关于民意调查业演进过程的叙述基本重复乔治·H.盖洛普式的线性民调简史:模拟投票时代,可以追溯到1824年;现代民调时代始于1933年,此时盖洛普对议题和候选人预测进行民意调查;真正“转折点”是1936年,三家民调机构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预测罗斯福的胜利[2](P116)。很显然,1824年在民调发展史上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模拟投票(straw poll①Poll在汉语中有“投票”“调查”“民意测验”“投票站”等译法,straw poll有“假投票”“虚假投票”“模拟投票”“模拟民调”“草根投票”等译法。本文统一译为“模拟投票”。)首次用于预测美国总统选举,并成为现代意见调查最早的“对应物”[3](P34)。
1824年总统竞选有四个候选人:安德鲁·杰克逊、约翰·昆西·亚当斯、亨利·克莱和威廉·克劳福德。按照《民意调查》一书的说法,选战正酣时,《哈里斯堡宾州人报》(Harrisburg Pennsylvanian)记者在特拉华州的威明顿(Wilmington)市发出模拟选票,询问公众:在未来的投票日,他们的票是投给亚当斯、克莱还是杰克逊、克劳福德?大概发了900张选票,回收600多张。根据对公众投票的点算,7月24日该报刊登了结果:杰克逊得票335;亚当斯得票169。这种经询问后所计算的结果便成为“预示未来大势的小事”(a straw in the wind)之理论,亦即“模拟投票”滥觞[4](P9)。同年8月份,另一家报纸《罗利星报》(Raleigh Star)报道了在北卡罗纳州清点出席政治集会的人数:在4256个选民中,杰克逊获得3428张选票;亚当斯获得470张;克劳福德,358张[3](P35)。此后的总统选举中,许多报纸常用这种“模拟投票”预测选举结果。
从民调发展史而言,《哈里斯堡宾州人报》和《罗利星报》所进行的模拟投票是现代民调科学的先驱[5](P69)。问题是,为什么《哈里斯堡宾州人报》和《罗利星报》是在1824年前后而不是其他时间刊登模拟投票?动机是什么?还有一个相关问题:为何“民意调查是一种奇特的美国产品”“适合消费者取向的美国经济”[6]而不是其他国家?目前大多数文献仅仅记载了此次模拟投票的时间、地点或影响,而本文所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似乎却隐而不彰,需要借助相关资料去还原首次模拟投票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历史语境。本文的分析从《哈里斯堡宾州人报》模拟投票的“新闻趣味解释”开始。
一、《哈里斯堡宾州人报》源起新闻趣味性?
本文所谓的“新闻趣味解释”是指:在不少学者看来,《哈里斯堡宾州人报》等报纸刊登模拟投票的主要动机是“读者趣味”、市场价值或“新闻价值”。按照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文献,最早对此作出系统说明的或许是克劳德·E.罗宾逊(Claude E.Robinson)。他出版于1932年的博士论文《草根投票:政治预测研究》虽然没有提及《哈里斯堡宾州人报》所进行的初次模拟投票,但在分析19世纪末《芝加哥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尤其名噪一时的《文学文摘》的模拟投票活动时提出这样的问题:“致力于这些模拟投票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和不菲的成本,就出版机构而言,必定有某种特别的兴趣驱使这种资源方面的巨大支出。那么,这种兴趣是什么?为什么报纸杂志要进行模拟投票?”在罗宾逊看来,报刊大动干戈,试图获知选民投票意愿的首要原因是选民的投票意愿具有新闻价值,另一个不太明显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刊登模拟投票而带来的促销价值[7](PP51-52)。
新闻趣味或促销价值几乎成为解释19世纪美国报刊进行模拟投票的常见路径。如戴维·W.摩尔(David W.Moore)就认为选前民调在美国历史悠久,传媒早就试图预期选举结果,不仅要在竞争中抢占先机,还要独家获得调查活动的新闻[8](P33)。国内发表于1986年的《民意调查:一个有待开拓的社会学新领域》一文认为:“据目前所知,最早的民意测验由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人报》和《明星报》于1829年举行,在公众中作小范围抽样调查,征询人仍对消费品和新闻媒介工具的态度,带有市场调查的性质。”[9]出版于1991年的《舆论学概论》提出: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舆论调查起源于经济发达的美国……最初人们称它为民意调查或民意测验,是由美国报刊杂志社为追求报纸新闻的趣味性而发起[10](P154),随后,这种“新闻趣味”或“新闻价值”解释在国内几乎成为定论[11](P146);[12](P31);[13](P278)。
2005年出版的《舆论学:原理、方法与运用》对“趣味说”有更为详细的说明。该书认为,现代民意调查开始于1824年《哈里斯堡宾州人报》的调查,并紧接着解释说:“1824年对于美国新闻业发展而言,是个什么年代呢?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报业大众化发展的时代,即廉价报纸、黄色报纸蓬勃发展的时期。可以说,现代民意调查起源于这个时代,不是作为一种严谨、科学的政治性测量手段出现的。本质上说,是大众报纸为了增加报道的趣味性、吸引力、可读性而制造的所谓人为投票事件,然后把该事件作为报道题材报道出来。”该书得出结论说:“大量地采用投票方式来征求民意,成了报纸报道内容中比较煽情、容易吸引社会关注的一个常规的形式,所以,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民意测验为趣味性阶段。”[14](PP181-183)
从历史事实来说,对《哈里斯堡宾州人报》刊登模拟投票的“趣味”解释似乎遇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障碍。首先,诸多研究结论均认为,从历史年代而言,19世纪20年代美国报刊正处于新闻史学家们大都引以为憾的所谓“政党新闻的黑暗时代”,距离19世纪30年代的所谓信息通信革命的“巨变”[15](P48)尚有时日。詹姆斯·M.李(James Melvin Lee)出版于1917年的《美国新闻史》将1812-1832年作为“政党新闻业时期”[16](PP140-163);弗兰克·L.莫泰(Frank Luther Mott)出版于1969年的《美国新闻事业史》则把1873—1801年作为“初期政党报纸”、1801—1833年作为“中期政党报纸”、1833—1860作为“后期政党报纸”,并把“中期政党报纸时期”称为“党派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17](PP93-285)。2008年出版的《政党新闻业:美国媒介偏见史》则把1789—1824年作为“政党新闻业”的崛起时期、将1824—1860年作为“传媒、政党和庇护”时期[18](PP21-139)。无论各位研究者在具体分期上有何分歧,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1824年距离真正意义上以“趣味性、吸引力、可读性”来吸引读者、第一家取得成功的便士报——《纽约太阳报》1833年9月的创办,尚有近10年的时间。同时,1824年这个年份,距离一些著名便士报的创办时间更远:如《纽约先驱报》,1835年5月创办;《巴尔的摩太阳报》,1837年5月创办;《论坛报》,1841年4月创办;《纽约每日时报》,1851年创办,1857年改名《纽约时报》。用“为了增加报道的趣味性、吸引力、可读性而制造的所谓人为投票事件”来解释《哈里斯堡宾州人报》刊登模拟投票,理由并不充分。
“趣味”解释同样无法面对这一事实,即报纸的发展与报纸的党派属性构成了鲜明对比。特贝拉和瓦茨所提供的数据说明,1810年至1828年间报纸的数量从359种上升到852种,而且年印数大约从2 200万份增加到6 800万份。到1830年,全国有1 000多家报纸[19](P109)。正如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所指出的,此际报刊的力量“归根结底要建立在报纸编辑们创建并领导一个党的能力上。报界就其本质来说,是注定要成为某个政党的喉舌,或至少也是某个学派的话筒”[20](PP79-95)。埃默里(Emery)父子解释说,“由于报刊上谩骂成风”,一些历史学家才把这一时期称为“新闻事业的黑暗时代”,“不过,这只是个过渡阶段,而且也许新闻界所反映的强烈的党派偏见,恰恰是为了发泄一些战后积累起来的反英怨气”[21](P83)。这种状况直到1830年代美国报业史上的平等主义“革命”,才真正“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陈述’战胜了‘意见呈现’”[22](P17)。换言之,“政党报”时期新闻自由的原则确立了,报刊骤然增多;然而读者与报刊的关系,形式上是一种买卖关系,可是双方观点信仰的相同远高于这种买卖关系,买报与卖报之间关系主要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政治、宗教或文化的捐助和受助关系[23]。那么,既然买报与卖报之间主要是捐助与受助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报纸无需像后来的普利策与赫斯特那样为了报纸发行量采用“煽情新闻”或“黄色新闻”进行近乎疯狂的竞争。即使是存在竞争,也不是商业性的发行量的竞争,而是读者党派忠诚的竞争或者是对本党派支持者人数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趣味解释”还忽视了模拟投票之所以诞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按照基恩·M.康弗斯(Jean M.Converse)的说法,鉴于统计研究在大学文化中所取得的建制性的学科地位,统计研究者往往从内部主义(interalist)视角来看待他们的活动,也即将统计学科的发展看成是由统计学家自己来完成的理论和资料驱动的工作,而非从一种外部主义(externalist)的方式,也即把学科视为人类文化的另一种形式,大多数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语境来加以阐释[2](P3)。内部主义视角在说明科学史、学科史或艺术发展史上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对于以社会现实问题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政治民意调查来说,内部视角把调查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割裂开来,某种意义上降低了自己理论的说服力。康弗斯谈到自己的社会调查史研究时也坦承:“把这些(商业、政治)领域降低到先驱的角色是需要请求原谅的,因为就其自身而言,这些领域的重要性确实被降低了。比如,在解释社会统计时,我考虑了一直贯穿到‘新政’的某些演进阶段,但我没有把所有社会事实收集的历史一直追踪到1960年代。……我选取了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的某些素材,表明它们作为先驱者、间接的促进者和有时的统计研究联盟的压倒性影响,他们广泛的政治和文化重要性因而被降低了。”[2](P4)康弗斯之所谓的内部主义、外部主义区别实际上强调了一点,即离开了社会环境与政治转型,仅仅对民意调查的发展作内部主义的分析无法回答为何恰恰在“此时”能够得以产生“如此这般”的调查,更无法解释民意调查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方法得以发展的社会语境。
二、模拟投票出场的逻辑提前:“人民同意”宪政体制的确立
我国学者早就提出:“舆论测量是与一个社会的民主开放程度关系密切的,可以说,舆论测量能否受到重视和能否发展,是衡量社会管理者如何对待表达社会舆论的民意的重要方面。”[24](P204)从民意调查本身的逻辑结构而言,民意调查或民意表达的出现本身就蕴藏于这样的前提中:民意是重要的、值得重视的、让人敬畏的,因为民意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以特定的方式行使它的权力。民意表达以及对民意调查的重视首先潜隐于民意是“民主的脉搏”这一政治逻辑之中。《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以及《权利法案》等一系列经典文献,特别是宪政制度确保民众和民意对政府的统治、确保了在美洲殖民地上所诞生的美国政府是一个必要的“恶”——一个用来保护人民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有限责任政府。
《独立宣言》以毋庯置疑的绝对主义口吻昭告天下:“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上帝赋予的某些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24](P3)《独立宣言》尽管不具有在司法上适用的效力,也没有确立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但“它宣布了所谓‘美国信念’,反映了‘美国信念’的准则。这个‘信念’强调人民的权利,法律上的平等,权力有限的政府,以及被统治者接受的政府等。”[25](P1)中国学者王希则更为清晰地呈现了《独立宣言》的内涵意义:《独立宣言》最重要的功能并不在于提出了新的政治思想或政府理论,而在于将原来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思想从一种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现实政治的原则,并通过后来的革命将其变成了新生美国宪政的理论基础。当原来那种虚无缥缈的、停留在言辞之中的自然权利通过与英国决裂的革命而被转换成具体而现实的实质性权利时,它们就不再是空幻之物,而是现实的权利。捍卫和扩展这些权利便成为新社会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独立宣言》标志了美洲和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的政治生态环境的开端[26](P61)。
《独立宣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在1787年《宪法》中得到有效的发展和弘扬。该《宪法》开宗明义地阐明了其性质:“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内部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27](P225)序言明确说明,《宪法》通过之后,合众国不再是13个州的联合体,而是由全国人民组成的统一国家,“我们合众国人民”即明确表明这一意涵,同时这句话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即主权属于“我们合众国人民”——联邦,联邦政府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最高政府和主权代表者。
就本文论题而言,《宪法》在18世纪末的美国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宪政、权力制衡、三权分立这一共和主义的政治体制,是当时流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一件惊天动地的“新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宪法》第一次将联邦制、政府权力制衡及人民主权等抽象理论变成了现实。同时,《宪法》还为使美国转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准备了条件。制宪和批准宪法的过程是一个利益讨价还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美利坚民族的政治原则和理念进行讨论和检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那些平时抽象的概念——包括共和政体、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公民权利、自由与平等——因与实际的政治机制相联系而被普及化了、大众化了、日常生活化了。它们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抽象理论,而是日常的政治实践[26](PP134-135)。
人民主权与人民协商表现在公众参与的政治行为上就是所谓的“代表议事制度”,也即人民虽然是主权者,但作为复数意义上的人民无法直接行使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委托给代表自己意志的“公意代表”来间接行使。麦迪逊(Madsion)为此提出的理由是,“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的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在这样的限制下,可能发生下述情况:由人民代表发出的公众呼声,要比人民为此集会,和亲自提出意见更能符合公众的利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还进一步指出,“谁是公众选举的对象呢?凡是其功绩能赢得国家的尊重和信任的公民都是这种对象。财富、门第、宗教信仰或职业都不得限制人民的判断或者使人民的愿望受到挫折。”[28](P49)
代表议事制度所发展起来的、使政府领导人向一般人民负责的特殊机制,就是选举制度。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将民主定义为对执政者之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安排,人们选择那些能够表达他们意志的人,“自己决定争论的问题,从而实现共同的幸福。”[29](PP395-396)
大多数担任公职的官员不是固定的、终身的,而是有任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人民对官员或代表不满意时,有可能更换他们,选举给了人民这种选择的机会。显然,这种代议制和普选制与封建的君权神授及君主专制的世袭制相比,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因为“政党‘挂名’下的定期选举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保障,它体现了‘民有’(of the people)和‘民治’(by the people)的原则。在选举中,政党候选人与选民进行交流,这是倾听民意的最好机会。由多数决定胜负的选举制度要求候选人必须在选举中形成一个多数的‘胜选联盟’才能当选”[30](P9)。
这种由人民定期推选或选举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迫使政党和政治家们密切观察大众意见、大众态度甚或大众情绪,“大众意见成为西方政治过程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组成部分,选举、国会、全民投票以及许多其他的制度机制常规性将大众情绪与国家行为联系在一起”[31](P6)。被称为“美国民调业、世界民调业主持牧师”[32](P3)的乔治·H.盖洛普(George H.Gallup)就认为,隐含在民主理想中的民意是有形的、动力性的,其发源地就深藏在个人日复一日的体验之中,而这些个人组成政治公众,并阐述这些意见作为政治代表们的运作指南。这种民意倾听大多数相互矛盾的宣传,试图从论点和辩论的冲突、矛盾中区分出真实与虚假;为了它的存在,这种民意需要批评,并通过批评,得到调整和模塑。它通过行动而行动和学习,它的真相是相对的,随着行动获取的结果而变化。它的主要信念是相信实验。它相信个人对政治生活的价值,相信普通人在决定自己命运时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民意是民主的脉搏”,“大多数人的观点必须被视为社会政治问题的终级法庭”[3](P9,P15),“普通人在想些什么”,寻求对此至关重要问题的解答能够追踪到民主生活史的全部[3](PV)。
代议制制度的确立为模拟投票以及后来的现代科学民调(public opinion polls)在19、20世纪的兴起提供了思想与法理基础,正如舆论学者基恩·M.康弗斯所强调的:“民意调查与统计测量是民主政治体系的理想选择,既与官方的民主结构和价值观相符,又反映这种民主结构和价值观。美国精英不可能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一心一意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罔顾他们大众选民中的‘意见持有者’。这些精英被视为民主改革和自由的先驱还是垄断或退步的后卫部队,取决于人们的意识形态趣味、乌托邦希望以及对社会现实限制的判断。”[2](P2)
三、模拟投票出场的特定时代语境:“杰克逊民主”
“人民主权”与“人民协商”在宪法保证下赋予模拟投票和现代科学民调以思想和法理基础。但吊诡的是,尽管美国《宪法》为集体决策设立了民主程序,但是建国之父们明显不想设立一个回应大多数人意愿的政府。事实上,《宪法》最初设计与执行时,公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联邦政府设有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均审查另一个部分,以限制政府权力;联邦政府在《宪法》明确规定的有限联系中运作,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执行大多数人的意愿;在选择一个政府部门某些成员中,宪法仅仅给予公民有限的输入[33](P83)。建国之初的美国选举政治仅仅局限在一个少数享有投票权的政治精英之手,“即使在民主政体下,选民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选举权仍然要有财产资格,官员仍然长期任职,人民很少参与选举他们的官员。政权仍然掌握在有产者和绅士手中。”[34](P92)
尼克·莫恩(Nick Moon)认为:“如果人口中的大多数没有选举权,统计总人口就没有意义。当政治权力掌握在从狭窄的社会谱系中挑选出来的少数精英投票者手中时,富有理想的政治家所要知道的仅仅是那些精英的观点,而且,因为其自身来自同样的社会谱系,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恰恰是广泛投票权的引入,或至少广泛的男性投票权的引入,使得了解更广泛的公众的意见变得非常重要。”恰恰正“因为有了广泛得多的投票权,美国为民意调查的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机遇,也正因此大西洋沿岸各州成为许多人设置第一批模拟投票的地方。”[35](PP2-3)莫恩的这一说法实际上意味着,模拟投票的出现首先来源于此际正在出现的“杰克逊民主”。
19世纪初以来,“注定要击溃地主贵族的势力、铲平老的独占堡垒,为更具有民主性质的政府开辟道路的激进运动,采取了杰克逊民主形式。它的领袖们对民主政治学说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是他们扩大了已为人熟知的原则的应用”[34](P93),这些原则首先就突出表现在选举权上。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把财产和自由相连,使得财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局限,建国之初仍然如此。但是,实际上,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挑战,也同时在独立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并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达到了高潮。1821年,纽约州的立宪会议上有代表批评选举中的财产限制。他们鲜明地提出:“我们没有不同的等级,只有不同的利益”“我们都是相同等级的平民。”[36](P117)一些新加入联邦的西部各州明确规定成年男子每个人都有选举权,东部各州也相继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样一来,有产者的经济独立与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传统对应关系被切断了。公民资格所必须的自主不再基于财产的拥有,而是以对自身的拥有为基础。”[37](P88)1800年至1824年,选举人由选民投票而不是州议会来选出的州逐渐增多,由四分之一的州逐渐增加到四分之三的州,全国的选民人数也由40万增加到110万。
投票权的扩大,使得投票者手中的选票数量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意味着人数成为政治的主要资源。无论是清点选票还是塞满街道都是‘数量’说了算。‘质量’——不管是天生的贵族还是教育的结果——仍可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然而理论上‘质量’并不享有任何特别的权利。”[38](P155)正因如此,19世纪初期的杰斐逊政府期间,开始了常规性的党内投票者倾向清点活动:只问投票者的倾向,个人基本变量和态度等问题没有包括在内,应该作为早期民意调查的起点。《哈里斯堡宾州人报》和《罗利星报》的调查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39]。
1824年的模拟投票还直接来源于国会核心干部会议的瓦解,并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候选人提名程序[40]。从《宪法》的制定开始,局限于联邦政府的内部动员形成了美国历史上两大敌对党派:联邦党和反联邦党,或联邦主义和反联邦主义。这些党派在国会内建立“核心干部决策会议(congressional caucus system)”,操纵总统提名和选举过程,并形成了第一个非正式的总统选举提名机制——国会党团核心干部会议。从1788年到1799年,以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人为首的联邦党人在政府中占据上风,该党崇尚贵族政治,主张“君子不党”。1800年以后,以杰弗逊所领导的国会反联邦势力,在总统与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自此开始了所谓的“弗吉尼亚王朝”时期,杰斐逊、亚当斯、麦迪逊、门罗等几位总统都是这种核心干部机制直接操控的结果。然而,到了1824年,原先的联邦党衰败以至于无法推举出一位有力的候选人来参加总统竞选,杰弗逊领导下的民主——共和党在失去政治对手的情况下,候选人的提名过程就成为州立法机构的党团会议、群众集会、代表大会共同与国会核心干部会议混杂一起的大杂烩,最终人数集中到4个候选人:安德鲁·杰克逊、约翰·昆西·亚当斯、亨利·克莱和威廉·克劳福德。这样,“选择候选人的基础就是个人的,而非政治的”[41],而彼此竞争的候选人及其背后的政治精英迫切需要了解选民情绪的风向,同时还寻找种种证据,以便在各种支持中证明对己有利的“人民意志”[42](P25)。
按照汤姆·史密斯(Tom W.Smith)的解释,4个候选人的出现在瓦解国会核心干部会议的同时,为首次进行的模拟投票提供了直接的刺激[40]:一是民主政体通过公民选举选出其领导人,与自由投票一起增加了人们对选举结果的好奇心:只要自由的选举存在,人们就想方设法要预测选举结果。1824年4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将人们极高的兴趣与对结果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这导致了许多猜测与创新的方法去预期公众的情绪。
二是某个选区的投票趋势也许可以通过人们之间的往来、讨论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评估,但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将各个选区的趋势集中起来以了解全国的投票趋势。因而,将各个区域的选情报告刊登在报纸上,从而评估选民的整体倾向就获得了可能性,而且也恰恰这样做了。布鲁斯·宾伯也提供了这样的旁证:19世纪20年代,信息的传播和交换还局限在面对面接触和缓慢的人力传送的方式,这限制了人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总统是选民代表选出来的,而这些代表对他们自己选民的愿望知之甚少,并不能真正代表选民”,同时“代表制实际上建立在极为粗略的基础上,因为政府官员没有系统性的方法来了解他们的选民。同样,选民也很难完全信任官员,让官员对后果负责任”[15](PP45-47)。在此情形下,在报纸上刊登模拟投票结果就为评估选民投票意向提供一个粗略的暗示。
三是无论如何,选举是需要计数的,对某个样本进行计算自然是预测最终结果的恰当方式。尽管此时尚未出现统计或抽样理论,但是对数量的评估已经很常见,正如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指出的,数字在美国的存在具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在宪法中对代表和议员数的划分也是以数字为基础的,因为数字“提供了一些办法,把人们聚合成一些有意义的集团,而无需作出令人反感的区分。数字是中性的。没有哪一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好’。计算人数(一人一票)这件事本身似乎象征了民主社会的目标——平等。”[43](P244)
此外,伴随投票权扩大、核心干部会议瓦解的,还有新型政治活动家的出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德指出:1820年代,贫穷的农场主和工人逐渐取得投票权,同时也就出现了一类政治活动家,这类人在杰斐逊时期只是处于胚胎状态——领导大众的能人,投合群众情绪的人;1815年至1824年间,正是全国各地这类人形成的小圈子聚集到杰克逊这位著名人物的周围,这些领袖人物在政界一般处于陪衬地位,肥缺也没有他们的份,因而大力向民众鼓吹官员的人选及政策的制订应由民众意愿决定。他们把民众对政治小圈子的不满引向针对政党干部会议制度,指责这种制度公然篡夺人民的权利,并宣传一种信念:必须从社会名流或一群专职官僚手中夺回政治和行政管理仅,并将它开放,让民众参与其事[44](P51)。尽管汤姆·史密斯认为1824年的首次模拟投票不可能是由报纸发起的,但政治家尤其是候选人普遍寻求甚至购买媒体的支持,州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推荐以及各种立法机构的背书都被看成是接近草根或“在草根中”颇受欢迎的标志[42](P25)。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充满黑暗”的政党报纸时期,尤其充满攻击和谩骂的总统竞选中,模拟投票在19世纪20年代政治舞台的出场自然也有服从或服务于总统竞选的需要,或者正如苏珊(Susan)所指出的:“来自模拟投票的量化资料常常在政治争论中被作为权威的民意性质的证据:19世纪中叶前,测量结果常常被寻求自身立场合法性的党派官员和记者视为符号资产”“在选举期间,这些模拟投票常常被政党报纸记者和政客们用来去除对手候选人以及对手政党的合法性,夸大自己候选人和政党的取胜机会。”[5](P5,P69)
结 语
尽管“在方法论上,早期的模拟投票或草根调查与现代民调技术几乎没有多少共同点……但这唤起了兴趣,抓住了政治家的眼睛”[34](PP7-8)。模拟投票在1820年代出现之后越来越多地嵌入到政党、选举、报纸等政治机制或政治运动之中,被作为一种赢得选民、表明胜利在望的工具,或者将其作为自身立场、论点的合法性盾牌,以致到19世纪中叶以后“人民调查”(People’s Polls)非常流行和简便,成为此际报纸中经常重复出现的内容[5](PP76-85)。
[1]MARTIN L J.The Genealogy of Public Opinion Polling[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84,(Polling and the Democratic Consensus).
[2]CONVERSE J M.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Roots and Emergence,1890-1960[M].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3]GALLUP G,RAE S F.The Pulse of Democrac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Inc.1940.
[4]陈义彦等.民意调查[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
[5]HERBST S.Numbered Voices:How Opinion Polling Ha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6]VERBA S.The Citizen as Respondent:Sample Survey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6,(1).
[7]ROBINSON C E.Votes:A Study of Political Predic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2.
[8]MOORE D W.The Superpollsters:How They Measure and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in America[M].New York:Four Walls Eight Windows,1995.
[9]陆震.民意调查:一个有待开拓的社会学新领域[J].社会学研究,1986,(1).
[10]马乾乐等.舆论学概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11]卢毅刚.舆论学教程:2版[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2.
[12]蒋剑辉.民意测验与社会测量: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科学方法[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13]郑方辉,朱一中.民意市场研究:理论方法与典型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14]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运用[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15]布鲁斯·宾伯.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M].刘钢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6]LEE J M.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sim[M].New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7.
[17]MOTT F L.美国新闻事业史[M].罗篁,张逢沛,译.台北:世界书局,1975.
[18]SHEPPARD S.The Partisan Press: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M].Jefferson,North Carolina:McFarland& Company,Inc.,Publishers,2008.
[19]约翰·特贝拉,萨拉·迈尔斯·瓦茨.从华盛顿到里根:美国历届总统与新闻出版界[M].余赤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
[20]罗伯特·E.帕克.报纸形成的历史[M]∥罗伯特·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译.城市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1]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展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22]迈克尔·舒登森.探索新闻[M].何颖怡,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23]陈力丹.西方新闻传播产业化的进程[J].现代传播,2001,(6).
[24]秦志希等.舆论学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5]卡尔威因·帕尔德森.美国宪法释义[M].徐卫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6]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7]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M].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8]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9]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0]张立平.美国政党与选举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1]GINSBERG B.The Captive Public:How Mass Opinion Promotes State Power[M].New York:Basic Books,Inc.,1986.
[32]ROBINSON D J.The Measure of Democracy:Polling,Market Research,and Public Life,1930-1945[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9.
[33]HOLCOMBE R G.From Liberty to Democracy: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Government[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
[34]梅里亚姆.美国政治学说史[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5]MOON N.Opinion Poll:History,Theory and Pratice[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
[36]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37]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M].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8]查尔斯·S·迈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主[M]//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39]刘德寰.在游戏、质疑与验证中走向决策支柱的民意测验[J].市场研究,2005,(7).
[40]SMITH T W.The First Straw?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Election Polls[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90,(1).
[41]BROWN E S.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24-1825[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25,(3).
[42]RUBIN R L.Press,Party and Presidency[M].NewYork:W.W.Norton&Company,1981.
[43]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南北战争以来的经历[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44]理查德·霍夫施塔德.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M].崔永禄,王忠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