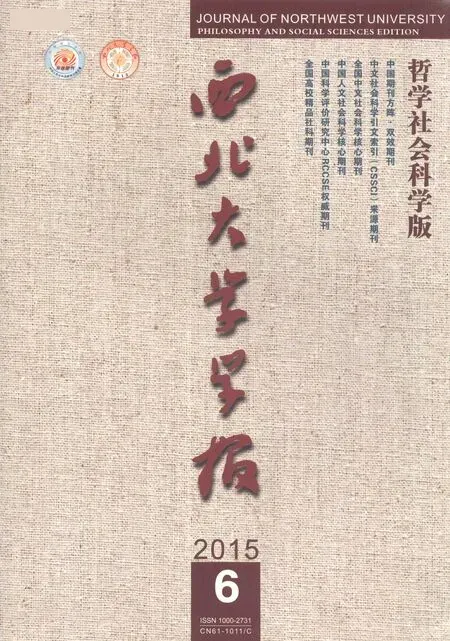论军事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赵丛苍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论军事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赵丛苍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军事考古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并与相关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军事考古学与考古学、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学、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史、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地理学、军事考古学与人类学、军事考古学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的关系进行相应讨论,旨在推动该学科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军事考古学;军事学;人类学;自然科学
军事考古学是我们在考古学领域提出的新分支学科[1][2][3],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并与相关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兹就军事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相应的讨论,旨在推动该学科的深入发展。
一、军事考古学与考古学之关系
军事考古学隶属于考古学,其研究对象是与古代军事有关的所有遗迹遗物,来源于各类考古遗存。考古学所具备以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科属性,使其在真实再现古代军事情况、揭示与复原中国古代军事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性诸方面,有着其他研究方法与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军事考古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一致,即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只是二者的研究范围不同,后者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更多过去社会以及人类发展的事实,而前者更多关注过去军事史实的重建和解读。
考古学发展至今,已有一套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如地层学、类型学、埋藏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聚落形态等方法以及物理勘探、化学勘探、科技测年和理化分析、模拟实验等技术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是发现和发掘军事考古遗存的有效途径,尤其可以借鉴聚落形态的研究思路来分析不同的军事文化遗存之间的组织关系和结构。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学者们已经从其他学科吸收和借鉴了许多理论和方法,更为细致、精准地解读考古材料,注重文化形成过程、人类生存环境、社会如何组织等方面,这些对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至关重要;而众多的考古学理论流派,更丰富和促进了军事考古学的研究。
军事考古学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属性规定了其与考古学的其他诸多内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必然要继承考古学发展的全部成果,它只有在与相关考古学内容广泛联系中,才能使研究如期展开。但是,它又是专业性考古,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其他专项考古的研究方法有所区别:考古学更多关注考古学文化、聚落的结构和布局、文化之间的联系和进程、动力法则,而军事考古学更着重于考察古代物质遗存中有关军事的证据及其背景信息。此外,军事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增加了考古学研究的深度,使学者在同一研究对象中取得比以往更多和更加准确的信息;与此同时,军事考古学又检验着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所发现的一幅驻军图,反映了汉初长沙诸侯国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通过这幅军事守备图,考古学家可以考察当时该地的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4]。
二、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学的关系
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二者均以战争为研究对象,由于战争的复杂性,战争的准备和实施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故军事考古学和军事学都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军事学属于综合性科学,军事考古学属于交叉学科。二者的目标亦相近,军事学是研究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其根本任务是透过极其复杂的战争现象来探索战争的性质和规律;军事考古学也要对古代战争的发生、过程及其规律进行探索。
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由于军事是以准备和实施战争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军事学的内涵和外延远大于军事考古学,它包括武装力量的组织、训练和作战行动,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使用,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应用,战争物资的储备和供应,国防设施的计划和建造,后备力量的动员、组织和建设等;而军事考古学是以考古发现的军事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透过其研究各种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维修等,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武器装备、作战方法等。对于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如正义、非正义,或进步、反动),军事考古学的研究能力有限,对于促进和制止战争力量的讨论,军事考古学更难以为之。此外,二者的时空范围不同,军事学包括古代的、近代的和现代的军事、军事论著、军事装备、军事技术、军事理论等,主要研究现实的军事现象和对未来的探讨,而且将来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人类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军事学也将最终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军事考古学不涉及现代的军事诸如现今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且以发掘和发现的军事遗迹、遗物为主,军事考古学的研究也不以战争根源的消除而结束。
军事考古学和军事学对于战争的探索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程度不同。军事考古学是以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故其结论和研究成果相对客观,而同时受到考古材料的局限,军事考古学揭示的可能仅是战争的冰山一角,难得具有全面性。军事学的研究因人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不同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军事学受各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状况和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的影响,具有各自的民族特征;但军事学所研究的战争是一定时空范围内关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特殊社会活动形态,多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
尽管二者的差异较大,军事学和军事考古学又可相辅相成。军事学的思想、理论对于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可以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如战争根源的学说可以帮助考古学家分析一个军事文化遗存及其所反映的战争的进程,暴力革命学说也可以解释陶寺遗址晚期凸显的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以及被肢解的人骨现象。而军事考古学的遗迹、遗物又补充着军事学的发展,如公元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对特洛伊城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荷马史诗时期的战争,秦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则直接促成了秦代军事学的研究。
三、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史的关系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密切,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的“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军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与其关系紧密的历史学为军事史。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是交叉学科形成的分支学科,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目标与所属的学科相近,军事史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渗透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其主要是通过研究过去的战争和军事建设以总结经验,探索军事指导原则和军事发展规律,包括战争史、军队史、军事思想史、军事学术史、军事技术史等。而军事考古学则是考古学与军事学形成的交叉学科,旨在通过实物资料复原古代军事的史实,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揭示古代军事发展规律。军事考古学和军事史在某些课题,如战争的过程以及起决定作用的客主观条件、以军事作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等方面,两者是相近的,两者也越来越共同关注战争及武装力量的结构和分析。
与此同时,军事考古学和军事史存在一定差异。在研究对象上二者是有区别的。军事史的研究对象或客观实体是军事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涉及的范围较广;而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遗留至今的古代军事遗迹、遗物及与其相关的自然遗存。二者的研究角度、出发点和归宿亦不同。军事考古学以军事遗存及其文化为主要研究重点,研究视野在一定意义上较军事史广阔一些。如李济讨论殷墟出土的五种兵器和工具便放在横亘欧亚大陆的青铜文明中来分析,推测带銎或带环的兵器与工具应有中国以外的因素。而军事史则研究自古至今军事的发展过程,并根据社会生活中物质技术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的变化研究以往的战争和军队以及群众、阶级、政党的军事活动经验,更多注重一个个军事事件之间内部的联系。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军事考古学是以考古学的方法获取资料和进行研究的,研究时注意军事遗存与周围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军事史则主要以各种文献为据,把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以战争发展为主线,以军队、国防、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为重点,研究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军事理论、军事政治、古代战争、兵种、战争方式、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更多关注一些历史事件(战争)的发展和过程。
尽管各具自己的特点,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史的研究仍可以相互启发。军事考古学的重要发现和相关的资料,为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开阔了思路和视角,补充一些史书不载的军事史实,甚至可以纠正其研究中的谬误。比如,中山王墓所出的铜器上记载了中山国乘燕王子哙禅位后引起内乱之机,举兵伐燕,取得辉煌战果的历史[5]。而镇江发掘的东晋、隋唐军事砖砌甬道则为志载东晋的苏竣作乱、孙恩起义、南朝的侯景之乱、唐代的永王兵变等事件提供了物质依据[6]。再如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证明了古代确实有分别出自孙武与孙膑之手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书存在,从而使这一历史疑案有了明断[7]。军事考古学的研究也扩充了军事史的内容,因考古资料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军事考古学分析这些考古遗存及其背后的战争史,这弥补了军事史一直以来注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军事家等精英阶层的分析而忽略对中下层军事人物和中小型军事遗迹分析的缺憾。反过来,正确的军事史观和理论对于解决有争议的军事考古学问题帮助匪浅,尤其是唯物军事史观和军事历史辩证法。如龙山时代,大量的城址和暴力色彩的遗迹现象,是否意味其已进入文明时代和阶级社会学界存有争议。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曾用过“军事民主时代”一词,或许可以概括这一阶段出现的诸多现象。而目前在古代军事史研究成果中所体现出的旗帜鲜明的和平主义,对于军事考古学研究武器装备、战术和战略以及对古代战争的想象和恢复更加现实和准确。军事史的成果也可以解释军事考古学出土物的用途和用法,古希腊陶器上手持各种兵器的武士和战争场面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各类兵器的名称、功用以及战争方式。
四、军事考古学与军事地理学的关系
军事活动的展开和进行需要合适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资源也是造成古代战争频繁的原因之一。此外,军事指挥人员对地理环境的掌控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故伴随战争的发展,军事地理学诞生并发展起来。
军事考古学与地理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军事地理学方面。首先,军事考古学为军事地理学提供了基本的材料。由于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大多一去不复返,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可依靠军事遗存复原地理环境,学界对历代军事防御体系研究的主要依据就是考古遗存再加上文献资料。其次,二者有比较接近的研究对象,共同关注地理形势、自然条件、经济因素、社会状况、交通运输、城镇要地、历史战例等内容,当然军事考古学更多关注城邑位置、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如对长城的调查和研究两学科相互补充,不仅了解了长城的构造方式,而且得出其布局主要是根据军事形势和环境而定。还有,军事地理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为军事考古学提供了范例和思路,如前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大陆心脏说”“地缘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后者文化的多样性。当然,二者的互补性日显突出,如军事地理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关中地区是山河四塞,而历史上关中地理的军事地位和地理概况则要依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来完成。
二者的区别也较明显。二者研究的时空范围不同,军事地理学的绝大多数资料取材于当今之世,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战争规模和作战方式不断变化,其研究范围将由地面、水面进一步向地下、水下和外层空间扩展。而军事考古学主要研究古代的军事遗存,当然也包括被淹没的水下军事遗存,但仍以地下为主,更遑论外层空间。二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军事地理学探索地理环境对国防建设、军事行动的影响以及在军事上运用地理条件的规律,为制定战略方针,研究武装力量建设,进行战场准备,指导作战行动提供依据。军事考古学的任务相形之下更多地集中于军事遗存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二者的出发点也有所不同,军事地理学根据国家政治和军事战略的需要,全面分析与战争关系密切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地理环境以及与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之间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作用突出;而军事考古学依据发现、发掘的考古遗存进行相关研究,政治性和实用性相对要少,其研究成果对指导军事行动意义一般说来不及军事地理学。
五、军事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本质的学科,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规律。
由于历史及政治的因素,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长期无法得到区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开展学术研究。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二者的研究都将推动对人类及其社会的认识,“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将日益走向联合而不是更清楚地分界”[8]。这一认识在军事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互动中也有参考价值,随着学科的发展,军事考古学必将与人类学(民族学)走向联合,但其还是有较为清楚的分界的。
从考古学发展史来说,考古学的发展本身就有两个系统,一是人类学的系统,二是历史学的系统。我国考古学长期有着历史学的传统,但人类学对考古学研究的关照也有着不小的影响。许多学者就提出,把开展民族文物的研究工作和验证考古学某些方法和理论作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新途径[9]。我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我们能够从当前的民族志材料中活动对古代人类活动的推测。如对阴山岩画的考察,有学者就提出将其运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民族考古学“以考古实物为对象通过民族志资料、历史文献去研究考古实物的内涵。阴山岩画研究主要是结合历史文献,民族志材料进行的,即利用了民族考古学方法”[10]。民族考古学的提出就是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合流的结果。
人类学不仅对史前考古的参考意义较明显,而且有些民族学的材料放诸军事考古学视野,能够获得对古代军事活动的相关资料。战争频繁的结果,使战俘数量大增,而战俘是可以随意被杀死的。民族学材料记载,处于军事民主时代的中美洲亚齐克人,曾以战俘充奴隶,并且杀奴隶以献祭[11](P316-330)。我国龙山诸文化中出现的乱葬坑和殉葬现象,应与这种情况相类似。藏族史诗《格萨尔》在军事方面有着丰富的反映,该史诗本身就是部落战争史,它让人类童年的军事艺术跃然纸上,为后来的军事文化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资料,也把最初的军事文化完整地介绍给了今天。又如保安族的传统工艺——腰刀,目前已经失去了其军事意义,但从今天的腰刀制作工艺,与出土的宋元兵器进行类比,我们可以窥测宋元时期西北军事状况,特别是武器装备情况。
六、军事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古代军事战争中有许多遗物涉及物理学内容。如作为远程射击兵器的弩机,原始社会晚期已出现木弩,春秋时以青铜造弩机,结构精巧,便于瞄准。战国时燕国制造了强弩,韩国劲弩能射600步之外。炮的出现和弩的改进与大量使用,是军事技术进步的另一表现。中国最早的炮是抛石弹杀伤敌人的机械,称“投机”“飞石机”“发石车”等。《汉书·甘延寿传》注引《范蠡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
中国发明的指南针, 在11世纪已用于舟师导航。 大型战船除楼船、 车轮船外, 明代还建造了多桅多帆的宝船和福船等巨舰, 能作战于江海和远航大洋。 郑和下西洋所组建的舰队, 舰船曾多达200余艘, 其中宝船60多艘, 官兵至2.7万余人, 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舰船建造与军事航海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军事考古学与化学密不可分。中国火药的发明和火器的创制,在世界军事史上影响深远。北宋初利用火药创制的火毪、火箭等燃烧性火器用于战争,开始了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期。南宋初,陈规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杆火枪。之后,寿春府又制成了能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在发射原理上是欧洲近代枪炮的先导。元军把竹火枪改进为金属火铳,为近代枪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环境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战术的重要作用因素。中国古代长城的修建,凸显了环境对军事战略的影响;骑兵的出现则集中体现了环境对军事战术的影响,环境为军事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军事考古学与生物学也存在联系。生物在古代军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历史上军事所需的大量战马,修筑长城及烽火报警使用了大量的草类植物。
据上述,军事考古学与古代科学技术关系之密切不言而喻。密切二者的联系,可为进一步的交叉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深化对古代军事科技的认识。
军事考古学是以军事遗存为研究对象,而军事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前述内容之外,还如军事考古学与政治学的联系,主要是战争与文明和国家的产生、近代国家的兴起、军事组织在政治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作用等;军事考古学与建筑学一起分析军事防御体系和工程的修建、发展;军事考古学与经济学可以共同分析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国家经济基础与实力,因为这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可以从孙子总结的“度、量、数、称、胜”五个方面考虑;军事考古学与宗教学的联系要注意不同地区宗教对于战争的作用大小,西方军事历史上宗教被用来鼓舞斗志、激励士气,古希腊、罗马的神庙中都供奉着战神,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领袖亦多利用宗教动员百姓的,等等。只有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联合攻关,军事考古学的将来才会更辉煌!
参考文献:
[1] 赵丛苍.军事考古学初论:上[N].中国文物报,1999-11-10(3).
[2] 赵丛苍.军事考古学初论:下[N].中国文物报,1999-11-17(3).
[3] 赵丛苍.军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论纲[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4]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J]. 文物,1976,(1).
[5] 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J]. 文物,1979,(1).
[6] 镇江古城考古所.镇江晋、唐军事甬道遗迹考古简报[J]. 南方文物,1995,(4).
[7] 银雀山汉墓发掘队.徐淑.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0,(11).
[8] 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9] 容观琼.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再论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J].东南文化,1990,(3).
[10] 麻国庆.民族考古学与阴山岩画研究[J].阴山学刊,1989,(1).
[11] 杨群.民族学与考古学[M]//民族学研究(第七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刘炜评]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litary
Archaeology and Its Relative Subjects
ZHAO Cong-cang
(SchoolofCulturalHeritag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Abstract:Military Archaeology is a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and has strong connections to its relative subject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ilitary Archaeology and archaeology, military science, military history, military geography, anthropology and natural science etc. accordingly, to promote the Military Archaeology for a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Military Archaeology; military science; anthropology; natural science
作者简介:郭妍利,女,陕西澄城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大学副教授,从事青铜器和商周考古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军事考古学研究”(13&ZD102)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07-11
中图分类号:K854.1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