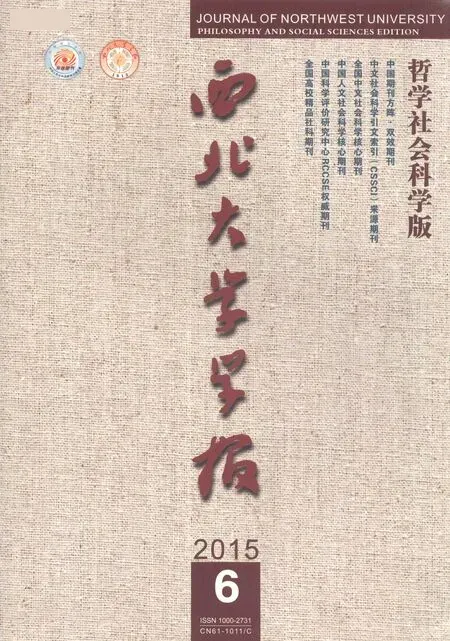秦直道建筑探究
高子期, 周晓陆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秦直道建筑探究
高子期, 周晓陆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210093)
摘要:秦直道作为军事运输工程,主体是道路,其沿线还有关隘、桥梁、阙台、烽燧、城镇、驿站等各类建筑。这些共同架构成直道的立体军事防御网和军需供给网,成为当时南北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融汇的桥梁和纽带。对直道沿线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其战略地位,也成为确定其走向的有利证据,同时对推动秦汉交通史、军事史、历史地理和丝绸之路等研究都有较大作用。
关键词:秦; 直道; 建筑
一、秦直道述略
秦代是古代中国陆路交通网的初创期。秦统一前,北方日益强大的匈奴成为中原政权的威胁。统一后,始皇嬴政即派蒙恬北伐,收复河套以南地区,次年又越过黄河,将匈奴赶至阴山以北,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设立九原郡,在迁徙移民屯垦的同时修筑长城。秦始皇认识到出于保卫边防目的,必须建立交通、通讯和军需补给等快速反应体系,一旦战争爆发,中央能在最短时间内启动应战机制。于是在公元前212年,命蒙恬和扶苏在镇守边关的同时监修直道。
《史记·六国年表》卷十五“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1](P758),《史记·匈奴列传》索引十三:“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1](P2887)这条南北走向的道路大致呈直线,故被称为“直道”。该工程前后用了近五年时间,约至秦二世三年(前207)竣工。直道南起云阳林光宫(西汉为甘泉宫,今咸阳市淳化县梁武帝村),由甘泉山一路向北,途经陕西、甘肃、内蒙古等三省区,穿横山山脉、黄土高原、鄂尔多斯草原,跨黄河直抵九原郡麻池古城。《河套图志·秦汉塞道》载:“今以秦人塞直道考之,自九原起,南至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则今之泾阳至延(安)榆(林),北达乌剌忒旗之五原县,皆秦建筑古道。”[2](秦汉塞道)直道是秦首都咸阳通往北方前线最便捷的道路,它和早年修筑的长城互为依托,构成了一个既能阻挡匈奴南下,又能快速为前线输送军队和补给的整体防御体系。
秦直道所在地势较高,施工较平地困难,却因此减少了人为破坏,减少了河流冲毁导致的水土流失,使它成为遗迹保存较好、较接近原貌的古道路标本。虽历经两千余年的环境变迁,部分路段至今仍能使用。史载直道“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3](P2328),可见直道的设计规划和施工,已具备今天高速公路的雏形。秦林光宫位于渭河谷地的北缘接黄土高原处,是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交汇、对峙的敏感地带,名为帝王避暑离宫,实乃抗击匈奴的军事指挥中心。直道作为秦帝国的交通和信息网络系统,连缀着沿途的关塞和城镇,加上道路自身具备的综合功能,又使它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它的修筑增强了中原王朝军队的战斗能力,使匈奴势力在很长时段内,都忌惮它的存在而不敢贸然进攻。到了两汉时期,其政治、军事、经济作用得到极大发挥。
随着魏晋隋唐时期匈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以后中原政治格局改变,当时威胁中原的突厥人一般由宁夏经甘肃攻打关中,秦直道的军事战略地位和意义因此降低和减弱。由于政治中心东移,而且直道多修建在远离居民聚集的北部高原山地,人迹罕至,该道路自宋代后逐渐荒芜,待到清初,已基本淡出人们视线,这条曾经的军需补给通道也不再行用。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 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呈放射状传播, 到达陇东后与秦直道交汇。 在直道沿线两侧, 目前共发现数十处北魏、 西魏、 北周、 隋、 唐、 五代、 宋、 元各代石窟。 直道自诞生之初至明代, 在军事、 文化、 经济、 民族交往等方面发挥过历代相同或相近的作用, 同时它也被看做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
对于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 早期文献记载并不多。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五年, 除道, 道九原, 抵云阳, 堑山堙谷, 直通之。 ……关中计宫三百, 关外四百余……因袭三万家丽邑, 五万家云阳, 皆不复事十岁。”[1](P256)“秦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1](P264-265)《史记·蒙恬列传》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这些记录指明了直道的起始地点和启用时间,但缺少对路线的具体走向、宽度、途经郡县的名称以及使用情况等的说明。唐代《括地志》及《元和郡县图志》载:庆州华池县(今甘肃省华池县东华池镇)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有秦时的“故道”,即秦直道。
文献匮乏使直道的研究面临不少困难,也正因如此,更吸引着当代各学科学者的关注。秦直道的相关考古研究,始于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的田广金。20世纪史念海《秦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发表后,引起学者们对秦直道起始地点、所经路线、修筑及竣工时间、沿途遗迹、军事防御和经济交流等进行多方考证。其中有关秦直道线路的走向问题争议较大,最新关注点则是如何将该历史遗存纳入当地旅游开发,使直道保护和利用并重*关于秦直道的相关研究,主要成果先后分别有: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文博》1988年第4期;王开《秦直道新探》,《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姬乃军《陕西志丹县永宁乡发现秦直道行宫遗址》,《考古》1992年第10期;吕卓民《再论秦直道》,《文博》1996年第2期;吴宏岐《秦直道修筑起讫时间与工程分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第3期;吴宏岐《再论秦直道》,《文博》1994第2期;1996年由甘肃省文物局组织了秦直道考察和研究,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秦直道考察》一书,从考古学角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秦直道的总体情况,此后内蒙古文物考古部门也对其境内的直道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发表了调查报告;李仲立《秦直道新论》,《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姚生民《秦直道与甘泉宫》,《文博》1997年第5期;《秦直道起点及相关问题》,《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刘治立《秦直道与子午岭地区的佛教遗存》,《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王富春《榆林境内秦直道调查》,《文博》2005年第3期;张多勇《秦直道研究综论》,《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关照》,《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建筑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吴长川《秦直道两三问题谈》,《文物世界》2011年第2期。。但已有的研究多依据文献资料和简单的野外调查立论,并未对直道进行科学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经过2009年和2010年的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大致还原了被岁月所掩埋的秦直道的本来面目*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项目“陕西富县境内秦直道调查发掘”获得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称号,发掘出路面车辙、脚印及大量建筑遗迹。。考古发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对直道相关建筑的分类及技术探讨。
在研读史料基础上,笔者对秦直道进行了为期两月的实地调查,同时采访了主持发掘秦直道富县段和陕甘交界的子午岭段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徒步踏查秦直道第一人的李永强老师以及直道沿途各地文物工作者,据此对秦直道及周边的建筑遗迹概况作出初步整理和分析。
二、秦直道建筑探究
直道作为军事工程,主体是便捷通行的道路,其次还有关隘、桥梁、障塞、阙台、烽燧、驿站、城镇等沿线各类建筑设施,这些建筑设施共同架构成为立体的军事防御网和军需供给网。对这些建筑的研究,是了解直道在各历史时期所发挥作用的支撑基点。既可以深入揭示其战略地位,也能成为确定它走向的证据,对推动秦汉交通史、军事史、历史地理以及丝绸之路和秦汉建筑研究都有独到意义。
道路为人们的交通出行提供便利,同时也是连系城市各功能性建筑间必不可少的要素。《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叙官一九》“遗人”对中国上古道路的修建形式有如下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 三十里有宿, 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名候馆,候馆有积。”[4](P196)这些形式规范了道路的基本设施状况。 《国语·周语》又载: “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5](P66)行道树的种植, 一可作里程标志参照, 二可绿化和保护环境。 偏远地区要为旅客提供就餐住宿等服务和设施, 以确保旅途的畅通与便捷, 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这些虽交待了道路设施的概况, 却很少涉及具体的修建情况。
依《周礼》推测,在直道开口处及沿线应该有着一系列功能齐备的建筑设施。通常在道路的起点和终点会设置有阙和广场。这既是道路起讫的标志,也是部队屯兵和宣誓的场所。宫殿为最高统治者巡幸提供休憩之地,而城镇和驿站等一般性实用建筑,则有着双重的意义:既能作为部队的屯兵之所,也可以作为军需后勤补给、军属安排和军队缓冲休息之处。驿站具有多重功用,在承担邮传职能的同时,还能为军民提供食宿便利。以上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基本涵盖秦汉时期日常生活建筑的多种类型。
(一)道路构筑
秦直道之前相关道路记载,仅有周武王在两京间修建的“周道”*《诗经·国风·桧风·匪风》:“顾瞻周道。”《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四牡》:“周道逶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彼周行。”《诗经·小雅·鱼藻之什·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和以洛邑为中心而呈辐射状向四方修建的等级不同的道路,很少提及其他道路的修建过程和形式。文献对直道的修建情况也讲得较为简略,这是研究中国古代道路建筑的一大遗憾。考古发掘出的直道路基、沟渠、桥梁、涵沟等固态建筑以及路两旁行道树等共同构成道路的标志,为中国古代道路的构成形式提供了复原依据。结合至今尚存的古蜀道“翠云廊”,可以推见当时道路修筑的基本情况。
通过考古发掘,核定了直道的基本路线:起点是陕西省淳化县北铁王乡梁武帝村,终点为内蒙古包头市的麻池乡,陕西富县是直道中部重要的军事要塞和交通驿站。发掘揭露了直道的路基构造、路面状况、护坡形式、排水系统遗存以及施工规模等方面的真实面目。
古代道路一般沿河谷选址修建,而直道的设计者则抛弃了常规的选址方式,而选择了远离河谷的高山之巅。他们在黄土高原的子午岭(现陕甘交界处)沿线,沿山脊设计线路,在低凹处挖山填谷夯筑垫方,建成了古代中国唯一沿山脊和高地修筑的国家级道路。路基由黄土夯筑而成,平坦坚实,目前已发现的道路遗迹全长736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6米,最窄处约20米。陕西境内已发现直道遗迹全长498公里,其中富县段长125公里。桦沟口段直道位于陕甘交界处张家湾乡五里铺村,横跨葫芦河及其支流桦沟河的交汇地带,大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路面一般宽30米至40米。该段发掘工地的位置正处于直道由高岭向平川盘旋而下的路段,在山区的路面一般宽约10米至30米,部分路段宽约40米至50米。道路剖面共有植被层、自然堆积层和碾压层三层,其中碾压层厚度约15厘米至35厘米。直道下层路面的铺筑时间约为秦代和西汉早期,上层路面约为西汉中晚期。在路面发掘出了遗存的车辙和脚印。
经测量得知位于黄陵县兴隆关(即沮源关)以东的堑山路面宽度66米,是直道现有路面的最宽值。该段直道路面宽阔,弯道较大。考古证明,直道全段共有三个路面最宽的节点,该段直道是除起点淳化和终点九原郡之外的另一最宽处。经发掘显示路面铺设情况最为典型的路段,位于富县张家湾乡车路梁和尚塬转弯处。在道路弯道外侧的夯土护坡之外20余米处,又发现与之平行的夯土。两道平行夯土宽达61米,可能是类似甘泉县方家河段直道的夯土隔墙,即在需要大面积夯筑垫方(“堙谷”)的直道外侧,沿路夯筑出数个平面方形隔墙,在隔墙内填土以形成护坡或路面。
富县桦沟口段中心区,发现有与道路平行的沿河高3米、靠山侧延伸5米至6米护坡夯层厚约6厘米至8厘米,靠山侧厚度递减。中心区下方有长达66.5米呈倒梯形的夯土护坡,外侧残高1.4米至1.6米,夯层厚12厘米至24厘米。中心区上方夯土护坡残高1.2米至1.8米,夯层厚6厘米至10厘米。排水系统位于盘山道靠山侧路面,与道路平行,宽1.3米,深30厘米至50厘米。上层为斜坡状叠压堆积土,下层为淤土,沟底铺垫有碎礓石*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陕西富县秦直道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1期。。
有了上述考古依据,便可以基本复原秦直道道路构筑技术。
(二)房舍建筑
直道富县桦沟口段沿线两侧,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及陶器、铜器、铁器、兵器等遗存,这些资料断代明确,为了解秦直道附属设施的分布和内涵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建筑材料堆积中以秦汉时期粗细绳纹、抹带绳纹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残片为主,铜镞和钱币的时代在两汉之间或稍晚。其中有多处直径为55厘米至65厘米的圆柱形夯土磉墩及其上部的石柱础。从布局分析,在道路两旁各有面宽约3.5米的房屋遗存。由于葫芦河水的冲刷和人为破坏,房屋的间数和进深不详。沿河流一侧,还有多处以夯土为基成片相连的建筑基址,面积最大约200平方米。考古领队张在明先生认为该建筑基址是直道上规格较高的关卡性质遗址。
此外,在旬邑县石门关南峰发现了长64厘米、宽16厘米、唇长4厘米的绳纹筒瓦和长70厘米、宽40厘米的绳纹板瓦以及长37厘米、宽37厘米、厚4厘米的几何纹和乳丁纹铺地砖、菱形几何纹空心砖、陶井圈、云纹瓦当和长生未央瓦当,山顶还有大型石柱础等秦汉建筑材料堆积,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根据出土材料及规模分析,该处可能为当时宫殿遗址。在距石门关两公里处石门村东台地,还有南北长约40米、东西宽约10米、总面积约40 000平方米的建筑遗址[6](P75-78)。这些发现能够明确直道沿线有关卡、宫殿等建筑遗址,带给人们全新认识。
(三)桥梁与关塞
2005年7月,甘泉县文物工作者在洛河南岸台地桥镇乡安家沟村发现了一处秦汉建筑遗址,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80米,总面积约 12 000 平方米左右,与洛河北岸人称“圣马桥”的秦直道引桥遗址隔河相望。遗址内绳纹板瓦、筒瓦、云纹瓦当、空心砖等建筑构件以及罐、瓶、盆、甑等陶制生活用品残片随处可见[7](P14)。据现场遗存分析,这些或是集洛河渡桥的保护和管理于一体,同时兼具驿站功能的机构所在地。
洛河北岸的方家河村西引桥至今尚存高20米的桥墩遗迹,夯土每层厚约12厘米至20厘米不等。北方多为季节性河流,所以路旁往往建有大型冲沟,与都江堰、灵渠等南方水利工程不一致。有关直道桥梁建筑的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研究。
在距离旬邑县石门关中峰南坡,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南北长约10米、东西宽约30米、总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建筑遗址,离行宫约200米处,与石门关仅一沟相隔。考古研究者由此推论,此遗址可能是石门关要塞的屯兵处[6](P75-78),与富县段直道建筑性质相同,相关的研究亦有待继续深入。
(四)阙台遗迹
在直道遗址的南部起点淳化县,其端口处有宫城的北城墙遗迹,东端南部现存一对圆锥形的夯土遗存,如巨冢般伫立于天地之间。该夯土遗存底部宽宏,在其南侧尚有大量残砖断瓦及草拌泥墙面的残留遗存,它们应当是土木结构残阙的夯土台基。其中西侧夯土台现存约高15米,底部周长约200米,顶部周长约40米;东侧夯土台现存约高16米,底部周长约220米,顶部约30米[8](P32)。类似的夯土遗迹在直道的中部富县和终点九原郡所在的包头市各发现一处。道路前立阙的相关记录虽未见诸文献,但在当时有着凡重要建筑前必定立阙的传统,例如商鞅在咸阳宫区“筑冀阙”。直道作为秦帝国国防的标志性建筑,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阙的树置是显而易见的。文献记录秦直道最宽处约60米,而现存两夯土台基之间距为57米,若经考古清理,这对封土基部直线距离当略大于60米,与现测秦直道之最宽处大体相符。联系两夯土台基周围的建材遗存,根据秦始皇陵的勘探资料以及汉茂陵前置阙的情况,特别是已发掘的景帝阳陵南门阙址资料为依据,再参照画像砖石中道路、桥梁前均有双阙的设置,笔者认为该夯土遗存为直道起点处的土木阙基址遗存。
两阙在汉武帝时期改作“通天台”*姚生民《甘泉宫志》:“东北方中部以下向外突出,呈台阶状,原似为三出阙。其下有础石、草泥块、白色壁面,壁面上曾见朱、黑色绘画痕。……台基底部夹有大量残砖瓦。两大台基雄峻壮观,远瞩醒目,为通天台遗迹。”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8](P32)。阙以南是黄土高原与渭河谷地的结合部,既地势开阔又沟壑纵横;近阙体前后,显然为人工平整过的、好似阅兵誓师的广场。直道如砥由此向正北延伸,雄伟的嵯峨山投影正好插入两阙之间。极目向北,由黄土高原攀上蒙古高原,有直冲蓝天之势。直道沿线虽然有着众多的烽燧遗迹,但与巨大的阙的封土遗存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直道中部的富县及终点处的内蒙古包头九原郡,也各有一对与梁武帝村类似的大型夯土遗存。因所见三处夯土遗存处的直道宽度基本一致,均达到直道的最宽值,又分别位于直道三大重要节点,故笔者确认该夯土为秦直道起点、中部及终点处的土木阙址遗存。沿着秦直道一线,尚见有多处秦汉残砖瓦建筑遗存堆积,是否还有阙台,尚待考察。
三、结语
直道与以军用为目的长城有着不同的性质,作为连接关中和北方地区的军事通道,不仅满足了始皇帝“欲游天下”的私心,更加快了中央政府与北方各地的联系速度,保证了政令的畅达。在发挥军事防御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流与融汇的纽带。
秦直道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意义重大,在工程测绘、设计和施工、管理等方面,反映了秦代经济、文化、交通和建筑技术水平的较高成果。直道建筑是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却也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对它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拙文仅指出了有关直道的道路建构、房舍、阙台和桥梁等部分建筑遗迹,事实上的秦直道建筑遗迹较上述几类遗迹可能更为丰富,值得人们作出更多探索。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张鹏一.河套图志[M].在山草堂(铅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 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6] 国家文物局秦直道研究课题组,旬邑县博物馆.旬邑县秦直道遗址考察报告[J].文博,2006,(3).
[7] 王勇刚,崔风光,李延丽.陕西秦直道甘泉段发现秦汉建筑遗址[J].考古与文物,2008,(4).
[8] 姚生民.甘泉宫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刘炜评]
【考古与文物研究·军事考古学专题之一】
Architecture Study:The Straight Path of Qin Dynasty
GAO Zi-qi,ZHOU Xiao-lu
(SchoolofHistor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The straight path of Qin is a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The main function is street, together with passes, bridges, que, beacons, towns, posts and other kinds of buildings. All these construction elements consist the three-dimensional military defense and supply network along the main straight road. The straight has became the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national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ing. The research on these buildings along the straight is useful to understanding its strategic situation. It will also offer clear evidence to determine its geographic orientation. This research has also a great effect on the research of the transportation history, the geographic history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also the research on the silk road.
Key words:Qin Dynasty; straight; architecture
作者简介:孙俊,男,吉林人,辽宁师范大学特聘三级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隋唐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S012)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16
中图分类号:K878;E291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