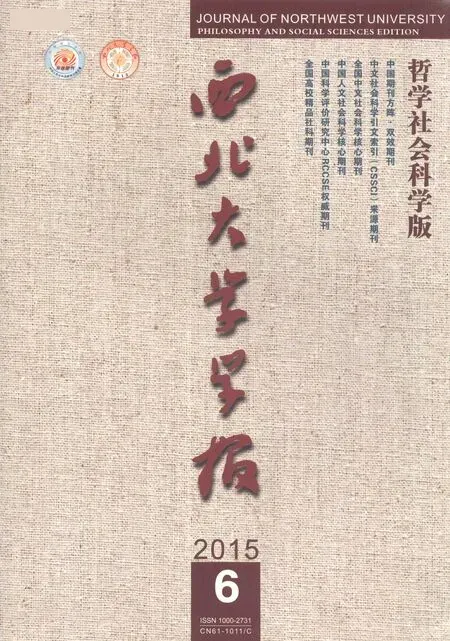商周青铜兵器研究回顾——兼论军事考古学目标下青铜兵器研究的新思路
郭妍利,张杨力铮
(1.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2.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商周青铜兵器研究回顾
——兼论军事考古学目标下青铜兵器研究的新思路
郭妍利1,张杨力铮2
(1.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710119;2.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青铜兵器作为商周文明的重要象征物,很早便受到学者重视。目前学界已经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然其研究尚存在不平衡现象。除了加强基础研究外,对其深层次的分析更为重要;在军事考古学研究目标和视野之下,商周青铜兵器的深入研究可另辟蹊径,即通过对青铜兵器各种组合的动态研究以达到以物透人、透史之目的。
关键词:商周时期;青铜兵器;军事考古学;新思路
《孙子兵法·始计篇》云: “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①《左传·成公十三年》亦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首要社会活动。作为商周战争的物化形式,青铜兵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故历代学者对其有所关注, 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其有专门的探讨。 然纵观青铜兵器的研究简史, 可以看到有关研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目前的讨论虽呈一定的上升之势, 但深度和广度亦有待加强。 如何突破研究瓶颈, 是学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年来军事考古学的提出, 为青铜兵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就之进行讨论, 以期促进青铜兵器的研究。
一、商周青铜兵器研究简史回顾
金石学发轫以来,历代金石学著作大都对商周青铜兵器有所收录,对其进行简单的描述和考订,尤其关注铜戈。而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书中所附的《商周兵器说》则是首篇分析商周青铜兵器演变之作。总的来说,此时的兵器研究不被重视,大多附在杂器之下,基本为器类或铭文的介绍,其中有些真伪混杂,时代有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的15次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篇章,也使青铜兵器的研究跳脱传统金石学的窠臼,进入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的科学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与相关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商周青铜兵器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内涵不断加深。
在兵器通论性著作中有不少对商周兵器的研究。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第二章内容为铜兵,介绍了夏商周各代的兵器[2],其后的论著以杨泓的《古代兵器通论》最为系统和全面,该书第三章的内容为青铜时代的兵器[3]。
郭宝钧立足于考古资料,结合文献材料,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专论了殷周的青铜兵器[4]。朱凤瀚论述了二里岗、殷墟两期的青铜兵器[5]。郭妍利系统讨论了商代青铜兵器的时空框架、纹饰、铭文、组合、源流和分布格局[6]。徐坚则以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为指引系统研究了商周青铜兵器和玉质兵器[7]。而罗樾所著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兵器》使中国商代兵器处于世界范围的大框架中[8]。林巳奈夫所著的《中國殷周時代の武器》[9]则是当时乃至时下日本研究中国商代兵器最优秀的著作。
青铜兵器种类的研究成果最多,以钺、戈、戟、矛、剑的研究为重点,也有对铜刀、镞、殳等进行分析的。学者们多归纳了各类兵器的基本类型和演变特征、时空框架、功用等问题。斧钺研究以杨锡璋和杨宝成、陈旭和杨新平、陈芳妹、钱耀鹏、刘晨的文章为代表*参见杨锡璋、杨宝成《商代的青铜钺》,《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37页;陈旭、杨新平《商周青铜钺》,《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陈芳妹《商后期青铜斧钺制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刘晨《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斧钺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铜戈的研究以李济对勾兵演变的探讨[10]、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11]、加拿大明义士1942年对商戈的研究[12]最具代表,戟的考证以马衡、郭宝钧、郭德维、李润训、钟少异等人的成果为代表*详见马衡《戈戟之研究》,《燕京学报》1929年第3期;郭宝钧《戈戟余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集;郭德维《戈戟之再辨》,《考古》1984年第12期;李润训《勾戟、戈戟考辨》,《故宫文物月刊》第139期;钟少异《试论戟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年第11期。,铜矛的研究比较零散*主要的成果有:沈融《吴越系统青铜矛研究》(《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和《商与西周青铜矛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李健民《商代青铜矛》,《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374页;胡保华《中国北方出土先秦时期铜矛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青铜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越剑、巴蜀柳叶形剑和短剑的分析上*主要的成果有:朱华东《吴越系青铜短剑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段渝《商代中国西南青铜剑的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年第2期;乌恩《关于我国北方的青铜短剑》,《考古》1978年第5期;翟德芳《中国北方地区青铜短剑分群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吕军《中国东北系青铜短剑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青铜刀的研究以刘一曼对殷墟刀的全面整理和讨论最见功夫[13],铜镞的系统分析则见于石岩的博士论文[14],防护性兵器以张卫星对先秦至两汉出土甲胄的分析[15]和成东对先秦时代盾的讨论[16]最具代表性。
对特定区域青铜兵器研究的文章亦不少,尤其以讨论殷墟、吴越、巴蜀为多。殷墟的青铜兵器以李济、陈志达、陈芳妹、郭鹏的研究为代表*参见李济《记小屯出土的青铜器(中篇)》,《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陈志达《殷墟武器概述》,《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337页;Chen Fangmei, Bronze Weapons of the late Shang Period, London University,1997;郭鹏《安阳青铜武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集刊》第15集。,吴越地区的青铜兵器以肖梦龙的专论最为用力[17],童恩正、李健民、范勇、李冬楠、范晓佩分别讨论了西南地区的戈和剑、矛、斧钺、晚期巴蜀文化的青铜兵器及随葬制度*参见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和《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李健民《云南青铜矛》(《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和《论四川出土的青铜矛》(《考古》1996年第2期);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李冬楠《晚期巴蜀文化出土兵器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范晓佩《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兵器随葬制度的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杨丁、梁法伟分别讨论了山东地区商和西周、东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参见杨丁《山东地区商西周青铜兵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梁法伟《山东地区出土东周时代铜兵器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毛洪东分析了关中地区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18],周攀探讨了江淮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19]。
早在20世纪50年代, 石璋如就利用组合关系来研究殷墟的兵器[20], 其后郭鹏将安阳殷墓中青铜兵器组合归纳为四种模式[21](P151-171), 刘一曼将殷墟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归纳出12种不同的组合方式[22]。近年来, 一些对商周兵器进行区域研究的硕士论文也涉及对兵器组合及其所反映问题的一些讨论。
对青铜兵器的纹饰研究,多讨论虎纹、菱形纹等纹饰*代表性成果有:姚智辉、孙淑云、肖璘等《巴蜀青铜兵器表面“虎斑纹”的考察、分析与研究》,《文物》2007年第2期;代丽鹃《晚期巴蜀文化兵器装饰性动物图像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谭德睿、廉海萍、吴则嘉《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也有分析商周青铜兵器上乳钉纹者[23]。对青铜兵器铭文的研究比较零散,多以战国时期各国兵器铭文考释为主*主要成果有:黄萍《新出兵器铭文的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卢冀峰《河北出土商周青铜兵器铭文辑证》,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周翔《战国兵器铭文分域编年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人聪《江陵出土吴王夫差矛铭新释》,《文物》1991年第12期。。
以青铜兵器为出发点,并与其他材料相结合,讨论其文化寓意的研究在逐步增多,内容包括从兵器看作战方式*杨泓、郭妍利认为商代还没有制出专为作战使用的战车(杨泓《战车与车战二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郭妍利《夏商时期的作战方式蠡测》,《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而罗琨、石晓霆等认为商代晚期已经进入车战时代(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石晓霆、陶威娜《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随葬兵器制度*陈芳妹提出铜兵器在墓葬中与礼容器的数量关系是了解墓主身份与军、政关系的指标,指出青铜兵器到殷商时代才开始普遍随葬于墓中。井中伟对西周墓中“毁兵”葬俗进行了观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兵器文化属性*例如印群以三角援戈为切入点,分析了随武王伐纣的蜀人(《商周之际三角援青铜戈与蜀人随武王伐纣》,《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再如朱凤瀚认为在武丁至祖甲时段遗存中存在的北方式青铜器特别是兵器的存在是此时商人与北方族群频繁战争的体现(《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等。
从科技史角度或跨学科研究青铜兵器的合金分析、铸造工艺等方法,始于殷墟的最初发掘之时,而此后青铜兵器成分的分析长期作为主流课题,其手段方法也日益多样化、精确化,重要的考古发掘基本都有相关的科技分析,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殷墟、吴越、巴蜀等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上*代表的成果有: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铜器的化学组成再研究》,《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2-638页;万家保《殷周青铜盔的金相学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之六十;贾莹、苏荣誉《吴国青铜兵器的金相学考察与研究》,《文物科技研究》2004年第2辑;廉海萍、谭德睿《东周青铜复合剑制作技术研究》,《文物保护与科学》2002年增刊;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王琳《从几件铜柄玉兵看商代金属与非金属的结合铸造技术》,《考古》1987年第4期;王运辅《对青铜镞长铤的模拟实验研究》,《文物》2007年第11期。。
以上的简要回顾显示出目下商周青铜兵器的研究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门类,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夏商周时期青铜兵器的研究尚不平衡,多为类型学的分析,纵向的演变分析较多,横向的分区和对比较少;就空间范围而言,主要集中在殷墟、吴越等青铜兵器特征性明显的区域,其他区域包括两周时期京畿之地论述较少;对青铜兵器的基础分析较多,如分类、分期多,而对兵器的组合、纹饰、铭文、工艺方面不够,更不重视青铜兵器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涵义和背景信息;专题性研究较多,且多为某一学科的研究成果,综论性文章阙无,多学科的结合较少,缺乏系统的、深层次的研究。
二、军事考古学目标下的青铜兵器研究思考
如上所述,目前青铜兵器的研究仍处于积累和初步研究阶段,其研究尚不及青铜礼容器成熟。那么,如何更好地促进青铜兵器的研究呢?除了学者们继续完善夏商周时期青铜兵器的文化谱系、微观分析外,对其深层次的宏观把控和归纳也非常重要。而兵器是军事的一部分,倘从军事考古学的角度去讨论青铜兵器的研究定会有新获。基于此,本文拟分析军事考古学背景下的青铜兵器研究。
(一)军事考古学的定义和研究思路
迄今为止, 何为军事考古学, 学界尚无统一定义, 本文参照军事考古学的提出者赵丛苍先生的基本看法*“军事考古学”命题的提出和论述详见赵丛苍《军事考古学初论》和《论军事考古学的现实意义》,分别见《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10日和2013年8月16日。。
我校会计学课程建设加大了管理会计课程的比重,增加管理会计专业知识的比重,构建财务转型时期的会计学人才培养体系。在会计学专业与CMA管理会计相关课程有机整合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课程体系。当前课程体系培养财务人员财务管理能力、战略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
军事考古学是以古代军事遗存及其相关的自然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学科,旨在通过揭示考古发现的各类军事遗存与其赖以产生并保存的各种文化因素直接的关系,来认识人类的军事行为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规律。
以现有的认识,军事考古学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对考古遗存中的军事类信息的诠释;二是借以获得相关信息的方法和手段如地层学、类型学、考古调查与发掘、科技考古分析等;三是军事考古学的理论性研究。军事考古学除了贯彻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外,要结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其方法,逐渐创建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军事考古学的提出立足于考古学及军事学、社会学的发展,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手段探讨中国古代军事发生、发展等历史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必须首先结合考古学与军事学,再综合其他各类学科的手段方法才能实现军事考古学的目标,仅仅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手段是无法完全满足的。
(二)青铜兵器研究的新思考
目前绝大多数商周青铜兵器的研究尚停留在“就物论物”的层次上,少有“以物见人”的论述,兵器所能体现的当时单兵装配情况、部队的兵种配置及作战方式等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虽然也有学者对该类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很好的看法,但仍略显宽泛,缺乏细致、系统的梳理,且多将视野集中在车战问题上,也缺乏对单兵装备、部队构成的研究,致使该类问题缺乏一个全面的研究成果。而作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兵器的研究理应纳入到军事考古学的体系之中,这种视角也为现今青铜兵器研究的突破提出了更好的思路。
兵器是士兵乃至军队最基本的需求品,是与军士们关系最为密切的物品,这种先天的紧密联系是今人能够“透物见人”的基础条件。其次,如今我们获得的绝大多数商周青铜兵器的资料都来自于考古发掘的墓葬之中,还有一部分来自窖藏、祭祀坑,这三类遗迹都构成了相对稳定、完整的信息场。特别在“事死如生”的时代,墓葬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缩影,通过随葬器物我们可以复原当时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况。这是我们“透物见人”的必要条件。拥有这些条件,便可复原当时最小作战单位——单兵乃至较大的作战群体的武备状况,再以此为基础探讨部队兵种构成与作战方式等问题。
首先,加强青铜兵器与其他质地兵器之间的组合。青铜兵器与其他质地兵器的组合直接反映着青铜时代攻守双方的武器配备以及作战方式。过去的研究多关注某类兵器的研究或青铜兵器之间的搭配。但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石质和骨质兵器一直存在于青铜时代,尽管其制作不及青铜兵器精良,但却作为青铜时代武器的有力补充。如商代王妃妇好墓中出土有铜钺、戈、镞134件,29枚骨镞[25](P105,P208),王妃墓尚且如此,遑论一般墓葬?此外,不同时间段各类兵器的尺寸和搭配比例有所不同,显示着作战方式的不同,夏商时期兵器多以短柄的戈、钺、矛、镞为主要组合,应是徒兵作战的体现;而两周时期,车之五兵与步之五兵之分充分体现了“兵惟杂”“兵不杂则不利”(《司马法》)的原则。所以,从兵器使用功能着手,分析进攻性兵器和防卫性兵器、近距离格斗兵器和远射兵器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它们在一个士兵的装备上是怎样组合的。在此基础上,从兵器的数量组合上观察作战单元是如何组织的。
其次,注意青铜兵器与其他遗物的组合。青铜兵器既是实用的作战器具,也是青铜时代使用者身份的象征和财富的指示。研究表明,质地精良的钺、大刀是商代军事统率权的重要标志,其与青铜礼容器、玉器、海贝、车马等一起为使用者陪葬。正如罗森指出的,尽管武器与马车受到的关注要少于礼器,它们的不断出现显示了其在实际战争与标志等级两者中的地位[26](P363)。对青铜兵器与其他遗物的研究可以使用context方法,注意各种遗物的出土信息、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
第三,关注青铜兵器与相关遗迹之间的组合,包括与防御设施、军事边防、后勤保障系统等的关系。兵器作为战争的手段之一,与其他战争设施一起构成特定时段战争的物化形式。只有结合起来看,才可以精确区分不同时间兵种的构成,进而结合不同兵器的使用性能观察其适应何种作战方式。结合这些信息,就能够复原商周时期从单兵装备到部队构成的详细信息和作战模式,进一步分析特定时间段战争的形式状态、性质,乃至战争双方的布局及其对策。
第四,强调青铜兵器的研究与古代军事学、军事地理学等学科上的组合关系。青铜兵器有赖于古代军事学的研究,后者关于军队的产生与发展、军制装备和战略战术的变化、军事交通与工程技术成就、军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均为青铜兵器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青铜兵器的形制主要因作战环境的要求而产生,也受到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军事地理学探索与战争关系密切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地理环境对国防建设、军事行动的影响以及在军事上运用地理条件的规律。军事地理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为青铜兵器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和思路,更为作战模式的构成提供了背景信息。
当然,上述研究都必须放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加以考量。结合现今已经比较成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成果,贯穿时间轴线于研究始终,获取演进、变化的情况,就能够解释中国军事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利用区域对比的方法,观察同时期内不同族属或文化势力在兵器装备、部队构成以及作战方式上的异同之处,就能够看到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对于人类战争行为模式的影响。
最终,再结合相关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从中分析并得出具体的演进原因与发展规律,从而得到商周时期军事状况在此方面立体、翔实的图景。
可以说,军事考古学的提出开拓了青铜兵器研究的新领域、新思路,而以此为研究手段所得出的新成果又能够丰富军事考古学的内涵,为该分支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孙武. 孙子兵法·始计篇[M]. 北京:线装书局,2013.
[2]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 杨泓. 古代兵器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4] 郭宝钧. 殷周的青铜武器[J].考古,1961,(2).
[5]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6] 郭妍利. 商代青铜兵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7] 徐坚. 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8] LOEHR M. Chinese Bronzes Age Weapons: the Werner Ja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M].Peking. Ann Arbor: Universuty of Michigan Press; London: Geoffrey Cumberle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9] 林巳奈夫. 中國殷周時代の武器[M].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2.
[10] 李济.俯身葬[J].安阳发掘报告,1931,(3).
[11] 井中伟.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2] MENZIES J M, SC B A. The Shang Ko: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 Weapons of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1311-1039 B.C. Toronto: The Far Eastern Department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University of Toronto,1965.
[13] 刘一曼.殷墟青铜刀[J].考古,1993,(2).
[14] 石岩.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5] 张卫星.先秦至两汉出土甲胄研究[D].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6] 成东.先秦时期的盾[J].考古,1989,(1).
[17] 肖梦龙.吴国青铜兵器研究[J].考古学报,1991,(2).
[18] 毛洪东.关中地区出土西周青铜兵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9] 周攀.江淮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兵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20]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22集), 1950.
[21] 郭鹏.殷墟青铜兵器研究[J].考古学集刊(第15辑),2003.
[22] 刘一曼.论安阳殷墟墓葬青铜武器的组合[J].考古,2002,(3).
[23] 韩金秋,杨建华.略论商周时期兵器上的乳钉纹[J].文物春秋,2010,(5).
[24] 陈梦家.殷代铜器[J].考古学报(第7册),1954.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6] 罗森(Jessica Rawson).中国的丧葬模式——思想与信仰的知识来源[M]//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炜评]
【考古与文物研究·军事考古学专题之一】
The Restrospective Study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ronze Weaponry: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on Bronze Weaponry by
The Objective of Military Archaeology
GUO Yan-li1, ZHANG-YANG Li-zheng2
(1.ShaanxiNormalUniversity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 710119,China; 2.NorthwestUniversitySchoolofCulturalHeritage,Xi′an710069,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the bronze civilization, the bronze weaponry in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has attracted many scholars′ attention since early time. However, the study of the bronze weaponry is still unbalanced. Besides strengthening the basic research, the deep analysis about the bronze weaponry is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military archaeology research goals and vision,the further research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Weaponry could find a new way,which means to understand human beings and history through materials by studying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bronze weaponry.
Key words: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bronze weaponry; Military Archaeology; new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高子期,女,四川雅安人,美术学博士,南京大学考古学流动站博士后,从事艺术考古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界2013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研究项目(2013C085)
收稿日期:2014-11-12
中图分类号:E291;K871
文献标识码:A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