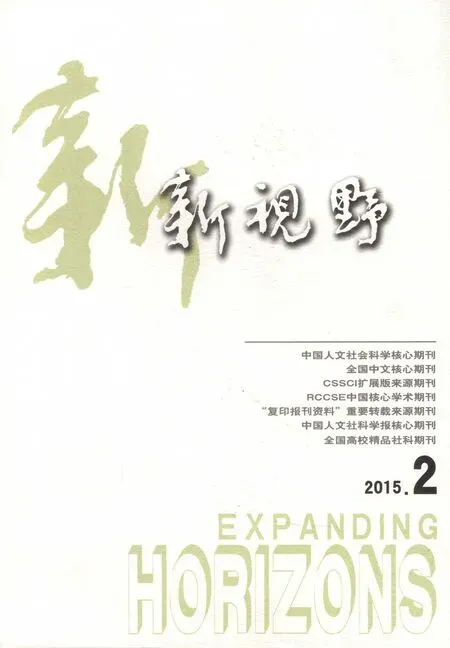城乡关系、乡土危机与社会重组
——费孝通的《乡土重建》及其当代意义
文/王建民 张 璐
城乡关系、乡土危机与社会重组
——费孝通的《乡土重建》及其当代意义
文/王建民张璐
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剖析了中国乡土危机的经济与社会根源。费孝通分析了乡土社会农工混合的经济特质以及城乡间机械的经济循环模式,进而提出,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潜藏的土地问题,导致城乡关系紧张与社会矛盾叠加。因此,必须重整乡土工业,发展乡土工业本土化,建立新的合作性的社会组织,最终实现社会重组。时至今日,《乡土重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新时期的农村建设、城镇化战略,而且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也具有示范价值。
乡土重建;乡土工业;社会重组;社会学本土化
晚晴民国以降,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部分地区乡土经济严重衰落,引发了知识界对“乡土社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费孝通早期的乡土社会研究便是在这种现实与思想背景下开展的,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乡土社会内部结构的张力及其危机,指出中国社会变迁逼迫乡土社会必须在自力更生中重建,进而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发展乡土工业、实现乡土重建的思想。费孝通在1948年发表的《乡土重建》一书,正是他多年的乡村社区调研的思想结晶。本文拟重新解读《乡土重建》一书的主要观点、分析思路及其当代意义,尤其关注此书所展现的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剖析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思考路径,以期对认识和思考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有所裨益。
一 乡土社会中的乡土经济
在《乡土重建》一书的《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乡村和都会是相互关联的一体,即乡村与都会可能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也可能会势不两立、两败俱伤。一般而言,乡村与城市是一种循环关系,城市的地主阶级是消费群体,依靠土地所有权和高利贷吸收乡村的一部分土产品和资金,并通过购买农户手工业产品使小部分资金回到乡村;付出地租后的农业生产剩余不能满足农户的生存需求,农户需开辟家庭手工业来弥补生活开支。不过,传统社会的这种城乡循环,是一种片面的、不利于乡村发展的循环关系。
(一)城乡结构:乡村、市镇、都会
从城乡分别来看,乡村是传统中国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乡下百姓依靠土地耕种来获得农产品,通过乡土工业(主要指手工业)来获取轻工业收入,以此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市镇以商业贸易为目的,因商业活动形成人口聚集,这种小市镇和乡村在经济上是一种互助关系。但随着中国人口累积,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村中一些拥有土地的相对富庶的百姓出租土地、脱离农村,住入设施较为完全的城市,他们以征收地租和利息等方式来获得所需的粮食和劳役,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市镇。
在乡村、市镇之外的另一种社区形式是都会。都会是一种不同于市镇的工商业社区,主要以通商口岸作为主体,包括其他以推销和生产现代商品为主的通都大邑。现代都会一方面把大批洋货运进来,一方面又利用机器制造日用品,这就挤垮了乡土工业尤其是手工业,夺走了乡下百姓的手工业收入。并且,都会和乡村并不直接进行贸易,它们通过大市镇进行经济交易,这就导致市镇中的地主们进一步压榨乡下百姓的血汗钱,结果是,与日俱增的地租、利息使农民贫困至极。
那么,倘若乡村离开都会,这种局面是否会缓和,乡下百姓的生活水平是否会提高呢?倘若乡村脱离都会,在短期内可避免农产品外流,但从长期看却是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恢复到原始的简陋生活。并且,都会和乡村的隔离威胁了依赖乡村供奉的地主,都会的畸形经济难以维持,中国经济将会面临都会破产、乡村原始化的悲剧。因此,都会与乡村命运相系,无法各自行事、独立发展。
(二)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特点——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并不集中在都会里,而是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1]可以说,这种观点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特征,对动辄将中国传统经济归结为“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观点无疑是一种警醒。
传统乡土工业以家庭工业和作坊工业两种形式为主。家庭工业是农民为解决生计问题而从事的工业活动,这是乡土工业的主要形式。作坊工业的基础是农业里积累下来的资本,需要特殊设备和技术工人,比如造纸、碾米、烧窑等,这就逐渐发展成后来的工厂。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相互配合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进而可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所需,以维持城乡相对稳定的循环结构。
在认识了城乡关系以及乡土经济的主要特征后,近代以来乡土经济乃至乡土社会的危机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乡土社会的危机与根源
近代以来,西方机器化大生产、工业扩张进入中国,致使乡土工业崩溃,建基于其上的城乡之间的循环也逐渐瓦解了。费孝通认为,这正是乡土社会危机甚至是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中国社会的各种潜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也全面暴露,形势十分严峻。
(一)乡土工业崩溃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在这一经济模式下,乡村百姓可以依靠农业和乡土工业(主要是手工业)获得经济收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费孝通描述的“江村”(开弦弓村)就拥有这种农工混合的典型经济特征。江村农民两大收入来源即农业和蚕丝业(手工业的一种),蚕丝业的收入填补了农业收入的不足,从而维持正常生活所需。但是,现代制丝业的先进技术引进中国之后,乡村制丝业开始衰退。不仅如此,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个乡土工业都经历西方机器工业冲刷,直至崩溃。乡土工业的崩溃是它和西洋都会机器工业竞争的结果,大规模机器生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品质,但维持传统社会平衡的农村手工业也随之衰落,乡村逐渐单纯农业化,农民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农业生产,这些变化激化了中国的土地问题。
(二)土地问题
2.3 两组患者血糖、血液流变学、血清相关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变形指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低氧诱导因子-1α水平低于治疗前,且B组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红细胞变形指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低氧诱导因子-1α水平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5。
由于乡土工业崩溃,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农民面临着饥饿问题。一方面,农民失去了乡土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带来的经济收入,更加依赖土地带来的收入;另一方面,地主阶层不断追求享乐、消费西方舶来品,更加依赖地租的收入,他们成了佃户们眼里要最后一颗谷的“催命鬼”。由是观之,与其说中国乡土社会的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毋宁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机器大工业的进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乡土经济结构以及城乡关系,进而引发了乡土危机。在乡土社会中,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民的开支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礼仪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农民的开支中最严峻的一种是最后一种。如果人们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2]因此,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制度,尤其是租佃制度。如何扭转土地分配方式、优化土地制度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
(三)阶级关系
土地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或者说是社会关系问题。费孝通认为,土地问题的合理解决不仅需要土地权的重新分配,也需要减少寄生在土地上的一部分人,即为地主阶层寻找另一经济基础。在乡土社会,地主这一阶层是寄生在农民身上的剥削者,他们已经侥幸地被供养了几千年。乡土工业衰落前,农民支付地租、利息后的剩余和手工业收入共同勉强维持基本生活,农民虽然怨恨地主阶层,但温饱的生活使他们安稳下来。由于乡土工业的衰落,单纯依靠土地的生产并不能同时养活地主和佃户,而地主阶层又不断消费西方舶来品,他们更加依赖农民地租和利息的供奉,不断加重对农民的剥削,导致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空前激化。因此,解决中国土地问题迫在眉睫。就中国的人地比例而言,需要重新分配土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秩序。然而,在这期间必须要给地主阶层一个新的经济出路以避免土地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暴力因素。费孝通认为,中国地主阶层的合理出路只有“放弃农业,开拓工业”,放弃阶级特权,放弃地租,转变阶级角色,即从寄生阶层变为服务阶层,构建城乡之间、农民地主之间相辅相助的经济配合体。
三 重建乡土工业
费孝通认为,要想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必须重整乡土工业,发展乡土工业本土化,建立合作性的乡土工业,进而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最终达到社会重组的目的。
(一)乡土工业本土化
中国传统乡土工业有家庭工业和作坊工业两种形式。家庭工业是最原始的乡土工业组织,是以农业里的剩余劳动为基础,农民在农闲时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以自产自销、随制随卖形式为主。乡村的作坊工业是以农业里积累下来的资本为基础进行工业投资,进而产生作坊工业。作坊工业是需要特殊设备、雇用技术工人的工业,例如造纸、榨油、烧窑等。但是此种工业需要大量资本,只能由有权势的人来从事,普通农民只能望而却步。但无论是组织分散和制造单位过小的家庭工业,或是托庇在权势之下依靠垄断获利的作坊工业,都难以充分利用无生动力增进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收入。所以,费孝通指出,乡土工业本土化应该是新的,是合作性质的。具体来说,它有如下的特点:第一,一个农家可以不放弃他们的农业而参加工业;第二,地点分散在乡村里或乡村附近;第三,这种工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参加这一工业的农民的,所以应当是合作性质的;第四,这种工业的原料主要是由农民自己供给的;第五,最主要的是这种工业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广地分配给农民。可以看出,费孝通期待一种乡土性的现代工业的建立——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建立合作性的乡土工业并成立服务工厂。
(二)社会重组
乡村工业的改造转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改进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重组”(social reorganization)的过程。重组中国乡土工业不仅需要在技术上有所革新,例如蒸汽动力和电力代替人畜动力,同时这种新技术必须配合到人民的需要里,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使新动力和新技术推动乡土工业本土化的发展。另外,中国乡土工业的转化这一“社会重组”过程不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式,而应建立在农民们“合作”的原则和基础上,以使经济发展惠及最普通的广大农民,并形成农民的资本积累。[3]费孝通认为,要使农村经济复兴,其根本纲领是保证每个人能得到不饥不寒的水准,同时也要保证这水准上的剩余能量储蓄起来有效地积聚和利用并成为资本。因此,农民的资本积累也是社会重组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主张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和理性分析而得出的。如果把这一主张放置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
四 《乡土重建》的当代意义
时至今日,《乡土重建》一书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新时期的城镇化战略、新农村建设,而且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也具有示范价值。
(一)对当前城镇化战略的启示
费孝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深入研究中国乡村,把乡村置于中国城乡区域发展的框架下进行研究。事实上,在费孝通的基本思路中,一直潜存着“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他多次使用“城乡发展”“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等词语,强调城乡平等协调的互助发展模式。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他期盼中国城乡间能够从刚性机械的循环关系转变为弹性有机的经济互助模式。
与《乡土重建》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农村社会相比,当前我国农村的主要问题也许不是农民无法满足“不饥不寒的水准”的问题,也不是农民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问题,因为农民的“吃饭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党和国家尚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基层社会秩序。不过,两个时期的重要相似之处是,城市高度依赖农村,而且这种依赖建立在低成本运行的基础之上。相比之下,20世纪初,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主要是汲取农产品和租佃收入;而当前城乡社会流动背景下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二者均存在城市对农村的隐性剥夺。从未来的趋势上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仍将以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为重要支撑,如此一来,农村、农民、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地位或将长期持续。从长远来看,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城乡如何相得益彰、互助循环的问题。
当前,我国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倡导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但反观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处在一个“大跃进”的态势,表现在:城镇化速度虚高,特别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化”变成了“高楼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水平及就业岗位增加不能适应此冒进式的城镇化,城镇化内涵不足;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和补给不足,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巨大;等等。
费孝通曾撰文指出,发展城镇化还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遍地开花的道路。以沿海的上海、香港、北京、天津和内地的重庆为重点发展大都会;以200万到500万人规模的大中城市为主体,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以星罗棋布的几万个几千人到几万人上下的小城镇和几十万人上下的小城市为依托,承载下一步农业产业化进一步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工业化的浪潮,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4]这些早在1998年提出的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思考和研究城镇化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真借鉴。可以说,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决不能以脱离农业、牺牲农村、损害农民为代价,盲目追求城镇化,而是要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农民变成工人、农田变成高楼的过程,而是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它既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优化,也应是城乡人文方面的协调发展。
(二)对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启示
在《乡土工业的新形式》一文中,对于发展乡土工业,费孝通更看重乡土工业的组织形式,而不仅是技术本身。“技术的改进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须的条件,一个社会的生活程度最后也决定在生产力,但是单就技术上求改进却并不一定能提高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因为这里还包含着一个分配的问题,那就是,从新技术中所增加的生产结果不一定能分给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5]费孝通进一步强调,“我们如果要复兴乡土工业,在组织上不能不运用新的形式。”开弦弓村的蚕丝业改革是费孝通对此问题的思考与试验,并且提供了一个以合作原则组织乡土工业的案例,并希望农家自行组织合作社来管理发展农村实业,这对当今新农村建设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中国城乡社会流动频繁,农村的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社会治理任务冗杂。比如,农村社会治理体制不完善,社会保障不健全,教育发展滞后,农民的组织与合作总体上处在衰弱或涣散的状态,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一些村落形成“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人口格局,农村社会习俗与自组织能力可能面临进一步衰落。这些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创新农村社会服务机制,发展基层社会组织,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不足。对于发展农民合作、建设农村社会组织,我们似乎应该回到费孝通早期对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路径上,从国际背景、城乡关系、阶层结构等方面分析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源。
(三)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启示
在《乡土重建》等著作中,费孝通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工业本土化道路——将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改造为工农结合、城乡协调发展的农村,进而实现乡土重建与社会重组。费孝通巧妙地将先进的工业文明与传统乡村社会内部的动力结合起来,实现了对中国基层经济社会性质的准确定位。这种思考方式与研究路径,堪称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早期典范。
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6]在我们看来,社会学本土化不是高喊本土化的口号而没有实际作为,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制造一堆概念,也不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摒弃西方理论,固步自封地炒作已有的本土概念,而是在充分消化已有理论成果和充分研究国情的过程中,建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社会科学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学本土化的“真意”在于:一是充分理解和消化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是培养社会学意识的前提。二是立足中国现实,将社会学研究建立在对社会的充分了解之上,并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三是在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反思西方理论的限度并努力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重新审视费孝通包括《乡土重建》在内的早期研究成果,我们或许能够更冷静平和地思考“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14-415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237页。
[3]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1994年第10期。
[4]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5]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第447页。
[6]郑杭生:《社会学本土化及其在中国的表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秀秀
C91
A
1006-0138(2015)02-01234-05
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资助课题“‘燕京学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对新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启示”(YETP0976)
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北京市,100081;张璐,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北京市,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