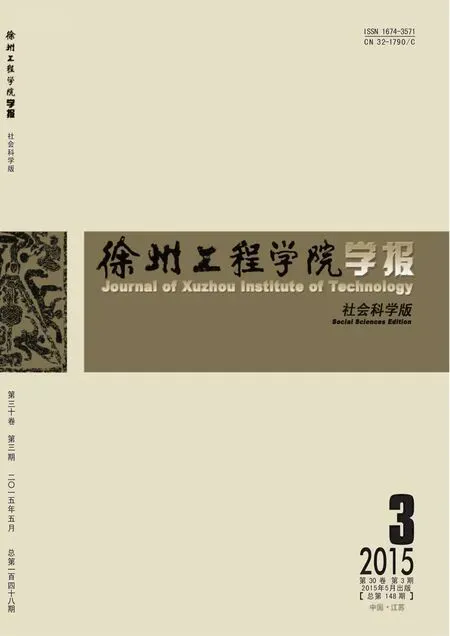尊孔而抑孟——杨文会居士的《论语发隐》与《孟子发隐》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 215123)
尊孔而抑孟
——杨文会居士的《论语发隐》与《孟子发隐》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215123)
摘要:晚清杨文会居士著有《论语发隐》与《孟子发隐》二书,使儒家经典中深隐之义在佛理的映照下得以充分开显和发露。从《论语发隐》来看,杨文会对于孔子,服膺其究竟,感佩其慈悲,赞叹其契机,称扬其善巧,作为佛教的一名大居士,他对孔子的这种尊崇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所无法比拟的。与《论语发隐》对孔子极度推崇不同,《孟子发隐》对孟子则颇多贬抑之处。杨文会不满于孟子处,在其以赤子之心言性,以仁义与利为对立,错会古人意旨,有失慈悲等。杨文会尊孔而抑孟的原因,是由孔子与孟子的思想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决定的,也是出于反击理学家辟佛的需要,同时也使他可以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基督教进行一定程度的批驳。
关键词:杨文会;《论语发隐》;《孟子发隐》
自明代以来,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多有以佛释儒者,如憨山德清之作《大学直指》、《中庸直指》,蕅益智旭之著《四书禅解》、《周易禅解》等,皆为巨作。至晚清,著名居士杨文会著有《论语发隐》与《孟子发隐》二书,亦为名篇。
杨文会居士(1837—1911),号仁山,安徽石埭人。自幼读书,不喜科举,同治三年(1864)因病休养,接触《起信》、《楞严》等,由是信佛。同治五年(1866),倡立金陵刻经处,募款重刻方册藏经,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契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于刻经处设祇洹精舍,招收太虚等僧俗学生十余人,开启近代僧教育的先河。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十宗略说》一卷,《阴符》、《道德》、《庄》、《列》、《论语》、《孟子》发隐各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观经略论》一卷,《阐教编》一卷,金陵刻经处编印为《杨仁山居士遗著》。今人周继旨点校、增辑为《杨仁山全集》,收入“安徽古籍丛书”。杨文会自谓“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但他在教学中兼顾诸宗,规模广阔,鼓励学生深入余宗,开一代新风,影响深远。
“发隐”者,发露其深隐之奥义也。儒者读儒书,习为滑熟,安于惯常,使其奥义深隐而难显。而佛教学者读之,使儒家经典处于佛教思想的语境中,与佛教义理相互映照,则其高下、是非、曲直、长短粲然毕现,无所隐伏,故可称之为“发隐”。《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为杨文会所论者不过寥寥数十则而已,显非完璧。编者在二书《发隐》之末加按语云:“《论语》、《孟子》二书,先生欲加阐发,各章均于原书加以标识,未遑属稿,间有批于原书上幅者,实其少分。兹为撮录如上,盖皆未竟之稿也。”[1]212如此可知杨文会有愿未果,赍志而没,《杨仁山全集》之五《论语发隐》、之六《孟子发隐》二书实为部分遗稿,管中窥豹,赖此一斑,吉光片羽,尤足珍贵。
一、对孔子的尊崇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古有“素王”(无冕之王)之称,无论朝野,历代均奉之为“大成至圣先师”。佛教传自印度,东来中土,虽不以儒学为至极之论,但亦许其为应世化导之谈,卫国护家之具。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儒家的攀缘依附,就成为佛教得以立足中土的契机。从《论语发隐》来看,杨文会对于孔子,服膺其究竟,感佩其慈悲,赞叹其契机,称扬其善巧,作为佛教的一名大居士,他对孔子的这种尊崇可以说是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所无法比拟的。
其一,服膺其究竟。杨文会认为,孔子与佛毫无二致,并皆究竟至极。他读《论语》至“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一章,“合掌高声唱曰:南无大空王如来!”在他看来,孔子与佛“设有二致,则佛不得为三界尊,孔子不得为万世师矣”。他认为在《论语》一书中,只有这一章充分展现了孔子的“全体大用”。孔子所说的“无知”,就是佛教“根本无分别智”所显示的“真空”实相,为一切有情生命及无情木石等的本然之体。即便是对所谓的“鄙夫”,孔子也以这最高深的真空之理教导他:“鄙夫”无非执著于“有无、一异、俱不俱、常无常”等两端之法,孔子“先以有知纵之,次以无知夺之”,“叩其两端,而竭其妄知,则鄙夫当体空空,与孔子之无知何以异哉?”[1]194孔子自己已经具备“无知”之真知,又能使素质最为低下的“鄙夫”也达到“空空如也”之境地,如此则可知孔子无论是自行还是化他,并皆臻于究竟至极之域。他解释“曾子有疾”章云:“菩萨现身人道,欲护持在家律仪,毫无违犯,难之又难也。曾子冰渊自懔,至临终时,方知得免。若据此章,便谓儒家修己局于一生,死后无事,亦浅之乎测纯儒矣。”[1]193这一方面表明,在杨文会的心目之中,曾子等儒家学者都是“现身人道”的“菩萨”,这自然是一种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杨文会看来,“临终知免”意味着曾子已经知晓“此生冰渊自懔至临终、来生得免三恶道苦”,故而他认为纯儒的修己工夫绝非局限于一生之中,而是能通向究竟终极的。他解释“克己复礼为仁”章云:“己者,七识我执也。礼者,平等性智也。仁者,性净本觉也。转七识为平等性智,则天下无不平等,而归于性净本觉矣。盖仁之体,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只因七识染污意,起俱生、分别我执,于无障暗中,妄见种种障暗。若破我执,自复平等之礼,便见天下人无不同仁。”[1]196在这里,杨文会将孔子的“克己复礼”直接等同于佛教的转识成智了。
其二,感佩其慈悲。慈能与众生乐,悲能拔众生苦,有无慈悲之心是佛教区分为大小乘的基准,杨文会正是以中国流行的以自利利他为职志的大乘佛教来衡量孔子的。在杨文会看来,孔子自既究竟于“空空如也”之境,却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汲汲于列国之间,惶惶不可终日,这正表明孔子慈悲心重,利他心切,绝非那种耽空滞寂的自了汉。杨文会解释“樊迟请学稼”章云:“樊迟见得世无可为,遂欲高蹈弃世,作独善之计。然有不敢自决,故请学稼。孔子以旁机答之。复不甘心,又请学圃。孔子仍以旁机答之。樊迟心折而出矣。孔子以小人斥之者,斥其舍离兼善之心也。孔子行菩萨道,不许门人退入二乘,其慈悲行愿有如此者。”[1]197对此章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尊孔子者谓孔子教导弟子应胸怀致君舜尧、安民衽席之大志,贬孔子者以之为孔子轻视农业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佐证,然皆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而杨文会此释则首尾融贯,前后一致,既无心驰外骛之弊,又无轻稼贱农之难,而孔子利他惠人之心卒不可掩,不意孔子于两千多年后于佛教营垒中得此解人。杨文会释“知其不可而为之”云:“形容孔子,至此言而尽矣。胡氏谓晨门以是讥孔子,不但不知晨门,亦并不知孔子。盖孔子不论可不可,但尽其在我而已。”[1]198孔子不是功利主义者,故他虽知世不可为,但仍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不息,当时人以此语评价之,赞欤?非欤?其谁知之!而杨文会谓此语乃是对孔子最好的称颂,也是对那种不计成败利钝而竭力以从事的赞扬;实际上,这也是杨文会的自我期许,他刻印佛经,作育僧才,有谁保其必定成功呢!所以杨文会认为“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赞叹孔子“有心哉!击罄乎”正是“孔子之知音”,不过其“斯已而已矣,深则揭,浅则厉”的建言却有“以自了汉期孔子,实未知孔子之用心”的弊病,而孔子志存济世,故而能“轻小果而不为”[1]198-199,此其所以为孔子也。
其三,服膺其契机。孔子自既究竟,而又心怀慈悲,志存匡济,故而能倒驾慈航,回入娑婆,广收门徒,大施化导,其因材施教,即佛教所谓的“契理契机”,其运用之妙,深为杨文会所赞叹。孔子尝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杨文会说:“《维摩经》中,三十二菩萨,皆以对法显不二法门。《六祖坛经》,以三十六对禅宗妙义。子贡闻一知二者,即从对法上知一贯之旨也。若颜子闻一知十者,乃证《华严》法门也。经中凡举一法,即具十门,重重无尽,名为圆融法界。子贡能知颜子造诣之深,复能自知修道分齐,故孔子印其弗如而与之也。”[1]191-192杨文会的这一番解说含义极其丰富,世俗或以谓子贡闻一知二为《维摩》不二法门,颜子闻一知十即《华严》圆融法界,可称得上是惊天之语,旷世之见,实则以佛理说儒经,乃是将两种标准进行对接,使两种语境实现相互转换,自然如此,无多奇特;而孔子印成子贡之说,一者可见得子贡有自知之明,二者正表明孔子深知二位贤弟子之根机不同,各有所宜,而非有意于厚彼颜回而薄此子贡也,此言之深契子贡、颜回之机,可知也。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夫!”杨文会以为,“意、必、固、我,四者皆无,故用行舍藏,无可不可。孔子独许颜子,非他人所能也”[1]192。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理有固然也;知颜子之能,亦知他人之不能,是孔子自有知人之明也;故孔子此言,颇为契理契机。
其四,称扬其善巧。孔子因材施教,自佛教观之,也是一种说法善巧。《论语》谓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注者多以此谓孔子之仁心及于禽鱼,而杨文会却从中体会到了孔子的教学之道:“时人有设网与射宿者,孔子辄止之,钓与弋则未尝禁也。门下士因悟孔子接引学徒之方,遂记此二言。观陈亢问伯鱼一章,便可知矣。一部《论语》中,弋钓之机,时时有之。乃至古今圣贤,莫不如是。禅门所谓垂钓看箭,亦此意也。近世以传教为务者,则设网射宿矣。”[1]192-193钓为愿者上钩,弋为有发必中。儒家教学,历来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主张“师如钟,叩则鸣,不叩则不鸣”,非常重视学生求学的主观意愿和主动自觉,这种思想对中国佛教师资传授自然也会发生重大影响;而网则为迫其就范,射宿则为乘其不备,事涉强行灌输,为儒家所不取,中国佛教的“佛不度无缘之人”与之尤相抵牾;如此则师资授受及其效果必完全依赖于人格感召与说法善巧。如季路问事鬼神与事死,而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杨文会理解为:“子路就远处问,孔子就当处答,大似禅机。盖子路忿世俗以欺诈事人,问其事鬼神亦容得欺诈否?孔子答以既不能事人,亦不能事鬼。子路又问此等人死后如何?孔子答以生不成为生,死亦不成为死。复次子路问事鬼神,意谓幽冥之道,与人世有别也。孔子答意,能尽事人之道,则与事鬼神无别也。又问死意,谓死后无迹可寻,一真灵性向何处去?孔子答意,当知生时灵性何在,便知死后不异生时也。”[1]195在杨文会看来,孔子之答,语含多义,而能使威武昂扬之子路心折口服,其说法可谓善巧。
很显然,杨文会的《论语发隐》对孔子进行了佛陀化的改造,使这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具有了佛祖的背光。《论语发隐》仅涉及孔子语录29则,约相当于原文的十五分之一,然而从这些极为有限的解释中,我们确可以窥见他对孔子所怀有的无比崇敬的心情,了解他要在佛教的语境中开显孔子的究竟、慈悲、契机与善巧的解释原则。所以这短短的29则发隐,实具有整部《论语》发隐之发凡创例的功能。
二、对孟子的贬抑
与《论语发隐》极度推崇孔子不同,《孟子发隐》对孟子则颇多贬抑之处。《孟子发隐》序云:“《孟子》全生宗旨,曰仁义,曰性善,立意甚佳,但见道未彻。其所言性,专认后天,而未达先天。以赤子之心为至善,殊不知赤子正在无明窟宅之中。其长大时,一切妄念皆从种子识内发出。所说仁义,亦以情量限之,谓与利为反对之事,以致游说诸王,皆不能入。若说仁义为利国之大端,而说仁义当以利国为首务,则诸王中或有信而乐从者矣。”[1]203也就是说,杨文会不满于孟子处,在孟子以赤子之心言性,以仁义与利为对立,而在正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杨文会对孟子经常错会古人意旨、持心有失慈悲的批评。
作为服膺华严宗义理的佛教大居士,杨文会所肯定的人性应是那个“空空如也”而又“十法具足”、“重重无尽”的“一真灵性”,因此认为孟子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以明人性本善的论证不够究竟。告子以杞柳喻人性,孟子驳之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贼人以为仁义与?”杨文会认为,“告子不知自性本空,故以杞柳为喻。孟子以戕贼破之,仅破其妄计,而未显其本愿也”[1]208。这是说孟子破斥告子的杞柳之喻,仅破斥告子以无为有的虚妄计执,而未能开显人性的究极之义。告子又以湍水为喻,孟子以“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破之,杨文会指出:“告子又认随物流转者为性,是知有妄缘,而不知有真常也。孟子立性善为宗,就先天说则可,而孟子专指后天说,故非真能立,亦非真能破。且以搏跃激行喻人之为不善,试问普天下苍生,不搏不激其能人人向善乎?”[1]209意谓孟子虽知随物流转者非人之本性,无乃所论仅局于后天行为的自然趋向,立宗不彻,故破亦乏力。告子又以“生之为性”为说,而孟子以“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反诘之。杨文会主张“性本无生”,故不赞同告子的“以生为性”,但他认为孟子“就生字上判犬牛与人性有差别,是以随业受生之识为性,岂知六道智愚,虽判若天渊,而本原之性未尝异也”[1]209。孟子所说的“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杨文会所说的“性”,是“六道愚智”共同的“本原”,在此凸显了儒佛论性之差异。告子接着以“食色性也,仁内义外”立宗,孟子以“耆炙亦有外乎”反诘,主“仁义皆内”之论,杨文会对孟子此论却颇赞成,“食色牵引妄识,认作自性,故有仁内义外之执,孟子所辩,根于内心,是为得之”[1]210。也就是说,杨文会虽认为孟子论性不够究竟,但较之于告子,则还是颇有见地的。由此可见,杨文会之著《孟子发隐》,实际上还具有一种融摄《孟子》之不究竟而使归之于佛教之终极的意味。
中国佛教以自利利他为职志,并不否定个人追求世俗利益的正当性,而是主张通过利他之行实现利己效益的最大化,故而杨文会对孟子在游说梁惠王时将“仁义”与“利”对立起来的思想极其不满。他对此评价说:“利者,害之反也。王曰何以利吾国,是公利,非私利也。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则专指聚敛矣,与梁王问意不合,故非真能破。《告子》下篇,宋牼欲罢兵,将言其不利,孟子以去仁义怀利斥之。可见孟子以利与仁义决非并行,亦不合孔子之道。观乎‘子适卫’一章,先言富而后言教,又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亦以富强与信交相为用。至必不得已之时,方去兵去食而留信。未有专言信,而概废兵与食也。”杨文会之意,应严格区分公利与私利,私利固不能与仁义并行,但谋求公利却正是仁义之所在;梁王欲利国,宋牼欲罢兵,所追求的都是公利,非聚敛者比,而孟子责备他们去仁义而言利,自然不能使梁王与宋牼心折口服,而孟子所追求的仁义,亦将因陈义过高而无法实现。孟子对郑国执政子产以己之乘舆济人溱洧不满,认为是子产不善为政的表现。而杨文会认为,子产以己之乘舆济人溱洧不过偶一为之,“孟子好责人,于此可见”[1]204。好责于人则人难与之为善矣。孟子尝以五谷不熟不如荑稗,提出“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杨文会认为:“此喻不洽。盖为仁无论熟不熟,总胜他道。不知孟子心中以何为仁耶?”[1]211孟子责人过苛,不免使人对他心目中的仁义发生疑惑。
历来论学,皆以孟子善言《诗》、《书》,而杨文会却列举了孟子多处错会古人意旨的地方。如,孟子以“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为周公使管叔监殷而畔开脱责任,杨文会对此颇不以为然:“以弟兄二字,为周公文过,实不足以折人心。盖周公以刚健正直之心,行大公无我之事,岂有私情萦怀,而行赏罚于其间乎?”[1]204在杨文会看来,孟子的“弟兄”之解,不免陷周公于私情,实为厚诬古人。孟子以孔子赞水乃为其“有本”,并得出“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观念来。杨文会则认为,“仲尼之叹水,勿论其有本无本也。观其重叹,乃叹其性德耳。水性常清,虽泥混之使浊,而清性不改。水性常静,虽风鼓之使动,而静性不改。恰似人之本性,是以仲尼亟称之也”[1]205。仲尼之称于水,且与水而俱逝,其意旨究何在,谁能知之?孟子之解释固然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即便是杨文会之解释,又岂能真合孔子之意旨乎?对于瞽叟、象与舜的故事,孟子有一番说辞,重点在突出舜的“孝悌”。杨文会认为:“大圣应现,非凡所测。完廪浚井,皆以神通得出。瞽叟与象,均是大权菩萨,成全舜之盛德。孟子所解,全无交涉。”[1]205此解近乎《法华经》的“开权显实”,难怪他会指责孟子“以世俗之情而观古圣”,并且想象出“帝舜在天之灵,当发一笑”的情景来[1]207,可谓是浮想联翩,意兴畅然,充分显示出佛教的思想观念在他理解儒家经典时作为前解读结构的重大作用。
孟子之为人,鹰扬伟烈,意气风发,若泰山之岩岩,高自位置而不屑于群小之琐琐,在杨文会看来,这与菩萨不舍众生、与物为缘的慈悲精神颇不相合。孟子曾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焉?于禽兽又何难焉?”孟子强调的是君子若能尽其在己,即便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只要问心无愧,自当处之泰然,不必为此而戚然不安。杨文会不同意孟子的这种态度,他对此评价说:“菩萨见此等人,益加怜悯。孟子乃以轻慢之心视之,去圣道远矣。”[1]205杨文会重视的是菩萨应具有怜悯一切惑苦炽然的众生而尽皆普度之的慈悲之心,思想家与宗教家不同的思想情感取向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较之于《论语发隐》,《孟子发隐》的分量更少,疏解所及,不到《孟子》原文的百分之一,但已足以使人窥见杨文会对《孟子》所持的基本态度:与而为论,孟子固然是学孔子者,是人伦道德的扶持者;夺而为论,则孟子尚未达于究竟、善巧、慈悲之地,于杨文会心目中的佛陀化了的孔子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敢于腹非儒家的“亚圣”,这对于与洋务派和维新党人都有广泛接触的杨文会来讲多少都有些思想解放的意味,也表明他所致力振兴的佛教此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对话并对之造成冲击的能力。
三、尊孔抑孟的成因
在儒家语境中,孔子“至圣”,孟子“亚圣”,“孔孟”连称,由来已久。而《论语》、《孟子》二书作为儒家要籍,入宋之后,跻身四书之列,地位和影响或在五经之上。因此,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对此二书进行解释和论述,是通过会通儒佛宣扬佛教思想的极好方式。而杨文会却认为孔子足以媲美于佛陀,而以孟子实难继武于孔子,杨文会对孔孟的评价何以如此轩轾呢?溯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者这是由孔子与孟子的思想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决定的。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弟子后学结集的《论语》一书之中,往往都是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具体问题有感而发的睿智的议论和劝诫,生动体现了孔子胸怀的坦荡、人格的纯粹和思想的平实,并没有多少理论的发挥和建构,如罕言利,不语怪、力、乱、神,祭如在,以至于弟子如子贡都未曾得闻其言性与天道,这就很难与佛教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发生直接的理论冲突,为后世的佛教学者按照自家的理解和需要改造孔子形象预留了思想空间。孟子则不然。孟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一书中。与《论语》中都是孔子的简洁平实的告诫不同,《孟子》中的文章不仅充分展示了孟子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滔滔雄辩和“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而且还深入探讨人的本性问题,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所在,这就很容易与以佛性论为义理重心的中国佛教发生对抗:排佛的儒家学者固然可以据此攻讦佛教不知人禽之辨,而佛教中的护教大德也往往以此讥讽儒家只以后天为性。也就是说,孔子可以为佛教利用和改造,而孟子则无此余地。随着儒家的官学化,孔子逐渐被历代王朝推尊为“万世师表”、“达成至圣先师”,与“天地君亲”一起享受全社会最高规格的崇敬和祭祀。孟子虽然也被尊为“亚圣”,但其地位不仅无法上侔于孔子,甚至尚在颜回(“复圣”)、曾子(“宗圣”)与子思(“述圣”)之下,而且由于孟子具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及“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寇仇”的民本思想,触犯了历代专制君主之所大忌,以至于明太祖朱元璋曾一度想废除孟子的庙祀及配享孔庙的资格。这就是说,既然孟子之圣远不及孔子,历代王朝对孟子的推崇也远逊于孔子,那么,作为佛教居士的杨文会在推尊孔子的光环之下对孟子小有非议,为佛教义理争取空间,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中,都成为一件可以被容忍的事情了。
二者出于反击理学家辟佛的需要。孔子之时,虽然已经是礼崩乐坏,但形式上周天子还是统治的权威、秩序的象征,孔子初办私学,百家尚未兴起,故而无争鸣之事。而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战国时期,将当时流行的杨墨之说譬为洪水猛兽,故而以“我善知言”自矜,以“辟杨墨,拒邪说”自任,认为杨朱“为我”与墨翟“兼爱”为“无父无君”的“禽兽”之行。孟子的勇毅和言论为后来儒家学者的排佛提供了榜样和理据,韩愈据此认为孟子足以“配禹”,以其“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比之于孟子:“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既亡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且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2]215入宋以后,《孟子》的地位更加崇高,与《周易》、《论语》等一起成为宋儒创建理学的主要经典依据,对孟子的疏解自然会激发理学家排佛的豪情壮志。朱子注解《孟子》至“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引程子之言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盖杨氏为我疑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止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所以为害尤甚。”[3]272-273这可以说是理学家们据《孟子》反佛的代表性言论。王阳明也以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攻击佛教,他认为佛教讲的“本来面目”,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儒家所说的“随物而格”,就是佛教讲的“常惺惺”,二者本来极其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4]178。杨文会的时代,理学仍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仍然有许多儒生以辟佛为己任,如稍后于杨文会的印光法师、谛闲法师等人,在出家前都曾撰文辟佛,就更别说一般士大夫了。杨文会若与此等人深辩,则辩不胜辩,难免会劳而无功,他为《孟子》发隐,阐明孟子论性的不够究竟、彻底,此对于反击历史上盛行的和社会上流行的排佛之论,无疑具有拔本塞源的巨大功效。
三者杨文会的抑孟使他可以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基督教进行一定程度的批驳。17、18世纪,耶稣会士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在当时为了克服中西两种文明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基督教(天主教)得以立足中国,利玛窦等人采取了“补儒易佛”之策,即希望以基督教取代佛教而对儒家思想形成必要的补充,为此他们利用“索隐法”(“以神秘主义的态度,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上帝的原始启示和弥赛亚救主形象”)和“考证法”(“以实证主义的态度考察中国上古史,并试图证明中国历史与《圣经》历史的吻合”),“19世纪,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来华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们仍然面临者如何协调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继承并深化了耶稣会士的作法”[5]17。当然了,无论是“索隐法”还是“考证法”,其共同目的都在于以儒家经典证明基督教义在中国传播的合理性,在儒家经典之中寻求存在于中国的合法性,孟子所屡屡言及的那个“天”,自然就成为基督教传教士们论证中国早就知道有上帝、造就已经信仰上帝的极好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对孟子天论的批驳,不知不觉间就具有了佛教与基督教进行思想斗争的一种方式。如孟子尝谓舜之有天下,非尧与之,乃天与之。杨文会对此评论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此善于言天者也。孟子言天,迹涉有为,是高于天下一等耳。西教盛行,当以孟子为证据也。”[1]207孟子认为禅让之“与贤”及世袭之“与子”,皆由天定。杨文会对此深致不满:“与贤与子,皆天主之。后世与暴与虐,亦天主之。天既能主,何不尽弃暴虐而与圣贤?则永远天平,不见乱世矣。”[1]208孟子以尧舜之子不肖而禹之子贤“皆天也”,杨文会反诘之曰:“以子之贤不肖,均归于天。不解天何薄于此而厚于彼耶?”[1]208我们说,杨文会的指责,是孟子所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也是基督教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文会.杨仁山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0.
[2]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王守仁.传习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5]姚兴富.儒对话与融合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孔凡涛)
Respecting Confucius While Suppressing Menciu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ang Wenhui's Books ofOnAnalects
ofConfuciusandOnMencius
HAN Huan-zhong
(Religious Institute,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China)
Abstract:Yang Wenhui, a Buddhist disciple in late Qing Dynasty,wrote two books of O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On Mencius, which exposed and interpreted the implicit meaning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light of Buddhism theory.In the book of On Analects of Confucius,Yang Wenhui respected Confucius so much that his admiration surpassed any other Buddhists in the history.However,on the contrary to his respect to Confucius,Yang Wenhui had many dissatisfactions to Mencius in the perspectives like Mencius defined human nature by the innocent heart of children,caus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s,misunderstood ancient books and lack of mercy etc.The reasons why Yang Wenhui admired Confucius and dissatisfied with Mencius lay in not only the different ideological characters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but also out of the needs of counterattack to Confucius' critics and therefore,to refute Christianity to a certain degree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Buddhism.
Key words:Yang Wenhui; On Analects of Confucius; On Mencius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3-0020-06
作者简介:韩焕忠(1970- ),男,山东曹县人,苏州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佛教四书学研究”(13FZJ001)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