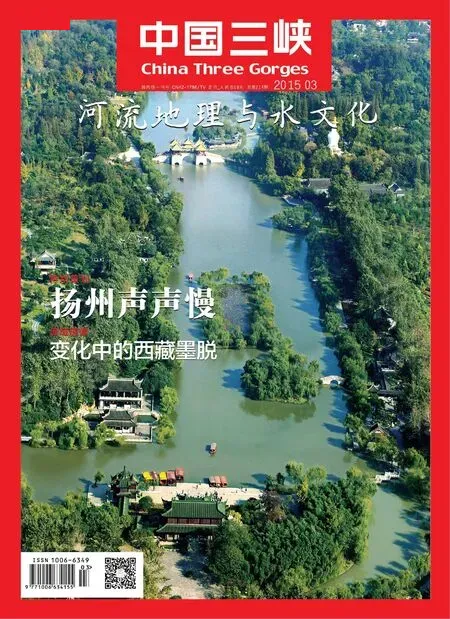扬州诉话
扬州诉话
一把扇,无舞台,不化妆,无布景和音响,只需一袭长袍。一把折扇,一只醒堂木,一个人站台上,历史风云、江湖恩怨就在抑扬顿挫的扬州方言中娓娓道来。去扬州重宁寺,不为瞻仰“江南诸寺之冠”的百年名刹风采,而是去扬州曲艺团见见平时只在古装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扬州说书人。
才走进寺门,咿咿呀呀的女子唱腔和嘈嘈切切的琵琶声让人寻声望人。空旷的房间内,七八个年轻的女孩正抱着琵琶边弹边唱,歌声和琵琶声让屋中儿女情长绕梁——扬州戏曲评弹并称,评话说的是英雄气盛,弹词唱的是儿女情长。

照片墙可以助人了解扬州评话的历史。在“昨夜星辰”分组中,排行第一个是王少堂的相片。“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早就听过这句话,今日第一次见到评话宗师王少堂,不由仔细打量。一袭灰布长袍,张手甩开一把折扇,这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很符合我对评话艺人的想象。
正当我准备穿越到王先生说书的书场听一场《武松打虎》时,有人拍了我的肩膀。回头一看,那是一位穿牛仔裤,手持iPhone的帅小伙,感觉脸熟,但又不知在哪儿见过。小伙子看出了我的迷惑,指了指相片墙,原来在“今日新星”分组中,他排行第一个,是青年艺人马伟。
马伟介绍,扬州评话起源于明末清初,《柳敬亭传》中所写的说书先生柳敬亭是扬州说书艺人公认的祖师爷。扬州评话兴起之后,开始在江苏、上海、安徽等地流传,到上世纪中期出了扬州评话史上宗师级人物王少堂,扬州评话发展到巅峰。如今的扬州评话,退守到扬州,重出扬州是王派第4代传承人现阶段的目标。
1997年,马伟决定报考扬州曲艺团。专业的评话艺人,演艺太苦,更重要的是当时是扬州评话最低潮的时期。之前在扬州曲艺之友社,他把说书当爱好,评话对他来说是新奇的,花几天功夫背一个小段子,模仿说书艺人的动作摆几个造型就会博得满堂喝彩。然而,到扬州曲艺团后,说书就不再是一种兴起而说、兴败下台的爱好,变成了一门需要精益求精的艺术,更成为了坚守的事业。
做专业评书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背书。王派说书人的根基是《水浒传》。一部《水浒传》被王少堂按人物故事编成了《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四个“十回书”,每个王派说书人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左:慕名而来的外宾通过翻译的讲解观看评话表演。

右:扬州评话在表演时,根据剧情的不同,表演者会表现出各种夸张的表情和动作。
那时学艺不像现在用录音笔记,用摄像机录,师傅不允许用一点辅助手段,必须口传心授。学艺的过程,徒弟痛苦,师傅也难受。但是这样的记忆,一旦记住了,想忘也忘不掉。就像现在打字打多了,就不用看键盘,可以盲打了。评话艺人站在书场里,是没有时间想台词的,必须张口就来。
马伟背完四个“十回书”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进入学艺的第二阶段——表演,用身体去演示出书中的情景。当表演得惟妙惟肖后再进入第三阶段——把二者重叠起来。
没见过王少堂,从没看过他的表演,是马伟最大的遗憾,也是他最大的幸运。遗憾,是因为没能和大师同场竞技,少了提高的机会;幸运,是大师气场太强大,他同时代的说书人都完全被他的气场笼罩,这也算是扬州评话一直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而马伟从没有这个顾虑。
华灯初上,老书客们早已泡好茶在扬州甘泉路书场坐定,他们在等待今晚的评话表演。一个着中山装的青年缓缓走出,手上没拿折扇也没醒堂木登场,说的内容不是英雄豪杰也非江湖恩怨,而是名为朱怀镜的现代人从升迁到最终被“双规”的故事。这是马伟历时三年创作的长达100万字的扬州新评话《国话》中的内容。马伟认为扬州评话应该借鉴海派清口的自由和即兴,他将这部《国话》定位为“新编散打评话”。看来在经历了多年沉浸后,在评话新人身上,扬州评话开始风云再起。
——苏州光裕书场现状调查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