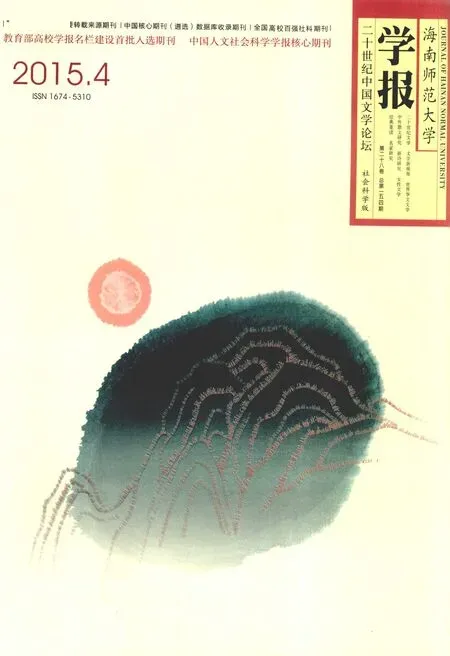发现、阐释与重估
——评李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金 星,杨洪承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发现、阐释与重估
——评李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论》
金 星1,杨洪承2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被相关研究者使用过。①乐华图书公司在1932年就曾专门出版过一套“当代文学读本”丛书。而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郑作民编著)以及1947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胡云翼编著)等书中都曾以单独的章节出现过。以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为时间起点来看,“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1956年由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而它产生的源流最早要追溯到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文。时至今日,我们所通识的“当代文学”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时间上特指1949年建国后迄今的所有文学,在空间上涵盖了大陆文学、港澳台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等几个特定区域的文学。在将近60年的研究史中,“当代文学”无论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都已不再年轻了,然而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却依然不够成熟。这种“不成熟”的背后恰恰反映了其作为一种学科的活力所在。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以及研究范式的革新使得当代文学研究将始终面临着下一轮的“更新”与“重估”,文学史的书写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重构”过程中完成它的主体性塑造。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研究对象也不仅仅局限在教材的编选中,一些个人化的论文解读正蕴含着新的突破点。可以说“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进程是一个“公共视野”和“个人视野”相融合的进程,要研究整个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状况,“个人化”的学术论著以及论文是无法遮蔽的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宗刚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简称《史论》)不仅是一部当代文学研究的“补缺”之作,更是一部“个人化”文学史书写实践的探索之作。在该书中,著者尝试以“现象”、“作品”、“历史”三位一体的方法来突破以往偏重其一的研究范式,尤其是注重在“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观照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对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逐一作出科学的评价与重估,提出了许多富于创新的观点,对当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其中,当代文学史书写新的“景观”意识、“史论结合”的研究路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个人化叙述”是该书最突出的三个亮点。
一、文学史书写的“景观”意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史书写框架的构建延续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模式,以历史分期、作家作品的分类搭建起文学研究的主体框架。这种文学史的书写模式在教材编著中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就当代文学研究的个体而言,如何建构一部个人化的文学史,是每个研究者均要面对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当前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在书写上都难以跳出‘历史文化背景、作家作品简介、代表作文本分析”的模式’”[1],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中,而要突破这样一种文学史书写的局限,不能仅仅依靠教材书写模式的改变,也需要关注“个体”的研究之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在“当代文学”内涵极为深广的前提下,如何构建起一种当代文学书写的“景观”意识,不仅体现着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筛选与把握,更意味着对文学史书写对象的更新与拓展。尤其是在当下文学创作依托新媒介进行传播之时,如何扩大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增添新的研究板块,成为“当代文学史”书写不可忽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史论》一书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尽管它在整体建构上显得尚欠成熟,但却意外地打开了一种文学史书写的新视野。《史论》一书在整体构架上以史实为基,以年代时间为纬,以文学典型现象与作品为经,构建起了一种“点、线、面”结合的立体文学研究景观。
首先,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史论》一书以“十七年文学审美范式研究”、“当代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当代影视与文学互动研究”作为三个主要研究对象。文学史的书写,总是需要放置到一定的“框架”中,然而文学史的书写除了需要对作家作品进行分类把握之外,还需要一种“景观”意识,即如何为种种文学现象设计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框架,从而在这样一种宏观的框架下展开对研究对象的解读与阐释。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突出了文学的“主流”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个人对19世纪欧洲“文学景观”的一种瞭望与俯瞰。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其复杂性与丰富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呈现中国当代文学景观,仍需要相关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就《史论》一书而言,它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没有拘泥于对文学本身的探究,而是将文学现象放置到时代背景中作整体的观照。将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带入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中,不仅反映了著者研究方向的多元化,同时也别具一格地拓展了文学史书写的空间。
其次,在章节安排上,《史论》一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十七年文学审美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探究。著者先从“文化语境”、“审美特征”、“发展脉络”三个方面理清十七年“英雄叙事”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而以作品为基础对其进行了“文学叙事样态”的划分,最后以“个案解读”的方式验证了这种划分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它区别于以往研究中将“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夸大和低估的两极模式,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十七年文学”作出了理性的重估。中篇“当代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研究”主要以“十七年”之后文学的“当代转型”为例,着重从孙犁、郭澄清、刘心武、莫言等几位重要的作家作品出发,探究政治“解冻”前文学创作和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编辑与发表过程作了精细的史实考察。其中在“版本比较研究”、“文学生产内在规律探究”以及“文学经典化与历史化”的综合探究中,不乏对当下文学研究冷热现象的理性反思。下篇“影视与文学互动研究”中,著者不满足于将文学割裂于当代影视之外,将文学研究纳入“新媒介”的范畴,并别开生面地探析了文学与新媒介二者互利共生的文化现象。这种结构的安排不仅表明了作者对文学研究的一种体系化设想,也体现了著者在文学研究中所拥有的开放性视野。
最后,在内容细节上,《史论》一书的研究在一种文学史书写的“景观”意识下展开,对于研究对象的把握与分析不追求宏大的“史诗”叙述,而是从“历史的细节”中力图勾勒出属于一个时代文学的特殊风貌,探寻它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以小中见大的方式将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文学现象一一放置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作详细考察,进而还原出作品从创作、修改到出版的几个主要过程,跳出了以“文本”解读“文本”的片面性,在更为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为作家与作品寻找准确的定位。这是一项极富有史学意义的文学史书写的探索,它不仅反映着作者研究角度选取的别出心裁,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被人忽视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承载着那个时代文学的精神密码。
二、“史论结合”的研究路径
在《史论》一书中,我们不仅能够从篇章安排上看到著者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景观”式的文学史书写构想,亦能从文本的阐释中发现作者在从事文学研究时所持有的严谨心态。这种严谨性表现在对“史实”的充分尊重上,既不标新立异,也不固步自封,而是以“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精神,对文学现象和作品作本真的解读,因而其得出的结论更具“规律性”特征。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著者切实地履行了“以史为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式,其中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关注文学的外部研究,注重对那些影响了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研究,依托作品与时代事件相互印证,最大限度地将文学研究的“审美性”与“历史性”相兼顾。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韦勒克在论述时认为:“流传极广、盛行各处的种种文学研究的方法都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这些对文学外在因素的研究方法,并不限用于研究过去的文学,同样可用于研究今天的文学。”[2]文学的外部研究更多地强调要“回到历史现场”,连接当时的时代情境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分析,也正是因为对作品及文学现象作了历史的还原,文学研究因此多了一份史学的厚重感。
在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中,“发现”与“阐释”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不仅需要研究者透过已知的文学现象回到“历史的现场”,更需要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把握文学与社会以及作家本身的精神联系。在《史论》一书中,著者在对“十七年文学”文本以及历史情境作了“还原式”考察后发现,即便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历史情境下,作家仍然能够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3]48。这一重要精神细节,不仅弥合了“十七年文学”“政治化”与“审美化”之间的精神差距,亦为我们理解政治时代的文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参照。在分析“十七年”“英雄叙事”时,著者更注重对毛泽东“个人魅力型权力”的阐释,并且认为“十七年”间文学创作所面临的种种大环境,正是由于新政权的领导者担心“个人魅力型”社会走向式微而进行的“神话再造”的社会行动。这导致了作家在创作时“英雄情结”的复现,因为其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使得“英雄叙事”风行一时。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的那样:“占主导地位的乌托邦常常是作为某一个人的愿望和幻想首先提出的,只是后来才被合并为更广泛的群体的政治目标。”[4]在中篇“文学作品与现象研究”中,著者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孙犁在1956年后“编辑家”的身份转变与文学“体制化”之间的关系。著者不仅从编辑角度切入谈及了作家孙犁的创作风格对从维熙、铁凝和贾平凹的影响,而且还发现了导致孙犁这一身份转变的具体原因。这为我们理解建国后作家创作与文学体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在谈及孙犁编辑者身份的转变时,尽管著者没有对孙犁编辑的《文艺周刊》作详细考察,但是已经点明了《文艺周刊》对当代文学产生的重要影响。
版本学的运用是《史论》一书的重要特色。“版本学”作为一门中国传统治学方式的分支,虽然在晚清以降颇受诟病,但是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依然显示出它独特的生命力。贾植芳先生曾言:“众所周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目录学和考据学的问题,如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和研究着的同一性质的问题一样,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历史性特点。”[5]关于当代文学的“版本学”研究,金宏宇等人曾就当代文学作品出版、删改修订等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版本学”的研究不是要停留在诸多版本内容的简单堆砌上,而是要从这些“变化”的内容中寻找出关乎历史与个人的原因。在版本学的运用下,作者重新对郭澄清《大刀记》1972年版和1975年版这两个版本作出差异性比较,通过比较来探究郭澄清在个人文艺创作追求的“史诗”品格与政治意识形态“赞歌”形式之间的冲突,发现了作者在删改本中修改了自己的创作契约背后的一些权力纠葛。从这一点勾勒出“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作家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纠正了长期以来我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表象化认知。这种文学研究看似停留在一种简单的版本比照上,但其背后却实际反映了文学与权力之间的较量与纠葛,一部作品的版本史往往会成为一个时代文学与政治、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缩影。因为“守正”故而“创新”,在以史实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中常常能够带来许多出乎意料的学术创新点,而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作品版本问题,至今尚存在诸多未解决的版本问题。洪子诚先生在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曾考虑过“作品年代”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学中的作品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有一些标明是写于五六十年代或‘文革’期间的作品,是80年代以后才发表的。另一种是,当时曾以不同方式‘发表’过,如‘手抄本’,如手稿的相互交换阅读,或在一定场合朗读过。”[6]这些作品创作于何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发表,为何延迟发表,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史论》一书中关于“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班主任》的“经典化”探析一节,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细节。如果将文学生产规律的探索总结为“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那么,对文学传播规律的探索可视作一项研究文学“如何传播”和“怎样经典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著者无疑跳出了文学文本研究的固有空间,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对文学“研究之研究”作出了科学的观照。关于文学经典化的问题,吴义勤认为:“‘经典’的价值是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7]这虽然是基于当下文学如何实现“经典化”的分析,但是却点明了文学作品“经典化”一个不可忽视的“人为”因素,文学始终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它从创作、出版到受众无不与它所在的社会紧密相连。关于这一点,《史论》一书亦有精到的论述。例如在对刘心武作品《班主任》经典化过程的考察中,著者发现:“一些文学作品进入文学史,并不是因为其‘文学性’使然,而是由于它是文学史不可绕过的一个关键点,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潮等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关系,被历史所记忆。”[3]209~210这种文学作品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与其说是其审美性使然,倒不如说是一种“被经典”的历史化过程。
应该看到,《史论》是著者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所集中关注的几个重要的文学史板块。采用“史论”来命名,正如作者所言,“意在更有效地把这些文章整合在一个史论结合的学术目标上。”[3]38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采用的“史论结合”的研究路径,更注重于“史”的梳理与再现,在严格的史实基础上,再进行深化阐释,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完整性与科学性。
三、“个人化”文学史书写的“叙事自觉”
在当代文学发展至今的60余年间,“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实践经历了同现代文学史书写一样的坎坷进程。上世纪80年“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将一场以“人”为主体的文学史书写实践推向历史的前台,引发了一大批学者对以往的文学史作去政治化的尝试。毋容置疑的是,“重写文学史”的反思精神至今还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史书写,然而在具体“重写”的过程中,一种“纯文学”的审美机制将“文学史”仅仅放在“文学的维度”上作了简单回归,它所带来的局限是非常明显的。“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过后,一大批学者开始重新反思“重写”的目的和意义。将文学归还给“文学”还是将文学归还给历史,抑或是二者的结合,种种疑惑导致“重写”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它产生的根本原因起于研究范式的冲突,而它的难以书写恰恰验证着文学在本质上多元化的特点。90年代下半期,文学史的“重写”热情在面临着多种现实困境的情况下,转向了个人化的研究,试图在“个人化”的研究中寻找它的“方法论”意义。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通过对文学史中的个案作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一个时代的文学光景,恰恰反映了当代文学史书写实践由“公共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变。在“解构”与“重构”的辩证交织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史的书写的“宏大叙事”主要停留在教材编写中,而在它的另一面,个人化的文学史书写实践则正在悄然勃兴。《史论》一书正是这种“个人化”文学史书写实践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尽管它的书写对象与整体架构尚欠“宏阔”,但是作为一部“个人化”书写的文学史,却显示了著者通过个人努力来重估文学史的叙事自觉。
首先,《史论》一书的“叙事自觉”体现在著者对文学史叙述的“外部”转向上。《史论》一书反映了著者从文学内部研究向文学外部研究,甚至是“文学研究”之研究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了作者“考镜源流”的学术追索历程,更体现了其追求“真实”的学术勇气与热情。在文学研究中“后学”大行其道的90年代,正是西方理论与研究范式被膜拜与反复复制的时代,文学研究一度陷入了理论堆砌的表象繁华之中,而文学的内在肌理却长时间地被人为地遮蔽乃至遗忘。对此,陈晓明曾指出:“很显然,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并不是要杜绝其他学科或门类的知识的运用,而是如何立足于文学本身。如何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8]可以说,“回到文学本身”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一个沉重的命题,它不仅要求研究者不断反思自身的研究方式,对研究的附加之物作“祛魅”式的思考,更要求他们在众声喧哗的学术研究热潮和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坚守文学研究者应有的姿态。显然,著者对这一点是有深切体会的。
其次,《史论》一书的叙事自觉,体现在著者对文学对象的科学把握与分析上。作者在分析所选取的文学史论述对象时,不仅关注作品本身,而且对作品以外的种种因素也加以细致的考量。在“十七年文学”研究受冷落的年代,著者对它进行的认真梳理与历史解读,便使其得以重现学理的光芒,这不仅仅是需要一种甘于寂寞的学术勇气,更需要一种透过表象见本质的学术眼光与智慧。回到“文学本身”,就是要依据历史事实来达到对感性批评的祛魅,从而构建起一个充满辩证色彩的文学研究空间。对王蒙早期创作的成功学解读,对孙犁作为“编辑和批评家”的身份解读,均带有几分“精神考据学”的意味。文学创作往往是一个作家与自我心灵不断对话的过程,研究一个作家如果不从“人”的角度出发,很可能意味着研究出现偏差。“从人出发,关乎时代”,这是研究任何一个作家的基本路径,同时正是在对作家创作进行“心理还原”的过程中,发现了容易被人忽略的精神情结,这些对全面评价一个作家的文学功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史论》一书的叙事自觉表现在著者“以史为鉴,透视当下”的现实关怀。如果说对文学作品生产的“考据”是《史论》一书的重要学术线索,那么这种“考据”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著者对作家作品本身所持有的关怀态度。《史论》一书中对莫言小说《红高粱》从“边缘”到“中心”的分析,在“边缘”与“中心”对比的辩证反思中,呼吁当代批评家对那些存在争议的作品既不能“棒杀”亦不能“捧杀”,以维护作品的尊严;在对影片《山楂树之恋》的分析中,指出张艺谋如何在经济大潮中通过一种“情感的回归”来坚守自己的文化使命与现实关怀。以史为鉴的研究姿态,使得《史论》一书区别于一本单纯的文学研究著作,而带有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著者不甘于对文学作单一的解读,更强调通过对文学的研究来透视当下的种种问题,进而努力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之道。在学术体制化日渐加深的当今时代,《史论》一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学院派”学者在“高墙”之内默默耕耘,希望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来启蒙公众的苦心孤诣。
诚如作者在《史论》后记中所言:“学术史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个体的人生体验和思想认知能否最终被历史记忆下来,实在不是依赖著者的意志而转移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某些珍贵的思想在历史的发展中遭到忽略冷遇乃致质疑是历史的常态,但是它们不会被长久地埋没,一定会在某个历史时期重现理性的光芒。具体到文学史的书写,王卫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一书中认为:“文学史中的价值评判,其标准不应该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大概是由对象主体和创作主体的特性所决定的。文学作品作为独特的审美创造,当然离不开审美主体的精神劳动.但它最终离不开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开放体系,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层面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包含着多元价值的综合体系。”[9]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任何一本研究专著的出版都是研究者不断探索以求创新的学术心路历程的反映,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对当前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填补和深化,而且会为今后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并拓展新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史论》是一部颇具份量的当代文学研究著作,应当受到学界的关注。毕竟,在文学研究的漫长历史中,能够检验研究的标准并非是惟一的,我们更需要关注那些曾经跋涉在此条道路上的人留下的脚印,因为他们的坚实探索,或将预示着一条新路的诞生。
[1]吴笛.经典传播与文化传承——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97.
[2]〔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65.
[3]李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10.
[5]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1.
[6]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94.
[7]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J].文艺研究,2008(8).
[8]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J].南方文坛,2003(1).
[9]王卫平.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名家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Review of Li Zonggang’s O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JIN Xing,YANG Hong-cheng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2.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I206.7
A
1674-5310(2015)-04-0059-05
2015-03-26
金星(1987-),男,安徽六安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杨洪承(1954-),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