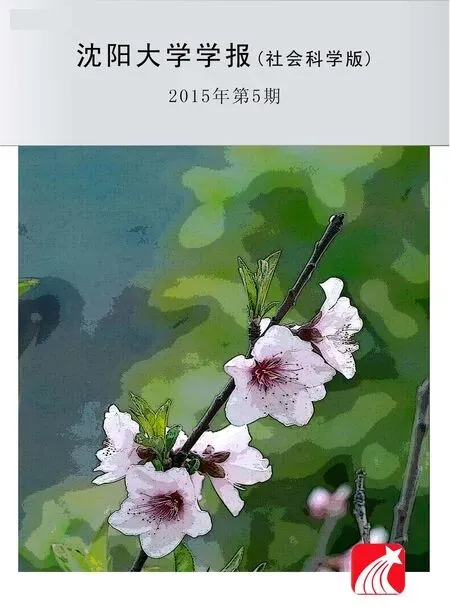宋初白体诗人群体的思想考察
沈 童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北京 100083)
宋初白体诗人群体的思想考察
沈 童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北京 100083)
分析了白体诗人群体在宋初百年文学复兴过程中特殊的文学贡献,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唐以来,韩、柳等人所构建的“道统”传承,并为后世欧阳修等人标举的“古文运动”的复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对白体诗人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加以考察,有助于对北宋初期文学史的深入研究。
白体诗人;思想;文学观
作为“宋初三体”中的组成部分,白体是任何文学史和诗歌史在书写过程中都无法忽视的一个诗歌流派,然而,白体诗歌却始终未能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重点。诚然,从当下的视角看,白体诗人群体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总体上有限,其成员中也罕有文学史上的旗帜性人物,但是,就北宋初期而言,白体诗人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尤其徐铉、王禹偁等人对当时的文学复兴和思想接续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白体诗与白体诗人群体
北宋初期,白体诗歌盛行,现在已找不到关于白体诗这一指称的确切内涵,然而,因《蔡宽夫诗话》有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故在考察了当时的诗歌风格及后人的评价之后,当下的诗歌史书写中,对于白体诗多适用如下定义:“宋太宗、真宗时,诗坛流行的学习白居易‘闲适’,‘浅易’,‘通俗’的诗”[2]。从这样的定义不难得出结论:宋初盛行的白体诗效仿的是白居易创作之中那些描摹闲适生活,表现其乐观放旷乃至“知足”精神状态的诗作,同时,白居易与刘禹锡、元稹等人的唱和诗也是宋初文人效仿的重点。
同白体诗类似,无论是宋初白体诗实践者自身,还是后世的诗话著作,乃至当下的学术体系,都没有对于白体诗人的数量和具体成员作出明确界定,只是在许多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载,如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3],又如欧阳修《六一诗话》云:“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行于容易。”[4]264,吴处厚《青箱杂记》:“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5]从上述的一干文献当中,可以看出,白体在当时颇为盛行,且流传甚远,自太宗、真宗朝兴起并兴盛,直至仁宗朝,仍泛余波,而其作者以徐铉、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为代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体的代表魏野同样也深受白体的影响,如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中称魏野“其诗效白乐天体。”[4]276查阅《全宋诗》,也不难发现,创作于太宗,真宗乃至仁宗朝的诗歌,风格近似于“白体”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这一层面上看,太宗、真宗和仁宗朝的许多文人和官僚,甚至皇帝本人,均是白体诗歌创作的参与者,而上述几位诗人的创作,集中体现了白体诗歌的风格特点和文学水平,同时,这几个人对宋初思想和文化的重建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太宗一朝文坛和政坛的重要领袖,李昉在宋初文化建设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几部大型类书,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均是在其总纂下完成;另一方面,作为由五代入宋的官员代表,李昉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这些官员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同时,李昉也是白体诗歌的积极推行者和参与者,如他在《二李唱和集序》中谈及唱和之事:“南宫师长之任,官重而身闲;内府图书之司,地清而务简。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缘情遣兴,何乐如之。”[6]从中,可以看到宋初官吏优游自适的生活状态。在创作方面,李昉“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诗歌方面,也是极为偏爱白公诗,达到随身携带,手不释卷的程度。然而,李昉虽执掌权柄,身居要职,但在其诗文之中,却很少见到他关心政事,忧心民瘼的话语,更多的是表现其台阁闲情,描摹花鸟江山,以及记录他与友人、同僚的日常交往,其仕宦生涯中也极少见到上书直言的行为,甚至因为这一点遭人弹劾:“先是,有翟马周者击登闻鼓,讼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平章事李昉身任元宰,属北戎入寇,不忧边思职,但赋诗饮酒并置女乐等事。”[7]在李昉及宋初大量官吏的思想之中,“制度意识”[8]颇为显著,这也是他们喜爱白居易诗歌的原因所在,后世对于白体诗人多有微词,也来源于此。
二、徐铉思想动态考察
与李昉、陶谷、范质、卢多逊等由五代入宋的士人群体不同,徐铉所代表的是宋初官员中另一类群体,这便是由地方政权归降入宋的文臣,其中,以南唐与西蜀两地的文臣为其中翘楚,这些人的文学修养和学术思想均远胜李昉等人,然而,囿于其降臣的身份,这些人在入宋以后的仕途命运并不顺利,在宋初白体诗歌盛行的风气下,这些文臣同样参与到了诗歌写作和唱和之中,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中,徐铉作为南唐和宋初的一代文宗,最具代表性。
1.回溯“三代”与复古思想的接续
徐铉的儒家思想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复古思想,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徐铉在自己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也建立起一个一以贯之的“道统”谱系,如《宣州泾县文宣王新庙记》:
“故斯教也,衰於战国,废於嬴秦。汉魏以降,续而复绝。夫仲尼日月,重昏千祀,非圣人孰能廓之?故斯教也兴於武德,盛於贞观,极於开元,理自然也。”[9]
“圣则应天顺人,西伯受代殷之任。贤则开物成务,太师有佐命之功……自汉参霸道,魏济奸雄。藐尔千年,荒哉七德……高祖奉天革政,扇牧野之高风,太宗屈已师臣,蹑渭滨之盛轨”[10]9230
在上述文字当中,依稀可以看出徐铉所建构的真理体系,即唐代经由汉魏直接接续“三代”。这种对于上古时期“三代之治”的追慕,在徐铉的笔下亦多次出现。如在其《说文》序中,徐铉建构了完整的文字谱系:
“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虽王帝之后改易殊体,六国之世文字异形,然犹存篆籀之迹,不失形类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隶聿兴,便于末俗,人竞师法。古文既变,巧伪日滋。”
“……夫以师心之独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而贱目也。”[11]
如果说在《宣州泾县文宣王新庙记》《武成王庙碑》等文章中,徐铉建立了一个由“三代”而至盛唐的完整体系。他通过《说文》序所呈现出的是他对于“三代”理想世界的倾慕,在他的观念之中,“三代”不仅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理想世界的参照,同时也是后世思想文化的源头,后世学术的失落,正是因为“古文既变”和“自为臆说”。
与回溯“三代”思想相对应的是徐铉对于圣人的追慕和呼唤,将圣人作为建立其思想体系的关键环节,这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处乱世,希望通过圣人重建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的内心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士人精神一以贯之的承接,如:
“故立其教者谓之圣,大其业者谓之贤。圣则应天顺人,西伯受代殷之任。贤则开物成务,太师有佐命之功。”[10]9230
“皇天有造物之柄,有爱民之仁,必待圣人而后行。王者有承天之德,有济世之量,必待圣人而发后。”[12]
“夫道被万物,处其中者是曰贤人。功济横流,让其先者方称君子。施之则开物成务,兴广业而同归。卷之则保族宜家,垂令名于必大。”[13]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圣人”在徐铉的思想体系中是顺承天命而生,其功绩在于协理阴阳,制定人间秩序,成为一切合理性的源头,这样,“天命”与“人事”便通过圣人而联结于一处,这样的思想体系,与后世的理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4]的观念之间,也产生了某种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徐铉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态,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复古思想之外,同时附有十分明显的道家印记。在道家体系中,“道”是统摄一切的源头,万物皆以“道”为存在及运行的凭据,政治生活亦概莫能外,于是,徐铉认为:“自然而然,有道存焉,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言达,王者得之,则三五之功,其余事耳”(《剑池颂(并序)》)。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便是“广无为之为,执无象之象,万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最高统治者必须做到“承积德之基,法自然之道……学洞精微,守谦光而冲用。明昭隐伏,体大度以包荒。动则庇民,不矜功而尚智。静惟修政,恒务啬而劝分”。
2.徐铉的文学观
徐铉的文学观是徐铉儒家思想的又一个方面。其文学观,详尽地阐释了徐铉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审美标准,以及对于文学功用的要求。
在文学的功用方面,徐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观,以及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观念,强调诗歌要“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强调“文以载道”。如在其《成氏诗集序》中,徐铉认为“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又如《文献太子诗集序》中,徐铉谈到“鼓天下之动者在乎风,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於风可以言者,其惟诗乎?……理必造於元微,词必关於教化”。上述可见徐铉极其重视文学的现实意义和教化作用,并强调文学,尤其是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道”的载体。
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诗歌乃至文学本身,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而是有着“吟咏性情,黼藻其身”的独立精神和自身形态:
“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故君子有志于道,无位于时,不得伸于事业,乃发而为诗咏”[15]。
故徐铉对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艺术性和审美标准同样提出了较高要求,《文献太子诗集序》提到:
“夫机神肇於天性,感发由於自然。被之管弦,故音韵不可不和。形於蹈厉,故章句不可不节。……”[16]又如《萧庶子诗序》:
“其或情之深,思之远,郁积乎中,不可以言尽者,则发为诗。……精诚中感,靡由於外奖,英华挺发,必自於天成”[17]9213
综上所述,徐铉认为诗歌本身并非依附于“道”而存在,作为一种非功利性的文学形态,诗歌本身便具有着审美方面的存在意义。在创作方面,不仅要“感发由于自然”,更要具有“肇于天性”的神机,“自于天成”的“英华”,这便对于文学本身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在风格方面,徐铉认为“若乃简练调畅,则高视前古。神气淳薄,则存乎其人。亦何必於苦调为高奇,以背俗为雅正者也”(《文献太子诗集序》),提倡“博赡渊奥,清新相接”,“词赡而理胜,行洁而言方”的艺术特色。而作为宋代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徐铉等人的文学观念对于宋初平易晓畅文学风格的建立及宋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王禹偁思想观念考察
王禹偁、田锡、张咏代表的是宋初的另一代知识分子,同徐铉、李昉、范质、杨徽之等活跃于五代时期的官僚不同,他们是北宋建国以后,通过科举得以晋身的人才,故他们身上,多已不带有五代时期的痕迹,而多以关注政事,复兴古道为特征。如王禹偁在上《御戎十策》的同时,田锡和张咏也同时上疏,参议时政。虽然他们也参与到了宋初诗歌的唱和之中,然而,他们的身份和思想构成已经脱离了“白体”这一窠臼,成了真正的具有宋代特色的复合型知识分子,其中,王禹偁的成就最高,其思想也最具代表性。
1.王禹偁的儒家思想和政治观念
同许多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王禹偁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占有着绝对的主体位置,在其留下的诗文当中,可以发现,王禹偁始终以孔门弟子自居,乃至将孔子推举到了“素王”的位置。如其《仲尼为素王赋》中有言:“鳯鸟不至兮,河不出图,圣人无位兮,立教崇儒。”[17]9214,又如《昆山县新修文宣王庙记》:“夫圣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为一时也三五帝皇之谓乎?无位者天使之立教,为万世也先师夫子之谓乎?”这也为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在君权统治之下相对独立的身份和意识,以此可以保证其一定程度上的话语权威。
在如此观照之下,王禹偁的思想中自然会带有儒家思想的另一种形态,即对于“回溯三代”的复古思想的倾向性,“乃知君子心,所乐在稽古”。如在其《籍田赋》中,王禹偁认为“自周德下衰,礼文残缺”,将有周一代视作道德和思想变化的分野,对于秦汉尤其近世以来的思想颇多指摘之处。
儒家思想对于王禹偁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王禹偁一生的命运。一方面,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王禹偁的内心深处充满着建功立业的抱负,这在其刚刚踏入科场之时便已形成,虽遇小挫,仍抱雄心:“我朝甚明,我志俱壮,誓雪前耻,庸何恨哉,夫如是偶负小屈,岂能芥蒂”,又如其直东观时,“阅五代史,见近朝名贤立功立事者,耸慕不已”。而其建功立业的目的,并非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为其“行道”寻求有效的途径,力求“上致君,下利民,终利身,建一时之功,垂千载之誉”。另一方面,王禹偁一生之中,无论身逢何种境地,始终保持着他孤直忠贞的品性,正如其《三黜赋》所言:“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又如《闻鴞》诗中所言“报国惟直道,谋身昧周防”。而这一人格特征的形成,同样受到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影响。
王禹偁在其仕宦生涯之中,始终保持着对于政治的极大关注,曾多次上书进言,裨补政治,这些言论,几乎涵盖了朝政的各个方面,如在端拱元年(988年),王禹偁被太宗召入京师,授官右拾遗,“拟把微躯杀,惭将厚禄尸”(《谪居感事》),遂于当年三月上《端拱箴》,以寓规讽,言到:“无侈乘舆,无奢宫宇,当念贫民,室无环堵。无崇台榭,无广陂池,当念流民,地无立锥。……勿谓丰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勿谓强兵,征伐不息,须知干戈,害民稼穡。”(《小畜外集》卷十)。同年,王禹偁又上《三谏书序》,再次对当下的三处弊病加以批判,并希望太宗以此三文为鉴,加以革除。
端拱二年989年正月,王禹偁上《御戎十策》,重点提出边境之安定在于“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并对两个方面提出自身的建议,“各有五焉”:“外任其人有五者:一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二曰侦逻边事,罢用小臣。……。三曰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四曰以夷狄伐夷狄,中国之利也。……五曰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內修其德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经费也。……二曰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也。……三曰信用大臣,参决机务。……四曰不贵虚名,戒无益也。……五曰禁止游惰,厚民力也。”从上述的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禹偁所提及的诸多政事,无一不切中时弊,而其所提供的解决方式,却又带有着浓烈的复古精神,然而,正如其本人所言:“安用学腐儒,矻矻守礼法”(《怀贤诗》并序),王禹偁在解决实际政务上,并未拘泥于礼法,而是因时而行,因势利导,体现出其出色的政治才能。
在王禹偁一系列政治思想之中,有两项是值得重点关注的:①其思想中带有强烈的民本色彩。“善化民者,以天为则,善知天者,以民为先,若天人之理洞达,则帝王之道敷宣”;“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故王禹偁在许多诗文之中,都表达出他对于民间生活的关心,如:“因思河朔民,输挽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对雪》),“麦田少时雨,蚕月无闲人。自惭怀禄仕,蠹此力穑民”(《太一宫祭回马上偶作寄韩德纯道士》),“路旁饥冻者,顔色颇悲辛。饱暖我不觉,羞见黄州民”(《十月二十日》),“君恩无路报,民瘼无术瘳。唯惭恋禄俸,未去耕田畴”(《月波楼咏怀》)。②其对待佛教的态度。在政治上,王禹偁力主排佛,在《酬处才上人》之中,他着重道出其中原委:“我闻三代淳且质,谁人熙熙谁信佛。茹蔬剃发在西戎,梵法不敢干华风。……可怜嗷嗷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织。”在王禹偁看来,佛教东来乃是源于周德下衰,三代之治不竟,秦汉以来,多行暴政,百姓遂皈依释教,以求解脱;然而,佛教之风大兴,却使得劳力减少,生民益困,这便同时动摇了思想和政治的根基,在这一情形之下,王禹偁对于铲除佛教的决心,必然十分坚定。
2.王禹偁的文学观
作为北宋文坛承前启后的知识分子,王禹偁对于北宋的文学创作发展,北宋初期的文化复兴,以及后世古文思潮的兴起,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自王禹偁等一代士人起,“文自咸通后,流离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的情形便逐渐改变,自中唐以来埋没不闻的“道统”得以重振和延续。
王禹偁在其文学观念的形成中,首先将文学界定为“载道”之用,在《答张扶书》中,他言道:“夫文传道而明心也,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在这种文学复古思想的统摄下,王禹偁进而确立了道统的传承:“行王道者,禹汤文武周公而已。……言王道者,孔子孟轲荀卿扬雄而已。”(《答黄宗旦书》),这便与中唐时期,韩愈等人所创建的道统遥相呼应。与此同时,在文章写作方面,王禹偁认为应“远师六经,近师吏部”,同时,要力求“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反对迂腐艰深的文章风格,此外,王禹偁也强调了文章的现实性作用:“夫进贤黜不肖,辟谏诤之路,彰为诰命,施之四方,延利万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纤之言,岂足轸虑思、较轻重於琐琐之儒哉?”[18]在这一系列的论述之中,不难得出结论,即在欧、苏等人之前,王禹偁已然深受韩、柳等人影响,着力恢复中唐所失落的古文运动精神。
另一方面,王禹偁对于诗歌的功用也作出了类似的界定,在他的观念之中,诗赋一类,并非小道,理应在诗赋创作之中重拾“风雅”精神,这也将宋初白体诗歌创作的领域大幅度拓展,从单纯地模仿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以及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之中脱颖而出,加入了书写现实的讽喻诗,在这一范畴上,王禹偁同白居易等人一样,希望以此作为进谏君主的另一种方式,使民间疾苦得以上达天庭。
然而,这并不表明,王禹偁只是一味强调文学的载道功用,而将其审美因素置之不理,相反,他十分重视审美意义,在《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中,王禹偁集中论述了文学的发生和创作:“山川之气,气形而不自名,故文藻之士作焉。为歌,为诗,为赋颂,为序引,必丽其词句,清其格态,幽其旨趣,所以状山川之梗概也”,这便在文学的现实性之外,“获得一种愉悦的审美体验和感受”[19]在这方面,王禹偁的成就更是远远超过宋初古文诸家。
[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398.
[2]韩经太.中国诗歌通史:宋代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9.
[3]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2:10.
[6]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全宋文:第二册[M].成都:巴蜀书社,1988:18.
[7]李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 2004:647.
[8]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9.
[9]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9219.
[10]武成王庙碑[M]∥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9230.
[11]文苑传[M]∥宋史:卷四四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5:1347.
[12]舒州周将军庙碑铭[M]∥全唐文:卷八百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9240.
[13]唐故德胜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扶风马匡公神道碑铭[M]∥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9247.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7.
[15]邓生诗序[M]∥徐骑省集:卷二十三,四部丛刊本.
[16]全唐文:卷八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9213.
[17]王禹偁.小畜集:卷二[M].四部丛刊本.
[18]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3:52.
[19]齐海英.中国古代理趣诗艺术审美特征[J].沈阳大学学报,2009(5):92- 95.
【责任编辑 王立坤】
An Exploration to Thoughts of the Group of Bai Juyi-Style Poets
Shen To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search Base,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83,China)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group of Bai Juyi-style poets in the duration of the recovery of culture in the fist hundred of years in Song Dynasty is analyzed.It considers that,to some degree, the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movement started by Han Yu in Tang Dynasty, and made a foundation for Ouyang Xiu and other scholars in the middle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Bai Juyi-style Poe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ntensiv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Bai Juyi-style poets;thoughts;opinions of literature
I 207
A
2095-5464(2015)05-0629-05
2015- 04- 16
沈 童(1989-),男,辽宁沈阳人,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