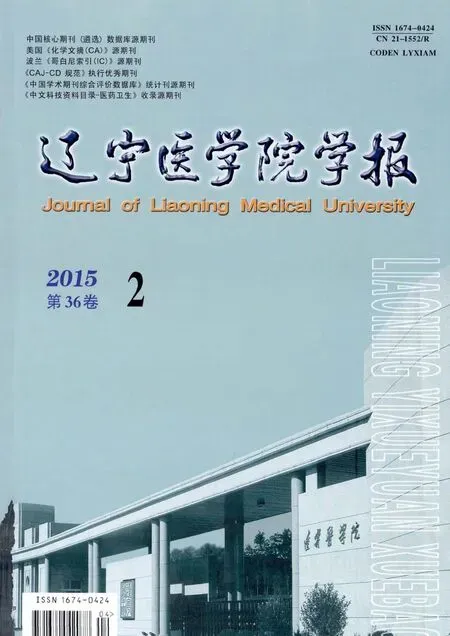社会文化对中西医学的影响
陈国晨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19世纪以来,西医通过其技术简化的理论体系得以快速发展和普及,在占领了更多医疗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与社会认可。此背景下提出的“西学东渐”,把中西医之争推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风口浪尖上。表面上,中西医之争所反映的是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成见,实质上知识表层的冲突背后必然隐含着文化的推手。从中西方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以中医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侧重于理学、宏观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而西医背后的西方文化强调实证、解析的分解性逻辑模式。所以,与其说医学是一种经验、技术,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1]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西方在社会、文化上交流日益加深,刚开始的文化冲突也许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融合。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融合的结果是产生一种积极的新的文化,就像英语在今日不再具有民族意义一样。[2]虽然文化本身存在多样性、同一性,但就中西医学的社会文化基础来看,差异还是普遍存在的,笔者认为从哲学观念、认知方式、价值伦理、人与自然关系和治疗方式这五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能够较好的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对中西医学的影响。
一、哲学观念的差异
中医(本文中,中医专指汉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医学体系,不包括藏医、蒙医等诸多体系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古代先贤们在朴素哲学观念的影响下,结合阴阳、五行等学说而形成的一种关于认识疾病、诊察疾病、治疗疾病的经验性知识体系。从医学史的角度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医在古代朴素哲学观和宋明理学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自己思辨特点的发展路线。中医师们撰写医书对先辈们的诊治心得进行总结,这是医疗实践活动的经验性积累;此外医家们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中医药知识,这是辨证施治的体现。在这种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医把人体视作是宇宙与自然的结合,人体本身像一个小宇宙,体内的机能活动映射着体外的大宇宙。当体内的小宇宙与周身外的大宇宙处于一种和谐交融的状态时,人体是健康的,不易受到外邪的侵犯。这种人与自然的理想状态就是中医中强调的“人身小天地,天地大人身”的哲学观念。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西方哲学倡导的是身心对立的二元论。西医(西医的概念较为宽泛,又称生物医学、主流医学、科学医学,它可以包括西方国家任何与健康及疾病相关的认知、实践。生物医学被认为是世界性的医学、现代医学,而不专属于西方,由于在讨论中医的语境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中西医说法,因此本文沿用此习或与生物医学交互使用)的发展始终受到这种二元哲学观念的影响,加之由科学主义兴起所带来的一种理性精神,使得西医在它的理论知识体系中努力构建出一套标准化检测、可还原化操作、原子解析式的分析方法。正是在这种身心分离观念的影响下,西医通过解剖学、组织学等学科把人体从客观上以器官的位置和功能为主要特征分为九大系统。人体的正常状态指标是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统一调节下,由消化、运动、神经、循环、呼吸、生殖、泌尿、感官、内分泌这九个系统,各司其职又互相链接,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任务,实现复杂的生命体征指标,让人体作为一种物理属性上的有机体完成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命活动。生物医学眼中的人体构成就是一个个独立于彼此的器官,通过各个系统之间的复杂运行使得它们可以联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碳基生命体。那么生物医学眼中的疾病必然是孤立存在于九大系统之中的客观因素,虽然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影响人体的不同脏器,但它的产生只是处于一个限定区域,即疾病是一个实体。西医师们通过一系列的化验检测数据来推断疾病的位置、形状、程度,在他们的眼中人体如同一部机器,病情是机器某个部件发生了障碍从而影响到整体的运转功能。而对于损坏或发生障碍的零件,我们只需更换或者添加化学制品即可修复。但中医眼中的人体是身和心的统一,不仅要注重疾病的治疗,还要注意患者情性的调养。因此,如果西医是现象世界,那么中医不仅包括现象世界,还包括体验世界。[3]这种哲学观念的差异进一步决定了两者在对疾病、自然等物化对象上认知方式的不同。
二、认知方式的差异
东方文化中的认知方式强调天人合一。这种认知方式背后体现的是整体综合的思维特点。在这种认知方式下,古代中国人把他们的世界观分为天、人、地。“天”位置最高,“人”居于中,“地”为基础。首先“天”以“天之人道”为核心,要求人们要有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品质。所以《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次,先哲们对居于天地之中的“人”要求甚严,表现在把“人”的世界观划分为三个方面,“人之天道、人道、地道”三者分别以《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为代表。所以《论语》一直强调人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更好的实现人之天道的要求;《孙子兵法》虽通篇讨论如何用谋以达到奇兵的效果,其实反映的是人之人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事中要注重运用才智谋略;《道德经》云“自然无为”,自是告诫人们不要苛求、索取太多,克制贪欲,谨守人之地道从而以无事取天下。最后,作为基础“地”的世界观强调“地之人道”,要求人们注重自己的身体,身体乃是一切外在条件的本源,所以《黄帝内经》中一直在暗示人们要休养生息。这种天、人、地的认知方式,经过几千年岁月的沉淀和各家学派的弘扬,形成了中医特有的世界观即治本正心,达到本我(小宇宙)和他物(大宇宙)的自然和谐。
由于受到身心二元论的影响,西方文化注重实证、分析,在这种概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原子解析为主要特征的思维逻辑,这种探求事物真相的认知方式,深深影响着西方文化及西方人。所以西医认为自然界中的事物都可进行物质还原,我们把规律从表象的层面抽离加以归纳,我们独立于自己的感知,通过规律的收集和整理来认识客观的自然界。正是这种认知方式,导致了生物医学对疾病的简化,把疾病作为一种现象从人体中离析出来,加以概括和总结,从现象到现象、从逻辑到逻辑加以推理认知,最终解决病灶。这种过于重视疾病表象而忽略病人的西医,自然和重视病人的中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生物医学认为中医的那些技艺性手法仅仅是在患者的心理层面上缓解了疼痛。例如,在纽约,由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虽然中医的诊断技巧没有有效缓解病人的症状,但这些病人却高度评价中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倾听他们的诉说,与他们培养了信任的关系,从而有效的缓解了患者内心的病症。[4]
三、价值伦理的差异
由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的长期影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忠孝的理念丰厚。这种厚重使得中国人的价值伦理注重宗族内部的利益,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的血缘性群体意识。在这种观念的长期熏陶下,以仁义为宗,以忠孝为怀的价值伦理观的形成自然也就不那么吊诡了。
正如上文所述,科学主义的诞生所带来的理性精神毫无疑问催生出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本身又进一步催化了西方文化中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的出现,所以我们从古希腊的史诗神话到现当代的西方国家,强调个体的感受,尊重个人的利益一直是西方价值伦理观的主旋律。概括来说,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契约关系。
由此发展出来的潜意识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认为若是超出了个人自身所认定的那个群体范围,那么他更愿意去隐藏自己的知识很少愿意拿出来与非该群体的人分享,这一群体是他自己所认定的,而非一种以知识特征本身所划定的范围。在西方文化中,西方人更注重社会的实体性,注重一种契约关系,所以他们更愿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他们可以无私地为了一个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学术力量。正是由于价值伦理观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学不同的知识传承体系。
此外,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医持有奇怪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是一种原始或巫术思维,如果病人被治愈了,也是一种安慰剂效应、心理暗示、偶然性等因素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更古老,更注重整体性和精神层面,因而比西医更“真实”,这种观点倾向于把中医从一种知识体系转向宗教体系。显然这两个方面阻碍了对中医的正确认识。
四、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
以整体综合为认知方式的东方文化和以原子解析为认知方式的西方文化自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概括来说,东方文化主张以自然为师,天工开物,西方则以自然为材,强调人力驭天。[5]古人认为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以自然为师是相处之道,人是来源于自然,当然也要回到自然中去,只有与之和谐相处,达到物我交融的地步,才能真正的认识自然界,获得一种普遍规律的把握。而西方人强调神人相分,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人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主观主体。想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就需要把自然作为获取资源的对象,以人力为主体对自然进行开采,即以自然为材。毫无疑问,这种自然观上的差异深深影响了两种医学体系。在中医的眼中,病人和疾病是一个整体,疾病存在于病人身上不能脱离人体本身而存在,同时疾病本身又受制于病人体质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所以中医看病不仅治病,而且医人;西医是强调身心对立,疾病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虽寄存于病人身体中,但客观事实却有着一种普遍的规律可以把握,所以西医治病首先把疾病从身体中分离出来,只是治病,而非医人。所以美国人类学家Martha L.Hare认为中医的实践经验并不是个体对理论的简单应用或经验积累,而是具有历史性、集体性和发散性,是中国人认识自然的一种特殊方式。[6]这种形象的比喻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中医在药物运用上,更加注重整体性的疗效,药物进入人体中如何消灭疾病,中医用气在人体中的运转来加以解释,并不局限于患病部位的具体描述。而西医的白箱理论更好的阐释了西方文化力求探索真相的观点。西医知识体系中的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的设立就是为了更好的告诉人们,每一粒药丸所包含的大分子化合物如何通过肝胆循环、小肠绒毛上皮细胞的吸收进入血液系统的,如何通过血液的运输达到患病的部位。为了验证白箱理论,西医中的CT、MRT的使用把病人的身体透明化在患者眼前,更让人眼见为实。
五、治疗方式的差异
在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对于诊断的描述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医认为详细的描述诊断不仅是治疗的开始也是治疗的一部分,西医对于病人自身的叙述不太重视,反而更倾向于一系列理化检测的数据。中医对于病人脉象的描述和症状的判断成为治疗的中心,西医对于病人一系列检测数据的分析解读,最终开出处方是西医治疗的主要手段。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不同文化赋予了疾病不同的含义。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同一种客观状态可能是一种病痛,也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所采取的治疗方式也就千差万别。
马来西亚独有的“拉塔病”(Latah) 长期被生物医学工作者们认为是文化领域中的一种精神综合征,根据观察事实上是一种对惊吓的反应,而无需采取治疗。中医里有七情的概念,即把人的精神状态分为七种情感——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感若因外因或内因的改变,会影响人体的正常运转从而患病。若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拉塔病”,可能的诊断结果是情感过激过久而引起的疾病,所以一般会开出一些安抚宁神、休养生息的药物来加以治疗。
食欲亢进综合征,目前在西医看来是一种病理行为,可能是由神经系统的损伤引起的一种病症,但是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中医却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即使在当今我国医学体系中这种疾病也没有得到公认。
在治疗疾病的药物选择上,中医采用的药物是自然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的食材,造成这一行为的原因是,古人在采食野果、野菜、种子以及狩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现有些植物不仅可以充饥还能治疗疾病,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发现了一些药物的作用和特性。
西医认为人体是由一系列的细胞、器官、组织构成的有机体,在神经系统的调节支配下完成生命活动和身体机能的运行。因此,对于治疗疾病的药物也注重探求它的分子结构,虽然西方早期也是从自然界获取草药来对疾病加以治疗,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物科学的发展,西方药物在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帮助下,工业化制药业规模也日益扩大,小小的一粒药丸包含的不仅仅是大分子化合物,还有中西方社会文化的不同。
所以,社会文化对构建医学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医看来,治疗结果是治疗的终点,成功的治疗结果是排除了疾病和解决了身体机能的系统紊乱,而中医对于疾病的治疗总是与文化背景和疾病变化相联系。可以说,中医对于疾病的治疗方式是一种对于生命现象的一般反应,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治疗是一种服用两片阿司匹林即可减轻头痛的化学反应。◆
【参考文献】
[1]关晓光,车离.脉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医脉诊文化研究引论[J].医学与哲学,1996,17(5):232.
[2]尚杰.思维方式的冲突——目前中西哲学观念的差别刍议[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17~20.
[3]张有春.医学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01):211.
[4]Martha L.Hare“The Emergence of an Urban U.S.Chinese Medicine,”i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New Series,1993,7(1)30~49.
[5]吴宗友.堪舆文化——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生态学[J].江淮论坛,2011,(01):114~118.
[6]席焕久,王如松,关兴华,等.医学人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