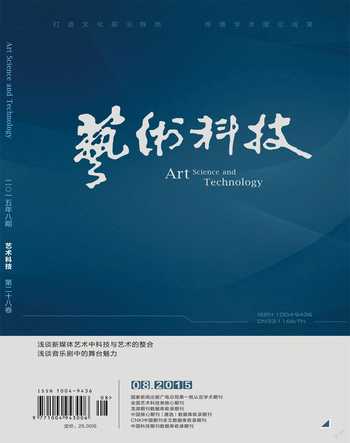新旧相遇下的焦虑
陈明黎
摘 要:昆曲《玉簪记》由明代剧作家高濂所作传奇剧本,[1]被学者誉为十大古典喜剧之一,不仅作为昆剧剧目经久不衰,更被川剧、京剧、越剧等其他剧种借鉴,其中《琴挑》一折更是作为昆剧经典。2009年,作家白先勇在推出青春版《牡丹亭》五年后,重新包装《玉簪记》,再次体现其昆曲新美学的理想,从而达到吸引更多青年人的目的。然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究竟新在何处,美在哪里,它将给昆曲以新生,还是成为昆曲的回光返照?这套新美学又给我们以何种启示,都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话题。
关键词:玉簪记;昆曲;美学
1 新《玉簪记》之新
2004年,白先勇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名噪一时,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之一,一时间,昆曲这种古典温雅的艺术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时隔五年,白先勇召集原班人马,并集合书法家董阳牧的字、画家奚淞的白描佛像、王童的服饰设计、王孟超的舞台设计制作了新版《玉簪记》。[2]
在这出青春版《玉簪记》中,将戏曲动作与舞蹈结合,群众演员在开场以舞蹈形式变换队形,男女主角在《秋江》中凭舞蹈动作表现剧情,使《玉簪记》的节奏更紧,让人眼花缭乱便不易困倦。在舞台布置上,将剧目以书法形式呈现,尽可能使剧目内容与书法行云流水融为一体,在女贞观的几出戏中,又用奚淞所画观音像和董阳牧所作“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书法作品作为舞台布景之一;在道具运用上,更动用唐代皇家宝琴“九霄环佩”为全剧音乐添彩;而在灯光效果、演员服装上,更是做到中西对接。[2]这些都是白先勇在这场《玉簪记》的青春盛宴中十分得意之处,将昆曲改造的宜中宜西,不仅能抓住中国青年的眼球,更能为昆曲艺术走向世界,进入西方视野打下基础,无论这些是亮点还是噱头,不得不承认的是,白先勇通过改编《玉簪记》的确再次达到了吸引年轻人走进剧院观赏的目的。
与此同时,新版《玉簪记》对高濂的剧本也做了大量处理,修剪了潘必正陈妙常爱情故事外的枝节,在老版昆剧剧本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由《投庵》《琴挑》《问病》《偷诗》《催试》《秋江》六出组成,故事一开始由女观主道出娇莲投庵的来龙去脉,结尾处则将王公子的引诱略去,更重要的是将才子佳人故事中的大团圆结局一并剪断,全剧最后的场景是,妙常在前艄婆在后,妙常一脸寂寥一束灯光打在她的脸上,光从暖色变成冷色最后黯淡。这个开放式的结尾一反传统中国戏曲的剧情模式,非但将结尾截去,从灯光的色彩以及最后女演员表演出的落寞,将结局推向另一个方向:或许潘必正此去仍落第,他羞于见父母也羞于见妙常一味逃避;或许潘必正功成名就,但身在金陵女贞观的妙常只是一个匆匆路人,最终成了段始乱终弃的故事。
在青春版《玉簪记》中,陈妙常与潘必正在《投庵》的最后相遇,只是匆匆一瞥却一往情深,紧接着便是《琴挑》互探,原剧本中潘必正与陈妙常的惺惺相惜概不赘述,似乎两人定情只是因貌而起,而在之后潘必正对陈妙常的追求,更是将这出戏的娱乐精神发挥出来。陈妙常与潘必正的爱情,从头至尾都由色心而起,成了顿青春享乐的料理,满足了观众的视觉爱好后,便再无其他可留恋之处了。
不同于高濂对人本身努力的认可,青春版《玉簪记》是彻底沦为爱情小品,剧院中的确能听到开怀一笑,可笑过归笑过,似乎总难引起人对昆剧这个剧种的欣赏之情,也不失为一种遗憾。白先勇尽管引梅兰芳改编京剧的事例来证明自己对昆剧的改编是利大于弊,他借用西方的舞美让昆剧走出国门,也的确对昆剧的传播起到很多积极作用,然而,这出青春版的似乎这不是一出昆剧,而只是一出名为昆剧的话剧,白先勇的改编其功劳也止步于将昆剧推广传播到更大平台上而已。
2 传统新编的未来
白先勇对昆剧的改编是指望自己能建立起一种昆剧新美学,自然昆剧只是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其中一种,但昆剧被誉为大雅之音,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具体体现,白先勇对其青春版昆剧寄予的希望也体现出他试图使中国古典美学走出故纸堆迈进新世纪的野心。白先勇能召集众多琴曲书画行当的大家,为这次新版《玉簪记》出力,无论最后大众评价如何,不得不否认他们与白先勇希望中国传统文艺能重树辉煌的动机是相同的。
白先勇定位青春版《牡丹亭》首演是一出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戏曲,在制作新版《玉簪记》的时候是尝试通过琴曲书画将昆剧回归雅部的传统,尝试将昆曲美学推向更高的抒情詩化的境界。[2]可以见得,白先勇的理想是远大的,然而从最后的成果也看得出,这样的理想最终只是理想而已。所谓琴曲书画,不过是借用灯光舞美服装将昆剧包装得更华丽一些,但如果这便是所谓新美学,未免太潦草了。
高濂的《玉簪记》其舞台效果和表演功底我们如今是不能见到了,但是古典戏曲台词的优美却分明可见,这些词句登台可唱,同时又可当案头读物细细品味,其辞藻清丽,每一出都是抒情意味大于叙事功能,更使得这出戏荡气回肠充满感情。新版台词虽易懂,却少了这份典雅之气,于是整出戏便流于俗套,高濂的剧本有意无意间使做戏不只是做戏,而白先勇的新作,则是由于强调做戏的概念而使戏只是戏,不得不说是件可惜的事。
昆剧改编只是中国古典艺术遭遇当代西方思潮的其中一个体现,如京剧拍成电影、流行歌曲与戏曲混搭等,都表现出戏曲人对戏曲处境的焦虑,他们纷纷试图摆脱这种困境而不断进行新的尝试,但这些尝试最后都无疾而终,并未见到扭转传统戏曲越来越边缘的尴尬处境,艺术家们没有创作出在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更不用说建立一套新的美学。
对于古典艺术的改编,过于大胆便让戏不成戏,过于谨慎又让变不成变,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其生命,然而,既然是生命自然也有始有终,并不是说这种形式即将终结,而是某种艺术因不能顺应潮流而走向边缘就并非是毁灭,如果因为想占据中心地位就使原本优美的艺术沦为四不像,哪怕能一时间受到关注,最终不过是场回光返照的表演。
戏曲如果只有年长之人方能体味个中滋味,那么好好经营让长者品味也不见得未来就暗淡,白先勇自身就是极好的例子,他年轻时崇尚西方之美,如今又被东方气韵折服,这就表示因为担忧年轻人不赏昆剧之美,而卑微地改造自己去迎合青春的口味并不见得高明,这么做不但未必能让年轻人体味到真正的古典艺术,更有流失原来就颇懂戏曲的爱戏人的风险。
当代社会语言习惯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而传统戏曲要求不仅有精通韵律的创作者,还要求能听懂台词意味的接收者,这些都是不可回避也是无法改变的问题,从这方面而言,戏曲的改造永远只能专攻于皮毛功夫。如果戏曲本身只是古典美学的外化形式而已,如果坚守这种艺术形式为的是坚守中国的美学,只要这种美学能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体现,那么是借昆剧表现还是借电影表现也就都不重要了,中国古典之美从戏曲中走出,也一定会走入另外的艺术形式中去。因而,执着于戏曲是否能吸引年轻人,是否能吸引西方人,也就成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夏征农.辞海(艺术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83.
[2] 白先勇.云心水心玉簪记 琴曲书画昆曲新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8-17,147-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