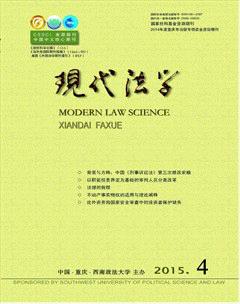法理的救赎
摘要:
政府管制的利益不可能匀质分布,很容易遭到管制性征收规则的阻遏。互惠原理可以适当磨平征收规则的刚性棱角,在法理上扮演救赎的角色。互惠原理在美国经历了经济互惠和社会互惠两个阶段,分别形成各自的规则。北京的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措施符合社会互惠原理,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关键词:法理;互惠原理;平均利益互惠;管制性征收
中图分类号:
DF31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4.06
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北京峰会召开前,北京施行了包括汽车按单双号限行在内的多项管制,北京的环境质量一度跃上了新台阶,被戏称为Apec蓝中华网.“APEC蓝”从哪儿来?[EB/OL].[2014-12-26].http://news.china.com/jiedu/1104-1/.
Apec会议结束,人们想Apec蓝永驻北京,有关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话题再度被提及。2014年12月26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草案第45条系向地方授权限制机动车通行的条款,如获通过,该授权条款可能成为“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法律依据。一些委员疾呼:“不能随便给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开口子。”王伟.不能随便给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开口子[EB/OL].[2014-12-31].http://money.163.com/14/1227/19/AEGB3F2Q00254TI5.ht.《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涉及机动车限行的内容有2条,即第45条和第72条。第45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排放控制区域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第72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包括限制或者禁止部分机动车行驶等应急措施。”第72条是作为临时措施的限行,第45条是作为常态措施的限行。
其实,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并不是什么新话题,2008年奥运会后,该话题就曾被热炒如莫纪宏.机动车限行必须要有正当的公共利益[J].法学家,2008(5);余凌云.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是临时还是长效?——行政法学的视角[J].法学家,2008(5).
这次有关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争论与以往不同,除“一辆车变半辆车”的抱怨张维.北京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合法性存疑——专家称重大决策须保证程序正义[EB/OL].[2014-12-26].http://www.legalinfo.gov.cn/index/content/2014-11/28/content_5864328.htm?node=66689.
“3000亿民财被剥夺”的愤慨刘太刚.单双号限行与短线思维[EB/OL].[2014-12-26].http://www.cssn.cn/index/sy_sqrd/201412/t20141212_1441622.sht.
“拥堵之苦,一限了之”的调侃之外中财网.单双号限行成常态?北京不能“一限了之”[EB/OL].[2014-12-27].http://www.cfi.net.cn/p20141201000961.ht.
多了些法律层面的解剖。学者或从宏观的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入手,或从微观的征收规范出发,对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合法性作多维度分析谢玮.争议“单双号限行常态化”[J/OL].中国经济周刊,2014(47).[2014-12-31].http://www.ceweekly.cn/2014/1208/98298.sht;
张维.北京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合法性存疑专家:须程序正义[EB/OL].[2014-12-31].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28/c70731-26109600.ht.
法治原则过于宏观,争论双方很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知识论陷阱。相对于法治原则,引入比例原则倒有可能得出问题的唯一正解,但引入该原则的前提是解决一些前设性的问题,政府行为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如果涉及,政府行为是否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如果构成,这种限制是否正当[1]?只有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之后,才有引入比例原则的空间。毫无疑问,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必然涉及公民的财产权,处理此类问题的常规路数是用征收规范评判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只有回答了政府行为是否构成征收后,才能讨论比例原则的适用,进而讨论法治原则是否被违反。如果构成未经依法补偿的征收,则可直接推出政府行为不合法,没有比例原则适用的空间;如果不构成未经依法补偿的征收,则可导入比例原则,最终判断政府行为是否符合法治原则。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车辆单双号限行后,政府变相给予了车主一定范围的补偿参见2008年6月30日,北京市地税局《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停驶机动车减征车船税的通告》。
Apec会议结束后,政府没有给予补偿。将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之后,补偿根本无法操作。因此,如果单双号限行措施常态化构成征收,一定是没有补偿的征收。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构成征收?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并没有剥夺车主对汽车的所有权,不构成典型征收。是否构成管制性征收呢?即虽没有剥夺公民财产权,但管制事实上达到征收的效果?这需要复杂的法律解释作业。
即便在美国,管制性征收案件的裁判也一直是法官智识的博弈之地,围绕管制性征收案件的裁判,口水不断,标准频繁更迭。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公平补偿,私有财产不得因公用目的而被征收[2]。最早的征收概念事关物理性侵占——即政府在物理意义上侵入私人财产,随后发展出管制性征收的概念——即政府对私有财产的管制走得太远,产生了与物理性侵入相同的效果,也构成征收[3]。政府管制究竟走到哪里就算“太远”?政府管制的依据是政府拥有的警察权[4],警察权的行使和征收处于一条线段的两端——一端是警察权,另一端是征收权,警察权行使结束之处即征收出发之地,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来确定二者的界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6年讲了这样一段话:没有一套固定的公式,用以判断管制何时结束,征收何时开始。endprint
当然,征收的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一部分人承受了按照公平和正义原则本应由公众承受的负担,简称“超过公平份额的负担。”[5]但这个公式也只能在粗略的意义上适用于管制性征收——所有管制带来的收益不会均匀地流向所有纳税人,每个人因为管制承受的负担也不会全部一样,经济学甚至发明了“管制俘虏”的概念——管制总是服务于压力集团[6]。如果政府要为所有的管制支付补偿,政府将难以为继。于是,法院进退维谷:如果将征收规范的适用疆域无限扩大,源自警察权的政府管制无法进行;如果放任政府依据警察权的管制,“超过公平份额的负担”作为征收的构成要件又难以在逻辑上圆融自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寻觅到了“互惠”原理,以“平均利益互惠”概念助力政府管制逃脱过于宽泛的征收规范的羁绊,法理救赎了司法。
为清洁环境,道路畅通,将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收益为所有人共享,但负担却不均匀——对没有车的行人,没有带来任何负担;对用车少的人,负担较轻;对用车多的人,负担较重。有车一族能否因为承受了“超过公平份额的负担”,借用管制性征收概念,主张单双号限行构成管制性征收?互惠原理能否证成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的正当性,从而救赎管制?梳理美国法上互惠原理在管制性征收案件中的适用,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启迪。
一、利益、损害标准的式微与平均利益互惠原理的早期功能
十九世纪晚期以前的美国司法界,一直将利益、损害标准作为认定管制性征收的圭臬。如果政府的管制不是为了防止财产的损害,而是增进公共利益,则构成管制性征收;如果政府管制的目的在于防止财产的损害,公共利益不因此增进,则属警察权的行使[7]。其中的理由是:阻止妨害,被认为是财产权本身的界限,没有从财产权人的利益中析出一部分给公众,无需补偿;征收,被认为是从财产权中析出一部分利益给公众,因此需要补偿。
十九世纪晚期以前,因土地广袤,土地的利用率偏低,相邻土地用途不兼容的情形尚未大面积出现,政府的土地利用管制并非常态。但随着土地的密集开发,相邻土地用途之间的冲突开始呈现:砖厂周围出现大量的居住区,砖厂排放大量浓烟,影响居民生活;河流的上游地带建造了工厂,污染物流向下游,影响养殖……政府的土地利用管制日益频繁。财产的概念也在悄然变化:财产不是一个物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相互竞争的用途彼此依存的网[8]。土地不相容的用途极可能体现为用途客观上彼此冲突,又体现为达致财产的最好最佳用途需要彼此合作,即互惠。但自愿的互惠无法形成,于是政府作为第三者,强制执行互惠。此时,政府成了一个强制互惠的职业机构。执行这种互惠经常遭遇征收挑战——是不是为了一个私人的利益,强制另外一些人承担成本?如此一来,是否构成管制性征收?用以区分警察权行使和管制性征收的利益、损害标准此时显得捉襟见肘。一方面,不兼容的用途之间,很难说谁妨害了谁;另一方面,什么是阻止妨害,也极难界定。A打了B的脸一拳,也可以说成B的脸挡了A的拳头的道;[9]还有学者更为夸张,“即便是政府直接从我口袋里拿钱,也可能不是剥夺利益而是阻止妨害。这种妨害可能是:我倾向于消费而不是节约,我可能用于坏的消费而不是好的消费,也可能是:我有钱而别人没有。”[10]
警察权有轻盗窃罪的倾向,利益、损害标准却无法给这些灰色地带贴上标签,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证成政府管制的正当性。
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在库利的时代就出现了,但其原初的功能不是证成政府对财产的管制,而是限制政府对财产的管制。政府对财产的管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但仅仅用公共利益来限制政府管制的恣意显然不够,因为任何为了私人利益的财产管制也会带来公共利益,库利曾经指出:所有的旧房都翻修,所有的洼地都排水,所有难看之地都变得漂亮……这也满足了公众的审美要求。但普通法显然不能仅仅基于此种考量而允许征收不动产,必须进一步考量其他因素。如果管制产生的公共利益是附带的,就需要进一步证成管制的正当性:被管制的财产权人如果也从管制中得到了互惠的利益,则管制正当;否则,不正当库利是美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该段引文出自:ThomasM.Cooley,ConstitutionalLimitations660(Little,Brown,5thed.1883);转引自:LyndaJ.Oswald.TheRoleofthe“Harm/benefit”and“AverageReciprocityofAdvantage”RulesinaComprehensiveTakingsAnalysis[J].VanderbiltLawReview,1997,50(6):1490.
一个本用以限制政府管制财产的概念,在利益、损害标准遭遇困境时,却被用来证成政府对财产的管制。其机理何在?从平均利益互惠的早期功能来看,平均利益互惠是作为公共利益的补强要件呈现的——如果管制只能产生附带的公共利益,则公共利益不能单独证成管制的正当性,需要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补强。而政府土地利用管制也正是在这个节点遭遇尴尬:政府会不会借强制互惠之名,行管制性征收之实?平均利益互惠概念在此救场,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平均利益互惠概念在管制性征收案件中的引入:杰克曼诉罗森鲍姆案
首先提及平均利益互惠概念的案件是杰克曼诉罗森鲍姆案,该案发生在著名的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诉马洪案前一个月。案件起因是一部界墙法。
原告杰克曼有一座剧院,与被告罗森鲍姆的土地相邻。根据宾夕法尼亚界墙法,为保证消防安全,相邻房产之间应有界墙。罗森鲍姆开始修筑界墙,准备与杰克曼剧院原有的界墙连接起来。但杰克曼原有的界墙已经斑驳,安全性能大受影响。依照市政当局的命令,罗森鲍姆拆除杰克曼原有的界墙,重新修建。杰克曼剧院原有的进出口正好在界墙的中间,罗森鲍姆修筑界墙耽误了剧院的演出季。为此,杰克曼认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界墙法给其施加了负担,构成未经补偿的征收,且只是为了邻居的利益,不符合公用要件,遂诉诸法院,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霍尔姆斯法官书写法院一致意见:警察权的行使“在一些案件中得到支持,理由是我们所称的‘平均利益互惠,尽管在具体案件,利益不相等。”[11]霍尔姆斯法官主要追溯三个判例,来说明“平均利益互惠”作为不予补偿理由的正当性:沃茨诉霍格兰案[12]、弗布鲁克灌溉区诉布拉德利案[13]、诺贝尔州银行诉哈斯科尔案[14]。前两个案件的情形大体相似,沃茨诉霍格兰案事关共担排水系统修建费用立法的合宪性,弗布鲁克灌溉区诉布拉德利案事关共担灌溉系统修建费用立法的合宪性,原告均认为法律强迫他们加入一个合作的体系,并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费用,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诺贝尔州银行诉哈斯科尔案事关俄克拉荷马州存款人担保法的合宪性,该法要求各州银行按照其存款的一定比例缴纳一笔资金给政府,将来如有银行破产,就用这些资金赔偿存款人的损失。诺贝尔州银行不愿意加入这个合作体系,不愿支付这笔款项,认为该法强迫银行加入合作体系,并支付费用,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上述三个案件中,法院均认为,当事人虽然承担了费用,但从合作中获得了利益,没有遭受损失,因此,强制合作的立法属警察权行使的范畴,不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上述三个判例道出了“平均利益互惠”的内涵,却并未提出“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让人感到蹊跷的是,霍尔姆斯法官在杰克曼案中将上述三个判例的判决理由归纳为“平均利益互惠”,但究竟什么是“平均利益互惠”,其适用边界如何,霍尔姆斯法官语焉不详。更为诡异的是,霍尔姆斯法官经过长途的判例考证,第一次抛出一个模糊、没有定义的“平均利益互惠”概念,最后却并不以“平均利益互惠”概念来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界墙法,认为支持界墙法无须考量“平均利益互惠”问题,因为界墙的习俗在宾夕法尼亚州已持续两百年以上,足以应对依据第十四修正案的挑战[11]。endprint
霍尔姆斯法官判决杰克曼案时,只是将“平均利益互惠”概念作为补强理由,认为界墙习惯存续两百年足以支持受到挑战的法律,但“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却在后续案件中反复出现,成为消解财产权与征收权紧张关系的利器。为此,霍尔姆斯法官也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件中,霍尔姆斯以自豪的口吻说,“在判决意见中,我创造了‘平均利益互惠概念,我想,这个概念干净利落地表达了一些案件判决的理性。”[15]也许,霍尔姆斯法官清醒地看到,“平均利益互惠”概念刚刚提出,尚未获得广泛认可,但该概念又具有超强的解释力,故只让其在杰克曼案的判决中“灵光一闪”。学者在霍尔姆斯法官的灵光一闪中,捕捉到了“平均利益互惠”概念的内核:财产权人从政府管制中得到的利益是“特殊”的、可“甄别”的,大于政府管制给财产权人施加的负担,“平均利益互惠”原则“就其原始形式看,该规则意在说明,一项土地利用管制给被管制财产权人带来的利益大致等同于施加给他们的负担,这并不违反美国宪法。”[16]杰克曼案通过计算用以补偿管制负担的直接利益,在判例法上建立了平均利益互惠。在两个案例中,给请求人的具体、特殊利益可以甄别——界墙提高了安全性,给另一方提供了特殊的服务。两个案例中,成本小于利益,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求。这种“互惠”可以称之为“经济互惠”或“直接互惠”。
三、“经济互惠”原理的展开: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诉马洪案
1922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了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诉马洪案[3],该案一般被认为是管制性征收的肇始。也正是在这个案件中,平均利益互惠概念第一次在管制性征收认定中绽放光芒。
该案并不复杂。1878年,马洪与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签订一项契约,煤炭公司将地表土地转让给马洪,明确保留开采其地下煤炭的权利。马洪接受相应风险,并且放弃要求赔偿因开采煤矿而产生的损失的所有权利。宾夕法尼亚州于1921年5月27日通过《柯勒法》(KohlerAct),该法对地下煤炭的开采施加诸多限制柯勒法案规定,开采无烟煤不得造成房屋下陷的后果,但也允许存在某些例外情形。例如,煤矿所有权人拥有煤矿之上的土地,且该幅土地与其他人任何已增值的土地距离150英尺以上。
马洪遂以该法为依据,要求法院禁止宾夕法尼亚州煤炭公司在其土地下采煤,认为那会导致地面失去支撑,引起地表和房屋下陷。马洪称,不管煤炭公司基于契约能享有哪些权利,它们都已被《柯勒法》(KohlerAct)所剥夺[3]412。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认为《柯勒法》构成对自己财产的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违反美国宪法中的征收规范。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诉马洪案最相关的先例是普利茅斯案[17]。普利茅斯案涉及一项煤柱法案的合宪性,法院最终判决,该法案“要求每一个相邻的矿主对不予开采的煤层增加弯梁,是两个相邻矿主的利益互惠……这种管制不是为了另一个人利益而给一个人增加负担,而是无偏私、公平和理性的,是对受益的每一个矿主施加普遍的负担”[18],因而不构成征收。还是煤矿,还是安全,时过境迁,法院要做出与普利茅斯案相同的判决,认定不构成征收吗?霍尔姆斯法官几乎以先知的口吻言说了一个先验的命题:“平均利益互惠原理在很多案件中都被认识到了,该原则为多种法律提供正当性辩护。”[3]法院进一步认为,法院之所以判决普利茅斯案中不存在征收,是因为普利茅斯案中的系争法律提供了平均利益互惠:煤柱保证了雇员的安全,从而避免了给矿主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诉马洪案不同,《柯勒法》没有给煤炭公司提供平均利益互惠,因此,构成管制性征收。
其实,在普利茅斯案中,法院根本就没有提及“平均利益互惠”这个概念,将法院的判决理由理解为“平均利益互惠”,是霍尔姆斯对先例再解释的结果。在霍尔姆斯看来,只有将普利茅斯案的裁判要旨理解为“平均利益互惠”,才能找到该案与马洪案的连接点,也才能根据先例做出裁判。正是在是否提供“平均利益互惠”这个维度上,马洪案与普利茅斯案分野,法院才得出迥然有别的判决。从法院对马洪案的判决我们可以看出,“平均利益互惠”中的利益,指的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如果财产权人因政府管制遭受了财产上的损失,如果没有得到经济利益上的补偿,管制就可能被法院视为“走得太远”,从而构成管制性征收。
布兰代斯法官同样认为本案中的柯勒法没有提供“平均利益互惠”,但坚持认为煤炭公司开采地下煤矿构成“公害”,《柯勒法》禁止开采地下煤矿的目的是“防止公害”,属警察权的行使,因而不构成征收。布兰代斯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谈道:煤炭公司没有得到“平均利益互惠”,除非将这种互惠理解为“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3]422。布兰代斯阐述平均利益互惠原理时,其实略带调侃,将“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理解为“互惠利益”,更是戏语——“社会互惠”的概念几乎以“小丑”的形象登场。但布兰代斯法官这略带狡黠的机智,却歪打正着,成为法院将“经济互惠”概念拓展到“社会互惠”概念的序幕。有学者戏称:平均利益互惠概念其实是布兰代斯法官的私生子[16]1512。
四、“社会互惠”概念的嬗变:从佩恩案到安德鲁斯案
(一)“社会互惠”概念的含蓄登场:佩恩中央运输公司诉纽约市案[19]
1965年,为保护市内历史性地标,纽约市通过《地标保护法》,佩恩公司所有的中央车站随后被确定为历史性地标。1968年1月22日,佩恩公司与一家地产公司签订了一份租期为50年的租赁合同与转租协议,地产公司据此将在中央车站上建造一座高达55层写字楼。接着,地产公司和佩恩公司向地标保护委员会提交了两份建设许可申请,但均被驳回,理由是,在中央车站上建造写字楼会破坏历史地标的风貌。佩恩公司主张,地标保护委员会根据《地标保护法》,驳回其在中央车站上建造写字楼的申请,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案件最终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判决:适用《地标保护法》不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佩恩中央运输公司案确立了一系列认定管制性征收的规则,包括三步追问法——即经济影响、投资回报预期及管制的性质,此外还提出手段-目的标准。在衡量佩恩中央运输公司是否因为《地标保护法》的适用而遭受损失时,布伦南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里有这样一段话:《地标保护法》除了适用于中央车站外,“还大量适用于车站以外的建筑……保护地标有益于所有纽约市民和建筑,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活品质”[19]134,这种城市品位的提高也能泽被佩恩中央运输公司。法院多数意见虽没有直接使用“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但平均利益互惠的内涵在法院多数意见中游弋——伦奎斯特法官在反对意见中,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法院判决依据之一是“平均利益互惠”。伦奎斯特法官也依据“平均利益互惠”原则,认为中央运输公司“遭受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无法根据地标保护的利益得到补偿”[19]147,从而认定《地标保护法》的适用构成对佩恩中央运输公司财产的管制性征收。endprint
相对于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诉马洪案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在佩恩案中隐晦适用的“互惠”概念已经宽泛了很多。“互惠”已不限于经济上的“互惠”,还包括因“城市品位提高”而带来的利益“互惠”,这种“互惠”是间接的“互惠”,是因为管制有利于社会,然后有利于财产权人,被称之为“社会互惠”。
(二)“社会互惠”概念的登堂入室:安德鲁斯诉阿拉德案[20]
亦如前述,佩恩中央运输公司案虽然援引了平均利益互惠的基本原理,但没有直接适用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更没有直接援引“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而且,佩恩中央运输公司案判决的标准很多,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只是一笔带过。在安德鲁斯案和阿金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直接适用“社会互惠”的原理,认定财产权人从政府的管制中收获“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判决系争管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安德鲁斯案事关一项禁止出售羽毛的法律的合宪性。1962年的《鹰保护法》和1978年的《候鸟条约法案》(MigratoryBirdTreatyAct)对候鸟实施严格保护[21],禁止买卖候鸟及候鸟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比如羽毛),禁止买卖在法律实施之前已被屠宰的候鸟,违法者将遭受包括刑罚在内的制裁。阿拉德长期从事印第安手工制品买卖,这些手工制品上装饰了很多候鸟羽毛。在《候鸟条约法案》实施以前,阿拉德已经购进了大量此类手工制品。在《候鸟条约法案》实施之后,阿拉德因仍然出售这些手工制品,遭到刑事指控。阿拉德认为《鹰保护法》和《候鸟条约法案》部分条款违宪,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用大量的篇幅论证,虽然系争管制影响了阿拉德的财产价值,但并不因此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阿拉德虽然“承受了这些管制的成本”,但这是“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所必须承受的负担[20]67。换句话说,阿拉德因管制遭受的损失已被“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所冲抵,因此,两部法律的部分条款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五、“经济互惠”和“社会互惠”的纠结
“经济互惠”概念要求的“互惠”是直接的、财产利益上的“互惠”。“社会互惠”概念完全突破“经济互惠”的边界,是间接的、超越财产利益上的“互惠”:管制通过提升“社会利益”,间接惠及受到管制影响的财产权人;财产权人得到的互惠利益是“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一项管制如果满足了“经济互惠”的要求,就无需继续考量是否满足“社会互惠”的要求;如果一项管制不满足“经济互惠”的要求,还需考量是否满足“社会互惠”的要求。不满足“经济互惠”要求,但满足“社会互惠”要求的管制是否一定合宪?如果满足“社会互惠”要求的管制一定合宪,就意味着“社会互惠”概念彻底取代“经济互惠”概念——满足“经济互惠”要求的管制一定满足“社会互惠”要求,但满足“社会互惠”要求的管制却不一定满足“经济互惠”要求。“经济互惠”要不要为“社会互惠”规定边界?
(一)没有任何“经济互惠”的“社会互惠”不能证成管制合宪
“经济互惠”概念考量财产权人的负担和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负担远超收益,则不满足“经济互惠”要求;如果负担大致等于收益,则满足“经济互惠”要求。如果一项管制完全剥夺财产权,却满足“社会互惠”的要求,该管制仍然违宪。
霍德尔诉欧文案[22]:1983年,美国国会《印第安土地合并法》规定,太小的不可分土地(一宗土地中的份额小于2%,且收成上一年度少于100美元)的所有人不能将土地继承给后人,也不能遗赠给他人,应该交给部落,以整合起来产生更大的收益,并不予补偿[23]。欧文是南达科他州奥格拉拉苏部落成员,其父辈拥有一块土地,正好符合上述情形。欧文认为《印第安土地合并法》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在考量《印第安土地合并法》对当事人财产的影响时,也认为欧文等人尽管被剥夺了对土地的继承权,但作为部落成员,可以享受到“平均利益互惠”,其他人的小宗土地也被充公,而且,财产权人被剥夺的权利很少,土地整合后的收益远大于土地分散经营带来的收益。如果按照“社会互惠”的概念,《印第安土地合并法》中的相关条款就应被判合宪。但联邦最高法院忽然笔锋一转,从政府行为性质的角度展开论证,认为政府完全剥夺财产权人的权利,不属于警察权的行使,仍然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
随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卢卡斯诉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管理委员会案的判决中再次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点[24]。卢卡斯于1986年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县棕榈岛购买了两块住宅用地,准备建造单户住宅。然而,这却被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管理委员会禁止,依据是该州1988年通过的《海滨地区管理法案》。卢卡斯认为,海岸管理委员会的禁令,导致其土地价值全无,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卢卡斯的观点:“在土地的全部生产性或营利性用途都被禁止的情况下,仍然想当然地认为,这只是立法机关‘调整经济生活中的利益和负担,以此确保每个利害关系人都获得‘平均利益互惠,这种假设显然不太现实。”[24]1017
从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例可以看出,“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只适用于部分征收的案件,即只适用于裁判那些部分剥夺财产权人利益的案件:当一项管制彻底剥夺财产权人利益时,没有适用平均利益互惠的空间。如果将财产权人的损失理解为负担,从管制中流淌出来的利益理解为收益——这种收益可能是“经济互惠”,也可能是“社会互惠”,都应有特定的媒介——剩余的不动产。如果不存在剩余的不动产,或者虽然存在剩余的不动产,却被剥夺全部的财产利益——财产完全变为给公众提供服务的工具,财产权人事实上也难以居住和生活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受惠”。收益没有特定的指向,故平均利益互惠没有适用的空间。
(二)没有实质性促进政府目标实现的管制不能用“社会互惠”证成
诺兰诉加尼福利亚案[25]。诺兰夫妇在其拥有的一块临海土地上建造了住宅,但由于年久失修,他们决定拆除并建设新住宅。1982年2月25日,他们向加州海岸委员会提交了海岸开发许可申请,但却被告知要想获得开发许可,他们必须让出一块土地供公众通向海边。诺兰夫妇反对附加的条件,认为这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endprint
四名发表反对意见的法官则以平均利益互惠原则为由支持附加的条件。布伦南法官认为,诺兰得到许可的利益大大超过让出一点土地供公共通行带来的损害。同时,海岸委员会也要求其他土地所有人让出一点土地,这也便利了诺兰去海岸的其他区域。从“社会互惠”的角度看,诺兰得到了“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但多数意见却认为,“如果土地用途管制‘实质性促进合法的政府利益,而且没有完全‘剥夺所有者对其土地的经济可行性用途,它就不构成征收。”[25]834多数意见认为,海岸委员会要求诺兰夫妇让出一块土地供公众通行,并不能实质性促进政府目标的实现,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
从该案的多数意见可以看出,社会互惠其实也是收益成本的考量。如果社会得到的利益少于财产权人支付的成本,财产权人从社会互惠中得到的利益必然小于其承受的负担,本案事实上以成本收益分析法描绘出社会互惠的边界。
(三)过于严苛的管制不能用“社会互惠”证成
多兰诉蒂加德市案[26]。多兰的一宗土地位于蒂加德市中心商业区的梅恩街,沿溪流建造了一个店铺,还剩一些空地。为扩大店铺面积,多兰向市政府提出重新开发该地块的许可申请。市规划委员会要求多兰捐出部分土地用于改进溪流沿岸的暴雨排水系统,还要求她捐献土地另一侧的部分面积用作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之后才能批准其许可。多兰认为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斯蒂文斯法官认为,市规划委员会要求多兰捐献土地,可以“拓宽水路,可以大幅便利运输”,政府的管制合宪。斯蒂文斯法官采用的路径显然是“社会互惠”,虽然只有多兰被要求捐献土地,但多兰捐献土地后,便利了公众,也便利了自己,市规划委员会的行为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同样认为市规划委员会的管制是为了公共目标,而且要求多兰捐献土地与促进合法公共目的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但认定管制过于严苛,“虽然不要求负担和利益之间有精确的数学上的关系……但该市应该做出一些努力证明其认定的结论。”[26]395,396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判决:市规划委员会的行为构成管制性征收。
马洪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曾以管制“走得太远”为由认定政府行为构成管制性征收,多兰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几乎以相同的句式,以管制“过于严苛”为由认定“满足社会互惠”要求的政府行为构成管制性征收。
“社会互惠”与“经济互惠”有相通之处:被管制财产的所有人都得到了利益,而且得到的利益大致等同于自己承受的负担。只不过财产权人从“经济互惠”中得到的利益是直接的、财产性的利益,而从“社会互惠”中得到的利益是间接的、不限于财产性利益。“没有实质促进政府目标实现”的管制因财产权人得到的利益太少,不能用“社会互惠”证成;“过于严苛”的管制则因财产权人付出得太多,同样不能用“社会互惠”证成。
六、“平均利益互惠概念”正当性的补强
“平均利益互惠”概念之所以能证成管制的正当性,使其免于征收规范的拘束,原因在于:管制必须对财产权人产生经济影响,即克减其财产利益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构成征收。但法院经由“平均利益互惠”原理认定,管制虽然给财产权人增加了负担,但由于财产权人也从管制中得到了利益,故政府管制不构成征收。但这种论证路径本身也面临正当性追问,尤其是“社会互惠”概念——模糊当事人负担和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证成?是否存在脱离管制性征收三要素的论证方法?
在多兰案前以及随后的一些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用大量的篇幅论证“平均利益互惠”概念的正当性。
(一)类比征税证成“社会互惠”概念的正当性:启斯东烟煤协会诉德本迪克提斯案[27]
宾州立法机关于1966年制定的《烟煤矿下陷和土地保护法案》第4条规定:禁止在下述三类建筑下方开采,以防造成下陷损害:公共建筑和通常由公众使用的非商业性建筑;居所;墓地。法案还授权宾州环境资源局制定和执行一项综合规划以阻止或尽量减少下陷事故。环境资源局根据该法案授权,要求受法案第4条保护的建筑物下方50%的煤炭储量不能开采。
1982年,启斯东烟煤协会认为,环境资源局的管制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并认为本案可直接适用马洪案的规则。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定政府管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理由之一就是“平均利益互惠”:《烟煤矿下陷和土地保护法案》要求煤炭公司将50%的煤遗留在地下,以支持地表建筑物,“每个人都因这种限制承受了负担,但都从对别人的限制中收获了利益。”[27]491至于财产权人承受的负担与得到的利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法院在这段话的脚注中给出了解释,基本的思路是将征收与征税类比,“征收规范从来就不要求美国各州或各法院讨论一个具体的个人,在某一规则下承受的负担是否超过了其享受的利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从其纳税中享受到了足够的利益,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他纳税的数额超出他从中享受到的利益而请求补偿。”[27]491,n.21.
美国法上,征税行为一般不受征收规范的约束,因为征税行为很难放置在负担“不合比例”原则的语境下解释。也就是说,公民从纳税中获得的收益基本上无法在定量的意义上考证[28]。启斯东烟煤协会案中,法院将征收与征税相比,这意味着法院将财产权人的负担与收益之间的联系充分模糊化,拒绝考量财产权人损失与收益之间的联系。法院以征税的正当性类比“平均利益互惠”概念的正当性,巧妙转移了“平均利益互惠”正当性的证成负担。
(二)以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证成“平均利益互惠”概念的正当性:圣莫雷酒店诉旧金山案[29]
圣莫雷酒店将部分客房改为酒店式公寓,减少了客房数,这意味着减少了旧金山接待游客的能力。为此,旧金山市和旧金山县依据《酒店转化条例》(HotelConversionOrdinance),要求该酒店支付一笔开发影响费。圣莫雷酒店认为该规定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支持政府管制,联邦最高法院维持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判决。endprint
法院首先认定,财产权人从管制中得到的利益不一定是直接的、经济性的利益,也可以是间接的、抽象的,即“在一个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法院认为,旧金山的管制令可以“让每个财产权人从中受益”,通过使旧金山社会和文化多元,吸引游客,间接有利于度假酒店。法院接着论证,财产权人应该为公共利益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平均利益互惠不要求精确平衡因一部法律承受的负担和收获的利益,也不要求所有财产权人的负担精确的平等,但在一个利益——经济利益或非经济利益——连锁的体系中,一个民主社会的参与者可能都希望得到,这也就要求每个人为了公共利益,一直要牺牲一些利益——经济利益或非经济利益。”[30]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德国基本法中的规范,美国宪法并无相应的法条。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将“公用”作为正当化征收的理由,法院进一步将其拓展为认定某些管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的依据。法院将财产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放在一个交互的语境中考量,认为财产权人从公共利益中享受到了好处,就应该为此做出财产上的牺牲,这几乎与德国法上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概念相通德国法也认为,财产权也从社会中得到了收益。(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J].中国社会科学,2012(9):100-119.)
(三)从民主原则证成“平均利益互惠”概念的正当性:塔霍-塞拉保护委员会诉塔霍区域规划局案[31]
塔霍湖盆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是内华达山脉北部断层形成的淡水湖。为保护塔霍湖的自然风景,两州立法机关于1968年共同通过《塔霍区域规划协定》(1980年修正),成立塔霍区域规划局。1981年6月25日,塔霍区域规划局为保护塔霍湖区风景,根据《塔霍区域规划协定》及其修正案,决定暂停许可对该地区的开发,持续时间为32个月。塔霍湖保护委员会是代表塔霍湖盆地业主的非营利组织,近2000名业主在1980年《塔霍湖区域规划协定》修正案生效前就已购买塔霍湖的自然风景内的土地,拟建造养老或休假住宅。业主认为,塔霍区域规划局暂停许可开发风景区内的土地,相当于在一定期限内全部剥夺了财产的经济用途,构成未经公平补偿的征收。塔霍区域规划局颁发暂停开发许可的禁令有明确的规范依据,即《塔霍区域规划协定》修正案的相关条款,争议的焦点是《塔霍湖区域规划协定》修正案相关条款的合宪性。案件最后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于2002年4月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塔霍区域规划局依据《塔霍区域规划协定》修正案的相关条款颁发禁令不构成管制性征收。
法院认为:推迟许可或者临时限制许可是正当的警察权行使,根据分权原则,法院不能对此置喙,因为改变禁令就意味着变更立法,“要对法律做如此重大的变化,应是立法的产物,而不是司法的产物……32个月暂停开发正是为了让大家充分讨论,避免做出草率低效的决定”[31]335;而且,规划局的禁令会使塔霍湖的湖水更加清澈,业主财产的价值会随之增长,业主从政府的管制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利益互惠”[31]341;最后,法院拒绝判断禁令期限是否适当,至于业主从管制中得到的利益能否补偿其损失,“将这一任务交给立法机关更合适。”[31]342
在塔霍湖案中,法院没有简单地“以案论案”,而是“以案说法”,将平均利益互惠作为法院判断管制性征收的一般立场。也就是说,法院做了一个近似于“合宪性推定”的判断——多数情形下,管制都可以形成互惠利益,不构成征收。法院不要求政府提供量化的、经验的数据,以证明互惠利益的存在,认为将其交给立法机关判断就可以了。这也就意味着,法院可能更宽泛地适用“平均利益互惠”原则。
七、结语:互惠理论对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管制措施的救赎
如果北京将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常态化,互惠原理能否将该项管制从征收的泥沼中救赎出来?
如前文所述,不合比例负担是判断管制是否构成管制性征收的一般标准,即“一部分人承受了按公平和正义原则应由全体公众承受的负担”,就构成管制性征收。政府管制面临的悖论是:任何管制流淌出来的利益都不是匀质分布的,同样,每个社会成员承担的成本必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承受不平等的负担无规范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如果只要比别人多承受了一点负担,就可以要求补偿,则政府无以为继。但政府无以为继不能作为让财产权人多承受负担的正当性理由:财产权是先在的,不能以政府的存续为由证成对财产权的侵蚀。于是,“平均利益互惠”的概念登场。这事实上是一个模糊财产权人负担和收益比例的概念工具,旨在磨平财产权规范过于刚性的棱角,给政府管制留下必要的空间。但另一方面,互惠概念又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将根本颠覆财产权规范。于是,我们需要利用互惠原理在两极之间寻找平衡点。寻找平衡点的过程是一个计算的过程,大体上包括两个公式:
经济互惠公式:“一项管制给财产权人带来的利益大体上等同于施加给他们的负担,该管制措施不违反宪法,”[16]且无需补偿。按照经济学更刚性的语言,如果管制的变化不仅给财产施加了负担,而且带来了直接的利益,不构成需补偿的征收。
社会互惠公式:“如果一项管制给社会带来的利益粗略地等同于给财产权人施加的负担,不构成需补偿的征收。”[16]因为受到管制的土地所有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与其他成员一样平等受益。不构成需补偿的征收。
从上述两个公式可以看出,“平均利益互惠”概念采用的是效益标准:“经济互惠”概念适用帕累托改进原理——“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境况变得更好”[32],“社会互惠”概念适用卡尔—希克斯改进原理——“只要某种变革提高生产效率,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受损者就会自然地得到补偿。在长时间的一系列政策改变中,这次变革使这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下次变革则可能使这部分人受损而另一部分人受益,相互抵消后益大于损,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大。”[33]endprint
我们可以用上述两个公式分析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常态化。
经济互惠公式:如果在车主中考量利益和负担分配的比例关系,则符合经济互惠公式:单号车不出行,双号车出行更通畅;双号车不出行,单号车出行更通畅。但我们显然不能仅在车主中考量利益和负担分配的比例关系——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常态化的目的除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之外,还有减轻环境污染,受益人不限于车主。在车主和没有购买汽车的市民之间,利益和负担的分配不成比例——车主付出了更多的负担(一辆车变半辆车),但享受的利益却是一样的——空气比以前更清洁,出行比以前更通畅。车主的损失无法从没有购买汽车的市民那里得到补偿——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并未损害没有购买汽车的市民任何利益。
社会互惠公式: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常态化能使空气更清洁,环境更美丽,社会总体福利增加,车主也能从中得到收益,即从管制中间接受益,即收获“在文明社会中生活和经营的利益”。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是否为不能带来任何“经济互惠”的管制?如果是,则不能认定该管制符合社会互惠公式;能否实质性促进政府目标实现?如果不能,也不符合社会互惠公式;该管制是否过于严苛?如果是,还是不符合社会互惠公式。如上文所述,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并不是没有带来任何经济互惠,道路通畅也会减少车主出行的成本;根据生活经验,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可以部分减少车辆使用率,从而有利于道路通畅,同时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即能实质性促进政府目标实现;该管制没有将车主的财产价值减少到几乎为零的程度,不能认定为过于严苛。因此,汽车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符合社会互惠公式。
互惠原理是一个“魔法字眼”[34],我们无论怎样将其公式化,都无法达致数学所要求的精确度。但“无论何时,我们创立一个法律规则时,都要容忍在边缘处,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不会因检验所有法律规则的某种边缘分类问题而站立或坍塌。”[35]互惠原理在讨论政府管制是否构成征收时出场,扮演救赎者的角色,并不是要置换征收法的一般原理,也不旨在颠覆财产权,而是削平财产法和财产权过于刚性的棱角,避免社会和个人、权力和权利陷入“双输”的窘局。
当然,对于汽车单双号限性措施常态化的分析还有很多其他进路,互惠原理仅仅能够论证:该项管制措施不构成需补偿的征收。不构成管制性征收不意味着一定符合比例原则,也不意味着一定就符合法治原则。要论证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常态化的合宪性和合法性,还需要其他的法律解释作业。
参考文献:
[1]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J].法学家,2008(1):134-139.
[2]“Norshallprivatepropertybetakenforpublicuse,withoutjustcompensation.”U.S.CONST.AMEND.V.
[3]PennsylvaniaCoalCo.v.Mahon,260U.S.393,415(1922).
[4]刘连泰.政府对拟征收不动产的管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2):101-105.
[5]Armstrongv.UnitedStates,364U.S.40,49(1960).
[6]王俊豪,鲁桐,王永利.西方国家的政府管制俘虏理论及其评价[J].世界经济,1998(4):26-28.
[7]ChristopherSupino,ThePolicePowerand“PublicUse”:BalancingthePublicInterestagainstPrivateRightsthroughPrincipledConstitutionalDistinctions,inW.Va.L.Rev.110(2007-2008).
[8]JosephL.Sax.Takings,PrivateProperty,andPublicRights[J].YaleLawReview,1971,81(2):150.
[9]WalterBlock,GuillermoYeatts.TheEconomicsandEthicsofLandReform:ACritiqueofthePontificalCouncilforJusticeandPeaces“towardaBetterDistributionofLand:TheChallengeofAgrarianReform[J].JournalofNaturalResources&EnvironmentalLaw,1999-2000,15(1):60.
[10]JedRubenfeld.Usings[J].YaleLawReview,1993,102(5):1099-1100.
[11]Jackmanv.RosenbaumCo.,260U.S.22,30(1922).
[12]Wurtsandanotherv.Hoaglandandothers,Comrs,etc.114U.S.606(1885).
[13]FallbrookIrrigationDist.v.Bradley,164U.S.112(1896).
[14]NobelStateBankv.C.N.Hasekell,G.W.Bellamy,J.P.Connors,J.A.Menefee,M.E.Trapp,andH.H.Smock,219U.S.104(1911).
[15]MarkD.Howe.Holmes-LaskiLetters:TheCorrespondenceofJusticeHolmesandHaroldJ.Laski1916-35[M].NabuPress,1953:466.endprint
[16]LyndaJ.Oswald.TheRoleofthe“Harm/Benefit”and“AverageReciprocityofAdvantage”RulesinaComprehensiveTakingsAnalysis[J].VanderbiltLawReview,1997,50(6):1489.
[17]PlymouthCoalCo.v.Com.ofPennsylvania,232U.S.531(1914).
[18]Commonwealthv.PlymouthCoalCo.,232Pa.141,149(1911).
[19]PennCentralTransportationCo.v.NewYorkCity,438U.S.104(1978).
[20]Andrusv.Allard,444U.S.51(1979).
[21]BaldEaglesProtectionAct,§1etseq.,16U.S.C.A.§668etseq.;MigratoryBirdTreatyAct,§2etseq.asamended16U.S.C.A.§703etseq.
[22]Hodelv.Irving,481U.S.704(1987).
[23]IndianLandConsolidatedAct,§207,asmended,25U.S.C.A.§2206.
[24]Lucasv.SouthCarolinaCoastalCouncil,505U.S.1003(1992).
[25]Nollanv.CaliforniaCoastalCommission,483U.S.825(1987).
[26]Dolanv.CityofTigard,512U.S.374(1994).
[27]KeystoneBituminousCoalAssnv.Debenedictis,480U.S.470(1987).
[28]刘连泰.宪法上征收规范的效力是否及于征税:一个比较法的观察[J].现代法学,2009(3):119-126.
[29]SanRemoHotelv.CityandCountyofSanFrancisco,545U.S.323(2005).
[30]SanRemoHotelL.P.v.CityAndCountyofSanFrancisco,27Cal.4th643,675(2002).
[31]Tahoe-SierraPreservationCouncil,Inc.v.TahoeRegionalPlanningAgency,535U.S.302(2002).
[32]厉以宁,吴易风,李懿.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5.
[33]曾艳玲主编.英汉西方经济学词典[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428-429.
[34]WilliamW.Wade&RobertL.Bunting.AverageReciprocityofAdvantage:“MagicWords”orEconomicRealityLessonsfromPalazzolo[J].UrbanLawyer,2007,39(2):364.
[35]RichardA.Epstein,Takings.PrivatePropertyandthePowerofEminentDomain[M].Bost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11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