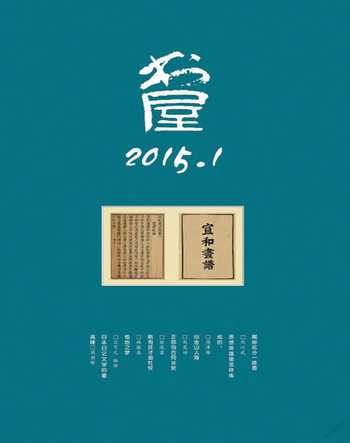中国历史上的“吃货”
曹亚瑟
吃惯中国饭菜的人,再去吃英国的黑暗料理,多半是会觉得难以下咽的。那些海外华夏游子浓浓的乡愁,我想更多是那只“中国胃”没有得到满足的失落感,因而被一缕缕地牵引至故乡的美食,幻化为一碗烩面,一碟鱼香肉丝,一钵老火靓汤,一屉小笼汤包……
现在流行当“吃货”,“吃货”已从“饭桶”转变为一种能吃、会吃的崇高赞誉。能够做一个无所顾忌的吃货,吃遍各地美食,吃得口舌生津,吃出意境门道,吃得心满意足,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然而,当吃貨并非易事,吃货的前提是要有钱、有闲,标准是能吃、会吃,还懂吃,知道什么时候吃哪些,能说出吃的道道来。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吃货”,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胜数的。
历代帝王是“饭桶”的不少,真正能成为“吃货”却不多。帝王能调动的资源多,天下美食都能为其享用,但他并不一定懂吃、爱好吃、欣赏吃。比如周天子,在饮食方面摆的谱可谓大矣,据《周礼》记载,仅负责王室饮食的膳夫就有一百五十二人,再加上庖人、内饔、外饔、亨人、兽人、渔人、鳖人、猎人、食医、酒正、酒人、凌人、笾人、醢人、酰人、盐人,每种职位都有数人至三百人不等,总计有一两千人,那是一个庞大的厨师班底,非蕞尔小国的大王可比。但周天子并没有美食家的清名,因为他要边吃边盯着江山是否旁落,吃得并不能忘我、恣意。
夏末商初,伊尹对国王商汤言说拿下天下的必要性时,就以各地丰阜的物产相诱引,告诉他只要对天下施以仁义之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那么这全天下的美食都非他莫属。伊尹,是被现在的餐饮行拜为厨神的,他厨子出身,以厨艺之道治国,自有其高妙之处;但如果比较商汤和伊尹的话,我以为商汤是“吃货”而伊尹不是,汤是因为爱吃才取得天下的。
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中论述过厨子的重要性:“我们的生命并不在上帝的掌握中,而是在厨子的掌握中。因此,中国绅士都优待他们的厨子,因为厨子是在掌着予夺他们的生活享受之大全。”但厨子只是我们通往饮馔自由王国的工具,厨子本身并非“吃货”,他烹饪的菜肴要经过食客的检验。
鸿门宴、杯酒释军权,是历史上两个著名的政治饭局,一个发生在秦末,一个发生在宋初,那都是借饭局之名除掉异己威胁的圈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饭桌之上又岂容他人分食?朕者,特点就是吃“独食”。朕赏你吃一口,是你的福分;想觊觎朕的江山,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
所以,争天下的事还是让“肉食者”谋之吧,对百姓来说,过好柴米油盐的寻常日子才是最真实的。在《诗经》的《国风·豳风·七月》中,每个月该吃哪些新鲜果蔬,百姓们早就合计好了:“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然后,再弄个兔头,来个“一兔三吃”:“幡幡瓠叶,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看看,这也是十分惬意的吧?
孔老夫子已经被命名为“丧家犬”,我再给他加上个“吃货”的头衔当也不会挨扁吧。他奠定了儒家饮食及礼仪的基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他对饮食的讲究已经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是最早的生态主义者和食品安全的保卫者。
屈原,那绝对是个懂行的“吃货”,不然不会连招魂都把各色美食亮出来,吸引鬼魂回到人间:“我的五谷结穗长又长,菰米做的饭正香。鼎镬中都是煮好的肉啊,五味调和扑鼻香。肥嫩的黄莺、鹁鸠、天鹅肉,伴着鲜美的豺肉汤。魂啊,归来吧!美馔佳肴任你品尝。新鲜甘美的大龟、肥鸡,再加上楚国的鲜酪浆。快把猪肉剁剁碎,再拿炖狗肉蘸上酱,香草切细味喷香。吴国的香蒿做酸菜,吃起来浓淡正恰当。魂啊,归来吧!任你选择哪一样。烤乌鸦,蒸野鸭,还有鹌鹑炖成汤。油煎鲫鱼麻雀羹,多么爽口齿间香。魂啊,归来吧!各种美味任你品尝。”这种诱惑,任它什么鬼魂都挡不住啊。
南朝时的周颙虽然只吃蔬食,但他是以审美的标准来对待吃的,极讲究蔬食的品种和色彩搭配。他在山中常吃的是“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最为推崇的蔬菜是“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这里不仅有意境美、色彩美,摆在桌上直接就是一幅画,难得的是读起来还有音节之美。
到了唐朝,诗人“吃货”比比皆是,但我最为推崇的是白居易,他的那首“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足以完胜其他诗人而坐上唐代的头牌。平时,他也是“晓日提竹篮,家童买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极有“吃货”的情趣;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与吃配套的享受,“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美好的一天,吃吃酒喝喝茶,睡到自然醒,仙人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嘛。
宋朝是一个精神和物质都极为丰饶的时代,从《东京梦华录》到《梦粱录》、《武林旧事》里都记录了绵延不尽的酒楼脚店,各式各样的食味和羹,“吃货”更是层出不穷。有两个人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是苏轼,一个是陆游。
且不说苏东坡写下的《老饕赋》、《菜羹赋》、《酒子赋》、《猪肉颂》,单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菜肴就有“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玉糁羹”、“东坡芽脍”、“东坡饼”、“东坡酥”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很多是牵强附会,但也说明了苏东坡在美食界的影响之巨。苏东坡在任何险恶的政治境遇下,都能保持宽厚、达观的心态,同时因地制宜,满足一点微博的口腹之欲,发之为让人馋涎欲滴的诗文。他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黄菘养土羔,老楮生树鸡。未忍便烹煮,绕观日百回”、“鲜鲫经年秘醽醁,团脐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活如酥,先社姜芽肥胜肉”、“欹枕落花馀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等诗句早已脍炙人口,咏之足可下酒。
陆放翁虽是一员文官,却总想着收复北方大好的河山,无奈只有在辗转全国的播迁中,留下上万首诗作,其中就有两三百首与饮食相关。“霜余汉水浅,野迥朔风寒。炊黍香浮甑,烹蔬绿映盘”、“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唐安薏米白如玉,汉嘉栮脯美胜肉。大巢初生蚕正浴,小巢渐老麦米熟”,充满了对新摘园蔬的热爱和对鱼米芳泽的眷恋;“洗君鹦鹉杯,酌我蒲萄醅。冒雨莺不去,过春花续开”、“团脐霜蟹四腮鲈,樽俎芳鲜十载无。寒月征尘身万里,梦魂也复醉西湖”,又有把杯一醉的痴迷和壮志未酬的遗憾。这里吃的就不仅是美食,而是情怀了。
南宋的林洪也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吃货”,他不仅懂吃,而且对吃的主人公有一种“理解的同情”,他的《山家清供》不只是保存了宋代的山野食谱,更有许多关于吃的故事、妙喻,读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有明一代,张岱是个大大的“吃货”,应该是无人质疑了。他那被人引用的滥熟的“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已成为他的招牌菜。但从《老饕集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岱确实在饮食一道上理论功夫不浅,他对各地名产方物的了解,对煮蟹持螯的痴狂、乳酪制作过程的稔熟,都非一般段位的美食爱好者所能相比拟的。
明代《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和清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可是两个资深“吃货”,无怪乎读这两本书,有一半精力是在读菜单。《金瓶梅》里面的市井食单,没有三二十年的浸淫是写不出来,“一根柴禾炖猪头”、“糟螃蟹”等等放到现在也都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同时,看着那“一碟头鱼、一碟糟鸭、一碟乌皮鸡、一碟舞鲈公”,以及“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炸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能不勾起你浓郁的食欲吗?而《红楼梦》记述的是钟鸣鼎食之家的生活,看了难免让人感觉高高在上,那“茄鲞”、“烤鹿肉”、“燕窝粥”都不是平常人的吃食,大观园的少爷小姐们把螯对诗、猜拳行令也都透着一个“雅”字,我辈俗人恐怕是消受不起的。
真正雅中带俗的是李渔和袁枚,也是清朝两个最有名的“吃货”了。李渔最讲究食物的清淡,他对蔬食的要求是“清,洁,芳馥,松脆”,最为推崇的是笋和蕈。他认为笋“能居肉食之上者,只在一字之鲜”,而蕈能吸收“山川草木之气”,所以食之无渣滓。而袁枚不仅是个知味之人,且是个高超的烹饪理论家,他的“作料须知”、“搭配须知”、“火候须知”、“器具须知”、“上菜须知”等,现在拿到五星级大酒店,都可以直接当作培训教材的;他所欣赏的菜肴,越是寻常的食材,就越是要用几十种海鲜、香蕈和鸡汤来“众星拱月”,以吊出奇味。比如,他极为得意的“蒋侍郎豆腐”、“杨中丞豆腐”、“王太守八宝豆腐”,要么是用大虾米一百二十个或小虾米三百个加秋油一并煨出来;要么是把鸡汤和鳆鱼的味道浸入到豆腐中;要么是用香蕈屑、蘑菇屑、松子仁屑、瓜子仁屑、鸡屑、火腿屑,与豆腐一起在浓鸡汁中煨制。而这些鸡鱼虾屑的精华和鲜味被豆腐吸收后,则要统统丢掉,以免夺了豆腐的风采。对此,我們只能说:子才,你真能吃,也真能造!
当然,我前面说过,现在“吃货”是个褒义词,是人人奋而争当的。所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吃货”是很有必要的,这里列举的,只是史海的几朵浪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