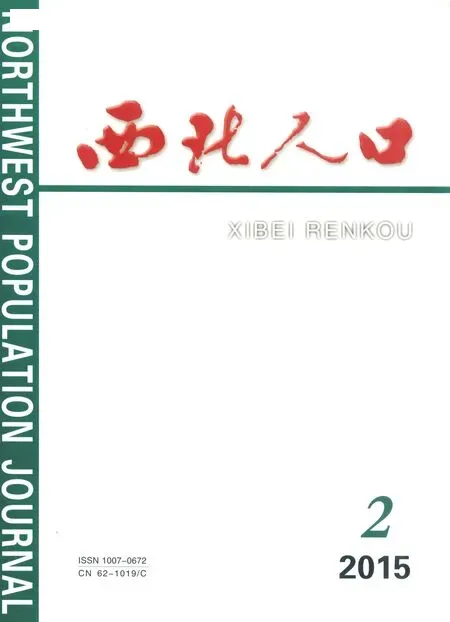基于时间序列的角度对劳动力流动成因的实证研究
吴鹏(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沈阳 110036)
基于时间序列的角度对劳动力流动成因的实证研究
吴鹏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沈阳 110036)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政府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劳动力的流动量不断增加,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本文利用1978年到2012年的年度数据,运用动态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成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得出: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社会因素将日益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制度和政策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逐渐减少。
收入差异;流动成本;人力资本;制度因素
一、文献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Lewis)第一次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劳动力流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被称为劳动力流动最著名的理论。他认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而现代工业部门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投入的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的流向工业部门[1]。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强调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他们认为,农业部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把技术进步和资本的积累看成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的两个途径,同时提出了人口的增长对劳动力流动会产生阻碍的作用,确定了临界最小努力准则[2]。托达罗(Todaro,1969)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于预期收入引起的,城市创造就业通过提高预期收入使得更多的劳动力迁移,而不是由当前的收入引起的。因此,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决策理论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即城乡实际工资差异和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托达罗模型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的增加,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就会大于零,此时就会引起劳动力流动。而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出现稳定状态时是绝对存在的,因此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异[3]。
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的成因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宏观政策变化尤其是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制度因素、经济因素、以及劳动力个人和家庭特征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赵耀辉(1997)利用四川的数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得出农村外出劳动力大都是年轻、未婚或者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部门间流动有显著的影响,但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区部门间的转移要比外出部门间流动的影响要大的多。因此,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劳动者倾向于在本地区部门间流动[4]。蔡昉(2001a)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的主要推动力是人均耕地资源较少和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缺乏,而对于农村劳动力是否流动以及流动的方式则主要的取决于对流动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同时,蔡昉也提出,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是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之一[5]。蔡昉(2001b)就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得出传统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户籍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得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放松了许多,但是中国的改革并未完成,制度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6]。朱农(2005)基于多个logit计量模型,就城镇GDP等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镇人均GDP越高,越能吸引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农村人均GDP越低,则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出意愿越大[7]。程名望、史清华和徐剑侠(2006)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递推方法,同时结合 “推—拉理论”通过建立模型对中国劳动力流动进行理论分析,得出城镇的拉力特别是城镇工业化的技术进步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他们利用宏观经济变量的logit模型和微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他们提出,中国要加快劳动力流动,就必须提高城镇工业化的技术进步,特别是消除户口、就业机会等歧视,提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8]。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受到宏观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劳动力自身特征和社会文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这都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复杂性和阶段性。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成因呈现出多元化和动态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尝试从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个方面对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分析
(一)经济因素分析
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深,经济发展速度日益的加快,区域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使得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也呈现出日益活跃的态势。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对于劳动力是否流动来说也是成立的,因为劳动力也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与否的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差异、流动成本、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收入差异。当前,中国劳动力区域流动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由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流入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城镇地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扩大直接导致了收入水平差异的扩大。托达罗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主要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只有劳动力预期收入增加时,才会引起劳动力流动,否则不会引起劳动力流动。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主要是为了追求个人效用水平的最大化,最终驱使劳动力向经济发达且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流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以及优惠的政策倾向等,使得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导致地区间和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异,2012年城市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几乎为农村地区人均纯收入的两倍多,巨大的收入差异正是引起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2.流动成本。与收入相对应的是成本,劳动力是否流动,也取决于流动总成本的大小。当流动总成本较大时,劳动者一般会选择留在原地,而不选择流动。相反,当流动总成本较小时,劳动者一般都会选择流向经济发达的地区。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可以分为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流动的经济成本主要包括显性成本和机会成本。流动的显性成本主要是指,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消耗掉的费用和时间,例如交通费用、在流入地的生活费用等等。机会成本是指劳动力放弃了其在流出地的工作以及福利等所造成的成本。这两大类都是流动的经济成本,是可以通过货币价值很好度量的成本。然而,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非经济的成本,主要包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劳动力流入到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地域的文化差异、生活习惯差异、在流入地的孤独感,以及一些地区歧视等,都会给劳动力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风险成本主要是,由于流动的劳动力大多技能比较低、文化素质比较低,增加了其在流入地寻找工作的风险,即使暂时找到工作,也会面临着失业的风险等。
3.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配第—克拉克定理可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使得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的上升,有效地提高了其容纳劳动力的数量和规模,进而也对劳动力的流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流动的劳动力角度来看,由于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中国大多数的流动劳动力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其流入经济发达的地区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给劳动力提供较大的就业空间,从而对劳动力流动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认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会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则有更多的劳动需求,从而造成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在国家政策倾向以及自身拥有的有利条件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以及资本投入等进一步加快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相对来说其提高的幅度比较小,释放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造成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地区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流动。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劳动力的流动。
(二)社会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成因,就很有必要研究社会因素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影响。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家庭抚养负担、城市的人口密度、以及城市的失业率。
1.人力资本。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其流动的意愿也就越大。较高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素质修养、以及专业的技能知识等,这些更有益于劳动力的流动。主要表现为:
首先,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可以有效地减少其流动成本。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对是否流动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并且有能力依据自身的条件做出合理的决定。同时,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拥有比较好的知识基础,能够花费比较少的时间寻找工作,更容易接受岗前培训。较高人力资本拥有比较广泛的知识,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可以很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从而减少其流动所产生的成本。
其次,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增加了其就业机会。人力资本主要是依附在劳动力身上的教育程度、专业技能等,这些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就业范围、收入水平、其生存能力、以及其培训时间和适应工作的能力。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劳动力可选择就业的岗位比较多,收入水平以及福利水平相对比较好,能够较快的接受很好的培训,进而很好的适应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其工作的稳定性,增加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更有益于劳动力流动。
最后,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更容易接受世界先进的知识和技术。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不断与世界接轨,需要更多的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因为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拥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有较高的开放性和探索性,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接受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的能力比较强,更容易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2.家庭抚养负担。家庭抚养负担可以通过家庭抚养比来进行很好的衡量,家庭抚养比是指,在家庭成员当中,14岁以下(含14岁)和65岁以上(含65岁)的人口数量占15岁至65岁间的人口数量的比例。若家庭抚养负担越重,意味着家庭当中儿童和老年人的比重较大,则家庭越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劳动力向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流动,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提高家庭的基本生活状态。当前,医疗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抚养负担,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和农村地区。因此,儿童和老人在家庭中的比重越大,则家庭抚养负担越重,需要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推动劳动力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流动。
3.城市的人口密度。城市的人口密度是指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面积之比,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越小。城市的用地面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变动是比较小的,而城市现住人口变动是比较大的。随着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逐渐减少,劳动力流动会加快,造成城市人口增加,进而导致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大。对于城市的发展来说,城市的发展规模都存在一个最优的规模,在这个最优规模范围之内,劳动力的流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的劳动量,能够推动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旦城市的规模超过了这个最优的规模,那么劳动力继续流入,只会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例如,交通拥挤、用地紧张、城市生活环境恶化等。因此,城市人口密度越大,在一定的范围内,越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4.城镇的失业率。城镇的失业率是指城镇的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城镇的失业率衡量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以及劳动力在城镇地区找到工作的难易程度。若城镇的失业率比较高,说明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比较紧张,劳动力在城镇地区找到工作难度比较大。即使可以找到工作,由于专业技能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工作的不稳定性比较大,工作的环境和待遇相对来说比较差,都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相反,若城镇的失业率比较低,说明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处于非饱和的状态,提高流动的劳动力在城镇找到工作的概率。因此,城镇失业率越低,提高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进而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三)政策与制度因素
中国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较强的自发性,但同时也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干预,因此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随政策和制度因素波动的阶段性的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中国提出优先发展东部地区,进而制定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政策,同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东部地区很大的支持,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来说比较慢,造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为了缩小地区间经济差异,中国又制定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平衡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因此,由于受中国政策倾向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大规模的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最近几年,为了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在相应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劳动力呈现出回流的现象,以及向西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这说明,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与中国发展经济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制度因素,特别是户籍制度,是阻碍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巨大屏障。建国初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下,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的阻碍了劳动力的区域流动,造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状态。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渐的放宽对户籍制度的管理,劳动力的流动量也逐渐的增加。在20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在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的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原则下,逐步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放宽人口向中小城镇流动的限制。这项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快中国劳动力的流动。中小城镇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劳动力提供了工作机会,提高就业的概率,也就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因此,户籍制度逐步的放宽,在一定的范围内会推动劳动力的流动。
三、实证研究
鉴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利用动态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选用1978年到2012年全国的年度数据,基础数据均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年《中国劳动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库,利用Eviews6.0计量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一)数据的选用和处理
对于劳动力的流动量,本文采用陆学艺[9]的计算方法来统计,即城镇工作的非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工作的非农劳动力之和,而城镇工作的非城镇劳动力为城镇的就业人员减去城镇的职工人数,农村工作的非农劳动力为乡村的就业人员减去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这个统计指标可以比较合理的统计出中国劳动力的流动量,因此本文选用这个指标对劳动力的流动量进行衡量。
城乡收入差异选用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差来衡量,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经过以1978年为基期的城镇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折算,以剔除物价水平对人均收入的影响。由于劳动力流动主要取决于上一期的收入差异,因此本文的计量模型当中是引入上一期的城乡收入差异来衡量收入差异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人力资本存量反应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劳动力流动的难易程度。其计算方法为:

其中,H为人力资本存量,N为就业人数,E为各种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比重,h为教育折算指数。i为受教育的水平,分为六种水平阶段,即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对于教育折算指数的设定,参考胡永远[10]、以及周晓[11]等的设定,本文把教育折算指数以此界定为,未上过学为1,小学为1.1,初中为1.2,高中为1.4,大学专科为1.6,大学本科以上为1.7。
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用经过消费价格指数剔除物价水平的实际量计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就业空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是经过消费价格指数缩减之后的实际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反映出城镇居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以及生活环境。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选用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衡量,分别经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物价水平的影响。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反映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成本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城镇的失业率反映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
制度因素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的因素,而制度因素主要是通过制度的变迁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影响反映出来的。因此,对制度因素的衡量,本文借鉴了樊纲、王小鲁等[12]对制度变迁和制度因素的衡量的基础上,设置三个指标来衡量制度因素。三个指标分别为:一是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二是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衡量制度变化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程度;三是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用GDP减去国家财政收入之差,再比上GDP,用此表示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给予这三个指标相同的权重,以测算制度因素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程度。
(二)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上述因素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程度,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的模型为:

其中,mt为t期劳动力的流动量,Yt-1为t-1期的城乡收入差异,Ht为t期的人力资本存量,Et为t期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It为t期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Ct为t期城乡消费支出之比,St为t期城镇的失业率,Pt为t期制度变迁指数。εt是白噪声过程,均值为零,方差为不变的常数δε2。
由于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为了避免Granger所谓的伪回归问题,必须先对所有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保证各序列平稳的基础上,再对各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只有在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下对模型进行估计才能得到有效的估计结果。本文选用ADF检验方法对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知,各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统计上不显著地,说明各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序列。因此,对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除了城镇失业率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外,其余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下均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即I(1)。在各序列都是I(1)序列的基础上,进行协整分析以研究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的协整分析方法,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2。

表1 各序列的ADF检验的结果

表2 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从Johansen的协整检验结果得知,模型存在着协整关系。从特征根的趋势值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存在着5个协整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存在6个协整关系。从特征根的最大值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4个协整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则存在5个协整关系。综上所述,模型存在着协整,说明各序列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为:

其中,括号当中的数值为各变量的标准误。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收入差异对劳动力的流动量有正向的影响,即上一期的城乡收入差异上升1%,则劳动力的流动量将会增加0.329%,并且其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之一,特别是收入差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收入差异越大,引起劳动力的流动量越大。
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流动量是正相关的关系,当人力资本存量增加1%时,劳动力的流动量就会增加1.704%,其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这说明随着社会文化水平整体的提高,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越趋向于流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劳动力流动量的影响是正的,当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一个单位,则劳动力的流动量将会提高5.6%,其t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大,说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空间较大,给劳动力进入发达地区提供更大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空间,也越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上升一个单位,则劳动力的流动量将会提高0.5%,其t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这说明,投资比例越大,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就越好,也就越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城乡消费支出之比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是负的,当城乡消费支出之比上升一个单位时,劳动力的流动量将会下降33.7%,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幅度,其t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城乡的消费支出之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入到经济发达地区后的生活成本,流动成本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净收入,因此城乡消费支出之比越大越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城镇失业率上升一个单位,则劳动力的流动量将会减少7.9%,其t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城镇失业率直接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失业率越大,说明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比较紧张,找到工作的机会就比较小,因此也就越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当制度变迁指数上升一个单位时,劳动力的流动量将会上升5.2%,其t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这说明制度变迁指数越大,制度因素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程度在下降,越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从模型估计的整体来看,模型整体拟合的很好。判定系数和调整的判定系数都在99%以上,说明模型当中的变量解释了劳动力流动总变异的99.64%。F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统计上显著地。通过上述模型,写出误差纠正项ecm,即:

对误差纠正项进行ADF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为-4.962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误差纠正项是平稳的序列。因此建立误差纠正模型:

其中,ηt为白噪声过程。
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为:

从误差纠正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存量、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制度变迁指数对劳动力流动量在短期内有正向的影响,除城乡收入差距外各变量的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地;城乡消费支出之比和城镇的失业率在短期内对劳动力流动量的影响是负的,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误差纠正项ecm为-0.5824,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当短期内劳动力流动量偏离其长期均衡趋势时,则模型会以0.5824的速度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四、结论
本文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的角度对引起劳动力流动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计量实证检验。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可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中国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整体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势必要求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再配置,以优化其资源结构,进而加快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中,制度和政策因素曾是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但随着中国制度的改革,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成为当前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因素。从实证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异、城市生活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最大,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要逐步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缩小区域间和城乡间的经济差异。同时,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有效提高流动劳动力的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
[1]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143-181
[2]Fei.J.C.and Ranis.G.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J].Theory and Policy,Homewood
[3]Todaro.M.P.A Model of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141-147
[4]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2):37-42
[5]蔡昉,都阳.区域差异、趋同与西部开发[J].中国工业经济,2001(2)::48-54
[6]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1-49
[7]朱农.贫困、不平等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J].经济学季刊,2005(1):167-188
[8]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4):68-78
[9]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J].社会学研究. 2003(4):1-9.
[10]胡永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3(1):54-60.
[11]周晓,朱农.论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J].中国人口科学,2003(5):17-24.
[12]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10):24-36.
From the Angle of Time Sequenc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Labor Mobility
WU Pe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China's marketization,the government relax restrictions on labor mobility,and labor flow has increased.So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abor flow mainly includes:economic factors,social factors,and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factors.This paper by using annual data from 1978 to 2012,appli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dynamic time series to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of Chinese labor mobility.It is conclusion that:economic factor is still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labor mobility,social factor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labor mobility,and the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factors impact on Labor mobility decreased gradually.
Income Disparity;Flow Cost;Human Capital;Institutional Factors
F249.21
A
1007-0672(2015)02-0006-07
2014-07-01
吴鹏,女,河北邯郸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民收入分配,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