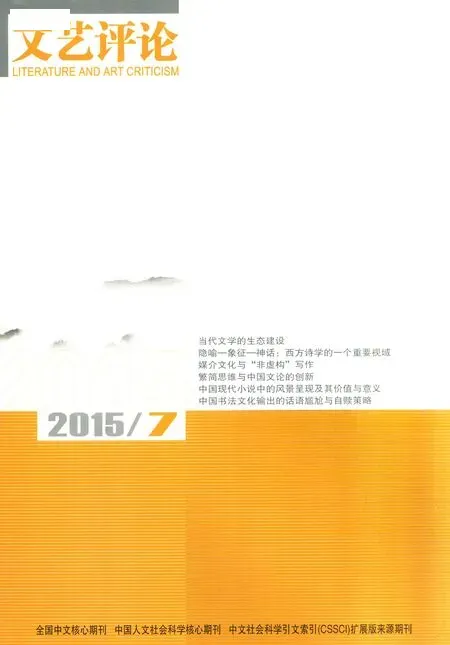论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启蒙叙事的意义与困境
○吴国如
论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启蒙叙事的意义与困境
○吴国如
为使交往活动过程中①主流话语的内涵和意图能为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正确领会和有效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阐释者周扬早在第一次文代会时就明确指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必须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否则就是错误的发展方向。②不久(1953年),他又就左联时期引进我国、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前苏联文艺纲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理论层面进行了非常有指导意义的重要阐述。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题中之义首先是要求作家立足于现实的革命的发展真实地去表现现实,作家对于生活中所存在的矛盾不要回避,同时也要突出现实发展的主导倾向,对于新的东西坚决拥护,旧的要坚决反对。③应该说,在当时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主流话语这种关于文学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强调与设定,为十七年作家创作的最基本规范和最重要追求目标。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具有强烈社会象征行为的基本话语实践活动——与自身具有同构性质的知识分子形象叙事,来对主流话语有关知识分子的书写规范和政治思想彻底转变的现实询唤进行响应,以此自我指涉地凸显自身普遍而急切的工农兵身份归属诉求和无产阶级集体性话语建构。④但在实际过程中,创作者的内心始终难以摆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标志的五四启蒙思想,其自我意识、个体思想总是草蛇灰线般延续在知识分子叙事话语中,从而导致作品与时代语境下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主流话语叙事成规和话语规范发生龃龉,并带来叙事的困窘。
一
通读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可以发现,其启蒙叙事主要从两方面突进:一是于自我意识层面关注个体生命存在和现实社会现象,以一种介入的创作姿态进行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体性表现和社会生活干预。前者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宗璞的《红豆》等。女主人公林道静、江玫在寻求个体命运归宿和个人情感寄托的曲折历程中所具有的女性生命意识,尤其是纠结不断、复杂微妙的情爱心理,被作者以细腻生动之笔予以传神表现。后者以方纪的《来访者》为例。小说对于“健壮”的车夫面对与他素不相识的无辜无助者——知识分子康敏夫自杀时所表现出的“憎恶而愤怒”冷酷神态的形象揭示,颇能说明作者有意无意地触摸到了自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中所一直存在的国民性改造的启蒙命题,在彼时工农兵广受尊崇的时代语境下显示出特立独行的创作姿态。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与此类似。小说不但将有钱人以强凌弱(舞厅老板)、穷苦人无助哀嚎(乞讨小孩)、看客们陶然沉醉(有微弯着头的,有抄着手的,也有口含着烟卷儿的,姿态不一)的场景描述得惟妙惟肖,且返躬自省地以抑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丈夫“我”的怯弱和麻木)扬彼(作为工农干部的妻子的挺身制止)的对比方式,含蓄地表达了对于知识分子自我精神品格的部分否定,显示出作者非同一般的批判性思想认知视野。
由此而来的就是,该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启蒙叙事往往会因作家在自我意识层面关注个体感性生命存在和唯美情怀的艺术渲染,而自觉不自觉地在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上显示出文学自主性诉求。以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为例,仔细阅读该作品可以明显体会到,作家以极简省的篇幅把两个阶级出身完全对立的大学生(江玫、齐虹)之间的恋情描写得伤感而缠绵,包蕴其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个性元素浪漫而又唯美,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时代话语禁忌的超越和阶级视域的突破,也因此而复活和表征了压抑已久的现代知识女性微妙细腻的感触和敏感情思以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独特典雅的审美情怀,丰富而复杂的非理性个体生命存在得以真实呈现。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散步,就这样,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酽的甜香里,然后又是雪花飞舞的冬天。
在此,作者运用电影蒙太奇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散步为核心意象,由迎春花而雪花,通过视觉性和画面感都非常强的写意性诗意描绘,刻写出岁月轮转、时空变幻背景下两人地老天荒般纯真美好恋情的持续演进和良辰美景的短暂易逝,凄凉华美之感如绝世挽歌般缠绵徘徊于当事人心底,令人留恋却又备觉伤感和无奈。贯穿于整篇小说的雪花意象和冬天场景通过思想启蒙和政治文化的双重变奏,各自于现实的描述和过去的回忆两个层面彼此前后呼应,缠绵悱恻的两性情感、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哀愁和遗憾在作品的场景描写中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华美感伤的气韵格调也于此被烘托得遍披华林。
从文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维度来看,上述于自我意识层面关注个体生命存在和干预社会生活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思想诉求和美学样态是与十七年时期主流话语所强调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的宏大叙事理念及其维护并强化的一体化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相龃龉的,不能说与政治无涉。伊格尔顿就曾明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切批评都关涉政治。⑤特别是,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不多的类似《红豆》这样追求文学自主性的作品所体现的强烈艺术审美特性,在当时崇尚集中、统一,追求规范化、程序化叙事的文学生态境遇下,不应看作只是追求艺术自律的体现。从该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启蒙叙事对当时小说普遍的创作模式和审美观念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来看,这类创作恰如马尔库塞所言:“即使在政治内容完全缺乏的地方,也就是,在只有诗歌存在的地方,都有可能具有政治性的艺术。”⑥
二
对于知识(启蒙)与叙事结合的样态、合法性价值以及存在的效果和意义,利奥塔认为,重新引进叙事作为知识有效性的合法化方式,可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或者把叙事主体表现为实践主体,或者表现为认知主体;或者是自由的英雄,或者是知识的英雄。因为存在这种抉择,不但合法化的意义并不相同,叙事本身也无力给合法化提供一个完整版本。⑦也就是说,一旦知识分子叙事里的启蒙话语突入强调体现历史本质,以统一、集中、宏大叙事等为主要特征的主流话语、政治话语领域,它的这种天然的、不安分的分裂特性,势必造成两类话语之间的矛盾乃至剧烈冲突。这也正是启蒙话语介入的语境下,利奥塔质疑总体性、系统性、元话语和宏大叙事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情形的根据。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除了意识形态可以使统治阶级所控制的制度、实践、价值和社会秩序取得合法性之外,又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叙事合法化呢?”⑧利奥塔对此显然持赞成态度,如上所述,他不仅看到了叙事既可能与知识结合,也可能与意识形态结合,更看到了三者共存于文本时的分裂和矛盾。
应该说,从十七年启蒙叙事以其不同于主流话语所强调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基调的话语方式,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和普遍的美学样态所形成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异质”性因素所造成的叙事分裂的事实来衡量,利奥塔所说的不相容性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虽然他对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总体性、元话语、系统性和宏大叙事所作的怀疑与批判并不一定为人所认可,但在政治文化一元化的现实语境要求下,以往曾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启蒙话语,尽管和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里所提到的启蒙异化性、过度性有一定距离,但还是因其“异质性”被认为和主流话语一体化的现实需要之间有一定龃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强调体现历史本质,反映“共同精神”的意识形态的某种“分裂”。在这方面,据持五四启蒙情结的知识者或许很无奈。纵观古今中外的大量文学现象,作为对某种时代理念的疏离或悖逆,文学自主性追求确实以它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有意无意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彼时社会政治现实的介入。这也就意味着这种看似与时代的精神状况、审美精神相龃龉的“有意味”的“政治性的艺术”,必然在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方面遭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质疑乃至否定。
以经编辑秦兆阳修改后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例。从这篇被学界普遍认为在批判官僚主义现象方面具有激进风格特征的多处叙事可以看出,作品中年轻的男女主人公林震和赵慧文之间的关系因为有爱情元素的介入已超越了一般同志范畴,由于组织纪律、道德伦理等多方禁忌,他们对这份情感彼此都十分克制。尽管如此,两人之间的交往还是被叙述者表现得多少有些感伤与暧昧。很明显的是赵慧文在家门口送别林震时候的场景,只关风月而无涉政治,李商隐无题诗诗意而惆怅的韵味隐然呈现: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她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
显然,上述场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具“小资”情调的,这就不难理解当时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批评尺度的研究者会用充满讥讽的语言批评说该作品有种似曾相识的“陈腐老调和淡淡的哀愁”,不仅没有表现出革命时代的青年应有的感情境界和政治态度,其有悖于时代主潮的“不健康”的思想倾向和“可疑”的创作立场(意图)也很值得注意和警惕。⑨
三
十七年时期,在公开的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其作者基本上都是左翼作家,对权力话语的认同与趋向、“文以载道”(主流意识形态)是他们创作的一致目标和共同取向。这是当时一体化政治文化语境下外在的客观现实与作家内在的心理诉求彼此作用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这些作家,尤其是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作家,其内心深处一直固守着作为知识精英和文化英雄的内在思想诉求,难以放弃五四启蒙情结。但是,如上所述,站在主流话语的立场来看,他们创作中的这一启蒙趋向无疑显示了新形势下另类的姿态存在,其客观叙事效果或方式方法不仅很难体现时代精神,也难以反映无产阶级的历史本质。如1957年春的时候,何迟写了一篇名为《统一病》的相声作品,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评,如做事不考虑实际,不走群众路线,强求划一,命令主义作风等。林默涵读后很中肯地指出,作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写法上也可圈可点,但需防止被人误解,甚至以偏概全。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冯牧有关战争题材小说爱情书写的评价里面。如他认为,战火中的爱情应该是“平静而纤细的”,而非“缠绵、沉醉的”,否则便不能与“那钢铁般的战斗声音”十分和谐地交融在一起,造成对革命叙事的解构。⑩谢冕就曾客观地指出,宗璞的《红豆》所以被人认为不太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和美学规范,就是因为党的工作者江玫对自己与资产阶级银行家儿子的过往爱情所作的非常伤感、缠绵的情绪性回忆,并没能在现实的有利于革命建设和主题表达的理性层面获得节制和超脱,读者难以从中获得一个积极、健康的判断标准与评价视角。⑪
以萧也牧、杨沫、方纪、赵树理、宗璞等该时期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为例,这些人普遍于早年受到过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于抗战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意识形态层面受到过深刻的思想洗礼,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⑫,因此,他们身上既有的五四启蒙精神往往会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谏士、诤臣情结一道,伴随着对党的忠诚意识根深蒂固地潜隐于其无意识心灵深处。赵树理去世前疾病缠身仍亲笔抄写具有表露心志性质的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对于宗璞的《红豆》写作,有论者这样评价:“正如许多愿意改造的知识分子一样,宗璞有一个难以改造的‘自我’,促使她以那种温和的方式,履行一份批判社会的职责。”⑬革命是自由的争取,就促使人的解放意义而言,五四启蒙思想和无产阶级政治文化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契合性。毛泽东自己曾多次强调指出:土地革命既是一场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承续五四启蒙运动的、以夺取农村文化领导权为目标的新文化革命。⑭杨沫《青春之歌》里的主人公林道静所以会抗拒封建旧家庭的安排,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并最终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其逻辑起点和一贯动力就是五四启蒙思潮给这些时代知识青年提供了不懈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生自由的动力和平台。许多像林道静这样在特定的年代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最初几乎都是启蒙精神作用的结果。可以说,五四启蒙思想作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在此发挥了巨大作用。或者说,作为小说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作家,往往会以小说(尤其是自传类小说)为媒介,通过描绘思想启蒙所引发的鲜明意识形态效果,凸显他们本人一贯自以为“是”的“大我”情怀。将“对党对人民是否有利”设定为自己创作的目标、根据和标准,这是具有五四启蒙思想的左翼作家自延安时期以来在给自己的创作寻求心理安慰和现实辩解时很有代表性的观念,十七年时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这些具有五四思想启蒙意识的十七年知识分子作家看来,他们本人的这种执着于“自我”的写作方式,仅仅是在“否定的辩证法”逻辑思维理念支配下以一种特殊的叙事范式实现这种意图(有利于党和人民)。但是,世易时移,客观地讲,他们其实也应该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天然就具有“异质性”特点的写作方式(以谏士、诤臣的身份进行启蒙叙事)客观上所暴露出的作家本人不逊的现实社会存在姿态,决不亚于延安整风运动前丁玲(包括其作品《在医院中》中的人物陆萍)、莫耶、舒群等作家,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且仍危机四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百废待兴、思想意识形态亟需高度统一的新中国,显然并不符合时代主旋律要求,难以从现实的、直接的根本意义上有效保证统治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控制权,⑮因此,在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方面要想获得主流话语的认可其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在知识分子改造时代氛围中,作为需要“原罪认知”和“灵魂救赎”的“他者”,知识分子作家要想不被主流话语放逐,在真实地表现现实、揭露生活中所存在的矛盾的写作过程中,通过凸显现实的革命发展的主导倾向来获得主流话语的思想接受和身份认同,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而又恰切的表意策略和政治实践。也即,为了使主流话语能更好地理解并接纳自己的创作意图,十七年知识分子作家无论在自我意识和集体理性之间怎样矛盾彷徨,最终普遍还是竭力会/要以中国传统的讽劝结合、曲终奏雅的书写方式皈依主流政治文化的正轨,回到意识形态叙事的原点。方纪《来访者》中的知识分子康敏夫实际是作者本人艺术人格的体现,被压抑自我的外化。他的主动劳教寓意了知识分子(也是方纪自己)对主流话语的认同和接受。就像前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中徘徊于爱情与革命之际的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忍痛让与自己阶级立场相对的恋人成为倒在自己枪下的第四十一个敌人一样,江玫最后也在极度痛苦之中“枪毙”了自己那份条件不成熟的爱情。这样的举动,未始不是现实生活中作为需要改造的知识分子宗璞自己皈依主流话语意愿的真诚传达。没有敌人也要树立一个,包含爱情在内的启蒙话语是手段、是媒介,更是自己渴望被主流话语认同的心迹证明。他们在此过程中竭力将启蒙话语组织到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凸显知识分子作家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迎合主流话语,是为了实现作为“他者”的他们身份转换的政治诉求或者巩固他们已然的革命者政治身份。
四
这就在事实上给该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造成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现象:宏观、总体的肯定与局部、细节的否定(如《我们夫妇之间》,作为叙事者的知识分子“我”在事关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肯定并皈依了作为工农干部的妻子,而对她粗俗的生活观念和行事作风进行了调侃、揶揄,《在悬崖上》作为技术员的丈夫婚恋问题上起初的见异思迁与最终的悬崖勒马),欲而不能的两难抉择(如《红豆》中的江玫在革命理想与个人情欲之间的艰难取舍、《青春之歌》的林道静由自由知识分子余永泽投向无私无畏的革命者过程中的心理纠结),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隐晦性叙述(如《来访者》《我们夫妇之间》对新社会大众仍存有的性格缺陷——国民劣根性痼疾的含蓄批判,《百合花》《红豆》《风云初记》《青春之歌》等对女性情感的曲折传达)。由于多种因素(如政治逻辑、艺术审美、道德伦理、文化心理等)的介入,小说的真实性效果和倾向性表述之间常常造成内在的分裂和龃龉,或者说,这种分裂和龃龉造就出来的叙事张力充分暴露了创作者矛盾、复杂的文化人格,分裂、不自信的政治心理。在本质真实和艺术真实、生活真实三者之间,叙事者(作者)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混淆或忽视它们的差别,突破其间的限度,往往因为倾向于后者而又难以舍弃本质真实,在灵魂的挣扎和人格的分裂情形下导致三者的错位和重置。因此,十七年知识分子启蒙叙事犹如戴着镣铐跳舞,总是左支右绌于政治与审美、超验与现实、他律与自律、彼岸与此在以及宏大叙事与个人体验的叙事夹缝之中,窘迫而又多少有些“乖张”。这显然难以自洽于日本当代著名左翼批判理论家柄谷行人的主张——“现代国家”的建立必须以集中化、同质化为前提。即如上述谢冕评价《红豆》时所说,在政治文化一元化的现实语境要求下,作家要让读者从现实的有利于革命建设和主题表达(党性、人民性)的理性层面获得一个“积极”、“健康”的判断标准与评价视角。基于此,我们没法否认新政权成立之初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启蒙话语作为一种“异质性”复杂存在难以被主流话语体系认可的当然性,其元叙事暧昧、总体性模糊的客观叙事效果造成彼时作家本人无产阶级主体身份建构诉求的消解也就不难理解。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周扬文集(第l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3页。
③《周扬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④吴国如《“十七年”小说知识分子叙事流变及其意义阐释》[J],《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⑤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⑥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5页。
⑧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⑨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⑩冯牧《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略论〈红日〉的成就及其弱点》[J],《文艺报》,1958年,第21期。
⑪《“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J],《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⑫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⑬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⑭马社香《前奏:1965毛泽东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⑮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J],《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度项目(ZGW1408)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考试与文学生态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