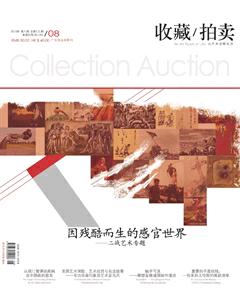触手可及——雕塑家隋建国新作漫谈



今年7月,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佩斯画廊,隋建国个展《触手可及》揭开了神秘面纱。《引力场》以其巨大的体量与怪异的雕塑形状霸占着整个展场;沉重压抑的黑色充斥于空间之中,仿佛黑洞一样,吞噬着光与人的灵魂。这种不携带“文学”意义的形象,仿佛在挑战着观众身体与思维的底线。
在隋建国的创作脉络中,对于材料的探索一直是一条时隐时现的主线。从上世纪90年代的《地罣》、《殛》,到新世纪以来的《时间的形状》、《运动的张力》、《有限行动》等,媒介材料的边界在各种实验性的作品中不断被拓展。2006年以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成为了雕塑家隋建国在三度空间之外的又一个要素,并通过材料在这一维度上的“开放性”传达出来。单纯的“物”变成了与艺术家生命同步的具有“绝对时空”的存在。如何将新作放置于艺术家一贯的创作逻辑之中阐释,是本文采写的一个重要目的。在北京这闷热的暑期,笔者与隋建国先生约见在他工作室的后花园中。雨后,清爽、明媚的上午,艺术家与笔者就这一话题娓娓道来。
王:王青云
隋:隋建国
物与媒介
王:今年在北京佩斯的展览《触手可及》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仿佛作品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年轻人”,让我们大家都感到很陌生。但仔细想想,这“新”中也有着和“旧”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装置《引力场》这种“开放性”与“材料性”。虽然《引力场》并没有像《时间的形状》那样随着时间而“生长”,但是材料本身的“浇筑”与“流淌”却给人以“正在进行时”的持续感,而这种开放性即指向了“时间性”;同时,作品本身的“材料性”后面所隐藏的是您对“物”的理解。
隋:这确实和《时间的形状》有关系,原来那个油漆球表面特别光滑,这一两年起皱了。我发现可能是因为球体面积大了之后,球面的曲率降低,球体表面拉紧颜料膜的能力就降低了,球面变得褶皱,“长得”也慢了。球在涂蘸油漆时,液体受地心引力向下滴,这让我想到液体对其所附着的环境有一种抵抗力。另外,“形体”不变,为什么表面变了呢?这牵扯到球体的基本形状和表面微形状的关系。本来,我认为做雕塑研究“形体”就可以了,但没想到形体之上有更复杂的东西。我注意到液体转固体材料和引力之间其实有些特别偶然的关系,所以开始了对石膏、聚氨酯的实验,这就形成了这次展览作品的主要趋势。
王:这次展览中的素描作品,比如《夜》系列、《春》、《秋》和装置之间有什么关系?
隋:我希望尽量减弱“我”在作品中的作用,让“物”自己呈现。前几年,我用铅笔通过胳膊反复的机械运动在纸上画素描,这就积累了很多铅粉的厚度,这种厚度在纸的边缘可以看出来,我很在意这个厚度。现在我用上了聚氨酯,这个就更厚了,所以它本身的“物质感”也更强,这点是我非常喜欢的。聚氨酯与纸发生接触之后产生很多微妙的变化,出现很多不可控的偶然因素,这其实也很像《引力场》中浇石膏的这种感觉。
王:您希望超越视觉去定义雕塑的本质?
隋:其实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视觉。我只是在制作过程中发现视觉所起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比如《时间的形状》,球需要每天蘸一下油漆,单凭视觉是看不出其中的变化的。在这一点上,《盲人肖像》和《时间的形状》、《引力场》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致性的。
王:您这次对《引力场》的形状有控制吗?
隋:我用泡沫在里面把作品的形状搭起来,然后在外面浇筑黑色石膏。这个有点像《时间的形状》,从一根细钢丝开始,慢慢累计成形状,外面再形成表皮。这里的关键是将《引力场》和佩斯的展览空间结合起来,所以我让形状嵌入到43米挑高的锯齿形厂房当中。让观众进门就看到《引力场》,并产生一种压力感,就像范宽的《谿山行旅图>那样。
王:“远望不离坐外”,哈哈。
隋:哈哈,对。
王:是您用石膏浆兑上纺织颜料,然后浇筑出来的,白石膏本身的颜色、质感不好么?为什么会选择黑色?
隋:黑色是我的心情,这无关于生活的痛,而是种更为宏观的思考和担忧吧。
王:这也是贯穿您的作品始终的。
隋:对,这种情绪是莫名其妙地进来的。我着迷于黑色这种吸光的感觉,所以把石膏里兑上了黑色。
时间与身体
王:其实,“时间”与“身体”的因素在您2006年以后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比如,2009年您在今日美术馆做的《运动的张力》。从作品的外在形式上看,运动的大钢球与空中钢管内奔流的钢球在不断重塑着展览现场的环境,而这种“开放性”恰恰印证着“时间”的维度。同时,当进入到展场后,作品通过对观众身体的“胁迫”达到互动的目的。今年的作品<引力场》也同样贯穿了这两方面的因素。
隋:我认为视觉这个东西太灵敏,同时也会太皮毛。其实,当我们感知一个物体或者空间本身时,是身体的判断在起作用,身体的尺度,身体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对于时间的发现,源于我个体生命的体验,也可以说是源自一种焦虑。于是就有了《时间的形状》这种在时间上“开放”的作品,作品与我同处于一个时间和空间之中,在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刻,这个作品的形态也就“闭合”了。借用哲学上的说法,这种作品拥有自己的“绝对时空”,就像一个生命一样,这和那种创作完就“封闭”的作品相区别。
抽象和具象
王:您曾经说过,雕塑没有“抽象”和“具象”之分。
隋:其实所谓的“具象”一般是指古典或者现实主义艺术层面上的模仿,用一种材料去模仿另外一种形象被叫做“具象”。所谓的“抽象”,是从古典到现代艺术的个转变过程,似乎相比较而言一个作品没有模仿其他任何事物;从字面上看,作品原来应该有的“象”,被抽走了。但这种问题对于现代主义之后的今天的雕塑来说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所谓的抽象雕塑自身都是具象的,因为它就是它自己,它是独立于其他形象的。雕塑和绘画的不同,这里来不及展开了。
原来说“具象”雕塑,往往是因为这个雕塑以一种材料作为载体,模仿了另外一个事物(或者原型)的形象,或者说作品具有“文学性描述”,它是用来替代文字描述的。如果一件作品的造型过程是按照“经典的抽象主义”原则来的,比如柱、球、四面体等形状,那么这个雕塑可被视为属于抽象的范畴,因为这些基本形状被认为是万物万形的出发点或者最终归宿,被认为是万物存在的抽象形式。但实际上,这些“象征”的意义都是人的思维给予它的。所以,即使对一个抽象雕塑来说,它也是由非常具体的材料,形成了具体的形状。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这件雕塑本身也还是它自己,它已经是它的存在和所要表达的全部了。所以在我看来,雕塑没有抽象。退一万步,即使一个尽可能纯正的球体,因为它相对于概念中完美球体仍然是有缺陷的,不纯粹的,所以,它还是“这个”具体的球体;更何况,这个球体只能用具体的材料制作而成,这具体的材料也减弱了其抽象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在绘画上,蒙德里安也坚持认为,他的作品中,每一个具体的方形,三角形,都是再具体不过的具有某种颜色和形状的造型。
这样说起来,我的《盲人肖像》,它就是一块泥,作为一块泥,一旦经过我的手的认可,它的形状与形象就是如此合一,它自己的形状和它自己的质料再也不可分离;它被艺术创造过程所加持而拒绝被有用性的看法所计算。任何一块泥都是有形状的:如果它是在自然中形成的,那就是和“树”“草”一样,都是由造物主造的;而如果这块泥,是在机器中刚刚被挤压出来的,那就属于杜尚“现成品”的范畴;但是如果是人将身体作用于泥,这块泥就拥有了它的另外的具体形状,这块泥是由人手工所造的,是“人”这个物质存在与意志存在和它相互作用形成的。我认为,在“自然”与“现成品”之间的这块区域就属于雕塑,属于艺术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雕塑是具体的,它很具象,它就是它自己。在这个意义上,铸成青铜的《盲人肖像》是这块泥的肖像,是这块泥的具有纪念碑性的肖像。
偶然与必然
王:关于这次展览,您反复提到了偶然性、不可控性。我倒是觉得在我们的艺术遗产中对此已经提供了非常成熟的媒介和技法系统。比如,中国画中的毛笔、生宣、水墨,简单的材料之间就会发生千变万化的效果。何苦冒着这么大风险,去尝试各种“新”的材料?这种“试错”您不觉得风险很高吗?
隋:很久之前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完全可以在古典的书本里找到类似答案。我们的古人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各种艺术形式,其中的任何一种,都足够我们终生沉浸其中;甚至都足够用来表达一个人一生中的各种喜怒哀乐。可是,我不能永远用古人的方式去理解、表达我的存在吧?毕竟,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不一样了,今天的网络、交通、生活的技术条件已经和当时用毛笔宣纸的时代完全不同了。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代人能否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生活方式上的精神生活呢?我们的可能性在哪儿?我并不是在“进步论”的意义上强调时代性,而是说我们这代人就是这么生存的。这些年,我时常会反省自己,隐约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毛泽东时代所给予我生命的最大的馈赠。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予我的。
我还是把自己定位于改革派。上世纪50年代出生,经历“文革”,从80年代的启蒙中走出来。当时我们这一代是从两个传统里反出来的:我们先是上溯先秦时代的“诸子”思想,跨越了这以后近两千年的文化轮回,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对于“五四”精神的种延续;另一个是对我们自己所在的学院体制——“法苏”传统的出走,这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意识形态的反省。
一旦将历史的眼光放到五千年的跨度,并且试图在这样一个时空里对于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时候,“先秦”似乎总是会成为一种本能的选择。在刚刚开始面对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要找到自己从精神上、文化上超越这一现代文明的立足点,只能采取这种“跳跃式”的办法,追溯至我们文化的根源之处。
这当中难免会有虚无主义的成分,但它的精神取向,给我们这一代提供了一个新的理想高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频繁的交往下,西方变得不再神秘;同时,传统文化也在回潮、升温。但这些并不足以改变我当初的志向。我坚信我们的传统文明是伟大的,但是这种伟大的文明需要在当下获得再生。所以,我坚持对传统持有怀疑和批判的立场,如果我的批判能对传统的自我更新有所贡献。
我今天的艺术实践和尝试也无关“成功”,不管作品好坏、成熟与否,这就是我。而且,只有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我对世界的看法,形成了我自己的创作方式,所以我才会做《时间的形状》、《盲人肖像》、《引力场》。如果说我的手可以“对话造化”,创造出“物的存在”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面朝着“老庄精神”了。
王:在“天籁”、“地籁”、“人籁”的等级结构中,去寻求“天籁”的境界。
隋:对,这是我的目标。“天籁”“地籁”是自然造化,是人无法规定的;“人籁”是人受过训练后形成的,是集体无意识下所达成共识的“规矩”。也可能我的努力是徒劳的,就像我无法抓住我的头发脱离开地球。很多时候,我真的想超越自己,超越传统,超越这个时代,但是,看看这些作品(《引力场》、《锥》、《回》等),仍然到处都是黑色——我心情的颜色。
边界与本质
王:以往聊天,我能感受到您是希望通过各种实验去定义“雕塑”的边界,探索雕塑的本质。而今天您所说的对于自我的“超越”,我感觉这是在通过实验去界定“人”的本质与边界。
隋:我是想通过做雕塑来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理解物,理解社会,最终是理解整个世界。做雕塑就是让“物”成为我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媒介。研究“物”,其实就是研究生产物、认识物的“人”;对物的理解,就是对人的理解。
世界本来是“空”的。这个意义上的“空”不是空无,而是人这一认识主体参与之前的世界的本原状态。即当人还没有自己的主体,还不能将世界客观化的时候,物质世界的自然存在形式。
由于人类现代文明的介入,世界被作为有用的物质系列,对象化地存在着;同时,作为“物自体”的世界被遮蔽在文明世界之外,等待着作为人类最高使命的艺术的降临。
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与世界之间需要很多技术性的中介。这些中介,就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包括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生产工具等全部物件。但是,在人与世界之间,最纯粹的中介就是艺术,因为它是非“工具性”的人类实践,它是饱含着人类生命意志的创造性实践。雕塑因为它的“物质性”对应于人类生命意志本源的肉体之“物质性”,决定了它与原本“空”的世界的种种独特的根源性关系。
王:《引力场》这个名字很有意思,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地球对于人的吸引力,对这一人类生存的物理空间的关怀。
隋:对,这里面有很多指向,其中也有人与地球空间的关系。我们每天都处在大地这个“引力场”之中,只不过我们不自知或者模糊不清而已。为什么一天工作下来我们都会感到疲劳?是因为我们的肌肉、骨骼无时无刻不在对抗着地心引力。但要是没有这种引力,我们反而无法生存,因为人的所有身体机能都是和这个引力环境相匹配的。对于人与其存在环境的思考,是我做这个作品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