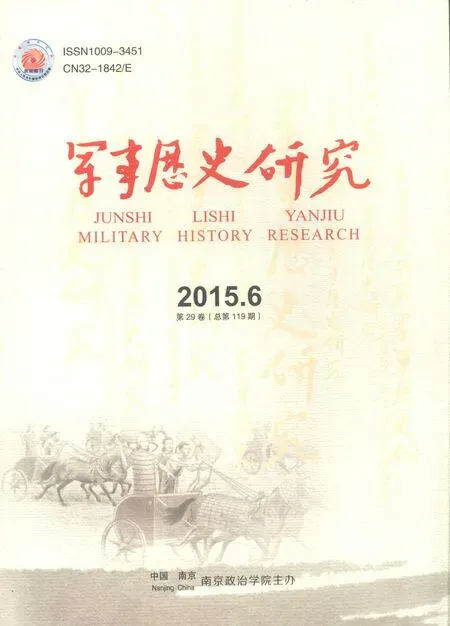隋唐东征相关地理问题考辨
刘向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北京100091)
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隋唐对高句丽(南北朝时始称高丽)的战争,是隋代和唐代前期的重要战事,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学界对这场战争的起因、性质、进程、历史影响以及双方战略得失、后勤补给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研究,但对隋唐军队进行战争准备和向前方推进时所涉及的一些地点、地名的记述,尚有模糊和讹误之处。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隋唐东征所涉及的几个地名及其今址等相关地理问题略加考辨。
一、临渝关
隋唐时期的临渝关,是华北地区由辽西走廊通往东北地区的一处重要关口。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以汉王杨谅为元帅,率水陆军30万征伐高句丽,“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①魏征等:《隋书》卷81《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16页。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率军亲征高句丽还军时,于“冬十月丙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②刘昫等:《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8页。这两次东征高句丽的隋唐大军都经过临渝关。
临渝关具体在哪里?临渝关得名自临渝县。《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条载:“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此处渝水即今大凌河,西汉之临渝县故址当在今辽宁义县东北。①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1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0页。东汉时,临渝县迁置于今山海关附近②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1卷,第388页。(城址见后文所述)。《三国志》中不见临渝县之名,盖此县在曹魏时已被废弃。唐初,复置临渝县,属平州北平郡,武德七年(624年)被废,贞观十五年(641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改名石城县。③史载:“汉县,属右北平。贞观十五年,于故临渝县城置临渝。万岁通天二年,改为石城,取旧名。”见刘昫等:《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20页。史载:“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渝关,一名临闾关。有大海关。有碣石山。有温昌镇。”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21页。《新唐书·地理志》载,平州北平郡石城县本为东汉临渝县,“有临渝关,一名临闾关”,④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第1021页。营州柳城郡“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⑤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第1023页。可见临渝关又称“临闾关”,简称为“渝关”。
自宋以后,一些史书又将临渝关称作“榆关”。其起因比较复杂,有必要作一辨析。
实际上,临渝关并非榆关,两者不是一回事。隋唐时期另有榆关,此关位于当时的榆林郡治榆林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部十二连城)东南30里,又作“榆林关”,⑥谭其骧:《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932页。置于隋开皇三年(583年),⑦史载:“(开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榆关。”见魏征等:《隋书》卷1《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9页。史载:“金河,开皇三年置,曰阳寿,及置油云县,又置榆关总管。五年改置云州总管。十八年改阳寿曰金河,二十年云州移,二县俱废。仁寿二年又置金河县,带关。”见魏征等:《隋书》卷29《地理志上·榆林郡》,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3页。即汉代之榆溪塞,隋、唐之际曾被废,贞观十三年(639年)复置,⑧史载:“胜州榆林郡,……有隋故榆林宫。东有榆林关,贞观十三年置。”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75页。五代后荒废。榆关置关的第二年,隋文帝即“以陇西频被寇掠”,任命素习边事的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⑨史载:“(开皇四年)夏四月……丁巳,以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为榆关总管。”见魏征等:《隋书》卷1《高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1页。史载:“文帝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人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人虽散居,必无所虑。’帝从之。帝以子干习边事,授榆关总管,迁云州刺史,甚为虏所惮。”见李延寿:《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2页。唐代诗人韦庄《赠边将》云:“昔因征远向金微,马出榆关一鸟飞。”诗中“金微”即唐代贞观末年以回纥仆固部所置之金微都督府,在今蒙古鄂嫩河流域,韦诗中之“榆关”无疑是指榆林郡之榆林关。不过,因“榆林”与“临渝”音近,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将榆林关、临渝关混淆的情况。唐代兵学家李筌的《太白阴经》一书,将唐代从西京长安出发,到达周边各个主要边塞、部族及域外的交通线路总结为十二条:关内道、黄河北道、河东道、陇右道、河西道、北庭道、安西道、剑南道、范阳道、平卢道、岭南道、河南道。其中平卢道“自西京经范阳节度,东至榆林关,至平卢节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东京二千里。抵安东,渡辽水,路接奚、契丹、勃海、靺鞨、高丽、黑水”,10李筌:《太白阴经》卷3《杂仪类·关塞四夷篇》,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60页。这正是隋唐东征部队由中原北上幽州,再东抵营州、进兵辽东的陆路交通线。但其文中之“榆林关”明显系“临渝关”之误。唐亡以后,将“渝关”讹为“榆关”已基本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等正史所记载的“榆关”,均指辽西走廊西端之临渝关(渝关),而不是北方榆林郡的榆林关。
关于临渝关的关址,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清代以降的一些考证大抵分持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河北抚宁县东20里的榆关镇;一说在今山海关。①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即持此说:“山海关,县东百里,本名渝关。……今关,盖汉唐旧址,非明朝创建也。”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7《直隶八·永平府·抚宁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54页。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卷》中关于临渝关的今址定位就不统一,如“辽西走廊”条将“渝关”的今址注为“今河北抚宁榆关镇”;②《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而“山海关”条则谓“渝关”即山海关,“位于河北与辽宁两省交界处”。③《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地理测绘气象卷》,第476页。
除上述两种意见外,还有学者提出,位于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古城村的汉代古城遗址当为隋唐临渝关的关址。④康群:《渝关考辨》,《辽海文物学刊》1998年第2期。该汉城遗址东距今山海关约8里,城址呈方形,四周夯土城墙俱在,直径300米,遗址中有大量的卷云纹瓦当、菱格几何纹空心砖残块等东汉时期的建筑构件出土。从其地理位置和考古遗迹来看,该城极可能是东汉辽西郡临渝县城的所在地。但是,笔者认为据此将其作为后来隋唐时期“临渝关”的关址和“榆关守捉”故址,未免有些牵强。
关于临渝关的关址问题,张会发的《临渝关考》一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综合性分析,和对今河北抚宁县榆关镇、山海关、古城村及今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边墙子村的实地勘察,得出“古临渝关的关址当在今山海关东10里的边墙子村”的结论。⑤张会发:《临渝关考》,《秦皇岛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94年12月。该文指出:临渝关产生于北齐长城,而边墙子村的“红墙子”遗迹就是北齐长城。《新唐书》卷192《贾循传》载,渝关(榆关)守捉“地南负海,北属长城”。⑥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192《贾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33页。根据《康熙字典》的解释,“属”字含义为“相连续,若尾之在体”。“地南负海,北属长城”说明临渝关南向面海,北边与长城相连。这个长城无疑是北齐所筑东至于海的长城。史载,北齐曾“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⑦李百药:《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3页。北周、隋时均有增筑。临渝关作为控扼辽西走廊的关口,必然处于北齐长城与沿渤海岸古交通线的交叉点上。今山海关,虽称天险之地,但是明长城由角山起就与北齐长城分道扬镳,改道正南由老龙头入海,因此今山海关绝不是隋唐时期临渝关的故址。至于古城村之古城,它既不属长城,也不处在交通要道上,不可能是临渝关。
张会发还对史籍中有关临渝关的道里记载进行了考证,他根据《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⑧《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北京:测绘出版社,1986年。所标注的里程进行计算,得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杜佑《通典》卷178《州郡八》“卢龙县”条载:“临闾关,今名临榆关,在县城东一百八十里,卢龙塞在城西北二百里。”隋唐之卢龙县城即今河北卢龙县城,⑨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按《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标注里程计算,今卢龙县至边墙子村为176里,至山海关166里,至古城156里,至今榆关镇80里。另,《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匹。”1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即持此说:“山海关,县东百里,本名渝关。……今关,盖汉唐旧址,非明朝创建也。”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7《直隶八·永平府·抚宁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754页。0《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载,营州柳城郡“西四百八十里有渝关守捉城”。1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第1023页。隋唐时期,营州(治柳城县,今辽宁朝阳市)是中央政府经营东北地区的战略基地。从唐太宗征高句丽出师、回师均经由营州这一事实看,当时走的路线就是由今辽西走廊循傍海道到今辽宁兴城,然后向正北直达朝阳市。按《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标注里程计算,边墙子村至朝阳市全长为481里,而朝阳到今山海关为490里,至古城为500里,至今榆关镇为570里。很显然,以今边墙子村为临渝关关址最为符合《通典》有关卢龙县至临渝关和新旧《唐书》有关营州至临渝关道里的记载。张文还以边墙子村周围环境与史籍中有关临渝关地理环境的记载相符、边墙子村明代时称“老边门”等事实作为佐证,有力地印证了边墙子村即为临渝关关址的结论。笔者以为,张会发《临渝关考》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为酬谢契丹(辽)出兵扶持自己,而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至金、元两代,辽西走廊东西之地亦俱在金、元版图之内,临渝关作为关隘,显然已失去其军事价值,遂渐被废弃。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在北齐长城最东端以西重修边墙,于临渝关故地以西10里处重筑关城,即今山海关,并置山海卫。因为宋代以后,人们已普遍将临渝关讹称为“榆关”,虽然历尽沧桑变迁,但“榆关”一词又作为山海关的别名(或雅称)而流传于世。《明史》《清史稿》中所载之“榆关”,即指今山海关。今山海关(榆关)、隋唐时期临渝关二关关址虽然相距10里,但是二者的军事地理价值与功能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可以视二者具有历史沿革关系,即临渝关是山海关的前身。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山海关就是隋唐时期之临渝关。
至于在今河北抚宁县东约11公里处的榆关镇,其名称来源于辽代在此处设立并沿至金、元、明各个时期的榆关驿。辽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因临渝关已经失去军事价值,遂在此处设置榆关驿,既作为马驿,又负责稽查行旅,征收过境货税。①史载:“(统和四年)十一月……壬申,以古北、松亭、榆关征税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见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页。徐达在今山海关筑关置卫的同时,将原本设于隋唐临渝关故地的榆关驿内迁到今榆关镇,仍沿用其名。因此,今榆关镇的前身——明代榆关驿虽然得名于临渝关的别称“榆关”,但它已不在隋唐时期临渝关的旧址,应该将二者区别开来。
二、怀远镇
怀远镇是隋唐时期辽西地区的重要军镇,处于营州(治柳城县,今辽宁朝阳市)至辽东的交通要道上,隋唐东征部队多次从这里进军辽东。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筹备东征,征“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55页。第二年春,隋军从泸河(今辽宁锦州市附近)、怀远二镇向辽东进发时,每名军士领取了100天的口粮,“又给排甲、枪矟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第5664页。大业九年(613年)东征时,负责督运军粮输往怀远镇的是当时担任隋卫尉少卿的李渊。④史载:“(大业)九年迁卫尉少卿。辽东之役,督运于怀远镇。”见刘昫等:《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页。史载:“炀帝征辽东,遣高祖督运粮于怀远镇。”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页。大业十年(614年),炀帝三征高句丽,“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八月己巳,帝自怀远镇班师”。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2《隋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691页。贞观十七年(643年)六月,“丁亥,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⑥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98页。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军东征,“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趋甬道,出高丽不意”。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第6218页。唐灭高句丽后,在此设怀远守捉军。
关于怀远镇的地理位置,学界颇多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一说在今辽宁辽中县境内,《奉天通志》卷七十《山川志》认为,辽中县“古城子村为隋唐怀远镇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奉天通志》说法进行了修正,将怀远镇定点在辽中县城。一说隋、唐怀远镇与辽、金梁鱼务相近,即今辽宁黑山县东姜民屯附近,持此说主要代表为中国著名东北史地学家金毓黻先生。一说在今辽宁阜新市西南,如《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的标注。一说在辽宁北宁市(今北镇市)境内,张博泉等人所著《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和孙进己、冯永谦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第2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第277页)均持这种意见。
先看“辽中说”。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筹备东征,曾积粮于泸河、怀远二镇。今辽中县城东边的蒲河是隋唐时期的辽河故道,古城子村则地处蒲河东即隋唐时期辽河故道之东,但此地当时属高句丽所有。隋军怎么可能把军粮运过辽河,而贮存于高句丽的辖地?认定怀远镇为今辽中县古城子村,显然于理不合。那么,今辽中县城位于隋唐辽河故道西岸,是否就可以作为贮粮基地呢?《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置辽西郡,并辽西、怀远、泸河三县以统之”;《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亦载:“燕州,隋辽西郡,……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现已勘定,辽西县(辽西郡郡治)在今辽宁义县东南张家堡乡王民屯一带,泸河县在今辽宁锦州市。①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隋唐时期,今辽宁西沙河、饶阳河下游至辽河下游之间是宽达200里的水网地带,称“辽泽”。隋唐辽西、泸河二县,均在今大小凌河流域,位于辽泽之西,而今辽中县则在古辽泽之东。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东征,于五月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第6220页。可见当时辽西与辽东之间交通运输的艰险困阻。如果隋唐怀远县(镇)在今辽中县城,那么它与其它二县之间就隔着“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的辽泽,彼此之间有效的行政联系和及时的军事策应,必然会受到巨大影响。换言之,将一个重要军镇置于交通不便且极易受到高句丽军队攻击的辽泽之东、辽河沿岸,使其呈孤悬之势,并在此贮存大批军粮,无疑是违背常理的。因此,怀远镇也不可能在今辽中县城。
再看“阜新说”和“黑山说”。根据《东北古代交通》一书作者王绵厚、李健才的研究,隋、唐军队由营州(治柳城县,今辽宁朝阳市)向辽东进兵,有北、中、南三条主要通道。北道,即从怀远镇向东北行,趋通定镇(今辽宁新民市东北高台子),由此渡过辽河,进攻高丽的玄菟城(今辽宁沈阳东上柏官屯古城)、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高尔山城)和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市劳动公园古城);中道,即东出怀远镇,渡过辽泽、辽河,进抵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南道,即从今辽宁义县南部七里河镇、张家堡乡一带向东,绕行辽泽之南,经盘山、沙岭(今属盘山县)、牛庄(今属海城市),折而东北行,至辽东城,向西南则至高句丽建安城(今辽宁盖州市东北青石岭山城)。③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年,第138—152页。在贞观十九年(645年)的战事中,李勣率唐军从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出发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趋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第6218页。这条记载说明,李勣军一边虚张声势,造成由怀远镇走“中道”东进的假象;一边从“北道”潜行至通定镇(今辽宁新民市东北高台子)渡过辽河后,直趋高句丽玄菟城(今辽宁沈阳东上柏官屯古城)。而今阜新市更在这一路线之北,将怀远镇置于今阜新市境内,显然失之过北,与地理形势不合。就黑山县姜民屯而言,从地理方位上看,它正处于李勣军“潜师北趋甬道”所走的“北道”之北,也不应是隋唐怀远镇的所在地。
“北宁说”是较为合理的一种意见。但是,隋唐时期的怀远镇究竟在今北镇市的何处呢?是否就在今北镇市市区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唐灭高丽后,在辽西置有燕郡、汝罗、巫闾、怀远等守捉军,其中巫闾守捉即驻于今北镇市市区,怀远守捉不会与之同在一地。根据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渡辽泽、辽河,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的行军路线和方向来判断,怀远镇应位于今北镇至辽阳之间的交通线上,并距北宁不太远的地方。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巡视东北地区,为驱逐沙俄侵略势力进行战争准备,翰林院侍讲高士奇受命扈从,并著有《扈从东巡日录》一书。康熙一行路过广宁(今北镇市)时,高士奇在其《日录》中记载道:“有唐文皇屯兵旧垒,在城东南三十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山东八·辽东行都司》“通定镇”条亦称:“唐垒,……在(广宁)卫东南三十二里,唐太宗征高丽,屯兵于此,因名。”这个“屯兵旧垒”很有可能就是怀远镇的旧址,大致在今辽宁北镇市东南柳家乡一带。
三、辽东古城
辽东古城是东北军事重镇营州的贮存基地。《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纪六》载,大业九年(613年)正月,炀帝准备二征高句丽,“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此条下胡三省注曰:“前伐高丽,围辽东,言即汉襄平城,今言复修古城,盖城郭有迁徙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山东八·辽东行都司》“通定镇”条云:“(大业)九年诏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即所置辽东郡城,以仍旧名,亦曰古城也。”认为所谓“辽东古城”就是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首征高句丽时设置在辽河西岸的辽东郡郡城通定镇(今辽宁新民市东北高台子)。
然而,稍加分析便会发现顾祖禹以通定镇为“辽东古城”的意见并不成立。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东征时,隋军只在辽河西岸攻取了高句丽的哨城武厉逻,并在此设置了辽东郡及通定镇①史载:“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贼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见魏征等:《隋书》卷81《高丽传》,第1817页。,并未攻取辽河以东高句丽的一城一地,高句丽的军事实力也未受到根本上的削弱。通定镇(原武厉逻)东距辽河仅有10里,将其作为贮粮基地,极易受到高句丽军队的攻击和破坏,此其一;其二,先隋各朝从未在这一带设置过辽东郡,以通定镇为辽东郡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即便当时对通定城进行了扩建,也应该名之曰“新城”才是,何来“古城”之说?显然,以通定镇为“辽东古城”,与当时的军事地理情势以及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皆不相合。
那么这个“辽东古城”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应当以辽东郡侨置于辽西为线索进行追寻。公元5世纪初,高句丽占领辽河以东地区后,北燕侨置辽东郡于今辽宁省西部大凌河流域,延至北魏。北魏辽东郡“治固都城”②魏收:《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营州·辽东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95页。,领襄平、新昌二县。固都城于隋朝而言,是前朝辽东郡故城,称之为“辽东古城”方名副其实。今北票市西境有顾洞河,曾名固都河,于今朝阳市区东北约11公里处汇入大凌河,固都城当距此河不远。再联系大业八年(612年)八月隋炀帝“敕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第5666页。(望海顿在今辽宁锦州市东南大凌河入海口处)的史事,我们可以做如下推测:大业九年(613年)正月炀帝诏令“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很可能就是为了贮存在望海顿由海运转为河运(经大凌河)而来至营州的中原各大仓的军粮;隋炀帝下令修复它,原因很可能是嫌泸河、怀远二镇的贮存能力不足,同时它们距离柳城也较远,不易于管理和调配,而“辽东古城”则完全可被纳入柳城的管控范围,其贮粮基地建好后,可以成为营州一带直接服务于对高句丽战争的军资基地。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辽东古城”应该就在今顾洞河与大凌河交汇处附近,即今朝阳市东北一带。
四、古大人城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载,唐太宗筹备东征时,在“北输粟营州”的同时,亦“东储粟古大人城”。廖德清主编的《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金盾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将古大人城今址置于辽宁锦县(见该书第379、390页),即今凌海市。这一说法显然有误。
其实,古籍中对古大人城的地理方位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一《河南道七·登州》“大人故城”条载:“大人故城,在县北二十里。司马宣王伐辽东,造此城,运粮船从此入,今新罗、百济往还常由于此。”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七·登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3页。北宋《册府元龟》卷四九八《邦计部·漕运》载:“太宗贞观十七年时征辽东,先遣太常卿韦挺于河北诸州征军粮,贮于营州;又令太仆少卿萧锐于河南道诸州转粮入海。至十八年八月,锐奏称:‘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黄县二十三里,北至高丽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岛接连,贮纳军粮,此为尤便。’诏从之,于是自河南道运转米粮,水陆相继,渡海军粮皆贮此。”②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册府元龟》卷498《邦计部·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966页。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六《山东七·登州府·黄县》“大人城”条载:“大人城,县东北二十里。志云:魏司马懿伐东夷,将运粮入新罗,筑此城贮之,以大人为名。”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6《山东七·登州府·黄县》,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55页。以上三条史料对古大人城的记载,虽然在名称、方位、道里上都不太统一,但所指无疑是同一处古城。综合来看,其地点应当在今山东龙口市东北方向海滨处。
五、三山浦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诏陕州刺史孙伏伽、莱州刺史李道裕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岛,越州都督治大艎偶舫以待”,④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220《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5页。准备再次大举进攻高句丽。第二年五月,太宗病逝,各项东征的准备工作暂停。
乌胡岛,亦作“乌湖岛”,即今庙岛群岛最北之隍城岛,隋唐时期地处山东、辽东之间海上交通要道上。⑤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177页;谭其骧:《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第145页。而关于“三山浦”的地理位置,史家一直没有搞清楚。各种文献资料中的所谓“三山浦”归纳起来大致有三处:一处是今山东莱州市北25公里处三山岛;一处在今辽宁大连市区青泥洼一带;一处即今辽宁大连市以东的三山岛。
《〈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将唐时之“三山浦”置于大连市以东的三山岛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篇》,1979年,第83页。,这明显有误。因为地名中之所谓“浦”,是指水滨或河流注入江海的地方。⑦《辞源》第3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92页。大连三山岛是海中岛屿,与“浦”字义不合。关于“三山浦”的位置,我们还是从史书有关山东到辽东半岛的地理记载中寻找。唐代贞元年间(785—804年)的宰相、著名地理学家贾耽《皇华四达记》记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是一条从今山东半岛纵渡渤海海峡,经辽东半岛南岸、朝鲜半岛西岸近岸水域南行至新罗、日本的沿海航线。《新唐书》载:“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⑧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7页。另,此处原本文句明显有倒误,“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应为“鸭渌江千里至唐恩浦口”。其中,“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是指今庙岛群岛各岛,“青泥浦”是指今大连市区青泥洼,“桃花浦”即今大连普兰店市东清水河口之红水浦,“杏花浦”即今大连庄河县碧流河口之花园口。可见当时人们对“岛”和“浦”的区别是很严格的,大连三山岛只能称“岛”而不能称“浦”。
那么,辽宁大连市区的青泥洼,唐代时称“青泥浦”,它是否就是唐军东征的储粮地点呢?清人吴承志在《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中称:“小滨岛至三山岛海底俱污泥及硬泥,浅处泥滩,青泥浦由之而名。今小滨岛市埠尚沿俗名青泥洼,是古名之遗。”小滨岛在今大连市西南,青泥浦即在此处。现在各种介绍大连市的资料均称:今大连市区一带东望海中三山岛,在汉魏时称“三山浦”,唐时改名为“青泥浦”。但是,笔者利用《二十五史》网络版进行检索,并查阅了《东北古史资料丛编》(东郭士等编,辽沈书社1989年版),都没有找到今大连市区在汉魏时称“三山浦”的依据,唐以前各史书中凡称“三山”者也都不包括大连三山岛。而莱州三山岛称“三山”却由来已久:《史记·封禅书》载,战国、秦、汉时,帝王祭祀“八神”中之第四神“阴主”于“三山”,“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也”;《汉书·郊祀志》载,宣帝“祠参山八神于曲城”,此“参山”也即三山;《汉书·地理志》亦载:“东泰山,汶水所出,东至安丘入维。有三山、五帝祠。”那么,“青泥浦在唐代以前叫三山浦”的说法从何而来的呢?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有学者主观认为史书中记载唐军储存粮械的“三山浦”是今大连市区海滨地带,而它在《新唐书》中又明确地叫做“青泥浦”,于是便臆断“青泥浦”在唐代以前称“三山浦”,只是在唐代改了名。但即便“青泥浦”当时又称“三山浦”,也不会是唐军的储粮重地。因为唐太宗在位时辽东半岛尚有高句丽军队盘踞,试问唐军怎么会把粮械储存在如此危险的境地呢?再联系前文所引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的诏令内容来看,当时是由越州都督负责修造大船(即“大艎偶舫”)以待军用,并未渡海,由此来看,孙伏伽、李道裕用以储存粮械的三山浦也不可能在辽东半岛。
从各种情况分析来看,“三山浦”只能是今莱州的三山岛。莱州三山岛地处海滨,北、西、南三面环水,王河(旧称万岁河)在它的南面汇入渤海,只有东部与陆地相连,称之为“浦”名副其实。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储粮械于三山浦和乌胡岛,而此三山岛当时属莱州管辖,由莱州刺史李道裕负责粮械储积工作自是顺理成章。顾祖禹指出:“三山岛在(莱州)府北五十里,海之南岸,……贞观二十二年,将伐高丽,……储粮械于三山浦、乌(胡)岛。”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6《山东七·莱州府·掖县》“高望山”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34页。这也说明唐代“三山浦”即今莱州市北的三山岛。
战争是在一定地域环境中展开的,对古代军事地理进行科学考证并得出合理结论,无疑有助于深化古代军事史研究。然而时间的流逝、山川的变易及相关史料的缺乏,使得目前尚有诸多古代军事地理问题无法查证,这直接影响古代战争史的研究。隋唐对高句丽战争所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需要结合古代辽河流域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交通路线和高句丽的山城防御体系以及隋唐军队的战略战术等进行综合研究,难度较大。对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目前有的在学术界尚存争论,如玄菟城、新城的地理位置问题;有的凭借现存史料已无从可考,如隋唐军队重要渡辽地点临辽顿,目前只能推知其在辽河西岸,并不能确定其具体位置;有的则仅能靠个别古迹进行推测,如高句丽于贞观年间在辽河以东修筑的千里长城,有学者根据现存于吉林省德惠市、农安县境内的土筑边岗推断:这段高句丽长城起自今德惠,向西南延伸,经农安、梨树、开原、新民、沈阳、海城到营口入海。②王健群:《高句丽千里长城》,《博物馆研究》1987年第3期;李健才:《唐代高丽长城与夫余城》,《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诸如此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于相关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