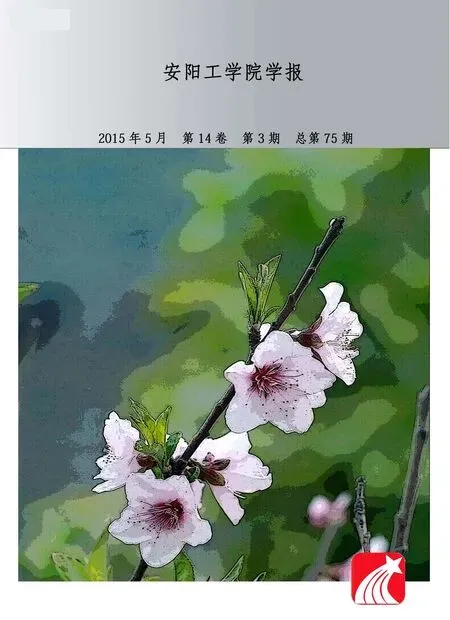论霍桑创作风格与时代的关系
孙根(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06)
论霍桑创作风格与时代的关系
孙根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06)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在霍桑生活的年代中,美国资本主义及迅猛发展,工业文明也取得极大进步,但是在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重压之下,人们的个性逐渐消失,社会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正是在这种极度迷茫、浮躁的社会中,霍桑独具一格,坚持自己的秉性,以模糊不确定的表现手法,通过变幻、多样的人物形象在批判“恶”与“美”之间用自己的作品去揭示现实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异化,企图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以实现真正的“诗意的栖居”。
霍桑;时代背景;创作风格;异化;精神家园
纳撒尼尔·霍桑是19世纪美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极负盛名。纳撒尼尔·霍桑生活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美国,他是以反现代性的审美视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实质,对资本主义腐蚀人性、异化人性以及异化社会的本质不以为然。纳撒尼尔·霍桑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品质,用自己的作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真实面貌。他通过一些模糊不定的艺术表现手法,利用变幻、变形艺术技巧去构建自己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努力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善”与“恶”的真实本质,希望人们能够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和精神异化的状态,去寻求与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从而回归于人类社会真正的精神家园,以期待实现真正的“诗意的栖居”。
一、霍桑时代的社会境遇
霍桑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在美国开始大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实施对外扩张、对内残酷镇压印第安人的政策,大量的欧洲居民也开始涌进了美国社会,这必将带来诸多新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强烈地冲击着美国社会旧有的秩序,使得美国社会面临着诸多巨大的挑战。在这种巨大的挑战面前,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日益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在这种喧嚣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异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而陷入深重的黑暗之中。此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一片空虚,就像艾默生所说的那样:“商人极少认为他的生意具有理想的价值,他被本行业的技艺所支配,灵魂也沦为金钱的仆役。牧师变成了仪式,律师变成了法典,机械师变成了机器,水手变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1]64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语境之下,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着或多或少、或积极或消极的反叛。
(一)个性的消失
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全世界尤其是欧美各国,都近乎疯狂的追求工业发展,实现现代化,建设资本主义强国。然而这样疯狂追逐工业革命的结果,虽然带来了工业的巨大进步,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有力前进,但是这些浮躁喧哗的物质文明却没能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找到一个安逸的栖身之所。相反,它给人们带来的是势利的物质生活、无止境的喧嚣浮躁、精神生活的匮乏以及人的个性的泯灭,动摇了人们的心灵,迷惑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它是“体系的主流,生命和本质的东西,而这种体系曾将自身溶于人类的要害器官,并用它致命的支配力抑制了人类原来的天性”[2]884。这与卢梭的观点有相同之处,他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变坏了”。[3]43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道德意识不断沦丧,物质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带了种种的丑恶现象。人们不再表现的富有自由之人格与独立之品性,人类的天然秉性已经被工业文明的物质利益淹没了。例如《红字》中的齐灵沃斯是一个医生,但是科学并未让他走向理性,他身上充满着复仇的烈焰,体现着卑鄙与邪恶,这就是科学使人们的个性泯灭的真实代表。
(二)社会的异化
异化的概念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的,他提出“精神异化论”。而指出异化实质的是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概念。它是一个哲学范畴,有着自己的哲学深意。主要表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现象:主体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实践中创造了客体,而客体却又反过来拒绝或扼杀了主体的需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异化”现象。
异化首先表现为社会本身的异化,“即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官僚机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成为人自由生存状态的对立物。”[4]在霍桑的著名小说《红字》中,以贝灵汉总督和威尔逊牧师所代表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就是主宰一切的力量,他们可以对辖区内的人们进行随意的惩罚。虽然从表面看来,这个政府是公正严明的,但是它背后却是无尽的黑暗和深渊。这样的一种社会已经被宗教的偏执于罪恶而掩盖了真实本性,成为人们精神复归的羁绊和枷锁。
异化再次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异化,这其中又包括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两个方面。人与人的异化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相互之间的怀疑,猜忌。譬如说海斯特和梅斯代尔之间,一个勇敢,一个懦弱,彼此差异巨大,两者之间也十分隔膜。而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是指整体的人与个体的人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为人们在强大的社会体制中显得无能为力。海斯特一度出走却又返回家乡,她从一个独处的个体走向了社会整体,从社会的对立面走向了与社会的和解,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已经成了社会的组织者和安抚者,而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给她造成的影响。
二、霍桑的时代境遇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说过,文学的四要素是“作家、世界、读者、作品”。毛泽东也说过:“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脑中的反映的产物。”[5]860由此可见,作家的艺术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极为密切。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创作从来都不是脱离社会的,而是深入社会,和社会紧密相连的。一个作家的艺术构思、形象创造、语言表达,每一步都沉浸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作家创作的材料、主题、语言等都是来源于社会,由社会提供的。即使如卡夫卡那样的作家,有时候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其实也是社会生活在头脑中的反映。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文学的艺术分风格自然也印证着时代风格,这两者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
霍桑的时代促生了他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正是基于霍桑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迅猛的发展、社会和人性的异化,直接促使了他以模糊不确定的表现手法,通过变幻、多样的人物形象在批判“恶”与“美”之间去揭示现实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异化,企图寻找人类精神的家园以实现真正的“诗意的栖居”。
(一)在批判“善”与“恶”之间摇摆
资本主义社会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并没有给霍桑带来对于未来社会的无限憧憬和向往,反而给他带来的是无尽的迷茫和失望。霍桑用疑惑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呈现在他眼中最多的是人性与社会的恶多于善,对于人类心灵的堕落感到失望和悲观。于是霍桑在自己的作品中最大限度的去揭示了人性的罪恶和堕落,他的作品充满着对于腐化社会和堕落人性的批判与讽刺。《红字》中的齐灵沃斯有着深厚的文学知识,但是这些并不能解决他的爱情,他的家庭,他的幸福,反而让他变成一个自私狭隘的复仇者,霍桑对他是憎恨的,但是同时,他又对齐灵沃斯表现出了一种同情,他认为这些人性的恶,社会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都是源于社会中的“恶”,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伦理道德的腐化和新观念的虚伪。所以霍桑对深受其害的这些人物在表现憎恨的同时又多少有一些同情。霍桑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这种徘徊于“善”与“恶”之间的挣扎与动摇。
(二)多样、梦幻的人物形象
“文化是多元的,不同质的文化蕴含着人对自我的不同解释和理解,因而不同质的文化映照出的人的形象也是各有差异的”[6]7。霍桑生活的时代让他感到迷茫,可以说他与这样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霍桑利用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霍桑的时代是社会异化的时代,是人性异化的时代,社会的光怪陆离,人性的变态扭曲,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作者想要极力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与无奈,他以形形色色、多样变幻的人物形象来展现人们在异化社会中的种种心态与处境,传达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与感悟。
霍桑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多是模糊的象征,而这也是源于作者(甚至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解、一种无奈,更是一种迷茫和虚妄。他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两重交替的性格,让人捉摸不定,真假难辨,对于这些变异的多样人物,霍桑既有同情又有批判,而这些梦幻人物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他们集中反映了霍桑对于工业社会的感受,也传达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变革的认识。
(三)模糊不定的艺术手法
霍桑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与他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理解是相辅相成的,他不停地摇摆在“善”与“恶”的边缘,以多样、变换的人物形象来展现自己的思想。但是他对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却又是模糊不定,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工业社会中的这种“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恶”,他探索“美”的途径是曲折的,结果也是十分渺茫的,这种曲折的途径反映在他的思想当中,也对他的创作风格产生影响。
人性和社会的异化使得霍桑处于一个极度迷茫与徘徊的心境当中,他的思想也因此变得复杂而矛盾。他的作品中描述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带有很大模糊性的世界,这其中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真或者假、实或者虚、现实的人或梦幻的人,所有的这一切都难以让人分辨,对于这些,霍桑的心里都是矛盾的,所以在小说中揭示自己对于异化现实的反思,自然而然就选择那种罗曼史的形式,选择了以这种不确定的象征手法来满足自己对于现实的反抗与无能为力的矛盾的双重要求。
三、结语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和人性的异化影响到了文化的各个领域,使得整个的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改变,导致了自我人格的丧失、人际关系的落寞。人性的异化给文学艺术的创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变化,霍桑的文化观念也在改变,他需要极力追求一种能够抒发自己情绪、揭露社会弊病的表现方式,文学便成了他首先选择的途径。
霍桑面对当时的社会中的人生、人性和社会,他能够自觉地运用作品加以表现,去自觉地揭露社会以及人性的阴暗面,激发社会的反思,希望寻找到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摆脱精神的困扰,进入真正的人性化的世界中去,从而实现人类的真正意义上的“诗意的栖居”。
[1]艾默生.论美国学者[M]//波尔泰.艾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上.北京:三联书店,1993.
[2]罗伊·哈维·皮尔斯.霍桑集:故事与小品:新亚当和夏娃下[M].北京:三联书店,1999.
[3]卢梭.爱弥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4]方文开.论霍桑的审美现代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5(5):134.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王彦永)
I06
A
1673-2928(2015)03-0092-03
2015-04-11
孙根(1990-),男,安徽池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