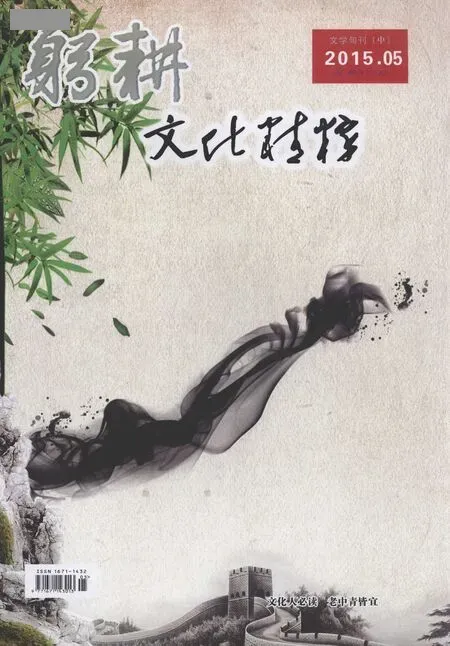乡间野菜
◆ 王振东
野菜,饥馑之年的救命菜。历史上的每次大饥荒,都是野菜让无数人的生命得以延续。我没有遇上过大饥荒,没有完全靠野菜、树皮充饥的经历,只是在儿时春上缺粮时,母亲才剜来野菜,充实一下碗里的内容。明代徐光启编纂的一部《农政全书》,收录了朱元璋第五个儿子朱橚著述的专门介绍野菜的书,叫《救荒本草》,书中写到的野生植物有414种之多,可见野菜在古时已被人们所认知,也足见野菜对农人是何等的重要。如今,农人已不再靠野菜充饥,野菜倒成了吃多大鱼大肉的人们调剂口味的上等菜品,想来令人感慨。
荠菜
荠菜,我们那地方叫荠荠菜。它属十字花科,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羽状分裂,裂片有缺刻,花白色。花开时,远远望去,恰似天空的一颗颗小星星,在绿色的田野上闪烁。但有的地方叫它鸡心菜、枕头菜、地菜。我无法一一考证这些地方为什么给它起这样的名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名字都赋予了它一定的含义吧!
荠菜是野菜中味道最鲜美的菜,也是营养和药用价值最高的野菜。它所含的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等均高于一般蔬菜,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但在我小的时候,吃荠菜是为了果腹,根本不知道现代人发现的这些价值。那时村里所有人家过的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每到开春荠菜发芽,人们都蜂涌到田野里挖荠菜,大有风卷残云之势,不待荠菜长大,就被人们抢挖一空了。拿回家洗净,或拌上苞谷面蒸菜吃,或放入锅里煮,再搅点苞谷面做成菜汤喝,一顿饭就这样打发了。
现代人吃荠菜最经典的做法是包饺子。我的家乡曾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荠荠菜,包饺子,不够小妮儿一碗吃。采摘一把鲜嫩的荠菜,择去老叶,掐掉毛毛根儿和花茎,洗净后在锅里焯一下,淋去水分,剁碎,再剁一点猪肉或炒几只鸡蛋,加上葱花儿、姜沫儿、盐和小磨香油拌匀,半盆绿莹莹、香喷喷的荠菜馅就做成了。不大一会儿,一锅薄皮大馅的饺子就出锅了,咬一口,那个鲜劲就甭提了!除了包饺子外,荠菜还可以凉拌,也可以做汤。既好看又好喝的汤是荠菜豆腐羹。把豆腐切成苞谷粒大小的块,加盐、葱花儿和姜粒儿在锅里煮一会儿,勾芡后放入嫩嫩的荠菜段,锅开后淋上小磨香油,白绿相间的荠菜豆腐羹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汤,白的像美玉,绿的似翡翠,喝起来,润滑爽口,清香扑鼻,是汤中上品。
如果野菜也论资排辈的话,荠菜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家乡不仅有“阳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谚语,还流传着“春食荠菜赛仙丹”的说法。可见它不仅是美味一碟,更是灵药一方,具有凉血止血、清热利尿、清肝明目的功效。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荠生济济,故谓之荠。”在我的家乡,荠菜还有一项特殊的功能——补亏。农历三月初三这天,薅一把荠菜洗净,放在锅里煮一会,然后把鸡蛋打入锅里,做成荠菜荷包蛋。村里人说,荠菜荷包蛋营养价值极高,对身体虚弱的人有很好的疗效。
荠菜其貌不扬,但很泼实,田间地头、沟畔渠旁都有它的身影。早春时它枯黄中略现青色,不容易被人发现,一场春雨过后,它开始返青,渐渐露出俏模样。我时常想,春寒料峭的时候,它为啥能像小麦一样开始返青?在一次挖荠菜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麦田里的一棵荠菜,它的根很长,这引起了我的好奇,细心挖掘,尽量不伤及它的根系,挖出后把整棵荠菜拿回家一量,好家伙,其根竟有25厘米长!小麦的根系就是如此发达,难怪它也像小麦一样能抗寒越冬哩!
荠菜的身份尽管卑微,但它在文人雅士眼里却是尊贵的。辛弃疾曾在两首诗里赞颂荠菜:“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南宋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菜勿忘归。”宋代大诗人苏轼也诗曰:“时绕麦田求野菜,强令僧舍煮山羹。”而清代诗人、画家郑板桥不仅将荠菜入画,还在画上题诗:“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望却异乡情。”一种生长田间路旁的普通野菜,竟引得千百年来文人如此不惜笔墨,恐怕也只有荠菜才有如此的身价吧!
灰灰菜
初春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县城的赵河公园散步,在一沟畔处,发现一蓬绿十分眼熟——它们的茎粗状,有棱和绿色或紫红色条纹;叶片菱状卵形,边缘呈锯齿状,向上的一面呈绿色,向下的一面呈灰色。我忽然记起,这蓬绿是灰灰菜。小时候因为家里缺粮,母亲在初春时常领我去田野里剜野菜,篮子里就躺有灰灰菜,它让我家原本稀汤寡水的碗里变得热闹、充实起来。
灰灰菜的学名叫“藜”,别名野菠菜、婆婆菜、野灰菜等。“灰灰”二字并不是因为它是灰色的,而是因为它的叶子背面呈灰色,并且还带有一层如灰尘般细细的白色粉末,所以家乡人叫它灰灰菜。
灰灰菜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充其量就是一种杂草,人们只所以称它为菜,是它可以当菜吃。可以吃的杂草就是菜了。灰灰菜味道鲜美,口感柔嫩,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脂肪等,含钙量每百克高达209毫克。当然这些都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后的今天才知道的,过去谁知道这些?只知道吃它可以充饥。那时的春上,我家常缺粮,母亲也和许多人一样去田野里剜野菜,或煮或蒸,以此稍稍撑大家里人的胃。母亲剜回灰灰菜后,把菜反复揉搓,尽量把上面的绒毛搓掉,然后用清水反复清洗几遍,拌上苞谷面蒸熟吃,或下到搅了糊糊的锅里煮汤喝,有时还可以放锅里焯一下,放上盐凉拌吃。就是这样不起眼的野菜,让家里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荒春。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灰灰菜不可多食,因为灰灰菜属于含有嘌呤类物质的光感性植物,如果多食后再被阳光暴晒几个小时,可引起急性光毒性炎症,会出现皮肤红肿,周身刺痛、刺痒等症状。所以吃灰灰菜时,一次别吃太多,而且吃后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强烈的日光照射。想想,过去的人们在不知道这些时,身体受到了痛痒的何等折磨!就是知道,恐怕也顾不了那么多——饥饿比痛痒更难以让人忍受。
灰灰菜不像在温室生长的蔬菜那样娇嫩,倒像一个灰姑娘,虽地位卑微,但极耐贫瘠和干旱,没有架子,田间地头、荒野路旁和房前屋后,只要有土的地方,就有灰灰菜的身影。灰灰菜结籽甚多,十分容易繁殖。它一般不是孤零零地生长,往往是一簇簇、一片片,很有气势,很有威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但为灾荒之年黎民百姓提供了聊以果腹的食物,而且也给贫瘠的大地带来了生机。
灰灰菜自古就是一种被人们食用的野菜。《史记》中已有“藜藿之美”的说法。藿,指豆叶。藜和藿经常并称,意为贫贱之菜,唐朝时仍为穷苦人家食用。姚合《过张邯郸庄》云:“野饭具藜藿,永日亦不饥。”韩《卜隐》云:“世间华美无心问,藜藿充肠苎作衣。”就是中等人家,有时也会烹食藜菜。徐夤《偶吟》:“朝蒸藜藿暮烹葵”,就反映了藜在疏食中的一席之地。《韩非子·五蠹》中的诗句“尧王天下,粝粢之食,藜藿之羹”,表明尧帝那时也吃灰灰菜。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是,古代名人吃灰灰菜,大多不是为了果腹,如果真的沦落到靠野菜充饥,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对野菜赋诗咏吟?人家吃的是一种品位,就像现在城里人吃野菜一样,只是换换口味罢了。
马齿苋
马齿苋,叶青、梗赤、花黄、根白、籽黑,故又称“五行草”,有些地方还叫它长寿菜、生命菜、安乐菜,而我们那地方却叫它马石菜。这些名字,犹如五月麦子的芳香,八月红薯的甘甜,让人感到亲切、温暖。种种称谓,都那么富有诗意,那么恰如其分,说不出哪一个更悦耳,哪一个更确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饥馑年代对人类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的野菜。
我在数说这些名字的时候,突然想起小时候跟母亲去田野剜马齿苋的情景。那时家里分的粮食少,一年至少有三四个月没粮食吃,作为家庭主妇,母亲只好把数量不多的粮食平均到全年吃,使本就不稠的碗里变得更加稀疏。为了让碗里的汤水变得稠些,夏秋两季,母亲就去拾麦穗、溜红薯;到了冬季,就捡白菜帮、萝卜缨;开春以后,就去剜野菜。记得有一年春上,我七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哪里知道家中缺粮的窘境,尽管肚子没吃饱,但还是满地奔跑着捉蝴蝶。每捉到一只蝴蝶,就拿去让母亲看。母亲手提篮子,两眼紧盯地面,生怕漏掉每一棵野菜。她并不看我递上去的蝴蝶,只“嗯”了一声,继续低头寻找野菜。我不知道母亲剜的野菜叫马齿苋,只看到那菜的茎是棕褐色,叶为绿褐色,叶片长而肥厚,手一碰就会碎掉。我问母亲那是啥菜,母亲说是马石菜。那天,母亲的运气不赖,竟剜了一篮子马齿苋。回到家,母亲把菜洗净,拌上苞谷面放笼上蒸,出笼后浇上蒜汁水,味道酸酸的,特好吃,现在还能忆起当年蒸马齿苋的香味。后来,母亲用马齿苋又做出了疙瘩汤、菜卷、凉调菜……在马齿苋生长的旺季,母亲天天去田野里剜,剜回后洗净,放在开水里炸熟,捞出后晒干存放起来,入冬后用水泡开、剁碎,用红薯面或苞谷面包角子(形状像饺子,但比饺子大)吃,或和在苞谷面里蒸窝头吃。正是有了马齿苋等野菜,才让我家度过了缺粮的岁月。
随母亲剜了几次马齿苋后,我们小孩子也认得马齿苋了,就结伴去田野里剜。篮子剜满后,女孩子就把马齿苋叶子撸掉,把茎一正一反一小截儿一小截儿掐断,只连着一层皮,挂在耳朵上当耳坠,挂在脖子上当项链。她们还会把“耳坠”、“项链”放在一起比,看谁做得精细,评出最好的,大家会为她鼓掌。得到表扬的那一个,忘却了饥肠辘辘的肚子,自豪的笑一直挂在脸上。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让贫穷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戴上首饰,让她们的童年多了些许欢声笑语。女孩子们忙碌的同时,我们男孩子也不甘示弱,把马齿苋的茎掐成一寸多长的段儿,弯成一张“弓”,用弓把上下眼皮撑开,把眼晴撑得像牛眼,两只手弯曲成牛角状,贴在太阳穴上,做出十分吓人的怪状,逗得伙伴们仰天大笑,惊得落在田野上的小鸟箭一样飞上天空。
马齿苋性耐旱,生命力强,田间地头、屋边庭院都能找到它们。我曾经在所住房屋的山墙头儿发现了几棵马齿苋,那里虽少见阳光,但它们还是顽强的生长着。它谦卑,不事张扬,从小就匍匐在地面,默默地吸吮着大地的养分,使自己变得强壮,时刻准备着为人类牺牲自己。
马齿苋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自古就引起了文人墨客的青睐和赞誉。唐代大诗人杜甫最爱品尝的野菜就是马齿苋,他在《园官送菜》中吟咏道:“苦苣针如刺,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园。”而它的药用价值更是不可忽视,唐代医学家陈藏在《本草拾遗》中写道:“人久食之(马齿苋),消炎止血,解热排毒;防痢疾,治胃疡。”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它对糖尿病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哩!
曾经在饥馑年代为农人的温饱做出巨大贡献的马齿苋,在物质丰裕的今天,也是城里人追逐的宠物。每次去饭店吃饭,我都要点一盘马齿苋蒸菜。吃着酸酸的、香味扑鼻的蒸菜,仿佛穿越时空,又回到了吃马齿苋的童年。
蒲公英
在沟边,在路旁,在田间地头,在房前屋后,我看到蒲公英匍匐在初春的边沿。成片成片的蒲公英,好像春天廉价批发的墨绿色纸,张开并不受人青睐的粗糙叶片,遮挡着脏乱的沟沿和寂寥的路边,给春天带来了无限生机。
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婆婆丁,我的家乡则叫它黄花苗,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含白色乳状汁液,叶子倒披针形,羽状分裂,花黄色,既可食用,也可入药。据《本草纲目》记载,它性寒、味甘、微苦,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退黄之功效。此外,它还有催乳作用,对治疗乳痛十分有效。《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还少丹”一方,便是以蒲公英为主制成的。
我小时候,家乡贫穷,缺医少药,人得了大病,只好等死;得了小病,就用偏方治。记得有一次,我的嗓子疼,小便呈赤黄色。母亲说是上火了,得赶紧败火。母亲去田野里剜回蒲公英、毛毛根,又去苇塘挖回芦苇根,放到锅里一起熬,熬成“三根汤”让我喝,一次喝一大碗,这样连喝三天,还真见效,嗓子不疼了,尿也不黄了,我又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样在村街上疯玩起来。
在生活困难时期,蒲公英的最大功用是食用。每到初春时节,几场春雨过后,田野里就长满了鲜嫩碧绿的蒲公英、荠荠菜等野菜,这时喊上几个小伙伴,挎上篮子,唱着儿歌,连蹦带跳地向田野进发。我们散落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像一只只颠簸的小船,晃动着、起伏着、惊呼着,一边说笑,一边比赛剜野菜,看谁剜得又好又多。不长时间,每个人篮子里的野菜都满登登的了。剜时,若蒲公英的叶或根被扯断,会有乳白色的汁液(我们那地方叫“津”,就好比人的唾液。如红薯津、构树津等)渗出来,沾到手上,没多久就生成黑黑的斑点,回家洗了手,抓起馍都带着一些苦味,似乎那苦穿透肌肤,渗入骨髓了。母亲总是变着法儿,把蒲公英的苦味减少变淡,做成一些饭食,让我们一家人充饥。凉拌蒲公英。家乡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黄花苗,油盐调,大人小孩儿吃了好……把洗净的蒲公英的嫩叶焯一下,用冷水浸泡降温后,挤去水分,佐以盐、醋,淋上香油,也可以浇上蒜泥或辣椒油,吃起来脆生生的,鲜美可口,清香开胃。蒲公英饺子(包子)。将蒲公英嫩茎叶洗净水焯后,挤干水分,剁碎,加佐料调成馅儿,包成饺子或包子。蒲公英蘸酱。选择鲜嫩茎叶淘洗干净,淋干水分后蘸酱吃,略有苦味,苦中有咸,咸中带苦,味美爽口。蒲公英蒸菜。把洗净的蒲公英拌上苞谷面,放笼上蒸,出锅后浇上蒜泥,别有一番风味。蒲公英炒鸡蛋。把洗净的蒲公英切成小段,打入鸡蛋里炒。炒熟的鸡蛋金黄,蒲公英翠绿,色美味佳。不过这个菜只有在家里来了客人,或家里某个人生了病时,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味。
暮春,蒲公英老了,簇拥的叶片中间会伸出一支细长中空的莛子,像一把张开着的洁白、毛茸茸的小伞。我和小伙伴们会顺手摘下身边蒲公英的白色蓬松柔软的绒球,玩吹蒲公英的游戏。据说,能一气吹掉一整束白毛种子,就会带来好运。我们噗噗地吹着,白色的绒球左右摇晃,飘洒出一朵朵洁白的小伞,像天女散花般飞去。这时,我们就会欢快地唱起来:蒲公英,开黄花,花儿落了把伞打。小白伞,长长把,风儿一吹上天啦。落到哪儿,哪儿安家,明年春上又开花。
蒲公英谦和、低调,整个身子隐逸在草丛中,从不高高站起显示自己。它像一位甘守寂寞、默默笔耕的文人,坚守着自己的净土,只有在开花时才敢伸出头来,但它不是为了张扬、卖弄,只为伸头开花后盼春风把它捎去远方,让无数子孙用它们的身姿把远方的大地伴靓。
面条菜
面条菜虽不属我们河南独有,但在河南分布最广,吃法最多。
面条菜的学名叫啥,我没有考证过,也没有去考证的想法,但它有很多别名:麦瓶草、米瓦罐、梅花瓶……而在我的家乡叫面条棵,因其叶片细长,形似面条而得名。
面条菜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腺毛,节部膨大,叉状分枝,开蓝色或红色小花,基本生长在麦田里。由于在麦田里生长,有的甚至长在麦笼里,麦菜互争水分、阳光,面条菜尤其显得势单力薄,因此长得瘦瘦弱弱,如果不仔细寻找,还真难发现它们哩!
面条菜和其它野菜一样,在生活困难时期曾经牺牲自己的身驱,延续了无数人的生命。面条菜在我们家乡吃法众多:凉拌、做馅、炒菜、煲汤等等,每种做法都能吃出菜的鲜味,但最主要的做法是做蒸菜吃,做法也不复杂:往洗净淋干的面条菜里倒少许油,轻轻地揉搓,让油均匀地附着在菜的表面(这样可以避免蒸出的菜太湿),然后浇上蒜泥、辣椒油,还可以加一些炒熟的芝麻或炒熟研碎的花生粒儿,就可以吃了。吃后只一个感觉:真得劲!
面条菜除食用价值外,还有养阴除热、调经止血的功效,可治虚劳咳嗽、月经不调、吐血等症。夏季把它割下来晒干,需要的时候,煎汤内服,具有很好的保健和治疗作用。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曾经让很多人免遭病痛折磨。
面条菜的一生是短暂的,更是平淡的,虽然总是不断地奉献自己的生命,却从不被人们所注目,相对于荠菜、灰灰菜等野菜被文人墨客的称颂,我们在无数的文字里,始终没有发现面条菜的名字,哪怕一句的颂扬。对于这样的不公,它很大度,很绅士,没有一句怨言,像老黄牛一样,在默默地劳作一生后,最后被人们剔骨吃肉,奉献终生,无怨无悔。自初春发芽起,到麦子收割止,除了被人们剜去食用外,面条菜就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茎叶是一色的枯黄,让人看了有些凄凉,更有些心疼。燥热的南风刮过,黄黄的枯叶抖出细碎的、哀婉的声响,听着仿佛是一声声低沉的哭泣。随着人们把麦子割倒,它们也随着麦子一样倒下,一样被石磙碾碎,但它们却在粉身碎骨之前,将成熟的种子悄悄地播撒在麦田,开始孕育新的生命。
在评价一样东西的价值时,人们往往在需要它时,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甚至把它奉为“座上宾”,来称颂它,赞美它;一旦不需要它时,就会把它弃之一旁,甚至斩草除根。面条菜就是这样的命运。在生活困难时期,面条菜是一种救命菜,如今人们不需要它救命了,就成了一种杂草。每年刚开春,村人就在麦田里喷施大量除草剂,让面条菜慢慢枯萎,直至死去。这种死法比起被人们吃掉的死法,未免有点凄惨,实在令人哀婉、叹惜!
刺蓟菜
写下刺蓟菜这个名字时,我忽然想起一则医药典故:三国时期,庞统在一次战斗中身中数箭,血流如注,跌于马下,士兵中有知医识药者,忙从道旁扯来一把草,揉搓后塞入他的伤口,很快止住了血。这种草,我小时候就见过,它棵棵直立,高逾尺许,叶片上长有细密的针刺,开紫红色小花。它就是刺蓟菜,学名大蓟,我们那个地方叫刺角芽。《救荒本草》一书中记述的400余种野菜,第二个记述的就是刺蓟菜:“出冀州,生平泽中,今处处有之。苗高尺余。茎叶俱有刺。性凉无毒。”
记得我六岁那年秋天,母亲去东南地给生产队摘棉花。因为家里没人照看我,母亲就把我领到了地里,嘱咐我在地头玩。我很听话,坐在地头玩泥巴。天空像一面用水洗过的镜子,湛蓝深邃,清澈透明;秋风像少妇的玉手,轻抚面颊,挠得人心里发痒;蝈蝈像要发泄心中的郁闷,一刻不停地叫。玩够了泥巴,我被蝈蝈的叫声吸引,扔下泥巴,循着叫声找去。我要逮一只蝈蝈,装在笼子里玩。我蹑手蹑脚地向蝈蝈靠近,还没走到近前,蝈蝈的叫声便戛然而止。四下找寻,连蝈蝈的影子也没看到,倒惊飞了成群的蚂蚱:有拇指般粗细,像成熟庄稼颜色一样的“老飞头”;有和绿草颜色一样的“老瘪”;有扇动翅膀发出吧嗒吧嗒响声的“登倒山”……我追着满天飞跑的蚂蚱,眼睛里伸出了一根根草棍儿,恨不得把它们一一串起来。突然脚被绊了一下,身子直直地朝前趴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膝盖重重地磕在地上,划了几道血口子,火辣辣地疼。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母亲听见我的哭声,赶紧跑到我身边,见我的膝盖浸出了血,心疼得泪都快流出来了,让我坐地上别动。母亲的目光向四周扫了一圈儿,伸手扯了一棵草,压在两只手掌中间一阵揉搓,掌缝中就流出绿绿的汁液,凑近我的膝盖,使劲一挤,汁液便滴到伤口上。这样连滴几次,最后把揉碎的茎叶拍成菜饼子,捂在我受伤的膝盖上。说来也怪,一阵轻微的刺疼后,血不流了,伤口居然也不咋疼了,只觉得像有无数根小针扎着一样,有点痒……这种被母亲揉搓的草,就是刺蓟菜。当时,目不只丁的母亲绝对不会知道一千多年前的庞统也用过刺角芽止血消炎。我长大后问母亲是咋知道刺角芽的这种功用时,母亲说,我小时候也磕破过腿,你姥姥就是用刺角芽为我止的血。有一次我流鼻血,你姥姥就揉了一疙瘩刺角芽,塞到我的鼻孔里,血立时就止住了。这些法儿,都是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刺蓟菜是一种能吃的野菜。第一次听母亲这样说时,我吓了一跳,问母亲,刺蓟菜混身都是刺,吃着能不扎嘴?母亲说,咋不扎嘴?没粮食时,扎嘴也得吃,总比吃坏红薯、大雁屎强。听你姥姥说,民国十八年大旱,庄稼旱死,野菜也都干枯了。只有刺蓟菜,困为根扎得深,才没有干死。你姥姥每天去田里剜刺蓟菜,煮熟了吃。正是刺蓟菜,才让你姥姥一家熬过了年成。我听了心里一阵刺疼,像吞了一把刺蓟菜。好在我没遇上过大饥荒,一生只吃过一回刺蓟菜。那年春上,母亲剜回一篮子刺蓟菜,择掉根,用水淘净,拌上面,放上盐,蒸了一锅菜团子。那尖尖的针刺,因面搅得少,包不住菜,以至于蒸熟后,刺仍很锋利。我咬了一口咀嚼,顿感像嚼一棵蒺藜,咽时,扎得喉咙生疼;进肚里,像吞了一只刺猬。后来,我家再吃刺蓟菜时,我都有一种恐惧感,说啥也不吃了。母亲嗔怪道,作孽吧,要搁年成,早把你饿死了!
尽管刺蓟菜同其它许多野菜一样,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但它似乎是一种不太受人们喜欢的野菜,它不但刺多,难吃,还因为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扎根很深,很难根除,和庄稼争水分,甚至争阳光,为害庄稼。我们那里就有这样一段民谣:刺角芽的根,七八尺深,犁地使死牛,锄地累死人。此外,刺蓟菜当牛草,牛不爱吃;长老后割下当柴烧,又太扎手。因此,它成了农人心目中的恶魔,在耕作时,恨不得斩草除根而后快。当我长大,渐渐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后,我曾为刺蓟菜打抱不平:当刺蓟菜无法体现自身价值时,人们便忘记了它的价值。这是对刺蓟菜的最大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