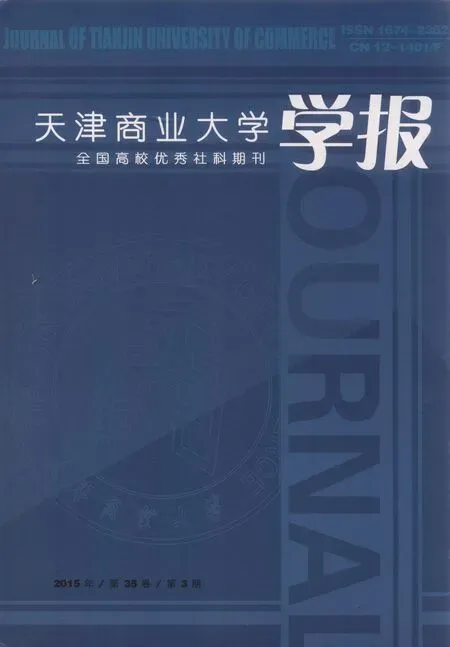对“居民迁出”式遗产保护路径的效果评价和反思——以中山市翠亨村为例
谢春红 ,于 玉 ,徐 虹,黄梓莹
(1.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300071;2.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510275)
长期以来,对于古村落的保护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古村落的古建筑上,而对古村落的村民、活态文化、社区发展等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古村落保护及其研究应该也必须注意它作为村落社区的一面。[1]早期的古村落、古建筑的保护通常是由文物局出钱买断该地的产权,产权划为国有,社区居民在与国家进行了产权交易后就迁出村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护了古村落完整的物质形态。但是,古村落作为传统民俗文化和物质遗存的综合体,居民迁出后失去了活力,成为空壳式的文物。在市场化背景下,社区居民也开始意识到了古村落的旅游价值,渴望参与到旅游经营中,居民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使得早期的“居民迁出”遗产保护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回答:政府单一主导的“居民迁出”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效果如何?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什么?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社区参与的“集体缺位”对于旅游地的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研究以文化人类学视角,从社区参与传统文化保护、文化传承来分析“居民迁出”对文化遗产带来的影响,指出“居民迁出”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局限和困境,对“居民迁出”式保护模式的效果进行评价和反思。
1 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与社区参与
1.1 遗产保护模式及问题
我国古村落与民居的旅游开发存在多种模式。从遗存形态来看,物质遗存的保护与开发模式有博物馆式、大遗址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式、城市历史街区开发式和村落开发式五种基本类型;非物质遗存的保护与开发模式则有民俗博物馆式、文化节庆保护与开发式、特色餐饮开发式、演艺开发式、主题公园开发式、物化产品开发式和影视开发式七种基本类型。从投资主体看,目前所采用的模式大致可以归为两种类型——外部介入性开发模式和内生性开发模式。[3]外部介入性开发是指以地方政府或企业从外部刚性介入的模式。这种开发模式忽视了作为村落主体的社区居民的利益,导致开发成本高及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旅游开发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内生性开发就是指古村落或传统民居居民及其基层组织作为直接利益主体,对村落进行自我保护和开发的模式。
在对国内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实践进行审视的基础上,有学者总结了较为成功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新天地”模式是对传统保护区域进行改造,“整旧如旧”,将传统旧区的空间形态进行合理重组和改造,传统建筑融入新的都市风格,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高投入、高回报、资金运转周期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才能成功。丽江模式则是对传统民居进行高原真性的修复,对遗产地居民进行教育和培训,以旅游业的发展反哺遗产保护。丽江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保护了古城,但是旅游的过度开发导致商业化严重,文化的原真性受到威胁。平遥模式是在丽江模式的基础上,对遗产进行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对居民进行教育和技能培训,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相结合,解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旅游开发和古城保护三者之间的矛盾。[4]在后两种较为成功的模式中,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之间矛盾的协调解决离不开对居民利益的合理分配。
传统村落兼有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5]除此之外,古村落的整体性特征还表现于村民与村落的共生。[6]因此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须是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社区居民的整体保护。将居民迁出由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是遗产保护的一种惯用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对于单个的、小体量的文化遗产无疑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体量大的、成规模的、无法移动的文化遗产却无能为力;[7]其次,博物馆式保护多依靠外部力量,缺乏有效的社区参与,一旦外部力量的援助退出,遗产的命运岌岌可危。古村落保护采取哪种模式要根据保护对象和社区生活的具体情况,但目前我国古村落保护多数的情况是“比较注重外观、景点、路线,比较偏重于物质遗产”。目前对现有的文物保护和管理效果评价的实证研究不足,也缺乏以社区、居民、游客、管理方四维度系统分析的视角。
1.2 社区参与旅游与文化传承
根据利益主体理论,社区是村落旅游开发的重要主体。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的旅游社区参与仍处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被动参与地方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8]如今的村落景观保护是以学者、社会精英、政府为主开展的,当地社区仍处于缺位的状态。[9]部分社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型或村寨型社区,其居民大多遵循政府旅游规划下的奖励制度而对建筑方式予以保留以获得奖金补贴。[10]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事务的行动。[11]除了使居民获得经济效益外,其积极作用还表现在居民自我文化认同、文化生存空间培育与拓展及精神内涵的展示等层面。社区居民始终是当地文化资源的亲历者、塑造者和所有者。[12]社区参与赋予社区居民接触“他者”的机会,激发其自我文化价值认知,使其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13-14]唯有社区居民参与,才能把与人不可分离的民俗风情转化为旅游产品,才能让游客在社区居民对民风民俗活动背后的民族观念、思维模式、民族性格、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的诠释、解读中体味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内蕴。[13]
社区本应该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居民是村落遗存的创造者和延续者。[15]有学者[16]认为将历史街区的原居民全部迁出、把民居全部改为旅游和文娱等设施会使街区失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就失去了“生活真实性”。社区参与旅游,既有利于突出地缘文化,让游客体验感知不同文化,也有利于保护和培育文化生存空间、保障其健康发展。[13]社区的参与有助于文化遗产地保持自身特性、维持“真实性”,增加自身魅力,社区居民是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良好的社区参与,不仅使居民受益,也会增加居民对遗产地日常经营管理的理解与配合,有助于提高遗产旅游地的经营管理效率。反之,处于弱势地位社区如果无法从遗产中获益,则不会主动对遗产进行保护,被动参与会引起社区居民的抵制情绪甚至是恶意破坏,如开山采石、破坏生态植被、砍伐树木等。[18]
2 研究方法与案例说明
2.1 研究方法
对“居民迁出”式遗产保护路径的效果评价,涉及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现状与困境、社区文化变迁、游客感知等内容,较为全面与系统,需综合社区、居民、游客、管理方多元视角收集资料,因此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具体如下:
(1)观察法: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的深入观察,详细描绘目的地的保护和发展现状,包括古村落建筑及周边物质景观的现状、游客在目的地内的行为特点、社区居民与游客的互动情况等。(2)访谈法:访谈对象主要是当地社区居民和故居管委会人员。针对居民方面,主要关注翠亨村的居民迁出过程、社区记忆和迁出后的社会交往、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变化。针对故居管委会,则主要了解翠亨村的遗产保护和村落管理的原则、方向与措施,发现遗产保护和管理自身的困境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问题。(3)问卷调查:以利克特量表形式,针对进入目的地的游客,了解游客的旅游体验、主客交流程度、遗产保护感知、社区文化与孙中山精神感知等信息。(4)二手资料收集:主要获取故居管委会历年来对目的地社区的规划和保护方案,用以补充对管理人员的访谈内容。
2.2 案例说明
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的翠亨村,是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86年10月孙中山故居被国务院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翠亨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孙中山故居、古村落民居等物质遗产保护、孙中山精神宣传一直是景区管委会的核心工作,并取得很好的成效,目前孙中山纪念馆是AAAA级景区和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翠亨村的社区文化传承、非物质遗产保护效果未得到政府部门与景区管委会重视与有效评估。
自20世纪80年代孙中山故居管理处陆续对核心保护区内的民居产权进行收购,翠亨村原住居民持续10年历经3批次不断迁出至新居,至今只有5户左右居民住在原址。“遗产保护”、“旅游发展”、“孙中山”等词打破了一个农业村的平静,翠亨村在空间结构、社区居民构成、社区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见图1)。

图1 迁出后翠亨村的分区及杂居分布特征平面图
翠亨村历史文化名村由居民住宅区、孙中山故居保护区构成,是社区与景区相邻而又截然分离。翠亨村产权收购后,居民从保护区内的翠亨村旧址迁入现在的居民住宅区。目前,古民居被收购或长期租赁,仅有几处民居处于产权谈判状态,古村落的维护和管理也基本由故居管理处负责。对于居民来说,他们并无搬迁,只是迁入集体新房而已。居民住宅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翠亨新址,是居民“迁入区”。另一部分为翠亨新村,对外已正名。这部分土地是当年“迁入区”的多余土地,用于建设商品房屋和员工宿舍,因此居民并非本村居民,也不再由原村委会管辖。在本土居民概念中,翠亨新址才是翠亨新村。
3 “居民迁出”式遗产保护路径的效果评价
3.1 社区:社区文化发生变迁
(1)居民更替呈杂居分布
20世纪80年代翠亨村总人口为80多户人家,目前发展到100多户。翠亨村旧址还剩5户左右原居民,并以老人留守为主,其余居民当年迁出后基本在新址上建宅。随着居民外出务工、出国等流动,翠亨村新址出现普遍的房屋空置和租赁现象。翠亨村新址附近建有小型工厂、靠近中山纪念中学和翠亨学校、故居旅游等因素引致许多外来非正规就业者、学生、家长等群体流入。翠亨新村住户主要为水电厂和景区等单位员工。由于人杰地灵,名义翠亨新村有别墅、商品房等旅游地产,其户主多为华侨和珠海、中山、澳门等第二居所购房者(见图 1)。
本土村落居民流出,许多旅游劳工、学生、家长和第二居所购房者流入使得翠亨村的居民不断更替,杂居分布特性明显,社区人口构成复杂化,并重塑着社区文化与风气。居民更替置换对社区文化的传承、孙中山情感的维系都有着影响。
(2)居民生计模式改变
20世纪80年代前,村民主要以务农为生,后由于国家土地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村落土地逐渐开始流转,部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目前村落剩余农田约50亩,主要分布在景区的农业展示区及周边,长期用于租赁。本村居民不再以务农为生,多外出打工,“以前人们有田种的时候就耕地,现在田地卖光了,就到工厂里面打工……剩下的田地也不够给那么多居民分啦,已经出租了……大概是100元每平方米吧。”
极少数靠近景区的居民将房屋改造为商铺做些小生意,“餐厅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在经营,只有纪中旁边有两家档口是我们村的人经营的,上层给自己住,下层卖冷饮、猪肠粉之类的。”景区管委会对翠亨旧村以及纪念馆范围内的经营活动管理更为严格,居民“有讲过(到旧村开展经营活动),但是他(管委会)不给……说不让那么多人进去里面经营。”实际只有少部分居民(一般为村委亲属)可获得景区的管理、经营、后勤的工作。可见,文物保护单位开放给本村居民创造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盈利点相对较少,居民的社区旅游参与度极低,但遗产旅游的发展已经使得村落的生计模式发生改变。
(3)文化空间骤减,亲缘关系松散化
“迁出”模式使居民交往空间得以重塑,公共游憩空间转移,精神空间功能弱化。亲友间交往频率降低,组织松散,族人与邻里间的情感维系淡化。目前,原居民的公共游憩空间转移为翠亨大道边上的本土居民经营的餐饮店与商铺,基本不去景区游玩。
迁出前,居民多围绕宗族祠堂而聚居,亲缘关系的住户比邻相依,房屋布局紧凑相连,间距小且巷道窄。迁出后,居民通过抽签获地建房,在新的空间生产生活,居住格局打破,长期建立的邻里关系被重组,旧村原有的公共空间也基本不被沿用。迁出前村落精神空间节点较多,有大小宗祠、北极殿、村口的大型土地神,几乎每户都有小型土地神。新村落的公共游憩空间减少,新建的篮球场、老年人活动中心利用率又很低,取代的是围合的私家小院,同时居民新宅很少再建小型土地神,许多宗祠在文革期间已被破坏拆除,“现在是分开祭祖的,每一家自己都有活动。”“(以前)过节会聚在一起祭祖。但现在祠堂也拆了,没有祠堂啦,还有个北帝庙遗址。”迁出后只有少部分居民会回到旧村,“(旧村入口土地神、北极殿)初一十五的时候,还会有人去拜的。”大部分居民仍保留神学信仰和拜祭习惯,社区文化空间的功能已越来越弱化。
3.2 居民:社区记忆模糊和情感淡漠
(1)居民旅游开发的参与度低
居民与故居景区缺乏互动,联系薄弱,经济与情感关联都很弱。村落旅游引致效应不大,提供居民的间接就业机会不多,直接就业岗位有限,经济联系也多为一次性买卖关系。居民与景区双方的互动极少,居民在遗产保护、旅游发展方面没有话语权。居民如同是遗产保护之外的,处于边缘化状态。
大部分古民居已被景区一次性收购,少数民居与农业展示区的部分农田则处于长期租赁给景区的状态。据翠亨居民回忆,当时集体性迁出进展顺利,居民对遗产旅游的经济价值认知也不高,所获得的一次性经济赔偿、固定租金并不高,只有少数留守居民日后以市价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虽然“在评一级馆的时候,是有具体雇佣多少当地人指标的”,但集中在景区的一线运营部门(包括环卫、闸口、维修、农业区等部门),这些少量的直接就业机会也多为村长及其亲戚获得。“非遗展示区打扫卫生的人就是本地人,老村长的儿子也是在维修组工作。新村长的媳妇也在这里工作,大概五六个人。”翠亨村的旅游发展所引致的餐饮、住宿、商铺的发展很弱,集中在中山纪念中学附近的翠亨大道,只有少数居民有机会参与经营活动。
(2)居民的孙中山情怀不浓郁
孙中山精神与相关历史本是翠亨历史文化名村的核心遗产,但在本土居民看来,这些与翠亨村和自身关联很弱,只是多了一个可接待亲友的景区。居民长期的边缘化且与景区互动匮乏,导致本土居民的孙中山情怀普遍较弱;故居景区与居民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没有形成翠亨社区的文化自觉。
景区管委会每年组织孙中山诞辰庆典等一系列节庆,“……很少(和村委会合作),节庆时他们(居民)会派代表过来”,但居民参与度极低。大部分居民对孙中山精神了解不深,“我们都不认识孙中山的。只是以前听人讲过,小日本打中国时不打翠亨村,他们会打隔壁村。因为他们敬仰孙中山,都不会打翠亨村的。”中年居民“很少(以孙中山为榜样教育小孩),因为过了很久了,隔了好几代了”。而年轻居民多数“不会(因为家乡有孙中山这一伟人而自豪)”。可见孙中山及其事迹在代际间的传递频率减弱,社区的孙中山情怀培育效果不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故居景区的旅游符号被翠亨居民高度认同,年长及年轻的居民都“会(带到访亲友参观孙中山故居),“以前有门票都会带亲戚进去孙中山故居(目前故居免费)”。
3.3 游客:空壳式的文化遗产感知
故居管委会介入较早,采用的是传统的社区与景区分离式旅游发展模式。从游客旅游感知看,游客认为景区古村落的整体风貌保存完好;在孙中山精神、生平事迹等历史的展示与宣传效果佳。这不意味着游客有着非常好的文化遗产感知,静态的物质遗产保护方式让游客形成的是空壳式的文化遗产感知。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游客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逗留时间相对较长,逗留其他古民居的时间非常短。有些游客甚至抱怨:“这有什么好看的,和我们老家没有人住的老房子差不多”;还有游客惊讶道:“还有个翠亨村?我只知道有孙中山故居,还以为就只是这个围起来的小公园而已,翠亨村离这远不远,怎么走?”还有部分游客绕过景区想进入翠亨古村落进行深度体验,频频被景区设置的自动闭合铁门拦截。这些情境足以说明完好民国风貌的民居建筑并不足以让游客有着完整的遗产体验,活态的社区、社区文化在游客体验中是缺失的。
在旅游体验方面,游客普遍认为古村落的“古”风貌是吸引自己前来的重要因素,“走进故居的村落社区,了解村落风貌”、“与故居居民交流,了解当地文化及其对孙中山的情感”的意愿强烈。实际体验是游客认为“在景区内,几乎不能从当地人口中听到孙中山家族相关故事,根本无法与当地居民交流”。“居民迁出”式模式使得主客交往机会匮乏,这对于文化旅游地,不利于体验时代背景,不利于提高游客满意度。
在旅游发展方面,游客十分期待与社区居民交往的机会,并支持开放更大的民居展示区。但基于旅游商业化的顾虑,游客在“让本地居民回迁原村适当开展旅游商业活动(如旅游纪念品、餐饮、住宿等)”这个问题上总体支持居民回迁但又十分谨慎。但对于“雇佣更多的当地村民,增强居民与游客的交往”则持赞同态度,在“对游客开放更大的民居展示区域”则表现出十分赞同的态度。
3.4 管理方:社区缺位导致景区管理困境
因资金、人力受限和社区的集体缺位,遗产保护力度不足,旅游发展动力缺乏直接导致了翠亨村旅游发展滞后,推进受阻。居民淡出遗产保护视野,社区缺位,对于文化遗产地而言是缺失了文化传承载体,这对物质遗产要素的保护、社区旅游的推动有着负面影响,使得景区陷入管理困境。
(1)古民居空置,保护有限
面向游客展示的故居每天都有专人负责环境维护和检查,保护较为妥当,但未向游客开放的民居保护区内的房屋现状不容乐观。“现在有人住,但是不多,不到五户人家”,尽管管理方“尽量安排员工到里面去住”,但多数房屋都是空置状态。这些既不对外开放又无人居住的房屋没有承担任何实用功能,长期空置更加速房屋的破损。其次虽然民居几乎被统一管理,但也只是选择性优先保护。“因为现在人力和财力也不够,所以不可能将所有的古民居都保护成像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房屋那样,只能对一些重点的建筑进行保护,以后旅游开发当然这些也会是重点。”
(2)社区旅游薄弱,就业供给有限
面对膨胀的大众旅游需求,管理方也曾想开放更大的民居展示区和农业展示区以提高旅游体验,但因维护资金不足、工资低难以招到员工而无法落实。民居展示区与农业展示区本是原居民的生活区,原居民无疑是最合适的管理主体或雇佣劳工。迁出后社区与景区分离,社区参与度极低,提供居民的就业机会很有限。景区内商业设施除了官方纪念店,仅存在三家居民经营的小店并且商品同质化严重。“这些商铺在90年代就有了,一年年地签合同”,至今景区内旅游商业未有所增加。民居展示区内有保存下来的商铺建筑,管理方希望有商家能够租赁开展相关商业活动还原真实生活场景,但商家“觉得赚不到钱,位置太偏,游客不会到那里去”,管理方在培育居民就业机会方面重视不够。
(3)博物馆型景区,旅游发展滞后
孙中山故居景区是博物馆属性,实行免票制度,没有收入来源,一切资金全部靠上级拨款补贴,这不同于自负盈亏的景区,这一方面削弱了管理方推进旅游的动力,另一方面,博物馆的非营利属性使得故居即使作为4A级景区,在旅游商业方面(旅游活动、商品类型、商铺位置)也有颇多限制,无法给予旅游经营者足够的信心与盈利空间。翠亨遗产保护中忽略了居民这一重要的保护主体和文化载体,社区文化传承效果不佳,社区旅游没有被激活,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动性没被激发,翠亨村的旅游发展滞后,推进效果并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居民迁出”式遗产保护路径不利于社区文化传承
本文以中山市孙中山故居所在地翠亨村为例,还原翠亨村的迁出过程,深入分析迁出模式的影响,从社区、居民、游客、管理方四个维度系统地对我国早期“居民迁出”式的文化遗产地保护路径的效果进行评价与反思,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物质遗产保存完好。由于在“居民迁出”式保护方式之下,遗产要素的控制权和管理权被集中于管理方手中,古建筑和民居的改造和开发被严格控制。在该层意义上,“居民迁出”的保护措施具有一定合理性与有效性。(2)居民迁出后,原有的居住格局被打破,由于新居住区的公共空间和精神空间功能相对原有空间较弱,导致居民间亲缘关系被稀释减弱。原有的社区文化环境因缺乏社区居民的参与而空壳化,社区居民因缺乏原有的文化环境而出现文化缺位的现象,造成对孙中山精神的淡漠和村落文化认同的弱化。因此,“居民迁出”式保护路径未能完好保存蕴含在孙中山故居内的精神文化遗产。
4.2 反思:文化传承才是遗产保护的核心
“居民迁出”式这一遗产保护路径使得翠亨村的物质要素得以很好的保护,但是对保护村落的文化、增强居民对孙中山的情感维系、活用物质遗产、增强社区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明显,甚至有负面影响。可以想象,当游客来到孙中山故居参观,只是一种旅游形式,不再关注中山精神,不再关注古村文化;而居民与遗产旅游地脱节,没有文化的认同感,对孙中山的情感不再重要时,这个古村落也在丧失其魅力。
本研究认为,对遗产地而言“居民迁出”式保护路径应持慎用态度。“居民迁出”式是一种保“居”不保“民”的模式,游客的旅游体验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缺乏深度的观光感知。“居民迁出”式保护路径仅保护了遗产的物质形态,而忽视了其精神内核。尤其国内后期其他遗产案例地的开发过程日益凸显的冲突问题更是强化了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和“居民迁出”式的不适用性。对文化的保护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居民是文化传承、社区凝聚的真正载体。
4.3 讨论:社区参与旅游视角下遗产保护模式
从目的地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角度看,遗产保护路径还需结合实际进一步研究。而对于早期采用“居民迁出”式的遗产地而言,后续的旅游开发该如何转型,社区如何参与旅游也需进一步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提供了中间道路。国内众多案例研究证实,适度的可持续的社区参与旅游对于促进社区居民认识自身的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14]游客对于目的地原真性的追求使得居民将社区的传统文化找回来,社区居民认识到了文化和资源的价值与重要性,保护意识也逐渐萌生,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归和保持。
遗产保护路径的寻找将永无止境,旅游并非遗产保护的最佳选择,但为适度化的选择。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因为有政府部门的大力倡导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停留在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的倡导层面,当地成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因而也在走向博物馆化。[19]文化是活的生命存在,具有变动性和开放性,把文化当作固化的“遗产”来保护的强特性途径难以实现。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内生力量,这种外部力量的扶持所带来的遗产保护效果时常是阶段性的。一旦外部力量退出,文化遗产的保护便陷入困境。20世纪末我国在贵州、云南、广西的少数民族社区建立了一批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命运就是例证。整体看来,旅游的适度开发和有效控制,将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19]旅游可以作为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中,为社区居民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和选择空间,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体,外来者在任何时候都只是遗产保护的辅助力量。
致 谢:感谢刘岳林、谭靖敏、冯锐昌、李乾毕同学参与本文实地调研,感谢所有受访者对本研究的信任和提供的宝贵信息。
[1]黄涛.古村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以浙江省楠溪江流域苍坡古村为个案[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31-134.
[2] 傅才武,陈庚.当代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93-98.
[3] 齐学栋.古村落与传统民居旅游开发模式刍议 [J].学术交流,2006(10):131-134.
[4] 康健.古村落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08.
[5]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民间文化论坛,2013(1):7-12.
[6]魏成.路在何方——“空巢”古村落保护的困境与策略性方向[J].南方建筑,2009(4):21-24.
[7] 孙九霞.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J].旅游学刊,2010(5):10-11.
[8] 保继刚,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地理学报,2006(4):401-413.
[9]刘夏蓓.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景观保护——三十年来我国古村落保护反思[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18-122.
[10]艾菊红.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J].民族研究,2007(4):49-58.
[11]彭思涛,但文红.基于社区参与的村落文化景观遗产保护模式研究——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社区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2):94-98.
[12]曹兴平.文化绘图:文化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实践的新途径[J].旅游学刊,2012(12):67-73.
[13]邓小艳.文化传承视野下社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思路探讨[J].广西民族研究,2012(1):180-84.
[14]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正效应[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35-49.
[15]陈庚.以居民为核心主体的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基于婺源李坑村的实证调查分析[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5):49-58.
[16]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1(10):2-9.
[17]AWORTH G J,TURNBRIDGE J E.The Tourist Historic City[M].London:Belhaven Press,1990.
[18]王涛,张立明,任亮平.基于社区参与的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5):114-116.
[19]孙九霞.旅游拯救民族与文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