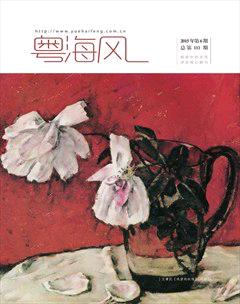现代视野下的知青运动
周思明
一
作为一名1970年代的下乡知青,当笔者决定要写这篇反思文章的时候,心情之复杂,思潮之汹涌,真是一言难尽!虽然笔者插队下放历史不长,仅有2年的时间;虽然笔者经过自身努力,迄今也还算混得不算太差,然个体与群体尤其这个特殊群体本身的命运滑坡,也许只有亲历者本人才能体会。1960—1970年代,1700百万知识青年响应号召被政府安排去上山下乡,乃出于当时的权宜之计、应付之策,至于他们插队落户以后会向怎样的实践逻辑和生存维度滑行,事实证明亦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始料不及且难以掌控。与改革开放以后自愿进城务工的2.7亿农民工相比,上山下乡对于1700万的知青来说并非自愿,乃是赶鸭子上架不得已而为之。正如土地是农民的命脉一样,城市是知青的命根。插队落户之后,自幼在城镇土壤上存活的知青们,其生命陡然之间被“移植”到了农村,文化生活的荒芜和生产劳动的艰苦,令缺少精神与物质给养的他们难以适应,对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毫无概念乃至一头雾水。尤其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两个持论者同一、但其意义龃龉的命题,也教知青们发生理解上的困厄——既然农民也存在着“严重”的“教育”问题,何以又要知青千里迢迢跑到农村去接受其“再教育”呢?所谓“农民意识”又当作何解释呢?说实话,这种疑问,恐怕并不限于少数人持有,只是慑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不敢提出罢了。
何为“知青运动”?系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大量城市“知识青年”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动员令或者说辞,被号召和组织离开城市去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知青运动”始自1960年代中后期,鼎盛于1970年代前中期,结束于70年代末期。但如果深入研究,“知青运动”的源头当追溯到 1955年,是年有60名北京青年自发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盛大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亲手将“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邢燕子、侯隽等津京青年作为典型模范在媒体上红极一时,得到官方持续的宣传。
真正大规模、有组织地将大批城镇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是在文革后期。如此重大国策的骤然推出,意在给业已失控的红卫兵运动刹车,让因“文革”国民经济停滞不前造成的城市青年无法就业局势得到暂时的缓解。笔者记得非常清楚,1968年12月22日夜,所有的电动扬声器(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所谓“最高指示”传达不过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主席的上述指示。一时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口号响彻云霄,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舆论先导,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于是拉开大幕。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生、高中生成为“老三届”的最后一批(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俗称“老三届”),几乎全部开赴农村。
据统计,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总人数多达17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遣散到了乡村。与十多年后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大迁移(农民工)相反,那是一场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向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不夸张地说,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下乡知青联系在一起。政府指定知青的劳动居住地,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逃过了上山下乡,或者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诸如城市郊区落户。如今反观“知青运动”不难看出,在1千7百万知青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大有作为型”,二是“蹉跎岁月型”,三是“伤痕累累型”。
二
先看“大有作为型”。这部分知青满怀革命理想和豪情壮志,主动积极投入到知青运动中去,高呼“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口号,从大中城市奔赴最艰苦的农村,先行者有邢燕子、侯隽等人,后继者亦不乏其人。据资料记载:1975年9月15日至l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即第一次会议)。有12名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出席。10月27日,毛主席看到他们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这12名知青堪称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代表:邢燕子,女,天津市宝坻县大中庄公社,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朱克家,男,云南勐腊县勐仑公社大卡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共候补中央委员(后因政治形势变化跌入低谷,未能返城而滞留云南);薛喜梅,女,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共青团省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程有志,男,河北涿鹿县温泉屯公社,大队党支部书记、县革委副主任;柴春泽,男,辽宁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崇辉,男,黑龙江兵团5师55团,副团长;戈卫,男,陕西宝鸡县圩头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肉孜古丽,女,新疆莎车县十二公社,青年队副队长;曾昭林,江苏邗江县六圩公社红旗大队,科研小组代表;林超强,广东宝安县附城公社连塘大队,生产队长;张登龙,男,安徽临泉县高塘公社,修配组负责人;刘裕恕,男 ,四川黔江县黑溪公社,生产队长。当然,这12名知青只是最炙手可热的代表,此外还有相对突出的知青代表,不管怎么说,他们是靠辛勤的汗水和过人的智慧喝到了政府给予的“头啖汤”,都是知青群体中的佼佼者,成为了特定历史与无为时代的有为者和幸运儿(至于有无类似朱克家那样命运大起大落者,笔者未经逐一考证,只好暂时存疑)。
但令人唏嘘的是,更多城市青年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第二、第三类知青,即“蹉跎岁月型”和“伤痕累累型”。这两种类型人数极为庞大,也不可能在此以“实名制”方式公之于众。以笔者所在的知青点为例,除了极少数知青干部如团支书副书记、副队长(正职均为贫下中农代表担任)勉强算是一类人物之外,其他均可划入二、三类范畴。造成二三类知青情绪低落、思想消极、情绪苦闷的原因并不复杂: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他们普遍感觉农村生活艰苦、枯燥、无聊,正值青春躁动阶段的他们,陡然间被抛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近于无,更看不到生存的价值与奋斗的前途,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凡此种种,不具备第一类知青的超人毅力和充分准备的他们,拿什么去取得农民老师的认可与接纳?而被冷漠、被怀疑、被排斥的感受,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知青自身思想的巨大矛盾和与农民们的情感冲突与隔膜,于是他们只能乖乖地认领“蹉跎岁月”乃至“伤痕累累”的命运——或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或吊儿郎当,偷鸡摸狗;或任人宰割、身受戕害。应该说,第二类“蹉跎平庸型”知青占据绝大多数,第三类“伤痕累累型”知青也不在少数,如此怪异的历史命运格局,乃是位国策构建者与实施者们始料不及也不愿看到的惨烈风景。以至于到1970年代后期,在知青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他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知青抗争最为突出。
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提出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1]其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与此相呼应的是,1978年12月, 数十位云南知青冲过重重阻隔来到北京,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横幅,这一天,距离第一批上海知青到达新疆已时隔15年。那年冬天,上海知青丁惠民带着十多个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远在上海的一些高干家庭率先体察到了政策的转向,开始以各种理由准备调动回城。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和思考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而其他有门路的上海家庭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眼睁睁看着有门路的知青返沪,这些事实对“周公正们”的冲击巨大,他们迷惑,进而开始思考,大规模的抗争由此开始。78年9月,丁惠民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明确表达了回家的要求。时任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命赴云南调查,西双版纳勐定农场知青以绝食明志,长跪不起。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要求立即组成请愿团北上。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强行抬过了澜沧江。留在西双版纳的知青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抗争,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了所有人。知青的决心已经不可阻挡,1979年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表示“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而朱克家成为了这场政治运动最大牺的牺牲品。由知青典型沦为阶下囚服刑期满后的他,曾试图调回上海崇明岛一家国营农场,但终究因“历史问题”未能成功。朱克家至此落脚云南,2004年退休。上海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已经没有了“回去”的动力。
三
最为悲摧与不堪的是,在第二、第三类知青中,出现了大量因期待返城、不堪苦累而被管理部门、带队干部、农民中的不法分子的迫害与侮辱的知青,其中尤以女知青为最。以上海为例,资料显示:仅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不少犯罪分子利用职权,使用暴力奸污女知识青年;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教唆、勾引知识青年实施犯罪活动;拐骗女知识青年;冒充领导干部招摇撞骗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蓄意残害知识青年的刑事犯罪分子,施用残暴、胁迫手段强奸下乡女知识青年;利用职权严重违法乱纪,打击报复,残酷迫害下乡知青的刑事犯罪分子。张国良是原沈阳军区某部“雷锋团”连长,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71年张借谈心之机强奸了第一名女知青。女知青含羞忍辱未敢声张。此后张胆子愈发大起来,频频得手。据材料揭发,张任连长三年丧心病狂地强奸几十名女知青,造成多人多次堕胎。以至于李先念副总理都知道,女知青只要听见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抖。[2] 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激烈竞争,最终有70余人获此幸运。然而令人瞠目的是,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医生发现,70名女知青无一人是处女,且几乎皆非“陈腐性裂痕”,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换言之,这70名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通行证的。在众多下乡女知青中,遭色狼奸污后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另有一些被奸污后而上大学、入党、 提干的女知青更不会将隐情暴露。上海一返城女知青,新婚之夜被丈夫毒打并赶出家门,因为她不是处女,其处女贞操在插队时被公社党委书记就给破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上海女知青,因拒绝连长调戏被发配到20里外水渠口去开关闸门,每天在四十度酷暑中来回一次,半月后她不堪苦累终于屈服,与做了一个交易:连长将她调回连队驻地食堂工作,她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连长。
作为一名知青,笔者也曾亲历了上述噩梦。1974年至1976年两年内,笔者所在的知青点,也曾发生带队干部与贫下中农代表联手迫害“成份不好”的知青,带队干部猥亵、奸污多名女知青的事件。一名看似冠冕堂皇的带队干部,将他看上的女知青、回乡女青年、女干部、农村妇女,以各种卑鄙手段变为他的“下酒菜”。这位带队干部利用手中推荐、把关、审查、鉴定等等权力,压制、迫害那些具有“成份软肋”的知青,侮辱、猥亵、奸污那些意欲返城、升学、招工的女知青,大搞权色交易,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最终被多名女知青告发而锒铛入狱。荒唐且反人性的是,知青之间不能谈恋爱。谈恋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几乎所有谈恋爱的知青都得偷偷摸摸,似有一种犯罪感。笔者就曾亲眼目睹这样的荒唐。笔者所在的知青点,曾有一名女知青与省城一名男知青自由恋爱,被带队干部发现后,他居然发动男知青围捕那名男知青,严厉批评那名女知青,此事作为一个事件被传得沸沸扬扬,滑稽的是,这位带队干部自己却经常趁知青白天下地劳动在知青点花天酒地、偷鸡摸狗。如果将视野扩展至全国,此类的荒唐事更令人不堪。一女知青为了能回上海而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双腿被扎断的工人;一女知青为了户口能办回离上海近点的农村,嫁给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老农。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在大回城浪潮中,许多已婚的为了回城无可奈何地办理假离婚手续(因为当时规定已婚知青不能返城),原本打算回京以后再想办法把对方调回北京,但最后几乎所有的假离婚都弄假成真。一女知青在和当地农民结婚生下一女后得到一个返城指标,在父母催促下丢下丈夫女儿回到北京,不久就因家庭破裂受刺激疯了……至于像叶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中唱着“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的知青子女,更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知青悲怆命运的真实写照。
四
“知青运动”的乖戾、不堪、扭曲,终于令“李庆霖事件”浮出水面。1972年12月20日,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信中,李庆霖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揭穿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展四年后,知青劳动艰苦,生活困难重重以至食不果腹的真相。李庆霖在信的结尾控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读信至此,毛泽东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遂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6日”。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回信印发全党,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并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予以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第一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改进知青工作的措施。据《全国城镇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年)记载:“1973年6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前,国务院知青办曾对各地知青状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根据24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至1973年5月,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约占70% 以上。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披露: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仅1972年迫害知青案件就126起,其中奸污案119起,占94%。”
由于李庆霖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揭开了全国各地迫害知青惨状的冰山一角。1973年7月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第241号刊登一篇题为《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对有缺点错误的知青,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迫害。据1972年4月统计,该团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营教导员蒋小山,强奸女知青二十余人;连长张国良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五十多人。”这类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极大愤怒。7月5日,叶剑英在新华社记者写的《情况反映》上批示:“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7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新华社记者写的《情况反映》上批示:“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待,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李先念同时在新华社记者写的《情况反映》上批示:“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吗?”1973年8月22日,沈阳军区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6团召开公判大会,宣判因犯奸污女知识青年罪的原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死刑,立即执行。1974年,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命令,批准判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8团独立一营营教导员蒋小山、连长张国良等四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因为全国整肃了一批迫害知青的罪犯,全国知青的插队生活艰难处境有了一定改善,首先是提高了知青插队期间的经费补助标准。有福建师大2008届硕士毕业生陈文在毕业论文《福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阶段研究(1968-1973)》的记载为证:“福建省规定的安置经费补助标准如下:1969年—1972年,平均每人230元;……从1973年起,改为每人均补助480元;到新疆等边远地区的,补助700元。”随着知青插队期间经费补助标准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全国上下重提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视,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知青上山下乡、插队农村的新高潮。
回首“知青运动”,笔者作为一名与李庆霖的子女类似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插队下放,虽经自身努力当上五七青年队副队长、团支部副书记,但也遭遇多次被带队干部“偷梁换柱”之迫害,此公屡次将招工、招生等回城指标换成他玩弄过的女知青、或其父有权力的男知青的龌龊事情。犹记有一次,这位人面兽心的带队干部,将我叫到他的宿舍,坦承近期有一个招生指标,但他已安排给了一个女知青(知青点风传他与之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还扬言,即使如此,“我想你也不敢闹”。士可杀不可辱。我当即就跟他“闹”起来,但最终还是以我的失败他的胜利而告终。无奈,我只有打断胳膊和血吞,继续留在农村“改造”。后来,中央鉴于各地反映越来越多的知青问题,于1975年秋季向全国派出多个知青工作调查组。幸运的是,有一个调查组还光临到了我们那个知青点。然而,汇报情况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做了不少坏事(包括强奸、诱奸多名下乡女知青、农村女青年,拿知青辛苦喂养的猪的最优部位贿赂上级领导作为自己往上爬的筹码等等)年逾知天命的那名带队干部。自然,汇报工作时他把问题悉数“贪污”,而把知青队状况描绘成了一朵美丽无比的鲜花。
五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思的日子不值得过。今天回想起来,被裹挟在“文革”十年浩劫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过是乱世期间治乱的权宜之计、应付之举。不过是以冠冕堂皇名义将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的广大城镇青年打发到农村、山区去得过且过。因此,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决不值得提倡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这是在开历史倒车,违背了人类发展的规律。知青作家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对有些知青在上山下乡的苦难过后,好了伤疤忘了痛,“豪迈”地自称“青春无悔”予以驳斥:“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当然,艰苦的插队劳动,也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坚忍不拔意志的国家栋梁,至今还在忍辱负重支撑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这恰如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亚圣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里所预见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是,应该分辨清楚的是,难忘的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对经历苦难的广大知青固然是一种意志的磨砺,一笔宝贵的人生阅历财富,但这并不能成为某些人肯定和讴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由,更不应作为事后津津乐道、加以炫耀的资本。正如《插队往事》中知青高学冠笔下的《决不赞美苦难》结束语写到的:“而今回首这段往事,我想起一位学者的话: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
改革开放以后,知青运动结束,知青文学兴起,且经年不衰:从“痛说伤痕”到“青春无悔”,再到冷静反思。最近十几年来,知青运动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口述史》等研究专著,潘鸣啸等外国学者,也出版了研究中国知青的专著,以及知青的回忆录,等等。尽管如此,有关知青的研究仍有待深化。最为重要的是,是要进一步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对于知青运动的认识。知青运动从上世纪50年代的“初澜”,到1968年变为“大潮”,到10年后的“尘埃落定”,如此的历史轨迹背后,一定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由于相关历史档案解密程度不高,高层决策的动机和过程,至今仍未完整地呈现出来。以政权的力量停办大学,让一代中学生中断学业,上千万城市学生远离家庭,下乡从事农业劳动,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见不到的。这就使一代人的经历打上特殊印记。他们的命运落差之大,悲欢离合故事之多,除了战争时期,其他年代、其他国家的青年不可想象。虽然,知青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一部分在1977年、1978年考上了大学,但毕竟属于少数。多数人因为这场运动,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学历的劣势,使他们在社会发生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后,成为最先下岗的一群。舆论中容易听到功成名就的知青讲述劫后辉煌,而不容易听到知青中的利益受损者述说不幸。其实,沉默者才是大多数。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即便成为社会精英的成功者,身上也带着特殊的历史印记。对中国社会低层有较多的了解和体验,命运的大起大落,是知青中产生相对多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社会原因。但受制于知识训练的局限,知青一代中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专家相对较少,与他们的上一代人形成巨大的落差,以致影响到国家民族的科技进步与经济腾飞,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整整一代人失去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机会,只好以社会为大学,饥不择食地进行零敲碎打式自学。这种特殊的遭遇,难道能说对中国的教育、经济、科技、文化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吗?知青中,虽然出现了一少部分政治精英,已经走上领导岗位。底层的经历,能够使他们对民生有更为真切的体验,会影响到执政的理念和风格。但匮乏完整全面知识训练的他们,能否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民主带来更多的信心,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继续。从这个意义上看,知青研究仍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大课题。
六
文学是历史的孪生姊妹。以文学的角度反思知青运动,曾经有作家梁晓声、作家叶辛等为代表的诸多作品。梁晓声的反思更多是自豪和讴歌,显然没有抓住“知青运动”的本质和主干,叶辛的反思重点放在知青运动对于一代人造成的痛苦与分裂上面,较之前者显得比较深刻,也引起了更多共鸣。小说及其电视剧《蹉跎岁月》《孽债》等,看后给人以心灵的刺痛和历史的反省。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也有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青上山下乡不能否定。但是事实是无情的。正如叶辛所言: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分。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分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各种媒体高调宣传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而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这些知青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已没有了他们的归宿。无论其个人命运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出现在镜头中的他们,衰老和可怜;他们的青春,在知青岁月里荒废了。荒废了青春,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荒废了人生。
叶辛所言,发人深思!一个社会要前进,总要碰到各种各样问题和矛盾,解决问题和矛盾固然需要探索或开拓,需要寻求新的途径和方式。但是,在向整个社会推出这种途径和方式时,特别是要让千百万人参加实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在局部地区经过科学的试验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向社会推广。万万不能让千百万人在一夜之间狂热地投身于实践,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进行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如此“试验”结果,必然会导致象“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一样,留下无尽的遗憾。○3从这一意义上说,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700万青年失去大学深造机会,造成整个国家的科技停滞,文化破碎,人才断层,这种显在与潜在的精神文化凋敝与科技退步危机,势必会给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带来可想而知的负面影响。个中的深刻教训,足以令整个民族汲取和警醒!
注释
[1]《“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来龙去脉》2008-03-13《文摘报》
[2]《悲情往事 那些被蹂躏的女知青》2012-03-03 《博报网》
[33《作家叶辛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2009年08月15日《腾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