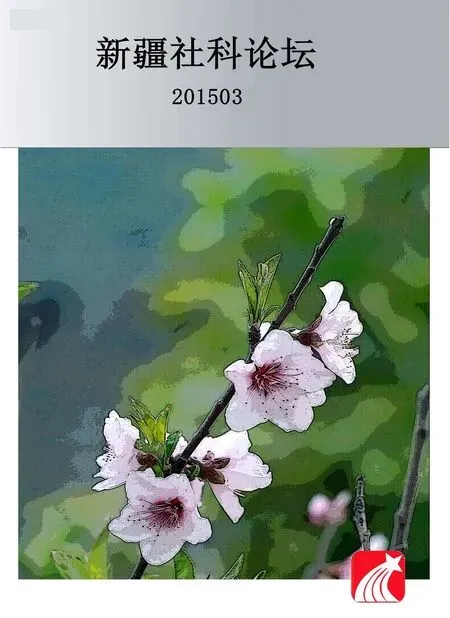边界与边境:边疆问题的中西方文化背景探析
边界与边境:边疆问题的中西方文化背景探析
阿依努尔·卡马丽
摘要中国边界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在传统中,中国各民族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互动下形成了文化和地理结合下“天下”体系。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主权观念的进入,这一体系被一条条边界线打破,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遗留下来诸多问题。我们看待边疆问题时不能附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原则,研究边疆问题时不能将边疆看作静止的、没有自主性的,也不应站在中心的角度来看待边疆问题,认为边疆只是中心的衍生。要从历史文化出发来进行本土研究,即边界研究到边境研究,充分揭示边疆自身的发展逻辑。
关键词中国边界中西方文化边境研究
文章编号中国图书分类号D823
文献标识码A1671-4741(2015)03-0096-04
作者简介:(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女,维吾尔族)
边界是界定国家主权的界线。国际法规定,国家的边界是指划分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未被占领的土地、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公海以及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界线,边界是有主权的国家行使其主权的界线。我国边界线漫长,与周边14个国家有着16000千米的边界线,我国边界问题最为复杂。近现代以来,我国几乎与周边邻国都存在着边界争端问题,重要的如中俄、中印等,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为什么我国边界问题在近两个世纪如此复杂,这要联系具体的时代背景对该现象作一个系统的分析。
一、现代边界问题的实质
边界的划分属于政府之间的行政行为,而国家和政府作为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其政治行为脱离不了国家的基础实力,如综合国力、地缘情况和资源等,同时也会深受社会文化的形塑。纵观世界发展形势,政府间的行政行为似乎越来越被文化所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由此提出“文明冲突”的论点,认为世界秩序将由文明之间的互动来主导。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①在塞缪尔·亨廷顿的阐释中,文明与文化是等同的。虽然塞缪尔·亨廷顿的结论比较绝对,但在实际中,边界冲突很可能是两种不同文化下的人群因为文化适应问题而导致的,而且在边界问题上,各国所制定的政策会受本国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由此左右了边界问题的发展。例如,印巴分治中关于克什米尔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致。
现代化潮流是西方国家发展带给全世界的,在此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自愿半自愿地参与了资本主义规则体系,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都遵循这一规则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并尊其为“圭臬”,在各方面深受西方体系的影响。在适应西方规则体系过程中,西方文化的传入与本国文化传统发生矛盾,一方面,西方文化要求抛弃传统;另一方面,文化的惯性使本国文化传统不可能轻易被废除。在两者错位关系的“张力”冲突下,在本国各领域内都产生了很多问题。在边界上确立国家主权,是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原则下进行边界划分、签订条约,这就要出示证明国家主权的确切证据。同时,基于传统的认知,出现“传统习惯线”等诸多概念,因此现代边界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
由此可知,现代边界问题不只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涉及社会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我们不能只从政治行为与国际关系入手,还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边界问题的由来。
二、边界与边疆
中国今日的版图继承于清朝,在边疆地区多有损失。清末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蚕食和鲸吞中国边疆土地。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清政府虽坚持原有的疆土观念,却在船坚炮利面前丧失了发言权和主动权,不能适应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为今日边疆民族问题埋下了伏笔。
1.西方国家的“边界”。
罗马帝国统一过欧洲部分之后,欧洲大陆就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教会代表上帝直接在精神上监管着这一地区,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神圣的东西。整个欧洲大陆被分为封建诸侯的采邑,采邑可以世袭,也可以转让。这时欧洲大陆尚没有国家观念,也没有边界概念。诸侯国之间的联姻使欧洲像是一个大杂烩,没有清楚的脉络。
近现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统一市场、统一关税的要求应运而生,以便于展开经济贸易的竞争。与此同时,也需要大量的专业化工人,需要统一的教育去培训等。所以,这就要求有一个封闭的范畴。而且,此时欧洲启蒙思想兴起,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要保证民主,就必须保证有明确的选区、选票,确定明确的公民身份,所以需要一个封闭的地域范畴来保证实施。
民族主义思潮在十八九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要求国家疆域与民族分布相重合,对外封闭,对内结合为一体。以此来保证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利益,保障本民族的发展。所以,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原则被神圣化,一个民族国家为主权而战。要保证主权,就必须确定明确的边界,确定活动的范围。这就需要边界线、边境哨所等,把一片地域封闭起来,不允许外人插足。
在近代历史上,德国的奋斗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确定德意志人的"生存范围",从普鲁士建立第二帝国开始,迫于法国的强大压力和发展本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便使用铁血政策来强力整合原罗马帝国。奥地利虽然也是德意志人的国家,但它又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其不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业。到第三帝国时,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极端上升,为了所谓德意志人的纯洁血统便制定了优秀人种的生存范围,并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边界观是要求本民族与外族之间绝对的对立。
2.中国的边疆。
西方国家未出现之前,“主权”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中国的“天下”。“天下观”是中国古代对地域与文化相结合的一种观念,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当时所知的地理范围都属于中原王朝的疆域,皇帝是“天下”范围内的共主。从中原向外,按照文化程度划分出一个个同心圆,在不同的圆里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体制起源于周代,后来随着中国范围的扩大而不断扩大,在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前夕,中国内地大都实行郡县制,中央直接设流官管理;而其周边地区则实行土司制度或王公制度,进行羁縻管理;再向外则是藩属国,其自身自治,而在礼仪、地位上从属于中国。总之,边界是以“文治教化”所达到的范围为界的。在中国,边界是流动的、不固定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不变的,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天下”的、有层次的格局,是没有确定的界线的。
与西方国家不同,在古代中国,由于游牧与农耕这两大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互动,在“天下”体系内纵横捭阖,共同遵循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例如“天下”、“四海”、宗法制度、敬天法祖等。使“天下”的范围大致保持不变。例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通过文化的融合,还以正朔自居,同样对周边少数民族推行“天下观”,使得中国古代文明得以延续。
同时,既然能成为边疆地区,说明其在地理分布上距离中心地区较远,从而受中心地区权力和文化的影响较小,所谓“山高皇帝远”。 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认为,地理环境是每个地区的自然基础,而边疆地带的环境又极具特色,它们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社会活动必然受到环境特色的制约。特定环境中的经济活动是起始层面然后展开社会的政治形态。②云南省边界地区河流众多,河流将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切割成一个个狭窄的河谷,居民点和重要城镇位于这些河谷之中,受地缘因素的影响,一个个河谷往往构成一个个由内部居民组成的经济文化生态系统,河谷内部的交流大于河谷之间或者河谷与周围地区之间的交流,云南多民族现象也与这种地理分布有关。在历史上,这些地区多归土司管辖,中央政府通过“羁縻”的方式来间接控制,绝对的边疆其实是这些没有实行“改土归流”的地方。
所以,边疆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在大多数学者眼里,边疆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③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边境地区,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④这种由地理因素造成的边缘性使其自主性很强,其内部之间的交流比对外更频繁。边疆地区处于中心的边缘,同时受到不同势力的多重影响。但其又处于各中心地区的中间地带,其为了保持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实际利益,往往会依赖一个中心地区的势力。在历史上,强大的中央王朝势力会努力争取其成为自己的“藩属”,云南边疆的土司们都向中原政权“上贡称臣”,同时维持着自己的“自治”王国,还和周围的缅甸、安南等保持着一定联系。
总之,边疆的异质性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小传统,从而决定了边疆民族、文化上的特色,也使边疆地区在国家政权中具有离心力。
3.中国边界问题的形成。
中国边界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在传统中,中国各民族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互动下形成了文化和地理结合下的“天下”体系。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主权观念的进入,这一体系被一条条边界线打破,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遗留了诸多问题。
在传统中,边疆的去留受中国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相互影响,由于大传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强势,使小传统始终不能脱离大传统,从而保持了“天下”的格局。这一关系在今日中国也还适用,这种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把“国家主权”的观念强行带入了东方国家,中国的“天下”边界观被打破。面对强大的西方国家军事和文化上的实力,中国自顾不暇,很多边疆地区的向心力大大减弱,甚至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且,与传统中原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政策不同,不再是封赏、进贡,而是必须在边疆上划定明确的界线,确立主权范围,以形成现代国家的格局。由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边界的划定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性和随意性很大,并不是完全基于历史渊源、地理形势进行的。而边境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其在本地形成了自己的居住格局,却在边界划分中被分为两半,比如云南省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而且在边境上有很多“河谷”、“坝子”分属于两个国家,而其内部往往却是一个民族。
所以,中国边疆的特殊性,是在外力介入下边界被突然固定下来,是中国急速进入现代国际规则体系的产物,不像欧洲那样,很多国家是在现代国家前就固定下来了,中国边疆原有的民族政治格局被打破,在边界的确定上必然带有 “硬伤”。
三、中国的边疆研究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边疆受到“大传统—小传统”结构和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其在民族、文化及地域范围内是不断变化的,没有“静止”的边疆,只有“变化”的边疆。所以,我们看待边疆问题时不能附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原则,研究边疆问题时不能将边疆看作静止的、没有自主性的,也不应站在中心的角度来看待边疆问题,认为边疆只是中心的衍生。要从历史文化出发来进行本土研究,即边界研究到边境研究,充分揭示边疆自身的发展逻辑。唯有如此,才能明晰其发生的各种情况。
“边界”是现代西方国家构建而出现的概念,意指国与国之间的权力行使范围必须有一条绝对的界线。这样划定封闭的范围后,边疆地带与内地之间相比便失去了层次感和差异性,边境地区被看作与内地一样,在政治、文化或生活方式上必须与内地保持一致。所以,边疆问题只剩下边界了。从帝国时代起,边疆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边疆虽然地处边缘,但国家在边疆的所作所为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非常关键。”⑤现今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多是为边界的划分、边界问题的产生搜集证据和材料,或进行不同层面的解释,或以边界为界限对边疆地区进行“静止”的民族文化“抢救”调查,这都是站在国家层面进行的边疆研究。袁剑在翻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时提到,中国边疆研究,主要以两条路径展开,其一为本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其二则是国外学者的成果译介,在这方面,目前以对专门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居多……怎样“进入”边疆,是关键所在,不仅要在材料发掘上有新的进展,同时也需要在视角和观念认识上加以转化与提升。⑥而没有从边疆地区自身的发展变化出发,不重视边民自身,可以说是沿着国家权力的思路进行研究的,不符合中国边疆的特殊国情。这产生的结果是对边疆静止的想象,对真正的边疆知之甚少,而且对边疆发生的事莫名惊讶。为此,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必须是“流动”的。只有如此,才能看出和解决边疆的某些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欣在其文章中提出,要从古代中国政治边疆、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的视野出发,充分认识和评价无形的经济边疆和文化边疆在有形的政治边疆形态发展和演变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中国国家形态自身发展规律,从而阐明当代中国边疆的历史延续性与合理性。⑦
综上所述,边疆研究应该转向对于边疆本身的重视,不用“边界”这个主题词,而要提倡使用“边境”这一主题词,一是因为“边境”一词没有现代政治的涵义,边境能更好地体现“边缘”的意味,让我们感到边缘的存在。二是“边境”比边界对环境、文化、民族等更有包容性,它不局限于边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会触及边界线以外的地区,它体现的是一种区域性和完整性。《国语·楚语上》有“夫边境者,国之尾也”之说,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尾有平衡身体、助跑等功能,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只进行边界研究,就会忽视边境的重要性,进而忽视其在整个国家中的作用。
总之,边疆研究要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找到符合本土情况的研究。边疆研究需要深入田野调查,不能只从文献资料入手,还要从边境本身存在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身体力行充实边境地区的资料和理论。对于历史问题,我们采取承认的态度,既往不咎,要解决边境当下的问题,解决如何认识边境重要性的问题。
注释:
①塞缪尔·亨廷顿(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
②欧文·拉铁摩尔(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③黄达远:《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例》[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3年第143期,第16页。
④施坚雅(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中华书局,2000年,第378页。
⑤欧立德(美):《乾隆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7页。
⑥巴菲尔德(美):《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⑦王欣:《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以欧文·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4年第166期,第30页。
〔责任编辑:李爱民〕
●文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