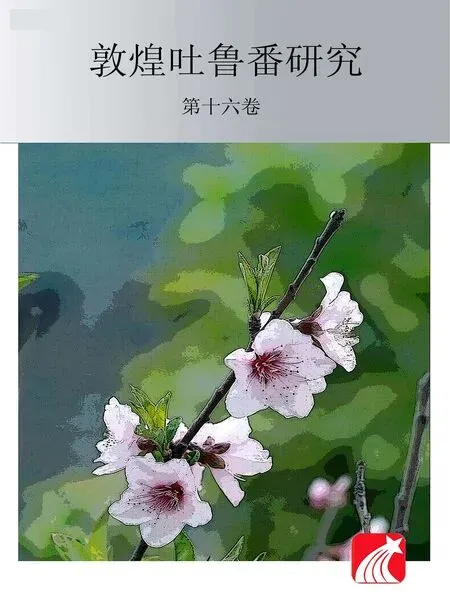敦煌的張淮深時代
——以歸義軍與唐中央之關係爲中心
李 軍
(作者單位: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敦煌的張淮深時代
——以歸義軍與唐中央之關係爲中心
李 軍
咸通八年(867),唐政府將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徵召至長安。張議潮歸闕之後,其侄張淮深開始執掌歸義軍大權。自咸通八年至大順元年(890),張淮深掌握歸義軍實際權力的時間長達23年。正是在這段時間裏,回鶻、嗢末等少數民族勢力陸續在河隴地區崛起,極大地改變了該地區的政治形態。在河隴政局持續動蕩的背景下,歸義軍與唐中央之間的關係對歸義軍及河隴政局均産生了重要影響。對於張淮深時期歸義軍與唐中央的交往,榮新江、楊秀清等先生通過宏觀的研究,歸納出雙方關係較爲冷淡的總體特徵*榮新江《沙州張淮深與唐中央朝廷之關係》,《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2期,1—13頁,收入同作者《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69—196頁;楊秀清《晚唐歸義軍與中央關係述論》,《甘肅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69—72頁。。本文希望能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從微觀的角度觀察歸義軍與唐中央政府關係演變及其對河隴政局的影響。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一
咸通二年(861),張議潮率軍收復河西重鎮涼州。與此同時,秦州刺史兼防禦使高駢則先後收復隴右的河、渭、鄯等州。咸通四年(863),唐政府通過新置天雄軍及涼州節度的方式,對此前主要依靠歸義軍掌控河隴的策略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對於高駢收復河、渭等州及唐政府析置節度的情況,可參拙文《晚唐政府對河隴地區的收復與經營——以宣、懿二朝爲中心》,《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3期,113—133頁。。由於歸義軍經營河隴的意願與唐政府的戰略意圖之間存在矛盾,所以,雖然張議潮在咸通七年七月有進奉“甘峻山青骹鷹四聯、延慶節馬二匹、吐蕃女子二人”的舉動*《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660頁。,但其在次年二月就被唐政府徵召入京*《資治通鑑》卷二五,唐懿宗咸通八年二月條,北京: 中華書局,1956年,8117頁。。張議潮在歸闕後不僅被授予右神武統軍的武職事官,更是被“宣陽賜宅”、“錫壤千畦”*内容見敦煌寫本《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以下簡稱《張淮深碑》),録文參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401頁。,中央政府希望將其長期羈絆於長安的意圖表露無遺。根據P.3281V《馬通達狀稿(三件)》第一件的記載,張議潮入京後曾派遣親信馬通達返回沙州迎接家人入京,該舉動表明張議潮最終接受了唐政府將其留置在京師的安排。但在入京任職之後,張議潮仍對河隴地區的政情保持了高度的關注。在張淮深以沙州刺史的身份派遣使者入京彙報吐谷渾等族的活動情況時,張議潮曾上表懿宗,希望能夠“逐件分析”*詳情見S.10602《張議潮奏藩情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非佛經以外部份)》第13卷將其定名爲《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奏蕃情表》,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4頁。。此外,面對唐政府以“糧料欠缺”爲由,希望放棄經營涼州的局面,張議潮又“遽有奏論”,明確提出反對意見,並由此獲得了懿宗的嘉獎*詳情見S.6342+Дx.05474V《張議潮處置涼州進表》。對於S.6342號文書的性質及寫作時間,唐耕耦先生認爲是張議潮咸通二年收復涼州時所上的奏表;榮新江先生認爲文書可能作於咸通四年左右;鄭炳林先生將其與Дx.05474V號文書綴合後,則指出此篇文書是張議潮在唐中央準備放棄經營涼州時所上的奏表,表文撰寫的時間應在咸通十一年至咸通十三年之間。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4輯,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363頁;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58—159頁;鄭炳林《敦煌寫本〈張議潮處置涼州進表〉拼接綴合與歸義軍對涼州的管理》,《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384頁。。根據張議潮歸闕後上表關注河隴政情的表現,學者多推測唐朝徵召張議潮入朝後,仍讓其遥領歸義軍節度使之任,以間接控制歸義軍政權*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63—164頁;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繫年(咸通七年—十三年)》,《慶祝寧可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273—274頁。《英藏敦煌文獻》第13卷的整理者將S.10602視爲“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的奏蕃情表,表明其接受了張議潮入朝後遥領歸義軍的觀點。。但筆者認爲根據現有的材料,似尚不足以證明張議潮入朝後遥領了歸義軍節度使之任。
首先,在張議潮入朝後所上的兩件表文中,並未顯現出其具有歸義軍節度使的身份。其中,S.6342+Дх.05474V《張議潮處置涼州進表》的作者被記作“張議潮”;S.10602《張議潮奏藩情表》的作者則自稱爲“臣”,均未見“歸義軍節度使”。如果唐政府確實允許張議潮遥領歸義軍,那麽歸義軍節度使就屬於其本人的合法身份。如此一來,張議潮主動放棄顯示自己合法身份的舉動就令人費解,更何況保存在敦煌文獻中的兩件表文屬於張議潮原表的抄件,表明其在歸義軍内部傳播時也未體現出張議潮的節度使身份。《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八月條載:“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爲歸義節度使。”*《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八月條,8164頁。由此可證在司馬光看來,張議潮在入朝後或保留了歸義軍節度使的職任。但該條記載中與張議潮之薨相關聯的曹議金代領軍府及繼任節度使兩事均誤,所以張議潮入朝後仍遥領節度使的記載是頗值得懷疑的。在筆者看來,司馬光在此處可能只是沿用了張議潮的舊稱而已,並不能作爲張議潮入朝後仍遥領歸義軍節度使的確實證據。
其次,在張議潮入朝後,歸義軍内部對張議潮的稱呼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證明其身份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在張議潮出任歸義軍節度使期間,由於其並未使用唐政府授予的歸義軍節度使,而是自稱河西節度使,所以歸義軍治下軍民多使用“河西節度使”或節度使加檢校官的模式予以指代。作爲張議潮收復涼州之後所修造的功德窟,莫高窟第156窟張議潮的供養人題記載“窟主□(河)西節度使金紫光禄大夫……尚書……”;繪於該窟南壁的《張議潮出行圖》榜題則爲“河西節度使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張議潮統軍□除吐蕃收復河西一道行圖”*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6年,73、74頁。。此外,據學者考證,P.3804《開經文》是沙州張氏家族用於咸通七年中秋慶寺法會的願文*楊寶玉、吴麗娱《P.3804咸通七年願文與張議潮入朝前夕的慶寺法會》,《南京師大學報》2007年第4期,66—72頁。。該件願文分别爲大唐咸通皇帝、河西節度使開國公、敦煌敕授金紫魚袋刺史張公等人祈福,其中的河西節度使開國公顯然就是指尚未入朝的張議潮。根據位於莫高窟第192窟東壁門口上方、由龍興寺沙門明照所撰的《咸通八年二月廿六日社長張大朝等發願功德贊文》,可知在張議潮入朝之初,沙州民衆仍然以“河西節度使萬户侯□司空張公”的舊稱指代張議潮*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85頁。。但是在張議潮出任統軍的消息傳回沙州後,即使是原屬張議潮心腹的恒安和馬通達等人,也不再稱張議潮爲節度使,而是僅稱其爲“阿郎”或以檢校官指代。在P.3730V收録的多件書狀中,恒安都是以“阿郎”作爲張議潮的尊稱;在S.6405V《僧恒安致郎君謝司空寄縑緗狀》中,恒安則致信郎君,對“司空”張議潮遠寄縑緗表示感謝。P.3281V《押衙馬通達狀稿(三件)》第一件則記載“自小伏事司空”的馬通達,在聽聞“司空出來”的消息後,希望能夠“匍匐到靈州已來迎候司空,卻歸使主”。其所謂的“使主”,指的是此時控制歸義軍的張淮深,而非前任張議潮。恒安及馬通達在張議潮入朝後仍然與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但均不再以節度使稱之,表明張議潮在被授予神武統軍之後已經喪失了歸義軍節度使的身份。
最後,根據張議潮入朝後所擔任武職事官的特性,也可以從側面證明唐政府並未以張議潮遥領歸義軍節度使。對於張議潮出任統軍之事,《新唐書》卷二一六下《吐蕃傳下》載:“(咸通)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新唐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6108頁。《張淮深碑》則云:“事有進退,未可安然,須拜龍顔,束身歸闕。朝庭偏寵,官授司徒,職列金吾,位兼神武。(自注曰: 司徒自到京師,官高一品,兼授左神武統軍,朝庭偏獎也。)”*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401頁。據P.3730V《張氏歸義軍時期書狀》第二件書狀所載,張議潮拜官的消息在咸通八年九月左右傳達沙州後,作爲心腹的恒安曾致信張議潮,對其“榮拜統軍”表示祝賀*吴麗娱、楊寶玉《P.3730V張氏歸義軍時期書狀考釋》,《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78—286頁;楊寶玉、吴麗娱《張議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人士的往來及其對敦煌政局的影響——以P.3730V、S.6405V爲中心,兼及P.3281V、S.2589》,劉進寶、高田時雄主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31—342頁。。按唐朝禁軍體系中設置統軍始於德宗興元元年(784)正月,是時“詔以六軍各置統軍一員,秩從二品”*《舊唐書》卷一二《德宗紀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340頁。。貞元十四年(798)七月,唐政府又於左右神策軍各置統軍,“品秩奉給視六軍統軍例”*《舊唐書》卷一三《德宗紀下》,388頁。。唐政府設置統軍的初衷本爲安置功臣,故不僅品秩較高,且“除制以白麻付外”以示恩寵*《新唐書》卷一六五《鄭絪傳》,5075頁。。不過在制度執行過程中,統軍卻由尊崇功臣之任逐漸轉化爲安置卸任節度使的閑職,故其品階也由從二品降爲從三品*《新唐書》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1290—1291頁。。通過檢索文淵閣《四庫全書》及“中國基本古籍庫”等電子數據庫,可知在張議潮之前,由現任節度使轉任統軍者至少有陳楚、程日華、韓游瓌、劉昌裔、范希朝、孟元暢、高固、張伯儀、史憲忠、石雄、鄭光、李祐、戴休顔、程懷直、張茂宗等十五人。但我們並没有在傳世史料裏找到這些藩鎮節度使改任統軍後仍遥領本鎮的案例。綜上所述,筆者認爲張議潮在歸闕後應並未繼續保留歸義軍節度使之職任。
咸通八年九月,歸義軍的入朝使者爲沙州帶回了張議潮留任長安的消息。從時間上判斷,P.3730V《張氏歸義軍時期書狀》第一件書狀中提及的使團應該是在張議潮入朝後,張淮深以歸義軍實際統治者的身份所派遣的首班入朝使團。而S.10602《張議潮奏蕃情表》則載:
臣伏蒙聖恩,許賜對見。緣臣生長邊塞,習禮不全,所奏蕃情,恐有不盡。今逐件狀分析,伏乞皇帝陛下,俯賜神鑒,謹具如後:
一、 昨沙州刺史張淮深差押□[衙](下殘)
急被退(下殘)
敕割屬(下殘)
(上殘)退渾(下殘)*録文參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63頁;圖版見《英藏敦煌文獻》第13卷,74頁。
從表文中“伏蒙聖恩,許賜對見”的表述看,該表應作於張議潮入朝後不久。彙報吐谷渾活動情況的押衙,或即將張議潮出任北衙禁軍長官的消息帶回沙州的使團成員*據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繫年(咸通七年—十三年)》(278頁)考證,該表或作於咸通九年二月左右。。而P.3451《張淮深變文》文末的附詩中,有涉及所謂“退渾小丑”的内容。雖然其下文殘缺,但結合詩歌的總體内容,可知“退渾小丑”之下應該是張淮深擊敗與歸義軍爲敵之吐谷渾的内容。所以,張淮深在張議潮歸闕後不久就已經遣使入朝,而使團所彙報的蕃情,應該是張淮深本人穩定治内統治秩序的功績*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繫年(咸通七年—十三年)》則根據S.10602《張議潮奏蕃情表》中“急被退[渾]”等内容,推測張淮深所遣的入京使者被退渾所劫,未能平善到京。。
根據P.3730V《張氏歸義軍時期書狀》第四件書狀的記載,在張議潮的家人離開沙州赴京之後,張議潭的死訊始傳回歸義軍,故恒安纔會再度致信張議潮以示哀悼。而在張球所撰的P.3425《金光明變相一鋪銘並序》中,提及“使持節沙州刺史充歸義軍兵馬留後當管營田等使守左驍衛大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河張厶乙……今者所丹繪前件功德,奉爲亡考常侍,唯願承兹法棹,生就蓮宫”*《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69頁。。對於所謂的“張厶乙”及“亡考常侍”,榮新江先生已經指出應指張淮深及張議潭*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82頁。對於該件文書的寫作時間,榮新江先生根據張議潮入朝的時間及撰寫者張球的官銜,指出應在咸通八年至咸通十年之間。。張淮深爲張議潭祈福的時間應在其亡故的消息傳回沙州後不久,而張淮深開始自稱節度留後的時間也應該在此前後。值得注意的是,張淮深並未沿用此前張議潮所使用的河西節度使稱號,而是使用了由唐政府所授予的歸義軍稱號。張淮深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擺脱張議潮遺留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面也能顯示出對唐政府的歸順態度,從而有利於得到中央的承認。
S.6405V《僧恒安致郎君謝司空寄縑緗狀》又載:
僧恒安。右恒安,二月廿日敦煌縣令宋智岳使回,伏奉委曲,兼疋段等,跪授(受)驚惕,無任戰懼。且恒安生自邊土,智乏老誠(成)……伏蒙司空……遠寄縑緗,願持掃灑之功,巨答丘山之福。限以道阻,不獲隨狀陳謝。謹録狀上。*録文參楊寶玉、吴麗娱《張議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人士的往來及其對敦煌政局的影響》,333頁;圖版見《英藏敦煌文獻》第11卷,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43頁。
由此可知,張淮深在遣使入朝以彙報自己擊敗吐谷渾的功績之後,又曾派遣以敦煌縣令宋智岳爲首的使團前往長安。據學者考證,S.6405V文書爲P.3730V第六件書狀的定稿,所作的時間不早於咸通九年二月下旬*楊寶玉、吴麗娱《張議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人士的往來及其對敦煌政局的影響》,337頁。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事繫年(咸通七年—十三年)》(279頁)則直接將S.6405V《僧恒安致郎君謝司空寄縑緗狀》繫於咸通九年二月。。宋智岳使團入京的時間,顯然應晚於將張議潮留京任職的消息帶回沙州的使團。根據S.1156《光啓三年(887)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所載,光啓三年二月二十日沙州使者宋閏盈在參見“四宰相兩軍容及長官”時,認爲在張淮深屢次請節的情況下,“廿餘年,朝廷不以(與)指撝”;張文徹在與宋閏盈爭論時,也指出“二十年已前,多少樓羅人來,論節不得”*録文參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87—189頁;圖版見《英藏敦煌文獻》第2卷,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241—242頁。。所以,張淮深開始請節的時間應始於咸通八年左右。由此看來,宋智岳入朝很有可能承擔了爲張淮深請節的任務。
與此同時,張議潮對張淮深急於取得歸義軍統治權的舉動卻並不認可。在張淮深遣使彙報自己擊敗吐谷渾的功績時,張議潮卻以“所奏蕃情,恐有不盡”爲由,爲懿宗“逐件分析”張淮深所彙報的政情,顯示出對張淮深的不信任態度。此外,身處長安的張議潮還通過書狀及歸義軍的使團與沙州的人員保持了密切的聯繫。張淮深所派遣的敦煌縣令宋智岳使團,在没有完成既定使命的情況下,卻爲與張議潮入朝後保持密切聯繫的恒安帶回了縑緗賞賜,證明其入京後與張議潮有所接觸。雖然張議潮離開沙州,但其對歸義軍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即使在張淮深自稱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的情況下,歸義軍僚佐仍然在沿用張議潮時期的做法,以河西節度使僚佐自居。張球撰於咸通十二年二月的P.4660(14)《故敦煌郡耆壽張禄邈真贊題記》明確記載張禄生前的職銜爲“河西節度押衙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敦煌郡耆壽”;S.530《大唐沙州釋門索法律義辯和尚修功德記碑》稱呼索忠信爲“前河西節度押衙”;P.4660《張議廣邈真贊》則記載張議廣的職銜爲“唐河西節度押衙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侍御史”。由此可見,歸義軍的僚佐對張淮深改弦更張的做法並不認可。
此外,正如筆者所指出的那樣,隨著宣懿的替代,唐朝的政治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唐政府針對歸義軍的態度也趨於强硬。在收復涼州、河州、渭州等河隴重鎮後,唐政府開始通過在河隴地區析置節度、分割歸義軍轄區等方式,持續削弱歸義軍的勢力。張議潮力圖控制河隴地區的意願與唐政府經營河隴的策略明顯抵觸,所以兩者的關係在咸通年間呈現出了惡化的趨勢,甚至張議潮都被唐政府强制徵召到了長安*拙文《晚唐政府對河隴地區的收復與經營——以宣、懿二朝爲中心》,113—114頁。。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張淮深通過主動放棄河西節度使稱號、派遣使者入京彙報蕃情等方式,明確顯示出依附於中央的態度,但册封張淮深並不符合唐中央政府削弱歸義軍勢力的初衷。所以,雖然張淮深在咸通十年(869)十二月爲悟真求得了河西都僧統的任命,但此際其本人的職銜卻只是“沙州諸軍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見P.3720(5)《沙州刺史張淮深奏白當道請立悟真爲都僧統牒並敕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13頁。。這也就證明在張議潮入朝後的兩年半時間裏,雖然張淮深多次遣使入朝,但卻僅獲得御史中丞的憲銜而已。
二
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張議潮卒於長安。在張議潮的死訊傳回沙州後不久,就有人再度抄寫創作於數十年之前的《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以凸顯與唐王朝中興密切相關的龍興寺之重要地位,政治意味較爲明顯*拙文《從敦煌龍興寺看張氏歸義軍的内部矛盾》,鄭炳林、樊錦詩、楊富學主編《敦煌佛教與禪宗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7年,104—119頁。。雖然上述舉動未必是張淮深所指使,但張議潮之死對於張淮深穩固内部權力及向中央請節,顯然都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張淮深在加强對内控制的同時,開始借助抵禦少數民族侵擾的機會頻頻遣使長安,希望能借此獲得唐政府的節度使册封。
《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條載:
初,回鶻屢求册命,詔遣册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册、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僖宗乾符元年十二月條,8174頁。
根據此時吐谷渾、嗢末的分佈範圍及郗宗莒的出使路綫,學者多認爲被擊破的應是生活在河西甘州一帶的回鶻*長澤和俊著,鍾美珠譯《唐末、五代、宋初之靈州》,同作者《絲綢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284頁;周偉洲《吐蕃對河隴的統治及歸義軍前期的河西諸族》,《甘肅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楊聖敏《資治通鑑突厥回紇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304頁;陸慶夫《論甘州回鶻與中原王朝的貢使關係》,《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但長澤和俊和楊聖敏先生將此回鶻視爲甘州回鶻,似未確。因爲雖然這些回鶻此時可能生活在甘州,而且與此後建立的甘州回鶻政權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但兩者此時尚還不能等同。關於甘州回鶻政權的相關問題,可參閲榮新江《甘州回鶻成立史論》,《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32—39頁。。唐政府之所以在乾符元年遣使册封“屢求册命”的回鶻,當與此前原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已卒於長安有關。正是因爲司馬光看到了張議潮之死與回鶻等少數民族崛起於河西之間的關係,所以《通鑑》中纔會在記載張議潮卒於長安後,又有“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爲羌、胡所據”的敍述*《資治通鑑》卷二五二,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八月條,8164頁。。而據筆者考訂,乾符元年之前迅速崛起於甘州等地的回鶻應來源自安西,而這些回鶻是由此前被僕固俊所殺的龐特勤之後嗣率領東遷的*對於甘州回鶻的族屬,學術界存在較大的爭論,而筆者認爲其應源自安西回鶻。在僕固俊於咸通七年發動政變殺死其同父異母的兄長龐特勤後,安西回鶻部衆發生大規模的離散,龐特勤的子嗣率衆東遷至河西的甘州一帶。對於具體的論證過程,可參拙文《甘州回鶻建國前史鉤沉——以甘州回鶻的淵源爲中心》,《中國中古史集刊》第3輯,北京: 商務印書館,待刊。。在唐政府長期虚設歸義軍節度使及張議潮逝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回鶻在咸通末至乾符初先後從歸義軍手中奪得伊州、肅州、甘州及瓜州等地*馮培紅認爲回鶻在乾符初年從歸義軍手中奪得了瓜、肅、伊三州,見《敦煌的歸義軍時代》,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136—142頁。。
在大中五年(851)設置之初,歸義軍的法定轄區爲河隴十一州的廣大區域。但是在唐政府於咸通四年以河隴新復地新置天雄軍及涼州節度使之後,歸義軍的轄區當被限制在沙、瓜、甘、肅、伊等五州,即歸義軍設置之初張議潮所實際控制的區域之内*拙文《晚唐政府對河隴地區的收復與經營——以宣、懿二朝爲中心》,113—133頁。,而新置的涼州節度則“領涼、洮、西、鄯、河、臨六州”之地*《新唐書》卷六七《方鎮表四》“河西”欄,1886頁。。根據P.4660《河西都防禦右廂押衙王景翼邈真贊並序》的記載,可知唐政府曾於咸通十二年(871)至乾符三年(876)之間將涼州節度使改制爲河西都防禦使,故原歸義軍僚佐王景翼生前出任了“河西都防禦使右廂押衙”。我們知道咸通末至乾符初正是回鶻於河西東部地區崛起、歸義軍政權風雨飄摇之際,唐政府借此機會,通過改置涼州地區的軍政機構,將本屬於歸義軍統轄的甘、肅二州劃歸給了河西都防禦使。雖然作爲沙州刺史的張淮深對於唐政府强制剥奪甘、肅二州的做法無可奈何,但對於唐政府所力圖册封的回鶻則採取了積極軍事打擊的手段。
根據S.389《肅州防戍都狀》的記載,中和四年之際,在被回鶻持續圍攻的甘州城内居住有吐蕃、吐谷渾、龍家等少數民族。爲了在吐蕃和吐谷渾撤離甘州後繼續抵禦回鶻,龍家派使者向涼州嗢末求救,並以“如若不來,我甘州便共回鶻爲一家,討你嗢末”相威脅。以上跡象可以證明,中和四年圍攻甘州的回鶻應該正是吐蕃、嗢末及吐谷渾等於乾符元年所破之回鶻。而P.3720《張淮深造窟功德記》有載:“河西異族狡雜,羌、龍、温未、退渾,數十萬衆,馳城奉質,願效軍鋒。”*録文參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267頁。《張淮深碑》亦載:“河西創復,猶雜蕃渾,言音不同,羌龍嗢末,雷威懾伏,訓以華風,咸會馴良,軌俗一變。”*録文參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402頁。所謂的“願效軍鋒”、“雷威慴伏”,應就是指上述少數民族曾擊潰原盤踞在甘州一帶,此後持續與歸義軍爲敵的回鶻而言*拙文《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再收瓜州史事鉤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64—71頁。。雖然根據已有的證據還不足證明嗢末及吐谷渾擊潰回鶻定是受命於張淮深,但我們知道在張議潮時期,歸義軍與吐蕃的尚婢婢集團之間就存在聯盟關係*陸離、陸慶夫《張議潮史跡新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期,95—109頁。;而在此後的金山國時期,張承奉在甘州回鶻圍攻沙州城的情況下,曾派遣羅通達前往吐蕃求援*P.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耆壽百姓一萬人上回鶻可汗狀》,《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59頁。。此外,在吐蕃等族擊潰回鶻並佔據甘州後,與歸義軍保持了長期和平共處的關係。所以,歸義軍與擊潰回鶻的少數民族勢力之間或存在某種程度的聯盟關係。也正是因爲如此,張淮深纔會將吐蕃等族擊潰佔據甘州等地的回鶻視爲自己的功績,並上報中央政府*根據P.3451《張淮深變文》的記載,在唐中央所派遣的李衆甫使團對張淮深進行册封時,張淮深曾有“微臣幸遇陶唐化,得復燕山獻御容”之語。因爲變文中有張淮深“引旆奔沖過大泉”,以抵禦侵犯歸義軍的回鶻的描寫,可知張淮深首敗回鶻是在沙州附近。由此可知,張淮深在首敗回鶻之前曾有“得復燕山”之舉,並將消息彙報給了唐中央政府。鄧文寬《張淮深平定甘州回鶻史事鉤沉》(《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5期)已指出“燕山”即位於涼州番禾縣至甘州删丹縣之間的焉支山。所以,“得復燕山獻御容”,應指張淮深驅逐此前佔據甘州的回鶻而言。。
P.3451《張淮深變文》中“去歲官崇驄馬政,今秋寵遇拜貂蟬”的記載*本文所引P.3451《張淮深變文》的内容,均參黄征、張湧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191—194頁。以下不再一一出注。,證明張淮深在獲得檢校散騎常侍的前一年,曾獲得過“驄馬政”即御史臺憲銜的册封。而據筆者考證,《張淮深變文》應作於乾符四年(877),所以張淮深獲得此次憲銜晉昇的時間或在乾符三年。張淮深之所以能在“去歲官崇驄馬政”,當是之前“得複燕山獻御容”的結果。乾符元年年底,回鶻始被嗢末等擊潰,所以張淮深將“得復燕山”之消息上奏給中央及獲得封賞的時間又當在其後。
此外,《張淮深變文》在記載張淮深首敗回鶻後,有云:“敢死破殘回鶻賊,星馳羽□□□□。初言納款投旌戟,續變□□□□□。早向瓜州欺牧守,今朝此處□□□。”根據唱詞的内容並結合相關敦煌文獻,可知這支侵擾沙州的回鶻此前曾宣稱要降附於歸義軍,所以張淮深曾派遣馬通達出任“勾當回鶻使”處理此事*P.3281V《押衙馬通達狀稿(三件)》第二件被塗抹的原稿中有“今歲伏蒙大夫威感,□到家鄉。到來便差勾當回鶻使及馬□”等内容,可與《張淮深變文》中回鶻“初言納款投旌戟”的記載相對應。。但之後事態發生變化,回鶻通過欺騙的方式奪得瓜州。爲了防止張淮深“徵兵來伐”,回鶻首領“受命”率軍侵擾沙州。在擊敗回鶻後,張淮深隨即派遣使者將“獲捷匈奴千餘人,縶於囹圄”的消息上奏僖宗。但僖宗在指責回鶻“不能堅守誠盟,信任諸下,輒敢倡狂”之餘,卻以“義不伐亂”的名義,命張淮深盡數釋放所俘的回鶻部衆。不過與咸通年間唐政府對歸義軍持續採用强硬的態度不同,僖宗時期的政策更爲緩和。爲了安撫張淮深,唐政府派出了由左散騎常侍李衆甫、供奉官李全偉、品官楊繼瑀等九人組成的册封使團,爲張淮深帶來慰諭詔書的同時,還爲其帶來了檢校左散騎常侍的任命。
由於有僖宗“義不伐亂”的詔命,且得到了散騎常侍的檢校官,故張淮深悉數釋放了被俘的回鶻。但在李衆甫等人通過肅州之後,又有“回鶻王子,領兵西來,犯我疆場”。榮新江先生根據中央使者的位置以及回鶻行軍的路綫,指出這股由回鶻王子率領的回鶻應來自肅、瓜之間*榮新江《歸義軍研究》,300頁。。而聯繫之前被俘的回鶻首領曾自稱“奉命差來非本意”、“實慮尚書徵兵來伐”,其與回鶻王子應同屬於一支勢力,即此時佔據瓜州之回鶻。這支回鶻在唐中央使團通過瓜州後,纔再度興兵侵擾歸義軍,可以證明其最起碼在名義上仍聽命於中央政府。回鶻王子領兵潛至西桐,從而與佔據瓜州的回鶻從東西兩個方向形成了對沙州的夾擊之勢。在生死存亡之際,張淮深先是率軍在西桐擊敗回鶻,隨即在乾符四年十月率軍東征,一舉收復瓜州*拙文《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再收瓜州史事鉤沉》,64—71頁。。
在立下收復瓜州的功績後,張淮深自認爲已經具備了獲得節度使册封的資本,所以在乾符四年年底派遣以陰信均爲首的賀正使團入京。該使團名爲賀正,但本意卻是希望借助張淮深收復瓜州的功績,爲其求得節度使的册封。雖然此次“奏論請賜節事”仍未得到唐政府的認可,但張淮深卻在獲得豐厚物質賞賜的同時,檢校官也得以由散騎常侍晉昇爲户部尚書。
三
S.329V《兒郎偉》正文前有雜寫兩行,即“敕歸義軍節度兵馬留(下空)”及“敕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觀察使御史大夫張”。據筆者考訂,S.329V《兒郎偉》應是歸義軍在乾符三年除夕祝願“大夫”張淮深能於次年獲得唐中央政府給予節度使册封的驅儺唱詞*拙文《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稱號問題再探》,《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43— 49頁。。第一行雜寫與《兒郎偉》筆跡相同,所以兩者所寫的時間當爲同時,由此可證張淮深至遲在乾符三年左右仍然在自稱歸義軍兵馬留後。根據《張淮深碑》中張淮深“加授户部尚書,充河西節度”的記載,證明其在獲得檢校官户部尚書之前應一直在自稱留後。不過即使在張淮深立下收復瓜州等功績的情況下,唐政府仍不同意爲其授節。這促使張淮深最終放棄之前自稱留後的做法,開始重新使用張議潮時期所慣用的河西節度使稱號。所以,張淮深放棄歸義軍兵馬留後,自稱河西節度使的時間應在陰信均、賀正使團將唐政府所賜予的敕牒帶回沙州之後。此外,P.2913《張淮深墓誌銘》中有“乾符之政,以功再建節旄”的記載,學者之前已經指出張淮深在乾符年間並未獲得節度使册封*榮新江《沙州張淮深與唐中央朝廷之關係》,《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2期,8— 9頁。;而我們也知道文德元年張淮深之所以被授節,與其所誇耀的“乾符之政”並没有直接的關聯,所以墓誌銘中所謂的“再建節旄”應該是指張淮深通過連續擊敗回鶻,尤其是收復瓜州的功績,借助唐政府授予其檢校户部尚書的機會自稱河西節度使而言。
根據《張淮深碑》的記載,在張淮深“加授户部尚書,充河西節度”之後,又因爲在内政上取得“九功惟敍,黎人不失於寒耕;七政調和,秋收有豐於歲稔”的功績,故得以“加授兵部尚書”,從而完成了“官遷五級”的第五級。對此,P.3718《張清通寫真贊並序》卻載:“大中之載,駕行西川。公能盡節,面對龍顔。詔宣西夏,溥洽遐藩。”“大中赤縣沸騰,駕行西川蜀郡,使人阻絶不通……公乃獨擅,不憚劬勞。率先啓行,果達聖澤。五回面對,披陳西夏之艱危;六度親宣,詔諭而丁寧頗切。奏論邊懇,申元戎憂國之心。”*録文參姜伯勤、項楚、榮新江《敦煌邈真贊校録並研究》,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241—242頁。對於寫真贊中的“大中之載”,學者已經指出當爲“中和之載”之誤*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443頁。。這就證明在中和元年(881)之際,歸義軍曾與播遷至成都的僖宗政權取得聯繫。正是通過中和元年的通使,纔使得“詔宣西夏,溥洽遐藩”。而唐僖宗此次下達給歸義軍的詔命,應即將張淮深的檢校官由户部尚書晉昇爲兵部尚書之事。爲了消除自己未獲得節度使册封的負面效應,張淮深命心腹撰寫《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大力表彰其在歸義軍内部治理方面所取得的功績。
S.2589《中和四年(884)十一月一日肅州防戍都營田康漢君等狀》提及由張淮深所派遣的宋輸略使團在完成出使中央的任務返回沙州途中,在邠州見到了“郎君二人及娘子家累、軍將、常住等廿人”*文書圖版見《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4卷,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11頁。。但令人意外的是,張議潮之子淮詮不是計劃與歸義軍使團同返沙州,而是希望追隨嗢末使者返鄉。事件最終的結局也頗富戲劇性,張淮詮等人因爲“裝束不辦,發赴不得”,而宋輸略等七人組成的使團則經行河州路,順利返回河西。根據上述狀文的記載,我們看到歸義軍使團在淮詮等人返鄉的問題上並未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協助。作爲肅州防戍都的官員,康漢君在向張淮深彙報政情時,也特别將淮詮等人意圖返鄉的事件著重點出,顯示出其已經預見到張議潮子弟返鄉將對歸義軍内政産生重大影響。光啓二年(886)之際,張淮深派出了以高再晟、宋閏盈、張文徹爲首的三班求節使團*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0頁。。此次遣使頗不尋常,首先是短短一年之内連續派遣三班使團求節,强度前所未有;再有就是人員規模龐大,多達60餘人,遠勝以往;而最令人矚目的則是使團内部針對請節之事發生了明顯的分裂。根據張淮深的舉動及歸義軍内部的分裂情況,或可以推測張議潮的正統繼承人張淮鼎在此之前已經返回沙州*可參拙文《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事跡考》,《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2期,1—14頁。。不過,即使在宋閏盈等人痛陳張淮深“拓邊効順,訓襲義兵,朝朝戰敵,爲國輸忠”,且指出“絶商量,即恐邊塞難安”的情況下*見S.1156《光啓三年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2卷,241頁。,唐政府仍然拒絶爲張淮深授節,而只是通過爲張淮深及其子張延綬等人加官的方式敷衍了事。
在唐政府設置河西都防禦使後,原屬於歸義軍的甘、肅二州被劃入河西都防禦轄區。此外,張淮深爲中央政府所承認的官方身份僅爲沙州刺史,所以在原則上其對於瓜州也不具有管轄權。由於甘州地區已被吐蕃、吐谷渾等少數民族佔據,且其地與涼州接壤,所以唐政府得以在中和元年以翁郜出任甘州刺史。也正是因爲如此,在甘州被劃入河西都防禦轄區後,甘州就已經脱離了歸義軍的實際控制。而隨著回鶻的再度崛起,中和四年之後甘州成爲甘州回鶻牙帳所在,所以莫高窟第148窟《大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中李弘諫在乾寧元年(894)所擔任的甘州刺史只能是虚銜遥領而已。但對於毗鄰沙州的瓜州及被劃入河西都防禦的肅州,張淮深卻始終並未予放棄。根據 P.4660(11)《瓜州刺史康使君邈真贊》的記載,可以證明在張淮深收復瓜州後,仍然是由歸義軍的僚佐出任刺史*對於該件邈真贊的寫作時間,齊陳駿、寒沁《河兩都僧統悟真作品和見載文獻繫年》(《敦煌學輯刊》1993年第2期,151—153頁)繫於乾符六年(879);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事繫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敦煌學》第27輯,臺北: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2008年,259頁)則將其繫於乾符三年(876)。。P.4638《瓜州牒狀》或是瓜州的官員請求張淮深同意索勳出任瓜州刺史的狀文*參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史事繫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266—267頁。,顯示出沙州刺史張淮深對瓜州的實際控制。肅州雖然一度曾被回鶻佔領,但很快就被張淮深收復。此外,根據S.2589 及S.389兩件《肅州防戍都狀》的記載,肅州防戍都的官員在中和四年至少曾兩度狀上張淮深,不僅向其彙報甘、肅等地的形勢,還涉及唐朝内地的政情等内容。這表明肅州雖然在名義上歸屬於治涼州的河西都防禦使,但由於守將多源自歸義軍,所以實際上卻聽命於張淮深。正是因爲如此,所以肅州守將對崔大夫收繳肅州防禦使官印的意圖進行了抵制。
中和五年(885)三月丁卯,僖宗車駕返回長安;己巳(十四日),御宣政殿,改元光啓並宣佈大赦天下*《舊唐書》卷一九《僖宗紀》,720頁。。P.2696《中和五年三月十四日車駕還京大赦制》鈐有河西都防禦使的印章,證明該制是由河西都防禦使下發至沙州的*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XV,2000年,14頁。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北京: 中華書局,1989年,425— 426頁)根據赦文中的“結正”字樣,認爲其書寫時間應在北宋初年。蔡治淮《敦煌寫本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車駕還京師大赦詔校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650— 659頁)則對文書進行了録文和校釋。。雖然張淮深已具有高級别的檢校官,但真正體現其執掌的只有沙州刺史的職事官而已。既然唐政府的大赦制書由河西都防禦使頒至沙州,表明唐政府此時並不承認歸義軍的節鎮身份,沙州及張淮深只能是處於河西都防禦使的從屬地位。由此可見,雖然歸義軍在乾符年間與唐政府保持了較爲密切的交往,但實際上雙方在河西控制權問題上仍然存在矛盾。這也應該是唐政府始終不願爲張淮深授節的原因。
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也就是在張議潮入朝二十餘年後,張淮深終於迎來了唐政府的節度使册封。榮新江先生根據日本京都有鄰館所藏敦煌文獻,指出唐政府派遣中使宋光庭親赴沙州,授予張淮深節度使旌節,應屬於昭宗登基後的新政之一*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91頁。。而據筆者所考,在張淮深獲得節度使册封的前一年,因涼州缺糧,河西都防禦使翁郜曾至少兩次派遣使者前往沙州求援。在張球的積極協助下,當年九月,張淮深同意援助涼州*可參拙文《晚唐五代歸義軍與涼州節度關係考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90— 96頁;《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譜〉與晚唐河西歷史》,《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42—55頁。。而在次年十月,爲張淮深授節的押節大夫宋光庭等人就抵達沙州。如此看來,張淮深援助涼州當是其獲得節度使册封的直接原因。但令張淮深始料未及的是,唐政府並没有授予其歸義軍節度使,只是授沙州節度使兼沙州觀察處置使*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59頁。,不僅甘州和肅州没有重新劃歸歸義軍,即使是仍由其所實際控制的瓜州也没有被納入轄區。龍紀元年(889)四月八日,在没有轄區調整的情況下,唐政府將河西都防禦使昇置爲河西節度使。此次改置的直接後果,就是迫使張淮深放棄了之前所自稱的河西節度使。
根據P.2854V《正月十二日先聖恭僖皇后忌辰行香文》的記載,大順元年正月十二日張淮深曾以“歸義軍節度使張僕射”的身份爲“先聖恭僖皇后”,即唐穆宗之王皇后的忌日舉辦行香法會*對於文書的撰寫時間,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86頁)認爲應在888—890年間,馮培紅《敦煌本〈國祭行香文〉及相關問題》(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出土文獻研究》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93—294頁)推定爲889年。而據筆者《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稱號問題再探》一文所考,文書應撰寫於890年。。該《行香文》在爲王皇后祈福之餘,還祝願使臣常侍大夫“往來無滯礙之優(憂),去住有清和之泰”;對於張淮深的祝福則是“紫受(綬)與紫蓮齊芳,金章與金剛不壞”*録文參馮培紅《敦煌本〈國祭行香文〉及相關問題》,292頁。。通過此次唐中央使團遠赴沙州,連張淮深的第四子延鍔都獲得了唐政府所賜予的“御史中丞”之憲銜及“賜緋魚袋”的章服*龍紀二年(890)二月十八日Ch.XVIII002《般若心經與四大天王像》張延鍔寫經題記,見松本榮一《燉煌畫の研究》,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122頁。,表明張氏家族中獲得封賞者不在少數。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張議潮之子張淮鼎應就是通過此次册封,獲得了沙州刺史的任命*拙文《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事跡考》,1—14頁。,從而使歸義軍回復到創建初期那種張議潮出任節度使、張議潭擔任沙州刺史的二雄並立局面。無論張議潭所謂的“推夷齊之讓”是否出自本心,但其於大中七年(853)入京確實避免了歸義軍内部出現重大矛盾和分裂。但長期以來,張淮深實際的官職唯有沙州刺史。當唐政府在僅授張淮深沙州節度使、以其領一州之地的情況下,卻將沙州刺史之職讓渡給了張淮鼎,這嚴重影響到了張淮深在歸義軍内部的權威。而張淮鼎在返回沙州前長期生活在長安,其與張淮深的關係同議潮兄弟的情誼顯然是不能比擬的。在唐政府明顯不支援張淮深的情況下,歸義軍内部的反對勢力發動政變也就不可避免了。根據P.2973《張淮深墓誌銘》的記載,在張淮深於大順元年年初舉行國忌行香活動的四十天後,張淮深就舉家被殺於沙州。由此可見,唐政府在大順元年對歸義軍内部統治結構的調整與政變之間應存在密切的聯繫。經過大順元年二月的血腥政變,張淮深一系基本被清除,並由此開啓了之後一系列政治爭鬥的序幕。
四
在張議潮於咸通八年歸闕之後,唐政府應並未以其遥領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是歸義軍實際的統治者。由於看到唐政府將張議潮留任長安,所以張淮深在放棄河西節度使稱號的基礎上自稱歸義軍兵馬留後,並派遣使者前往長安。張淮深希望通過向唐中央表示效忠及展示自己治理歸義軍功績的方式,獲得唐政府的節度使册封。但在懿宗政府以强勢的態度處理藩鎮問題的歷史背景下,張淮深在咸通八年至十三年間僅獲得御史中丞的憲銜而已。所以,在此期間歸義軍與唐政府之間呈現出歸義軍單向入使,唐政府較少回應的態勢,雙方之間的關係較爲冷淡。
隨著回鶻在河西的崛起,唐政府通過將涼州節度使改置爲河西都防禦使的方式,從歸義軍手中奪得甘、肅二州,並意圖承認與歸義軍爲敵的回鶻。在這種背景下,張淮深一方面借助吐蕃、嗢末等族,擊潰了盤踞在甘州一帶的回鶻;另一方面,通過戰爭的方式先後收復肅州及瓜州等地。在上述過程中,每當取得與回鶻作戰的勝利,張淮深都會遣使入朝報捷。雖然没有獲得唐政府的節度使册封,但張淮深卻先後獲得了御史大夫的憲銜及散騎常侍、户部尚書等高級别檢校官。所以,總的看來,歸義軍與唐政府在乾符年間保持了較爲良性的互動,雙方的關係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在僖宗鑾輿播遷的情況下,張淮深不僅始終奉唐朝正朔,而且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成都奉使。張淮深尊奉中央的舉動,受到了唐政府的贊許,從而得授檢校尚書左僕射。而張淮深應河西都防禦使翁郜之請,爲涼州提供物資援助的舉動,最終促使唐政府同意對其節度使的册封。不過唐政府在歸義軍足以掌握沙、瓜等州的情況下,卻只授予張淮深一州之地,仍有意對其進行限制。在張淮深統治末期,唐政府曾經派遣使者前往沙州,對歸義軍的統治結構進行調整,從而最終引發了大順元年張淮深舉家被殺的政治動亂。如果細緻觀察張淮深時期歸義軍與唐政府的關係,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唐政府對歸義軍所採取的措施對其政治走向所産生的重要影響。
附識: 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以誠摯的謝忱。
(作者單位: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2016年,231— 248頁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唐宋之際河隴地區政治形態演變研究”(項目批准號: 14CZS01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