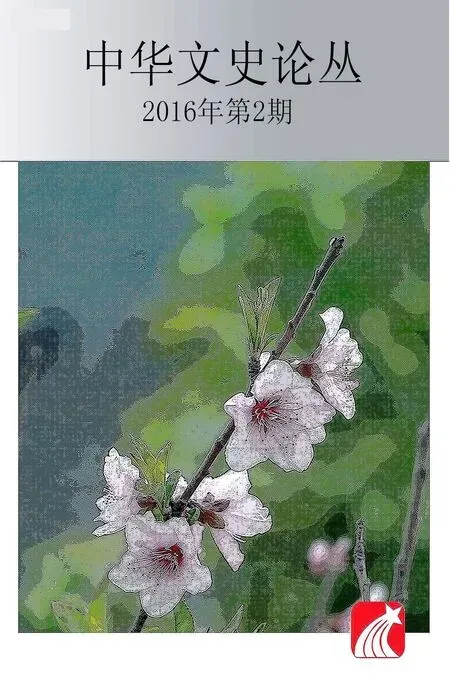郭店簡《魯穆公》篇“恆稱”新證
廖名春 楊 可
郭店簡《魯穆公》篇“恆稱”新證
廖名春 楊 可
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篇“恆稱”說屢見。本文支持“恆”、“亙”讀爲“亟(極)”的意見,認爲“極(亟)稱”實即“極言”,“極言”就是“直言規勸”。“極言”,爲什麽能訓爲“直言”呢?《呂氏春秋·先識》“極言”高誘注說得很清楚:“極,盡。”可見“極言”就是“盡言”,就是規勸諫,毫無保留。《穀梁傳·文公十三年》的“極稱”說亦同。由此看,馬王堆帛書《繫辭》篇的“大恆”讀爲“太極”,也是可以成立的。
關鍵詞:郭店楚簡魯穆公篇 恆稱 極稱 極言 大恆 太極
一九九三年冬出土於湖北省荆門市郭店一號楚墓的郭店簡,有一篇記載早期儒家重要代表、孔子嫡孫子思事迹的佚文,整理者名之曰《魯穆公問子思》。全文共八簡,雖稍有殘損,經整理者和時賢補綴,終成完篇。其文曰: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城孫弋見。公曰:“嚮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亙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城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亙稱其君之惡者,未之有也。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交(效)祿爵者也。亙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爲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①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41。案:除文中重點討論者外,釋文從寬式。
簡文“恆”字一見,“亙”字三見。整理者將後來的三個“亙”字,都讀爲“恆”。《説文解字·二部》:“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恆也。,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②《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頁286上。商承祚《説文中之古文考》:恆,甲骨文、金文“皆从月。既云古文从月,又引《詩》釋之,則原本作亙,从外爲傳譌”。③商承祚《説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14。此字通行體作“恒”。如此,“恆稱”就是“常稱”,就是經常稱說、時時稱說之意。學界早期研究之作都取此說,將“恆”、“亙”讀如本字。
陳偉對此通說卻有不同意見,他說:
先秦古書有“亟(極)稱”、“亟(極)言”的用例。《穀梁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極稱之,志不敏也。”《孟子·離婁下》:“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孫奭疏解“亟稱”爲“數數稱道”。《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孔穎達疏云:“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爲亟也。或當爲亟,亟,數也,數言之。”依此,簡文“亟稱”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屢次稱述”,一是“急切指出”。後一種可能性似更大。“亟”字釋文原讀“恆”。“恆”訓“常”,常常指出君主的過失,語義似不如讀“亟”。又先秦古書似不見“恆稱”用例。①陳偉《郭店楚簡別釋》,《江漢考古》1998年第4期,頁68。
這是說“恆”、“亙”當爲“亟”字之誤,先秦古書只有“亟(極)稱”、“亟(極)言”的用例,而不見“恆稱”用例。陳偉的意見,得到古文字學界的普遍認同。如裘錫圭先生就認爲“其說甚確”,並進而指出:“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數量不能算少的戰國時代的楚簡裏,基本上是借‘亙’爲‘亟’的。已有學者指出,‘亟’和‘亙’不但字形在楚文字中相似,而且上古音也相近,二者的聲母皆屬見系,韻部有職、蒸對轉的關係,所以楚人會以‘亙’爲‘亟’。”②裘錫圭《是“恆先”還是“極先”?》,“2007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臺灣大學中文系等主辦,2007年11月;又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卷《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26—329。這一分析符合事實,很有道理。
“極(亟)稱”的解釋陳偉傾向於“急切指出”說,李銳則取“屢次稱述”說。李說:簡文“亟”之義爲“屢次”,《呂氏春秋·當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數舉吾過”,即相當於本篇之“亟稱其君之惡”。③李銳《郭店楚墓竹簡〈魯穆公問子思〉》,轉引自鄧少平博士學位論文《郭店儒家簡的整理與研究》,清華大學,2013年4月,頁12。如此,“極(亟)稱”之義與“恆稱”就沒有多大區別了。因爲“恆”就是“常”,經常、常常與屢屢、屢次,意思非常接近。
黄人二則認爲:“蓋‘亟稱’指‘直言極諫’。好的君王,錯誤少;不好的君王,錯誤多,但都需要顔色正辭地‘亟稱其惡’,義之所在,諫必往之。好的君王會改正他的錯誤,不好的君王則會討厭‘亟稱其君之惡’的臣子,故下云‘亟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也’。《孝經·諫章》:‘父有爭子,則身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可爲此注腳。”①黃人二《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考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頁298。筆者認爲,較之陳偉的“急切指出”說和李銳的“屢次稱述”說,黄人二的“直言極諫”說更爲準確,但詞義還有未說透、證明還有未到位之處。筆者試爲補證。
“極(亟)稱”實即“極言”。稱,言也。《論語·陽貨》:“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稱人之惡”就是“言人之惡”,所以何晏《集解》引注包咸曰:“好稱説人之惡,所以爲惡。”②《論語注疏》卷一七,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78上。“稱説”就是言說。《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鄭玄注:“稱,猶言也。”③《禮記正義》卷六二,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1919下,1920上。《文選·王巾〈頭陁寺碑文〉》“則稱謂所絶”李善注引鄭玄《禮記注》同。④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6年,頁2528。所以,“極(亟)稱”亦可謂之“極言”。
“極言”就是“直言規勸”,《吕氏春秋·直諫》篇講得非常清楚。其文曰:
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
“言極則怒”,直言規勸則怒。“不聞極言”,不聞直言規勸之言也。
此篇又曰: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
“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即桓公可與言規勸之直言也。
此篇還有:
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①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554,1555。
“極言之功”,直言規勸之功也。《說苑·正諫》也録有此說,“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作“保申敢極言之功也”,②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22。說“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是保申敢於直言規勸的功勞,句式有別,但意思相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此篇名爲《直諫》,通篇說的都是“極言”。“極言”即直諫,明矣。
《呂氏春秋·先識》篇又有:
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③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頁956。
“國之興也”與“國之亡也”相對,“賢人”與“亂人”相對,“極言之士”則與“善諛之士”相對。“善諛之士”是善於逢迎、諂諛之人,於此相對的“極言之士”就是敢於直言規勸之士。
東漢王充《論衡》一書“極言”之說四見。其《問孔》篇有云: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樊遲〕,大材也,孔子告之敕;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敕)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憎)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①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99—400。
其《效力》篇也說:
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②黃暉《論衡校釋》,頁582。
這四處“極言”,注家雖不措意,但也無疑是直言規勸之義。
屬於先秦《尚書》之列的《逸周書·寶典》有“十散”之說,其六曰:“極言不度,其謀乃費。”盧文弨云:“極言不度,言汗漫也。”潘振云:“至言不揆,忠告之謀損矣。”陳逢衡云:“窮極其言而皆不合於法度,所謂言則非先王之法言也,故其謀乃廢。”③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90。黃懷信注譯:“極言,猶甚言。”“極度地言說而沒有節度,他的計謀就會報廢。”④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修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142。案:上述解釋恐怕都有問題。這裏的“極言”,即“直言”。照直而言,率性而言,“不度”,不加考慮,故云“其謀乃費(廢)”。
“極言”,爲什麽能訓爲“直言”呢?《呂氏春秋·先識》“極言之士”,高誘注:“極,盡。”①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頁963。可見“極言”就是“盡言”,就是規勸諫,毫無保留,毫不顧忌,言無不盡。在這一意義上,“極言”就是“直言”,“極稱”也就是“直稱”。
比如《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有載: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②吴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67。
這裏的“直稱之士”也就是“直言之士”,與《呂氏春秋·先識》的“極言之士”意義全同。而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的四處“極稱其君之惡”,“極稱”與《呂氏春秋》的“極言”、《晏子春秋》的“直稱”沒有多少不同,毫無疑義,也應該是直言規勸的意思。
《穀梁傳·文公十三年》有云: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③《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一一,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05上—下。
這裏的“極稱”如何解釋?學界尚有分歧。《漢語大詞典》釋爲“極力稱述”。④《漢語大詞典》(四),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9年,頁1142。而《穀梁傳》范寧注曰:“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⑤《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205上。駢宇騫、郝淑慧點校清人鍾文烝的《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標點同,也將“不復”歸上讀。①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02。其實,這錯得離譜。“依違”是模棱兩可的意思。《穀梁傳》說“極稱之,志不敬也”,怎能說成 “其文”是模棱兩可呢?這不剛好把意思說反了嗎?白本松將范寧注“不復”歸下讀,將《穀梁傳》“極稱之,志不敬也”譯爲“所以《春秋》毫不隱諱地記載此事,就是要記下文公對祖先不恭敬的態度”。②白本松《春秋穀梁傳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86—287。比較起來,白本松顯然是正確的。所謂“不復依違其文”,就是《春秋》經對文公的批評不再含糊。換言之,“極稱”就是“《春秋》毫不隱諱地記載此事”。鍾文烝《補注》曰:“所謂盡而不污也。”③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402。也是此意。《左傳·文公十三年》云:“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杜預注:“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共通恭。④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98。《公羊傳》云:“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⑤《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四,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353上。所謂“書,不共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云云,與《穀梁傳》“譏不脩也”、“極稱之,志不敬也”說同,都是對文公毫不隱諱地批評。這種對文公“志不敬”的“極稱”,絕不是什麽“極力稱述”的意思,明顯是“直言”、“直稱”之義,是照直而言,直接批評的意思。而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的“極稱”,也當作如此解。
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亙”作“亟”的現象,使我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軼事。1992年8月湖南省博物館召開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廖名春提交了一篇名爲《〈帛書繫辭釋文〉校補》的論文,對陳松長發表在《馬王堆漢墓文物》一書中的《帛書〈繫辭〉釋文》作了系統的校勘、補正。①傅舉有、陳松長編著《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頁118—126。認爲帛書《繫辭》篇“大恆”的“恆”字,乃是“極”字的誤寫,“大恆”乃是“大亟”形近之訛。饒宗頤先生不同意廖名春的觀點,在《帛書〈繫辭傳〉“大恒”說》一文中提出了批評:
頃見馬王堆會議論文,廖名春提出《〈帛書繫辭釋文〉校補》,他强調大恒的“恒”字,乃是“極”字的誤寫,他認爲《莊子》已經出現“太極”一詞,《繫辭上傳》必依據之,故大恒乃是大亟形近之訛。他說帛書寫得很隨便,不免有誤筆。按亟字從ク在=中,與恒之作(子彈庫帛書此字三見)、亙(金文)全不一樣。《繫辭上傳》大恒的恒字,和《陰陽五行》的《天一圖》均作亟,是漢初的字體,與篆文的恒非常接近,決非隨意寫錯。②饒宗頤《帛書〈繫辭傳〉“大恒”說》,《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8。
承蒙張光裕教授推薦,廖文後改名爲《〈帛書繫辭釋文〉補正》,發表在1993年刊出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二期上。不過,論大恒的“恒”字乃是“極”字誤寫的一段就删去了。現在看來,廖名春當時會議上論文的觀點未必就錯,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的“恆稱”、“亙稱”當作“極稱”就是證明。
(本文作者廖名春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可係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劉瑾任河北路都轉運使事
仝相卿
《宋史》卷三三三《劉瑾傳》記載,劉瑾被“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此處劉瑾爲河北轉運使誤。
檢1964年江西永新縣出土的劉瑾墓誌,其中記載劉瑾被召還後的仕宦經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除同修起居注,兼判流内銓。除史館修撰,河北都轉運使。”(《江西出土墓誌選編》)認爲劉瑾當時除授爲河北都轉運使。《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四也有劉瑾任命河北都轉運使的記載:熙寧六年(1037)八月九日,“詔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劉瑾爲史館修撰,充河北都轉運使。史館修撰帶出自瑾始”。並特别指出宋代史館修撰外出乃始於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七有劉瑾從“河北路都轉運使”改“河北東路轉運使”的記録:熙寧六年冬十月辛卯,“河南監牧使、司封郎中劉航權河北西路轉運使,河北路都轉運使、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瑾爲河北東路轉運使”。故可判斷,《宋史》本傳中劉瑾“河北轉運使”爲“河北路都轉運使”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