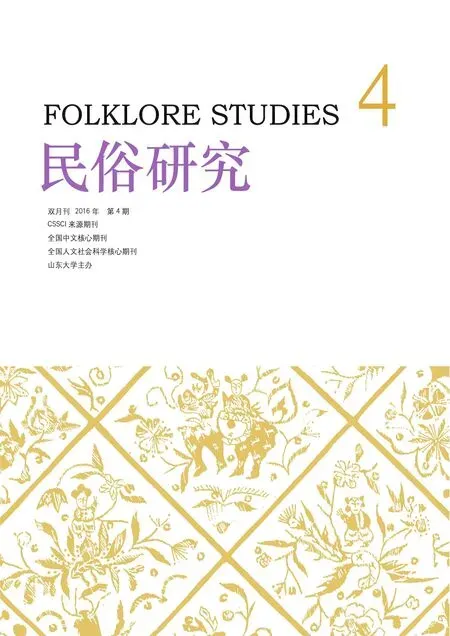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心意与学问
——在乡愁与大都市梦想之“前”的实践民俗学
吕 微
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心意与学问
——在乡愁与大都市梦想之“前”的实践民俗学
吕微
摘要:发源于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的熟人原则,不同于陌生人原则,前者是理论民俗学的认识对象,后者是实践民俗学的思想对象。熟人原则是主体归纳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的经验现象而客观地抽象的实用性、经验性知识(包括肯定性命题和否定性命题);陌生人原则是自由主体先于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的经验现象而主观地所与的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道德理由即道德原则的先验知识(肯定性命题)。熟人原则也可以被用作实践的准先验原则,即经验性理论知识作为准先验知识的非道德性、实用性实践使用,由此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心意”(柳田国男)民俗,即基于经验性知识-准先验原则的实用性心意民俗,以及出于先验知识-先验原则的道德性心意民俗。
关键词:实践民俗学;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
一、陌生人原则和熟人原则:先验与准先验知识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①本文是作者2016年5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座稿。一百年前,《新青年》创刊,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从此揭开了大幕,周作人作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方面或领域)的开创者、先驱者,提出了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乃至整个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陌生人原则。但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学者们一马当先)似乎要普遍地放弃当年的陌生人原则,而回归熟人原则了。②“如果说享受代表神圣,那么对于节俭的关中人来说,一定有更为神圣的东西让他们孜孜以求,从而淡化美食的诱惑力,使其长时间可以忍受低水平的生活,这种神圣之物就是家庭,就是下一代的生活——这才是关中人的宗教,是他们神圣感的源泉。”(陈辉:《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转引自《新京报》2016年3月5日《书评周刊》。)
何谓熟人原则?何谓陌生人原则?似乎并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前者是产生于熟人共同体(community)的为人处世之道,后者是产生于陌生人社会(society)③中文“共同体”和“社会”、“社区”,在英文中可以不很严格地一并使用community来表达,尽管滕尼斯已经区别使用了community与society。“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这是费孝通对community的功能论理解和解释,即,我们只有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直观实体的社区,才能认识实体社区的功能,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5页。的待人接物之理。但也许并不尽然,那么,还是让我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篇的第一段话做进一步阐明: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按照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是否真有这样一种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人们把这样一种知识称之为先验的,并将它们与那些具有后天的来源、即在经验中有其来源的经验性的知识区别开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先验的”,邓晓芒译文原作“先天的”。
以此,我把熟人原则类比为康德说的“从经验开始”即“在经验中有其来源”“从经验中发源”“具有后天来源”的“经验性知识”;而把陌生人原则类比为“独立于经验”“先行于经验”即“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先验知识”。这意思即是说,熟人原则在熟人共同体甚至陌生人社会的经验中有其来源,而陌生人原则却不是从陌生人社会更不是从熟人共同体的经验中发源的。具体地说,熟人原则可以从与熟人交往甚至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过往经验中归纳地抽象出来,而陌生人原则却不是从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过往经验中归纳地抽象出来的。
因为,既然是与陌生人打交道,就不可能有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过往经验。第一次打交道才叫陌生,第二次打交道就不再陌生;唯一一次打交道的人才是陌生人,不是唯一一次打交道的人就不再是陌生人。因此,陌生的意思就是一次性的面对,陌生人的意思就是面对世上独一无二之人,进而陌生人原则也就是面对世上独一无二之人一次性地打交道的先验原则*与笔者的观点不同,赫勒认为:“‘自在的’类本质活动是重复性的活动,单一性的行为不是习惯行为;偶然一次处理的对象不会由此成为富有具体意义的对象;唯一表达过的词不是词。”([匈]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用康德的话说,就是独立于经验、先行于经验,或者说,并不是从经验——无论是熟人共同体的中国经验,还是陌生人社会的西方经验——中发源的先验知识。
打交道次数多了,并不一定就会化生为熟,总结出一套与陌生人打交道的经验性知识。有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名字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讲的就是因多次与陌生人打交道而化生为熟的陌生人原则,以此,虽然说是陌生人原则,实际上已经是通过不止一次地与不同的陌生人打交道的过往经验而归纳地抽象出来的、与肯定性的熟人原则(例如“可以和熟人讲话”)相对应的否定性的熟人原则(即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用康德的话说,凡熟人原则,都是在经验中有其来源的经验性知识。但是,尽管熟人原则是在经验中有其认识来源的经验性知识(认识的结果),一旦被实践地使用,也会被用作肯定性经验或否定性经验的准先验原则(实践的原因)。
很有些出自经验来源的知识,我们也习惯于说我们能够先验地产生它或享有它,因为我们不是直接从经验中、而是从某个普遍规则中引出这些知识来的,但这个规则本身又仍然还是借自经验的。所以我们会说一个在挖自己房子基础的人:他本可以先验地知道房子要倒,即他不必等到这房子真的倒下来的经验。但他毕竟还不能完全先验地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事先总归要通过经验才得知,物体是有重量的,因而若抽掉它们的支撑物它们就会倒下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先验地”,邓晓芒译文原作“先天地”。
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的行为,就在于人的实践是意志自由地决定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有理由的原则性行为。由于人的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实践理由即实践原则,总是意志先于经验性知识的认识结果而“先验地产生”的实践原因,所以意志自由地决定的实践原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先验自由的实践原则。然而,尽管人的实践原因总是一个先验自由的实践原则,但是,作为先验原则的实践原因,意志的自由决定却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或者选择先验知识,或者选择经验性知识,以作为实践的原因。尽管经验性知识不能先验地决定自由意志(否则意志就是不自由的),但自由意志却可以反过来先验地选择经验性知识作为实践的原因(否则意志还是不自由的),这就是作为实践原因的经验性知识的准先验原则,以区别于自由意志先验地选择的作为实践原因的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原则。
这样,由于经验性知识也可以被意志自由地选择为准先验原则,我们也就知道,被用作先验原则的先验原则并非都是先验知识,其中也包括被用作准先验原则的经验性知识。对于本文来说,这类经验性知识包括:发源于熟人共同体的肯定性熟人原则,以及发源于陌生人社会的陌生人原则。后者其实并非真正的陌生人原则,而是否定性的熟人原则。而真正的陌生人原则是说,无论我们面对的是陌生人还是熟人,始终把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地抽象的先验知识用作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实践理由即实践的纯粹先验原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所谓熟人原则是说,无论我们面对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始终把从经验中归纳地抽象的经验性知识用作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实践理由即实践的准先验原则。
以此,所谓先验知识、先验原则与经验性知识、准先验原则之别,就是在与熟人交往或者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主体意志的自由决定的不同根据。即作为准先验原则和纯粹的先验原则,二者之间的相异之处,并非分别地起源于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这是应该悬置的),而是分别地发源于经验性知识或先验知识(这是应该进一步还原的)——准先验原则既产生于熟人共同体也产生于陌生人社会;纯粹先验原则既不是发源于陌生人社会也不是发源于熟人共同体——同样道理,作为先验原则,准先验原则和纯粹的先验原则,也就并非只能分别地应用于熟人共同体和什么人社会——正如周作人说过的:“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亦即,即便面对的是陌生人,我们也可以用否定性的熟人原则化生为熟;即便面对的是熟人,我们也可以用陌生人原则化熟为生。这就是说,陌生人原则是主体从自身(自由主体)中“先验地产生”的先验知识,被用作与其他主体的陌生人打交道的先验原则;而熟人原则则是主体从对象(自然客体)中经验性地产生的经验性知识,被用于与被视为客体的熟人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准先验原则。
被用作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与现实中不同类型的熟人的交往,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与可能是不同类型的陌生人打交道,因为,从经验中发源的经验性知识,其内容是无穷无尽的*“在以意愿的他律为先决条件的情形下该做何事,这是难以把握的,就需要万事通。”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页。——例如“不能信任陌生人”,但也“不能完全信任熟人”,“只能信任熟人中的好人”,“不能信任熟人中的坏人”“只能相信变老的好人”,“不能相信变老的坏人”——而陌生人原则,则无法为我们提供如何与熟人、陌生人以及好人、坏人打交道的无穷无尽的经验性知识。因为,被用作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其实只是一个唯一性的定言命令(因为与陌生人打交道永远是一次性的),即在对陌生人没有任何经验性知识的认识结果之前,如果我们仍然希望、愿意(应该且能够)与陌生人打交道,那么,除了以相信、信任的敬重态度(就像安徒生说的《老头子总不会错》)甚至信仰的爱的情感,视对方为平等人格的自由主体(即便对方不是好人而是坏人)——这就是作为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告诫我们的唯一的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实践理由——此外,更无其他能够被用作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实践理由的先验原则的先验知识;否则,与陌生人打交道就是不可能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准先验的实践原则即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与陌生人打交道;然而,一旦你用了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你就把陌生人熟人化,即用不同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对待唯一的陌生人了;而用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与熟人打交道的各种不同的实践手段——对待陌生人,如果你在把对方视为你的实践手段的同时,还没有忘记应该把对方视为你的实践目的,即让对方作为自由主体的平等人格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爱,从而你与对方就能够互为实践的手段和实践的目的,你的自由意志就会面临在实践目的、实践态度的纯粹先验理由和准先验理由,即发源于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原则和发源于经验性知识的准先验原则之间如何选择、决定的两难问题。
二、实践论的“爱人如己”与认识论的“推己及人”
我们已经讨论了被用作纯粹先验原则的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以及被用作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反过来说就是,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使用的陌生人原则,以及经验性知识的准先验使用的熟人原则。下面,我用“个人”或“己”作例子具体地说明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与先验知识的陌生人原则,在人与人之间交往、打交道时的不同用法。之所以特别用个人或己作例子,是因为,陌生人原则和熟人原则之不同,不在于其逻辑起点(主体先验的自由意志*“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31页。)的不同——二者作为先验原则,都是主体的自由意志、主观态度之有目的、有理由的实践使用——而在于实践地使用的不同形式、不同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即,无论是陌生人原则,还是熟人原则,在逻辑上都起源于先验的个人或己(从作为自由主体的“个人做起”),即都是从主体实践的自由意志出发,先验地建构人-己之间相互交往、交流的方式,但同样的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前者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实践目的的功能性手段,后者在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实践目的的功能性手段的同时,也把他人当作自己的道德性实践目的。*“(己)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31页。在后者的条件下,自己和他人先验地、交互地被用作实践手段(自然主体,其实是自然客体)和实践目的(自由主体)。我们先来看推己及人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地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5页。
费孝通先生在以上引文中说的“我的解释就是……”这句话。费孝通的意思是:差序格局是对被对象化、客体化的自然主体之间的人-己关系的经验性认识结果即经验性知识,正是根据起源于自然主体之间差序格局的人-己关系的经验性认识,我们才可能归纳地抽象出一整套适合于自然主体之间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经验性知识,并将其用作主体的自由意志先验地选择、决定的把其他主体仅仅作为自己的实践目的的实现手段(工具)的先验理由或主观态度的准先验原则即熟人原则。但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其他主体一旦被先验地视为与主体自身一样具有自由意志、有平等人格的自由主体,主体自身就必然可能(并非必然现实)给出(“提倡”)完全不同于经验性知识的熟人原则,即视其他主体为与主体自身互为实践手段和目的的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原则即陌生人原则。
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8页。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这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先验地——吕微注,下同)各是人类的一个(自由主体)。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利己(的互为手段和目的)的生活。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
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人间本位主义。
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自由主体的先验)资格,占得人的(自由主体的先验)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为先验的自由主体),怎能“如己”(自由主体)的爱别人呢?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第271-272页,第274页。
这样,我们就认识到准先验原则(经验性知识实践地使用的自由意志)的另外一层含义——准先验原则的实践使用,会让自由主体重新沦落为不自由的自然主体——即,如果主体仅仅视其他主体为实现自身实践目的的手段,则主体自身也就不会成为自由主体,因为如果其他主体被主体视为实现自身实践目的的手段、工具即对象、客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失之于自然主体之间根据经验性知识的交往或交流,以此,主体自身也就不再出于自由意志,在主体自身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非先验条件下,主体自身又如何能够用纯粹的先验原则对待其他主体呢?以此,实践的准先验原则,最终就仍然只能是一项经验性的实践原则。反过来说,惟有在也视其他主体为自由主体的自由条件下,主体自身才能够成为自由主体,作为自由主体的主体自身也才能够用纯粹先验原则的陌生人原则对待其他主体,即“先使自己有人的(自由主体的先验)资格,占得人的(自由主体的先验)位置”,主体才能够先验地“‘如己’(自由主体)的爱别人”,即用纯粹的先验原则对待与自身一样拥有自由意志、具有平等人格的陌生人。
人生的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它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自由主体的先验)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先验)感情,代表人类的(自由)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自由)意志便是他的神。*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3、286页。
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人生的文学”的上述说法,显然不是从种族、民族、国家、家族、家庭的自然主体之间的人-己关系的客观事实出发,经验地归纳、分析地抽象出来的经验性知识的熟人原则,而是在经验地认识自然主体之间的人-己关系的客观事实之前,就根据自由主体之间人-己关系的“个人自由的人间本位主义”的“理想”“信仰”的主观“实事”出发,“先(验地)使自己有人的(自由主体的先验)资格,占得人的(自由主体的先验)位置”,“从(自由主体的)个人做起”,推己及人——以自由主体的先验资格视其他主体同为有先验资格的自由主体——地“爱人类”,即“先知自爱(为先验的自由主体)”,“如己(自由主体)”地“爱别人”为自由主体的先验知识的陌生人原则。
周作人把文学划分为“贵族文学”、“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的做法,是凡学过大学中文课程的本科生都熟悉的。这里强调的是,与费孝通对被视为自然主体的人-己关系的客观事实的经验性认识、经验性知识不同,周作人所谓的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并非只是在时间中“最初与经济状况有关”的客观性事实,而首先是在逻辑上“假定”的“对于人生的两样(主观性)态度”的纯粹先验认识、先验知识。
在文艺上可以假定有贵族的与平民的这两种精神,但只是对于人生的两样态度,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虽然它的分布最初与经济状况有关,——这便是两个名称的来源。……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了。
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8、289页。
这就是说,同样的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的逻辑起点,即自由意志的实践主体(个人或己),如何看待、对待其实践的对象(其他主体及其实践),或者视其为经验性认识的客体化对象,或者视之为先验地信仰的主体性理想,对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开创者、先驱者的周作人以及鲁迅来说,具有完全不同于费孝通社会学经验论认识论意义的民俗学先验论实践论的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而且,周氏兄弟不仅在实践目的和态度上主张理想主义的先验论陌生人原则,同时也在行动的理由中身体力行了他们信仰的理想。
三、《一件小事》:实践目的论的精神现象学转变
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你怎么啦?”“我摔坏了。”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先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鲁迅:《一件小事》,《晨报》,1920年7月。
这是将近100年前发生在北平的“一件小事”,当事人之一是后来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的鲁迅。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鲁迅是如何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件小事的。换句话说,面对“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百年问题,当年的鲁迅究竟给出了怎样的回答。面对一位跌倒在地的老人,扶?还是不扶?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至今没有降低其直逼人的灵魂的拷问烈度。但是对于当年的鲁迅来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是一个熟人共同体或者陌生人社会(社区)的客观性经验事实问题?还是一个熟人原则或者陌生人原则的主观性先验态度——主观性或主观间客观性的准先验态度或先验态度——问题?其间的区别不可不论。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件小事发生在熟人共同体,那么,连带着发生上述哈姆雷特式问题的概率较低,即,或者根据先验知识(用作实践的先验原则):即便跌倒在地的老女人不是鲁迅的母亲鲁瑞或者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鲁迅也一定会不让车夫抢先下车,把老女人搀扶起来,因为这是道德原则先验地要求的。或者根据经验性知识(用作实践的准先验原则),鲁迅就是拒不下车,因为根据对老女人平日品性的清楚了解*“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5页。,鲁迅“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从而断定这老女人来这一手,就是想碰瓷。但是无论怎样“或者”,鲁迅都不会犹豫不决,相反会“毫不踌躇”地给出问题的答案。
在熟人共同体中,道德约束力,不仅出自人的内心的良知,也来自人心之外——惯习、宗法、舆情,以及长老——的权威,在狭小的自然活动空间中,后者的力量有时更甚。以此,无论“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也好,“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口气”也好,见到老人跌倒而不上前搀扶,自然会被人耻笑甚至遭人斥骂而无地自容,毕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熟人共同体一贯奉行的行为准则。但也正是因为,在面对面的熟人共同体中*“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里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在熟人中生活的,是个乡土社会。”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10页。,平日里谁好谁坏谁心地善良谁生性狡诈,“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无不心知肚明,因而像“装腔作势”地碰瓷这样“真可憎恶”的事情,倒也很少发生,即便是发生了,根据熟人共同体的经验性知识而被实践地用作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无论是谁都能够立即做出判断——好人肯定不会碰瓷,碰瓷的肯定是坏人——则碰瓷的目的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结果。
在传统熟人共同体中难得发生的哈姆雷特式的两难问题——先验原则命令应该扶老人,经验性知识认识到不能扶坏人——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因自然空间的拓展,却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尽管先验原则是普遍地适用于无论熟人共同体还是陌生人社会,但是在无限扩大的自然空间中,经验性知识的普遍化适用性大大降低。但是,无论熟人共同体,还是陌生人社会,毕竟都只是哈姆雷特式问题之所以发生的自然条件,就自然条件而言,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其实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自然空间(无论是熟人共同体还是陌生人社会)中,随着经验的积累,陌生人可以变成熟人;而随着经验的匮乏,再熟的人也会重新变回陌生人。以此,传统的熟人共同体只是一定程度地遮蔽了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而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也只是更大程度地突显了哈姆雷特的问题,二者作为经验性的自然(语境)条件,都不是哈姆雷特式问题的先验自由(超语境)的必然条件。而在悬置了哈姆雷特式问题的经验性自然(语境)的或然条件——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之后,经验性知识与先验知识被一并用作实践的先验原则——纯粹先验原则和准先验原则——的主体实践的自由意志,就是哈姆雷特式问题之所以发生的先验自由(超语境)的必然条件。
这就是说,鲁迅当年遭遇的“扶不扶”的哈姆雷特式两难问题,并非一定只能发生于陌生人社会,而必定不会发生于熟人共同体,但却必然是发生于主体自由意志的不同实践目的、实践理由——熟人原则和陌生人原则,即准先验原则和纯粹的先验原则——之间的主观间意向性态度冲突。正因为当年的鲁迅对待老女人和车夫的先后不同的态度转变——根据鲁迅的自述,他是先“憎恶”而后“诧异”“仰视”“惭愧”,最终因“自新”而“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我才认为,并非熟人共同体的旧社会嬗变为陌生人社会的新社会的经验性事件,而就是两种态度的主观间意向性之争的先验事件。对此先验事件,我的问题是:鲁迅态度的脑筋急转弯式的前后大转变,在现象学地悬置了其共同体-社会的客观性自然条件之后,究竟是如何主观地、自由地发生的?
承认《一件小事》讲述的是一桩发生在陌生人社会(但并非不可能发生在熟人共同体)的先验事件,却并不是否认陌生人社会也是此先验事件的经验性自然(语境)条件。没有了熟人共同体的经验性知识的比较普遍性的过往保证,一旦进入陌生人社会,以经验性知识的比较普遍性为或然性条件的人与人之间对对方实践目的、理由的真实性与真诚性的信任感、信赖度,就会大打折扣。鲁迅就是这样,在不了解老女人之为人即经验性知识匮乏的条件下,鲁迅对老女人没有起码的信任感和信赖度。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鲁迅并没有视老女人为应该相信、信任的陌生人(自由主体),而是视老女人为可以认识但尚未认识的熟人(自然主体或客体),面对自然主体(客体),在并不了解对方品性的知识匮乏的认识条件下,鲁迅不相信、不信任老女人,似乎是正常的;进而鲁迅根据经验性知识而将熟人原则用作实践的准先验原则,而不相信、不信任老女人实践目的、实践理由的真实性与真诚性,似乎也就是正当的。
如果说,鲁迅是在陌生人社会中,将经验性知识用作实践的准先验原则即熟人原则,来处理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车夫又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处理是与老女人之间的关系呢?显然,与鲁迅一样,车夫可能同样“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因为“车夫早有点停步”,且“眼见”老女人“慢慢倒地”,因此,老女人“怎么会摔坏”呢?但是,车夫仍然问老女人道:“你怎么啦?”且相信伊“摔坏了”,尽管老女人之“摔坏了”,多半是因为“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的缘故,而与车夫本人并无直接的干系,因而车夫的“多事”反而可能“自己惹出是非”“自讨苦吃”呢!
但是,“车夫听了这老女人(自述‘摔坏了’)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先前走”。以此,我们可以断定,车夫的行事原则,并非熟人原则,因为,根据实践的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我们不能排除老女人碰瓷的可能性,而且,即便老女人不是为了碰瓷,车夫这样做的结果,也会为自己找来麻烦。但是,如果车夫的行事,根据的不是熟人原则,那么就只可能是根据的陌生人原则了。因为只有根据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我们才能够有效地阐明,在并不了解(认识)对方为人、品性的经验性知识或然地匮乏的自然(语境)条件下,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进行下去——在《一件小事》中就是“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的后续事件——之必然可能的(超语境)自由条件。
根据实践目的的纯粹先验原则的陌生人原则,如果我们希望与在陌生人真诚地交往、诚实地打交道,在经验性知识完全匮乏的认识条件下,我们就只能用自己的爱心,信任对方、相信对方,甚至敬重地信仰对方是一个诚实、真诚的好人,只有这样,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交流才是必然地可能且可能是现实的。陌生人原则先验地要求于主体自由意志的就是,与陌生人的任何一次交往,始终都是第一次交往,都是一次性交往;即交流的对象,始终是唯一性的交流对象。陌生人原则,并不要求在对交往、交流对象有经验性知识的认识条件,才实践地应用陌生人原则,而是先于任何经验性知识并将其用作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之前,就应用先验知识的陌生人原则。
为车夫应用先验知识的陌生人原则对待老女人的做法所震撼,鲁迅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就是说,鲁迅旋即放弃了熟人原则,而选择了陌生人原则,即用车夫对待老女人的陌生人原则,转而对待车夫本人。这样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实际上,正如鲁迅并不了解老女人一样,鲁迅同样不了解车夫,对于鲁迅来说,车夫与老女人一样,同为在陌生人社会的自然空间中相遇的、从经验性知识看来的陌生人即可能的熟人。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老女人和车夫是否是鲁迅的经验性知识中的陌生人即可能的熟人,而在于鲁迅以怎样的先验原则的主观态度对待他们。显然最初,鲁迅是以被用作准先验原则的经验性知识的熟人原则无端揣测他们的实践目的和实践理由,于是,鲁迅才会根据经验性知识而推测,老女人是“装腔作势”。但是,对于车夫为什么用陌生人原则对待老女人,鲁迅无法理解。鲁迅尝试用熟人原则解释车夫对待老女人的主观态度的“多事”“惹出是非”“自讨苦吃”,但是就在一刹那间,鲁迅的思想突然短路了,或者说被一种因无法理解、无法解释而产生的巨大思想冲击波所阻断:“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但是,车夫为什么要帮助老女人?这仍然是思想短路的鲁迅无法想却又不能不想的问题。
车夫为什么帮助老女人,是因为车夫与老女人是熟人吗?不是,车夫并不认识老女人。是车夫牵扯老女人跌倒在地吗?也不是,在老女人“从马路边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筋斗,跌到头破血出了”,是老女人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自己跌倒在地的。是有人看见了上面的一幕,车夫害怕自己被别人误解为不负责任吗?更不是,当时并“没有别人看见”,车夫无需担心别人对自己可能的指责。那么,“便很奇怪车夫多事”,为什么偏“要自己惹出是非”“自讨苦吃”呢?
答案只有一个:车夫不是用熟人原则对待老女人,而是用陌生人原则对待老女人,车夫相信老女人说的都是真话,老女人的确“摔坏了”,因此她需要别人的帮助。于是为车夫应用陌生人原则的为人处世之道、待人接物之理——陌生人原则就是对他人的相信、信任甚至信仰的爱——对待老女人的主观态度(客观性主观性态度),与自己对待老女人的主观态度(纯粹主观性态度)之间的巨大反差,鲁迅深感震撼:在自认为能够用熟人原则解释的突发事件面前,车夫竟然使用了与自己完全不同的陌生人原则。
但是,鲁迅还有最后一次使用熟人原则的机会,也许能够解释车夫的行事态度所依据的理由或原则,那就是:或许车夫就是为了博取善良人、同情心的好名声。但这样的解释,尽管作为熟人原则,并非不可以解释得圆满,但却会把鲁迅自己置于绝望的伦理境地,难道自己在道德上的无义无情,竟然已堕落到如此地步(纯粹的功利化即彻底的非道德性)?!正是这种在道德上的自身反省,让鲁迅感到害怕:“我走着,一面想,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但也正是因为鲁迅“本真”的道德良知(先验知识)——对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间相互联结时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的必然性关系的直接领悟(“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让鲁迅对车夫的道德榜样(陌生人原则)之起源于理性而不是起源于感性的情感震惊。*“迄今为止,这些创作中影响最大、引用最多的是鲁迅的《一件小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对人力车夫的态度很是温和,并认为其形象需要仰视才见,以至于‘要榨出皮袍下的「小」来’。尽管在鲁迅笔下,人力车夫面前的文人道德上是如此‘微不足道’,但人力车夫的背影也带上了一缕阴郁、决绝甚或畸形的道德阴影。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力车夫实像相较,在五四‘劳工神圣’的光环下,这个需仰视才见的高大背影不过是一瞬间浪漫主义的臆想。无论同情心和良心的拷问是如何本真,当文人‘消费’劳工时,感性始终高于理性,笼罩在字里行间的是坐和拉双方都无力自拔、无可奈何而苍白、惨淡的光晕与晕眩。”见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声音——民俗、曲艺与心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8-99页。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
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鲁迅:《一件小事》,《晨报》,1920年7月。
以上就是将近一百年前,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国文系讲师身上的“一件小事”,但这却也是发生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现象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鲁迅实现了、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格式塔式的精神转变,即现象学地悬置了用理论理性的熟人原则对待经验性知识条件下的陌生人甚至熟人的做法,转而决意用实践理性的相信、信任甚至信仰的敬重与爱的纯粹先验原则的陌生人原则,对待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尽管如上所述,用经验性知识的熟人原则解释老女人和车夫的行为动机(实践目的、实践理由),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甚至还可能是较之陌生人原则更彻底的解释方案;但是若此,理论上的推己及人就会把实践上的爱人如己,推入黑暗的道德深渊。以此,如若一个人不想让自己因理论上的成功,而沦落为在实践上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是无道德)的人(理论理性“将它的疆界扩展到”实践理性之上);那么,面对道德的榜样,他就必须放弃熟人原则而转用陌生人原则并接受道德榜样的纯粹动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悬置熟人原则的推己及人的经验性知识,给先验知识的爱人如己的陌生人原则留有余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以此,我们才能够宣称:面对跌倒在地的老人,(假如不能,则)不扶,作为经验性知识的熟人原则,尽管可以是有条件的假言命令;但是,作为先验知识的陌生人原则,(只要应该,就去)扶,一定是无条件的定言律令,进而将实践上爱人如己的先验知识,采纳为民俗学的实践目的论与实践方法论的纯粹先验原则,即陌生人原则。
通过对一百年前发生的这桩精神事件的现象学描述,我们认识到,与被用作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不同,被用作纯粹先验原则的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的实践有效性,并不是仅仅通过主体对客体、对象(经验性事实、现象)反复、重复的单向度理论认识,能够成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对尽管是一次性、唯一性的主体实践的主观间客观性意向性的多层次现象学先验还原,才能够直观(现象学意义上的观念直观)地描述出来。即,《一件小事》的先验现象学实践意义,首先依赖于车夫对老女人的相信与信任,其次依赖于鲁迅对车夫的尊重甚至信仰,最终依赖于百年之后的今天,作为民俗学后来人的我们,对鲁迅的敬仰与敬爱……正是基于此实践认识的主观性交互性意向性的先验还原而实践地建构的现象学剩余物——主体间平等人格的自由意志——陌生人原则才可能被有效地用作实践民俗学的先验目的论与现象学方法论*“‘反思之旅’并不只是找到了一种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合法理由,与此同时,他也建构了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换言之,正是在转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民俗学家也转变了个人的身份认同。”(王杰文:《“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否则,就真的是一场无端的“臆想”了。*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声音——民俗、曲艺与心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8-99页。
四、作为先验原则和方法的家乡共同体与都市社会
按照时下的说法,也许我们可以说,无论贵族文学还是平民文学,无论老女人“我摔坏了”的“装腔作势”还是车夫“毫不踌躇”的“多事”,都是文学performance(表演),都具有民俗主义的performantive(表演性),所以,我才视鲁迅《一件小事》为民俗学表演研究的经典论著。在这件小事中,鲁迅先是依据“入世”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视老女人的“装腔作势”和车夫“多事”为平民文学的表演;在经历了一番格式塔式的精神现象学转变之后,鲁迅觉悟到,车夫所根据的“超人化”“出世”的陌生人原则的贵族文学先验知识的表演性,进而,鲁迅也就用与车夫同样的表演性——“仰视”的敬重与信仰的爱——回报于车夫。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康德问题:经验性知识在(感性)时间中与先验知识在(理性)逻辑上的起源。康德认为,前者在时间中“从经验开始”,而后者不是“从经验中发源”而是在逻辑上起源于人的纯粹理性的自由意志和道德情感。周作人基本上同意康德的说法而略有差异。
在文艺上可以假定有贵族的与平民的这两种(先验和准先验)精神,但只是对于人生的两样(主观)态度,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虽然它的分布最初与经济状况有关。*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
是周作人认为,无论熟人原则,还是陌生人原则,最初都有客观内容的“实质性”(索绪尔)如“经济状况”的起源,但最终却只是“人类共通的,并不专属于某一阶级”的“两种精神”、“两样态度”的纯粹主观形式。我本人更认同康德,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的,尽管熟人原则是“从经验开始”的,但陌生人原则一定不是“从经验中发源”的(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只是熟人原则发生的自然条件,甚至不是陌生人原则的发生条件)。只是在悬置了熟人原则(包括发源于经验性知识的陌生人原则)的实质性起源之后,我才同意周作人的“两种精神”“两样态度”说——或者视对象为自然主体(客体),或者视对象为自由主体——的纯粹主观性、先验性(包括准先验性)起源。是英雄无论出处,有自然(经验性)出处也好,没有自然(经验性)出处也好,都可以被用作表演实践的“心意”(柳田国男)与表演研究的学问的主观态度的先验原则;但是要区分开,同样的主观态度、先验原则,有纯粹的先验性与准先验性之分(见前引康德“房屋倒塌论”),前者是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原则的主观间客观性实践精神,而后者只是经验性知识的准先验原则的主观性实践条文。*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04页。
但是,如果我们执意为发源于经验性知识的准先验实践原则,设定一个自然空间的实质性起源,那么,不仅是熟人共同体(家乡),陌生人社会(都市)同样可以是熟人原则的起源之地。即,如果视熟人共同体、陌生人社会为理论认识的经验性对象,那么,二者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惟当我们视熟人共同体与陌生人社会,为不同的主观态度的先验原则(“两者所用的原则不同”*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54页,第50页。)的实践目的论建构对象,二者之间才显现出真正的本质差别。
以此,时下关于家乡民俗学与都市民俗学的划分,只有在先验自由的实践目的的建构意义上,将家乡、都市作为不同于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的纯粹先验原则的陌生人原则的实践方法,上述划分才有实践的理论价值;如果仍然视家乡和都市为自然空间的经验对象,而扩大了理论认识的经验性研究的领域、范围,那么,结果将是适得其反地遮蔽了实践民俗学的自由目的论和先验方法论,即用经验性的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自然空间)遮蔽了纯粹先验的陌生人原则(自由主体)。
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自然空间)之所以会遮蔽陌生人原则(自由主体),是因为,当我们用理论认识的方法认识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的时候,一方面固然可以经验性地描述熟人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可以深信(可以和熟人讲话)的经验性熟人原则,另一方面也经验性地描述了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之不可轻信的经验性陌生人原则,但这里的熟人原则和陌生人原则(后者并非真正的陌生人原则),看似不同,其实都是起源于同样的经验性知识而被用作准先验原则。于是,在此实践的准先验原则的经验性知识的理论视野中,都市只是被期待为熟人共同体的陌生人社会,而家乡则是被期待于陌生人社会的熟人共同体。但是,随着经验性人际关系的流失,家乡可以“进化”为陌生人社会的都市;更随着经验性人际关系的积累,都市也可以重新“退化”为熟人共同体的家乡。
如果说,熟人原则——可以和熟人讲话,或者“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时间中、“从经验中发源”于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那么,真正的陌生人原则(如车夫“毫不踌躇”的“多事”),作为非经验性即无功利性的纯粹道德性的纯粹先验的实践原则,则既不可能发源于熟人共同体,也不可能发源于陌生人社会,而只能先于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而产生,即发源于自由主体(个人、己)之间的平等人格的自由意志的先验知识。发源于经验性知识的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和陌生人原则,与发源于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原则的陌生人原则之间的方法论区别是:尽管同样是推己及人,前者是有等差(“差序格局”)的“泛爱众”(孔子),后者是无等差(“团体格局”*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30页。)的“兼爱”(墨子)或“博爱”即“爱人如己”(耶稣)。*“耶稣称神的父亲,是个和每一个人共同的父亲,他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否认生育他的父母。为了要贯彻这‘平等’,基督教的神话中,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亲子间个别的和私人的联系在这里被否定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象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30页,第33页。正是因为,真正的陌生人原则是先于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而发源的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原则,所以即便是在熟人共同体中,我们一样可以见及真正的陌生人原则的道德实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儿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真正的陌生人原则,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行为目的之出于法则的精神,而不是仅仅行为结果合于法则的准则的条文,例如在传统的熟人共同体中,从来都已经实践的各种陌生人原则的“金规则”*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0-221页;[美]罗斯特:《黄金法则》,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174页。和行为规范。
那么,讲到现在,实践民俗学所践行的究竟应该是什么原则呢?是经验性知识的准先验原则的熟人原则和陌生人原则?还是先验知识的纯粹先验原则的真正的陌生人原则?已经一目了然、无需多言,因为我们的学科开创者、先驱者周氏兄弟实际上已经提出并且给出了答案,只是被作为学科后来人、继承者的我们经常遗忘或者混淆。有时候我们以为,当我们把研究对象从乡村、家乡转向了城市、都市,或者相反,我们就算是回答了周氏兄弟的问题——用陌生人原则代替了熟人原则,或者用熟人原则代替了陌生人原则——其实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幻觉。我们曾经把熟人共同体的模式化行为称之为“民俗”(邓迪斯),现在我们又把陌生人社会的时尚化行为称之为民俗主义“新民俗”;但是,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转向还只是认识对象在不同程度上的转换,而非认识原则在性质上的转变。即,即便我们从陌生人社会(城市、都市)中发现了“不要和陌生人话”的陌生人原则,以及我们在熟人共同体(乡村、家乡)中发现了可以和熟人讲话的熟人原则,那么这里的陌生人原则和熟人原则也仍然是在经验性知识内部不断地打转。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陌生人原则呢?让我在这里援引胡塞尔的一个说法,叫作“共同的陌生性”。
个体意识,即每个感性的自我与其他的感性自我之间具有陌生性,因为每个个体意识的内容都不同,此外每个个体意识本身还包含着某种陌生之物——无内容的先验意识和先验自我[的纯粹形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两种陌生性之间的奇特关系:每个具体时间意识的人,无论他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把这个陌生的过去称为他自己的。这个人的意识和那个人的意识的区别在于不同的内容。而内容的不同性则取决于,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进入另一个人正在占据的位置。个体之间的距离(或是时间距离,或是空间距离)越远,个体之间就愈陌生。每个人都有他自为的体验,每个人都仅仅在他的意识中具有他的感觉,这些感觉对于其它任何一个人来说原则上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由于体验内容的不同,任何个体的感性自我都无法被其他感性自我所理解,它们之间相互陌生。但我们发现,个体意识之间是沟通的,它们并不完全陌生,否则社会就不会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有个体意识来说都感到陌生的东西,即它们的过去,却是它们所共同具有的[对象化的过去]。正是这种共同的东西构成了一条个体意识通向其他个体意识的桥梁。“就此看来,我们是通过我们共同具有的陌生性来克服我们各自具有的陌生性。”这种共同具有的陌生性便是[被“忘却”的“共同的自身”即纯粹形式的]先验的[自我]意识。这样,所有的个体感性自我都在完全的相同和完全的相异(陌生)之间摆动:它们各自内容的完全不同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永远有陌生感,保证了它们永远不会变成同一个意识;它们共同具有的先验自我和共同的过去则保证了它们之间的交往、理解,使它们永远不可能感到彼此之间完全的陌生。*倪梁康:《胡塞尔:通向先验本质现象学之路——论现象学的方法》,《文化:中国与世界》第2辑,三联书店,1987年,第307-308页;参见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
之所以特意援引胡塞尔“共同的陌生性”的说法,是为了进一步有效地区分经验性的熟人原则与陌生人原则,与先验的陌生人原则共同使用的推己及人的民俗学方法,只有清楚地区分了两种在民俗学方法上不同的推己及人,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何谓经验性的熟人原则和陌生人原则,以及纯粹先验的陌生人原则。胡塞尔区分了两种陌生性,一种是每个人过去的人生内容对于这个人现在的人格形式来说的陌生性;一种是每个人的人格形式对于其他人的人格形式来说的陌生性。胡塞尔说的这两种陌生性,对于我们区分准先验的陌生人原则和纯粹先验的陌生人原则来说,不无裨益。
胡塞尔发现,每个人过去的人生内容对于这个人现在的人格形式来说,尽管具有陌生性,但每个人过去的人生内容作为“共同的过去”,对于每个人来说又具有共同性*“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12页。,“正是这种共同的东西构成了一条个体意识通向其他个体意识的桥梁”。从民俗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种每个人共同地拥有的人生内容的“共同的过去”的“共同的陌生性”,理解为熟人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的模式化行为,即传统的民俗,一旦从中归纳地抽象出熟人原则(包括肯定性的熟人原则和否定性的熟人原则),每个人就都能够推己及人,“把这个陌生的过去称为他自己的”,一个熟人共同体就能够实践地被建构出来,甚至在理论上,一个陌生人社会也能够实践地被建构成为熟人共同体。但这里要注意,因为过去的人生内容,尽管具有共同性,却是有等差的共同性,因而据此“共同的陌生性”经验性知识,推己及人而实践地建构的熟人共同体甚至陌生人社会必然是一个差序格局的共同体-社会。
还有一种“共同的陌生性”,即人格形式的陌生性,每个人的人格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陌生性,因为这种共同的陌生性,根本就没有内容,是纯粹精神的人格形式,康德、胡塞尔等哲学家称之为“先验自我”“先验意识”。根据这种因没有具体内容而相互陌生的纯粹精神的人格形式而设定的陌生人原则,才可能是真正的陌生人原则。显然,这种陌生人原则既不可能产生于熟人共同体,也不可能产生于陌生人社会每个人过去的人生内容的“共同的陌生性”,而只能产生于每个人对没有任何人生内容的人格形式的交互的、普遍的信仰和敬重的爱人(格)如己(的人格形式)的纯粹之爱。
在现实(自然空间)的熟人共同体与陌生人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力包括交往能力、交流能力存在着自然的差异,而熟人共同体与陌生人社会作为功能论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对人的生活能力则是一种限制(或反限制)的自然条件。以此,即便你的社交能力是弱项但你的家庭实力比较雄厚,也许你更愿意留守家乡,因为在熟人共同体中,你拼爹的效果或更显著。然而对于一个家庭实力比较薄弱但业务能力是强项的人来说,也许他可能更愿意北漂。因为,尽管北上广等大城市、大都市并非已经就是真正的陌生人原则的实践目的论建构结果;但是毕竟,就自然空间的疏离感而言,大城市、大都市更接近于根据先验知识的陌生人原则人为创建的法理社会,而远离了从经验性知识的熟人原则中自然生长的人情共同体,从而每个人的——并非发源于陌生人社会,也不是发源于熟人共同体的——人格形式的先验的“共同的陌生性”(自由权利)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进而人生内容的经验性的“各自具有的陌生性”(自然能力)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承认和利用。但是,一旦我们如此定义大城市、大都市,北上广在我们的期待视野中,就已经不是依据熟人原则,而是依据真正的陌生人原则的陌生人社会了。所以为了定义的准确和周延起见,我们与其根据理论民俗学的经验论对象论,把民俗学区分为家乡民俗学和都市民俗学,不如用出于经验性知识的熟人原则与先验知识的陌生人原则的实践民俗学的先验论目的论和现象学方法论,来定义家乡民俗学与都市民俗学。但是这样一来,无论家乡民俗学还是都市民俗学,也就不再是理论民俗学的对象,而是实践民俗学的目的(态度)、原则(理由)和方法(理论)了;然而,我们看到,只有立足于实践民俗学的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我们才能够理解和解释,无论已经多年闯荡都市的打工者,还是仍然长期留守家乡的空巢人,对真正的陌生人原则的渴望。
王家坪与历山之间隔着一座高大的青龙山,两地村民平常日子以及信仰仪式活动期间都很少来往,杨三增是一个特例。我们在王家坪采访,问他为什么不辞辛苦翻山越岭跑去历山神立庙参加活动,他的回答是:“我到神立去比咱这里还吃开哩!”因为“村里人,咱无能,老百姓(因爱有等差——笔者补注),那看不起,瞧不起,到外边去不是这样子,过去这条山,那都是热情招待,就是凭的(信仰娥皇、女英两位)老人家这关系。”可见,凭着传说所建立的神灵关系,一个在本村毫无地位的村民,可以在别处找到(附加)身份上的情感安慰。*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希望得到对自我人格形式的尊重,是生活在熟人共同体中的人们也时时渴望的,而这也才是出于真正的陌生人原则的大都市、大城市梦想即中国梦。那么反过来说,家乡梦、乡愁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对自然空间的熟人共同体的熟人原则的回顾与想望吗?如果把家乡梦、乡愁仅仅视为对城镇化、都市化过程中对传统乡土的亲情、友情的恋恋不舍,那我们就仍然是自囿于自然空间中过去的人生内容的“共同的陌生性”的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
在城市社区和农村村社,许多组织实体以传统民间组织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与其把它们看作是传统民间组织,不如看作现代民族国家的社团。我们审视一下这些团体的组织要素和背景就会很清楚。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当下社会中人,它们都处在并且都知道自己处在国家的行政、法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之中。这些社团要在公共空间中活动,必须经得住公权力和公众的检验和监督。这些都决定了它们虽然以传统形式出现,但必然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组织。*高丙中、马强:《传统草根社团迈向公民社会的历程:河北一个庙会组织的例子》,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收入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今天,也许,我们已经不能再把家乡、乡愁简单地等同于经验性知识的自然空间的语境(生活世界)条件下,熟人共同体及其模式化行为的过去人生内容的“共同的陌生性”,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站在真正的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即实践主体当下人格形式的“共同的陌生性”的自由观念的“语镜”(生活视界)条件下,重新对待家乡、看待乡愁。例如,一年一度,在中国大地上上演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亿万人返乡潮中,人们所期待的,已经不再是在大都市、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得不到的等差性亲情与友情,而已经是建立在陌生人原则——对每个人先验的人格形式的尊重甚至信仰——的自由观念的“语镜”条件下的乡情了。当人们以平等的人格而独立地返乡的时候,他们不再是一度奔赴延安之后,再次回到熟人共同体大家庭的觉新、觉民,而重新体验的“三纲”、“三从”等熟人原则下的淡漠爱情,而是真正陌生人原则下自由主体的人格权利与意志形式的先验交互性的更加纯净的亲情、友情和乡情。
我所认识的老一辈人,他们都很难真正做到彻底的“革命”。据我所知,无论是周扬、夏衍还是荒煤、沙汀,当他们回忆起自己的封建家庭、自己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无一不在批判的同时又充满了眷恋和深情。我的母亲很早离家奔向延安,但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那个封建大家庭,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而我听阿姨讲述李锐老头儿在年轻时怎么一边斗地主一面又偷偷地想法保护自己地主母亲的故事那更是令人寻味……他们在挥舞着革命武器的同时内心真正的祈望是什么呢,真正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严平致吕微的信,2015年12月24日。陈辉认为“真正的祈望、真正的信仰”即“神圣之物就是家庭,就是下一代的生活——这才是关中人的宗教,是他们神圣感的源泉”;因此,也许,把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陈辉《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与陈忠实《白鹿原》、柳青《创业史》对照着读,将“更是令人寻味”。
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乡情、家愁只是温情脉脉、无可奈何的明日黄花,就是看不到百年中国的普遍性进程中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这一冥冥之手对乡愁故园情的纯净化淘洗——忽略了这一点,也会让我们远离了应该承担的建构真正的陌生人社会的道德责任与情感义务——如果说,我们今天仍然要像鲁迅当年那样,为“扶不扶”的问题而争论,这一方面说明,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爱人如己的陌生人原则的文学理想,至今没有完全实现为现实生活的陌生人社会*“在中国民俗学者这里,情况恰恰相反,民众自由地表演的权利还没有被确立……”见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74页。;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熟人原则的熟人共同体进步为陌生人原则的陌生人社会的逻辑与历史进程中,用陌生人原则而不是用熟人原则回答“扶不扶”,即参与建构陌生人原则的陌生人社会的问题,已经对民俗学者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实践要求。于是,我在这里就可以借用岩本通弥关于“不是以民俗为对象,而是通过民俗进行研究”*[日]岩本通弥:《以“民俗”为对象即为民俗学吗——为何民俗学疏离了“近代”》,宫岛琴美译,收入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0-47页。的命题,进一步阐明我在本文中的想法:不是视民俗为熟人原则的经验性知识的认识对象(内容),而是通过陌生人原则的先验知识的民俗之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的实践方法(形式),实践地建构——无论以陌生人社会还是以熟人共同体的自然空间为现实载体——的理想主义的“目的王国”(康德)。
[责任编辑刘宗迪]
作者简介: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