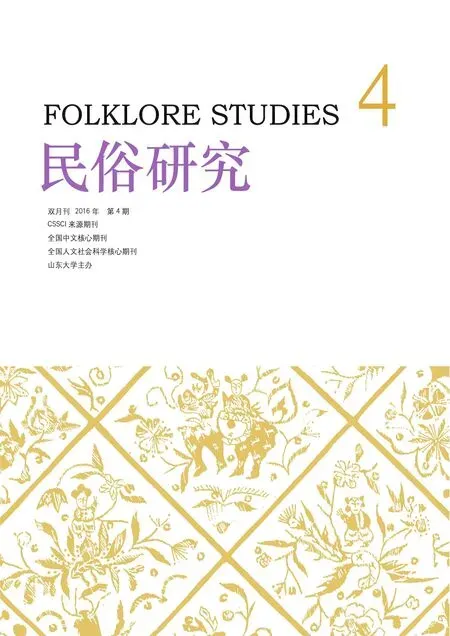明清以来年画中女性形象的母题探析
袁宙飞
明清以来年画中女性形象的母题探析
袁宙飞
摘要:女性是明清以来年画的重要主题之一。选取明清以来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生育女神的崇信和女性对女神纳吉祈福活动的分析,认为“生命绵延”和“吉祥求美”是年画中女性形象表达的两个核心母题。
关键词:明清以来;年画;女性形象;母题
民俗代表着一种传统的惯性,个人在参与这一传统惯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会不断地自我生成其情感、理性、理想与人格等。①张士闪:《眼光向下:新时期中国艺术学的“田野转向”——以艺术民俗学为核心的考察》,《民族艺术》2015年第1期。因此,民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年画是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艺术品”,不仅装点了人们的生活,还深刻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与美好愿望。年画通常图像艳丽,主题众多,女性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总体来说,年画中的女性主题表现,可大体分为两个核心母题,即“生命绵延”和“吉祥求美”。本文即主要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相关分析。
一、生育观中女神崇信的“生命绵延”母题
自远古时代,人类便产生了生殖崇拜的习俗。对孕育之谜的未解,形成了远古时期对可以繁衍后代的女性主体的崇信活动,进而形成了生命孕育的女神崇拜。这种崇信活动,在年画中即有反映,并进一步演变出有关女性人物形象的“生命绵延”母题。
(一)生育女神概况
中国最早的生育女神可以追溯到女娲。她是人类的始母,有补天、造人等功绩,是古代人类和古代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也是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崇拜和敬仰的女神之一。古代的文献中,记载了诸多有关女娲创造人类的神话故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东汉王逸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②(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32页。其中所言之“化”与《山海经·大荒西经》之“化为神”之“化”,皆有“化生”“孕育”之意。许慎《说文解字》:“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订,中华书局,1963年,第260页。
由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有关女娲生殖、生育的神话可以看出,上古时代人们对于强大生殖、生育能力的强烈渴望与崇拜,进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女娲为主体的“始祖母”神崇拜活动。“女娲氏的本义,应指生育娃娃、繁衍人类的始祖母或‘老母’,它是一个普通人名,不是一个专指人名,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有多少氏族便有多少始祖母,全可叫作‘老母’或‘女娲’。”*杨堃:《女娲考》,《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6期。由于女娲七日创生人类,所以在民间祭祀活动中将正月初七定为“人胜节”。这一天,人们常常通过剪“人胜”(即一串串连体小人)或供拜始祖母神祇的年画纸马来祭祀造人之主,表达对生命原初创生老母的崇信。
此外,民间也常常将蛙与女性生育崇拜相联系,因为“蛙”也即“娲”。如杨利慧认为,“以蛙为图腾的氏族,他们的共同名称叫蛙……故女酋长被后人尊为神圣女,称之为‘女娲氏’”*杨利慧:《女娲溯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赵国华的研究也指出:“女娲本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尔后再演变为生殖女神。”*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71页。远古时代,无论青蛙还是蟾蜍,都被视为蛙类,考古中出土的大量彩陶证实,蛙类通常被远古的氏族部落视为图腾而加以崇拜。蛙的繁殖能力很强,产子繁多,一夜春雨便可孕育出成群的幼体;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相似,一样浑圆而膨大,这就使得蛙具有了孕育和繁衍的象征性。由此民间便将蛙与女性繁育相关联,如年画中就常将蛙或蟾蜍与女性搭配作为画面主题,借以表达对繁衍后代、子孙延绵的美好愿望与祈求。
王母娘娘也是重要的生育女神,是与女娲并列的中华民族大母神,具有多种神格,司职繁多,如方位、刑罚、医药、长寿等。王母娘娘乃民间俗称,本名西王母,虽然古代典籍中有关其生殖神格的记载并不多,但在民间王母的送子神职却不少。如在广州一带,“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两送子者、两催生者、两治痘者,凡六位,盖西王母弟子。相传西王母为人注寿、注福、注禄,诸弟子亦以保婴为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后。壁上多绘画保婴之事,名‘子孙堂’。”*(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208页。另在山西阳城王屋山、河北房山等地也都有王母祠,在这些祠庙中,向西王母求子、求保婴的事例颇多。*陈丽琴:《西王母神话的传播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生育女神还有子孙娘娘,又名子孙保生之君,主管生育。由于生育事关重大,故民间还产生了子孙娘娘系列神,如送生娘娘、注生娘娘、催生娘娘等。这一系列也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分别形成了不同数量的女神组合,如北京著名的东岳庙娘娘殿内,就分三组供奉了九位神仙娘娘,皆于生育护养有关。在众多子孙娘娘系列中,又以碧霞元君最负盛名。相传碧霞元君为东岳大帝之女,因住在泰山之上,故又名“泰山娘娘”。“泰”,据《易经·泰卦》,意为“天地交而万物通”,故人们将其附会为妇女生子之意。泰山娘娘因“岱居本位,其色惟碧,东方主生,一本乎坤元之资生万物”,因其“滋生万物”,也就是说主生,故民间将其视为“送子娘娘”。*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在民间年画的神像画中,泰山娘娘常坐于中间,旁边侍女抱一活泼孩童,似予之,表达了送子护育的意题。
由民间存在的众多主管生育护养的女神可见,各地对生育信仰的细分和重视。这些女神,分别司职掌管着从投胎、受胎、定男女、保胎到生产、养育、哺乳等诸阶段,甚至还可以转胎,如将女性胎儿转为男性,形成为一套完整的神灵信仰体系,体现了民间多多益善、朴素的泛神化思想。这种泛化心理,也使得民间俗信中的女神几乎都拥有了送子护生的神格。
(二)年画中女性形象“生命绵延”母题的呈现
母题是民俗学中的经典概念*吕微等:《母题和功能:学科经典概念与新的理论性》,《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尽管在不同的理论中,母题的具体内涵有所差异,但一切母题却都具有一个基本特点,也是研究者辨识和把握母题的根据所在,那就是母题必以类型化的结构或程式化的言说形态,反复出现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种不变的、可以被人识别的结构形式或语言形式,是母题的重要特征。*孙文宪:《作为结构形式的母题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这种恒固不变性,也可以理解为“重复律”*美国学者本·阿莫斯指出,母题不是分解个别故事的整体所得,而是通过对比各种故事,从中发现重复部分所得,母题都是根据“重复律”这一纯粹形式化的原则做出的规定。转引自吕微等:《母题和功能:学科经典概念与新的理论性》,《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在不同时期的年画中,虽然女性人物形象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反复出现的同类图像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女性繁衍子嗣的类型化表达,也即生命绵延母题的呈现。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子孙昌盛家道丰”的传统观念,“多子”与“多福”紧密相关,子多也就意味着福多,是生活富足、家道蒸蒸日上的象征。于是,原初的民众在不了解生命繁衍的状况下,便将“子孙满堂”、生育保育的期望寄托于神灵身上,由此产生了民间信仰中诸多“概念化”的送子女神,并借助年画这一被民间大众广泛接受与认可的传播媒介,表达了人们子嗣绵延不息的愿望追求,进而产生了《天仙送子》《麒麟送子》等女神送生贵子系列年画。
从对女神的生育崇信中,我们看到了创造生命的女性主体形象,并与生命的繁衍生息呈现出直接关联的意义。这些女神形象,无论古籍对其原形如何描述,或人头蛇身,或虎尾豹齿,但于年画中,她们却都幻化为人类女性的形象。这种人化的表达,一方面是民间年画受传统绘画造像的影响,使神的塑造过程体现出人化特征;另一方面,也是民间受众对女神神性人格化的一种接受和认可,逐渐由神化转向人化的衍生和转变,进而产生了民众心理和意念中合理的女神形象。这种女神送子的生育观体现及女神人化的塑造,强化了女性在生命繁衍过程中的主体力量,构成为年画中以女性形象为表征的、生命绵延的母题图像,使得母子图及母女图大量的出现和传播,如《莲生贵子》《母女图》《圆满幸福》等。
在这些以女性为主体的“生命绵延”母题年画中,常常以民间约定俗成的谐音性或象征性的吉祥符号,对母题意义进行辅助性呈现,以满足人们“多子多福”的诉求实现。如“莲花”与“连”同声,且莲子多子,“笙”与“生”同音,故莲与笙合在一起就象征“莲生贵子”;“石榴”因其果实多子,因此具有“榴开百子”的象征意向;“葫芦”因其芦内多籽,因此具有“子孙万代”的象征表达;“鱼”因其旺盛的繁殖力及生殖信仰*详见陶思炎:《中国鱼文化》,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112页。,故有“多子”的寓意,并且与“玉”和“余”谐音,故又有“金玉满堂”“连年有余”等象征意义。
这些吉祥象征符号与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主体相结合,推进了对女神生育崇信的表达,使得女神逐渐由“神化”演变为“人化”,并借由吉祥符号的辅助演变为被民众广泛接受的“俗化”的形象,实现了女性人物形象在年画中“生命绵延”母题的恒常性。
二、民俗事象中女性祈福的“吉祥求美”母题
每一个民俗节日,都是以其民俗事象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如固定的日期、固定的祭祀或纪念的对象、相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模式化的仪式和娱乐活动等。*蒋秀英:《细说中国古代的妇女节》,《北方论丛》1999年第5期。在诸多的节日民俗事象中,以女性为参与主体的、向女神求吉纳福的民俗活动,呈现出对生产生活祈福和祝祷护佑的内涵。而在这些祈福祝祷活动中,为女性所崇信的女神会体现出“人的神化”的完美品格,并进而演化发展为年画中女性形象“吉祥求美”的母题。
(一)女性祈福的主题
岁时节日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在这些岁时节日中,女性也有专门属于自己的心意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乞巧、祈爱和以祈寿为主题的节日祈福。
农历七月七日乞巧节,民间又称“七夕节”“女儿节”“少女节”等,是女性群体参与最为踊跃的一个节日。乞巧节是古人由牛郎织女星故事所衍生出的节俗活动,是人们对男耕女织的社会构成在天上的心理投影。人们认为天上绚丽多彩的霞云,是由织女的一双“纤纤素手”所织成的,于是织女形象成为女性心目中心灵手巧的女神和乞巧的对象。
七夕萌芽于先秦时期,《物源》曾记载说:“楚怀王初置七夕。”*(明)罗颀辑:《物原》,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后,到汉代终于定型为一大节日。而乞巧的风俗,最早可见于东汉崔宴的《四民月令》,《艺文类聚》曾引载其文,介绍了最初的七夕习俗,“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庭上,祈请于河鼓、织女”*(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75页。。此后历经南北朝与隋唐,宋元时期,七夕已发展为一个相当隆重的民间节日;明清时期,乞巧更为盛行。女性乞巧,通常有穿针乞巧、漂针乞巧、蜘蛛乞巧、做巧果乞巧、生巧芽漂水乞巧、观巧云、拜魁星、乞美等方式。乞巧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普遍,由此亦成为重要的年画题材。
七夕之时向织女学纺织、学女红,是女性重要的心意寄托与表达,是传统女性寻求自我价值的体现,由此成为年画中有关女性活动的重要表现情景。如天津杨柳青年画《秋饮冬餐》,图中题诗“鹊桥此夕渡织河,美女穿针乞巧多”,便说明了七夕乞巧的节俗活动。画面直观地呈现了几名女性向织女星祈愿,以让自己的女红更加出色的场景。在她们上面的天空中描绘的是《天河配》的故事,而《天河配》则是年画中的常见题材,讲述了牛郎织女七夕节鹊桥相会的故事。这一情景在七夕年画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七夕节俗由来的展现;另一方面,也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社会中,民众对幸福生活孜孜追求的心意寄托。
古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魏)王弼:《周易注校释·系辞上》,楼宇烈校译,中华书局,2012年,第244页。,日月崇拜与祭祀是重要的原始宗教礼俗。“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81页。,日月分别代表阴阳,投射于人类,则象征男女。对此,《礼记·礼器》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清)朱彬:《礼记训撰·礼器篇》,沈文倬、水渭松校点,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0页。故在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说,拜月之俗,成为女性独有的风尚。月圆之时,女性常拜月以祈求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家庭。这种女子拜月祈爱习俗的流行,在一些词曲中便可略知一二,如南宋刘辰翁《虞美人·壬午中秋雨后不见月》:“便似佳期误,笑他拜月不曾圆”;宋曾允元《齐天乐·次韵赵芳谷曲,有香玉之怨》:“天上欢期,人间巧意,今夜明河如雪,新宽带结。想宝篆频温,翠銮低揭。雾湿云鬟,浅妆深拜月”。由这些诗词,可见女性借月圆寄托心思、祈愿自己能爱情圆满,是极其常见的习俗活动。
古时女性常常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所禁锢,恋爱往往不能自由,进而导致婚姻生活不幸福,于是现实中的愿望便被投射到天上,将月亮视为自己的知音,向其倾诉自己的隐秘,这在《拜月亭》和《西厢记》等爱情小说中均有相关描述。传统时期的社会分工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于是“主内”的女性常在月圆之夜拜月,期盼“主外”的男性能早日还家,期望全家团圆美满,于是月圆也便成为了家庭圆满的象征。
在古代神话中,月之女神主要有三个,即女娲、西王母、嫦娥,而嫦娥奔月的传说更是使嫦娥成为了最被广泛认可的月神。因嫦娥服用长生之药、飞升月宫之前是凡人,故具有人化神的象征,而长生不老药则寓意事事长久,所以凡间女子相信只要向其祈求,便可达成所愿。于是,女子拜月之时,常以嫦娥为祭拜之神,以祈求爱情的不老和长久。民间传说中,月神也常化为月华降临人间,遇到的人可向其拜请,愿望即可实现。拜月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向月亮跪拜、用木头雕刻为月姑祈拜等,而最常见的则是对年画《月光娘娘》于月出方向的供拜。年画神像《月光娘娘》中以女性为月神主体,并附以玉兔为伴。之所以以月兔为伴,源自民间“兔望月而孕”之说,如《尔雅·释兽》就解释说:“兔子曰娩。”所以向《月光娘娘》祈拜,也暗含借兔子能生育的特性以期望自己多子之意,充满了对生命繁荣的期盼。此外,年画中也常有女性拜月这一内容主题,如《拱向蟾轮》描绘的便是女性在月圆之时,向明月祈拜的景象。蟾轮即圆月,唐代元凛在《中秋月不见月》诗中就曾以蟾轮借喻明月:“蟾轮何事色全微,赚得佳人出绣帷。”图中款题,则诉说了拜月于女子的重要性,“十五学拜月,拜月十五夜。心自重月圆,何尝愿早嫁”,说明了拜月与女子嫁娶的关系。
自古以来,人们便希冀长生不老,如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典籍《尚书·洪范》中便有“五福寿为先”的记载。“寿”居首位,可见人们对长寿的渴望与期盼,于是就催生出了“寿星”“寿仙”等神灵,女性寿仙麻姑就是其中的一位。麻姑被誉为长寿女神,可追溯到晋葛洪的《神仙传》。麻姑随哥哥王平修炼成仙,多次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她不但长寿,而且年轻貌美,通晓方术,相传“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经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至得米便以撒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米,皆成真珠”*(东晋)葛洪:《神仙传》,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59页。。麻姑乐于助人的善良品格,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女性所敬仰和祈拜的女寿仙。此外,民间广为流传的“麻姑献寿”故事,也固化了其长寿的神格。相传三月三为王母娘娘诞辰日,设蟠桃盛会,众神仙前来祝寿,麻姑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献给王母。由“麻姑献寿”的传说可以看到,麻姑所献上的不仅仅是一份祝寿的礼品,而且还是以麻姑为象征的长寿祈福,体现了庆寿之人的尊贵地位。而这种吉祥祈寿的主题,是年画中喜闻乐见的题材。因此,在民间为女性祝寿时,常会赠送并悬挂麻姑手捧灵芝或蟠桃的年画,以表延年益寿的吉祥寓意。
(二)女性祝祷护佑的主题
在古代生产生活中,受自然经济的制约,人们常常会面临无法掌控的自然灾害,于是转而求助于神灵的佑护,这在年画中亦有反映,如各种以祝祷丰产、祝祷平安为主题的女性祝祷图像。
在传统的农耕经济中,“男耕女织”是最基本的社会分工形式。蚕桑生产是“织”的一个重要门类,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人们常常会面临诸多无法抗拒的灾害,使蚕桑生产无法获得丰收,于是人们便幻化出了蚕神来作为蚕桑生产的保护神。蚕神传说诸多,有嫘祖、蚕花五圣、三姑、马头娘娘、苑窳妇人、寓氏公主、蚕丛或青衣神等,大多为女性。其中在民间流传最广泛的是马头娘娘。关于马头娘娘,《蜀图经》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马头娘者,古之蚕神也。相传高辛氏时,蜀有蚕女,父人掠,惟所乘马在,其母誓曰:‘有得父还者,以其女嫁之。’马闻言,振迅而去,越数日,父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吃,父射杀之,曝其皮于庭,皮蹶然而起,卷女去。旬日,皮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叶,以丝成茧,以衣被于人间,为有蚕之始。蜀宫观塑女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转引自蒋猷龙:《蚕与马相联系的民俗学研究》,《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对于马头娘娘的祭祀,虽各地有异,但多数以供奉年画神像为主,如《蚕姑》《胜意蚕姑》《蚕花茂盛》等,用以祭祀并祈求蚕神护佑蚕茧丰收。
另外,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说法,并在此过程总产生了诸多的神灵信仰。如在沿海地区,为保护渔业生产与海上运输,就产生了妈祖娘娘信仰。她护海安澜,保护海上及江河渔业和航运的安全,是中国民间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据资料记载,妈祖实有其人,本是宋朝的一位民间女子,姓林,名默,也叫默娘,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二十三日生于福建莆田湄州湾的一个小渔村。她16岁时得神人所赐,从此“以巫祝事,能预知人祸福”*(宋)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98页。,常救助遇海难的商旅渔民,被人们称作“神女”或“龙女”。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九月初九日去世后,“时显灵应,或示梦,或示神灯,海舟获庇无数”*《琉球国志略》卷七,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98页。。因其熟悉航道,善观天文,精通法术,救助航险,故深受人们的爱戴和崇拜。人们感激妈祖的救助之恩,便修建了妈祖庙,以求护佑舟航平安。随着其事迹的广为流传,人们对她的信仰也越加虔诚,“至于居常疾疫,孕育男女,行旅出门,必以纸币牲物求媚而行祷焉”*(明)朱制:《天妃辩》,蒋维铁编校:《妈祖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页。。于是,妈祖逐渐从一个救人于海难的女性,演变成为一个神通广大、有求必应的女神,神格愈渐丰满,以至历代帝王对妈祖的褒封不绝于书。在民间,每年正月、三月、五月常会在天后宫或妈祖庙中举行庙会,对妈祖进行祭拜。沿海一带的民众也常将妈祖年画神像供奉于家中,出航远行之时更是会将妈祖年画神像供奉于船舶之上,借以祝祷舟航平安。
(三)年画中女性形象“吉祥求美”母题的呈现
在以女性为参与主体的民俗活动中,人们创造出了诸多的女神形象。这些女神可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由凡女变为女神者(如嫦娥、马头娘娘、妈祖),一是在人间留有凡迹后飞升而去的女神(如织女下嫁凡间牛郎、麻姑救助蔡经妻等),这种接地气的化升使得女神具有了人性化的亲和力。她们往往具有完美的精神品格,是德行美好、贤淑、给予、奉献、牺牲、仁慈、博爱、睿智、聪慧、宽宏大量等的综合体。这种完美的综合体,是民众趋吉求瑞的心理显现,表达了人们对完美形象的不懈追求。这种借助完美形象进行趋吉求瑞的祈福表达和追求,便构成了年画中以女性形象为表征的“吉祥求美”母题的呈现。
年画中女性的内在美好品格,常常借由女性外在的形象美和各种物象表征来进行传达,虽然不同时期对女性的外在美有着不同的追求,但女性形象在年画中所表达出的祥瑞内涵和美好祈愿却是恒常的。而这一“吉祥求美”的恒常性,是女性形象在年画这一载体中民俗性旨归的呈现,极具象征意义。如《双美人执扇图》,佛手树下,一位貌美的仕女坐于摆放菊花的石桌旁,一手持桂花,一手执团扇,另一仕女则呈“S”形温弱而立,执扇侧目微笑。两女周身皆以牡丹、莲花、如意等图案纹样加以装饰,呈现出祥和的图景。因“佛”与“福”谐音,故佛手树寓意有福,而桂花寓意富贵,菊花则寓意长寿,暗含了美好吉祥的寓意。又如新年画《岁岁平安,事事如意》,几位美丽的女性与孩童相伴于花园中,手持团扇,旁有果盘花瓶、柿子如意等物件,端庄坐立,女性美好的形象与手中的物象给人以强烈地端庄祥瑞之意。
此外,我们看到,在这些吉祥求美母题的年画中,普遍会以祥瑞物象作为象征意义的呈现。这是由于“在古人的观念中,‘物’之存在与驳杂决定着吉凶变化,因此,为控制这一变化,获取‘福善’与‘嘉庆’,祥物得到了普遍的应用”*陶思炎:《中国祥物》,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3页。。于是,这些吉祥物象便成为年画中女性祈福纳吉的凭依,同时也被作为美化和体现完美女性内在品格的直观表达,成为吉祥求美母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牡丹、柿子、凤凰、麒麟、戟、磬、风筝、如意等。这些高度凝缩,或具象或抽象的物象,都被民间艺人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吉祥象征,体现出强烈的功利趋向,倾注了民间群体发自心底、超越物象的感悟,并在年画中与女性人物形象共同体现出民众吉祥求美的心意诉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物象中,扇子是年画中女性常有的手持之物,因为于女性而言,扇子具有深刻的表意内涵。在古代,人们常将其作为辟邪或定情的吉祥之物。团扇是由汉代的偏扇演变而来的,因用丝绢或纸张做成圆形扇面而得名。团扇制作时,一根扇柄从中对分,共筑一圆形扇面,相对相连,故有“合欢”“同心”之意,因此又被称为“合欢扇”或“同心扇”,可托寓相爱相忆之情。因其有合欢寄情之寓意,故成为女性常用的钟爱之物。除此之外,“扇”与“善”谐音,故“扇”又有和善、善念、向善之意。在浙东一代的风俗中,闺女出嫁后的第一个端午节,娘家须派人携带各种扇子前去探望女儿,寓意“送善”,传达娘家人对出嫁女儿的心意寄托。
美与善历来可互释和代换,美即善,善即美,可用来指称一切美好的形象和情操,而贞德淑女更是美的形象、善的化身。因此,女性形象与祥瑞物象的结合,在年画中形成了对内容的善和对形式的美的同构,体现了“吉祥求美”母题美善合一、至善尽美的境界。
总之,女性是年画的重要表现主题之一。而所有这些与女性有关的年画图像,就其表现内涵来说,可大体总括为两个主题,即“生命绵延”和“吉祥求美”。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的主题,又与女性生理特征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神灵信仰有直接关系。民间信仰中对女神崇拜有加,而这些女神形象的形成,无论是“人的神化”,还是“神的人化”,都反映出民间大众对“人神合一”的、具有亲民和亲情女性形象的广泛认同。这种亲和力和认同感,使得女性形象在年画中具有了生命传承和趋吉求瑞的象征内涵,也即“生命绵延”和“吉祥求美”的母题呈现。
[责任编辑王加华]
作者简介:袁宙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山东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山东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化保护和传承关键技术及集成与示范”(项目号:2014BAK09B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二十世纪以来年画中女性形象研究”(项目号:2015M582067)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2015GN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