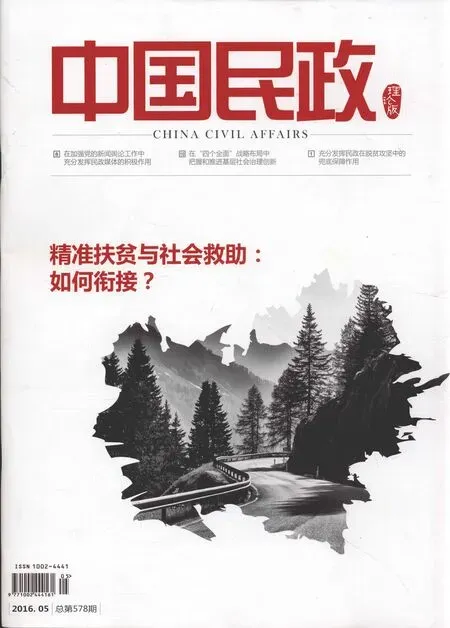城市社会救助对象瞄准方法、偏离原因和对策
姚建平
城市社会救助对象瞄准方法、偏离原因和对策
姚建平
一、城市社会救助对象瞄准方法
贫困人口瞄准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类别瞄准、财富瞄准、需要瞄准、区域瞄准、社区瞄准和行为道德瞄准六种方法。[1]从我国城市社会救助的实践来看,运用的方法包括财富瞄准、类别瞄准、社区瞄准和行为道德瞄准等几种。财富瞄准是我国城市社会救助项目最主要的方法。根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管理审批机关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除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外,我国几乎所有专项救助都对受助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要求,并且大都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捆绑在一起,因此也都属于财富瞄准。
虽然财富瞄准是所有社会救助项目采取的主要方法,但在实践中往往会结合其他瞄准方法识别救助对象。分类施保就是我国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类别瞄准和财富瞄准相结合的瞄准方法。例如,2007年的《济南市关于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分类施保的通知》规定,分类施保的对象包括六类家庭:家中有重大疾病患者;家中有重度残疾人员;“三无”对象;需要独立赡养两个或两个以上无收入高龄(70岁以上)老人的;由一方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父母双亡、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老幼家庭;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特殊困难家庭。专项救助除了经济状况要满足一定条件以外,通常也要结合人口学特征进行瞄准,因此实际上是财富定位和需求定位相结合。例如,2014年的《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规定,可以申请医疗救助的人员包括四类: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因患大病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自负部分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家庭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的人员。由此可见,医疗救助首先是通过收入将贫困人员确定为潜在的申请对象,再加上医疗需求者的类别瞄准来最终确定医疗救助对象。其他专项救助,如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瞄准方法也是如此。
瞄准受助者的行为和道德在社会救助的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在英国的济贫制度下,人们将贫困归结为个人责任,贫困者被分为值得救助的人和不值得救助的人。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早期对受助者的瞄准除了考虑收入之外,也有明显的行为道德要求。根据1997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益对象要向两类人倾斜:一是传统社会救济对象,二是下岗失业人员。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非完全按照收入标准,有很多人是排除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以外的,这些人包括:(1)外地来本地就读且具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在校学生;(2)户口虽在当地但长期在外地居住的人员;(3)由于征地而农转非并自愿领取一次性全额安置补助的人员;(4)违反《婚姻法》、《收养法》、《计划生育法》的人员和家庭;(5)因吸毒、赌博造成家庭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员和家庭;(6)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期间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部门和基层组织提供劳动就业机会的人员;(7)家庭中虽无从业人员,但主观认定其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成员;(8)家庭中拥有非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的家庭成员。[2]从以上对受益资格群体的限定中可以看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反映了与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衔接(传统民政对象优先),又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如将下岗失业人员作为重要救助对象明显打上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烙印。同时,对救助对象还有道德要求。例如,吸毒、赌博者和违反《婚姻法》、《收养法》、《计划生育法》的人员排除在外。
二、城市社会救助对象瞄准偏离及原因
社会救助制度出现目标对象瞄准偏离的可能性非常大。目前比较常用的计算社会救助目标对象瞄准偏离的理论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学者 George Dellaportas提出来的。他将瞄准可能出现的结果分为四种情况:两种成功可能和两种偏离可能。两种成功可能是:目标家庭获得保障和非目标家庭没有获得保障。两种偏离可能是:目标家庭没有获得保障和非目标家庭获得保障。在社会救助实践中,两种准确瞄准是理所当然的制度要求。而两种瞄准偏离则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关注。基于两类错误瞄准可以构建两个指标来衡量瞄准效率。没有获得保障的目标家庭数与目标家庭总数之比称为挤出率(没有获得保障的目标家庭数/目标家庭总数),获得保障的非目标家庭数与获得保障的家庭总数之比称为漏损率(获得保障的非目标家庭数/获得保障的家庭总数)。但是,已有的很多研究计算出来的我国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漏损率和挤出率都很高。例如,叶初升和邹欣使用OLS、LPM、Logistic模型和QR四种方法来计算,发现我国扶贫瞄准存在严重的漏瞄和溢出现象。四种方法计算的漏损率分别为50%、63.95%、55.63%和75.33%,四种方法计算的挤出率分别为21.01%、136.73%、100.63%和86.33%。[3]世界银行 Ruslan Yemtsov使用ASPIRE数据对孟加拉国社会救助制度瞄准效率进行计算发现,2005年和2010年的挤出率分别为79.1%和65.6%,漏损率分别为44.3%和59.8%。[4]
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对象瞄准偏离的原因非常复杂,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漏损率(错保)与调查时间密切相关。对贫困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往往是一个时间点上的数据,而家庭收入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动。对于那些收入接近贫困标准线的家庭来说,家庭收入的很小变化都可能超出标准线。很多临界的贫困家庭可能在年初符合收入规定,但是到调查时期可能突然收入增加超过标准线。由于在贫困标准线附近存在大量低收入家庭,而我国获得救助的贫困家庭得到亲属收入转移和灵活就业都非常普遍,因此通过经济状况调查来确定救助对象总会存在偏差。
第二,挤出率(应保未保)与申请程序所花费的时间相关。目前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行政程序包括个人向乡(镇)人民政府申请(或委托居委会代其申请),乡(镇)人民政府受理申请后组织人员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核实,家庭状况调查核实后,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民主评议并将结果在社区公示,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申请对象,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复核并交县民政部门审批。如果申请成功还要在乡(镇)、社区居委会公示。这套申请、审核和批准程序走完至少也要数周时间。因此,即使家庭经济状况符合社会救助资格条件,从贫困家庭提出申请到最后批准下来的这段时间实际上也是一个应保未保状态。
第三,挤出率(应保未保)与贫困家庭不了解社会救助政策或不愿意申请救助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研究发现,美国符合条件家庭的食品券项目参与率大约为50%。一项1993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艾黎格尼(Allegheny)县的调查表明,符合条件的人不去领取食品券的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很多人自认为他们不符合领取食品券的条件(59.7%)。如果这些人一旦知道他们有资格获取食品券的话,那么就会去领取食品券。二是很多有资格的家庭(22%)不去领取食品券是因为觉得项目每月的收益有限,他们觉得不值得或不需要领取。三是也有一些人(6%)认为不去领取食品券跟个人耻辱有关。[5]由于贫困者往往是那些信息闭塞的人员,因此他们很有可能因为不了解政策而不去申请。对于中国来说,一些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可能会更愿意接受亲友救助而不去申请政府救助。另外,还有一些贫困家庭(尤其是有孩子的贫困家庭)不申请救助可能与耻辱感有关。
第四,从瞄准方法来看,造成瞄准偏离的重要原因是对财产标准的界定。很多学术研究对瞄准偏离的计算很难将财产量化,因此计算出来的结果肯定会有很大的误差。在社会救助实践中,对贫困家庭的财产状况也很难有科学客观的估算,往往大都是工作人员主观估计的结果。虽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均有资格申请获得最低生活保障。但在实际操作中,资产是各地进行低保家计调查排除申请者最主要的标准之一。目前,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对于申请社会救助都没有明确的财产规定,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申请人员是否符合申请社会救助的资格。工作人员对贫困家庭财产的主观判断很容易造成瞄准偏误。
第五,除了资产之外,还有很多原因使得那些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家庭得不到低保。例如,《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明确提出6种情况下要停止发放低保:(一)自费安排子女出国留学的;(二)自费出国旅游的;(三)达到法定就业年龄且有劳动能力但未就业的家庭成员一个月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时间不足60个小时的;(四)离开居住地超过3个月,未向申请地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报告的;(五)无正当理由拒绝有关部门就业培训或者推荐就业两次以上的;(六)存在明显高于一般生活消费的情形。[6]消费相对于收入来说更难核实,因此,如果采用消费支出或消费方式来作为社会救助目标瞄准的方法,更容易造成偏误。另外,行为道德与目标对象瞄准挂钩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太好操作。
第六,相关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可能造成瞄准偏离。例如,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曾经将大量下岗职工纳入低保,各地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推动村改居政策也可能出现将大量低收入人员纳入低保制度等。由于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要在短时间内将大量低收入人口同时纳入救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政治和政策环境可能是决定是否进行救助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瞄准的准确性。
第七,调查质量也会导致瞄准偏离。现有家计调查手段包括信息核对、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但是每种方式都会有缺陷,要通过这些方式完全搞清楚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资产状况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想要申请救助的家庭更有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有意或无意地隐瞒家庭收入或资产。另外,贫困家庭成员本身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他们在计算和填答家庭时较之其他群体更可能出现偏差,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核查不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造成瞄准偏离的因素非常复杂。要判断救助制度目标对象瞄准效率,首先要确定哪些人是政策目标对象。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例,根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二条,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从法律条文来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瞄准认定是看家庭人均收入。另外,学者的研究瞄准偏离时也往往采用收入作为唯一标准。但是,在各地实践操作中并非完全将收入作为救助对象瞄准的唯一条件。各地出台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中对低保资格的要求除了收入之外,又加入了财产、消费支出、行为道德等因素,这肯定会导致很多低于收入标准线的人被排除在低保制度外。但是,这些被排除在低保制度之外的人实际上并不能够算作瞄准错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外是有地方出台的政策文件作为依据。除此以外,由于瞄准程序的执行无法准确查收家庭收入和财产、贫困人员因不了解政策没有申请等导致的瞄准错误则应该算作瞄准错误。
三、社会救助对象精准识别的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建设,坚持同时使用多种瞄准方式。当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核查手段主要包括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和信息系统核对四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对低保对象的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核查的方式也不同,对于收入和财产状况标准的规定也有不同的要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采用的是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传统方式,而发达地区(如广州、上海等地)已经建立了一套数字化的信息核对系统。借助现有的信息网络平台,利用银行、证券、税务、工商、社会保障等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对申请者和受助者的家庭财产和收入状况进行比对来查实申请者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与传统方法相比,信息核对系统在查实家庭收入和财产方面(尤其是城市家庭)更加可靠、准确,因此建议尽快在全国城市推广和普及。但是,信息核对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隐性收入和现金收入往往难以核实,资产的货币化也比较困难。如果仅仅依靠信息核对方法来识别社会救助对象,很容易造成偏差,有可能会导致“错保”、“漏保”等情况。因此,传统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法仍然是社会救助对象瞄准的重要手段。
第二,结合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提高社会救助制度的瞄准效率。由于家庭收入和资产认定比较复杂,因此完全建立在收入和资产基础上的社会救助对象瞄准在实践中很容易造成偏差。收入和资产仅仅是贫困风险的一个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剥夺和缺乏也是陷入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采用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低收入家庭面临的贫困风险,有助于提高制度的瞄准效率。建议从低收入家庭生计资产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对低收入家庭生计资产进行量化分析,测算反映其贫困程度的生计资产数值,按照生计资产总值由低到高的顺序确定社会救助对象,从而提高瞄准效率。在生计资产指标确定时,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除了与收入和消费相关的一些核心指标外,还应包括年龄、性别、就业、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社会关系、住房、家用电器和用具,甚至地理位置等。
第三,尽快制定社会救助制度财产标准,减少资产审查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社会救助制度的收入标准早就在全国有明确规定,但是各地却没有明确量化的财产标准。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主观判断来决定申请人员是否符合申请社会救助的资格。因此,财产评估的偏误是瞄准偏误产生的重要原因。为此,应该尽快制定社会救助瞄准的财产标准。在确定财产标准时,首先要区分哪些属于必需品和哪些属于非必需品,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类财产相应的价格上限。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形成财产标准清单,作为低收入家庭申请社会救助的依据。
第四,加强社会救助申请和审核程序管理,确保瞄准程序的公正性。目前,城市低保申请包括个人申请、社区初审、街道办事处审查和评议、县(区)民政部门审批四个环节。针对低保申请和审核程序流程长、环节众多的情况,在强化低保审核管理过程中,需要对程序中各个环节进行优化管理。建立申请机制、核查机制、评议机制、审批机制四个联动机制,坚持将家庭收人核查作为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通过加强低保审核审批过程中的管理力度,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严格把关,确保低保对象的准确瞄准及公正性。在低保对象认定各个环节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避免“人情保”、“关系保”等不规范现象的发生,从而降低保漏损率。同时,尽量简化社会救助申请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减少因行政程序过长导致的应保未保现象。
第五,加大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力度,强化社会救助申请者的法律意识。在社会救助对象瞄准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偏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收入家庭对现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了解程度不够,这很容易造成应保未保现象。为此,各地应当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做好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宣讲及知识普及工作,提高社会救助政策知晓率,有效降低挤出率并提高社会救助制度的覆盖率。同时,应加大对通过隐匿家庭经济收入等方式骗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最低生活保障户的处罚力度,增加违规成本,从而有效降低漏损率。此外,还应加强社会救助申请者的法律意识,使其充分了解福利欺诈的法律责任,从源头上减少瞄准的偏差。
第六,建立社会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机制,减少应保未保现象。目前的社会救助制度需要贫困人员主动申请才可能获得救助。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贫困人员往往由于很多原因并未申请社会救助。尤其是那些城市最底层的贫困者往往更容易被政策所忽视。这些人不申请社会救助不仅无法解决自身的贫困问题,而且很容易发生极端事件,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建立社会救助对象的主动发现机制,具体要做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城市贫困动态跟踪系统。采集并跟踪城乡贫困人员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重度残疾人员、患重特大疾病人员、老年人以及发生重大事故人员的信息,争取在极端事件发生之前进行干预。二是可以考虑利用现代通信方式和手段,建立一个包括社会爱心人士和志愿者,民政、残联、新农合、妇联、计生委、教委等有救助项目的部门经办人在内的网络(例如QQ群、微信群等),让人民群众随时提供潜在社会救助对象的线索,从而减少应保未保现象的发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理事、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
注释:
1. 尼尔·吉尔伯特.《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年版, 序言第6页.
2. 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40-141 页.
3. 叶初升, 邹欣.《扶贫瞄准的绩效评估与机制设》.《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
4. Ruslan Yemtsov. "Measuring performance of social safety nets:ASPIRE for global benchmarking", presetation PPT at Center for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of low income families,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November 2015.
5. Daponte. Sanders and Taylor. 1998."Why Do Low-Income Household Not Use Food Stamp?",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XXXIV·3, p612-628.
6. 《2015年广州低保最新政策:6种情形停发低保》.《信息时报》, 2015年9月23日. http://gz.bendibao.com/life/2015414/185049. 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