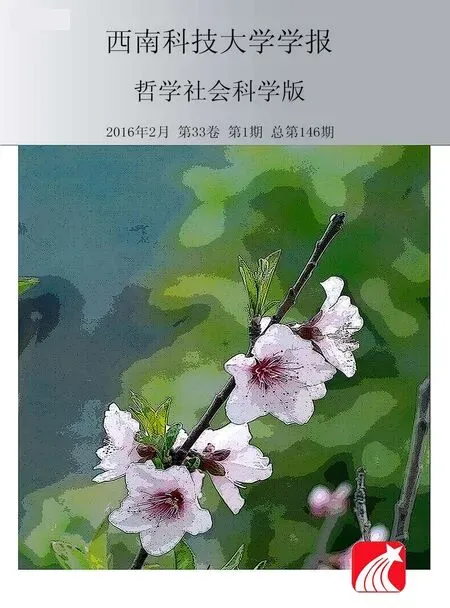《斐莱布篇》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影响——隐于“一体性”问题中的理解之路
王 骏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斐莱布篇》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影响
——隐于“一体性”问题中的理解之路
王骏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摘要】伽达默尔对《斐莱布篇》的现象学诠释,对于理解他的哲学诠释学思想以及20世纪初德国哲学思维方式是十分重要的。《斐莱布篇》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阐明《斐莱布篇》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揭示伽达默尔对当代德国的古希腊哲学诠释工作的批判,也有利于厘清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柏拉图;伽达默尔;斐莱布篇;哲学诠释学;影响
自20世纪20年代起,德国哲学对于古希腊文本的诠释工作普遍体现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式思维,即以逻辑的合理性作为古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评判标准。为了批判此种技术理性模式的方法论,伽达默尔重新回归到柏拉图哲学中去探寻一条诠释学的道路。伽达默尔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作为重点,实现了柏拉图哲学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融合,同时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建立起关联。在此过程中,伽达默尔呈现了哲学诠释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张力。
一、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张力
作为20世纪早期以现代科学思维诠释柏拉图文本的、具有重要影响力人物的纳托普,将柏拉图视为康德和现代科学思维的先驱,并以自然法则概念、现代科学方法对其进行了诠释。纳托普认为,柏拉图的理念是“易变的显现物的永恒图像”[1]40, 它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分离。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纳托普倾心于柏拉图哲学的理由始终是那种令人生畏的抽象性。”[2]56这种在逻辑演绎模式下,将柏拉图哲学对象化的研究方法不仅消除了研究者自身的历史性,而且遮蔽了柏拉图文本字面含义背后的意义。诚然,自笛卡尔提出普遍怀疑的方法论以来,旨在消除一切偏见的科学方法论便为人文科学所青睐。这种二元论背景下的技术理性方法论显然并不能满足伽达默尔对古希腊哲学进行研究的意图,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的研究进路则满足了他的要求。伽达默尔认为:“正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传统的思想文化(Gedankenbildungen)才具有了生命力,因为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问题的回答。”[3] 613在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主客两极化思维的批判,以及提出一种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发生”(ereignis)真理的启示下,为了解决现代技术理性思维方式的弊病,伽达默尔从柏拉图那里开始了诠释学真理的探索之路。伽达默尔正是在一种哲学诠释学与现代科学的张力中回归柏拉图文本,他以《斐莱布篇》作为范例来探讨柏拉图对话及其内在的辩证法,而这也是伽达默尔为探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内在关联所作的铺垫。因此,伽达默尔的《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实际上是一本未明说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3] 618。伽达默尔对柏拉图文本的诠释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现象学描述法,他沿着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道路正是为了反对现代科学的主客二分法。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的文本通过对话方式获得一种“发生”真理,这种开放式真理使得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区分开来。在伽达默尔看来,柏拉图的真理并不是通过对理念一系列严密的僵化的逻辑推论而获得,而是对对话中提问方所提问题的展开。提问与对话强调开放性,因而通过对话方式展开了不仅只有一种结果的可能。诚然,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更能体现实际生活中受环境制约的对话,这与现代科学追求“主客一致”的真理观是相悖的。开放性一方面是苏格拉底所强调的定义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也是柏拉图对话本身的特点。柏拉图从逻各斯角度为对话开放性提供了证明,而这种逻各斯基础正是伽达默尔现象学描述法中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保持一致的地方。对于伽达默尔来说,以对话的方式进行理解既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理性的反抗,也是诠释学发展的进路,正如伽达默尔自己所认为,他的诠释学应当作为一种对特定的、急迫的历史问题的回答。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伽达默尔看到了柏拉图对话中不同于科学概念中的演绎、发展的认识论模式,即在问题意识引导下开放的认识论模式。正是在这样的争辩中,伽达默尔和当代科学理性辩护者们一样,试图建立起当代哲学与古希腊思想的关系。这种关联的建立,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对古希腊文本作历史诠释,更可以说是为了从古希腊哲学文本中重新找到一条适合于现代哲学发展的进路。伽达默尔与古希腊文本关联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诠释柏拉图的文本;第二,采用现象学的描述艺术(Kunst),建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在关联。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着柏拉图所未能涉足的东西:如实践哲学,但是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已经揭示了两者的共同基础,亚里士多德哲学可以看作是柏拉图哲学的深入。伽达默尔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整体视域之中进行诠释的,这种整体视域表现为伽达默尔对“一体性”(Solidarität)问题的探讨。于是,伽达默尔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诠释的核心,并试图以此为契机将柏拉图对话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联系起来。
二、 《斐莱布篇》中的“一体性”问题
伽达默尔以《斐莱布篇》作为柏拉图哲学范本的原因如下:第一,《斐莱布篇》是柏拉图晚期著作,其所代表的柏拉图哲学思想已趋于成熟,以其晚年文本作为参照,既能把握柏拉图思想的核心,又能将之与其早期思想对比分析,找到柏拉图哲学本身的内在一致性;第二,《斐莱布篇》中具体探讨了柏拉图对话的辩证法本质,伽达默尔将之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并列,找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内在一致性。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斐莱布篇》不仅是柏拉图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关联的重要节点,而且是哲学诠释学理论的合理范型:《斐莱布篇》在逻各斯基础之上展开了对人类之善的问题的探讨。伽达默尔在《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序言中阐明了这样的问题:柏拉图的辩证法是否是,或者以何种方式是伦理学。这个问题直接提出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并形成了伽达默尔诠释《斐莱布篇》的问题视域,引导着伽达默尔对柏拉图文本进行现象学描述的全部过程。《斐莱布篇》中的苏格拉底围绕着快乐和知识何者更接近善的问题与普罗塔库进行对话,苏格拉底提出在快乐与知识的“混合”中寻求善。“混合”即是指向现实的逻各斯,这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探讨伦理学问题的基础。在伽达默尔看来,善的问题贯穿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它涉及两者的共同基础——逻各斯。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逻各斯之构成原则,这种善不能通过定义客观对象的方式,而只能在理念与实在的关联中获得。伽达默尔认为数的结构是柏拉图理念论的范型:单个数由于比例关系而构成总和数,而“这种关系的普遍性超越了它的构成因素”[4] 164。 对于柏拉图来说,与数的结构相对应的逻各斯中同样存在着理念的尺度和比例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逻各斯才能作为对现实事物的本质规定而指向某物。
在《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在按某种方式或某种尺度和比例构成的“混合”之中找到了善的居所,伽达默尔意识到,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所作的“一个‘种’的各个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与构成一个集合的事物共同具有的东西这二者的区别”是极其重要的[4] 147。善并不是作为某一类事物最高的种来把握的,而是每一个“多中之一”所共有的东西,而“一”正是通过理念之间分有构成的逻各斯。《斐莱布篇》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对人类生活的诠释:第一种代表斐莱布的观点,即人类与其他存在物一样,“享受、快乐、高兴,以及可以和谐地归入此类的事情构成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的善”[5] 176;第二种代表苏格拉底的观点,即人类借助理念的形式与世界发生着关联,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地方,因而“思想、理智、记忆,以及与此相关的事物才是善”[5] 176。因此,苏格拉底提出要在“混合”之中寻找善,这种善“被理解为人类灵魂的一种条件”[6]105。也就是说,善是逻各斯的条件,是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也是此在所寻求的东西。苏格拉底进一步对快乐作了区分,这充分说明了逻各斯与实在之间的关联:不同的快乐对应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唯有在纯粹的快乐中,此在才能完全理解自身,因而此在的存在才会被澄明,而身体的快乐会“混淆灵魂并且剥夺它的意识”[6]206。
柏拉图对快乐的区分还指出了“混合”的快乐总是涉及缺乏的痛苦。这种夹杂着痛苦的快乐需要理性提供相应的比例和尺度,正如蜂蜜和水的混合,只有达到一定的比例才能产生合适的味道。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此在不仅要树立正确的目标,还需要明智提供合理的方式达成目标。柏拉图所说的比例和尺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为“中庸之道”,只不过亚里士多德是从实践的层面来阐述的。可见,伽达默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终保持一致的方面正是在《斐莱布篇》中所反映的:“人类的任务是要经常不断地用尺度去限制无尺度。”[4]169伽达默尔认为,柏拉图在这里对快乐所作的区分旨在说明唯有首先理解了“X是什么”,我们才能朝向真正“善”的生活。这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是整个柏拉图哲学的关键,也是亚里士多德探讨“快乐”问题的线索。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就是关于快乐和痛苦的德性,……德性就是中庸,是对中间的命中。”[7] 28,34德性设定了此在的目标,明智则提供了相应的手段。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因而除了柏拉图所提出的“善”的生活,还有一种“善”的筹划,即对通达“善”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筹划是灵魂中的逻各斯对自身的言说,是对合理选择的决定,也即是实践智慧。
从《斐莱布篇》中的苏格拉底对话看来,快乐与知识的“混合”显示了逻各斯作为话语指向现实,而对快乐的区分则显示了逻各斯所具有的开放性,这种逻各斯的现实性和开放性使得对话始终面向事情本身,并且最终达成双方的一致意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同样基于这种逻各斯基础,相比柏拉图关注逻各斯的理论构成,他更加关注在现实境遇中的逻各斯所产生的效用。在不同的情况中,此在受到逻各斯引导的行为方式总是具有合理性,这种行为本身是善的,并且会达成善的目标。如果说柏拉图强调通过教育以“认识”,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强调通过教化以“实践”。但两者有着共同的基础,即逻各斯,这同时就是存在于柏拉图《斐莱布篇》中的“一体性”问题。
诚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所关注的仅仅是普遍意义上善的知识以及善的生活,所以善对于柏拉图而言还仅仅在理论层面。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善在不同的具体境遇之中有不同的表现,他认为在现实的具体情况中,往往会面对“何种行为合理”的“选择”问题。因此,伽达默尔看到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所实现的从理论之“善”到实践之“善”的转变,只不过两者都保持着《斐莱布篇》中所显示的共同基础,即逻各斯。《斐莱布篇》揭示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体性”,而伽达默尔正是在这种“一体性”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诠释学反思,从而构建了哲学诠释学,提出了不同于当代科学的对柏拉图的阐释。
三、 基于“一体性”问题的诠释学反思
伽达默尔在《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中,阐明了柏拉图对话(Dialog)辩证法之所以是一种伦理学以及达到共同理解,是因为蕴含于柏拉图对话中的逻各斯基础。他提出对话是我们在现实中达成共同理解的方式,自我认识和对他者的认识在对话的过程中同时发生。通过对话的方式,人类此在总是能够做出合理的理解,这种合理的理解能够澄明此在的存在。诚然,无论是设定善的目标还是做出善的选择,都离不开逻各斯的引导,人们的行为总是会受到前见的指引,而这正是伽达默尔所揭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一体性”所交代的内容。
伽达默尔认为,“哲学思维总是受到某种指导的支配:它在对原始的世界经验继续思考的时候,必然要透彻地思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语言的概念力和直观力。”[3] 614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哲学思维就是一场谈话,谈话不仅发生在“你”和“我”之间,而且还在“我”和“灵魂”之间。而逻各斯作为话语是谈话的重要因素,人类此在倾听作为自身前见的逻各斯对我们的言说,倾听不仅要求承认前见的合法性,而且承认前见的局限性。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柏拉图已经通过数的结构阐明了这种逻各斯的特性,由于逻各斯本身的缺陷使其总是呈现出一种无限性,人类此在总是处于一种“无知”的开放状态。而正是“无知”,使得人类在谈话中获得一致意见成为可能,“谈话”在“无知”与“知”的辩证循环中不断地进行,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此在不断地获得理解、不断地使自身前见合理化。
伽达默尔在柏拉图对话中融入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认为在生活活动的各种可能性中,必须通过实践智慧才能做出善的选择和决定,才能将善的理想目标落实和实践于具体的实践生活之中。”[8]171伽达默尔所提出的“理解的应用性”正是对理解中实践智慧的阐述。在《斐莱布篇》中,由最初的无区分“混合”到善的“混合”的过程,充分展现了逻各斯的辩证运动。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的每次“选择”,或者说对所探讨话题的推进,正是实践智慧的展现。“善”的混合,不仅仅表现为谈话双方经过视域融合之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致意见同时是一种合理的、善的理解,是实践智慧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谈话亦如此,“一种真正的谈话就是我们在其中力图寻找‘我们的’语言——即一种共同的语言——的谈话”[3] 642。伽达默尔通过蕴含于《斐莱布篇》中的逻各斯问题认识到谈话的实践是对差异的消除,在谈话中寻找的共同语言,不是谈话双方之间共有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谈话者所没有且渴望的东西,即是说,是一种潜在的东西,谈话实现了由潜在向现实的转化。这就如同苏格拉底所说的:“当一个人变得缺乏时,他显然想要得到他正在体验到的东西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他正在变空,期望得到补充。……灵魂领悟到补充,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要通过回忆。”[5] 212这正是苏格拉底“无知”的内涵:灵魂寻求知识以补充“无知”,这种补充既不是不及,也不是过度,而是保持一种和谐。美德本身是完满的,与夹杂着痛苦的快乐不同,它关乎此在的自我理解,真正拥有美德的人才能够做出合乎美德的行为。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到:“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7] 34。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实践智慧,它涉及伽达默尔的谈话结果的合理性。诚然,伽达默尔不仅仅关注逻各斯的现实性,同样重视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问题意识,因为柏拉图不同文本的共性是:苏格拉底对总是围绕着某一主题展开的,既不是单方面地灌输知识,也不是漫无边际的随意交谈,而是在就某一问题所进行的对话。问题是对逻各斯的开放性的限定,因而在对话中逻各斯表现为问题视域中的有条件的开放性。
伽达默尔在诠释学反思中尤其强调“提出问题”的重要性:问题的提出意味对自身所欠缺东西的发现,它引导着逻各斯由潜在向现实的转化,并且保证了对话辩证法的发展方向。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过程总是在问题引导下对前见的区分与修正,以及获得新的视域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人类此在的运动过程。
伽达默尔认识到当代哲学有着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借助对话通往“开放”真理的诠释学之路;第二条是借助科学方法论通往“绝对”真理的现代科学之路。伽达默尔基于“一体性”的哲学诠释学揭示了历史中的“不变”要素——逻各斯,作为哲学诠释学的基础,它涉及传统与现实的关联,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主要在传统习俗中形成的、能够对当下境遇产生合理效用的实践智慧。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它是理解的前提,也是历史发展的前提,更是人类精神文明延续的前提。这种基于“一体性”问题上传统与现实的关联,是通过一种本体论诠释学对话来完成的。本体论诠释学对话能够澄明存在、通达一种合理的理解。
结语
伽达默尔通过现象学的方法对《斐莱布篇》作了“指向‘事情本身’的解释”[3] 619,与海德格尔有别,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并非是存在遗忘的开端,恰恰相反,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贯穿于整个柏拉图哲学中。通过这种诠释方法,伽达默尔强调了柏拉图对话中的逻各斯要素,进而通过反思揭示逻各斯的诠释学意蕴——对话中的逻各斯运动能够使得对话双方达成共同理解,并且在现实境遇中具有一种实践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反思是在本体论范围内进行的,他所揭示的乃是澄明此在的本体论对话,而非技术理性统治下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其所体现的诠释学应用仍然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如果涉及一种真正现实的境遇,应用问题就必然会显现出其复杂性,甚至作为基础的逻各斯亦可能会受到扭曲。此时,方法论的丰富和完善就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当代诠释学家对于伽达默尔不重视方法的态度,虽然不能排除是其对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理论的误解,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不足之处。面对具体情况中的各种问题,维持理解的合理性就仍然需要依赖一定的方法。关于这一点,一些当代诠释学家如:贝蒂、赫施、利科尔等,都有做过深入的探讨。可见,丰富诠释学方法论是有利于诠释学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作为一种前提,追问“理解何以可能”对人类此在来说,亦是必不可缺少的。现代科学与诠释学并不是相互之间完全拒斥对方的理论,伽达默尔对《斐莱布篇》中的“一体性”问题所作的诠释学反思,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无疑会推动双方更好地向前发展。这条隐于“一体性”问题中的理解之路,显然为当代哲学的进步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章启群.伽达默尔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2]伽达默尔.哲学生涯[M].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Ⅱ[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M].余纪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5]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Gadamer.Plato’s Dialectical Ethics: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Relating to the Philebus[M].translated by Robert M.Walla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The Influence ofThePhilebuson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Hiding in the Problem of “Solidarity”
WANG Ju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Abstract:Gadamer’s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relating to The Philebus is the key of understanding hi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 ways of thinking of German philosoph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Philebus has an influence on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larifying the influence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reveal Gadamer’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on relating to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but also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Key words:Plato; Gadamer; The Philebu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6-0042-05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对话”与“实践智慧”——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古希腊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项目编号:2014yks117zd)。
作者简介:王骏(1990—),男,安徽池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西方诠释学。
收稿日期:2015-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