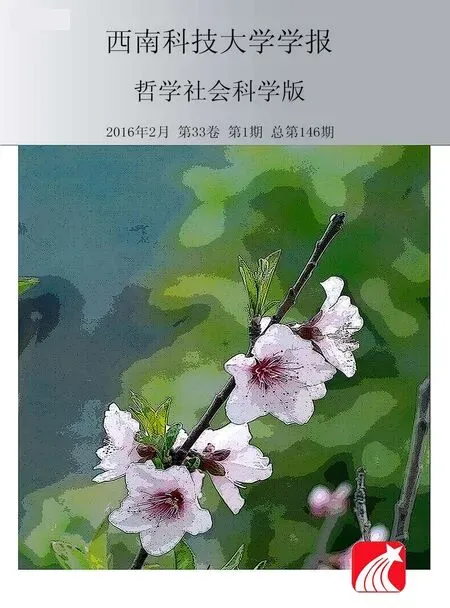论《萨勒姆的女巫》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
姚小娟 周天楠
(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8)
论《萨勒姆的女巫》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
姚小娟周天楠
(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
【摘要】阿瑟·米勒在《萨勒姆的女巫》中,深掘出“逐巫”事件的根源在于人性的沉沦,以此批判麦卡锡主义之下人性的沦丧。同时,米勒着力描述了主人翁普洛克托以良知对抗权威、自我决战群恐、名誉奋战报复的英勇行为,谴责了麦卡锡主义泯灭良心、麻痹思想、扼杀自我、蓄意报复的邪恶反动本质,同时向世人昭显了正义的力量。
【关键词】阿瑟·米勒;《萨勒姆的女巫》;麦卡锡主义;人性;正义
作为“美国的良心”[1]248的代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不仅仅是一名伟大的戏剧家,更是“美国文化的记录者”[2]Preface ix和“美国社会尖锐的批判者”[3]1。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米勒都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正如著名评论家克里斯多夫·毕格斯比(Christopher Bigsby)所称赞的“没有一位作家能像米勒这样如此成功的触动民族意识的神经”[1]248。米勒在其作品中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弊端也进行了解剖和猛烈地抨击。多格拉(O. P. Dogra)将米勒比作易卜生(Henrik Ibsen), 称其为“当代美国社会坚定严肃的批判者”[4]53。阿特马·拉姆(Atma Ram)也盛赞其戏剧作品“以现实的洞察力呈现出对时代的批判意识”[4]75。的确,米勒对美国历史文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故而艾卜哈·辛格(Abha Singh)称其作品为“美国社会意识的化身”[5]67。
米勒本人深信戏剧应是“反映社会的晴雨表”[6]Introduction xxiii。因此,他创作的所有戏剧都与美国历史中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从他最初的《吉星高照的人》到暮年之作《美国时钟》,都能窥见美国文化和社会万象:《全是我的儿子》揭露了资本家的罪恶;《推销员之死》剖析了美国梦的幻灭;《萨勒姆的女巫》讽喻麦卡锡主义的极权;《堕落之后》与《美国时钟》反省美国大萧条历史。对于米勒而言,“每次灾难都是鸟儿归巢的故事”[6] Introduction liv。
一、麦卡锡主义与《萨勒姆的女巫》
20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代来临。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是由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发动的美国全国性反共“十字军运动”。麦卡锡任职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促使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麦卡锡主义者则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乃至与其意见相左的人士。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5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数千名美国公民被指控为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进而成为被迫害、调查和审讯的对象。许多人因此失业,职业生涯被毁,甚至遭受牢狱之灾。在这种集体歇斯底里的氛围下,社会大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许多人尽管无罪,却发现自己被朋友们排斥,被公司解雇,甚至还受到一些极端“爱国者”的人身威胁。随后而来的恐惧,竟使得许多人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
“在美国,任何人只要在观点上不反动就容易被指控同红色地狱有密切联系”[7]183。许多党员、作家和导演,都被麦卡锡调查委员会传召,被迫承认有社会主义倾向并供认出其他支持者的名单。对此,米勒深感悲恸,“我吃惊地看到,那些多年的老相识从我身边走过时连头也不敢点,而且更使我震惊的是,我了解到存在于这些人中间的恐怖气氛是有人蓄意策划的,以致人们心里感到的尽是恐怖”[8]8。作为生活在麦卡锡主义恐怖时期的进步作家,米勒也受到了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1954年,美国政府拒绝发给他前往布鲁塞尔观看《萨勒姆的女巫》首映式的护照,1956年,他被多次传讯作为证人出席“非美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被要求供出共产主义支持者的名单。因他拒绝出卖朋友,1957年,他被指控“藐视国会罪”。1958年,在无罪释放的当天,米勒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正式声明:“我希望这一决定能对彻底根除国会委员会的过激行为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尤其是停止使证人互相告发老朋友和熟人这一不人道的做法”[8]9-10。
面对日益猖獗的反共歇斯底里情绪,米勒希冀借用文学的力量来做些改变,于是改编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AnEnemyofthePeople,1950),并创作了《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 1953)。在谈到麦卡锡主义对《萨勒姆的女巫》创作的影响时米勒说:“不仅仅是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激发了我,而且是更古怪更神秘的东西触动了我。因极右派所导致的政治的、主观的、有知识的运动不仅能制造恐怖,且能产生一种新的主观现实和逐渐发展成一种神圣共鸣”[8]8。1954年,米勒在《国家民族政坛》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缓和公众情绪的小建议》,抨击了集体歇斯底里的虚伪本质,对麦卡锡主义展开了更直接的、辛辣的讽刺。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以古讽今,对当时的压抑气氛和政治迫害进行了生动的、深刻地描述,尽力展示强权统治下的人心危殆、人性沉沦,以及人在与邪恶势力对峙中的失败和毁灭。与此同时,米勒通过对一些保持尊严、坦然面对死亡的正义人士的塑造,表现了他对良心和正义的坚定信仰。
二、麦卡锡主义和“逐巫”运动的根源
《萨勒姆的女巫》取材于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的“逐巫”案。该镇一群姑娘深夜来到树林里狂欢跳舞、裸体奔跑,结果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咬定是巫术作怪。于是,姑娘们开始了呐喊指控。一场以指控、逼供和株连为特征的“逐巫”行动在该镇全面铺开,众多心怀鬼胎之人藉此报复邻里之间的怨恨、羡慕、嫉妒以及过失,从而造成了恐慌、盲从和宗教狂热的可怕氛围。在这样的行动中,许多无辜的村民受到指控,被捕入狱,面临着绞刑和被剥夺财产的厄运。“逐巫”运动中,人人自危,人性沉沦,不少人为了活命,或者被迫承认犯有子虚乌有的罪名,或者陷入歇斯底里转而指控他人。
米勒察觉并发现,1692年萨勒姆镇“逐巫”案与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两大历史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被指控者公开接受莫须有的罪名;在公开场合放弃曾经的誓言和信仰;朋友之间互相揭发出卖;许多人纷纷堕入互相指控的无底深渊……对于《萨勒姆的女巫》的创作源头,米勒坦承:“毫无疑问,‘当时的氛围’为这一事件提供了真实的素材”[8]8。1969年,在接受罗纳德·黑曼(Ronald Hayman)的采访中,米勒承认他不可能写出另外一部历史戏剧,因为“想不起来任何别的时代会与我们的时代如此相关联”[9]8。
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影射了当时麦卡锡主义极权下的人性沦丧,竭力展示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报复、怨恨、猜疑、嫉妒……对于“逐巫”运动和呐喊指控的本质和源由,米勒在其戏剧中从人性沉沦的角度进行了充分的剖析。
“逐巫”运动爆发的首要原因是牧师赛缪尔·巴里斯的明哲保身行为。巴里斯是这场“逐巫”运动的始作俑者。作为小镇的牧师,本应虔诚、高尚和无私,而他却声名狼藉、猥琐自私。他本来知道姑娘们在树林里只是跳舞狂欢,但却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女儿像异教徒那样在树林里中跳舞”[7]163这一事实,以及担心他自己的敌人以此来对付他而唯恐自己的职位不保,于是尽力掩盖姑娘们“闹着玩儿”这一真相,将此推波助澜引导为巫术在作怪,从而成功点燃了逐巫事件的引信。以阿碧格为首“呐喊指控”的姑娘们到树木里跳舞狂欢裸体奔跑,只不过为了渲泄压抑已久的欲望。为了掩盖在森林中逾越了宗教和社会的准则和教条这一事实,她们屈从于恐吓和暗示的威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或性命,她们纷纷将矛头指向无辜的人。当阿碧格被审讯时,为了漂白自己的名声,她转而指控黑女仆蒂图芭为恶魔的工具。蒂图芭为了自保,承认巫术并供出别的无辜村民。其他的姑娘们为了掩盖她们违反了清规戒律这一真相,也纷纷呐喊出无辜村民的名字。米勒在其作品中写到,在萨勒姆,“为清除自己血液中的罪恶,人们将自身的罪恶转嫁给他人”[10]337。
“逐巫”行动的策划者是以托马斯·普特南为首的报复者。正如米勒所言,“‘逐巫’行动不仅是一种镇压行动,而且显然给每一个人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借以控告无辜的人为口实而极想坦白自己的错误和罪恶”[7]150-151。因“自己的名望和他的家族的荣誉让全村的老百姓给玷污了”[7]159,普特南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邻居们。在树林里狂欢后,姑娘们纷纷病倒,普特南认为这是“天意”,于是费尽心计将姑娘们生病引导为巫术在作怪。他先是一步一步地诱导牧师巴里斯相信是巫术在“对这些孩子下毒手”[7]160,接着蛊惑巴里斯“抓住时机,别等别人来指控您——自个儿就先把这事宣布出去。您发现巫术在作怪”[7]162,最后在姑娘们呐喊指控时,他以暗示的方式将要报复的对象让姑娘们指控了出来。正如米勒所言,“邻居之间的宿仇旧怨现在得以公开表露相互不顾圣经仁慈的训令而采取报复手段”[7]161。当然,“猜疑,不幸的人对幸福的人的忌妒啊,也在普遍报复的浪潮中爆发出来啊”[7]161。普特南太太因自己“生了8个孩子,只活了一个”[7]175而忌妒“一个孩子也不会丢,一个孙儿孙子也不会夭折”[7]176的吕蓓卡,并将仇恨的矛头对准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妇人,指控她犯了杀害自己婴孩的谋杀罪。
“逐巫”行动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争夺别人之物并将其据为已有。普特南掀起这一腥风血雨事件的意图在于争夺他人土地和产业。为了夺取村庄里最好的土地,他策划了多起有计划反对吕蓓卡和法兰西斯的活动。他让自己的小女儿在听审会上当场痉挛昏倒,并指控吕蓓卡撒出精灵鬼怪“在诱使孩子干些邪恶的勾当”[7]173。为了夺取他人产业,他阴险毒辣地怂恿女儿诬告乔治·雅各布和玛莎·考莱,企图吞并邻居的财产。阿碧格是这场“逐巫”行动的带头人。她迷恋普洛克托,但因无法成功地在普洛克托的生活及心中替换其妻子伊丽莎白的位置,阿碧格供出伊丽莎白为女巫并希望最终取代伊丽莎白。
因此,萨勒姆镇的“逐巫”行动只不过是一些别有居心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名声或地位,为了报复他人,为了强夺他人的财富而阴谋策划的诡计和精心设计的骗局。米勒本人也将“整个逐巫事件称作为诡计和骗局”[8]9,这也即是米勒对麦卡锡主义的控诉。
在《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影射以麦卡锡为代表的美国政府,揭露两次迫害运动类似的邪恶根源。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与“逐巫”案相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和亚洲相继出现,美国统治集团开始产生一种恐惧共产主义的心理。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巩固自己集团的统治,美国当权者纵容了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麦卡锡放肆地煽动反共舆论,伺机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以及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进行报复、恶意诽谤和无情迫害。米勒淋漓尽致地披露“逐巫”行动和麦卡锡主义的根源在于人性的沉沦,同时也批判了麦卡锡主义极权下人性的沦丧。
三、与麦卡锡主义极权与“逐巫”恐慌的斗争
尽管米勒深谙“逐巫”事件和麦卡锡主义的黑暗本质,但米勒并未被其带来的恐慌所吞噬。面对国会的多次审讯,他始终坚守良知,坚持自我,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名声。作为一位有良心的戏剧家,米勒“希望他的戏剧能打动别人”[7]49。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潜心刻画了坚守良知、坚持自我、勇于对抗权威、敢于奋战极权的勇士普洛克托,通过他甘于牺牲的英勇行为,痛斥了麦卡锡主义泯灭良心、麻痹思想、扼杀自我、蓄意报复的邪恶反动本质,同时向世人昭显了正义的力量。
(一)良知对抗权威
米勒之所以选择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创作这部戏剧,在《阿瑟·米勒戏剧集》前言中,他解释原因在于要解开“出卖良心这一谜题”[7]48。对于人文主义者米勒而言,“良知会告诉人们应该做的或不应该做的”[7]54,这也是他绝大多数戏剧的中心主题。在《萨勒姆的女巫》中,是听从良心的召唤还是服从权威是这部戏剧的主要争论。听从良心意味着死亡或监禁,服从权威意味着出卖良心和他人。在良心和权威的天平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权威而违背良心出卖朋友和亲人。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极力描述了个人良知和权威淫威的激烈冲突。评论家大卫·萨夫兰(David Savaran)注意到,“通过自己的理解,米勒深刻地谴责了那些为了确保自己稳固的政治和文化统治,而傲慢且随意行使自己权力的权威人士们”[11]86。
在戏剧的开始,米勒评论道:“萨勒姆居民为了良好的意图,甚至是严正的意图而发展了一种神权政治,一种政教结合的力量,其作用就是要保持社会上的一致性,不让任何分裂现象出现”[7]150。在这种政教结合的权威之下,“对现存的制度有一丝反抗的人士几乎都被迫将自己的罪恶转嫁到指控他人或恶魔化他人”[11]90,任何有个人自由思想的人都会受到排斥。本剧的主人翁约翰·普洛克托是这种政教权威的反抗者。他尊重品质高的人如伊丽莎白、吕蓓卡、法兰西斯和霍普金斯,而不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因此他频频与那些权威人士发生冲突。当听到普特南命令牧师巴里斯寻找巫术作怪的种种迹象时,普洛克托呵斥道:“你没权对巴里斯先生下命令。我们这个社会是靠记名而不是靠土地多寡来投票选举的”[7]176。对于宗教的权威人士牧师巴里斯,他解释不进教堂的原因在于牧师所讲的都是地狱之火和该死的诅咒,而且从牧师身上看不见上帝的光辉。面对巴里斯对于他没有自由来决定宗教内容时,他反抗道:“可我认为可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7]178。当巴里斯提到教区有派系之争时,普特南称之为反对当局,普洛克托便声称“真格的,那我倒要去找一找,也想参加”[7]178-179。他接着质疑以恐吓来强迫的权威,“我讨厌这里的‘当局’那股臭味儿”[7] 179。
“逐巫”行动爆发伊始,普洛克托便称其为“一场邪恶的鬼把戏”[7] 205和“骗局”[7]205。没能及时在法庭上揭穿骗局,他感到自己良心的指责。在妻子因被阿碧格诬陷而遭到逮捕时,普洛克托从执法人手中夺过副总督的拘捕令并将其扯碎,对当局直接进行挑衅。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时,他誓言要当众拆穿姑娘们的谎言。当法官丹佛斯同意对伊丽莎白缓刑一年并以此作为条件让他放弃申诉,他坚定地回答“我想我不能放弃”[7] 211。
在“只有忏悔或撒谎才能活下来”[11]86的审讯中,法官们以他的生命来威胁他忏悔时,普洛克托因为愤怒而保持沉默,拒绝撒谎。当被恐吓供出他人名字时,他拒绝说出任何人的名字,“我只能交待自己的罪恶,我不能瞎咬别人,我不会血口喷人”[7]305,并直接挑衅最高权威者法官丹佛斯,“甭想利用我!”[7]307同时表明自己对良知的坚持“我有3个孩子—我如果出卖朋友,还怎么教导我的孩子在人间应该心胸坦荡,为人正直呢?”[7]307。最终,米勒通过普洛克托的良心之举向世人表明:“人类良心才是最终的权威,只有良心才能决定其它所有事情。事实上,即使法律与良心发生冲突时,触犯法律也在所不惜”[11]98。米勒自己也将《萨勒姆的女巫》的真正内在主题确定为“良心与人格、不朽的灵魂以及名誉同在”[12]94。
在麦卡锡主义期间,数以万计的人被列进“黑名单”,遭到非法审讯。面对当局的恐吓和胁迫,许多人经不住时代的严峻考验而出卖良心和他人。著名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著名导演伊莱·卡赞(Elia Kazan)以及演员李·盖伯(lee J. Cobb)都纷纷“坦白”出卖他人。米勒对此痛心疾首,在《萨勒姆的女巫》中,他通过主人翁普洛克托挑战权威坚守良心的艰苦斗争,批判了麦卡锡主义极权统治泯灭良心的本质。
(二)自我决战群恐
米勒希望他的剧作能够揭露“公众的恐惧能使人偏离良心和自我这一罪恶”[13]61。在1692年的萨勒姆,恐惧弥漫着整个小镇,人们对荒蛮隐秘的边疆、神秘的自然现象和不可控的人世悲剧都充满了无知的惶恐。《萨勒姆的女巫》伊始,姑娘们莫名的病症引发了人们的猜疑和恐惧,姑娘们在法庭上集体歇斯底里的指控更使得全镇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乡镇里出现一种对这个法庭极大的恐惧心理”[7] 255,继而这种可怕的恐惧开始麻痹人们的思想,全镇人开始陷入相互指控的无底深渊。
恐惧麻痹思想也是该剧的另一大主题,同时也是米勒对麦卡锡主义的另一控诉,“人心中的恐惧是被蓄意策划的、经有意识改造的,以致人们所知道的只有恐惧……恐惧渗透于《萨勒姆的女巫》戏剧的字里行间”[8]8。在生或死的恐惧面前,许多人背离了自我而选择了妥协忏悔。是受制于恐惧还是坚持自我是这部戏剧的另一主要冲突。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着力刻画了普洛克托敢于坚持自我战胜内心恐惧和罪恶的英勇行为。
普洛克托“是个罪人,一个不仅违反当时的道德风尚、而且违背自己想象中的体面行为的罪人”[7]166。因对阿碧格动过邪念,他犯下了奸淫罪。“逐巫”行动爆发时,当伊丽莎白催促普洛克托去镇里告诉法庭真相时,普洛克托因为自己的罪恶而迟疑犹豫,惟恐说出真相,阿碧格会控告他犯了奸淫罪,自己因此身败名裂。在要求玛丽·沃伦去法庭讲出事实真相时,他决定抵制恐惧,撕下伪装做真实的自己,“上帝和魔鬼正在我们的脊梁背上搏斗;我们原来的一切伪装都给剥去了……我们还是原来那样儿,只不过现在个个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7]237-238。而且他已经准备鼓起勇气挑战自己的罪恶。在法庭上,他坦白了罪恶并承认自己是犯了奸淫罪的好色之徒,藉以希望法官们认识到阿碧格邪恶的本质以及认清整个事件是场骗局。面对执法者的执迷不悟,他疯狂了,怒吼着呼唤着撒旦魔鬼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给那些在一项摆脱人们愚昧无知的庄严事业前畏缩退却的人准备的,他们就像我曾经畏缩过那样,就像你们的黑心眼里现在明明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却畏缩退却那样”[7]280-281,再一次表明自己将不会惧怕恐吓。
普洛克托深陷牢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当妻子伊丽莎白前去劝说,得知有一百多人招认时,他也有所动摇,“我一直在想干脆顺他们的心意,向他们交待算了”[7]299,“我不能像一名圣徒那样登上绞刑架。这是一场骗局。我不是那种人。我的诚实到了尽头;我并不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向他们撒这个谎,早就不算什么堕落了,而且对谁也不会有损害”[7]299,他甚至一度对自我都产生了质疑,“约翰·普洛克托是个什么人,约翰·普洛克托是个什么玩艺儿?我认为这样做很诚实,我想是的;我不是圣徒。让吕蓓卡像个圣徒那样升天吧;对我来说,那是欺诈!”[7]301-302于是他开始要进行忏悔,然而在被要求供出其他人的名字时,他拒绝作不实的证词去控告他人,最终实现了自我的升华,“因为我现在确实认为我在约翰·普洛克托身上看到了一点点正直的品德。虽然它不够织成一面旗帜,却清白得足以不跟那些狗杂种狼狈为奸,同流合污”[7]301-302,于是无所畏惧、大义凛然地选择了死亡。正如伊丽莎白所证实,“他现在保全他那正直的美德啊”[7]310,而且谁也剥夺不了他的美德。米勒本人也评论道:“他肉体虽然被消灭了,但获得了自己的灵魂,也可以说,他成为自己的反叛者”[14]158。
1950年至1954年,麦卡锡主义达到了歇斯底里的顶峰。在这期间,不少人被指控充当“间谍”或犯有“颠覆”罪而遭到监禁;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因怀疑“不忠诚”而被强迫辞职。整个国家上自知名人士下至普通百姓都受到了麦卡锡的迫害。在这种法西斯式的恐怖笼罩下,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因惧怕而选择妥协。在文艺界,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陷入保守。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谴责了这种白色恐怖麻痹思想扼杀人类自我的累累罪行。
(三)名声奋战报复
在麦卡锡主义泛滥期间,米勒曾多次被调查委员会传讯要求供认告发他人。对此,米勒断然拒绝,“我是在维护我自己的尊严,而且将来我还要这样做,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提及别人的名字,给他带来麻烦……我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无法对别人负责”[1]191。作为一位执着于书写人类道德需求和名字尊严的作家,那种“出卖别人名字”的无理要求让米勒深感痛恨。在1953年1月25日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采访中,米勒说到,“没有人想成为英雄,生活中,人们会放弃许多东西,比如,希望、梦想、雄心壮志、信仰、爱好、自尊。但对每个人而言,有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是需要保留的,如核心信念、身份、名声。如果放弃了这些,那他就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自己了”[8]55。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凸显了个人对名声保护这一主题。
整个“逐巫”事件的本质,其实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蓄意报复。仇恨报复在萨勒姆作祟,普遍的报复竟然成了法律。牧师巴里斯因为报复那些对自己不恭之人而推动了这一事件;地主普特南因觉得村民玷污了家族荣誉和名声而鼓动了捉巫行动;阿碧格因为仇恨伊丽莎白而点燃了导火索。在整个“逐巫”行动中,“私人报复正通过这种作证在加紧活动呐!”[7]274。戏剧中,米勒从多方面戏剧化了维护名誉与抵抗报复这一激烈冲突。
在阿碧格的报复下,伊丽莎白入狱。为了尽快告诉法官真相,让人们意识到“逐巫”事件不过是骗局,尽管普洛克托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但他顶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坦白了自己与阿碧格的奸情,给自己的名字抹黑,“我给我的名誉制作了一口丧钟!我给自己的好名声敲响了丧钟”[7]270。在被要求供认其他人的名字时,他断然拒绝,“我不想破坏他们的名誉”[7]305,往他们脸上抹黑。虽然忏悔了,但他拒绝在证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这是我的名声!因为我一生不可能再另有别的名声!因为我撒了谎,还在谎言书上签了字!因为我在那些登上绞刑架视死如归的人面前连粪土都不如!我怎么能名誉扫地地活下去?我已经把灵魂交给你,别再碰我的名声!”[7]308,随即将忏悔书扯得粉碎,最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绞刑架,从而以生命的代价保护了自己的名声。“对于米勒而言,一个人的名声有着神奇的力量:即是内心正直的外在标志”[11]98。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动势力以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对付与他们政见不合之人,许多作证之人也借机报复他人。因此,蓄意报复和玷污他人名声是麦卡锡主义的又一邪恶本质。在《萨勒姆的女巫》中,通过普洛克托宁死而不屈的名声之战,米勒抨击了麦卡锡主义反动势力蓄意报复的秉性。
结语
在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米勒对人性沉沦的事实深感悲恸,于是借助文学的魅力剖析麦卡锡主义的邪恶根源。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借古讽今,采用犀利的舞台语言和激烈的戏剧冲突,批判了人性中明哲保身、伺机报复、攫为己有的邪恶品质,并以此影射麦卡锡主义兴起和泛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沦丧。麦卡锡主义泛滥时,人们出卖良心、舍弃自我和尊严、背弃名声,米勒对此深恶痛绝,于是精心塑造了坚守良心、坚持自我、维护名声的理想人物普洛克托,并通过这位勇者以良知对抗权威、以自我奋战群恐、以名声抨击报复的种种胜利,抨击了麦卡锡主义泯灭良心、麻痹思想、扼杀自我、蓄意报复的邪恶反动本质,向世人昭显了正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Bigsby, Christoph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Drama 2:Tennessee Williams, Arthur Miller, Edward Albee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Otten, Terry. The Temptation of Innocence in the Dramas of Arthur Miller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3]Carson,Neil.Arthur Miller [M].London:Macmillan,1982.
[4]Ram, Atma. Perspectives on Arthur Miller [M]. New Delhi: Abhinav Publications, 1988.
[5]Singh, Abha. Contemporary American Drama: A Study in the Plays of Tennessee Williams, Arthur Miller and Edward Albee [M]. New Delhi: Chaman Offset Printers, 1998.
[6]Miller Arthur. The Theater Essays of Arthur Miller [M]. Eds. Robert A. Martin, Steven R. Centol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Inc., 1996.
[7](美)阿瑟·米勒.外国当代剧作选4[M].陈良廷,梅绍武,郭继德,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8]Smith, Leonard. Macmillan Master Guides: The Crucible by Arthur Miller [M]. Houndmills: Macmillan, 1986.
[9]Hayman, Ronald. Arthur Miller [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2.
[10] Miller, Arthur. Timebends: A life [M]. New York: Penguin, 1995.
[11] Bigsby, Christoph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thur Mille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Miller, Arthur. Arthur Miller’s Collected Plays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7.
[13] Griffin, Alice. Understanding Arthur Miller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14] Miller, Arthur. Conversation with Arthur Miller [M]. Ed. Roudane, Matthew C.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7.
Miller’s Criticism of McCarthyism inTheCrucible
YAO Xiao-juan, ZHOU Tian-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Heilongjiang, China)
Abstract:In The Crucible, Miller explores the root of Salem Witch Hunt to be the fall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an insinuation of the decline of human nature during the McCarthyism times. By striving to depict the hero Proctor’s bravery in defending his conscience against authority, his identity against mass fear and his name against revenge, Miller denounces McCarthyism’s evil nature of selling conscience, paralyzing thought, stifling self-pursuit and vandalism, and simultaneously shows the power of justice to the world.
Key words:Arthur Miller; The Crucible; McCarthyism; Human Nature; Justice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5)06-0047-06
基金项目:2013年东北石油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阿瑟米勒戏剧作品中美国文化和政治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QN215)
作者简介:姚小娟(1979—),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收稿日期:2015-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