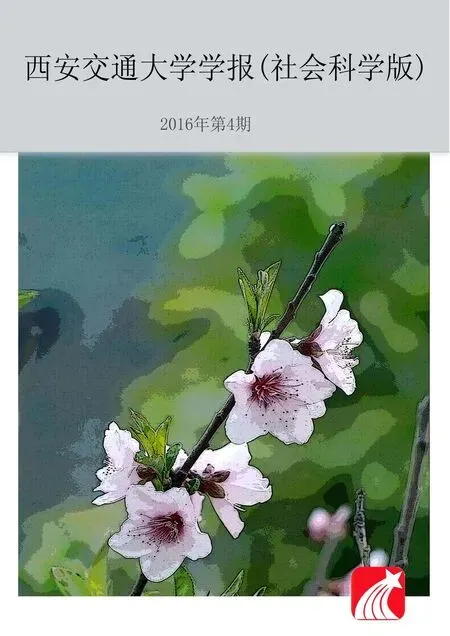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
胡德胜,欧 俊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
胡德胜,欧 俊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从义务的来源来看,有我国国内、东道国、国际层面以及其他一些非正式的环保义务要求。就争端解决的运行逻辑而言,选择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责任认定结果往往有所不同。中企预判自己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需要立足于环境争端的公正合理解决,明晰应该参照适用的环境标准、东道国生态环境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投资行为的真实生态环境后果和归责原则。
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环境责任;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而言是一项“行动规划”或者“发展战略”,对国际社会而言是一项“合作倡议”。它的核心语义是“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1]538我国政府在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表示共建的是绿色丝绸之路,提出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要求中企在“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投资贸易突出生态文明理念。这是将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2]。
生态环境保护是供给公共物品;从善治的视角来看,它需要多中心协同治理。企业是组织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实体,其直接投资行为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出现经济学上的负外部性,由此产生了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切实关注和认真解决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是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关键。基于中企在“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直接投资形势及其存在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本文讨论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认定,提出中企应对直接投资环境责任问题的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论方面,将直接投资发展转型、绿色发展、环境善治等理论综合运用于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拓展了理论维度;应用方面,讨论了中企这类环境责任的认定问题,提出了妥善的应对策略,可以为政府、企业、裁判机构等提供参考。
一、中企对外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一)中企对外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重新融入世界之门,我国正在进行从单纯引进来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转型。目前,我国既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也是最大输出国之一[3]41。一方面,这说明我国具备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业务、参与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双重身份”表征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巨变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国际贸易、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开放水平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存在正相关关系[4]397。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显著地提升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起步比较晚、增长速度快、体量巨大、国有企业主导、分布行业和区域比较集中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特点。
中企走出去,受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情势制约。从国内看,我国已经进入到“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目标与行动规划。从国际层面看,全球化在深入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区域一体化、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善治等理念、机制、规范业已形成并在不断深化与完善。“一带一路”的提出,综合体现了上述语境与现实,中企的直接投资参与需要准确理解其中的内涵。
我国的走出去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企业走出去、行业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5]77。从比较竞争优势理论视角看,抓住各个阶段的竞争优势及关键点,对成功走出去至关重要。对外直接投资是将自身比较优势在其他区域实现,或是在其他地区寻求资源以完善价值链,或是为特定目的建立战略联系,其是一个有着多元价值考量的综合实力竞争过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有了规模上的增长,但是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国际化水平低、绩效指数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日益暴露[6]39-41。对生态环境公益目标以及生态环境风险关注不够,是中企既往对外直接投资的重大缺点,不适应性越发明显。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64个国家和地区的累计直接投资额达到1612亿美元,约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0%[7]。在地域分布上表现为“东南亚>西亚和中亚>南亚>中东欧地区”。在产业分布上表现为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8]565-566。从既有的直接投资地域和产业分布上分析,它们表现出高度的生态环境敏感特性。我国国内目前提出的产能合作、能源革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等政策目标导向,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直接投资行为模式的塑造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见的是,这类直接投资未来仍将面临较高的生态环境风险。
(二)中企对外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首先,生态环境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支撑和基础。一个地方的发展应该也需要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情势,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和直接投资必须考虑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其次,生态环境保护正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价值取向。例如,欧盟是世界生态环保领域的领跑者和生态环保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制定有严格的环境标准、法律法规。亚洲许多国家由于过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因此正在正努力寻求改变。再次,生态环境合作(供给公共物品)是“一带一路”建设大有可为的重要方面。“‘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在这一平台上的诸多跨国活动具有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属性(如沿线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能源合作等)。”[9]142最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协同效应,其能够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其他事项发展。生态环境风险是合作项目推进中的重大障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从根源上杜绝许多问题。
然而现实却是: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成绩显著,但是其中不可持续发展的方面逐渐显露。首先,直接投资的质量并不高。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 较低(小于1),这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10]41。从行为模式上看,虽然正朝着“价值链延伸型”转变,但是“在高风险地区的资源寻求”仍是重要方面[11]33。其次,直接投资主体在结构上单一。以国企为主的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一方面反映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民营企业之国际化经营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显示出很强的国家组织动员或者“政治”属性 。最后,对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关注不够。重视“上层路线”而忽视“民间路线”的传统范式,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受了许多重大损失(如缅甸的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搁置事件)[12]37。
直接投资经营的绿色发展是中企关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逻辑前提。绿色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升华。后者的提出并获得广泛认同,体现着人类理解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13]38。绿色发展要求在一系列限制条件下满足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最大化[14]46。绿色发展既是一系列理念,也是一系列行为模式。在上层建筑层面,生态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具有根本性的广泛的国家目标或者政策[15]。在市场主体层面,它要求企业合理平衡追逐利润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直接投资表面上看是简单经济逻辑的外化,但是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创造价值、服务发展、永续经营才是其更为本质的内涵。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属性显现,缺乏约束或者集体统筹的自利行为会导致“公地悲剧”或者“零和博弈”。从中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遭遇的风险上检视,我们视乎还没有摆脱“零和”的思维;在全球各个领域整合力量加剧以及一体化治理加深的背景下,中企直接投资经营需要从实际行动上转向绿色发展路径,在实际效果上出现绿色发展的效果。
二、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认定
法律上的狭义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违反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本文所研究的环境责任是广义上的,不仅包括国际法、国际习惯、国际软法、相关国内法及政策等规范以及约定所确立的环境责任,而且包括基于良心、正义、担当等自觉承担的环境责任。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涉及多个法域,容纳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设计,有着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或者状况,从而导致环境责任的认定充满不确定性。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面临来自我国及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监管,一方面,环境责任的认定需要澄清环境义务的来源;另一方面,需要了解不同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行逻辑。
(一)环境义务的来源
在法理上,责任是义务的前提;但是就实在法而言,法律义务则是法律主体承担责任的前提。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其环境义务来源多样,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国内和国外(国别、地区、国际)的、静态和动态的 。
首先,我国对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一系列生态环保义务要求。如前所述,我国过去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走的多是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许多中资企业不注重社会和环境责任,由此招来了污染避难所 、中国环境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指责[16]630。随着国内发展方式转型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提出,虽然监管要尊重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促进“走出去”,但是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监管势所必然。为鼓励企业“走出去”,国家放松了许多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措施,然而在金融信贷、保险、外汇使用、国家担保、国资管理、税收、项目招投标等领域,仍有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义务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还发布了专门的导引性或者规范性文件。例如,商务部联合环保部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2013年);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贸易领域不良信用记录试行办法》(2013年)等。生态环保将是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立法的重要关注内容。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由于前述的生态环境敏感特性,来自国内的生态环保义务要求在许多方面还可能增加、趋严。
其次,东道国和国际层面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系列生态环保义务要求。“一带一路”国家众多,涉及多洲的不同地区,它们在生态环境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先性以及相关法治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而在生态环保义务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要求不尽相同。例如,欧盟(不论其自身还是其成员国)一直是国际环境政策的领导者,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环保义务要求较多而且严格[17]335。而东欧和亚洲许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环保义务要求较少、较低,有的甚至没有要求。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生态环保要求被许多区域合作机制、机构纳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生态环境治理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制度和规范体系[18]97,国际生态环保条约义务对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了直接或者间接规制。
最后,还存在一些非正式的外商直接投资生态环保义务来源。对非正式的来源重视不够,是中企对外直接投资过去遭遇许多重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中企韩国济州岛投资项目于2014年6月被叫停,中柬合作大坝于2015年2月被柬埔寨首相下令暂停建造。非正式的生态环保义务来源主要指来自居民、当地社区、公益组织、行业自治机构、政治压力集团等的环保义务要求。例如,由于缅甸境内铁路沿线居民及公益组织的反对,中缅铁路项目从2014年7月以来搁浅而不能实施。如前所述,对外直接投资要走“双层路线”,不仅要取得政府许可,还要获得社会许可。环境权、环境邻避运动、环境善治等的兴起,给“下层”主体的诉求提供了通道和“合法性”。虽然此类义务没有公权力强制的表象,但是在很多情形下会转化成公权力行为(如政府迫于公众压力而叫停项目)。
值得指出的是,需要动态辨证的看待环保责任义务来源。企业是市场主体,其经营决策要服务多重价值目标,环境责任义务的考量需要适当衡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环境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是客观事实。这里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只要中企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和路径,尽到“谨慎注意”义务,环境风险基本上是能够克服的[19]109。同时,环保责任义务的来源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中企要有所预见并及时回应。国际直接投资规则正在重塑,“支持可持续发展及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已成为共识;在新一代双边或多边直接投资条约中纳入环境条款已成为新常态[20]110。我国和“一带一路”其他国家过去签订的直接投资条约很少涉及环境议题,但是在这些条约更新及重新谈判缔结过程中,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权、投资者和投资国的环境保护义务、不得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直接投资等事项将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未来的直接投资规则中的环境保护内容必然会大量增加[21]92-93。
(二)环境争端的解决
由于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和价值判断准则,其责任认定结果往往有所不同,乃至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争端解决,国际社会在双边或多边层次上形成了丰富的制度化安排(如WTO、OECD、UN、EU、BIT、ICSID等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且在不断改进、演化[22]640-656。一般地讲,投资者私人之间争端解决方式有协商、调解、司法手段、仲裁等;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争端解决方式有司法手段(当地和国内救济)、仲裁、寻求外交手段保护等。随着国际直接投资争端性质由“政治性争端”向“管理性争端”的转变 ,国际仲裁日益成为较为重要和主要的争端解决方式23]153。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引发的环境争端,往往牵涉多方利益主体,解决的方式、路径多元。
着眼于环境争端解决,对于环境责任,中企需要明晰下列3个重点问题。
一是应当参照适用的环境标准。根据市场逻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投资者(特别是污染型产业)受市场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倾向于找寻“污染避难所”,即环境保护领域的“逐底竞争”现象[24]216。环境标准(正式义务来源)是影响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做出了放宽环境标准的较多特殊规定;从法律上讲,遵守这些放宽规定是不应该被追责的。但是,实践中的难题是环境标准的缺失或者模棱两可以及要求较低。环境标准的缺失会使中企形成误判;而根据环保义务的来源分析,中企仍然可能被追责。环境标准的模棱两可则留下了任意解释的空间,导致责任认定存在不确定性。环境标准较低可能诱发民众或者反对党派的(严重)抗议或者冲突,实质上很难带来责任风险的降低。2015年9月秘鲁邦巴斯铜矿抗议事件就是例证。环境标准还决定着中企具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以什么方式承担责任等。
二是东道国环境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东道国出于生态环境保护目的,对直接投资进行规制的权力已经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可[25]。在国际直接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仲裁机构往往要求“只有东道国政府的环境规制措施程序正当合法、符合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符合非歧视、比例原则和善意要求,且有科学报告为依据,才能够得到仲裁庭的支持。”[26]25从程序正义上讲,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不能仅由政府自己证成自身行为,一个中立的争端解决机构十分重要。基于前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正在考虑取消相关条约中投资者诉东道国的国际仲裁机制;这无疑会对企业责任认定形成影响。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和规制有一种互动关系,投资可能带来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而东道国的规制却是推动负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路径。因此,公平公正地判断东道国环境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离不开上述视角。
三是企业直接投资行为的真实环境后果和归责原则。争取和维护正当权利是对外直接投资经营中应当坚持的原则。讨论或者研究中时常存在“打稻草人靶子”(树立虚假目标进行攻击)的谬误,直接投资环境责任的认定领域也有类似现象。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泛政治化、地缘政治博弈等的出现或者加剧,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产生了一些“虚假”环境责任争端。例如,2015年斯里兰卡新政府以存在环保问题叫停了中企承建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客观、科学的评价对外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影响有助于破解上述难题。从争端解决程序上看,企业直接投资环境责任认定,涉及到归责原则问题。“归责原则既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也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事由、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等。”[27]5无过错、过错和公平责任原则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常见类型。从演化的趋向上看,“无论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对于环境侵权责任的归责,都经历了从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或混合责任的转变。”[28]136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在一些特殊类型案件中的责任认定不以加害人过错为必要条件,是当今环境民事责任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原则。
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环境责任认定要遵循上述逻辑与路径。“一带一路”环境标准体系复杂,而且有关国家环境规制措施日益趋严,囿于中企直接投资的环境敏感特性,争端在所难免,责任认定要考虑不同机制的运行逻辑。
三、中企解决直接投资环境责任问题的策略
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不仅事关企业的自愿、自律、自治问题,而且还关系国家干预、跨国治理、社会强制等问题[29]3。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既是我国国内问题(企业治理、发展转型、法治),也是国际问题(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治理)。从企业自身角度看,需要做好如下4个方面:
(一)转变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理念
根据路径依赖(制度惯性)原理,如果中企把国内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的思维与模式带到国外,不仅对企业自身发展不利,而且对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以及提高国际领导力极为不利。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明确的精神旨归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如果发展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环境保护则不符合上述要求。中企布局“一带一路”,不仅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面向,而且还有国家使命的面向,要求其合理决策。“一带一路”国家虽然面临不同的发展优先,但是从绿色发展及环境保护公共物品属性上看,企业要重视其环境责任。
为了切实转变投资经营理念,中企需要做到如下3点。一是破除侥幸、投机、搭便车心理。环境是公地,如果缺乏制度或其他形式的强制安排,会出现“公地悲剧”现象[30]1247。中企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要把自身命运同当地命运联系起来,打造命运共同体。二是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直接投资经营需要平衡好当前和长远利益,兼顾企业自身和当地的发展目标。三是打造自身综合竞争实力。要进行正当竞争,通过提升自己包括环境风险管理在内的各方面能力,来推动自身和东道国的协调发展。
(二)切实履行勤勉谨慎义务
国际市场波诡云谲,潜藏各种风险,中企走出去要勤勉谨慎。如前分析,以国企为主的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使中企遭受了许多额外审查和严苛要求。例如,2015年2月25日,菲律宾基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中止了同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的合作。因此,中企必须在企业运营思维(市场)、治理方式以及服务目标上有所改进。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根本上讲是要与它们和谐共生,环境是支撑基础,也是消弭冲突、矛盾的关键点。环境责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风险,另一方面是促进企业自我完善的机制。企业通过勤勉谨慎工作,可以化解部分环境风险及减轻不必要的环境责任(如勤勉谨慎义务是仲裁庭的重要考察内容)。
为了切实履行勤勉谨慎义务,中企要从如下4个方面入手。一是尽职调查,全面评估。对东道国的环境政策法律以及政情、社情、民情等进行充分调查;对国际、区域的环境政策及发展取向进行充分掌握。二是严格遵守有关直接投资的环境规范。项目开展要进行科学的环境影响评价,发生环境事故要及时通报和处置。三是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机制。将环境风险纳入风险控制管理,对重大决策的环境影响进行审查。四是建立信息披露机制。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许多争端的根源,及时向居民、社区、公益组织、政府等披露信息,有助于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及消解矛盾。
(三)合理利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环境纠纷是产生环境责任的重要诱因,如前分析,不同纠纷解决路径产生的责任结果不同,因此,具体选用何种路径要综合权衡。具体来讲:首先要区分纠纷的性质。民事纠纷可以通过协商、诉讼、仲裁等解决;行政纠纷可以寻求外交、诉讼、国际仲裁等解决。其次要考虑要达到的目的和利益取舍。很多时候纠纷解决本身不是目的(如通过激烈对抗方式获得胜诉,而导致发展基础丧失则得不偿失),通过纠纷解决实现多重目标及利益才是目的。最后要考虑实施的便利性和成本。采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耗费的人力、物力及其他隐性成本不同,理想的路径要考虑可获取的资源及成本约束。
值得指出的是重视社会许可机制对降低企业环境责任风险意义重大。随着公民社会、环保运动等的兴起与发展,公众对各种直接投资项目的影响日益巨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超越传统狭隘的视角,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的发展问题,以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信息交流机制、参与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把企业的发展同当地的发展联系起来,企业才能走的更平稳更可持续。最后,企业加强自身的纠纷解决能力建设也十分重要。
(四)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方式
中企走出去遭遇的寻找“污染避难所”、资源掠夺、环境倾销等指责,一定程度上讲是其经营缺乏创新的表现。解决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要靠直接投资经营方式创新。首先,中企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及客观评估自身能力。只有明确了自身定位及了解了自身能力,才能够选择最佳的直接投资运营方式。例如,通过跨国并购往往能够获得被并购企业在当地的大量资源,但是要求较高的管理水平和整合能力;企业自己设企建厂也许更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31]121。其次,要深入了解行业和市场情况。如能源、矿产、制造、建造等行业环境风险相对较高,而批发零售、金融服务等行业则环境风险较小。最后要强调合作和共赢。一方面要考虑同当地利益相关者合作,充分利用地方人才、资源和知识;另一方面要考虑同行业领先者(甚至竞争对手)进行合作,以求变不利为有利。
四、结语
共建“一带一路”是促进区域乃至国际和谐发展、全球绿色发展的重要倡议,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给我国及中企推动、融入和深化国际合作带来了大量机遇。中企走出去经历了一个相对粗放的发展过程,对生态环境风险关注不够是其重大缺陷之一。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必不可少的要义和内涵。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基础,而且还是大有可为的合作方面。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指引下,中企需要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需要立足于命运共同体的共建,树立共赢的思维和路径,积极履行自身的社会和环境责任。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标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企对其直接投资环境责任认定的预判需要从实际出发,综合考量其应该承担的环境义务以及不同争端解决机制的逻辑运行逻辑和价值判断准则。在环境义务上,中企面临着来自我国国内、东道国和国际层面以及其他大量非正式的生态环保义务要求。在多元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厘清中企应当参照适用的环境标准,检视东道国环境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客观、科学地评价相关行为的环境后果以及确定归责原则是重要的内容。应对直接投资中的环境责任问题,中企需要转变过去的不可持续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理念,切实履行勤勉谨慎义务,合理利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方式。作为市场主体的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要平衡好各项利益与目标,走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世界走向生态文明。
[1] 刘卫东.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5):538-544.
[2] 王会芝. “一带一路”绿色建设充满生机[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2-23(01).
[3]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R]. Geneva: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5.
[4] ZHANG X, DALY K.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11, 12(4):389-398.
[5] 杨欢, 吴殿廷, 王三三. 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阶段性及其策略研究[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6):75-85.
[6] 刘宏, 苏杰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J]. 国际经济合作, 2014, (7):37-41.
[7] 商务部新闻办公室.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2015-07-07)[EB/OL]. [2016-03-01].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507/20150701036542.shtml.
[8] 郑蕾, 刘志高.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5):563-570.
[9] 黄河.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6):138-155.
[10] 刘宏, 苏杰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J]. 国际经济合作, 2014(7):37-41.
[11] KOLSTAD I,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26-34.
[12] 李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海外社会责任战略[J]. 国际经济合作, 2014(6):35-38.
[13] HOPWOOD B, MELLOR M, O′BRIEN 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app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5, 13(1):38-52.
[14] ROGERS P P, JALAL K F, BOYD J A. An 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London:Earthscan, 2012.
[15] 胡德胜. 论我国能源监管的架构混合经济的视角[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1-8.
[16] MARCCNI 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Europe:is China a pollution have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20(3):616-635.
[17] KELEMEN R D. Globalizing European Union environmental policy [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0, 17(3):335-349.
[18] NANDA V P, PRING G 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M]. 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2.
[19] 刘恩媛.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J]. 理论与现代化, 2015(6):108-112.
[20] 韩秀丽. 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J]. 国际问题研究, 2013(5):103-115.
[21] 刘正. 中国国际投资协定的环境条款评析与完善思考[J]. 法学杂志, 2011(12):90-93.
[22] BREWER T 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the evolving regim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Law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994, 26:633-672.
[23] 徐崇利. 晚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之评判:“全球治理”理论的引入[J]. 法学家, 2010(3):143-153.
[24] DONG B, GONG J, ZHAO X. FDI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pollution haven or a race to the top?[J].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2012, 41(2):216-237.
[25] 胡德胜.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WTO规则及私有化或市场化[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67-70.
[26] 韩秀丽. 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看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措施[J]. 江西社会科学, 2010(6):22-27.
[27] 王利明.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以救济法为中心的思考[J]. 中国法学, 2008(4):3-15.
[28] 曾祥生, 赵虎.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6):135-139.
[29] BRAMMER S, JACKSON G, MATTEN 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New perspectives on private governance [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2, 10(1):3-28.
[30]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 1968, 162(3859):1243-1248.
[31] 衣长军.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创新[J]. 经济纵横, 2008(1):121-123.
(责任编辑:司国安)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FDI in Oth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ies
HU Desheng, OU Jun
(School of Law,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enterprises ne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rising from thei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ter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required to consider the sources of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s and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dispute settlement. Chinese enterprises face the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s from four dimensions which are domestic, host countries (regions), international and some other informal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s.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may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For pre-judging thei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on the base of just and reasonable settlement of environmental disputes, clarify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dentify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review the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and determine the doctrine of liability fix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multipl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2016-02-1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4JZD02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XJTU-SK2014049)
胡德胜(1965- ),男,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X-019
A
1008-245X(2016)04-004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