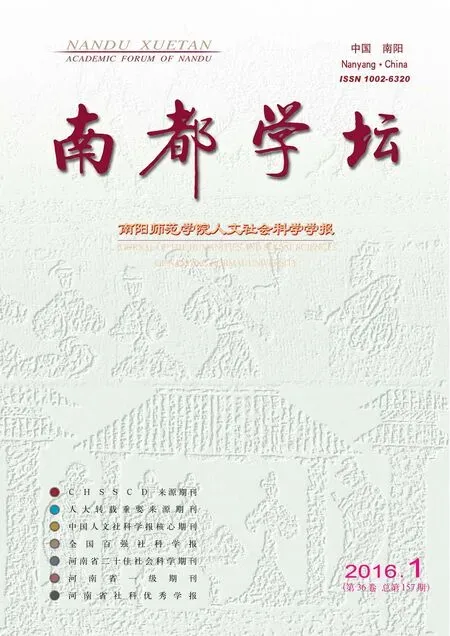秦汉时期南阳的商业气息
戚 裴 诺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秦汉时期南阳的商业气息
戚 裴 诺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秦汉时期,各主要城市精心规划,原本服务于军事和政治目的的城市,也大多在此时增添了工商业性质。南阳随着陆路与水路设施的修筑,交通通达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其地位已名列于长安和洛阳之后,跻身成为第三大商业都会。商贾大族的聚群而居促进了南阳城市商业发展。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南阳保持住数百年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
关键词:秦汉; 南阳;工商业; 城市; 贸易; 交通
关于中国古代城乡商业发展情况的记载,历来是史家着重笔墨的地方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促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1]3261的记载。而之后的班固,又转述了箕子向周武王建议重视八政的问题,其一与二便是食与货[2]1117,即我们现今提到的商业贸易。秦汉时期,南阳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从相关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战国中后期以来,当地便开始设置郡县①参见《史记》卷5《秦本纪》:“百里奚亡秦走宛。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封公子市于宛。”又见《水经注》卷31《淯水注》:“淯水又南迳宛城东。其城,故申伯之都,文王灭申以为县也。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称宛。”。同时,拥有众多矿产的自然环境又使得南阳奠定以冶铁业为主的商业模式,其锋利的兵器被世人称赞为“宛钜铁,惨如蜂虿”[3]281。秦至两汉,“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的迁移活动,又为当地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百姓多“好商贾渔猎”[2]1654的现象,并最终形成了“宛、周、齐、鲁,商遍天下”[4]281的评价。因此,本文试图从古代城市发展方式的角度出发,以有着“三京”之称的南阳为叙述对象,就其秦汉时期的商业气息进行梳理,并分析它在各个阶段能够得到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一都盛会:京畿以外的中心城市
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在相关著作中就指出:“在都市中,有一定的区域,是店铺开张的场所。”[5]47在他看来,汉代城市既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标志[6]2。因而,能够成为京畿之外的“都会”,其商业发展的背后应该有城市兴建之功劳。
论及城市的兴起,其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一为王公贵族的居住地,一为货物交换的中转站,抑或还有军事堡垒等原因[7]55。至先秦秦汉之交,城市内包含的部门逐渐增多。杨宽先生就提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城’和‘郭’中常设有‘市’”[8]119。由此得知,“市”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史念海先生曾经谈到,“都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条件”[9]192。考察南阳周边的环境,其“在南山之南, 汉水以北”[10]154,城北背靠紫山,东有汤穀水,又出产“铜锡铅锴”[11]等物产,可谓有着很好的经济地理条件。关于其在汉初的情况,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1] 359特别是金属矿藏,使得当地成了重要的冶炼基地[12]77。对此《史记》就曾描绘并评价到,“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遫,卒如熛风”[1]1164。参看有关南阳地区冶铁遗址的发掘报告①另可见如下考古发掘报告: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南阳汉代铁工厂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镇平县文化馆:《河南镇平出土的汉代窖藏铁范和铁器》,《考古》1982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冶金史研究室:《河南省五县古代铁矿冶遗址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瓦房庄汉代制陶、铸铜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鲁山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一号炉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我们可以发现,其冶炼技艺程度水平较高,拥有纯冶炼、纯铸造、冶铸结合等各个层次的制作场所[12]6,10。黄今言先生就曾谈论相关工艺说:“冶铁业对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有较高的要求,非一般的个体手工业者所能比。故当时这些大冶铁主的生产,具有相当规模。”[13]39特别是西汉中后期中央政府设置了工官制度,南阳郡中的宛县“有工官、铁官”,使得当地生产的铁质器具遍布全国各地。如西汉未央宫内的第三号遗址中就出现过题为“南阳工官”弩机,汉简中可见“盾一完,元康三年,南阳工官造”[14]35,瓦房庄作坊遗址出土了“阳一”的和铁犁等制品。此外,铁器的供应与背后赋税的征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维系王朝运转的命脉。在平叛羌、两粤以及西南诸地叛乱后,中央政权更是依靠“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2]1174,保证了地方安定团结。而“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2]1174的行为,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由此可知,铁的发现和冶炼铁器活动的开展,不仅扩大了南阳在汉代的社会影响力,还成为西汉政府赋税来源的一个渠道,也是其充满商业气息的原因之一。
据《新书》记载,汉初朝廷“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 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15]113。但到了汉文帝时期,朝廷解除了相关禁令,允许“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4]57行为的出现,并产生了“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2]1155的情况。管制的放开为商人逐利提供了便利条件,秦代被迁移至南阳的孔氏家族,继承祖辈才能,“大鼓铸,规陂池”,周游诸侯间,得到“通商贾之利”的效果。孔氏的行事风范,被评价为“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1]3278,受到南阳商人的效仿。而“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汉、江、淮”[1]3269的地理位置,成了沟通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纽带,且反映了当时经济城市(古代都会)应有便利交通条件的事实。对此,司马迁称:“宛亦一都会也。”[1]3269
自战国秦汉以来,南阳始终保持着商业气息氛围。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会稽典录》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将军也。本是楚宛三户人,佯狂倜傥负俗。”[1]1741虽然其辅佐勾践平吴之后,选择“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的陶地定居,获得了“致赀累巨万”[1]1752的收益,但仍可见得宛地之人具有的经商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此外,还有身为南阳堵阳人的张释之,曾“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2]2307。从中不难得知商业的发展为南阳人步入官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值得提及的是,新莽时期南阳地位得到明显上升,其与长安、洛阳等共六地,共同设立五均官,称之为“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2]1181。
对此,周长山先生认为:“王莽将这些大城市作为商业统治的中心据点,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它们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牵引带动作用。”[16]81而丁海斌先生则更加提升了“五均司市”的社会地位,称“它们主要是表现为商业功能的经济陪都”[17]91。至此,宛(今南阳)是“五都”之一的称号正式明确下来。若从诏书颁布的时段来考虑,政策实行的目的可能与“使朝廷直接控制交通运输及市价,俾物价稳定,增加国库收入”[18]201有关,进而“齐众庶,抑并兼”和收取赋税维持对内战争,“显示了对由封建国家控制垄断性生产事业的必要性的认识”[19]118。另外,从王莽选择这几个城市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在另一方面佐证了当地经济的发达程度。
二、通衢大道:紫山汤穀水旁的往来枢纽
关于古代中国的都会特征,其关键点是交通便利与商贸发达。《盐铁论》评价京城之外的都会大多是“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4]29。所谓“衢”,《说文解字》解释为“四达谓之衢”[20]44。参考当地交通脉络,《荆州记》称之为“从襄江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通周、郑、晋、卫之道”。《史记》载秦王政元年(前246),“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1]223。当中的“越宛有郢”,就是跨越宛城,而攻克楚国郢都。司马迁重点强调取郢过程,不仅仅是意在灭楚国旧都后,就掌握兼并战争的主动权,还可知宛应是前往郢都的一条重要通道。至西汉中期,人们回忆战国时大都市面貌时,也还有如下描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冲,跨街衢之路也。”[4]41可见,交通便利对于大都市发展的重要程度。
事实上,南阳除了“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11]154外,更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重新规划的道路,促成当地通达条件的明显提升。《汉书·贾山传》云:“(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2]2328而“南阳西出武关”的记载,不仅佐证了出自商洛县的武关道,经南阳,并过新野、襄阳,最终抵达江陵的路线走向,还被顾炎武的《读史方舆纪要》所述为“南阳为南北腰臂”[21]2400,又被评价为“蜿蜒横亘为秦楚往来通衢”[22]。特别是武关道的走向,使得“来往于南阳和中原间一般都要通过这个隘道”[23]25。而参考南阳的地理位置,则可以知晓“由此以东,便进入广阔的政治、经济重心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人们经由此道,与富庶的南阳盆地取得密切联系,它一直是南阳和中原间最重要的一条通道”[23]25。
秦汉时期南阳作为区域经济贸易中心,其经济都会的性质与周边城市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并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到先锋作用。范文澜先生评价说:“随着秦汉时期对吴、越、南越的继续开发,宛市商业愈趋繁盛,成为南北交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24]83-84这种现象表明,秦汉时期以南阳为代表的区域城市,伴随着道路和南部边疆的开发,其经济功能得到明显强化,成为往来要道。
三、朝廷重镇:别都旧乡里的经济与生活
从上可知,南阳起初是一个以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为主的中心城市。但到西汉末期,其政治地位明显上升。据统计,此时的南阳境内下辖诸侯国数量从平均4个,增加到10个,一跃成为拥有诸侯国最多的地区[25]101、116。至东汉时期,鉴于南阳为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和故乡,皇室“以南阳为别都,为之南都”[26]134,并修建刘秀父亲的章陵。时人谈及南阳,则有“昔我南都,维帝旧乡,同于郡国,殊于表章”[27]334的评价。至此,南阳与洛阳、长安一道被冠以“三京”的称号,为经济重镇的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保障。而由于政治陪都地位的确立,使得中央朝廷在选拔官吏上,特别重视将贤能之人派往帝乡。建武七年(31年),杜诗任南阳太守。职守的7年间,他“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28]1094。最终,南阳被称作“郡内比室殷足”。而大约到东汉永平、建初年间,南阳因为有着良好的水利设施,出现了全国“时岁多荒灾,唯南阳丰穰”[28]1023的情况。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良好自然环境和现实政治的影响下,使用当地物产进行馈赠的情况也是频繁出现,如《后汉书·羊续传》就有“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28]1110的记载。参看这一阶段的汉画像石,时常可见宴会期间,佣人将硕大河鱼抬入厅堂的场景。南阳汉画像中的车骑出行、宴饮歌舞的场景,也可以看出皇亲国戚和富商大贾的奢华生活[11]156。与此同时,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与之有关的游艺活动发展,如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祠章陵,又祠旧宅,作雅乐,奏《鹿鸣》”[28]113,被后人称之为“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11]1344。
此外,王子今先生曾指出,“帝王赐吏人、复田租等行为, 客观上也有益于当地经济”[29]12。可见,皇室祖居地的背景使得商人和官府将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南都的建设中,发展了当地经济,并为南阳在东汉近200年持续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四、富商大贾:聚群而居下的商业发展
前文提到,孔氏家族在南阳维持了百年之久的冶铁业,并凭借着富甲一方而跻身于丞相之列。伴随着“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2]1133的事实,秦汉四百余年间,还有许多生活在当地的豪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宁成在年少之际就有“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的抱负。虽然其后曾因治民“如狼牧羊”被治罪,但回乡后却积极进取,致力于田间生产,并“贳贷陂田千余顷,假贫民”[2]3653。没过几年,就获得了“家产达到数千万, 出骑从数十”的收益。汉昭帝时,南阳人杜延年因为为人和善,善于处理各项政务,并长期主管朝政而深得皇帝赏识,位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赀数千万”[2]2665。
东汉年间,樊宏和阴识两大家族相继成为名震一方的大贾。《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樊宏)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家业传承到他的儿子时,“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而阴识的儿子阴方,则是“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28]1130。此外,像李通、邓晨等人,要么“世以货殖著姓”[28]573,要么“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28]573,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对南阳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
基于这些事例,我们还应该看到,大族的聚群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百姓的正常耕作,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和商业往来。并且,他们通过亲族关系和对乡里的恩惠来笼络人心。如南阳宛人朱晖,在“建初中,南阳大饥”[28]1459时,便散尽家财,帮助境况困难和身体羸弱的乡亲,使得“乡族皆归焉”[28]1459。另据统计,西汉晚期、东汉中期和东汉三国之交,南阳郡内的人口数分别为“户三十五万六千三百一十六”[2]1593,“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28]3476,“户口尚数十百万”[28]2439。相比全国其他地区,聚群而居的富商大贾,对子嗣的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得当地户口数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4]121-122。
五、结论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南阳作为一个地处中原和江南地区相交会的城市,由于其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交通区位而得以兴起,冶铁场所、物资交换地点等遍布境内,充满了商业气息,被司马迁称之为“一都会也”。而除了这些天然优势之外,它的“帝乡”身份,是使得南阳在秦汉长达400余年的时间中持续繁荣的另一项关键因素。作为“南都”,它获得统治者长期关注,并将大量的人、财、物投入到当地建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同时,当地经济的发展又反作用于政治与社会领域,培养出新一代的官僚和富贾,如此周而复始。
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东汉末年群雄间的互相争斗,使得当地的经济遭受致命打击,而作为开国皇帝刘秀故乡所享有的特殊政策倾斜也灰飞烟灭,也不能再现往日浓郁的商业气息和身为龙兴之地的繁华景象。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王利器,校注.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陶希圣.西汉经济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6]彭卫.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秦汉城市史研究[C]//(日)中村圭尔,辛德勇.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J].教学与研究,1962(2).
[8]杨宽.战国史(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9]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萧统,编.李善,注.昭明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李京华,陈长山.南阳汉代冶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3]黄今言.秦汉商品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4]林梅村,李均铭.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5]贾谊,著.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6]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7]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8]沈展如.新莽全史[M].台北:正中书局,1977.
[19]孟祥才.王莽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20]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1]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2]邱铭勋.屈原岗碑文[Z].现存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回车镇.
[23]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J].史学月刊,1964(10).
[24]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5]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6]王应麟,撰.张保见,校注.通鉴地理通释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27]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9]王子今.南阳:东汉文化地图上的“朱光”“飞荣”之都[J].文史知识,2008(5).
[责任编辑:刘太祥]
The Business Atmosphere of Nanyang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QI Pei-nuo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major cities were well planned, and the cities which served fo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urposes also increased the nature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at this time. Alo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and water facilities, traffic access conditions of Nanyang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it became the third metropolitan, second to Chang’an and Luoyang. The merchants’ cluster promoted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Nanyang had kept its trade center status for hundreds of years because of the various effects.
Key words:Qin and Han Dynasties; Nanya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cities; trade; transportation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6)01-0011-04
作者简介:戚裴诺(1991—),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秦汉史。
收稿日期:2015-10-26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