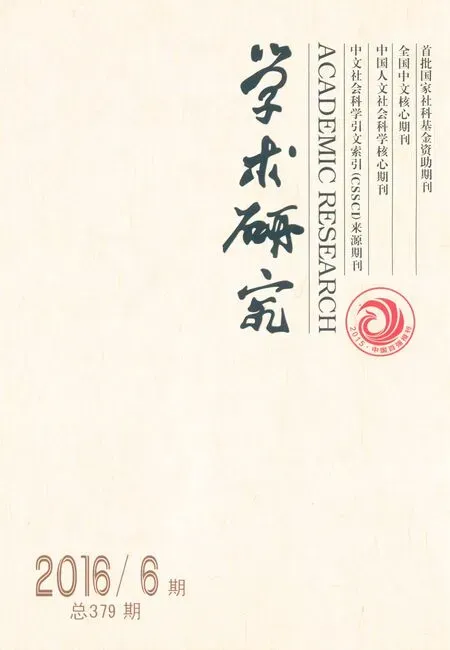当代西方文论神话的终结
——强制阐释论的意义、理论逻辑及引发的思考
李小贝
当代西方文论神话的终结
——强制阐释论的意义、理论逻辑及引发的思考
李小贝
[摘要]强制阐释论自提出之后,就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得到广泛关注。它在准确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病症与缺陷的同时,也建构了自身作为批评武器的理论体系;它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与批判,表现出了鲜明的价值立场与时代精神,不仅给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创造出的神话画上了句号,而且也从更深的层次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开启了思路。强制阐释论留给我们的,既有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指导与启示,同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价值诉求也有很强的启迪与警示作用。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当代西方文论神话终结
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及其引发的学术探讨,已成为文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对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在我国新时期之后的引介情况进行反思或研究的文章,新世纪以来在文艺理论界也常能看到、听到,“失语症”、“中国化”、“本土化”、“转型”、“中体西用”、“对话”、“理论自信”、“文化复兴”等词汇也可见于一些文章中,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及其系列文章之所以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其原因是非常值得认真探究的。
一、应时而生的强制阐释论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刚刚走出极“左”文艺束缚的国内文论界掀起了引入和接受西方文论的学术热潮,形式主义、新批评、叙事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各种文论思潮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然而,与西方文论的引介与研究热潮不相称的是,我国古代文论传统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却或被忽略,或被遗忘,处于哑然失语状态,原本属于它们的理论领地被西方文论纷纷占去,它们在被颠覆、被抛弃中慢慢由中心移向了边缘,最终促成了西方文论独大的局面,西方文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创造和演绎着一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传奇神话。
这个神话首先表现在对西方文论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上。新时期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发展史上有名的“方法论年”(1985年)和“观念年”(1986年)之后,秉持着先拿来再消化的思想,国内学界开始大量译介西方文艺论著。至上世纪末,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艺理论思想几乎全部在中国登陆,各家各派的代表性学术著述基本也都能在国内找到相关的中文译作。仅以1985至1990年间为例,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像A·杰弗逊、D·罗比等人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卡西尔的《人论》、《语言与神话》,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图腾与禁忌》,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杰姆逊的讲演本《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原理引论》,托多洛夫的《批评的批评》,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佛克马、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等等,这些著作就都译介了进来。而由国内学者编选的各种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等方面的相关译丛也是随处可见,那些研究西方文论的专著,系统梳理西方文论发展史的编著等,更是不胜枚举。其次表现在学术影响上。在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界,西方文论已经完全构筑起了它的话语霸权,形成了它的独特优势。今天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选择西方文论似乎就比研究传统文论要高级很多;高校课堂建设,外国文学、西方文论所占的比重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此外,在课题申报、学术研究等方面,西方文论明显更是学者们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正是在这种对西方文论顶礼膜拜的势头之下,我国学术界不仅在不长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现当代文论发展的百年历程,而且在思维方式、话语习惯、研究结论等方面已明显地呈现出西化特点。最后,反映在阐释能力上。由于对西方文论的过分推崇,加之自认为对西方文论的深入研究与特别熟悉,不管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现当代文学作品抑或是网络小说,不管是作品内容、表达方式还是人物形象,许多学者都习惯于随手拿来西方文论的术语概念,对这些作品进行批评分析、比较阐释,从而创造了西方文论阐释一切、解释一切、无所不能的神话。正像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弗兰克·兰特里夏所说:“只要你告诉我你的理论是什么,我便可以提前告诉你关于任何文学作品你会说些什么,尤其是那些你还没读过的作品。”[1]如此看来,西方文论真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说是神话恐怕一点也不为过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江发表了强制阐释论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围绕强制阐释论这一中心思想,直击当代西方文论的弊端和要害,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共鸣。有学者认为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是中国文学理论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具有逆转意义的重要理论事件”,[2]还有学者提出要将强制阐释论问世的2014年称为文艺理论界的“张江年”,[3]强制阐释论的影响由此可窥见一斑。强制阐释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当代西方文论的深刻辨析与检省,对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反思与批判,更在于其系统完整的理论话语背后所透露出来的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时代意义以及对中国文论健康发展的警示作用。强制阐释论必将从更深的层次为中国文论的发展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二、强制阐释论的理论逻辑
通过强制阐释论系列论文,张江不仅准确概括了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强制阐释病症,而且还详细论述了当代西方文论各学说的自相矛盾与违逆逻辑之处,批判了它们以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为主要特征的文本阐释方式,可以说是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使强制阐释论的整个理论体系呈现出严密的逻辑理路。
首先,用强制阐释来诊断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病症,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正如张江在文中所说,一百多年来,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些重要思潮和流派、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以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造就和推出无数优秀成果,为当代文论的发展注入了恒久的动力”,但同时,“一些基础性、本质性的问题,给当代文论的有效性带来了致命的伤害”。[4]特别是一些学者对于当代西方文论并没有很好地咀嚼和消化,就轻易地拿来进行文学批评和理论阐发,更进一步放大了它的本体性缺陷。但是对于这一缺陷,长期以来学者们似乎并没有给予准确的理论概括。意大利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安贝托·艾科曾于1990年提出过“过度阐释”的概念,对文学阐释的可能性、有限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力图把文学批评从范围过大过宽的无边界状态拉回到作者和文本规定的限度之内;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曾提出“妄事糅合”的说法,认为“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5]这种做法势必会使理论批评流于附会,而很难获得健康的发展。但是艾科的“过度阐释”只概括出了西方文论诸多缺陷的一个方面,并不完整全面;而我国学者提出的“妄事糅合”只是现象性描述,并非理论性概括,因此也并没有产生过多的理论效应。相比较而言,强制阐释论则观点明确,界判分明,既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又充满理论自信,其之所以受到学界的重视,与这一概念的这些特征不无关系。
在《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一文中,张江指出强制阐释“这一特征既存在于西方文论自身,也存在于后人具体运用的批评实践过程中”,[6]这就意味着它具有至少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西方文论自身具有强制阐释的特征。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西方文论中很多学说与流派不是产生于文学作品批评实践之中,而是运用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阐释文本、解释经验,进而推广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学规则。这种脱离了文学生产和实践的文学理论,不仅无法为文学作品提供正确的审美标准,而且也不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西方文论自身的强制阐释特征还表现在它的“偏执与极端”及“僵化与教条”[7]上。西方文论的繁荣建立在对以往理论和学说的批判乃至反叛之上,这很容易使一些学说因矫枉过正乃至过分极端而失去合理性,再加上一些学派由于过分推崇科学主义而存在运用固定公式和模板框定文本的弊病,使得文学理论越来越偏离文学本身,而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形式主义的窠臼之中,不能真正有效地指导文学创作与实践。第二个层面,学界在运用西方文论进行批评实践时存在强制阐释的特征。在《强制阐释论》中,张江详细论证了当代西方文论以场外征用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来源的强制性,以主观预设为特征的思维方式的强制性,以非逻辑性证明为特征的批评过程的强制性,以混乱的认识路径为特征的批评结论的强制性。这些由当代西方文论本身所决定的强制性特征,就使那些以西方文论为资源的批评者,在其“选定理论工具→确定批评方法→展开批评过程→生成批评结论”这一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处于“被强制”的状态。例如,用女性主义理论就必然会得出男权对女性的压抑的结论,用精神分析理论主人公就必然会有恋父、恋母情结或在成长时期受到过性压抑的经历,用解构主义理论则必然会得出传统是荒谬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结论。深陷于这些批评方法和观念之中,批评家们有时虽然会为自己得出了出人意料的观点而兴奋,但却茫然不知自己其实身似傀儡,早已被当代西方文论的话语逻辑所限制和框定。
其次,强制阐释论思路清晰,结构缜密,自成体系。强制阐释论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精炼地概括了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这种诊断式的现象性描述,而是深刻挖掘和阐述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在层层深入、条分缕析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完备的强制阐释论批判体系。这个体系既包括了论者对于强制阐释这一定义的科学解释(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也包括了强制阐释的四个具体表现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此外,在每一个特征之下,作者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条理清楚地介绍和分析了诸如原因、后果、表现方式、相似概念的区别等等问题,使强制阐释论成为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下面仅以场外征用这一特征为例,加以举证。
为了让读者明白何为场外,作者首先概括了场外的三种理论来源:第一,与文学理论直接相关的哲学、史学、语言学等传统人文科学理论;第二,构造于现实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之中,为现实运动服务的理论;第三,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规范理论和方法。这三种理论来源不仅能让读者明白何为场外,同时,如果以文学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出,这三种来源呈现出由最靠近中心点向外逐渐拓展的过程,反映了作者由近而远清晰的逻辑思维线索。那么这三种场外的理论来源,是如何由非文学的场外进入到文学的场内呢?作者将之概括为三种表现方式,即挪用、转用、借用,并分别举例介绍了这三种方式的具体表现。经过这样的论证之后,场外征用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接下来也就自然转到了对文学内部的论述。场外理论到底使用了哪些技巧,不留痕迹地进入到文学内部呢?论者又将之概括为四种方式,即话语置换、硬性镶嵌、词语贴附和溯及既往。而在论述这四种方式时,作者不仅详细地概括了每一种表现方式的内涵,还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案例让读者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至此,作者已经非常详细地为我们勾勒出了场外征用各个环节的内容所在。接下来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两个容易让人产生疑惑的问题。一是在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已成为科学发展动力的时代,文学的场外征用是否应该是正当的?二是新的理论一旦形成,能否用这个理论重新认识和改写历史文本?对这两个疑惑的进一步解决是重要的,这就从另一个方面推进了读者对于场外征用内涵的深入领悟和完整理解。由此可见,从概念的提出,到可能会有的疑惑,作者都周全考虑,一一道来,有逻辑有条理,全面而清楚地阐释了场外征用的理论脉络。对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强制阐释论的其他特征,作者也都通过详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相关举例进行阐述证明,令人信服。
在论证相关问题时,作者并不迷恋于论证说理,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文学案例用事实说话,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如在论述场外征用时,就列举了一些批评者用生态批评理论解读《厄舍老屋的倒塌》的案例,在论述主观预设时,则列举了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站在女性主义的前置立场对一些作品所进行的预设性解读模式,等等。强制阐释论不仅通过强大的理论论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而且还通过大量典型的文学批评实例来支撑结论,联系实际,事实求是,从而将西方文论的问题与病症很好地呈现给了读者,给当代西方文论在中国创造出的神话画上了句号,催人梦醒,引人深思。
三、强制阐释论所引发的理论思考
强制阐释论指出了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以及在中国的滥用情况,让我们对今后如何理性地对待西方文论,如何正确地进行文学批评有了更为科学客观的认识与理解。强制阐释论既有文艺理论或文学批评方面的指导与启示,同时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价值诉求也有很强的启迪与警示作用。
让理论归依实践,是强制阐释论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正如张江所说:“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始终没有解决好文学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些西方文学理论脱离实践,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其他学科理论的直接‘征用',中国文学理论脱离实践则表现为对西方理论的生硬‘套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文学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都处于一种倒置状态。”[8]正是这种倒置状态,使文学理论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最终走向了伤害文学的道路。这些源自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甚至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观点、流派,本无关乎文学,却被作为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式,大量地应用于文学领域。于是,本应作为理论指导的文学理论,并不能真正地指导文学批评,更遑论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不能面对文本,不能给文学以活的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又该以何面目存在?今天诸如“理论终结”、“文学已死”的判断虽让人有着“新亭对泣”的彻骨之痛,但文学理论自身的人云亦云,不够争气,却显然是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当然,学者们并非不够努力,我们去古典文论中寻找动力,从西方文论中寻找资源,向马克思文论中寻找规律,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倡中体西用,提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但我们忘记了这些思想资源只能作为理论成长的孵化器,绝不是理论生成的内驱力。只有回到丰富的社会实践和鲜活的现实生活,只有回到具体的文学作品和紧跟时代的文艺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才真正有可能健康成长。因此,“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面向具体的文学作品,面向具体的批评实践,从千百部作品中分析出特色,从千百次批评中看出规律,“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的归纳上升”,这才是文学理论的正确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
尊重作家、尊重作品,才能使艺术永恒,这是强制阐释论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如张江所说:“从道德论的意义上说,公正的文本阐释,应该符合文本尤其是作者的本来意愿。文本中实有的,我们称之为有,文本中没有的我们称之为没有,这符合道德的要求。对作者更应如此,作者本人无意表达,文本中又没有确切的证据,却把批评家的意志强加于人,应该是违反道德的。”[9]其实,对作者或文学作品进行妄意的批评,不仅是违反道德的行为,更是对艺术本身深层的戕害。虽然我们赞同“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但这个哈姆雷特可以是忧郁的、迷茫的,可以是敏锐的、深刻的,可以是刻薄的、审慎的,甚至可以是具有恋母情结的,但绝不应该是邪恶的,淫乱的。或者就像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旨诠释为肯定“一种同性恋秩序”[10]一样,都只能是在最初的新奇之后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诸如把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的“蜡炬”解读为男性的象征,[11]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视为“爱欲骚动的心理过程”,[12]都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了。而这种“无畏”的后果,并不是对于作品的意义再生产,而是遮蔽了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践踏了艺术的审美价值。长此以往,艺术将成为可以随意任人调笑、戏玩的工具,而当艺术的神圣性被消解之后,它还能否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能否成为“积蓄在苦难和耐劳的人的灵魂中的蜜”(德莱赛),能否带领我们去“探访现实中未知的一座座殿堂,走向一个同过去有着天渊之别的未来”(泰戈尔)?答案肯定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所以,尊重作家、尊重作品、尊重艺术,对神圣的事业保持敬畏,才能让它生生不息。
时刻捍卫自我的主体意识,以及不妄自菲薄的批判精神,是强制阐释论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长时间以来,我们视西方文论如珍宝,弃传统文论如敝帚,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从属者的位置,但强制阐释论提醒我们,在对待中西文论的关系上,我们应时刻明确谁是根本,谁是主体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张江《强制阐释论》的重要价值之一,便在于启发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平等对话的态度对待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既无‘我注六经'式的仰视心理,亦无‘六经注我'式的随意态度。”[13]向西方文论“取经”的过程与经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但在得失成败、向死而在之后,我们必须更加深切、更加透彻地领悟和明白,能使我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魂,还是这个古老的民族土生土长、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基因。近些年来,理论缺乏批判,如果能早一些批判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或许对当代西方文论不足的发现,对其所存在问题的征讨就不会等到现在,我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就不会举步维艰。学术不能没有批判,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强大的外来理论裹挟的时候,更应该有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学术不仅是埋头研究,学者不只是撰文著书,批判本身就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之一。没有批判,社会不能更好地进步,没有批判,学术不能碰撞出有价值的思想。强制阐释论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引起学界的注意,与其强烈的批判精神显然是无法分开的。全球化的到来,颇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但越是这样的时刻,越需要我们保持冷静,不妄自菲薄,保持自我的主体意识,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强制阐释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与批判,打破了长久以来唯我独尊的西方文论神话,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有关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启示,更因其深刻的批判精神而可以扩大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在我国对当代西方思潮与价值的膜拜在这些领域也同样存在。
[参考文献]
[1]Frank Lentricchia,“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an ExLiterary Critic”,in Alxander Star(ed.),Quick Studies: The Best of Lingua Franca,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2,p.31.
[2]高楠:《理论的批判机制与西方理论强制阐释的病源性探视》,《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3]姚文放:《“强制阐释论”的方法论元素》,《文艺争鸣》2015年第2期。
[4][9]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5]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6][8]张江、毛莉:《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第4版。
[7]张江:《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下)》,《文学报》2014年8月14日第22版。
[10]Jonathan Goldberg,“Romeo and Juliet’s Open Rs”,in Joseph A. Porter(ed.),Critical Essays on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New York:G. K. Hall & Co.,1997,p.83.
[11]颜元叔:《颜元叔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226页。
[12]高远东:《〈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
[13]李春青:《“强制阐释”与理论的“有限合理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法敏
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理解·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6-0006-05
作者简介李小贝,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北京,100011)。